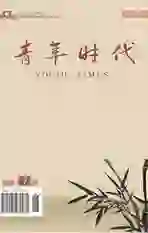史铁生之命运观分析
2018-03-31潘彩琳
潘彩琳
摘 要:史铁生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身残志坚的作家,人到中年身患残疾的飞来横祸使他度过了一段十分痛苦的时期,他对命运有了比常人更为深刻的理解,他在作品中探讨了无常的命运,作品中透露出的积极向上精神对许多人产生了鼓舞振奋的作用,也让很多人对命运有了新的认识。
关键词:命运观;偶然;救赎
一、命运是什么
命运一词带有宿命的意味,每个人或许都曾经思考过自己的命运,尤其当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在自己身上却又无从解释的时候,对命运的追问和思考就更加强烈。在佛教中,宿命观念与它的“业报”“轮回”思想相关。佛教认为,个体命运受人的道德行为影响,这种影响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业”前定,指一个人今生的作为会影响到他的来世,另一种是现世报应。这样看来,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握,但是仅限于下世。从这个角度看,人其实无法掌握自己现世的命运,这就给命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既然人无法掌握现世命运,那么该以何种方式去面对呢?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在绝望中灭亡,还是坦然面对积极抗争在振作中爆发?史铁生显然选择了后者。
每个人最终都逃不开对死亡的焦虑,但是对于命运的焦虑却是相对的。一个生活美满幸福的人或许很少思考命运,而一个历经磨难举步维艰的人对命运的焦虑感会十分强烈。这种思考有可能使人沉沦于宿命的无奈,但也可能增加一个人的生命厚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苦难是有价值的,绝望是有意义的。史铁生在生命的前20年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学习成绩好,在美术方面也很有天分,还是一个运动健将,在中学时期,曾经代表班级夺取过校运会初中男子80米跨栏第一名。可是谁能料到,在他21岁的时候,命运无情地夺走了他对未来的憧憬,让他患上一种叫做“蛛网膜脊髓炎”的病症,彻底剥夺了他行走的权利。对于史铁生而言,双腿的残疾,比死亡更加残酷更加无法接受。残疾所带来的痛苦不止是肉体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残疾后,他在街头被一群地痞流氓殴打却只能忍着,为找工作谋生,他的母亲带着他多次跑知青办然后被拒绝,21岁正是恋爱的年龄,爱情和残疾几乎一同到来,但在他们恋爱的消息曝光后,姑娘的慌乱和姑娘父母焦虑的眼神深深刺痛了史铁生的心。
被命运抛入绝望的深渊,他像一头困兽,仰天长啸命运的无常与不公,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结局:“一个失去差异的世界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也没有肥力的荒漠。差异是永远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存在的本身需要它”,但是他不明白,纵然苦难是必然存在只能接受的,那为什么是他?由谁来决定哪些人去承受那些苦难和体验这世间的幸福?找不到外在的逻辑原因,他把目光转向了命运,“只能听任偶然,命运是无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史铁生认为人受苦是必然的,至于谁受苦则是偶然的,命运就是由一系列偶然组成,既然是偶然就无逻辑可言,甚至显得有些荒唐,人们要做的不是去证明必然性的可信,而是去相信命运的偶然性然后接受它。
二、命运充满荒谬与偶然
他的中篇小说《原罪·宿命》以两则故事进一步阐述命运的荒谬与偶然。“原罪”中的“十叔”心智健全,但一出生就重度残疾,从脖子、胸、腰一直到脚全都动不了。不幸总是存在,只是它们的程度有所差别。十叔有什么错误吗?他没有,但是他一出生就被判处终身残疾,被限制在床上,注定和世界的一切美好风景无缘,谁也找不到十叔被判罪的原因。他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却要承受着生命无端加给他的苦难,毫无公平可言,如果非要给他的残疾找个理由,那只能把它归罪于命运了。命运是神秘莫测的,谁也无法预言它下一秒会对你做什么,它想让谁受苦谁就得受苦,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既然谁受苦是由命运随机选定无法改变,那么当被它选定时,人就只好承认这必然性,逃不过躲不掉,受苦就是必然的。在这篇小说中,史铁生表明了自己对苦难的态度,人的先天不幸,只能归结于原罪。“原罪”是基督教的一个教义,是解释人苦难的基本学说。原罪,基督教最基本的解释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由于受了蛇的引诱而偷吃禁果,违反了上帝的意志,犯了罪。人类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人一出生就继承了祖辈的原罪。在他看来,十叔是因为原罪而被命运选中,要用今生的苦难来救赎,这样看来,十叔的先天不幸似乎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史铁生借用了基督教“原罪”之说,但他并不认为,人是因原罪而遭受苦难的。他所表达的“原罪”与宗教原义无关。他所谓的原罪,旨在强调人受苦的必然,但这必然超出了因果逻辑性,超出了人的理性认知而无法找到自己受苦的原因,所以人要做的就是承认这必然性,这样好像有些不可知论的意味,但这世间有太多科学逻辑理性无法解释的事情,人的认识毕竟有限,也受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所以这暂时由理性无法认识的受苦必然性是存在的。在“宿命”篇中,史铁生同样借用了带有宗教意味的“宿命”一词作为篇名,但他不从宗教的神秘性中求解,而是用一种理性推演呈现了命运客观可見的轨迹与线索,从而证明了命运荒谬的本质。一个前途光明的青年,因为骑车时在路上轧到一个掉落的茄子被弹到路中间,又恰好与一辆刚经过的汽车相遇,结果被撞成残疾,人的一生在这短短几秒中被改变。推算这事情发生的时间序列,最后的原因竟是青年准备下班时,班上一个看上去智力有问题的学生突然神秘地窃笑不停,于是他花了些时间训斥学生,所以比往常晚些回家。如果他与往常一样按时回家,或许就不会碰见那辆车,就不会被撞成残疾。而多年后,当年的学那个生来看他并告诉他,那笑只是因为一只狗看着学校的标语牌放了一个很响的闷屁,这样推算来,导致他残疾的罪魁祸首竟然是“狗的一个闷屁”,这样的结局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命运是如此的荒谬,在它面前,人根本得不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
在《原罪·宿命》中,无论是先天的不幸,还是后天的苦难,史铁生都意在强调人苦难的偶然性。命运其实就是由一系列的偶然组成的,他强调人受苦的必然性,并且坚信世间一切生灵身上都包含着这不可讨价还价的必然性,存在即合理,去纠结必然性的存在于拯救受苦无益,反而还会使人陷入宿命论的无尽悲观之中,所以他觉得人们要承认并接受受苦的必然性然后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而不是终日苦苦追问一个理由然后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受难者只有看清这一点,然后找到一个信仰,一个值得为之苟活的理由,受苦的躯壳才不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余生才能更加从容,这样就完成了苦难的救赎。
三、对命运的超越
既然命运是偶然的且无公道可言,那么一切不幸者的救赎之路在哪里?生而不幸,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唯有一死,这场不幸方能结束,史铁生曾绝望地想过,既然灵魂失去了尊严,就无需继续在人的躯壳里滞留。但他最终活了下来,因为他找到了救赎之路——欲望,他认为是欲望指明了救赎之路。他在《我与地坛》中写道:“人的真正名字叫做欲望。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这欲望有一个怎样的人间姓名,大可忽略不计”,他说的这个欲望可以等同于信仰,对于十叔而言,相信自己的残疾可以治好然后享受正常人该有的权利是一种生的欲望,也是信仰;对老瞎子和小瞎子而言,相信弹断足量的琴弦就能复明然后把世界的风景一览而尽是欲望,也是信仰。于是便可以这样说,只要这欲望能让他们有活下去的勇气,那么它的名字究竟叫信仰还是其他都无所谓。
史铁生在中篇小说《原罪·宿命》里写道:“一个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了。”这是小说中十叔的原话,他一生下来就全身瘫痪但心智成熟,靠着心中的神话,准确来说是信仰,渴望活下去,相信能痊愈,然后感受世间的美好。而他的父亲也是靠着同一个信仰,放弃续弦,十几年如一日靠着磨豆腐买豆浆,把所有积蓄拿去给他求医问药。这个信仰就是——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药能治好十叔的病,因为这个信仰,十叔的苦难人生得到减轻,即使生活艰难,他们依然心存希望,在苦难中完成对自我的救赎。《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一生相信只要弹断一千根琴弦就能抓到药治好自己的眼睛,那藏在琴槽里的药方就是他的信仰。在知道真相后他终于明白,虽然那张药方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但是它支撑起老瞎子活着的全部信念,所以后来他把这个美丽的谎言延续到小瞎子身上,给了小瞎子一个活着的信仰,他告诉小瞎子,“目的虽是虚设的,但非得有不行”。故事就在信仰与救赎这一主线下展开,不论是十叔还是老瞎子,他们的不幸都是偶然且不可抗拒的,他们接受了这必然性,并且找到了活着的理由,他们的欲望让陷入苦难泥潭中的自己有了想要“苟延残喘”的希望,所以他们坚信那个信念,坚定不移,抑或可以叫做信仰,在信仰的指引下,他们开始为苦难的人生奋斗,忘却苦难,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信仰而活,在信仰的指引下,受难者从宿命论的泥潭中走出来,没有成为悲观主义者,这样就完成了对苦难的自我救赎。
史铁生相信命运是由一系列偶然组成的,正是这些偶然造成人受苦的必然,但這必然性超出了人所认知的因果逻辑和理性推理,所以人不必去证明这个必然性,它就存在那里,人只有去接受和相信这个必然性才能在苦难在找到存在的意义和合理性从而获得救赎。
参考文献:
[1]顾林.信仰与救赎—史铁生思想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
[2]张丽芝.生存危机和信仰崛起后的抉择[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
[3]戚国华.论史铁生对生命之路的探寻[J].东方论坛,2012(2).
[4]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