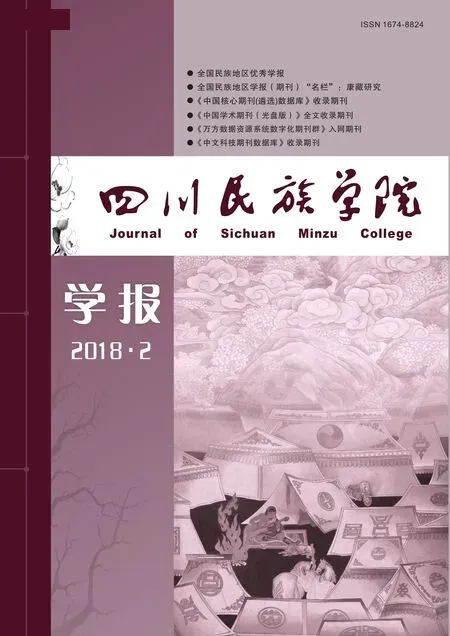三十年来清代瞻对事件研究综述
2018-03-31马越
马 越
瞻对问题是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的一大问题,贯穿了清代始末,瞻对(四川省新龙县)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部,历史上记载这里世代为藏族所居住,“户皆土民”,明代开始在此设置土司。清康熙年间,瞻对土司降伏于清,“缴明代印信,请授为五品安抚使之职,换给印信,仍令管辖瞻对”[1]。虽主动归降,但在整个清代,瞻对这一弹丸之地却掀起了很多风波,促使清先后八次用兵瞻对。清代瞻对土司常常骚扰周边土司,影响川藏交通。至同治初年,清廷调兵征讨,藏军奋勇夺取瞻对。同治四年,瞻对归属西藏地方,之后川藏两地以瞻对归属问题引起纷争,至宣统三年,改土归流,瞻对事件得以平息。
瞻对作为清代的边疆问题,围绕它而形成的八次战争不容小觑,瞻对事件贯穿清朝始末,对瞻对事件进行梳理,也有利于对清代整个历史的了解,以小见大,窥探清代处理民族和边疆问题的方法和态度,同时对英国侵略我国的史实进行谴责。基于前人对瞻对事件的研究,本文将对清代前中期及清末期瞻对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整理,归纳前人在瞻对事件研究中延伸出来的相关问题,如历史人物形象的评价、同一历史时期的事件相关性,如金川之役和瞻对问题的关联性的认识及研究瞻对问题的现实意义等。同时本文将前人的文章加以整合,找出其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方面或观点偏颇之处,以期对忽略的细节问题进行研究。
一、有关清前中期瞻对事件的研究
总结清前中期的瞻对事件缘由,学者对“夹坝”多有着墨,“夹坝”在藏语中为掠夺者,瞻对地区“夹坝”尤为猛悍,多劫掠西藏往来的商人、使者、清廷官兵。“夹坝”这一行为,促使了清廷对瞻对用兵。本文归纳清前中期的瞻对问题将着重于论述学者对“夹坝”的解读,从概念认识着手,了解历史主客观性,也能使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或有无偏颇加以思考。
陈一石曾从民族习性,生活方式,社会风尚,以及瞻对的地理位置等方面分析清瞻对问题存在的原因,他在《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一文中提出,瞻民强悍,精通战术,能武善战,同时瞻对地理环境复杂,实属易守难攻之地,这都是客观所在。喇嘛教对瞻对影响较小,在藏区政教合一的背景下,缺少制约。再其次,瞻对地处雅砻江,扼川藏大道之咽喉,战略地位显要。除此之外,瞻对土司也是一个问题,土司之乱主宰了八次瞻对事件的大多数,五次用兵都旨在镇压土司和遏制土司扩张。“窃惟三瞻之地,南接里塘,为入藏通衢;北界德格土司,为茶商入藏北路,”*鹿传霖.奏统筹川藏全局增移镇道并瞻对等处改流疏。之后出现的驻瞻藏官残暴,瞻对归属等原因引燃的动乱,也或多或少是因为自然疆界与政治历史错综复杂的关系。
同时,陈一石认为,“夹坝”是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是一种正常现象,属于川藏地区的社会风尚。“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获得财富已成为他们的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2]他认为,清廷错误的民族认识,使得决策错误,将事件升级至对整个瞻对地区的敌视。而瞻对地区民众,出于维护自身生存,不得不战。从“夹坝”这一问题,透露出清廷狭隘的大汉族思想和错误的“绳以汉法”的民族政策。
石硕举例历史上“逐鹿中原”和“问鼎中原”等事件,来论证瞻对“夹坝”的合理性。他认为,基于瞻对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遗风尚存,自然资源匮乏,劫掠川藏大道的外来资源,是部落习惯行为,并无挑衅之意。“冷兵器时代,人类历史上数千年的战争冲突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争夺资源。”[3]
刘源《乾隆时期的瞻对事件》中提及,前期的瞻对事件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瞻对动乱,影响清王朝的统治。经济上,川藏大道上,“夹坝”扰乱内地与边疆的物资输送、政令传达。其次他还提出了,乾隆皇帝的态度影响瞻对事件的走向,“乾隆皇帝迟疑的态度影响了开战后清军将弁,由此产生了轻敌思想,导致前期战争进展不顺。”[4]除此之外,部队松散,将领好大喜功、谎报战绩,也导致清廷对战局的预测偏差。刘源认为,瞻对“夹坝”,多为瞻对土司施放,指使之下进行的掠夺。清廷屡加劝诫,但土司依旧不守约束,变本加厉抢劫政府物资,公然挑衅朝廷权威,威胁川藏大道的安全。除此以外,他认为,“夹坝”在清统治者眼中原本不是大事,却因“夹坝”一再扰乱地方秩序,无奈出兵。仅仅作为对瞻对土司的一种震慑,然而因为这种迟疑不够果决的态度,使得清军队指挥不稳,战果不佳。根据刘源的文章来看,瞻对“夹坝”无疑是一场蓄意的恶性事件,而清的出兵镇压则深明大义。
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黄全毅,他认为,瞻对“番性反复”,清廷多次加兵惩戒,都无法遏制这种劣性。黄全毅在《浅析清同治朝瞻对事件》中提及同治之前的瞻对事件的原因,基本同刘源等人无太大出入,认为瞻对所处位置是主要原因,对川藏大道的交通影响,尤其以茶叶贸易和兵饷运输影响最重,“川藏商贾不通,兵饷运转维艰,汉番均有饥馑之虞”[5];瞻对民风也是一客观原因,“瞻对虽降服与清朝,但这里部族林立,民俗尚武,以土司为首,经常相互仇杀”[6]。
在“夹坝”这一问题上,一方面应考虑到瞻对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另一方面也该考虑到历史大环境下清廷作为实际的当局者的责任。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应多重考虑,不能顾此失彼。对于清长久存在的瞻对问题,也有学者着重从清廷的态度上加以考虑,阿来在《瞻对》一书中,指出,瞻对战事不能得以快速解决,除了因为其易守难攻的地理因素,官员的不负责任,含糊了事也是瞻对问题久治不愈的一个病灶。
清中期的瞻对事件,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看来归结为前期工布朗结叛乱未能处理妥当而产生的遗留问题。
陈一石提出,同治初年,工布朗结扩张占领了康区的大部分,骚扰周围土司,同时,“围攻里塘、截断川藏要道,使清廷和西藏地方政权理科陷入困境。”[7],清廷与西藏地方政府无法容忍工布朗结的生事,同治二年,清廷川藏会剿瞻对。同治四年,川藏联军平反瞻对。在文中,陈一石重点提及了瞻对的善后问题,清廷将瞻对赏给西藏,清廷内部“以夷制夷”的方略,将瞻对划藏,但并未注意到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西藏,“未感到边防危机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西藏上层的离心的倾向”[7],清廷的一贯治理民族的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也带来了之后的一系列问题。
黄全毅的《浅析清同治朝瞻对事件》一文中,也同样提到“瞻对土司工布朗结侵扰四邻,川藏交通被阻断,新任驻藏大臣无法入藏。严重威胁了清朝在川藏两地的统治。”[6],除此之外,同治元年的热振活佛事件,使西藏地方官员积极应对平定瞻对事宜。工布朗结威胁西藏地方政府,也逼使西藏地方政府出兵瞻对。政治上的对峙,导致瞻对中断川藏交通,西藏地方物资匮乏,经济困难,更加积极同清廷联军消灭工布朗结。而在平定瞻对后,瞻对归属西藏的原因,则是因为清廷对于军费物资的考虑,“打下瞻对后,清中央政府也无力解决藏军军费,瞻对划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6]
除了上述观点,玉珠措姆提出了“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为19世纪中叶瞻对事件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推动力。”[8]在《瞻对工布朗结在康区的兴起探析》一文中,她指出瞻对拥有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这种部落式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散的体制,使得工布朗结的兴起显得理所当然。“各国学者关注的传统农民起义观点,不能完全解释瞻对事件。瞻对没有诸如宗教怨愤、社会压迫危机或寻求经济公正诉求等思想动力起作用,而这些常常与农民起义有关。只能认为,那个时代,清廷和西藏噶厦政府都忙于处理各自内部的诸多问题,无暇顾及边疆地区发生的社会动荡,这使工布朗结得以顺利实施领土扩张。”[8]
在清中前期相关瞻对问题的研究中,学者除了梳理瞻对问题形成的原因经过和结果,也从新的角度对与瞻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特别是对金川之役与前期瞻对事件的相关性探讨。
金川战役和瞻对事件一直吸引着学者的关注,如上文中提到,看待历史问题,要放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注意其关联性。金川与瞻对相似,弹丸之地,也引得乾隆以举国之力与之进行角力,两地历史的相似度,引得学者对金川战役和瞻对事件的关联进行探究。
王纲在《清代四川史》一书中,引证大量史料,不止将视角放在金川和瞻对,从整个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概括,提出多事之秋的原因有:一、清政府官员处理不当;二、游棍汉奸挑唆;三、土司扩张;四、西藏达赖喇嘛干预地方政务。戴逸在《乾隆皇帝及其时代》一书中,指出瞻对事件是第一次金川战役的“前奏和诱因”[9]。张秋雯进一步挖两者之间的关联,提出乾隆皇帝有“待金川事毕,再征瞻对的打算”[10]。
刘源在《乾隆时期的瞻对事件》一文中,指出乾隆皇帝对瞻对事件态度的迟疑,导致瞻对之事未能得到很好处理,“最终酿成了大小金川战役”[4]。持相同观点的旦正加在《金川战役中清军受挫原因探析》一文中,提出了“夹坝”盛行,影响川藏大道,清政府因此征讨瞻对,但因为对瞻对之战的草率了事,导致清廷的威慑力降低,土司之间斗争愈演愈烈,导致了金川战役。周远廉在《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中,提出“金川之战,与清政府用兵瞻对事紧密相连的,乾隆帝不止一次讲到,对于瞻对首领班滚的处理欠妥,引起了金川之役”[11]。
齐德舜则在《清乾隆攻打川西北大小金川战役研究》中持反对观点,他认为,清政府的“以番制番”及“多封众建”的民族政策的错误,才是关键。认为瞻对事件与金川之战本无任何关联,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庄吉。但他们将宗教因素作为战争的起因,缺乏依据。
学界似乎对于瞻对战役与金川战役之间的关联性无异议,但一直缺乏深入的探讨,特别是一些学者曾注意过藏文史料的利用价值,却一直停留于设想,并无行动。
二、有关晚清时期瞻对事件的研究
黄全毅指出,同治四年的瞻对划归藏属,成为瞻对之乱形式的转折。西藏驻瞻对的藏官和四川当地的矛盾,以及对瞻对民众的压迫,成为了瞻对事件的导火索。直至宣统三年在瞻对改土归流,瞻对事件得以完全解决。
康欣平根据光绪二十二年到光绪二十三年的瞻对归属事件,提出瞻对事件中,清廷“收回”和“赏还”的摇摆不定,以及清廷官员内部关于瞻对及筹边思路的博弈,使得瞻对事件反复无常,停滞不前。除了这些,“清廷在瞻对收回归属四川上有一个前提,即要说服西藏地方政府及达赖。”[12],文中得出结论,光绪年间的瞻对归属问题,实则是清廷在内外双重矛盾下的筹边思路冲突,是历史情势下清廷的有效判断。
陈一石也提及,除了驻瞻藏官对瞻对民众的压迫,导致瞻对人民起义,清廷对瞻对人民的请求不予理睬,也是瞻对起义的重大原因。后期,清廷以鹿传霖为首的官员,对英、俄侵略西藏有一定认识,关心藏事,主张整顿藏务,改土归流。而德格拟议改流事件的节外生枝,扰乱了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英俄帝国主义趁清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产生矛盾之际,加剧侵略。文中,提出了针对瞻对问题不应存在“收回”与“失掉”,对历史研究中的大民族主义言论进行谴责。
张秋雯《清季鹿传霖力主收回瞻对始末》一文,以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为为主线,运用了大量史料,梳理了收回瞻对的原因、导火索、用兵经过,从清廷态度的转变和德格改流的节外生枝分析失败原因,同时也提及了大历史下的藏印条约,论证清廷错失整顿川边良好契机而付出的惨重代价。“以当时川边的乱象及藏官的不法情状,将瞻对收回,应属名正言顺,理智而气壮,亦不至于影响藏印问题的解决与否。但清政府最高决策者始终认为瞻对一事将牵动西藏大局,而瞻前顾后,犹豫踌躇,以至廷议前后数变,白白丧失早日整顿川边的良好契……有罪不罚,一味示好,只徒增其轻蔑之心,更有损国威体制,是毋怪乎川边、藏印问题未获改善……”[13]
朱悦梅在《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中,将瞻对事件放到整个清代格局中考虑,同时提及到了廓尔喀与西藏地方事务的关系,采用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在文中,朱悦梅指出,“一方面,朝廷对川藏问题自始便未能给出原则性方向,一味见机行事,反复不定,有些良机亦被错过;另一方面,前方官员或各自对边疆问题持不同观点,或各怀心思,所提供的奏报无法供朝廷做出一致性判断。”[14]瞻对事件的持续性和后期矛盾的愈发激烈,脱不开清廷保守的决策影响。
关于瞻对事件的持久性,史学界均有“罕见之至”的表达,但仔细分析缘由,也使得人们理解其历史渊源和事件走向,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国内外格局来全面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才能对瞻对独特且重要的地位加以深刻解读,明白其虽是“弹丸之地”,却实在可贵。
石硕在他的《瞻对:小地方 大历史》一文中,提出由点及面的认识方式。他认为,不应该只停留在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待一个历史事件,而应该把握更大的历史脉络和地域范围。文中指出应从三个角度去理解瞻对:一是把瞻对置于整个藏区来看待,二是把瞻对放在整个康区的历史和地域之中,三是从汉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看待瞻对。基于这三点,他从瞻对独特的地域文化、地理环境、边疆关系三方面概述瞻对问题长久存在的原因。瞻对险要的地理环境,又处川藏大道南北两路之要,易守难攻。但因为险要的环境,物资匮乏,相对封闭的环境也使得部落社会遗风尚存。“地最险、人最强”,算是最恰当的概括。由于这些原因,瞻对成为清川藏大道上的“拦路虎”。同时,康区高山峡谷的破碎地形,造成无统一的地方政权进行管理,土司割据,矛盾激烈。石硕这些观点,与陈一石提出的观点基本符合,但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认为,清廷对于瞻对这一弹丸之地,耗时耗力,其实从经济和军事支出来看,都不是件划算的事,但却没有听之任之,除了平反瞻对这一目的,也有着维系康区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工具作用。
三、瞻对事件的研究展望
学者们对清代清廷八次针对瞻对起兵的原因作了详尽的讨论,瞻对事件对川藏地区影响深远,体现出当时藏族地区社会诸多矛盾,在近代历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虽然现如今,新龙县似乎因交通闭塞,地域狭小等因素,淡出人们视线,但近年来史学界对瞻对这一地方的研究并未疏忽,且渐有成果,阿来《瞻对》一书,更是通过历史角度与文学角度,将瞻对推向了更为人们所了解的高度。对于历史事件的探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不断加深而形成新的见解。瞻对“归属”之论辩、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判、历史背景下文化旅游开发等问题的探讨,推动了瞻对事件的研究进程。
回顾前人成果,陈一石的《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一文,梳理了清瞻对多次动乱的历史脉络,对改土归流等问题进行了一定深度的解读。黄全毅,刘源等人,分别对清某一时期的瞻对问题进行剖析,黄全毅的《浅析清同治朝瞻对事件》,着重于土司工布朗结挑起事端,促使清廷对瞻对改土归流。刘源在《乾隆时期代瞻对事件》中,对乾隆朝清廷在处理瞻对事件的态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廷态度对之后对金川战役也有一定影响。除此之外,赵云田的《清末川边改革新探》、徐法言的《乾隆朝金川战役研究评述》等文章,有关瞻对事件也多有涉及,足以看出瞻对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康欣平则从瞻对归属问题入手,在《从“收回”到“赏给”:1896~1897年间清廷处理瞻对归属事件析论》一文中,提出清廷内部在筹边思路上的“博弈”观点。石硕将瞻对历史与当今瞻对旅游开发问题相结合,指出瞻对重要的文化价值与深刻的历史内涵,极富实用价值。
对历史人物应以客观的角度加以看待。对工布朗结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 ,陈一石提出与多数学者不同的看法,他同意工布朗结的土司和大农奴主的身份,对其压榨农奴,兼并侵占周围地区的行径加以认同。但他不仅仅站在一个指责者的角度,他同时指出,工布朗结是有胆有识的首领。他找出《定瞻厅志略·叛逆篇》中提及的“当是时,全瞻之民,全为所用”,加以佐证工布朗结作为土司深得民心,验证其在政治经济宗教上的积极作为。不同于往常学者对历史人物的单向评价,玉珠措姆从多个角度探究了史学界对工布朗结的形象构造,从汉文文献与藏文文献、汉族史家与藏族史家、传统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等角度较为全面分析了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和学术环境等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影响,指出“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通常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往往受诸多微妙与不是那么微妙的因素影响。意识形态的侧重点、官方文件的倾向、当代政治的语境以及当时学术研究所关心的问题都对工布朗吉的形象施加了影响。”[15]而康欣平在清末瞻对问题研究论述中,提及清廷官员内部的筹边思路博弈时,针对前人对鹿传霖等人的评价,提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很有可能源自后人们的“移花接木”的历史记忆,略有“歪曲”。因此,在评论历史人物和看待历史事件时,一定要网罗相关资料,对整体历史有一定的理解,能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思维,找到事件的关联性,从而避免片面认识历史。
对于概念性问题,也可进行深入探讨,如陈一石作为早期对瞻对研究的学者,曾提出了清廷对待瞻对不存在“收回”与“失掉”的概念,认为前人往往从四川角度出发,未能考虑西藏地区利益,“这在客观上形成畛域之见”[7],清廷官员大民族主义的言论伤害民族情感,造成恶劣影响。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谓一针见血。之后,康欣平提出,陈一石对清廷官员“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指责,“是一种后出的观念,似乎过于苛责前人”[14]。
除了关注历史事实,也可从新的实用角度加以分析。如石硕的《瞻对:小地方 大历史——清代川藏大道上的节点与风云之地》一文,除了探讨了学者们所关注的瞻对事件的历史事实,也从新的实用角度,探讨了当今对瞻对即四川省新龙县的开发保护。文中提到了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这一问题,这是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历史不止是回顾过去,更应该是着眼于未来。瞻对这一地方,在历史上尤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足以说明这一地区的宝贵价值,更应该为我所用。石硕提出瞻对“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而且是国家层面的遗产”[3],他所提及的当前人们对历史地名的忽视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运用历史文化,发展旅游经济,是当今热门的文化旅游话题,甘孜新龙县也大可借助阿来的《瞻对》效应,结合当地的雅砻江峡谷自然风貌,以及“康巴红”的康巴地域文化精神,发展当地旅游经济。
同时,阿来《瞻对》一书,掀起了一阵瞻对热,近年来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大受追捧,如何协调文学和史学的关系,也可加以研究。
[1]清实录·圣祖实录三(卷二百零八)康熙四十一年闰六月甲午 [Z].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p119
[2]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二卷)[M], p311
[3]石硕.瞻对:小地方大历史——清代川藏大道上的节点与风云之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4]刘源.乾隆时期的瞻对事件[J].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
[5]清实录·穆宗实录二(卷五十八)同治二年二月丙申[Z].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p129
[6]黄全毅.浅析清同治朝瞻对事件[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7]陈一石.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J].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
[8]玉珠措姆.瞻对工布朗结在康区的兴起探析[M].中国藏学,2014年第2期
[9]戴逸.乾隆皇帝及其时代[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p169
[10]张秋雯.清代雍乾两朝之用兵瞻对[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2年,p261
[11]周远廉主编.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下)[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12]康欣平.从“收回”到“赏给”:1896~1897年间清廷处理瞻对归属事件析论[J].西藏研究,2013年第1期
[13]张秋雯.清季鹿传霖力主收回瞻对始末[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年第29期
[14]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J].西藏研究,2012年第5期
[15]玉珠措姆.史学家对工布朗吉土司形象的构建[M].民族学刊,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