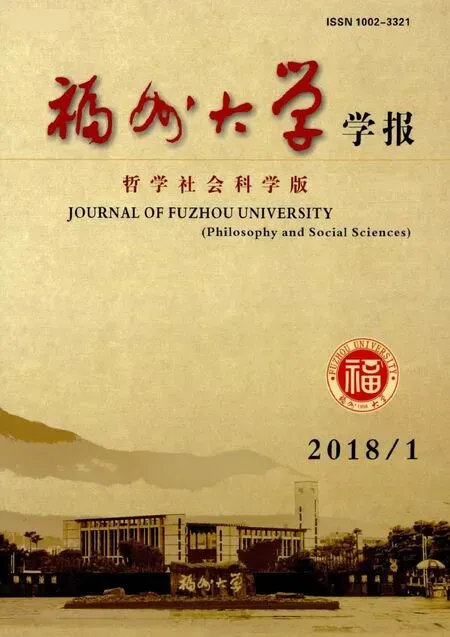欧阳修《春秋》说历代接受摭评
2018-03-31洪本健
洪本健 王 永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062; 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024)
《春秋》说是欧阳修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研究《春秋》的成果主要是《春秋论》三篇与《春秋或问》二篇,另有《石鹢论》《辨左氏》等文。[1]《春秋论》上篇谓当“舍君子而从圣人”,即舍传而从经;中篇谓《春秋》之作乃“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并以隐公之非摄证之;下篇以“赵盾弑其君”与许世子止“非不尝药”,再强调《春秋》记事贵在“求情而责实”。《春秋或问》上篇论《春秋》之义不在起止,下篇谓不可强经以从传。可见舍传而从经、求情而责实是欧阳修《春秋》研究的重要观点。如此《春秋》说,历代学者持何见解呢?
一
宋代《春秋》学是一门显学,著述极丰。四库馆臣称:“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2]北宋《春秋》研究之著名者,有孙复、刘敞、苏辙、孙觉、程颐等。孙复受中唐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的影响,弃传从经,直寻大义。此为欧阳修舍传从经的背景。欧撰《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云:“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欧笺·居士集》卷二七)这里“不惑传注”二句,正是欧《春秋论》所秉持的观点。孙复、欧阳修与刘敞已开宋代以义解经之先河。
刘敞小欧阳修12岁,两人交谊甚深,欧熙宁二年(1069)所作《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高度评价其经学成就:“其为《春秋》之说,曰《传》、曰《权衡》、曰《说例》、曰《文权》、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经小传》五卷、《弟子记》五卷,而《七经小传》今盛行于学者。”(《欧笺·居士集》卷三五)刘敞在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上极有造诣,叶梦得称其虽出欧阳文忠之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甫。”[3]但欧毕竟年长许多,景祐四年(1037)就撰有《春秋论》,时刘敞尚未及20岁。由是观之,欧、刘二者乃互有交流互为影响,客观而言,在经学上,早年欧当对刘熏陶较多,后来刘对欧的影响更大。刘敞曰:“学者莫如信《春秋》,则外物不能惑矣。《春秋》云甲,传云乙,传虽可信,勿信也。孰信哉?信《春秋》而已矣。”[4]又曰:“《春秋》之书要在无传而自通,非曲经以合传也。”[5]此与欧公肯定孙复的“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相一致。
苏辙的《春秋》研究,就关注人情,尊重史实而言,与欧公的“求情而责实”颇有共鸣之处。苏辙文中常提及“人情”,《栾城集·后集》卷七《周公》云:“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卷一二《颍滨遗老传上》云:“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栾城集·应诏集》卷四《诗论》云:“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夫圣人之为经,惟其于《礼》《春秋》,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同卷《春秋论》云:“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夫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6]苏辙以为,作《春秋》者,圣人也。圣人亦人,富于人情,触事感物,喜怒油然而生。喜怒形之于言,可由“辞气”之所向察知,故于“辞气”观喜怒,察人情,可探圣人之意,明《春秋》之旨。
欧阳修议事解经均不离人情,《纵囚论》批评唐太宗纵囚之举“岂近于人情”,谓“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欧笺·居士集》卷一八)《石鹢论》云:“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推至隐以探万事之元,垂将来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于《春秋》矣。”(《欧笺·居士外集》卷十)《答宋咸书》亦云:“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欧笺·居士外集》卷一九)《诗本义》卷一论《关雎》曰:“本谓文王太姒,而终篇无一语及之,此岂近人情?”卷六论《出车》曰:“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7]
“求情”为了“责实”,泛而言之,欧与苏辙皆欲探明事实,去伪存真。但真实何在,如何求真,两人有不同的看法。欧《春秋或问》云:“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又云:“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故欧以为,应尊经重经,以经为主,传则酌情用之,可“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欧笺·居士集》卷一八)在传不可靠的情况下,当舍传从经。苏辙云:“凡《春秋》之事,当从史。《左传》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盖孔子之作《春秋》,事亦略矣,非以为史也,有待乎史而后足也。以意传《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8]
苏辙谓《春秋》记事简略,当“有待乎史而后足”[9],三传中唯《左传》堪称史,最为可取。也就是说,应当以传补经,据传解经,如此,详则详矣,然而难免有迁经就传之处。可见欧、苏的差异很大。
到了南宋,朱熹视《春秋》为史,故而看重《左传》,与欧公相异而嘉许苏辙。被问到“《春秋》当如何看”时,朱熹曰:“只如看史样看。”又曰:“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当然,他并非一味肯定《左传》,而对三传有较公允的评价:“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有功,然记事多误。”[10]
王柏引欧公《帝王世次图序》“司马迁远出孔子之后,述黄帝以来,详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务胜” 等语后云:“及(欧公)订其缪,可以发千古之一笑,止以‘惑世’二字断之。苏黄门(辙),师欧公者也,习闻其说,亦谓迁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切中其病。其词已激昂,不如欧公之从容温润也。至于自编古史,又叙三皇,反加详焉,岂临文之际而忘之乎,抑不免于务胜而惑世也?”又云:“欧阳公《春秋论》辨鲁隐公非摄,如此之明,苏学于欧,岂不闻之?今《鲁世家》一信左氏语,岂忘之乎?”[11]
王柏肯定欧公对《史记》“述黄帝以来,详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务胜”,以致失误甚多的指责和舍传从经的观点,批评苏辙“一信左氏语”舍经而从传的做法。
宋世,针对欧阳修在三篇《春秋论》及《春秋或问》中提出的鲁隐公、赵盾、许世子止三事与《春秋》终始等问题,有不少议论。北宋末,萧楚作《春秋辨疑》,卷三《石鹢辨》引欧阳修“圣人记灾异著谨戒而已,何必谨于名数”等语,并驳之曰:
此说非深达《春秋》者也。且既曰孔子笔削矣,使旧史所志如此而无意义,自当削之,何必留此,以惑后人,且既笔之,则是有其旨矣……圣人于《春秋》记灾异,记灾,重其及害于民,示后世之忧民也;记异,著人道失政而兆祸乱,所以警训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册。[12]
其实,欧“记灾异著警戒”已囊括萧楚“示后世”“警训于世”之意。一定要探究“六鹢”“石五”等特定内涵,见圣人“笔削”之深意,未免有过度阐释之嫌。在《春秋或问》中,欧阳修称《春秋》“始终之义,吾不知也,吾无所用心乎此”,又称“义在《春秋》,不在起止……予厌众说之乱《春秋》者也”。 (《欧笺·居士集》卷一八《春秋或问》)萧楚《石鹢辨》驳曰:“经曰狩,不言所获,惟‘西狩获麟’,其年止书此一事。如此,则谓终之无义为不可也。”[13]黄震则肯定欧公的评说:“谓学者不信经而信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隐公非摄,赵盾非弑,许世子止非不尝药,乱之者,三子也。起隐公,止获麟,皆因旧史而修之,义不在此也。卓哉之见!读《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14]这里讲的“赵盾非弑”,意为“非亲手所弑”。吕大圭亦谓“欧阳公论止为弑,得其旨矣。”[15]显然,萧楚并不代表主流的意见。
生活在宋、元之交的家铉翁,评许世子止弑父事曰:
父非不慈于其子,子非失爱于其父,非若楚商、蔡般逞废黜之憾,而成滔天之恶也,而《春秋》何至加以弑君之罪乎!圣人秉法至公而存心忠厚,一不尝药而遂坐以弑君之罪,必无是也。欧阳子尝论及斯事,以操刃而杀与不躬进药、进而不尝三者,坐当同科,深有疑于传家之说,而胡文定不以为然。愚谓圣人之修《春秋》,多因旧史之所已书,而加以笔削。赵盾、许世子之弑,盖皆旧史已书,圣人因之而不改,所以垂法于后世也。[16]
他也是赞同欧公“求情而责实”的分析。“求情而责实”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得到家铉翁的认可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为以史证经、以史通经的代表。”[17]欧阳修自然认同孙复、刘敞,他们的“贬传”很果决,旨在打破汉唐以来轻经重传唯章句之学是求的陋习,树立重经典求本义的新风。其实就像刘敞杂用三传,经传连书,以己意裁断一样,欧阳修对三传也并非一概排斥,称“夫传之于经勤矣,其述经之事,时有赖其详焉”“其述经之意,亦时有得焉” (《欧笺·居士集》卷一八《春秋或问》)。当然,他重点是在尊经求义,而非着力于经传的会通。
二
金代,欧阳修的经学成果处在不断传播和被学者发展的过程中。金代经学发达较晚,贞祐南渡之后方有所研究,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人是经学方面的代表学者,他们对欧阳修经学成就进行全面论断的材料较少,值得注意的是金代王若虚对欧阳修《春秋》说成就的考查,多为一些实证性的细节问题,批判和质疑的色彩较浓。其《滹南遗老集》云:“王通曰:三传作而《春秋》散。欧阳子亦讥学者不从圣人,而从三子。君子之学,亦求夫义理之安而已。圣人之所必无也,传为经作,而经不为传作,信传而诬经,其陋儒已矣。”[18]这里肯定了欧阳修不沉溺于传注解说、注重经籍原典的态度,并更深一步提出,经传之中正确的义理才是学者真正要追求的。
元代关于《春秋》的著述不多,程端学有《春秋本义》《程氏春秋或问》《春秋三传辨疑》,赵汸有《春秋左氏传补注》《春秋集传》《春秋属辞》《春秋师说》《春秋金锁匙》。此外尚有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吴澄《春秋纂言》、李廉《春秋诸传会通》、郑玉《春秋经传阙疑》等,各有不同的收获。欧阳修的《春秋》说,其核心处是对信传而诬经观念的批判,在细节上,还有对赵盾、许止的弑君问题的考辨,对此,赵汸和程端学的研究都有所深入。
赵汸《春秋师说》卷中“论汉唐宋诸儒得失”条云:
三传重于汉而轻于唐,自韩退之《春秋》三传束高阁之语为卢仝发,而啖赵六氏及孙泰山之学为时所尚,故欧阳公说赵盾事皆不用三传,而三传愈轻矣。[19]
这里揭示了欧公《春秋》说理念的学术渊源,既指出了韩愈、卢仝、啖助、赵匡等人的启发,也点明了石介等同时代学者的风尚。卢仝是韩愈的好朋友,韩愈有《寄卢仝》诗,真实地记载了卢仝的家庭经济与隐居生活状况,以及卢仝的性格、品德、诗风等,其中“《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20]之语,体现了二人对《春秋》所持“重经不重传”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志趣。欧阳修在古文方面推尊韩愈,在经学方面也深受其影响。
程端学《三传辨疑》卷一载:
欧阳氏曰:“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也。使息姑实摄而称号无异于正君,则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息姑之摄也,会盟、征伐、赏刑、祭祀皆出于己,举鲁之人皆听命于己,其不为正君者几何?惟不有其名尔。使其名实皆在已,则何从而知其摄也?且其有让桓之志,未及行而见杀。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违本意。则息姑之恨,何由伸于后世乎!孔子书为‘公’,则隐决非‘摄’。”愚谓三传摄让之说起于不书即位,未必遽信史也,姑阙其疑。[21]
程氏部分肯定了欧公对《左传》等书鲁隐公“摄”位之说的质疑,但还是谨慎地保持“阙疑”的态度。
程端学在《程氏春秋或问》卷九及《三传辨疑》卷一八中倒是认可了欧公对许世子止药杀悼公的考辨,认为“欧阳公论止为‘弑’,得其旨矣。”[22]《三传辨疑》卷一八引欧阳修语:“买病死而止不尝药耳。学者不从孔子信为弑君,而从三子信为不尝药,其舍经而从传,何哉?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既而云:“窃意左氏、公羊之说皆是也,但后说不然耳。世子药杀其君,《春秋》故书‘弑’。《榖梁》晩出,因二氏有药杀之语,增附不尝药之说,凡后来为之辞者又皆惑於《榖梁》,故因凿之以饰义例耳,本无可疑也。《春秋》书‘弑’而左氏、公羊称药杀,亦‘弑’也。”又云:
愚谓左氏自许悼公疟至药卒,事或可信。自“太子奔晋”以下,左氏自为之言也。凡弑而出奔者,经必书之,以见臣子不讨贼之罪。如宋万出奔陈之类是也。今止果奔晋,经岂有不书者乎?此其事之不可信者也。自“君子”以下,乃无礼之言,有不足辨者。《公羊》惟“止进药而药杀”一句事或可信,其余皆无足取。其以贼未讨,书葬为义,而谓君子赦止之罪,谬妄之尤者。若《榖梁》皆言之无可取,其以日弑为正卒而不弑,固不足凭,至论君子即止自责而责之,尤不足辨。天下岂有不论其事之虚实,因其自责而遂诬之之理哉?[23]
这是在引申中生发己论,在欧公提出的论点上又补充了证据和思辨。
然而对赵盾弑君之事,元人则提出了与欧公不同的意见。赵汸《春秋师说》卷上云:
《左传》赵盾事首尾皆实,惟“越竟乃免”语意不备,故学者多疑之。若曰“越竟有罪乃免”则语意备矣。又赵盾之罪与栾书、中行偃不同,书、偃亲为弑逆,然经却又只书晋弑其君,又不曾书讨弑君贼。当是时,莫是书、偃为政而别不曾讨贼,则弑主非书、偃而何?此等处虽欲不信《左传》亦不可也。若欧公只据经文,则书、偃得免于弑君之罪,如此却出脱了多少恶逆之人?[24]
尽管欧阳修已经对舍传而从经后可能产生的对经书的盲从问题有所警醒,但《左传》等书中应该也的确有揭开经书所遮蔽的事实的地方,赵汸在这里找出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来反证和提醒。
综观元代,关于欧阳修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文及人,由文学而经、史,由推崇到讨论的过程,其中颇多有价值的观点值得后世学者探讨。
三
明人关于《春秋》学的专书并不少,收入《四库全书》春秋类的专书,包括胡广等奉敕编纂的《春秋大全》、湛若水的《春秋正传》、高拱的《春秋正旨》等就有21部,加上归入存目的44部,共有65部。就数量而言,比起宋代的43部(含存目5部)、元代的20部(含存目4部)并无逊色。但就学术价值而言,超越前代的不多。王介之有《春秋四传质》,徐浦有《春秋四传私考》,陈士芳有《春秋四传通辞》,“四传”是《春秋》三传加上南宋胡安国《春秋传》的合称。明代还有专门探析胡氏《传》的著作,如陆粲的《春秋胡氏传辨疑》、袁仁的《春秋胡传考误》等。明人说《春秋》每每以胡《传》为主,杂引诸说,此与明代科举考试《春秋》主“四传”密切相关。前述65部专书中,揣摩科举应试的参考书,并非寥寥几部。应该说,明代中期后,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对胡《传》一统的局面,形成有力的冲击,产生新的研究气象。王樵《春秋辑传》的《凡例》卷下《灾异》第十五[25],首条即以“欧阳修曰”引出《新唐书·五行志》的一段话:
夫所谓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类是矣。异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鹢之类是已。孔子于《春秋》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盖慎之也。以为天道远,非谆谆以谕人,而君子见其变,则知天之所以谴告,恐惧修省而已。若推其事应,则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则将使君子怠焉,以为偶然而不惧,此其深意也。[26]
欧强调“《春秋》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不应轻易地将大自然的灾异与社会上的人事牵强挂钩。因为“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即没有必然性。其意显然易见:即应当重视人事,不能相信谶纬之类的迷信,此为王樵所接受和重视。
卓尔康《春秋辩义》卷首《书义》三之《天文》,言及“至于灾祥征著有主事应者”,引了刘向的一段话,而“有不主事应者”,亦征引欧公上述《五行志》的论说,与王樵一样,反映了对欧公批判谶纬的进步观念的认同。然而,在《书义》四之《大义》中,卓氏对欧效法《春秋》的“笔法”深不以为然,曰:
昔永叔书五代之君,皆曰崩;佐逆皆曰薨。或者以为盗贼篡逆之徒,生前既以为帝为王,崇高富贵,止藉君子笔削之严,以稍诛其恶。而复崩、薨之,则此辈既得窃命于生前,又得徼荣于死后,是为恶者无时而不利也。然乎?闻永叔后亦悔之,而事亦无及,不能追改矣。[27]
这确是从某一方面道出《新五代史》的不足,即把重点放在《春秋》义例与笔削上,而问题是造成记事之过于简略。《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新五代史记》提要曰:“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28]其实“曰崩”“曰薨”,欧是基于“为帝为王”的历史事实着笔,并不涉及道德评价。《新五代史》由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徐无党作注,显然是发欧所未发,为欧所认可。卷一《梁太祖纪》注谓朱温“始而称名,既而称爵,既而称帝,渐也。爵至王而后称,著其逼也”,即是典型的春秋笔法。[29]当然,身为宋人为五代修史,过度强调春秋笔法,以求“义例谨严”,似过于“从古”,而由学生来阐发蕴意,难免有多此一举之嫌。
在实证研究方面,明人涉及欧阳修《春秋》说的论述并不多。关于鲁隐公之死,季本《春秋私考》云:
欧阳永叔曰:“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绝其为君。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永叔之言,诚得《春秋》之意,然诸君所以得成为君者,亦以国内无二君也。[30]
以上所引欧文见《新五代史》卷二《梁本纪》。季本赞同欧公对《春秋》据实直书的肯定。《梁本纪》载鲁桓公等四人以或弑或逐的手段夺取政权,均属实,且“国内无二君”,故不能“绝其为君”,不必为之讳。
关于晋灵公与许悼公之死,王樵《春秋辑传》卷六文公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条云:
以许世子止与赵盾之事观之,天下之事莫大于弑君,圣人安肯疑其文以启后世之惑乎?亦直书而已矣。许世子之事,欧阳公之说是也。惟赵盾则以左氏之记事,考经文之所书,其当书赵盾无可疑者。
同书卷七宣公二年“秋八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条云:
欧阳永叔以传不足信,谓经书赵盾弑君,则弑者实盾耳,非穿也。此亦过于立论也。
王樵认为许世子事当书弑君,而赵盾则非弑君,即前者从经,而后者当从传。
欧阳修《春秋论下》曰:
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
欧认为,赵穿为弑君之首恶,盾“不讨之”,即为“纵贼”。所以后文曰:“孔子所书是矣,赵盾弑其君。”他既是求情责实,又顾及“弑逆,大恶也”的《春秋》大义。而王樵赞成《左传》,以盾非实弑,加以大恶,是“过于立论”。王与欧的分歧表面上是在信传还是信经上,而根本上是在赵盾要不要因“纵贼”而负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上。
有关许世子止之事,陆粲曰:
饮其药而卒,是进毒以杀父也。父死而奔晋,是避讨也。止之为弑君,亦较然明矣。三传以异说乱圣经,君子不忍恣也。是故赵盾、许止之事,欧阳子之辨,圣人复起不能易矣。[31]
陆粲显然持欧公从经而不从传的观点。
王樵也有详论:
张洽问于朱子曰:“尝读欧阳公论许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读胡文定公《传》,未足以破其疑。洽继而考之《左氏》《公羊》之传自明,但后人因《穀梁》不尝药之说,遂执此一句,以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许悼公疟,饮世子止之药卒。’《公羊》曰:‘子进药而药杀也。此可见悼公之死于药矣。’当是之时,虽未有明文,而洽尝观近世治疟者,以砒霜煅而饵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杀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类也。不然,当时所进非必死之药,止偶不尝而已,则《公羊》何以谓之药杀?世子亦何为遽弃国而出奔?孟子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进药而药杀可不谓之弑哉?其所以异于商臣、蔡般者,过与故之不同耳。心虽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于君父不可过也。如此观之,似足以正近世传经之失而破欧公之疑。不知先生以为何如?”朱子曰:“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说,‘如律中合御药误,不如本方造御舟误不坚固之类,已有此意矣。但考之于经,不见许止弃国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谓也。’”[32]
以王樵征引张、朱对话观之,张洽怀疑欧阳修关于许世子止“弑君”“非不尝药”之说,读胡安国《传》仍未释疑,读《春秋》三传后,明了“过与故”虽有别,致“君父”于死地则无异。朱熹以“不见许止弃国出奔之事”,不敢苟同。联系同书卷六“许世子之事,欧阳公之说是也”的论述看来,王樵是倾向于张洽的见解。但他对欧公一味据经断定赵盾“弑君”,而无视《左氏》记事的做法是不赞成的。
卓尔康云:
许止一事颇极纷纭,然狱贵初情,事有原案,惟谳者洗出之耳。案经书“许世子弑其君买”,《左氏》曰:“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太子止之药,卒。太子奔晋。”《公羊》曰:“止进药而药杀也。”据二传,明是许止以药杀父矣。即《穀梁》“许世子不知尝药”一语,盖谓即使手自和剂,亦须先尝,以知药性味,非谓别医所进,世子仅一不尝而已。自《穀梁》有此一语,而永叔泥之。刻者推永叔之澜,以为许止必有实弑之恶;微者模子春之意,以为不尝之罪等于操戈。然而皆非也……夫诸儒蔽许止进药之罪是也,永叔蔽许子药杀之罪亦是也,其误认《穀梁》不尝药之旨则谬矣。永叔理学大儒,而每以文理阻碍,致起纷纷……误认《穀梁》尝药之语,而后贤聚讼,则亦读书未精之故尔。[33]
卓氏据《左传》《公羊传》,认定许止“以药杀父”,批评欧阳修受《穀梁传》的影响,纠缠于尝药不尝药的问题,遮蔽了“许止药杀之罪”。此说纯属臆断。欧阳修已讲得很清楚:“孔子书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之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耳。’学者不从孔子信为弑君,而从三子信为不尝药。其舍经而从传者何哉?”(《欧笺·居士集》卷一八《春秋论上》)
季本云:“许世子止弑君,以毒弑也。世儒相传皆以为止不尝药,盖本其国人为止讳弑之辞耳。言不尝药,则不问可知其为毒也。”[34]这是直截了当地下了许世子止以毒弑君的结论。《四库全书总目》卷三〇批评季本“不信三传,故释经处谬戾不可胜举”。黄正宪持同样的观点,云:“许世子之弑君,以毒弑也……故圣人直书之曰‘弑其君’,《公羊》云‘止进药而药杀’,得圣人之旨。”[35]
高攀龙曰;“欧阳公辨三传,以止为真弑;季氏《私考》及西亭《辨疑》,皆以为用毒药弑,恐不可以臆废古也。”[36]《辨疑》指朱睦木挈号西亭所著《春秋诸传辨疑》。高氏谓欧公信经,“辨三传”而不从传;认为《私考》与《辨疑》“以臆废古”,是错误的。欧公乃据经而断定许世子止弑君,云:“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欧笺·居士集》卷一八《春秋论上》)而《私考》与《辨疑》乃据传而得出许世子止用毒药弑君的结论,虽皆断定弑君事实,但依据各异,这是欧《春秋论》与《私考》《辨疑》不同之所在。
概而言之,明代由于最高统治者力推《春秋大全》,独重胡安国尊王崇道的《春秋传》,加上科举体制下的经学诠释日益庸滥,《春秋》学的探讨少有佳绩,即使是实证性的研究也难免空疏的议论,甚至以臆想代替考据。在社会上为应试而推出许多高头讲章的情况下,欧阳修论《春秋》仅有数篇文章而没有专书,受关注度不高,是可以理解的。但明代受心学影响的学者在学术上仍有自己发自肺腑的心声,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四
《春秋》学研究在清代的深入,与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当时环境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顾炎武曰:“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37]目睹明代经学的衰弱不振,他主张尊经从经,反对没有根底随意发论流于空疏的学风,指出:“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38]就尊经而求本义而言,顾氏与欧阳修是颇为一致的。《日知录》论《易》云:“《易》之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系九、六者,举隅之义。故发其例于《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变也……占变者其常也,占不变者其反也,故圣人系之九、六。欧阳永叔曰:‘‘《易》道占其变,故以其所占者明爻,不谓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39]这是他对经学家欧阳修《易》学观点的肯定。当然,顾氏尊经而不废传,主张会通《春秋》三传,此为欧阳修所不及。
张尚瑗在《三传折诸》的《自序》中说:
予师愚庵朱先生集《读左日钞》而序之曰:“欲成一家之学,必以经证传,以传证经,更复出入群书,展转相证。”欧阳永叔自谓信于孔子而不惑,经之所书,其所信也;经所不言,不敢知也。夫孔子未修之《春秋》,后世学者不得而见,何从测其笔削之意之所存?而丘明所为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者,皆为骈枝无用之物,唐宋以来经学传学之家,尤宜韬翰而不作矣。扬子曰:“天地简易,何五经之支离?支离盖其所以为简易也。”又曰:“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欧阳氏谓经简而直,传新而奇,学者乐闻而易惑。愚以为乐闻新奇,然后可以折诸简直。其新奇也,盖其所以为简直也。[40]
“予师愚庵朱先生”即著名学者朱鹤龄,张尚瑗借其言表达了经传互证的观点,不赞成欧“经所不言,予不知也”之见,认为重经轻传会导致后来的学者“韬翰而不作”。他还认为虽然“传新而奇”,但不能排斥其“折诸简直”的作用。因为“新奇”的传,对人们领会“简直”的经会有所帮助。当然,我们在承认经传互证、不应作片面排斥的重要性时,应该看到欧《春秋论》强调的是对“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的批评。且张氏所引扬雄“支离盖其所以为简易也”,实重经之说,意谓经虽分散,但只要认真梳理,沿波讨源,即能知圣人论道之简易。而“众言淆乱则折诸圣”,也正是欧所推崇与遵循的原则。
朱鹤龄以欧“力辨隐居位非摄”为非,云:“隐公称摄与周公异。周公之摄,止摄其政事而已,隐公则并君位而摄之……夫国政可摄也,君位不可摄也。若摄君之位,则嗣子长而复辟,将俨然太上自居耶?抑傫然北面复就人臣之列耶……欧阳子但信经文,以为隐公非摄,而不知隐实摄君位,故时史称公,夫子亦据而书之。”[41]朱氏又谓隐公“实摄君位”,与“王莽之居摄,亦摄天子位”同。[42]此乃以后史之事实证前史之必然,而完全缺乏隐公实摄的史实依据。
法坤宏以所谓“特笔”来解读隐公之“摄”:
继世即位,国君正始大礼,于法应书。隐、桓二公,一书一不书者,各于其遇而行事不同,故史氏之文亦异,孔子因之。隐以摄立,无正也。不书即位,以见其无正。桓以篡立,无王也。大书即位,以见其无王。书正书王,乃《春秋》取义大法,托始二公以见之,夫是之谓特笔。[43]
书不书即位,与无王、无正相对应,又称之为“特笔”,此纯涉主观臆测,似颇牵强。
张尚瑗指出:“欧阳公说赵盾事皆不用三传,而三传愈轻矣。”[44]可见欧说的影响力。但在赵盾、许止的弑君问题上,张氏所持的是与欧《春秋论》相反的观点,谓“于盾也见忠臣之至,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45]。焦袁熹也不认同欧之“隐决非摄”之说:“不书即位,非谓不即君位,不成为君也。三传之说略同……所谓摄者,身暂为君,终将退闲,非实不为君,徒以代行君事,若冢宰听政,而名之摄也。欧阳公驳之,谓隐非摄者,不深考三传之意尔。”[46]
欧阳修“求情而责实”的《春秋》研究,还是博得清代不少学者的认可。王夫之论隐公云:“隐公无可立之义,则可以摄;隐公固有可立之义,则不得复为摄矣。不得为摄,故隐公之立为争国,《春秋》必绌其乱;不得为摄,则桓公之立为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贼。”[47]王氏强调的是隐公非摄的观点,与欧说同。郝懿行也认为“传曰‘摄也’,非也。摄则不称公,称公则非摄。”[48]
王夫之论赵盾云:
抑以为盾之未躬之也,则司马昭之当辜,亦未尝躬之也。豢死士以竞勇于廷,穿之所与弑者,固盾之爪牙也。抑或为之说曰,赵盾能讨穿也,司马昭能斩充也,则可免弑君之罪。然则朱友恭、氏叔琮杀,而朱温免矣……盾固与灵不两立也,罢外争以专图之,伏死士以劫持之,盾之刃无日而不俟于灵之脰,所忌者襄夫人之唬耳。夫人薨而刃发,夫岂一朝一夕之故哉?[49]
此断定赵盾早就视晋灵公为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而要除掉灵公,有赵穿即可,完全不需亲自动手。
王氏论许止时云:
恶莫大于弑君。圣人之所尤惧,人之所尤闵,亦莫大于弑君……恶莫大焉,刑莫重焉。则正乎罪者之不可佚,不正乎罪者之不可陷。天讨所临,虽圣人莫敢易也。以此求《春秋》之旨,如日中天,无隐待索……故我知赵盾之弑其君夷皋,而不知其他也;我知许世子之弑其君买,而不知其他也。[50]
概言之,王氏谓《春秋》言弑言卒,其意已明,当以经为准,不必强为索隐。此意与欧说一致。
顾栋高感叹道:“欧阳公《春秋论》引据确切,辨析明快,而笃信三传者,犹不以公言为然。”[51]论许止事,顾栋高认定《左传》谓许止进药“无论故与误,皆不得辞乎弑”:“三传皆谓止非弑,《汇纂》亦从之,而斥欧阳子之说为非是。愚案:左氏之言与公、穀别。如左所云,则许世子不得辞乎弑。诸儒所称不尝药,与左氏之言绝远。若据之以为非弑,是非特不信经文,并错看《左传》矣。”[52]
毛奇龄认为赵盾难脱弑君的罪名:
灵公之弑,盾固已知之者也。不惟向知之,今亦知之也。若欧阳氏谓经书“盾弑”,则必盾实弑其君。而无与穿事,则又不然。从来操、莽行弑,并无手推刃以及其君者。律杀人者死,尚有造意知情与加功下手之不同。既已造意,亦何难令人加功?且不必加功而后可称为杀人也。[53]
论许世子止之事,毛奇龄亦以为止实弑其君,谓“经书弑君,而策书又云太子奔晋,是必世子欲速得其位,而假药行弑,故许人恶之,而止乃出奔”[54]。但他不同意欧阳修“谓操刃而杀与不躬进药及进药而不尝三者殊科”之说法。[55]毛奇龄作《春秋条贯篇》[56],卷七《宣公二年》有“晋弑君”条,谓“赵盾弑其君夷皋”;卷十《昭公十九年》有“许弑君”条,谓“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后有小注云:“自为药进之,卒。”顾奎光亦持同样看法,认为国君以疟疾被服药都是弑君者假药弑君的借口,“欧阳公竟以止为弑君,非无见也”。[57]
关于赵盾,万斯大云:
大抵灵公为人躁妄,未娴师保之训,长而渐黠,不堪赵盾之专,因欲杀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权久握,不容中失,遂萌逆节。己伪亡而穿行事,阳收其实而阴避其名。岂知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早为董狐两语断定。左氏惑于邪说,乃托仲尼之言以贤赵盾。嗟乎,弑君者为贤,将何者而后为不贤乎?[58]
据《春秋》与《左传》分析灵公、赵盾君臣的行为与心理,万氏信经而不从传,谓赵盾犯弑君之罪。论及许止,万斯大云:“左氏、公羊以为药杀,穀梁以为不尝药。愚揆之事理,以求书法,唯左氏可凭。”[59]他不同意公羊、穀梁之说,云:“唯左氏之言曰:‘许悼公疟,饮世子止之药,卒。世子奔晋。’兹数言者,足以定止之狱矣……杀父以药,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然则止之弑君无疑矣。”[60]万氏于此肯定左氏之说,以传证经,又符合事理,虽非舍传从经,但亦“求情而责实”,故与欧的推论一致,即许止实为弑君。
著名经学家姚际恒不仅在《诗》学上造诣卓绝,在《春秋》学上亦见解不凡。其论隐公非摄,与欧意同,辨析十分精辟:
经凡四公不书即位,此隐公与庄、闵、僖公也。盖即位于先君之年,故不书也。左氏于此谓不书即位,摄也。据谓隐公、桓公均非適,而隐居长,则自应立,岂可谓之摄乎?隐在位十一年,生称公,死称薨,与他公同,初无摄之事迹可证,固不待欧阳氏而后知其谬矣。所以然者,由左氏不得其不书即位之义于四公,皆附会其说以实之。谓庄不书即位,为文姜出故也;谓闵不书即位,为乱故;僖不书即位,为公出故:皆非其事而妄言。于隐公亦无以言之,则创以为摄,尤属凿空无据。合而观之,其悉为附会昭然可见矣。彼第从“摄”之一字辨之者,犹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耳。[61]
姚氏继承了欧阳修“隐公非摄”的观点,而在论证上比欧公更进一步。他统观《左传》全书,以隐公与同样“不书即位”的庄、闵、僖公放在一起考察,发现四公“皆即位于先君之年,故不书也”。又发现《左传》为了给“不书”找原因,就提出各不相同的四个理由,皆牵强附会,从而有力地证明隐公确实非摄。
至于赵盾,姚氏也支持欧阳修的弑君说,但对《左传》若干叙事之不可信有深入的分析:
经书赵盾弑则赵盾弑矣,即使赵穿弑亦赵盾弑矣。古来弑君者岂必皆手刃乎?固不必待前人之驳而后知之矣。左氏之言原不可尽信,今惟以二端言之。鉏麑将触槐而死之言,谁闻之而谁录之乎?一也。所载仲尼之言,如曰“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苟以盾为良大夫,必不书其弑君;今书其弑君,必不称为良大夫。且云“为法受恶”者,盖以《春秋》所书“弑君”,则盾受弑君之恶名也。若然,何不书“赵盾弑君”,而作此自缚自解之叹乎?至于“越境乃免”之言,则尽人可知其谬,二也。即此二端而其余可例矣。[62]
从“鉏麑将触槐而死之言”及“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等孔子之言中,姚氏发现不合情理的破绽,断定其为谬误,从而否定其可靠性。如此,遵循“求情而责实”的方法,搞清了欧《春秋论》所谓“疑似难明之事”,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赵盾,肯定了《春秋》关于“赵盾弑其君”的记述。显然,这比有的古书单说“经言赵盾弑君即为弑君”,更为具体,也更有说服力。
郝懿行亦持从经不从传的观点,其论赵盾云:“经曰盾弑,传曰穿弑,入穿所以出盾也,谬也。传所以出盾者,为盾贤也。贤也而弑君,则所谓贤者乃所以钓世之名而盖其弥天之罪,传者为所欺而曲庇之耳。”[63]按《春秋》的标准,郝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贤也而弑君”的荒诞,否定了穿弑而非盾弑之说。他认为传不可信,故又云:“赵盾、许止诸狱,如传所载,显悖于经,当如欧阳子信经不信传。”[64]郝氏论许止云:“谓止不尝药者,过与故。与君亲,无过。过而加之弑,当刑也,故而赦之罪,非法也。弑逆,大恶也。既责止,又赦止,是《春秋》成而乱贼不惧也。楚商臣、蔡般、许止一体书弑,止独以不尝药蒙赦,则书法无以别。若曰弑君不葬,此葬也,蔡景公亦葬,又可曰君子之赦般乎?”[65]郝氏将弑君者加以比较,从“弑君不葬”上,又发现了传的破绽,强调许止亦不可赦。继而云:“凡传所载多传闻之辞,传有可疑,考信于经。赵盾、许止,经实书弑。传必明其不弑,犹谓传不可废,是疑经也。欧阳子之论当矣。”[66]姚氏以其情理兼具、富于逻辑的分析,为欧《春秋论》作了很好的诠释。
晚清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云:“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其书弑者,以臣子弑君父,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67]皮氏亦本《春秋》大义与信经重于信传的原则,定许止为弑君。
有清一代,虽然对经传孰轻孰重的看法不尽相同,对隐公、赵盾、许止三人的情况也有许多细节各异或详略不同的论述,但多数学者原则上赞同欧阳修《春秋论》的观点,认为隐公非摄,赵盾、许止应承受弑君的罪名。
五
欧阳修《春秋》说各代接受情况,下面谨再作概括的梳理:苏辙虽与欧公皆关注人情,欲探明史实,但有别于欧的尊经以求本义,主张以传补经,据传解经,获朱熹嘉许。欧谓鲁隐公非摄,赵盾、许止实为弑君,王柏、黄震、家铉翁皆赞成欧“求情而责实”的分析。金代王若虚肯定欧尊重经典的态度,但指出必须追求经传中正确的义理,对欧《春秋》说的实证性探究,批判和质疑色彩较浓。元代赵汸揭示了欧公《春秋》说理念的学术渊源,对赵盾弑君说持有异议,认为《左传》有揭开经书所遮蔽的内容。程端学对隐公非摄问题持“阙疑”的态度,而认可欧对许止药杀悼公的考辨。明代,王樵、卓尔康赞同欧批判谶纬的进步观念,但对《新五代史》学《春秋》义例与笔削不以为然。欧公对《春秋》据实直书的肯定,获季本的赞许。实证性问题的研讨,学者们与欧的观点有同有异。王樵以为赵盾非弑君,而谓许止弑君。陆粲于许止事,与欧同持从经不从传的观点。卓尔康据传认定许止药杀之罪。季本则直接认定许止为毒杀。欧《春秋》说研究在清代得以深入,就尊经而求本义而言,顾炎武与欧一致。张尚瑗力主经传互证。虽然对对实证性问题有许多细节各异或详略不同的论述,但王夫之、顾栋高、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郝懿行等多数学者原则上赞同欧阳修信经而不从传,谓隐公非摄,赵盾、许止实为弑君的观点。
综上所述,欧阳修《春秋》说在历代接受中最受关注的是“舍传而从经”“求情而责实”,即注重经典、直求本义的观点。欧从孙复处受中唐啖助、赵匡、陆淳新春秋学派的影响,秉持“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的精神而治《春秋》,开宋代以义解经的先河,在历代皆产生影响。欧破除迷信、批判谶纬的观念,在其《春秋》说的后世接受过程中,也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欧主张实事求是地解经,反对于经书作过度的阐释,亦颇获后世认同。以经传互补而言,后世的接受中确认传有揭开经所遮蔽之处,就此对欧说有合理的质疑,显示了以史补经、经传会通的重要性。欧关于隐公非摄,赵盾、许止实为弑君的观点,历代有激烈的争论,但总的看来,获得较多的认同。
对欧阳修《春秋》说的研究,宋、清两代最为热烈。《春秋》学在宋代成为一门显学,跟欧阳修反对汉唐以来一味沉溺章句之学的陋习,开一代新风有极大的关系。金、元学者虽肯定欧的尊经,但已有所质疑,认为不能忽视传的价值。明代春秋类著述,捃摭旧文多,深入阐发少。但心学兴起,冲击胡《传》的一统局面,学者勇于发表自己的心得,情况有所改观。清代学者兼采汉、宋,既讲求义理,又重视考据,尊经而不废传注,故《春秋》学的研究又趋兴盛。欧阳修论《春秋》的主张,“求情而责实”的分析,得到诸多著名学者的肯定。当然,包括金、元、明在内,历代主张会通经传者,对欧一味信经而不够重视传的作用,有所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注释:
[1] 《春秋论》《春秋或问》见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后简称《欧笺》)之《居士集》卷一八,《石鹢论》《辨左氏》见《欧笺·居士外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2] 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九《日讲春秋解义》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3]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学津讨原本。
[4] 刘 敞:《春秋权衡》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刘 敞:《春秋权衡》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以上引文均见苏辙:《栾城集》,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 《诗本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 苏 辙:《春秋集解》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朱子语类》卷八三,清同治壬申刊本。
[11] 王 柏:《鲁斋集》卷八《复天台陈司户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13] 萧 楚:《春秋辨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黄 震:《黄氏日钞》卷六一,耕余楼刊本。
[15] 吕大圭:《春秋或问》卷一八《葬许悼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 见孙旭红:《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8]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19] 赵 汸:《春秋师说》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21] 程端学:《三传辨疑》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程端学:《程氏春秋或问》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程端学:《三传辨疑》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 赵 汸:《春秋师说》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王 樵:《春秋辑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
[27] 卓尔康:《春秋辩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 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9] 欧阳修:《新五代史》,徐无党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0] 季 本:《春秋私考》卷四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条,《续修四库全书》0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1] 《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下《昭公》“夏五月戊辰许世子弑其君买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春秋辑传》卷一一昭公十九年“夏九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卓尔康《春秋辩义》卷首《书义》四之《大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 《春秋私考》卷三一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条,《续修四库全书》0134册。
[35] 《春秋翼附》卷一八,《续修四库全书》0135册。
[36] 《春秋孔义》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丰熙伪尚书”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8] 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九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9] 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八九六”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0] 《三传折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42] 朱鹤龄:《读左日钞》卷一隐公十一年“使营菟裘在泰山梁父县南”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 法坤宏:《春秋取义测》卷二,《续修四库全书》0140册。
[44] 张尚瑗:《三传折诸》之《左传折诸》卷首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 张尚瑗:《三传折诸》之《谷梁折诸》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焦袁熹:《春秋阙如编》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王夫之:《春秋家说》卷一上《隐公》,《续修四库全书》0139册。
[48] 郝懿行:《春秋说略》卷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续修四库全书》0144册。
[49] 王夫之:《春秋家说》卷二上《宣公》,《续修四库全书》0139册。
[50] 王夫之:《春秋家说》卷三中《昭公》,《续修四库全书》0139册。
[51]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附录《韦轩手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四五《许世子止弑其君论》。
[53] 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卷二十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55] 毛奇龄:《经问》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 毛奇龄:《西河合集·春秋条贯篇》,《续修四库全书》0139册。
[57] 顾奎光:《春秋随笔》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万斯大:《学春秋随笔》卷七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条,《续修四库全书》0139册。
[59][60] 万斯大:《学春秋随笔》卷七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条,《续修四库全书》0139册。
[61] 姚际恒:《春秋通论》卷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续修四库全书》0139册。
[62] 姚际恒:《春秋通论》卷九《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条,《续修四库全书》0139册。
[63][64] 郝懿行:《春秋说略》卷七《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条,《续修四库全书》0144册。
[65][66] 郝懿行:《春秋说略》卷十《昭公》“十有九年冬葬许悼公”条,《续修四库全书》0144册。
[67] 皮锡瑞:《师伏堂春秋讲义》卷上,《续修四库全书》014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