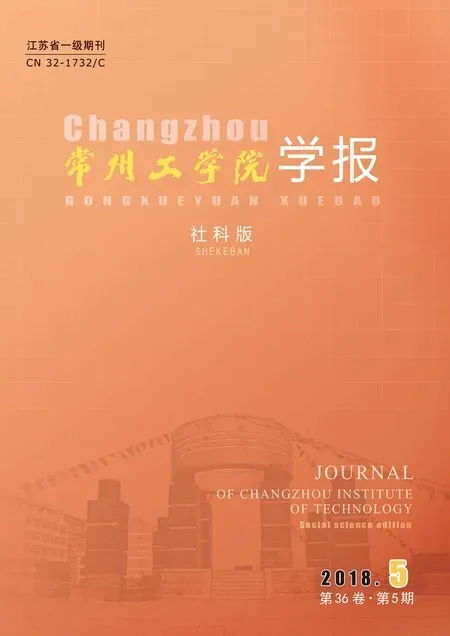论弗吉尼亚·伍尔芙《幕间》中的乡村共同体
2018-03-29戴润萍
戴润萍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幕间》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绝笔之作。伍尔芙运用复调的方法,讲述了1939年6月发生在英格兰中部一个叫波因茨宅的村庄里的故事,展现了这个有500多年历史的乡村的乡风民俗。伍尔芙设置了2条叙事线索,一条主要叙述乡绅巴塞罗缪·奥利弗一家的故事,另一条则讲述拉特鲁布女士指导村民排演露天历史剧的故事。这2条线索时而平行,时而交叉,作者借此把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艺术与人生、舞台戏剧与人生戏剧巧妙地结合起来。
《幕间》因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丰富的内涵意义而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主要从女性主义、空间批评和创伤叙事等角度来分析作品,然而,鲜有学者从共同体文化理论视角对《幕间》进行讨论。文章揭示了《幕间》中反映的乡村共同体的种种危机表征和以拉特鲁布女士为代表的波因茨宅村民们想要重构乡村共同体的呼声,指出伍尔芙的创作意图,即在人心日益浮躁的当今社会,人们如何守护一个美好的、生机勃勃的乡村共同体。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指出,共同体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1]58。传统乡村共同体源于村民们面对共同的外部风险时形成的一种凝聚力,诸如宗族、乡绅等内生于乡村中的治理力量及乡风民俗。然而,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日渐强盛,村民个体意识不断放大,传统乡村共同体凝聚力减弱。人们逐渐产生种种焦虑,开始反思共同体文化,并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
一、乡村共同体危机
弗吉尼亚·伍尔芙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幕间》创作于一战后二战前,这一时期正是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昔日“日不落帝国”的荣光逐渐褪去,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崛起,英国的帝国身份不断遭到冲击,人们开始寻找英国传统的共同体。此处的共同体指的是“人类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2]71。伍尔芙的《幕间》通过英国乡村景象和波因茨宅发生的故事来体现当时的乡村共同体危机。在作品中,乡村共同体危机主要体现在共同体成员之间关系的疏离、传统价值观的分崩离析和战争给乡村共同体所带来的威胁等方面。
乡村空间叙事是伍尔芙作品的特点之一。綦亮曾指出英国文化中有一种浓厚的田园情结,因为“乡村一直是英国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中蕴藏着英国人对英国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的集体想象”[3]86。与城市文化相比较,乡村地区生活的“共同体要强大得多,更为生机勃勃”[1]54。《幕间》中,有的家族在村庄里已经居住了几个世纪,他们从未出卖过任何土地。但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发展,人们乘车路过波因茨宅时总会议论“不知道那幢房子将来会不会进房地产市场”[4]5。土地的买卖宣示着乡村共同体受到商业经济的冲击,这种传统的“由于持久地保持与农田与房屋的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生活”[1]78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全村人排演露天剧时,村民的缺席让斯特菲尔德先生恼怒不已。在斯特菲尔德先生看来,一切罪恶的源头是“摩托车、公共汽车、电影”[4]72。作品中人们地域观念的淡薄、对共同体的漠视,反映了英国传统乡村共同体在现代化商业文明的冲击下面临危机。
疏离是作品中乡村共同体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主要体现为邻里以及亲人之间的关系疏离。家族是共同体的一种社会形态,“是共同体的植物形式,依托理念上的整体社会意志”[5]。奥利弗一家在波因茨宅才住了120多年,与其他家族没有血缘关系。而其他家族之间都有人情往来,甚至相互通婚。滕尼斯把共同体分为3种形式,即血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三者相互融合,密切相关。与地缘相对而言的便是“邻里”。在乡村共同体中,“邻里关系成为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形态”[5]136,奥利弗一家与其他家族之间关系疏远,显得格格不入。如果说邻里关系的不和谐是对地缘关系的挑战,那么夫妻关系的不和谐则是对乡村共同体作为“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1]58的巨大威胁。作为奥利弗家族的女主人,伊莎饱读古典诗集,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她与贾尔斯的夫妻关系仅仅由“他是我丈夫”“我孩子的爸爸”来维系。长期的分居让两个人渐行渐远。“正如威廉·道奇吃午饭时观察到的那样,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像小说里人们常说的是‘紧张的’。”[4]102。这些都打破了共同体的规律,即“相爱的人和相互理解的人长久地待在一起,居住在一起,安排他们的共同生活”[1]73。
历史剧是凝聚民族意识的艺术表现方式,相当于滕尼斯所言的精神共同体。它强调的是一种归属感和崇拜感。拉特鲁布女士试图通过排演英国历史中的光荣片段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但在指导村民排演露天历史剧的幕间,人们迅速收拾自己身边的东西转身离去,音乐突然转了调。“它吟唱:我们离散了啊。它呻吟:我们离散了。它哀叹:我们离散了。”[4]92“呻吟”与“哀叹”表达了对人们排演露天历史剧时的漠然表现的痛心疾首。看似平静祥和的乡村实际上充满了邻里矛盾。乡村的疏离感是当时英国乡村共同体危机的一个体现。
战争的破坏与“日不落帝国”的日渐衰落也威胁着当时的英国乡村共同体。作品虽然没有大篇幅地描写战争给乡村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伍尔芙还是通过对巴塞罗缪与贾尔斯的书写描绘了当时英国所处的政治局势以及“日不落帝国”的日落西山之势。英国在享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果实之时,也面临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停滞,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等社会问题。以巴塞罗缪为代表的英国殖民者仍然对大英帝国抱有一种帝国想象。在他们眼里,英国仍然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殖民地的人们在他们看来是野蛮人。斯威辛太太更是认为“那些野蛮人也真怪——因为他们赤身裸体不是很美吗?——竟然希望穿得像英国人,活得像英国人”[4]44。巴塞罗缪对阿富汗猎犬的态度依然保持着殖民地时期的那份骄傲,他会“把一条绳子套进它的项圈”,指挥猎犬像是“指挥一个军团”[4]10。帝国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了英国民族身份认知,是英国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参照”[6]。因此,帝国主义的衰落势必会引发人们民族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共同体的另一个重大威胁是战争。表面上看,乡村的平静生活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天空轰隆隆飞过的战机向人们释放战争即将到来的信号。当贾尔斯从报纸上获知战争导致“十六个男人被枪杀,其他人被监禁,这事就发生在那边,在海湾对面,在那块和他们隔开的平坦地带”[4]44时,他内心非常愤懑,却又无能为力。他怨恨自己的无能,埋怨斯威辛夫人送他去大城市。战争带来的不只是无尽的杀戮和创伤,还有文明的倒退。战争让人们失去了人性,违背伦理纲常。在露天历史剧结束时,人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没有军队,没有性爱。“我承认,说我们是没开化的野蛮人,确实有点道理。”[4]195
帝国主义的衰落让以巴塞罗缪为代表的具有帝国主义情怀的英国人产生焦虑感。綦亮认为:“正如帝国主义的在场是对英国民族身份认同的障碍一样,帝国的缺场同样引发了英国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3]87。每个人都试图在这个不稳定的共同体里找寻自我,因此产生了个人身份认同的焦虑。
二、乡村共同体的重构
伍尔芙一方面描绘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乡村共同体危机,另一方面又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了一个共同体愿景。如伊莎、斯威辛、拉特鲁布女士分别通过书写精英文学、延续基督教传统和指导村民排演历史剧等方式来再现英国的荣光。
在工业文明与现代化的冲击下,文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乡村,试图寻找他们的“英国性”①。此时的乡村更像被“赋予了一种重新定义英国民族身份、重塑英国民族形象的矫正和救赎功能”[3]87。如果说巴塞罗缪意欲维护的是帝国主义的优越感,那么伊莎通过她的言行展现的是英国精英文学传统②。伊莎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贯穿了作品的始终。她希望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即“那草、那花、那树是一个整体”[4]9。但是轰隆而过的飞机让伊莎觉得“维系我们的一切将会失去”[4]13。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英国仍然在维护传统乡村共同体的秩序。正如伊莎所说,她会因为她的贵族血统,以及“为自己是爱尔兰国王的后裔而倍感自豪”[4]13。在露天剧排演点名时,人们会强调“我是代表我的祖父或曾祖父来的”[4]72。可见,英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在人们的观念里根深蒂固。
同时,伍尔芙在这部作品中运用了意识流手法来刻画伊莎这一人物,例如:
她思索着:济慈和雪莱,叶芝和多恩。也许不是一首诗,而是一部传记。加里波第的传记,帕莫斯顿勋爵的专辑。也许不是一个人的传记,而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如《达勒姆城的古迹》《诺丁汉郡考古学会档案》。也许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科学——爱顶盾、达尔文或金斯。[4]17
伍尔芙试图通过伊莎这一人物形象来再现英国的精英文学。书籍在文中被比作心灵的镜子,可是人们逐渐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对那种高雅的书却不好奇,没反应,不敏感了”[4]51。为了打发旅途的无聊时光,他们去书摊买了本书——一本廉价的流行小说。因而“书籍这个反映高尚心灵的镜子也反映了厌倦的心灵”[4]14。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文学开始由精英文学走向大众文学。大众文学在当时被法兰克学派当作“文化工业”,预示着文化与社会的衰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现代化给传统文化和民族性带来了冲击。
斯威辛太太对基督教传统的继承也是伍尔芙重构英国乡村共同体的一个重要体现。作为一名留居在波因茨宅的寡妇,斯威辛太太时常佩戴着象征自己信仰的十字架。当斯威辛太太仰望星空时,伊莎认为她看见上帝坐在宝座上。她说:“这天气确实多变。恐怕要下雨。我们只能祈祷。”[4]21她摸了摸脖子上的十字架。“十字架”既关联死亡,又象征复活。“多变的天气”意味着世事变迁,“下雨”则让人联想到战争。巴塞罗缪总是不断地攻击她的信仰。斯威辛太太问“碰碰木头”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巴塞罗缪说那是迷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质疑宗教的职能和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基督教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斯威辛太太仍然试图唤醒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她带道奇参观保育室,“她似乎在说‘我们民族的摇篮’”[4]69。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她们“一直被排除在英国的民族叙事之外”[6]71。虽然伍尔芙在作品中尝试让女性来重构民族意识,可她一直受制于女性地位的边缘化和女性话语权的限制。事实上,现代化的发展也冲击着人们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能适应新的情况吗?在这种时候……在拉廷,没有人去教堂。”[4]194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们渐渐变得物质化,斯威辛太太想让基督教传统重返乡村的愿望终究会落空。
露天剧是英国早期文学创作的方式之一。它是团结人的纽带,是唤醒人们民族意识的一种方式。伍尔芙在小说中插入了一段露天历史剧,以再现历史片段,试图以此建立一个理想的乡村共同体。
拉特鲁布女士身材粗壮,举止唐突,做事果断,像个男士,所有这些特征都“令人恼火”[4]61。伍尔芙希望通过以拉特鲁布女士为代表的女性形象来重构英国历史,弥补英国历史上女性叙事的空缺。在拉特鲁布女士编导的露天历史剧中,她采用了一种戏谑手法:傻子艾伯格饰演王子,卖烟草的老板娘饰演伊丽莎白女王……“狂欢化”③的书写方式无疑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思与嘲讽。她也独具匠心地在戏剧里融入了音乐、话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艺术对共同体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而“通过音乐来想象共同体,是英国文学中古往今来的普遍现象”[7]59。拉特鲁布女士在露天历史剧中插入了大量的音乐,如童谣。音乐也“唤醒了我们。音乐让我们看见了隐藏着的东西,让我们加入心力交瘁的人们之中”[4]115。拉特鲁布女士选择伊丽莎白一世、莎士比亚戏剧、理性时代与维多利亚时代等片段来再现英国的繁盛时期,并让村民参与露天历史剧的排演,以此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
在拉特鲁布女士眼里,露天历史剧的演出最终是失败的。留声机和自然的干扰、村民的滑稽出演等让人们觉得这是一出滑稽戏。散场后空空的捐款箱暗示了现代商业文明对传统民族意识的冲击。人们的兴趣丢了,不愿理解历史剧的内容,更不愿捡起不知从何时起丢掉的看戏的习惯。留声机是伍尔芙特意设定的画外音,她一直希望“让我们把造成那种和谐的一切都保持下去吧”[4]192,可是大家都匆匆散场。历史剧的失败也宣告了伍尔芙重构英国乡村共同体愿望的落空。戏结束时扩音器里传出“那面被我们叫作(也可能错误地叫作)‘文明’的大墙,怎么由我们这样的饭渣、油渣和碎片去建设呢?”[5]183工商文明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急剧衰落都注定拉特鲁布女士重构乡间共同体的尝试失败。
当人们意识到英国传统乡村共同体出现危机时,每个人都试图去维护传统的共同体。伊莎对平等自由的追求、斯威辛夫人对基督教传统的维护、巴塞罗缪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及最后拉特鲁布女士排演的露天历史剧等等,无不是人们所做的努力,可是,面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三、结语
《幕间》通过描述英国乡间故事来反映20世纪30年代英国所面临的共同体危机。一方面,昔日的帝国荣光逐渐褪去,人们的民族意识越来越淡薄;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传统英国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伍尔芙试图通过《幕间》这部小说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并把自己对乡村共同体的愿景寄托于文中主要女性人物身上。但是,在商业文明的冲击下,伍尔芙的共同体愿景无法实现。
注释:
①“英国性”指的是最能代表英国民族共同体精神的特征,即英国精神。
②F.R.李维斯提出文化只属于少数精英分子,而非普通大众。
③巴赫金的“狂欢化”指的是一切权威的、不可改变的、严肃的东西被颠覆,打散,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