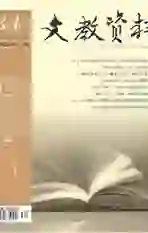青年的出路与困境
2018-03-27周青
周青
摘 要: 自中国都市文明兴起,关于农村青年如何融入都市的问题得到许多作家的重视。在三十年代以“骆驼祥子”为代表的青年奋斗失败标本,展现底层青年在社会中苦苦挣扎的辛酸图景。七十年代的高加林逡巡于城乡之间,反映出改革时期农村“知识青年”的两难选择。到了新世纪,时代迅猛发展,青年的出路问题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要命题之一,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身上,折射除作家对于农村青年奋斗的关注,也反映着底层青年寻找出路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 底层青年 出路 困境 陈金芳
一、青年的出路与陈金芳的出路问题
文学家对于青年的塑造方式不尽相同,各类青年形象构成现当代文学长河中耀眼的存在,他们或是意气激昂的启蒙者,或是追求性解放的零余者,或是被“文革”等特殊时期耽误的知青……本文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底层青年身上,以陈金芳为代表探讨他们在努力融入“上层社会”过程中采取的手段和结局。
陈金芳一出场就是一个“长得挺磕碜”的形象,是城市中的“他者”,同学故意孤立她,攻击她。但石一枫却让她使尽浑身解数留在北京,为她的出路挖掘尽量多的可能,最后喊出了当代农村青年想要“活得有点人样”的追求。陈金芳初识都市繁华后再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为了留下来她不惜与家人决裂,与顽主为伍,以身体为资本继续自己在北京的生活。
石一枫在采访中说过“创作的最大经验就是能把个人叙述的风格与作家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底层青年与家人的彻底决裂初步彰显出生命中的原始强力,他们在融入都市过程中爆发出不可遏制的决心。问题的关键在于“她们”留下来之后是否有出路,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老舍对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注。老舍在《骆驼祥子》通过刻画一位由农村进入都市的青年人:祥子,展现20世纪20年代底层青年进入城市以后的出路问题。老舍曾对人讲过“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1]”,而且《駱驼祥子》还是老舍“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可见老舍对“农村青年出路问题”的重视。
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音乐”和“美好的女性”具备拯救人性的力量。小说中多次介绍陈金芳和音乐的缘分,文中的“音乐”被陈金芳看成摆脱俗气,进入上层的主要出路。陈金芳第一次接触音乐是因为“我”每天被家长逼着在楼上练琴,而她晚上就站在楼下的树下听琴声,几乎“每晚必到”。这个时期的音乐启蒙奠定了陈金芳对于北京都市生活的向往,导致来自农村的陈金芳头也不回地选择留下,即使付出巨大代价。几年后陈金芳生活有了起色,“每逢北京有话剧、音乐会之类的演出都会去买票”,后来竟然为了买钢琴而和未婚夫彻底闹掰,多年后“我”与陈金芳的相遇也是在小提琴师伊扎克·帕尔曼的音乐会上,此后陈金芳混迹于各种“艺术圈”,声名鹊起。此时的她已经完全“蜕变”成为一个优雅,健谈的“成功人士”。
陈金芳沉迷音乐并且急迫地想借此成为“贵族”,对于她而言,音乐是自己走进都市社会的出路。21世纪的中国市场,各国资本大量涌入,阶级日益固化,对于白手起家的农村青年而言,想要融入“上层社会”难上加难。陈金芳看到“艺术圈”鱼龙混杂的现状以及巨大利益,不惜铤而走险,装神弄鬼,直到残酷社会将这条出路彻底堵死。石一枫的底层叙事促使读者对现代制度的反思,正视阶级固化的今天底层青年越反抗越绝望的现实,质疑都市进程中的“乌托邦”是否早已幻灭。作家曹征路曾说“底层叙事……是我们大家为了寻求文学精神,寻求真善美的统一叙事,它不存在谁为谁代言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的叙事。[2]”
祥子在20年代的出路是凭借自己的奋斗获得属于自己的车以及安稳的家庭。老舍为小说搜集大量素材,以文字介入现实,探讨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无论精神所寄托还是转移注意,都能使生命能量得到发挥。[3]”这就意味着,个人的精神寄托最大的特点是使得生命力量得到发扬绝非被削弱。对祥子而言,买车既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他的精神寄托,在这个过程中他努力即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他对于自己身体极为自信和爱护,“不抽烟不喝酒不去白房子”,信奉“天道酬勤”的朴素观念,相信拥有自己的车“只是时间问题”。
时代给了“祥子们”一条看似光明的出路,依靠自己的身体获得在城市中立足的机会。祥子们带着对城市的美好期待进入城市,秉持乡间的伦理法则,寄希望于奋斗带来的改变。但是老舍并没有因为祥子的朴实而安排给他一个美好的结局,而是让他堕落成一个“个人主义的陌路鬼”。毫无疑问,时代斩断了祥子想安定生活的出路,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必然,也有祥子自身的原因。虽然祥子的身体进入了都市,但是他的思想却停留在乡村观念中,支配他行为的依然是传统价值观念而不是现代都市契约精神。第一次丢车是由于好面子。他明知道兵荒马乱跑车危险,但是听到别人喊他“大个子”,他便觉得不能辜负这份赞美,硬着头皮去做生意。第二次丢车很大程度由于他对于都市契约精神的怀疑,没有听从别人建议把钱存进银行,选择把钱藏在闷葫芦里,最后被孙侦探洗劫一空。
在我国大变革前夕,社会矛盾错乱交织,农村和都市经历着变革与守旧,创新与顽固的激烈角力,这种背景下的底层青年的奋斗无疑带着浓厚的时代特色。高加林作为70、80年代的农村青年典型,展示了时代带给个人的出路和困境。高加林具备强烈的进取心,有远大的理想,他不甘于像父辈一样过着贫苦窝囊的日子,努力冲破周围的封建愚昧与落后。当他有了晋升的机会时,他能够用自己的才能胜任工作,成为“县城里的红人”,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些体现出新一代农村青年的共同特征。高加林始终以一种战斗的姿态迎接他憎恶的农村陈旧传统道德观念的猛烈冲击,他公然自由恋爱,为井水漂白,鼓励爱人刷牙,周围人的不理解反而激发他的倔强。作者路遥在谈《人生》的创作时说:“我日益感到,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的现象越发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高加林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里农村觉醒的对理想生活有追求的一代新青年的典型。时代向他们昭示着变革的出路,在这个看似充满机遇的改革背景下,他们努力挣脱农村束缚、满怀自信地站出来迎接挑战。客观来看,高加林们的思想动机中还存在着不纯的杂质,内心崇拜现代文明,但是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文明什么是资本主义文明,他们有强烈的欲望、野心,即使知道农村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却千方百计想逃离家乡,一心飞往大城市。高加林最后的结局是回到农村,失去了爱情和都市生活的资格,这一代青年想要进入城市的“出路”再次被现实证明行不通。
二、青年的困境与陈金芳困境
“底层青年”绵延于中国文学史中,其中底层青年的奋斗及其失败的终局即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也是缠绕作家身心的挥之不去的梦魇。有研究者指出:“社会纵向流通日益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精英发生发展机制已由改革初期的精英循环为主变成精英复制为主。[4]”作家安排给底层青年的困境也许过于残酷,但却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世间已无陈金芳》不同于一般小人物奋斗最终失败的套路,在陈金芳悲剧的内核出包含着可悲又可笑的内涵。可悲是因为陈金芳的努力不过是想活得有尊严一点,可笑的地方在于她被这个时代追求的“成功”的风潮所裹挟,一心在功名之路上狂奔,而这并不能真正活出人的尊严。作者石一枫所构思的陈金芳这个人物参照着新时代的变化给小人物带来的巨大影响,直面青年遭遇的精神难题。在展示底层青年的奋斗时,作者既看到市场的机遇,肯定人物的“勇于站在时代前面”的魄力,更强调梦想失败的必然。石一枫以现实主义手法,塑造新时代青年的典型,借此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困境。
最终陈金芳选择剑走偏锋,非法集资,靠骗取熟人的钱完成资本积累,最后功亏一篑。陈金芳在乡下利用了“熟人社会”,就是所谓的“杀熟”[5]。她彻底破坏了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中。陈金芳有着具体的理想,她不仅要留在北京,更要成为有尊严的城市人,她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她实现目的的手段是错误的,她在道德领域洞穿了底线。而她的急功近利和非法方式恰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難题,“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式微了……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这也是作家对时代和社会所应该负担的责任。[6]”这就是石一枫文学创作所坚持的价值观。
高加林和陈金芳是不同的,高加林对于农村的厌恶建立在对城市的美好幻想之上,可惜的是他是在一个相对“抽象”的意义上憧憬都市生活,这里的“都市”并不具体,因为总体来说高加林没有现代物质的概念,思想里也没有拜物教,属于“理想化”的进城向往。这些必然导致后来的种种悲剧。马克思曾经指出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高加林出身农村,却是个“知识人”,是一个思想复杂的人物形象,他一心觉得凭借自己的能力可以进入美好的都市,却不断遭遇现实生活带给他的巨大冲击。在工作中,自己的教师岗位被人走后门顶下去,在爱情中,为了更好的出路选择城里的女生最后失去自己真正的爱人,在晋升中,好不容易凭借自己的辛劳工作可以获得去南京的机会却东窗事发,自己不正当上岗的事情被揭发出来……
不难发现高加林本身道德和思想都存在着劣根性,但是社会历史的原因不容忽视。首先应该看到知识青年在农村所做的事情哪怕再微小都会引起众人一致的打击、反对,让新一代青年人看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强大的保守势力,必然产生逃离的念头。另一方面,高加林工作出色却被顶替反映出来中国改革时期制度方面的混乱现象依然触目惊心,提醒社会改革一切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环节,推动社会进步,避免“高加林困境”再次上演。
祥子的悲剧源自不彻底的“个人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内在制约,是双重不彻底导致的悲剧。祥子的精神独立并非建立在个体独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车夫拥有车的基础上,也就是物资满足层面,这个完全不同于个人主义者追求的“平等”“自由”。另一方面,祥子在职业的选择上出于自我本能的片面选择而非来理智的分析,导致后来行为的局限和盲目。其次,祥子缺乏对身体本能的正确认识,主要体现在两性关系觉醒后的精神异常[7]。祥子刚到城市中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恋”,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这唯一的资本上,“有了这结实的身体”,买车只是迟早的事,于是祥子一刻也不休息地拉车,“从东边到西边”,对身体的过度开发使之面临着不可逆的伤害,但是祥子没有意识到。吊诡的是,祥子与虎妞发生关系以后,瞬间失去对身体的自信,无法正视自己身体内的欲望,把一切归结为虎妞对自己身体的勾引。这说明祥子建立在自己身体上的自信脆弱敏感,而虎妞的出现不过是加速了这种危机的爆发。最后,祥子的失败很大程度上由个人奋斗理想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导致的。祥子在用尽全力挣钱买车的时候,洁身自好,作息规律,人际关系却一般。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并没有赢得周围人的尊重和重视,他们甘心于浑浑噩噩的生活。可是后来祥子堕落下去甚至染上性病的时候,周围的车夫却主动关心起他,为他提供解决的方案。在个人的价值和奋斗被漠视的时代,个人需求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祥子的困境带着必然性。
由此可见,不彻底的“个人主义”不是祥子悲剧的主因,是“祥子们”主动或被动地浸没在漠视个体生命价值的传统文化中,无法正视自身的欲望,人生追求得不到环境的支持,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
三、还原现实与石一枫的现实审美理想
不同年代的作家群体在创作中往往显示出鲜明的代际差别和不同审美选择。50年代出生的作家通常会自觉地背负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积极探讨现实的巨变和对历史的反思,宏阔开放的视野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写作的必要条件[8]。”以莫言、王安忆、韩少功为代表的50后作家充分显示出这个群体的追求。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对宏大历史或现实场景的正面书写,而代之以明确的个人化审美视角,着力表现个体生命的存在际遇,力图传达对于人性景观的纤细感受,例如,苏童、余华。石一枫属于70后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几乎不愿涉足历史,他们专注于当下生活的书写,现实秩序显然不再是创作的唯一参照,70后更多地依赖于创作主体的感性经验。戴来的《恍惚》,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魏巍的《化妆》等作家作品具备鲜明个人特色以及迷恋于都市生活经验的审美表达。
石一枫作品中烙印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同时也要“王朔”的影子:玩世不恭的态度,一口京片子,以油滑笔调结构世俗社会的新秩序……但是石一枫绝不是“王朔第二”,他在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不回避社会真相,还原惨烈现实。石一枫对于自己身处的环境有着敏锐的观察,用看似不正经的语言叙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却在骨子里流淌着作家本人对社会的真诚深刻的关怀,专注于书写当下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世间已无陈金芳》作为石一枫名气最盛的作品,体现出作者“还原现实”的审美理想,接下来以此文本为讨论中心。
石一枫擅长从一个小的切入点入手去针砭时弊,辅以玩世不恭的腔调,看似在回避,实际上是以小见大。批评家刘复生说过“没有思想深度与力量,就没有伟大作家……所谓思想,并非存在于艺术性之外可以抽离的部分它直接就是艺术性的内在构成因素,甚至是它的最深的动力源泉。[9]”《世间已无陈金芳》构成作者对于个人命运和社会环境的思考,在陈金芳这个“美好女性”身上,承担着中华女性勇敢、倔强的性格因子,她百折不挠、迎难而上的战斗精神凝聚成极富象征性和历史深意的原型,负载着深刻的历史反思。石一枫注意到新时代底层青年的精神特征,以文字介入社会改造,质疑“城市化”的今天“阶级固化”带来的冲击。在还原现实的过程中,石一枫采取的叙述方式看似是荒诞、夸张、油滑的。小说中多次出现插科打诨的贫嘴,对功名利禄的嘲讽。“大家装X都装得很在状态,就不需要我煽风点火了”、“这个画家创立了‘立体现实主义的政治波普这个流派——代表作是发廊小姐光着屁股学理论”、“这女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活好!”……小说中常见的“痞子腔调”以带有强烈性意味的粗俗语言狂欢,解构世间一切或真或假的“体面”,充满对社会与他人的恶意,似乎缺乏宽厚的理解和同情。但是一个作家特别变现出粗俗和刻薄的时候,往往隐藏中内心是症结。贺绍俊曾评价石一枫,“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用戏谑的方式去处理崇高,而不是否定崇高;他用民主的方式去迎接英雄,而不是颠覆英雄。”石一枫在小说中表现出的“混”正是源于对世人道德水准的极度失望,甚至塑造出无所事事的“我”,或冷眼旁观或插科打诨,调侃功名之路上疾驰狂奔的世俗人物,适当缓和作者的批判意识。
石一枫对于现实道德的关注可见其思想的力度。他的小说语言机智,可读性强,与读者保持平等姿态,但他最着力的地方是对既定价值观念的松动,同时不断接近惨烈的现实真相。在石一枫的书写中,所谓的艺术家都是“装X货”,周围的朋友听着音乐会却悄悄讲黄段子,最可悲的是这个时代没有给底层青年以向上的希望,陈金芳最终失败的宿命与祥子、高加林的结局遥相呼应。正如鲁迅所谓“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或许石一枫达不到鲁迅拯救国民性的深刻,但是其针砭时弊的创作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底层青年的形象一直存在于文学史中,他们身上凝聚着中华典型的民族性格,反映不同时代社会环境对个人奋斗的影响,体现不同作家的文学理想。就目前而言,而对于底层青年最终的出路问题却没有得到最完整的解答,这与作家自身的思考力度有关同时也和不同时代下标准的变动有关。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到现实中底层青年的出路与困境,但来自农村的青年能否成功融入都市的问题依然需要更多的反思与质疑。
參考文献:
[1]陈思和.《骆驼祥子》: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5-16.
[2]曹征路.文学精神的迷失与时代困惑[J].探索与争鸣,2006(08):14-15.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461.
[4]张群梅.当前中国阶层流动固化趋向与治理路径分析——基于集团分利视角[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34-39.
[5]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J].文学评论,2017(04):174-186.
[6]孟繁华.在现实与不那么现实之间——近期中篇小说的新突破[J].文艺争鸣,2016(04):140-146.
[7]魏家文,叶文敏.论“骆驼祥子”失败的文化根源[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27(07):1-4.
[8]洪治纲.再论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及划分依据[J].当代文坛,2013(01):10-15.
[9]师力斌.思想力和小说的可能性——从石一枫、蒋峰看70后、80后小说[J].创作与评论,2016(22):4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