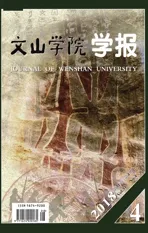万历年间文人的俗文学活动
2018-03-07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一、万历文人对俗文学的态度
万历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俗文学的兴盛奠定了现实基础,俗文学种类繁多、形式多变,富有民间风趣,吸引了大量文人的注意。文人们对俗文学表现出赞赏、反对和兼容的不同态度,体现出他们审美趣味的转变。
(一)赞赏派
《二十四桥风月》中记载了诸妓唱小曲娱客的场面,“发娇声唱《擘破玉》等小词”[1]51,反映出民歌在市井流传之广。随着文人向民间的趋近,俗文学逐渐突破民间的局限,成为文人阶层和市井大众共同欣赏的对象。比如张岱记载“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1]45,发源于里巷市井的民间小唱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受到文人的青睐。
冯梦龙是晚明的通俗文学大家,搜集整理了民歌集《挂枝儿》《山歌》。他将民歌视同于《诗经》中的《国风》,称其源于人民最真实的情感,具有不同于诗文的独特价值,虽然语言有粗鄙之处,但却真挚自然,故而辑录以传世。这一见解也得到其他文人的响应。沈德符描绘了民歌传唱的盛况:“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2]可见民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文人有意的选择整理,将民歌集刊刻成书,其流传的地域更广、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进一步加大。沈德符记载了民歌从宣正年间至万历年间的发展状况,体现出文人对民歌逐步加强的关注过程,反映出明代文人自觉地向民间性靠拢的意识。主张“性灵”的公安三袁同样是民歌的爱好者,他们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民歌的身影,比如“家家开老酒,只少唱吴歌”[3]361等诗句,甚至作诗打趣楚人不懂吴调,云:“一片春烟剪縠罗,吴声软媚似吴娥。楚妃不解调吴肉,硬字乾音信口吪。”[3]894明代文人仍有蓄伎为乐的传统,袁宏道曾有寻找歌伎的记录,云“有新到吴儿善歌,可急来”[3]1634,听唱民歌成为明代盛行的社会风气。卓人月将民歌作为有明一代的代表文体,曾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 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纽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4]
冯梦龙另有散曲选集《太霞新奏》,散曲选择的标准同民歌一样,要求“发于中情,自然而然”[5](15)11。曲,是明代影响较大的另一种俗文学体裁,无论散曲、套数还是戏曲,都有明显的文人参与痕迹。文人听曲、观戏、评戏、作曲,提高了曲的文坛地位,增强了曲的社会影响。曲的创作经历了从民间艺人到书会才人再到文人大夫的转变,是民间性和文人性融合的产物,得到大众和文人的共同认可。明代是文人辑曲、作曲的高峰期。沈德符《南北散套》中提到的明代曲作家就有李开先、梁伯龙、张伯起等数人,到了万历年间不仅形成了以沈璟、汤显祖为代表的曲作家群体,更是出现了王骥德的《曲律》和吕天成的《曲品》两部戏曲理论专著,它们合称为曲学“双璧”,是万历年间出现文人论曲高潮的象征。沈德符在其著作中也对《太和记》等戏曲作品进行评价,足见对于戏曲的关注。明代刊刻、印刷技术的成熟以及出版行业的兴盛也为俗文学传播做出了贡献。女性出版家周之标辑录出版了曲选集《吴歈萃雅》,而其出版的原因是由于时曲具有“真”的特质。无论是民歌、戏曲还是其他俗文学体裁,都具有着质朴自然的艺术特色。
(二)反对派
万历年间,俗文学的发展得到大多数文人的支持与肯定,不过其中仍然存在反对的声音。
张瀚就是这样一位代表。《风俗纪》中记载了明代晚期搬演传奇的盛况,富贵人家出资置办表演所用的服装、道具等物品,准备演奏乐器,组织人员进行搬演。戏曲演出不仅成为消遣娱乐的方式,更是富人相互攀比的重要手段。在一个郡城之内,以此谋生者不下数千人。词语的淫丽华靡形成放荡的社会风气,人们皆以此为乐。张瀚不耻这种社会现状,对此持否定的批判态度,称“余遵祖训,不敢违”[6],表达对此的不满。
顾起元也是俗文学的反对者之一。《客座赘语·俚曲》中列举俚曲凡十四种,但认为其只能够流传于民间,称其为“里巷童孺妇媪之所喜闻者”[7]204,否定其文学价值。在顾起元看来,俚曲虽然音调优美,然而语言鄙俚不堪,颇有郑卫靡靡之风,内容多为男女之情,有引导淫欲之嫌,民歌的广泛传唱不是盛世应有的景象。《古词曲》中,顾起元再次强调这一观点。《古词曲》罗列了以闾巷歌曲采入乐府的情况,分别为晋南渡后吴声歌曲二十一种、神弦歌曲十一种、西曲歌二十一种、杂曲歌辞五种;宋吴声歌曲三种、西曲歌六种;齐西曲歌两种;梁鼓角横吹曲十八种,凡八十七种。这些乐府正如明代《干荷叶》《打枣竿》之类的民歌一样,内容不出儿女之情、闺房之乐、思妇哀愁,因故将其划入李延寿所说的“亡国之音”[7]213的行列,对其鄙夷之情可见一斑。在戏曲方面,顾起元认同明初的国家政策。《国初榜文》中收录了明初颁布的关于戏曲的六道榜文,将戏曲视为低贱的行业,严格控制戏曲演职人员的穿着打扮和日常行为,对于违规者的惩罚力度极大。除此之外,在创作内容方面也进行限制,全面压抑了戏曲的发展。顾起元认为应“遵行律诰”[7]232,反映出对戏曲的不屑态度。
稍晚一点的钱谦益同样不赞同俗文学活动,这一观点出自其对母亲的记载。钱谦益认为他的母亲是一位颇有仪法的女子,符合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而其特点就是谨守礼法,不随意嬉笑、不施过多粉黛、不穿绫罗绸缎,并且“目不识优倡妖尼,耳不听吴歌瞽词”[8],即不观看戏剧演出、不听民歌和鼓词。这样的女性是被传统士大夫所称赞的。由此看出,钱谦益对俗文学也持有反对态度。
部分文人反对俗文学的现象也被支持者所察觉,冯梦龙《叙山歌》中称民歌是“荐绅学士家不道也”[5](42),故而不能称之为“诗”,而给其起名为“山歌”,但其确有诗所不具有的独特价值。谢肇淛对此进行详细阐述,认为“亡国之音”是不切实际的说法,孔夫子所说“郑声淫”并非指郑卫皆是有关男女私情的音乐,而是指这些音乐华艳巧丽,过于欢乐,后人把“淫”单纯理解为“淫欲”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圣人以为这些音乐不够庄重典雅,不适用于郊庙祭祀,故而不倡导学习。亡国的原因不是由于音乐华靡,假使《招》这样的雅乐出现在齐国,也不会改变齐国灭亡的结局。因此,郑国的覆灭是由于国家统治的失败,并非是音乐招致了祸乱。唐代的宋广平喜欢羯鼓,宋代的寇莱公善舞《拓枝》,但二人仍以刚正被世人所熟知,喜爱音乐并不妨碍他们的严正清明[9]230。谢肇淛通过对圣人之言的分析和历史故事的列举论证了音乐不能造成亡国的观点,凭此抨击了张瀚、顾起元等人对俗文学的批判态度,反映出万历年间文坛自由热烈的讨论风气与开放旷达的文学理念。
(三)兼容派
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采用儒家思想治国,宣扬仁义礼智,标榜节义孝悌,而在处事方式上则奉行“中庸之道”,讲求中正和善,统筹兼顾。使用这样的思想观念培养起来的文人自然也贯彻着中庸思想,力求不偏不倚,兼采众长。不同于前两派旗帜鲜明的认可或反对,兼容派努力取长补短,肯定其积极部分,而剔除其消极部分。王骥德和屠隆就提出了“兼容并蓄,雅俗并陈”的理论观点。
王骥德追溯戏曲源头,从帝尧时期追溯到明代,表现出音乐不断丰富发展的变化过程。他讲到明代南北曲兴盛,且南北各有小曲,北方有《粉红莲》《银纽丝》《打枣竿》数曲,南方有《山歌》《采茶》数曲,流传日广,这些小曲“不啻郑声,然各有其致”[10]56,听起来仿佛郑卫之声,批评其音调华靡,但却别有趣味,肯定其民间特色。王骥德在戏曲理论中同样秉承着中庸思想,面对格律和文辞孰轻孰重的问题,提出“大雅与当行得间,可演可传”[10]137的观点,即语言和格律相互配合,既能适用于案头阅读,又能满足场上表演的需要。这样的戏曲理论成为万历年间的主流思想,文人不再标榜清高,不屑于与民间为伍,反而能够自觉面向民间大众,迎合他们的需求,因而俗文学得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屠隆是民间歌谣的爱好者,他认为那些流传于民间、传唱于学识不多的野人里妇之口的歌谣“而机弥天,而音弥真”[11]183,天真活泼、自然风趣,故而能够得到统治阶级的注意,派遣专员进行走访辑录,并由圣人进行筛选。因此工于雕琢的诗句不一定比民歌更有价值。在《章台柳玉合记叙》中,屠隆提出了他的戏曲理论,称“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11](5)183,可谓精炼到位,鼓励使用民间的俚俗语言。正如同民歌一样,在戏曲创作时使用民间语言也可以达到使情感表达自然生动的效果,即“谐俗”的要求。顾及到戏曲创作的文人性,也强调对词语的适度修饰。总体而言,要使得雅俗平衡,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
由此看来,万历年间文学氛围浓厚,文人们对俗文学的注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俗文学没有得到全部文人的支持,但他们对俗文学的欣赏和品评进一步促进了俗文学的发展,也使得俗文学从民间走向文坛,在文人们不断的探索中,戏曲逐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俗文学文体都得以保存和流传,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万历文人的俗文学活动
万历年间,文人对俗文学的关注不止步于评价俗文学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更进一步主动地参与到俗文学活动中来,表现为记载、辑录、创作的不同形式,使明代文坛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独特面貌。
(一)记载
俗文学活动的记录多出现在笔记和文人文集之中。张瀚《松窗梦语》记载了明代民众喜听民歌的风俗,并指出江南三吴之地最为富庶,其民歌传唱也最为盛行。顾起元《客座赘语》罗列了众多民歌曲目,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列举民歌十六种,并记载了《挂枝儿》《山歌》的传唱盛况。这些都是关于民歌盛行情况的记载。
谢肇淛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他在《五杂俎》中记录了南北曲演唱中使用的不同乐器。演唱时,民间多使用觱篥、笙、箫、钟鼓等乐器,且南北有异,南方多使用觱篥而北方多使用箫筝。除此之外,音调也有南北之别,分为近雅的浙操和近俗的闽音,故而浙操多为士君子赏识,而闽音则多为民间喜爱。同时记载了擅长弹琵琶演口技的盲人演奏者及可同时演奏多种乐器的民间艺人,可见谢肇淛对民间的关注与喜爱[9]230。
张岱及其友人则亲自参与到民歌和戏曲表演的行列中来。《陶庵梦忆》中记载“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1]45,在不系园的这次集会中,彭天锡、罗三和杨与民一道表演了本腔戏,楚生和女伶陈素芝一同表演了调腔戏。文人从单纯的欣赏者逐步转化为参与者,弹琴唱曲、观戏唱戏都成为文人日常的娱乐活动。
此外,文人的文集中也不乏关于俗文学活动的记载。屠隆《白榆集》中有《长安元夕听武生吴歌》一诗,描绘了武生唱吴歌的生动场景:“初疑绛河响流月,再听泠风舞回雪。欲换故迟声转媚,繁音已尽意不歇。”[11](3)65给予武生吴歌高度的赞美,认为人生在世定当闻此歌声才不致虚度。屠隆同张岱一样,不仅观赏艺人演奏,自身也乐在其中。《栖真馆集》中记载了同王伯谷聚会的故事,屠隆记载自己“兴到,则口讴下里曲”[11](6)375,随口唱出当时流行的民间小调。旁边有一少年打鼓、吹笙为其伴奏,亲朋欢聚一堂,宾主各尽其兴。可见,与以往诗文会友的传统方式不同,文人相会也加入了流行于民间的唱曲等活动,表现出文人和市民的趋同性。屠隆自身也是一位戏曲创作者,不但形成了独特的戏曲理论,还创作出了《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等戏曲作品。邹迪光在《郁仪楼集》中记录下曾和屠隆一道观赏《昙花记》的故事。由于文人的特殊性,观戏时不免加入自身的思想感情,邹迪光就产生了戏如人生的慨叹,由观戏引申出生命无常的思考,正如其所说:“睹彼傀儡,念我肉团;听曲一声,胜似千偈。”[11](12)285民歌、戏曲等俗文学形式不仅仅有着娱乐的作用,更是寄托文人情感,表达文人思考的重要手段。
袁宏道则记录了虎丘中秋夜之时歌者竞唱的盛况。中秋之夜,无论市井小民,亦或文人仕女,纷纷云集虎丘。在此进行表演的歌唱艺人不下千百,他们的技艺能够使“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之下泪”[3]157,颇似韩娥演出的盛况。万历年间,民风开放,娱乐活动丰富,文人不再严格地与大众划清界限,反而主动地融入其中,在世俗常见的活动中获得乐趣。袁宏道文集中也有“丙子,宴于秦藩,乐七奏,杂以院本、北剧、跳舞”[3]1489的记载,戏曲演奏同歌舞表演一样,获得文人阶层的赞赏,无论在宴会场所还是日常生活中,俗文学都受到文人的欢迎,并得以蓬勃发展。
(二)辑录
在俗文学辑录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冯梦龙的两部民歌集《挂枝儿》《山歌》。冯梦龙的散曲选集《太霞新奏》,不仅收录了套数、杂曲、小令等内容,还附有其对曲的认识和理解,包含了作曲方法及曲坛掌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周之标有曲选《吴歈萃雅》。这些作品是研究明代俗文学的重要资料,反映了万历年间文人的创作倾向和审美标准。
综合来看,文坛认为俗文学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真、情、俗三个方面。冯梦龙《太霞新奏序》中明确批评文人卖弄学问、使用晦涩难懂的书面语进行戏曲创作,以此彰显自身才华的做法;戏曲的创作者不懂音律,使得作品不能用于表演而无法流传;戏曲的表演者不懂创作,容易使作品流于粗鄙之列。冯梦龙选取词语通俗易懂且不违背音律的作品进行辑录,将其命名为“新奏”,希望为词曲创作提供新的范式。而他选择民歌的标准则以“真情”为主,以真情打破所谓学士大夫的虚伪面具,真实不造作的作品才是历经千年而不灭,值得保存和流传下来的经典。周之标同样认可这一观点,她关注到数代以来的文人学士皆以做好八股文章,以求加官进爵为目标,全部精力都用以辞赋、诗文创作,以致时文出现用词艰涩、滥用典故、磨灭真情的弊病。但曲是一种不同于这些体裁的文体,它近乎歌谣,要求清丽婉转,真挚动人。周之标认为这样的作品比烂时文更有价值,故进行辑录,明确提出辑录的标准是“余论时曲,而惟取其情真境真,则凡真者,尽可采,不问戏曲时曲也”[12],表现出万历年间文人对于“真”的追求。周之标身为女流之辈,能够从事词曲选编、书籍出版的工作,在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万历年间思想和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止周之标,在《全明散曲》中也收录了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社会观念的进步、道德束缚的削弱,使得明代成为俗文学生长的沃土。
(三)创作
除了收集整理之外,文人也亲自进行俗文学创作,涉猎文体丰富。
民歌方面,主要以汪延讷、冯梦龙为代表。汪延讷著有《山歌二首》:
齐云云起接黄山,山上花开黄白间。曾见仙人骑鹤去,一声碁响复飞还。
春女春来春谷游,三三两两笑藏钩。折取娇花比颜色,一声齐响误回头。[13]
这两首山歌使用了“三三两两”等通俗化的口头语言,明白简质,通俗易懂。景物描写质朴自然,以黄、白两色山花覆盖的黄山生机勃勃,而对民间日常生活场景的描摹更是生动活泼,别有趣味,深得民歌精髓。冯梦龙辑录了《挂枝儿》《山歌》两本民歌集后,更采用顶真的修辞方式,创作了新的民歌样式《夹竹桃顶真千家诗山歌》,它是民歌和诗的结合,将雅俗的特征共同集中在一种文体上,是文学体裁方面一种新的尝试。
散曲方面的创作不胜枚举,《全明散曲》收录的万历年间散曲作家达百余位之多。散曲创作的语言多趋向口语,通晓易懂,即使有用典的情况,选用的多是为大众熟知的典故,基本达到老妪可解的要求。如沈璟【南仙吕解袍歌】《代友怀人》小令中有“不眠不睡。日长夜长。不言不语。情长恨长。不明不白多磨障”[14]3250的语句,虽然使用的全然是民间的口头语言,但“不……不……”的词语结构增强了人物的情感体验,将对对方日夜思念、如痴如狂的状态刻画的入木三分,后面“撇不了。凑不双。浑如撞入打毬场。说不尽。意不防。争些两地忽参商”[14]3250一句也使用了这样的创作方式,虽然使用“参商”比喻双方分离两地不得相见的状态,但这个典故在民间也广为流传,不会妨碍大众对作品的理解。
除了汤显祖、沈璟、王骥德、施绍莘等主要从事词曲创作的作家外,以诗文创作为主的袁宗道也作有【北南吕一枝花带折桂令】小令一首:
秋风高挂洞庭帆。夏雨深耕石浦田。春窗饱吃南平饭。笑先生归忒晚。明朝已是三三。雕虫呵懒拈象管。野鹿呵难聊鹿班。隙驹呵且养龟年。嫩柳成园。修竹围庵。讲什么道非道梦中的老聃。说恁么空非空纸上的瞿昙。只消过了寻常甲子万万千千。[14]3324-3325
“忒”、“呵”、“恁么”等模拟民间口吻语言的运用,体现出作者的情感态度,并且使作品具有了常俗自然的特点,活泼俏皮,增添了趣味性,描绘出闲趣惬意的田园生活。这首小令语言通俗,即使里巷小民也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并且描绘的就是民间常见的田园生活,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达到了俗文学俚趣自然的特点,能够体现万历年间曲作家的创作追求。公安派在诗文方面的创作主张和俗文学有相似之处,也反映出万历年间文人创作的新趋向。
戏曲方面,出现了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两大创作群体。汤显祖以《临川四梦》的创作闻名天下,《牡丹亭》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沈德符有“《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15]的记录,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临川派另有阮大铖《春灯谜》、孟称舜《娇红记》等作家作品。沈璟则著有《属玉堂传奇》十七种,成为吴江派的领袖。顾大典、吕天成、冯梦龙等人均是吴江派的戏曲作家。在戏曲创作之外,曲律、曲论也成为文人关心的对象。沈璟强调戏曲创作中的格律文体,编纂了《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另有曲论《唱曲当知》等著作,今已不存于世。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凌濛初《南音三籁》及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都是关于戏曲理论的著作,规范着戏曲创作的语言、格律、关目结构等内容。曲的创作在明代达到高潮,成为文人普遍使用的创作体裁。在论曲、作曲的反复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戏曲理论,成为戏曲创作和鉴赏的统一规范。
万历年间,小说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成书于万历年间的《西游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形势。冯梦龙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凌濛初两部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虽然刊刻于天启年间,但其在万历年间已经开始整理创作。“三言两拍”从宋元话本发展而来,是宋元“说话”技艺从口头转向书面的表达形式,部分故事也出自宋元旧篇。话本是说话人讲演故事时所使用的底本,故事题材多采自历史传奇、社会现状, 因其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是民间大众的缘故,其语言均为民间口语,即百姓平时生活中所用语言。白话小说继承了话本的这些特点,文人逐步从对其的整理加工走上独立创作的道路,除了帝王将相、神仙鬼怪、文人学士、才子佳人的故事外,也包含着一些民间故事,如《醒世恒言》中有《李玉英狱中讼冤》《徐老仆义愤成家》的故事,《警世通言》中则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的故事,《拍案惊奇》中开篇便是《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故事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物形象的选择也丰富多样,尤其是对奴仆、妇女、妓女等弱势群体的关注更能够体现出文人的社会关怀。在语言使用方面,全部采用白话进行创作,是对传统文言小说的一次突破,体现着万历年间文学创作的通俗化趋势。
除了文体上的创作,对民间艺人的关注也是明代文人的一大特点。出生于万历年间的说书艺人柳敬亭就得到许多文人的赞赏,钱谦益曾为其创作诗歌和传记。描绘其高超的说书技艺时,钱谦益有“吹唇芒角生烛花,掉舌波澜沸江水”[16]7-8的诗句,并且认为说书的职业非常值得尊敬,可以载入史册、流传千古,“此时笑噱比传奇,他日应同汗竹垂”。[16]8虽然人们将听书作为调剂生活的娱乐手段,但其中讲述的历史故事值得深思,也是向民间大众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故而有“千载沉埋国史传,院本弹词万人羡”[16]8之句。同时,钱谦益认为柳敬亭的盛名不亚于鼓词《蔡中郎》,两者难较伯仲,“盲翁负鼓赵家庄,宁南重为开生面”。[16]8-9钱谦益还有《书柳敬亭册子》一文,盛赞柳敬亭的说书技艺,将其与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艺人优孟比肩,认为其具有劝诫世人的社会功用,故而大加赞赏。柳敬亭在明代盛极一时,其他文人也为其写诗作传,如张岱著有《柳敬亭说书》、吴伟业和黄宗羲各自创作了《柳敬亭传》、周蓉则撰写了《杂艺七传·柳敬亭》,足以见得文人对俗文学的认同以及对民间艺人的尊敬。
俗文学成为万历年间联系在民众和文坛之间的一根纽带,文人的参与使得俗文学获得更为长久的生命力,而文坛对于俗文学俚、情、真等特点的保护也使得俗文学能够持续在民间传播。通过民间传唱和文集刊刻的方式,俗文学得以长久的流传和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