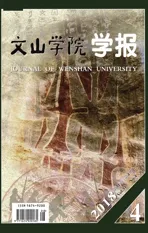英雄史诗与图像攀附
——作为族群记忆载体的大王岩岩画
2018-03-07张傅城黄亚琪
张傅城,黄亚琪
(1.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1;2.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大王岩岩画,因其图幅色彩、空间结构和包括人形岩画在内的丰富图像元素,成为岩画考察关注的重点。一般而言,在岩画断代、族属考证的研究之外,岩画研究主要是在岩画图像与岩画点当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之间寻找契合点,作出可能的定性解释。从调查收集上来的有关大王岩岩画材料中可以发现,不同的群体对大王岩岩画的文化内涵有着认识上的不同,存在着“傩舞表演”“男女守护”“蓝哥紫妹神话”和“侬智高身影投射”等等说法。当对诸多说法进行辨析时,首先排除大王岩岩画是侬智高“身影投射”的说法,同时可以肯定大王岩岩画与侬智高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时代以及族属关系,但如果我们将“侬智高身影投射说”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下产生的“地方性知识”,通过发现“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叙事框架,将当地人对大王岩岩画的解释放入皇权专制与地方政权消长的历史进程之中,去观察两者在具体历史背景下的关系,就会发现作为文化承载性质的大王岩岩画与当地人在历史意识、族群记忆与文化自觉等维度上的密切关联。
一、“纷繁”中的“地方性知识”
在对大王岩岩画内涵种种说法进行辨析的过程中,笔者实际上感受到大王岩岩画的解读工作目前正处于诸多说法交织在一起的“纷繁状态”,之前的论者更多的是对大王岩岩画的内涵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在诸多争鸣之中,成一家之言。如果我们借助人类学研究中常用的“主位”与“客位”的研究视角,便会发现“傩舞表演”“男女守护”和“蓝哥紫妹神话”等说法基本是从研究者自身的认知立场出发,即是一种“客位”的研究方法,以研究者的解读判断为最终结论,“当地人”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只是“可用的材料”,他们不断地被外在于“地方”的话语书写着。本文采用“主位”的研究视角,从尊重当地人的理念与知识开始,以当地人的价值判断为基准,从而发现岩画“地方性知识”内部的相互联结。
吉尔茨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指的是,研究者在研究异文化时的场位问题,应尝试摒弃研究者—“我者”自诩的“客观方法”,转而重视被研究文化—“他者”的理念与视域,即“理解者对于被理解的客体应持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1]。着重强调了知识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地方社会情境。大王岩岩画是侬智高“身影投射”的说法,植根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并通过地方共同体内部精英主导的历史记忆和纪念仪式及群众的普遍实践,逐渐在皇权专制时期宏大叙事的强压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表述,这体现了均质化的专制统治与地方共同体之间的对张。
官方“胜利者”把控的话语权与当地精英及民众对“失败者”的情感认同之间的巨大的张力,直接导致了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有关侬智高的基本史实是:侬智高是宋代邕州属羁縻广源州首领,宋皇祐二年(1050年)在安德州(今靖西县安德乡一带)建立“南天国”政权,皇祐四年(1052年)四月,起兵反宋。攻占邕州后,建立“大南国”,后被狄青率军击败,身亡[2]。在官方正史的书写体系中,基本将侬智高定性为“蛮寇”“贼寇”“入寇”“寇盗”等[3]。在云南、广西的壮族聚居区,地域文化将侬智高视为族群首领,尤以一种“英雄史诗”般的诉说形式,表明了不同于官方论断的民间立场。其中有关侬智高诸多“英雄史诗”的一种,即被表述为大王岩岩画是侬智高身影的投射。
“壮族说法:‘大王岩崖画’源于当地壮族民间传说,说的是北宋时期的壮族首领侬智高……兵败后,从广南退至麻栗坡县羊角脑山上,被宋军围困山中……传说,侬智高率先跳下羊角脑山悬崖时,太阳刚好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崖壁上。为此,这堵印有人影的崖石,就被叫做大王岩崖画。”[4]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大王岩岩画因本身的命名中含有“大王”二字,因而客体性质的岩画图像在具体历史文化展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地方性的话语表述体系,被动脱离了原本的文化意涵,地方族群依据新的现实需要将其攀附为“大王—侬智高”,同时族群文化成功地将新的意义注入到旧有的图像符号之中。这一做法的本身表明了“自己人”式的共同体内部的情感认同与维持认同的现实需要。
二、英雄何以被记忆
心理学家在探讨“遗忘”作用于个体的机制时,常常引入“干扰”的概念。在这里,笔者对上述研究范围进行扩大,着重说明地方族群在面对外部强压、内部文化变迁等“干扰”因素下“抗干扰”的文化实践,对族群如何拥有共同记忆和维持共同记忆的方式作出讨论。
论及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关键词所在的研究领域,需要提及莫里斯·哈布瓦赫和保罗·康纳顿二位学者奠定的人类群体记忆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型,这一理论观照已成为分析现象与历史之间关系较为理想的研究切入角度。
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先验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逐渐建构出来的概念,关注记忆不断被构建的重要特质。“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5]40。他从记忆领域中区分出历史记忆与自传记忆之间的差别,历史记忆是指主要通过书写记录非个人经验性的事件记忆,可以通过文本阅读、口耳相述和纪念仪式等活动存续下来。自传记忆是对我们在过去所亲身经历事件的记忆,同时自传记忆以集体为意义依托,离开集体的个人记忆是没有意义的[5]51。
保罗·康纳顿的研究工作正如其著作之名《社会如何记忆》,是关于群体记忆、社会习惯如何传承和维持的深化。“哈尔布瓦克斯虽然把集体记忆的概念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却不明白关于过去的意象和对过去的记忆知识,是(或多或少)由仪式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6]38他以社会记忆来取代集体记忆的概念,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作为至关重要的传授行为”[6]40。贯穿全书的核心是,“如果说有社会记忆这回事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在纪念仪式中找到它。纪念仪式(当且仅当)在具有操演作用的时候,才能证明它有纪念性”,更进一步地说,还有比纪念仪式更为广泛,更为基础的“身体社会记忆”[6]82,这也就是重新发现了身体对于社会记忆的重要性。
在引入了相关群体记忆理论后,笔者认为,在历史进程中的文山州当地人群将大王岩岩画攀附于侬智高的文化努力,有其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其一,在“大王岩岩画是侬智高身影像”的攀附中,需要群体内部的文化精英或者长者对建构什么样的群体记忆进行选择,这也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同时康纳顿提醒我们,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是关键的传授行为,但这些绝不是社群记忆的唯一构成成分,“非正式口述史的生产,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也是全部社会记忆的一个特征。”[6]40在“岩画”与“英雄”的联结中,需要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以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的身体作为记忆信息传递的必要构成,群体这时只是完成了记忆信息的制造和小范围传播的工作,主要体现的是口述生产、传播与身体承载的方式特征。其二,如果我们回顾康纳顿提出的维持记忆的两种重要方式,就会发现“身体”并不能解决客体性质的族群记忆在历史进程中对主体有限生命的持续依赖,族群记忆随时会面临淡忘乃至消失的危险。这时,年度复归“纪念仪式”便会发挥其稳固传递和强化记忆的应有价值,并伴以一定的仪式性操演活动。在文山州,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六月节”(或五月节、七月节),便是纪念侬智高的年节性仪式操演活动,以极具象征意味的“花米饭”作为祭品,诉说着“族裔”对“首领”的想象与怀念。具体到麻栗坡县的情况,当地的壮族群众每年农历七月初一来到大王山烧香、祭拜。因而,于历史情境中建构的群体记忆,因有民间信仰的参与,而得以有序稳固地传承。其三,大王岩岩画的人像主体有着类似于“刻写实践”的某些因素参与其中,作为丢失原有意涵的客体可以与新的族群文化相结合,以有一种近似于照片、印刷物的形式对族群信息加以保存,丰富了人们对记忆与介质的认识。另一方面,除了族群文化主动创造的记忆生产、传递和存储介质之外,大王岩岩画也使我们看到它作为族群记忆整个过程中的一环,岩画图像被纳入到地方社会整体性的表述之中,因而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大王岩岩画是侬智高的身影投射”这一现象,管窥到文山州独特的历史意识和族群记忆。
三、延伸讨论
(一)群体与边界
王明珂先生曾对强调内外亲疏有别的群体界限的产生原因给出过他的答案:“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的对外的异己感,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7]12。族群边界乃至群体内部的认同的产生是一个共同体内部主观运作的过程,在族群认同产生的原因的讨论中,有着“根基论”与“工具论”不同视角,“根基论”强调自然血缘,天然的情感认同。“工具论”强调的族群作为政治、社会、经济的现象,以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认同的形成、维持与变迁[7]32-38。在文献记载中侬智高作为族群首领的处境相当艰难,外有交趾侵掠,内附朝廷而不得,以起兵作为手段谋求所在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吾今既得罪于交趾,中国又不我纳,无所自容,止有反耳。”[8]146因此,笔者认为“工具论”的理论视角,更适合于理解侬智高与宋朝之间产生武力冲突的社会动因,以及解释侬智高兵败后,当地民众对侬智高持续性的认同活动,以及对族群记忆生成、内部的价值凝聚、群体边界的产生都可以有一个适当的观照。
(二)地方的内生话语
正如萨林斯在其论著《历史之岛》中描述的代表着世界性扩张力量的白种人与夏威夷土著本土宇宙观之间的遭遇[9]。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土著岛民”是与强势文化接触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非自身历史的主动创造者,地方历史的书写注定被外部的强势力量完全侵夺。通过萨林斯我们得到的教益是:地方的文化以及地方的群体从未放弃行使描述自身的话语权力,他们有着共同体内部自发的文化秩序。即使面对外部的强势侵入与打压,也会运用一种富有弹性的文化策略,或明或暗之中,将本土的文化体系独立于外部均质化的统一体,更多的是将地方的历史与文化多样性保留下来。回到侬智高历史事件的具体语境,可以看到皇权专制对地方自发权力与话语的钳制,壮地关于侬智高的记忆和后来的侬智高信仰与仪式,无疑是面对外部势力强压的内部回应与文化实践。拉德克里夫·布朗认为,社会的团结与凝聚力来源于社区仪式对共同价值的表达[10]122。侬智高的事迹在节日仪式的反复操演与回忆叙事中得以深入人心,族群记忆的具体内容和情感倾向在此进程中得以树立,重新确认了本族存在的合法性与神圣性。
(三)文化整体观中的神圣空间
大王岩岩画遗址作为族群记忆的承载客体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一,岩画的象征意涵植根于那个产生它的人群和相应的文化环境。因时代(或人群)不同造成的文化变迁,使得岩画丢失了原初的符号所指,但岩画符号本身固有的能指性,可以被后人运用于现实目的创造性阐释。“作为过去的物质性存在,遗迹既是自然,又是文化的;它是一种易受因果律影响的物品,但它同时也可解释为一种象征符号,一种意义。李科尔称之为‘象征效应’……作为一种象征符号,遗迹被人们解释着……它是对于过去的一种象征,其物质性表现在于,尽管不断有人在对之进行解释,但它却不会因此而被穷尽。”[11]将大王岩岩画攀附于侬智高的传说,正是后世对这一“文化可能”的现实实践。其二,大王岩岩画作为族群记忆多样承载方式的一种,呈现出的客体存在与侬智高的传说信仰、仪式操演等内在文化逻辑相结合,构成了功能意义上的文化整体。功能主义的文化观除了对人的生理、心理的满足之外,还强调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具有明确边界的文化整体,部分之间相互协调,使得文化整体得以良好运行[10]131。文山州当地有关侬智高的历史意识、祭祀信仰、仪式操演、族群记忆、共同体认同与记忆承载体(岩画遗址)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在满足族群共同体心理需求的同时,构成一个以侬智高为核心的文化有机整体。
相较纪念碑、塑像、空间中的神圣场域等其它族群记忆的承载体而言,大王岩岩画遗址与它们同样有着“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5]335这种群体共同享有的“东西”,即是岩画所处的神圣空间,以及大王岩岩画具有的神圣属性。从岩画的场域条件来看,大王岩岩画处于麻栗坡县羊角老山的山端,山势挺拔高耸。张光直先生认为古式社会的巫师往往会将高山作为出神之旅的介质工具,以寻求天地神人的交感[12]。大王岩岩画的所在场域是一个神显的空间,使得它具备了伊利亚德意义上的神圣属性和神圣空间,“即使没有人来祭拜的时候,这个空间的神圣性也不稍减损”[13]。因此,后世将岩画图像攀附为侬智高的文化实践,也是依托在大王岩岩画所在的神圣空间及图像符号本身具有的神圣属性之上。从族群文化建构需仰赖神圣性资源的层面来观察,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在壮族民间侬智高上升为集祖先神、守护神、丰产神等神格于一体的神祇的文化现象。
四、结语
本文在初始对大王岩岩画是“侬智高的身影投射说”进行了再思考,从诸多纷繁的解释中发现这一说法背后潜隐的“地方性知识”,并将其置于“中央—地方”的二元模式下进行考察,管窥到以侬智高起兵斗争为核心的族群记忆通过地方共同体的文化自觉而得以维系,大王岩岩画被攀附为“侬智高”的现象背后,正是有着共同价值、认同情感的族群的文化实践。通过引入莫里斯·哈布瓦赫和保罗·康纳顿二位学者开创的群体记忆的研究范型,分析了大王岩岩画遗址作为族群记忆载体的可能性和作为载体的特殊性。在文化整体观的观照下,确认大王岩岩画作为记忆的载体,已经被纳入到地方社会整体性的表述之中,与有关侬智高的历史意识、祭祀信仰、仪式操演、族群记忆、共同体认同等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的有机整体,同时,这也是当地族裔没有出现所谓“结构性失忆”的主要原因所在。本文最后引申讨论了持共有价值的地方共同体,从来不曾放弃“书写”自身历史和表达“自我”的文化自觉,以及族群内部对侬智高这一历史人物进行的神性建构,通过共同的族群记忆、价值认同来维持族群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与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