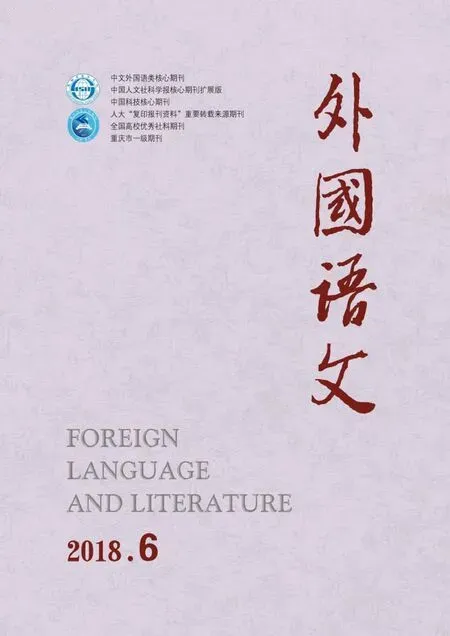非真实性与游戏性艺术
——米兰·昆德拉的创作与欧洲小说传统
2018-03-07刘英梅
刘英梅
(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天津 300204)
在20世纪的世界文坛,米兰·昆德拉无疑是享有崇高声誉的一位作家,美国的理查德·洛克(Richard Locke)称其为“欧美最杰出的和始终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Peacock,1999:201)。由于昆德拉的特殊经历,学界目前对究竟将其划归为捷克作家还是法国作家这个问题并无定论,但昆德拉本人更愿意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欧洲作家。对于欧洲文化,昆德拉一直非常认同。从小说艺术来看,昆德拉也将欧洲小说传统看作自己的文学渊源,并在创作中继承了欧洲小说的非真实性与游戏性的艺术精神。
1 欧洲文化:昆德拉的精神家园
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1975年之前,他一直以一个捷克作家的身份发表作品。但对于西方文化,昆德拉一直是自觉地认同。由于国际政治历史的原因,捷克在很长的时间里被划分为“东欧”国家,昆德拉对此坚决反对,认为从人文历史上看,捷克与东欧截然不同,“作为一个文化史概念,东欧指的是俄国,连同它那扎根于拜占庭世界中的相当特殊的历史。波西米亚,波兰,匈牙利,就像奥地利一样,从来就不属于东欧”(罗思,1999:520)。
在自己的著作中,昆德拉甚至不使用“捷克”这个称呼,而是用拉丁语的捷克名称“波希米亚”。从历史上看,波希米亚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王国,其历史文化发展的很多方面和西方文化同步,共同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巴洛克艺术等等。因此,昆德拉坚持捷克是“中欧”国家,而中欧不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它属于西方的一部分,“布拉格不仅不是东欧,反倒是欧洲的中心”(解华,2013:100)。
20世纪中期,捷克由于纳粹占领、暴政统治等因素的影响,与欧洲文明渐行渐远。对此,昆德拉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痛心,“有时,我担心我们今天的文化正在失去那个欧洲标准……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是欧洲精神的两个主要的源泉,现在它们几乎从受过教育的年轻捷克人的意识中消失了,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Matějka,1999:210)。
1975年,46岁的米兰·昆德拉离开捷克,移居法国。1979年,因为《笑忘录》的出版,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取消了昆德拉的捷克国籍。1981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授予昆德拉法国国籍,昆德拉真正成为一个欧洲人。1984年,昆德拉的母亲在布尔诺逝世,他和祖国捷克的最后联系点消失。
法国是欧洲文化的中心,昆德拉选择移居此地与他对法国文化的认同密切相关。在捷克时,昆德拉就非常迷恋法国文学和法国文化,可以说,他是在法国文化的气息中接受的教育,法国“是他的精神家园”(李凤亮,2003:55)。法国作家中,有昆德拉极为推崇的拉伯雷、蒙泰涅、狄德罗、波德莱尔、兰波、阿波利奈尔、布勒东、尤奈斯库等作家。法国一些作家的小说观念也让昆德拉尤为赞赏,他曾说:“我被法国19世纪以前的小说家深深吸引了,这些小说完全不同于巴尔扎克和他的后继者们。他们关于小说的观念比那些19世纪的小说更使我感到自由,我想到了拉伯雷,特别是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这本书虽鲜为人知,但却是小说类型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du Plessix Gray,1999:210)从昆德拉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他对拉伯雷、狄德罗小说艺术的推崇与继承。
很多人认为法国是昆德拉的流放地,昆德拉却认为法国是他真正可以成为作家的国家。他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他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在巴黎以法文首次出版的,90年代之后他甚至开始用法文创作小说。在法国,他的小说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文学上、艺术上而不是政治上的解读。实际上,他更愿意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欧洲作家。
2 欧洲小说艺术:昆德拉小说的文学渊源
昆德拉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发表后,一举成名。但因为小说涉及当时捷克的政治历史题材,被贴上了政治小说的标签。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解读让昆德拉极为不满,他在采访中解释道:“我的抱负并非批评政体。”(昆德拉,1997:44)作为一位有真正的文学艺术追求的作家,为了捍卫自己的艺术性,昆德拉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从理论方面对小说艺术做出阐释。昆德拉关于小说艺术的见解主要集中于《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和《相遇》四部随笔。在这些著作中,通过对小说的界定和欧洲小说艺术的阐释,昆德拉清楚地标明了自己小说的文学渊源和艺术追求。
昆德拉最看重小说创作,在第一篇小说发表后就确信自己找到了创作方向,“我成为一个散文作家,一个小说家,其他什么都不是”(Oppenheim,1991:250)。对于“小说是什么”这个问题,昆德拉是这样认为的,“散文的伟大形式,作者通过一些实验性的自我(人物)透彻地审视存在的某些主题”(昆德拉,2004:182)。具体分析,这个定义包括三方面内容:(1)小说是散文式的,创作形式上有很大的自由;(2)小说关注存在,通过一些主题探究世界和人类存在之谜;(3)小说中的人物(包括人物处境)是实验性的,与真实性无关。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昆德拉的小说观念与一些传统小说截然不同,显示出了一种美学上的革新性意味,“它表征了小说文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实进程。这一进程中,传统的情节、人物、结构等因素被做了新的处理,从而引起了小说形式整体上的变化”(李凤亮,2006:263)。
同样,昆德拉对“欧洲小说”的界定是他小说观念的进一步展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小说传统,而昆德拉将欧洲各国的小说视为一个整体,统称为欧洲小说。“我所说的欧洲的小说,于现代黎明时期在欧洲南部形成,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历史整体,到后来,它的空间超越了欧洲地域(尤其是到南、北美洲)”(昆德拉,2004:182)。可见,欧洲小说并不局限于欧洲人创作的小说,这个术语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精神概念,它指向的是一种内在共同性——欧洲小说精神。在昆德拉的小说观念中,欧洲小说精神指的是一种不断发现、挖掘小说未知领域的努力和传统。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曼等都是属于这个伟大传统的作家,他们或是发现了存在中不为人知的方面,或是创造了新颖的小说形式,而他们小说的价值也是在欧洲小说的超国家环境中得以凸显。
但是,从美学上来看,昆德拉并不赞同全部的欧洲小说。他将20世纪之前的欧洲小说划分为上下两个半时,时间界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具体来看,上半时的小说始于拉伯雷、塞万提斯,他们的小说形式自由、充满想象力和游戏精神,是昆德拉极为欣赏的小说类型,“他们创作上的自由令我梦寐以求:写作而不制造一个悬念,不构建一个故事,不伪造其真实性,写作而不描绘一个时代、一个环境、一个城市;抛弃这所有的一切而只与本质接触。”(昆德拉,2003a:166)。下半时的小说基本为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例如巴尔扎克的作品),它们在美学上与上半时完全不同,追求小说艺术的真实模式,使作品的文本内容与现实具有同构性。比较而言,昆德拉推崇上半时的小说艺术,但也没有完全否定下半时。确切地说,他认为下半时的小说在追求真实性艺术的同时,舍弃了小说的自由性、多样性和游戏性,缩小了小说的艺术范畴。
进入20世纪后,乔伊斯、普鲁斯特、布洛赫、贡布罗维奇、卡夫卡等伟大的小说家们重新恢复了上半时的小说艺术,昆德拉称之为第三时的小说。第三时小说的开创者是卡夫卡,昆德拉说,“在我个人心目中的小说史里,是卡夫卡开辟了新的方向:后普鲁斯特方向”(昆德拉,2004:32)。总体上看,第三时的小说重新将散文式的思考、自由的结构形式和游戏精神引入小说,摒弃了小说艺术上的真实性追求。事实上,第三时的小说家们在小说艺术上尝试了更多的未知领域,超越了前面的两个半时。例如卡夫卡,他在小说《诉讼》和《城堡》中使用现实与梦幻交融的艺术手法构建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虽然看起来不合情理但比现实更真实。通过这种方式,卡夫卡让小说穿越了真实性界限,但又更真实地把握了现代世界,不失为小说艺术上的革新创举。
昆德拉宣称自己属于第三时的小说家,继承的是后普鲁斯特的传统。通过对自己小说创作文学渊源的清理和解释,昆德拉表明了自己小说的艺术维度和追求。
3 非真实性与游戏性——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追求
昆德拉和对其作品进行政治性解读的评论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小说艺术的理解角度不同。在文学批评史上,作品研究是否需要与作家本人生平结合的问题早就存在不同的观点。法国19世纪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认为小说创作应该建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因此作品研究必须从作家个人生活角度进行,人与文不可分。从这个角度看,昆德拉前半生的人生际遇确实充满“政治”色彩,而其小说中的很多故事也在一个相似的捷克历史背景上展开,将他和小说联系在一起的批评解读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色彩。
但是,对圣伯夫的文学批评方法表示反对的也大有人在,第一个发难者就是同为法国作家的普鲁斯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代表着西方小说创作观念的根本转变,和圣伯夫的传统观念明显不同。普鲁斯特认为,作品是作家“另一个自我的产物” (普鲁斯特,2013:62),这个自我属于艺术生活的内在自我,它与社会生活的外在自我不同。因此,批评家阅读作品只需关注作品本身,作家个人生活的一切对理解作品没有任何价值。
昆德拉完全认同普鲁斯特的观点,认为真人真事是假小说,作品不是作者生活和现实经历的记录,在作品中挖掘作者生活的行为只会瓦解小说艺术。因此,从昆德拉本人的捷克经历出发对其小说进行解读的行为明显与小说的“艺术性”相悖。昆德拉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小说家,而是一个艺术性的小说家,其小说艺术继承了欧洲小说的非真实性与游戏性的精神。
3.1 小说与非真实性
众所周知,“存在”之思是昆德拉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也是他在小说的定义中提到的小说应该具有的功能之一。在小说中,昆德拉通过不同人物的故事,思索了诸如自我、玩笑、爱情、轻与重、灵与肉、不朽、记忆与遗忘、媚俗等等不同的主题,通过这些主题探询人类的存在。昆德拉强调,小说所审视的存在并非等同于现实,“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昆德拉,2004:54)。
昆德拉将小说中的人物与世界都看作是可能性,它们来自虚构的艺术,与真实无关。首先,小说人物是作者想像出来的,并非带有社会身份的真实人物, “我服从了小说历史的第三时的美学:我不想使人认为我的人物是真实的,带着一本户口簿”(昆德拉,2003a:168)。如果一定要寻找作者和小说人物之间的联系,昆德拉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这样说过,“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未曾实现的可能性”(昆德拉,2003b:263)。这一“可能”范畴的界定,使小说超越了对作者个人生活的描写与关注,转向对存在本身的探询。其次,小说中出现的捷克社会历史背景,是为小说人物行动所需而创造的舞台,它代表了人类历史的一种可能境况,而并非指涉属于社会政治范畴的具体国家。更进一步来说,历史环境本身也是一个人类处境,也应该作为一个存在处境给予认识和理解。
总之,昆德拉将小说作为一个实验场地,在其中“他虚构一些故事,在故事里,他询问世界”(德·戈德马尔,1999:516)。昆德拉从来不注重对历史本身的描写,他意在通过实验性的小说,让读者可以看到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可能会做出什么。正如赵稀方老师指出的那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表现暴政统治下的捷克,并没有仅仅满足于暴露伤痕和抗议政治,而是要探究这政治背后的人性”(赵稀方,2002:131)。在小说中,昆德拉对与人物活动相关的捷克政治历史题材都做了最大化的简约处理,或者直接将小说故事的地点作模糊处理,使其获得一种普遍性,使小说最终目的指向对世界和人类的关怀。如果因为他本人的生活经历,而将其小说简单地当作政治文本进行解读,是对他创造性智慧和才能的忽略。
世界是复杂的、模棱两可的,小说的功能是让人们发现这种复杂性、模糊性,而不是给出一个唯一的、真理式的认知。小说家与读者之间产生误解,就在于对小说的非真实性艺术理解存在分歧,作者只想通过小说进行实验,读者却将其看作唯一的现实。
3.2 小说与游戏性
小说不仅是非真实的,而且是游戏的。昆德拉认为,小说的游戏性始于塞万提斯、拉伯雷,他们通过那些充满想象的喜剧故事将小说与现实划开界限。到了18世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和法国小说家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将小说的游戏性发展到高峰,为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昆德拉将小说看作游戏的领地,在创作中,他不仅不将真实感塞给读者,反而在故事、叙述、结构等方面注入了很多游戏的成分。
昆德拉的小说中有很多玩笑故事,尤其是爱情玩笑故事。这些故事,通过一系列没有可能的巧合、相遇和误会不断引人发笑。如小说《玩笑》便是讲述了一个由玩笑开始、又以另外的玩笑结尾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路德维克因为几句玩笑被开除党籍、学籍,断送了自己的一生。15年后,为了报复当年整他的同学泽马内克,他诱惑他的妻子埃莱娜,让她背叛自己的丈夫。愿望实现后,路德维克却意识到自己错了,埃莱娜和丈夫早就不再相爱,他们只是维持一个婚姻的形式。在大街上,路德维克偶然遇到泽马内克,看到他带着年轻漂亮的新欢。泽马内克对妻子的背叛毫不介意,反而很高兴把妻子让给路德维克。而且,由于时代的变化,泽马内克已经抛弃了往日的政治立场,表示愿意和路德维克言归于好。路德维克想尽快摆脱埃莱娜,埃莱娜却爱上了他,甚至在遭到他的拒绝后服药自杀,不过却阴差阳错地吃下了轻泻药。同样,短篇小说《搭车游戏》《没有人会笑》《爱德华与上帝》的故事也由一系列玩笑、巧合、误会组成。
昆德拉以轻松、随意的笔调叙述故事,淡化和分解了其中的不幸与沉重,让娱乐、游戏的氛围充满小说。但娱乐不排斥严肃,体味这些玩笑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生活的复杂性、虚假性和欺骗性。就像《玩笑》中,路德维克的复仇初衷因为埃莱娜的爱以及与泽马内克的偶然相遇变得荒唐可笑,而埃莱娜自以为是的爱不过是路德维克的一个陷阱,他们的相遇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无论是路德维克还是埃莱娜,都身陷别人的玩笑中,对自身的境遇并不自知。人类在迷雾中前行,处在无知和盲目的人生命运中。由此,昆德拉在嬉笑游戏中完成了他对人类存在之谜的探索和展示,揭示出世界的荒谬性。在轻松的形式与严肃的内容交织的文字间,昆德拉的游戏精神与理性精神并行不悖,显示出其小说极富个性的艺术魅力。昆德拉作品的这种文笔风格,归根结底,与欧洲文化传统颇有渊源,它“是源于18世纪西方的理智主义和怀疑主义,对人的本性的深刻认识以及随之产生的游戏态度”(景凯旋,2012:161)。
从写作技巧上看,昆德拉也有意识地增加小说的游戏性。比如,他直接以作者的身份介入小说,对小说的真实性进行自我解构。在小说《不朽》《慢》中,昆德拉作为小说人物中的一员,参与情节并与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对话;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以作者的口吻对肉体和灵魂、媚俗等问题直接进行解说。这样的写作方式不但增强了小说的思辨性、哲理性,而且有意识地破坏了读者对小说的真实性期待,强调了文学的虚构性本质。对此,昆德拉直言不讳,“从第一个字开始,我的思考就是一种游戏、讽刺、挑衅,带着实验性和探询性的口吻”(昆德拉,2004:100)。
另外,昆德拉充分发挥了小说形式上的无限自由的特性,将梦幻叙述引入小说。在昆德拉看来,梦除了具有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心理学意义外,还具有一种美学上的意义,他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分析特雷莎的梦时这样说过,“梦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交流(也许是一种密码信息交流),还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想象游戏,这一游戏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昆德拉,2003b:71)。我们看到,与卡夫卡在小说中将梦幻与现实交融的处理方式不同,昆德拉将梦幻叙述作为小说复调结构的一部分,赋予它情节上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在《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慢》《身份》《无知》等小说中,昆德拉借助梦幻叙述的想象技巧,使小说穿越了真实性的界限,进入了游戏性的艺术空间。
总而言之,通过对欧洲小说传统艺术的阐释,昆德拉既标明了自己的文学渊源,又成功地捍卫了自己小说的艺术性,“在小说的世界中,借助于塞万提斯以来的欧洲小说传统,他最终巧妙地超越了所有的冲突和差异”(刘成富,2017:108)。而且,通过小说创作,昆德拉清楚地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树立起一个小说家的艺术形象。在当代的世界文坛,昆德拉对小说观念和小说艺术的革新意义毋庸置疑,对于他的文学成就,余中先先生这样评价道,“昆德拉无疑是捷克文学乃至中欧文学、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里程碑”(仵从巨,2005: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