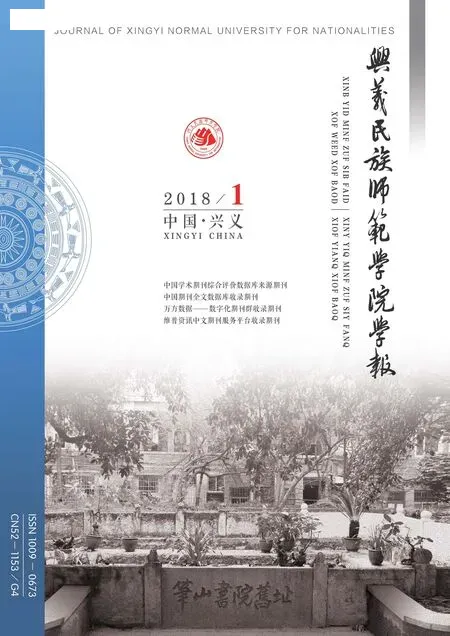试论语言接触与民族文化“共识阈”的拓展
2018-02-25贾晞儒
贾晞儒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7)
语言接触是指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人口流动、移民杂居、战争、外交活动等所引起的语言之间相互接触。就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部来说,各民族主要是通过语言这个“桥梁”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进而形成“族际通用语”。通过“族际通用语”又会使各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更加密切和频繁;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因此,语言的接触影响也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人种混合指血统而言,由此直接引起语言变化,就语言本身变化而言,则纯属于文化现象,其变化的动力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借词,采用它优美的音调,自然吸收,属于自然变化或谓‘融合’;另一种是统治语言挤掉被统治语言,使后者趋向前者致合而为一,意识也趋向统一,这是优势原则起作用,可谓‘优势同化’。”(欧潮泉,2007)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来观察语言的接触,语言的相互吸收首先是发生在词汇方面,借词就是文化的借用。借词所指称的事物,其中一部分是受惠语言中暂时没有的,一部分是受惠语言中存在相似、相近的,但为了表达的需要而借用。在语言借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施惠语言的某些文化成分引入其中,进而表现出受惠语言不但与施惠语言具有文化共识范围的重叠,其文化涵盖范围也扩大了。这种语言文化上的接触交融所形成的重叠范围,就是文化“共识阈”,体现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共通性及其联系。这种文化上的联系表现了语言社会群体之间互相依存、互相碰撞、互相竞争和互相吸收的的一种关系。
以下,我们从几个方面对语言接触与民族文化“共识阈”的关系进行讨论。
一、语言接触是促进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动力
在历史上,汉语曾经是“称雄于世”的语言,特别是盛唐时期,在国际交往中,汉语几乎处于“霸主”的地位。汉语言的这种优势也曾经成为中华民族心理优势的“增强剂”,而这种民族心理的强势,又反过来滋生了语言的旺势,它们互为表里,使得中国人民变得那样的自豪和大度,多少先哲贤达往返于中外多种语言文化世界之间,他们带去渊博的中华文化,又吸纳国外优秀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互补关系的发展。玄娤西天取经就是一个彰显民族自信和开放胸怀的壮举。唐太宗为此特意召见了他,并将其带回来的大量梵文经典,请人用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字拼集出《圣教序》,形成了汉语言文化和梵文化的大“联姻”的美好局面,至今在汉语里留存着这种美好的“符号”——词汇。例如:“阿浮陀”(arbuda)、“阿吽”(ahum)、“吠陀”(veda)、“ 佛 图 / 浮 屠”(buddhastūpa)、“袈裟”(kasāy)、“迷丽耶”(maireya)等。这些词语(当然不只是这些词语!)至今还在被中国人民所使用。它们都是一种文化符号在汉语中的“落户”,成为汉语大家庭中的成员,承担着巩固和传播佛教文化的功能,使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乃至扎根于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和佛教文化,影响了和影响着多少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诸如: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也都是来自佛教语汇;在国内,来自四面八方的少数民族商贾、文化人、政治家等会聚于国都长安,既学习传统中原文化,又传播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中,汉语吸收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为汉语的丰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终于使汉语言具有了“族际通用语”的基本功能。在此,我们不妨摭拾几个少数民族语言的词语被借入汉语之中的例子:“阿加”(彝语已婚配成家的奴隶)、“巴斜”(兹别克族语乌孜别克族的一种民间舞蹈)、已婚配成家的奴隶)、“阿蒙达”(纳西语二人对唱)、“奥娃”(黎语,“穷人”的意思)、“巴乌”(哈尼语[ba55u53]哈尼族单簧吹管乐器)、“博如坎”(鄂伦春语[barkhan],即“神”的意思)、“布犺”(傣族语,傣族的首领)、“春吉”(维吾尔语[qüqe],维吾尔族晾制葡萄干的土屋)、“达剌干”(契丹语[darkhan],辽代官名)、“打巴”(纳西族语 [da33pa33],东巴教的一个分支的巫师)、“打歌”(白族语[ta51gau11],一种边唱边跳的歌舞形式)、“打令调”(朝鲜语,朝鲜民间歌谣的一种体裁)、“笛哩吐”(傈僳语i31li31],一种小短笛)、“冬不拉”(哈萨克语[dombra],哈萨克族的一种拨弦乐器)、“洞萨”(景颇族语[tum31pa33],巫师)、“逗落”(匈奴语[toulo],“坟墓”的意思)、“多耶”(侗族语 [to23je342],侗族的一种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虷淮”(壮语[gaengvaiz],即蜉蝣,在水面活动,形似蜘蛛的小虫)、“给力全布腾”(鄂温克族语[kielipaphthin],用犴角、桦木制成的鞍子接头)、“骨豽”(突厥语[kuna],泛指貂、狸等动物)、“国论”(女真语 [gurun],“国家”的意思)、“罕伯舞”(达斡尔语[hakimbaileg],达斡尔族的一种民间舞蹈)、“珠咪”(佤族语,“富有者”的意思。解放前佤族农村公社中产生的富裕户)、“库姆孜”(柯尔克孜族语 [qhomuz],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三弦弹拨乐器)等,其数量之多,不胜枚举。程祥徽教授说:“借词借的是文化。”并举“泊”字为例,说:“‘泊’是个形声字,船停在水中,用三点水作形符当然合理;车停在陆地,用水作形符未必合于事理了,……汉字是一种讲理据的文字,总能找出解释这一语言现象的理由吧。……泊车、泊船所泊的都是交通工具,先有‘泊船’,跟着取‘泊’字的‘停下来’的意思用到停车上,……这是人类思维功能的联想与引伸。奇妙的是,字形上‘车’向‘船’借走了‘泊’,字音上却没有跟着借走‘泊船’的bo,这就是说,泊车的‘泊’是个英语借词,不过采用了已有的汉字。……‘泊车’既来自古代①,同时又来自外语,它是词的借用,在词的借用中充满了文化的内涵。”(程祥徽,2014)其中有的虽然成为历史的记忆,在日常生活中不再使用,但研究历史文化却是不可少缺的;有的已经融入到汉语的基本词汇里面,甚至成为构词语素,具有了一定的构词能力,与汉语原有的基本词汇在功能上难分彼此。例如:“圐圙/库伦”一词本是蒙古语的“”,原指“围起来的草场”、“营房”,今多指“院落”、“围墙”,也做地名用。例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库伦旗”、“库伦镇”等。又如,我们常说的“喇叭”,是一种吹奏乐器,源于蒙古语的“”[labai]本意为“紫箢”,亦指称“海螺”,即蒙古语的);再如满语的“剌忽”[laxu],我们几乎不以为是满语的词了。在汉语里被写成“拉忽”,即“马虎”、“粗心”的意思,完全汉语化了。
在汉语中少数民族语言借词数量最多的要算蒙古语、藏语和满语。198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共收录古今汉语外来词一万余条,其中国外语言中英语和日语词汇所占比例最高;在收录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词汇中,蒙古语、藏语和满语的词汇最多,据笔者粗略统计,按一万条计算,蒙古语有320条,占0.32%,藏语194条,占0.20%,满语90条,占0.05%。如果综合起来计算,蒙、藏、满共604条,占本词典一万条的6%。更有意思的是,当它们被吸收到汉语之中,用汉字来标记时,不但在形式上表明是一个借词,而且在词义上含有了汉语言文化的成分。例如:吸收藏语的[tsam55pa54]一词,用形声造字的方式创造出“糌粑”这个符号来标记,并进入汉文化“圈”里,出现了“酥油糌粑”、“糌粑美食”等之类的食品词语。藏语的一词被借入汉语后,用汉字标记时,起初是不统一的,有的写作“果谐”,有的写作“歌谐”,有的写作“果日谢”,有的还写作“戈协”,等等,近几年来,大多数都写作“锅庄”,并在其后加了一个汉语通名词缀“舞”,表明是一种舞蹈名。这个借词的汉语书写符号的变化,表明了人们对其真正含义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因为借用伊始,人们对其功能的认识还停留在表层上面,究竟用哪几个汉字去标记它,人们的认识还不统一,经过反复地、无数次地使用和汉、藏两个民族的文化交往日益深入、广泛,对于这个舞蹈的动作、形式、功能所具有的内涵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同舞齐唱,共享欢乐,沟通感情,增进友谊。因此,用“锅庄”两字来音译,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涵上都十分切合。“锅”一般都是圆形、无缝的,跳这种舞蹈不分民族、老少,谁都可以参加进来,而且都以同样的舞姿和动作,一个跟着个一个鱼贯而舞,不可间断,形成一种可大可小的圆圈,恰如锅状,紧密相随,情感交融,一边手舞足蹈,一边畅怀歌唱,气氛活跃、奔放;舞者热情、豪迈,大家一起共享这欢快、愉悦的美好时光。“庄”者,端庄、大方也。有气派,有激情,彰显了这种舞蹈的气质和气氛。在有藏族同胞的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不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可以自由参加。跳“锅庄舞”已经成为多民族的男女老少自发参与的一种健身、娱乐活动,不但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融,而且对于这种集体娱乐方式的文化活动的社会意义有了更真切的理解和认同,进而成为各民族共同认可和喜爱的一种文化娱乐形式,尽管是音译词,其内含意义已被人们所共同认知,根本不存在“排他性”的因素。因此,用“锅庄”这个音译词,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这种舞蹈的气质和大众化的特点。又如,蒙古语的“”曾经有过“鄂博”、“阿卜”、“阿不”、“恼包”、“鄂堡”等音译词,说明了人们起初对其内在意义的了解不够准确和深刻,在选择音译字时,人云亦云,难以统一。但是,随着蒙汉两个民族的密切交往,对于“”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有了比较准确和深刻的认识,最终选择了“敖包”作为它的音译符号,是十分确切的,既音译,又形似,且寓意。汉语“包”的一个义项是“物体或身体上鼓起来的疙瘩”,与地面堆起的砂石堆相似,但它与“装着东西的包”更神似,即里面包着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砂石堆。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里,对“敖包”的解释是“蒙古族人做路标和界标的堆子,用石头、土、草等堆成。旧时曾把敖包当神灵的住地来祭祀。”其实,今天的蒙古族人民依然把它作为祭祀神祇的地方,也是当代青年牧民聚会的地方。因此,它已经不再只是“做路标和界标的堆子”,而是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意义和现代文化意义相融合的一种文化符号,“敖包相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和深入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不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宏观领域的接触和交往更加频繁和密切,而且在微观上,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个体接触和文化交往也更加直接、频繁和广泛。同在一个社区生活、共事同一事业,同在一个学校(特别是民族学校)学习、娱乐、生活,相互间的语言文化接触与交流,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必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每一项文化娱乐活动都可能是多民族成员共同参加的,这样,就会出现语言的某些成分(特别是词)相互借用的现象。例如,藏语的“达堆”([tadod]代金)、“达尔康”(原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电报的机关)、“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摄政以下最高的主持官员)等词语,不但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进入到汉语之中,而且还有更多的藏语成分进入汉语,有的已被人们习焉不察了。如“曼巴”、“扎西德勒”、“锅庄舞”、“格西”、“赞普”、“乌拉”、“格桑花”、“格更”、“古尔毛”等。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汉语每吸收少数民族语言的一个成分,就在汉语言文化圈里面增加了一个文化符号,由少积多,由个别到一般,不断繁衍生息,实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的吸收和积淀,都是一种文化精髓、文化观念的大融合,是共同文化心理的集成,最终构成了中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价值观和民族观。换句话说,汉语言在语言接触中没有走向混合语的道路,而是在吸收周边民族语言成分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它的词汇及其结构特点正是融合了各民族语言文化成分和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在汉语上的表现。
二、借词是一种新的创造和民族共识阈扩大的标志
我们说语言是民族边界的一个重要标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由于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相互之间保持频繁的、稳定的社会交往,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共同体,使语言具有了民族性;二是这一群人使用的语言有别于其他人群使用的语言,于是,语言就成为民族边界的区别符号之一。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既是民族间交际的媒介,也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借词或者某个语言成分的借用,则是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在接触、沟通过程中形成的“感情铺垫”和认同阈的重叠和扩展。我们前面谈到的语言接触和文化吸收问题,旨在说明语言接触中,双方语言中的某些语言成分,特别是借词,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也是一种文化增补现象。凡是一个词语或者某个成分的借用,起初可能是偶然的,但是一旦被受惠语言所吸收,并经常被使用,就不仅仅是借词问题,它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精神和智慧。汉语在历史上吸收了大量的外语词汇,也吸收了大量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但是这种吸收,并不是囫囵吞枣的模仿,而是有一个“民族化”的过程。这种“民族化”过程,就是受惠语言在吸收施惠语言成分的同时,把自己民族的认知或固有的文化符号意义融入其中,使其内涵更丰富、深厚。
一般而言,凡是借用的成分都是语言交际、文化交流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种需要的前提下,任何民族语言都会出现语言成分特别是它的词汇的借用和被借用,并且都会有一个“本民族化”的过程。远的不必去说,就拿“巴士”这个词来说,它是英语“bus”的音译,汉语译作“公共汽车”。但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巴士”又有了特殊的用处,即与“公共汽车”有了分工,凡是“有固定路线和停车站,供乘客乘坐的汽车”都叫“公共汽车”(简称“公交车”),除此以外,作为运送乘客的汽车就叫“巴士”,而且有“大巴”、“中巴”、“小巴”之分,这种音译词使用的变化,其背后必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个借词的出现及其使用上的变化,从其表层来看,是表现一种新事物或观念被引入受惠语言之中。但仔细考虑,它又表现为人们获得了一种新知识、新认识。这是在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任何语言都存在的普遍现象,表现了语言所具有的包容性和自信力。例如英语的“microphone”被借入汉语时,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个新生事物,大多数人还不认识它,不理解它,只好采取音译的办法来推广使用,所以当初的译文就不统一,有的译作“迈科封”,有的译作“买可风”等,到后来就逐渐统一,并被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以“麦克风”的形式巩固了下来,表现了人们对这个事物的性质、功能的准确认识,作为“传声器的通称”,既代表了它的基本读音,又以“风”义(跟地面大致平行的空气流动的现象)表示这种事物的功能:人发出的声音通过传声器在空气流动中传播,被理解为风的力量,含有中国人的观念成分,后来又有了“话筒”的称名而并行不悖。又如,现在男女老少普遍使用的“拜拜”就是英语的“goodbye”中的“bye”音译的重叠,表示汉语的“再见”义,当初,在青少年中使用时并不被人看好,甚至还有非议。但是,随着使用范围的日渐扩大和人们对它的理解的加深,在语感上不再有排斥的情绪,并且用“拜”这个汉字来标记,因为“拜”含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表示比“再见”的语义内涵更丰富、更有“中国味”,使其在情感上更加亲近,不再有异样的感觉;在英语里也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例如fengshui“风水”、Mandarin“官话”、kongfu“功夫”、tuhao“土豪”、jiao“角”、yuan“元”等。yuan“元”又被引申出“钱”的意思。可见,一个借词不仅是文化的移植和文化的创新,而且也是文化的融合。任何一个民族语言都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当甲语言的词被借入到乙语言之中时,首先是交际的需要,是文化的需要,并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日渐“本民族化”,即在读音符号的选择上往往会考虑到尽量与本民族语言的某一个符号意义相接近或一致,在形式和意义上更加符合本民族的语言心理。所以,即使是音译词也不纯粹是“拟音”,而是一种创造。例如美国英语的cool是一个多义词,被借入汉语音译为“酷”,由“酷”本义(残忍、暴虐,也做程度副词“极”、“甚”和形容词,表示“帅气”、“时髦”、“令人羡慕”等意思)引申为表示一种生存状态,一种活法和对世俗的蔑视,追求个性,与众不同的“状态词”,常用来形容男性;show在英语里也是一个多义词,被汉语借用过来,音译为“秀”。“秀”本义为“植物抽穗开花”,后来又有了“清秀、秀丽;聪明、灵巧、特别优异;表演、演出”等多项意义,但是,当它作为音译词时,由英语的show原词的多义中引申出“弄虚作假,装样子骗人”的语义而被广泛用于现代汉语之中。
再如汉语的姓氏符号是汉民族文化的一个特点,其来源多种多样,有的是古代氏族的名称,如尧氏族称“唐”,其后裔就以“唐”为姓;有的本来是国名或者地名而演变为姓氏名,如齐、鲁、秦、晋、韩、赵等;有的本来是官职名称,也转用为受惠语言的符号形式标记所借之词,使这个借词的读音与原词接近或者一致,并保留原有词义成分,又赋予了与之相适应的受惠语言的语义成分(主要是文化因素),在客观上扩大了两种语言民族的“共识阈”。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一方面强调语言内部的认同,以区别其他民族,另一方面语言的接触,又在扩大着语言之间的“共识阈”和“重叠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今天世界语言数量的减少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再从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满语曾经是我国统治民族的语言,它给汉语以极大的影响,汉语中有许多满语借词,诸如“萨其马”(一种糕点名)、“包衣”(家奴、奴仆)、“贝子”(清代宗室爵号)、“笔帖式”(清代官名)、“依是拏”(是,可能是,表示应答词。本为[inu],借入汉语后,在[inu]中间加了汉语的“是”汉语东北方言的“嗯哪”可能是[inu]的借用)、“旗袍”(本为“衣介”,汉语意译“旗袍”)等。可见,很多借词都是文化借入的记录和结果,也就是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之间通过借词这个中介,使各自语言的文化知识、文化观念相互渗入和吸收、直至认同,使各民族之间在认知方面、价值观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重叠和“共识阈”、最突出的是,每年的春节、清明节、端阳节,乃至后来的姓氏名,如王、侯、司马等,有的是以图腾崇拜物为姓,如龙、牛、马、杨、柳等;甚至有的还以数字为姓,如伍、万、陆等。这些姓氏名在语言接触过程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及其意义也被周边少数民族所吸收,至今国内许多少数民族也都有了姓氏名。应该说,这种现象是语言接触过程中汉文化移入少数民族语言之中的一种外在表现。特别要提到的是,自周秦以来,尊孔读经,提倡仁义,奉行中庸之道,普及民间,无论是上层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其社会观念、道德伦理观念,形成了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观念。所以,国内其他兄弟民族在与汉族的往来中,通过语言的接触和互相学习,也必然影响到少数民族文化的结构。就拿回族来说,早在公元7世纪中叶,大批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经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长安、开封从事商业活动,并定居其地,使用自己的母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到了元代蒙古军西征时,一部分“回回民族”被编为“回回探赤马军”(即“回回骑兵雇佣军”)作为“马前卒”为推翻宋朝,建立元朝,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到了明代,朱元璋禁止回回民族说母语,改说汉语,出现了一大批回族开国功臣,诸如:徐达、常遇春、胡大海以及航海家郑和等。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本身就肩负着“宣教化于海外诸藩国,导以礼,变其夷习”的使命,不但发展海外贸易,而且传播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大大地促进了语言的接触和文化的传播,直到民国时期,回族中出现了一大批儒学大师喇世俊、史学大师白寿彝等。可见,回族改用汉语是有其历史、政治原因和社会环境的原因的。但是无论怎么说,当代回族所操的汉语里仍然有许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成分,说明回族人民在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守护着自己固有的那一片文化园地,这园地也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语言间的接触促进民族文化上的共识阈的扩大,增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观念,并表现在各民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崇拜龙不仅是汉民族,也是信仰佛教的各族人民的共同观念,蒙古族、藏族、土族以及南方的傣族、苗族、羌族、毛南族等,都是“龙的传人”,在这些民族聚居的地方和生活的社区里,到处可以看见龙的各种形象,如龙的雕像、龙的绘画、龙碗等龙的器皿、龙的服饰、龙的旗帜、以及龙字书法艺术等;端午节有龙舟竞赛;元宵节高挂龙灯,舞龙活动,等等。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这正是语言接触过程中的文化交融,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念和精神特质的基石。
三、加强语言接触研究,增强民族凝聚力
语言接触研究是语言学范畴的问题,但是,如果从语言民族学的角度去观察语言,语言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言接触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内容。因此,通过对于语言接触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民族之间、民族文化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关系和变化;通过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可以揭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和文化迁移的过程及其基本特点。德国历史语言学家格里姆(J·L·K·Grimm)曾经说过两句精辟的话,一是“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二是“关于各个民族的情况,有一种比之骨头、工具和墓葬更为生动的证据,这就是他们的语言。”②也就是说,语言是观察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窗口”。语言中的借词就是“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的标志,还往往可以作为两个民族发生接触的断代证据。”接着,作者举例说:“景颇语中有关水田生产的词,多借自傣语和汉语,这种语言上的事实说明,景颇族耕作水田是在与傣、汉等民族发生文化接触之后的事情。”(林耀华,1997)再如,我们对于借词词义的演变、发展的研究就可以揭示出一个民族社会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例如,早在元代汉语从蒙古语里借入的(原为“路”),是指“驿站”,即《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古代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及往来官员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于是,就和汉语固有的表“站立”、“停留”义的动词“站”有了分工,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在蒙古语里则是用“”[orto:]和“”分别表示“驿站”和“停留、住宿之所”之义,即“车站”、“机场”、“宾馆”、“旅店”等。从蒙古语里借来的“站”,在汉语里又有了独自发展的空间,构造了一系列新词,这些新词当然是反映汉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状况和文化观念的变化的。例如,在元代,“站”是指“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③后来却指客运、货运的停车之所和为某种业务设立的机构。如“记者站”、“粮站”、“医疗站”等,与原来的“定义”有了差别。语言接触过程中出现的这种语言事实之多,是枚不胜数的,有的甚至难以辨别出它们的源头。例如汉语中与“钱币”有关的字,如“财”、“货”、“贷”、“赚”、“赊”、“贪”、“贿赂”等都属于“贝”部,究其原因可能与我国许多民族在古代都曾经以贝壳为钱币的文化有关。这是汉语固有的,还是在与各民族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吸收来的?也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在语言接触研究中,地名研究更是涉及到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地理历史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多民族地区和社会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地名,更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例如在青海境内有许多地名是双语的或者是多语合壁的,有的是同一地理实体的多名指称,等等,既是民族语言接触的历史标志,又是文化交融的历史结晶,更是民族共识阈的聚合与凝结,从而在民族心理上具有了鲜明的亲和力和向心力。例如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优干宁”这个地名,从本义看是指称“汉族”的,经考察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汉族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地方,这个地名也就成为民族之间进行经贸活动的历史记忆,又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的“乎勒茶卡”是蒙藏合璧地名“,乎勒”是蒙古语词的“”“野骡”;“茶卡”是藏语词,即“戈壁滩”,表示“有野骡的戈壁滩”。说明这个地方不但有野驴出没,而且曾经是蒙古族、藏族居住过的地方(可能与蒙古族征伐云南大理路经此地的历史有关)。一般说来,双语合璧地名往往是民族杂居或者民族迁徙的历史佐证,在一定意义上讲,它又是民族和睦相处,构筑共同家园的历史见证。
总之,任何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都会真实地保留在自己的语言之中,诸如对于自己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识和经验等,都凝聚、积淀在自己的语言之中,其中也包括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新的语言成分(主要是词汇),而这些新的语言成分既可能是受惠语言的新的文化成分的标志,也可能是历史的碎片,折射出民族之间的某种关系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所以,语言接触不但会引起语言结构本身的变化,而且语言变化本身能折射其民族生存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的状况。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杂居相处,友好往来,语言间的接触影响源远流长。这种语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也正好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可见,语言是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是文化交流的中介,是构筑、扩展、巩固民族共识阈的通道,也是凝聚中华民族亲和力、向心力的“粘合剂”,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语言接触的研究。
注释:
①是指“泊”字来自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②转引自1957年12月《民族问题译丛》载前{苏}阿巴耶夫:《语言史和民族史》一文。
③引自《元史》卷101,《兵志》四。
参考文献:
[1]欧潮泉.基础民族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28.
[2]程祥徽.借词借的是文化[N]澳门:澳门日报.新园地版,2014,4-2.
[3]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