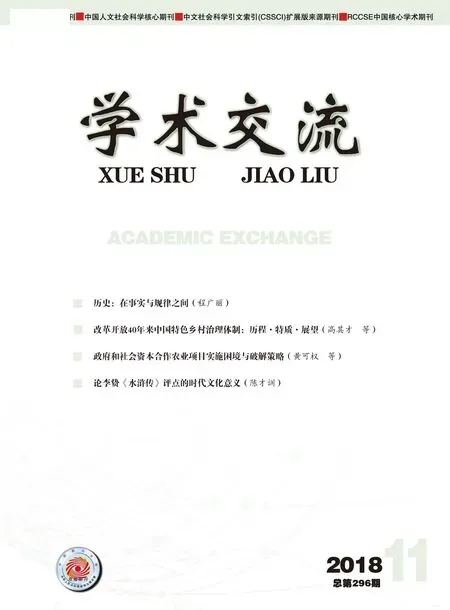五四落潮之后的反思
——刘半农同五四时代精神的契合与疏离
2018-02-21张承志
张承志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自由、民主、科学、个性等观念为五四的主旋律,五四之后,经过“狂风骤雨”的洗涤产生了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精神面貌。对五四新文学作出过诸多贡献的刘半农本应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对象,他的文学作品更不应该被简单地遗忘。虽然他的作品与五四呈由契合到疏离的状态,但契合与疏离的同构交错恰恰呈现了刘半农在五四时期真实的声音与真实的精神状态。所谓契合就是达成一致,引起共鸣。这种与“五四时代精神”的契合,从内因来看,刘半农的文学创作观及平民意识与“五四时代精神”有着较多相似之处;从外因来看,作为一位有良知的文人学者,刘半农看到了当时祖国的江河日下和世界的日新月异,忧国忧民的他如饥似渴地寻求与引进当时东西方的先进思想,他时刻关注着时代的脉搏,关注着底层人民的命运,希望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康庄大道,他用文学创作来启蒙昏懵的大众,并发出了时代的强烈之音。所谓疏离,就是逐渐远离五四时代精神的主流话语。刘半农这种疏离的内在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身份的转变及潜心于学术,另一方面更是缘于刘半农本人对以往所秉持新文学观的深刻反思——他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了五四新文学激进派的最终历史命运与文化抉择;外在原因是五四高潮过后,政治黑暗的逆流与军阀之间的混战再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时局险恶,再加上刘半农的二弟刘天华突然逝世给他情感上造成的冲击迟迟不能平复。所以,笔者把刘半农同“五四时代精神”的契合与疏离归结为气质的异同:五四时期所建构的是在五四潮流下峻急奋进的“勇士气质”,五四落潮之后所建构的是远离政治风暴的“云散疏离”的“隐士气质”。
从刘半农所发表的新诗来看,其内容、思想、主题并不完全与五四的轨迹相一致。而正是这种“于五四中成长”,又“于五四中潜隐”的转化彰显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不拘一格的“时代特色”。本文通过刘半农于1918—1933年发表的《卖萝卜人》(《新青年》1918年第4卷5号)、《战败了归来》(《扬鞭集》1926年)、《疯人的诗》(《京报副刊》1926年第429期)三首诗歌来探究刘半农与五四的复杂纠葛。
一、苦中含泪:“一个人”与“两个车夫”的命运契合
五四到来之时,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家们竭力地批判了中国旧道德的虚伪与荒谬,让昏懵的国人猛然警醒,且带来了多元的现代化精神追求。这种时代精神征候的骤变正如一位海外研究者所言:“五四运动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人权和民族独立观念的迅速觉醒。”[1]众所周知,《新青年》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而且也是带有标志性的时代刊物,更是新道德、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窗口。作为新文学闯将的刘半农在《新青年》共发表了27首新诗,可见刘半农与《新青年》呼唤的“五四时代精神”有着高度的契合。在给五四新文学重镇《新青年》投稿的阶段也是他“鼎新革旧”全面呈现的时期。为此,被鲁迅评价为:“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2]398而从整个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刘半农同其他新文学家们一样,主要是以“恒古至今”的一种表述方式——诗词来感怀忧国、抒发壮志。如果从与“五四时代精神”的距离来看,刘半农的《卖萝卜人》无论是在神韵上,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属于与五四最为契合的一首诗。
纵观在《新青年》上所发表的几十首新诗,多数是以反映“人”和唤醒“人”为主题的,沈尹默的《人力车夫》(《新青年》1918年第4卷1号)与胡适的《人力车夫》(《新青年》1918年第4卷1号)是五四新诗中能够传达追求人文关怀、自由、个性的诗篇。这两首诗歌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关注“社会底层人”的苦难,这是五四时期处于思想巅峰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性表述方式。所以,基于“深切的表现与新颖的文体”来说,二者可以一脉相通地互文式阐释:
《人力车夫》
沈尹默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可以看出,沈尹默运用对比手法对所描述“人力车夫”的境遇给予了悲悯的同情。如“河水不流”而“车水流”,“穿棉衣的坐着”而“穿破单衣的跑着”的两组对比、衬托鲜明可见。同样,胡适的“人力车夫”则以人道主义的“怜悯”与“悲伤”为基元阐释了底层百姓生活贫苦的现状:
《人力车夫》
胡适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能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胡适所描绘的“人力车夫”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付出成年人的劳动才能换得温饱,再现了当时旧社会压迫与剥削的现实。可以说,两个“人力车夫”的塑造自然而形象,朴素而简洁,没有浓艳的字眼,也没有蓊郁的诗意,只有同情与伤悲,以至于形象有余而意蕴不足,在一洒同情之泪后,没能引起读者进一步深刻地思考他们苦难的根源。
《卖萝卜人》
刘半农
一个卖萝卜人——很穷苦的——住在一座破庙里。
一天,这破庙要标卖了,便来了个警察,说:“你快搬走,这地方可不是你久住的。”
“是!是!”
他口中应着,心中却想:“叫我搬到哪里去!”
明天,警察又来,催他动身。
他瞠着眼看,低着头想,撒撒手,跺跺脚,却没说——“我不搬。”
警察忽然发威,将他撵出门外。
又把他的灶也捣了,一只砂锅,碎作八九片!
他的破席、破被和萝卜担,都撒在路上。
几个红萝卜,滚在沟里,变成了黑色!
路旁的孩子们,都停了游戏奔来。
他们也瞠着眼看,低着头想,撒撒手,跺跺脚,却不做声!
警察去了,一个七岁孩子说,
“可怕……”
一个十岁的答道,
“我们要当心,别做卖萝卜的!”
七岁的孩子不懂:
他瞠着眼看,低着头想,却没撒手,没跺脚!
《卖萝卜人》是刘半农现代“无韵诗”的尝试之作,因此,难免流露出古典诗词“回旋往复”的痕迹,同时又可以看作是一首“现代讽喻诗”。中国自古以来讽喻与批判现实的诗词不胜枚举,如李白《乌栖曲》、白君易《卖炭翁》、苏轼《满庭芳·蜗角虚名》、龚自珍《咏史》等,这些诗词由讽世到厌世,寓意精深,以微见著、讽刺辛辣、含蓄有力。可以说,刘半农承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批判传统,且加入了现代气息的元素,颇为新颖和率真。《卖萝卜人》无华丽词藻,也无雕琢的痕迹,有的只是朴素的文风、简洁的语言及“真实”的画面来反映五四时期的社会现实。关于“真实”,刘半农认为:“做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3]在《卖萝卜人》中刘半农没有冷眼旁观社会而作自然主义式的描摹,他以血泪为诗,“真实”而有力地批判了“旧中国警察”乃至“旧社会恶势力”的流氓、土匪本质,同时也在强烈地呼唤以五四为表征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的尽快到来。正如王瑶所说“刘半农的诗歌是今天现实主义诗歌的萌芽”[4]69一样,刘半农是以张致姿态来呈现出与五四的契合,他对当时的“尊君权、重阶级、较忠孝、受奴役为旨归”[5]的封建愚忠思想发出了强烈的愤慨与批判。所以,大胆地批判阶级对立、揭露贫富悬殊根源以及重视平民精神是刘半农现实主义新诗的“底色”,这种“底色”没有雕饰的色彩,完完全全是一种质朴真诚的风格,平民精神十足,体现了五四——作为一场本质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尽管承载着时代的梦想与激情,但诗人的“想象”依然是追求民主、科学、个性、自由,并且探寻着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这必将引起无以名状的依恋与愁思。刘半农的《卖萝卜人》同沈尹默的《人力车夫》与胡适的《人力车夫》相比较而言感情更加真挚,对“社会底层人”受奴役、受压迫的愤慨与批判表现得更加深刻、坚决。其主旨意蕴不仅契合了五四的思想潮流,而且是一场恣肆彻底的表达,更是五四一代人对现代人自由、平等、个性的渴慕与祈盼。可以这样说,刘半农的新诗作品中多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复杂的心路历程,表达出对个体意识觉醒以及民主、自由、平等、个性的期待,而且刘半农的这种探索平民的精神、平民的人生意义与平民的终极社会价值的“指路标识”作用则更具现实意义,且在艺术形式的转换上他敢于探索新的形式与样式,从而形成和强化了他新诗作品的现代性,这也深深地契合了“五四时代精神”的潮流。
二、离开与归来:战场与情场的异质抉择
在诗歌的主题内容上贴近五四,但于精神意蕴上又疏离于五四的一首诗是《战败了归来》。当《新青年》于1926年7月被迫停刊后,刘半农转而成为《语丝》(1924-1930年)的“经常撰稿人之一”[6],可以说《语丝》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风暴的洗礼之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新青年》的战斗与批判传统。鲁迅认为《语丝》是:“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2]171仅鲁迅自己就在《语丝》上发表140多篇作品,该刊的战斗性也就不言而喻了。鉴于此,《新青年》与《语丝》可以看作是一脉相承的时代进步期刊,而恰巧这期间刘半农出版的新诗集——《扬鞭集》则继续地遵循着《新青年》与《语丝》的时代风貌。然而刘半农在《语丝》期间发表的《战败了归来》这首诗却与“五四时代精神”有着一定的疏离。
近代的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武力与话语双重霸权的包围之下,腐败的政治制度使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被当时西方的威胁所笼罩,在处于战败国地位的启蒙者看来,已经拥有亡国奴身份的民族没有任何资格乞求尊严与平等,唯有以武力争取独立自主的“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7]之战争精神,因此,近代以来无数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危亡主动地呼吁一种迎合战争需要的“战斗精神”。
实际上,从清末民初乃至整个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上,鼓吹与歌颂战争的作品不胜枚举,但是以反战及反思战后心灵伤疤的精品却是凤毛麟角。缘于此,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屈辱苦难被时代刻上了深深的“历史印迹”,而当我们陷入到这种“历史印迹”中自暴自弃时,也就丧失了人类对战争之残酷及战后之悲惨的深刻反思。进而言之,人们对战争“不义与不值”的悲恸反思往往是被中国现代文学中所遮盖的“有益”片段,显得尤为珍贵与虔敬。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在中华民族漫长而艰苦地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战争岁月中,这种对战争本身的意义与价值的否定思想不仅是疏离主流叙事的,而且是有悖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乃至是消解在主流话语里的不合时宜或者会遭到禁锢的。新文学家刘半农以独特的“视角与视野”突显了迥然不同的文学遐想,他从多角度来重新审视、憧憬人类光明前途的愿望是令人肃然起敬的。鲁迅曾说:“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8]鲁迅的这段话给人以深深的启发性与警策性,他的这些思想在五四时期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数”。与之相似,刘半农的《战败了归来》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特例”,或者说,在五四激情鼓吹铁血精神与仰慕战争之神的大背景下,刘半农对战争的“反思”颇具有人道主义特点的异质色彩。
《战败了归来》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是一首记录战争题材的诗歌。这首诗以神韵见长,诗中没有讲述战争的原因,也没有交代这场残酷战争本身的正义性与否,只是从人间 “血与泪”的角度来描述这场战争给人们造成的创伤:
战败了归来,
满身的血和泥,
满胸腔的悲哀与耻辱。
家乡的景物都已经完全的变了,
一班亲爱的人们都已不见了。
据说是我的爱妻,
也已做了人家的爱人了!
冷风吹着我的面,
枯手抚摸着我的瘢,
捧着头儿想着又想着,
这是做了什么个大梦呢?
一班亲爱的人们都已不见了,
据说是我的爱妻,
也已做了人家的爱人了!
该诗的灵感来自一幅叫做“战败者”的刻铜画,画中一位衣衫褴褛的战败“英雄”坐在破屋旁的一块石头上,两手捧着头,悲与泪倾注在死亡与颓废的脸上。刘半农对画中这位“英雄”战后凄凉的遭遇是深刻同情的,同时也透露出了反战的信息,他简练的笔触写下了对战争的控诉:这位归来的“英雄”无疑是这场战争机器的精致组件之一,个人永远臣服于不可撼动的国家招募的“战争律令”,毋需说战争与杀伐的动机与否。反之,战争与杀伐也能诱发人们反思“非人性的意欲与遐想”。所以,那种“从金戈铁马到袍泽之情,从投笔从戎到马革裹尸,多少壮烈的意象吸引一辈辈青年志愿献身,生死许之”[9]的乌托邦式愿景——在战场与情场“双失意”后将受到人们的怀疑与省思。刘半农这种近乎实录地描写生存与毁灭不仅丰富了诗歌本身的“象征性”表达,同时也见证了战争与杀伐对女性“献身与陷身”的无情戕害。妇女与儿童往往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死亡、病患、失踪或者为了活下去的“献身与陷身”是她们在故事中的角色,尤其是女性,不断地成为串演的主角。这些女性梦游般地与爱人邂逅或分离的“情爱沧桑”往往演绎出了诗歌中悲惨的乌托邦,由此“自我泯灭”的无奈选择有时是一个社会无法回避的悲剧结局。正因为如此,妇女的生存、地位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应该关注的问题。刘半农借战败归来“英雄”的境况所要表达的是一个爱和平、爱生活、爱妻子之“英雄”的悲惨结局以及战争与杀伐不但给主人公温馨而幸福、自由而快乐家庭所带来的现实伤害,而且给被卷入战争中的众生灵以巨大的精神损毁。当战争的绝唱与绝灭上演之后,这些“英雄”的还乡不仅仅是现实的还乡,更应该是奋勇与苍凉褪去之后的强烈而纯洁的精神还乡。毋庸讳言,在人类探索与追求世界永久和平的进程中,残酷的“人间之血战”(无论大小)的的确确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疯狂的罪恶”。从与“五四时代精神”上来说,《战败了归来》是与五四时代的呼唤相疏离的一首诗,但是战后的反思才是该诗的核心所在,所以才具有不同寻常的超时代意义。
三、重写与颠覆:“疯人”与“狂人”的大相径庭
《京报副刊》一直是《语丝》的阵地之一[10],刘半农在此发表了一首《疯人的诗》,该诗如实地记录了一个“疯人”自言自语的疯话,这是与“五四时代精神”完全疏离的一首诗。
在多元价值共存的五四时代,“狂人”“疯子”“超人”这些常常被看作“异类”的形象已经成为新文学家创作的素材之一,但是“狂人”“疯子”“超人”从医学角度来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有精神疾病的人,相反他们是悖逆传统与世俗的“精神界斗士”,是封建旧制度的反抗者与破坏者,二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他们具有现代人的思想与思维,具有进步的意识与改革的要求,同时也具有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光辉历史。这些“狂人”“疯子”“超人”的另一大特点还在于他们“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事物。实际上这些“狂人”“疯子”“超人”是五四时代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写照,更是一些敢于挑战传统世俗的“超前斗士”形象。鲁迅笔下 “狂人”与“疯子”的系列形象是为了让昏懵的国人变清醒,化无用之徒为有用。因为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已经站在现代化前端的门槛上,对所谓“现代主体”进行了冷静的谛视,他对“新社会”的预言不脱急切的道德焦虑,他所描绘的“狂人”与“疯子”的集体参演更是对蒙昧大众惯性思维的一次有意义的“汰旧更新”。鉴于此,那些被大众认为是“狂人”与“疯子”的形象恰恰是五四精神界的“启蒙斗士”,在他们身上呈现了历史的必然和突破历史黑暗与愚庸蒙昧的决绝姿态。此时,新文学家刘半农的笔下也出现了“疯人”的形象。然而,“疯人”与“疯子”只一字之差,但是刘半农所描写的“疯人”却是真正的发了疯的人。“疯人”与“狂人”“疯子”“超人”都带有精神受损的时代征候,但前者是受封建礼教毒害的“被吃者”,后者是已经觉醒了的且冲破蒙昧思想的“觉醒者”。在这些精神受损者的身上不仅寄寓着民族性危亡的隐喻,也寄寓着新文学家们的“人道主义情怀”。刘半农的这首《疯人的诗》并没有显示出在五四精神线上或在五四延长线上。相反,刘半农诗中的“疯人”与五四时代的“狂人”“疯子”“超人”有着很大的区别,二者基本上处于意义的悬隔与不搭界的状态。在该诗中,刘半农近乎以“实录”的笔法记录了法国巴黎街头一个“疯人”的所言所语,抑或可能是刘半农自己内心的写照:
哈!哈!哈!
我把我静的眼睛看你们动!
我把我动的眼睛看你们动!
这样…………
这样…………
永远是这样…………
丑…………
但是你们说,
自你家坟墓里的祖宗以至你粪缸里的蛆虫都是这么说:美!
…………
你说我是疯子吗?
你看不见你,
犹如我看不见我。
刘半农在这首诗开头的小序中作了简要的说明:《疯人的诗》一共有两首,第一首是1924所做的长篇诗歌,有二三十张稿子,但已经遗失。[11]目前我们看到的是1926年创作的第二首《疯人的诗》,可是个中的详细缘由并没有介绍,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刘半农在“疯人”身上没有寄寓着多少“五四时代精神”的深刻涵义,诗中没有精警与寓意,也没有虚矫与繁华,唯一的一点意义是“疯人”对自己曾经的过往有着一丝丝虚荣与怨怼的回忆。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家是借助文学来揭示问题、针砭时弊的,且用文学来启蒙愚昧的时代,以此来挽救那些精神上被绞杀和陷入旧有伦理困境的芸芸大众。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确证了现代中国人的人生价值与生命方式的交错,规引着后来的新文学家的艺术旨归与精神倾向,其中“启蒙思想”无疑成为新文学的时代先锋。就已被锁定的时代话语权利与文学价值的圭臬来说,刘半农的这首诗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历史印痕,因此,也就近乎一种“零价值”。然而,从文学历史的进化角度来看,这种“零价值”并不一定“无价值”,因为任何一件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与时间性,今天看似“无价值”也许正蕴涵着未来“超价值”,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一种无法言明的吊诡。
四、从文学革命“闯将”到“隐士”的潜隐
毋庸置疑,刘半农以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拥护者、参与者的身份与“新青年派”形成了并肩前进、协同作战的亲密战友关系。就是这样一位奋勇前进的新文学家,由于非当时“章门”(章炳麟)弟子、非某流派作家且仅有中学肄业资历的刘半农在北大初期备受学历歧视,尤其是一直以来并肩作战的战友和朝夕相伴的同僚胡适的所言所行深深地刺痛了刘半农的自尊心。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提到:“来到北大以后……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不起他……遂想往外国留学。”[12]此刻,身在全国最高学府中的刘半农的郁闷之心可想而知,为了解心头的这股闷气,刘半农毅然绝然地留学英法。然而在1925年获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的刘半农,归国后一下进入了“沉潜期”,虽然不时地创作一些杂文与诗歌,但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语言学研究之上,从此以后刘半农更加疏离于五四。一方面归国后的刘半农由于受到西方教育背景与教育理念的影响,他寻求向学术皈依的心态明显,这就与五四的距离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刘半农的文学创作理念开始疏离于五四,原因是他对五四新文学激进派的看法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与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也是他对以往文学创作动因的再审视。由此观之,刘半农认为时代的变化对于个人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当他承认“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就已经间接地承认了与时代疏离的态度,后来归国后的一些印证也确实如此,刘半农一下子钻进了书斋,潜心学术,很少有像五四时代那样激情的个性作品问世。因此,刘半农这段“隐士”或是“落伍”的偏移时期极容易被人怀疑乃至非议。自1932年以后,刘半农陆续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上发表打油诗,共计63首之多。他和林语堂等人相唱和,文风开始幽默起来,其中自注自批的打油诗集《桐花芝豆堂诗集》可以为证。这时的刘半农,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出五四时代的“勇士气质”,诙谐与幽默成为他的“代号”。这63首打油诗大多是调侃一些日常生活的琐碎事件,更谈不上多么重要的社会意义。例如:《偷银盾》描写小偷的狡猾,《文白之争》中“引注”运用的戏谑与无聊,《一变》中本来是有鼓励爱国的意愿却变成了无聊的谩骂,《答林妹妹》描写林黛玉状告刘半农抄袭其诗句无聊冤案,《阅卷杂诗五首》无情地嘲弄学生卷中的错别字、病句等,这些毫无价值、毫无意境的诗作显得极为无聊。当然,在《桐花芝豆堂诗集》中有个别的打油诗,针砭时政、剖析问题仍然有一定意义。如《汽车铭》,《双易篇》,《民国二十二年国庆》《有所不知》《后煤山》等,但这些诗终究与五四有一定差距。刘半农这一失去五四战斗热情的姿态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叛徒与隐士在现实社会里……周作人林语堂还不够典型……可以举出刘半农,那发展的道路确实是由叛徒到隐士的。”[4]157所以,从《新青年》《语丝》到《论语》,从一种边缘到另一种边缘,从开始构建“勇士气质”到后来沉潜于“隐士气质”,无法自控的命运与“消沉”的超脱是一种现实的悲哀。然而,在历史采撷事实之下,刘半农不仅迷失在自己的蓝图中,而且已经完全疏离了五四。
五、结语
以三首诗与五四的“契合与疏离”之关系来探讨刘半农只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知微细节,在现代文学史的漫长进程中,文学本身就是人类心灵与历史的记录。刘半农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完全遵循已经“被规划”好的轨迹前行,相反,他以自己的信仰在理想与现实的场域中坚定地选择了自我的存在方式。在不断的寻求与失落中,刘半农选择了最初饱满的激情与最终痛楚的隐抑。这里有诸多复杂的历史因素,兹不赘。不论是“叛徒”也好还是“隐士”也罢,对于新文学作出过诸多贡献的刘半农,其创作不应该是一个被“束之高阁”的现实存在,然而“以‘五四’为时间节点和精神节点的系列事件在历史的建构和想象中愈来愈被纯化为一种价值尺度,一种精神表征,乃至一种道德立场”[13],所以,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历史事件锁定了特定的历史人物,每个生活于其中的独立个体都难逃历史时代宏阔的掌心。剖析刘半农的文学作品同五四的契合与疏离,是对历史弊端的一种有益消解,从而获得了矫枉过正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当我们回顾那些复杂与鲜活、荡涤与摒弃、继承与复苏的历史细节时,历史本身固有的丰富性与曲折性只有在当时“沉潜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辨清其合理性与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