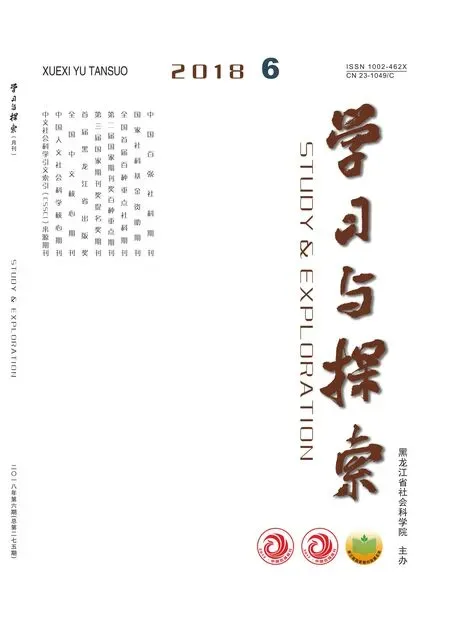“天开皇清”:计六奇的历史书写与政治认同
2018-02-20刘文鹏
刘文鹏,屈 成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计六奇,天启二年(1622)生,卒年不详,撰有《明季北略》《明季南略》①① 本文将《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分别简称《北略》《南略》,统称时则称《南北略》。等,该二书是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计六奇及其著述的研究尚显薄弱,仅有几篇论文专门探讨,或在些许史学史著作中有所提及。对计六奇及其史书较早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张崟先生,他是发现和整理该书旧本的主要学者之一。张崟先生于1964年开创性地撰写《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一文,对计六奇的生平、撰写《北略》等书的经过及全书的义例、资料来源及其版本问题做了详尽考证和基础性分析,为后世研究者所倚重。因此,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南北略》时,专门将此文附于《北略》书后[1]。后《南北略》点校者任道斌在张文的基础上专门为计六奇作传,对其生平详细论述,分析计六奇的撰写动机与时代背景[2]。另一位点校者魏得良亦进一步论述了《南北略》的版本与史学价值及缺憾[3]。中华书局出版《南北略》后,此书成为重要史料来源,所载史事被广泛采择到明末清初的历史叙事中。
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计六奇及其《南北略》等史书的研究成果总贯穿一个相似的价值判断,即认为计六奇撰写史书的动因之一就是为了寄托他的“民族思想”,特别是华夷大防的政治思想,从而表达他抗清反满的态度,也就是将计六奇视为明朝“遗民”。
奠定这种价值判断基础的是张崟,他认为“计六奇的历史著作,还是他课余劳动的结晶。……他炽烈的民族思想要有所寄托,于是他要从事著述;他生长在一个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战火纷飞的时代,他的民族思想的最好寄托,就是记录这个时代。《南北略》两书即撰写于此时。所馆诸家,仅知其姓,不详其名,可能都是些或多或少地具有民族意识的故家。特别是社土夅王氏,‘门墙清简’,对他的编写工作帮助很大。”[1]731
张崟关于计六奇民族思想的观点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接受。任道斌认为“明清之交发生了许多反压迫、争自由的可歌可泣斗争,有些民族感较强的知识分子,为了不使这段历史湮没,冒着杀头毁家的危险,千方百计地搜集资料写史,计六奇就是其中之一”[2]201。胡晓彤也谈到:“济之异母弟谋,字献之……清顺治三年(1646)仲冬十一日,起义抗清……兵败被杀,这对青年时代的计六奇当有很深的影响。”“计六奇撰写《明季南北略》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为了寄托他自己的民族思想。”[4]葛星则从“充满敌意和歧视的字眼称满清”等六个方面论述了计六奇的华夷大防思想[5]。一些论著甚至认为,计六奇书中称赞清朝的话语是其“为自己撰写晚明历史,避触时讳,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6]。
很明显,在这些论著中,计六奇被塑造成为一个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史家,他的著作也被视为记录可歌可泣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辉典籍。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颇有值得商榷之处,这些价值判断可能并非计六奇要在书中表达的思想,而是当代学者的民族主义观点不断叠加到计六奇史书中的结果,或许不自觉地带有一些“强制阐释”的色彩。为此我们应该回到计六奇的著作本身,对《北略》《南略》进行全面分析,避免陷入望文生义、以偏概全的困境。
一、对目前有关计六奇政治认同、史学思想之学术观点的反思
计六奇传世最广的著作当属《北略》与《南略》二书,以往研究者已有详论,此处略作概括。《北略》全书共二十四卷,记事起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迄至崇祯十七年(1644);《南略》全书十六卷,记事起自甲申四五月,迄至康熙三年(1664)。学界多以为《北略》《南略》撰成之后并未刊刻,直到嘉道之时才刻印流传。但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言有海盐朱氏旧藏康熙活字本[7]。此说也得到韦力的支持,他指出《北略》有康熙十三年(1674)的刻本[8]。雍乾之际文狱大兴,许多书籍遭到禁毁,《北略》《南略》也转移私下流传,①据张崟先生考证,《南略》列入《禁毁书目》。见张崟:《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计六奇著,魏得良、任道斌点校,载《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32页。至嘉道时期方才大量刻印出版。②谢国桢、韦力两位先生所言康熙刻本是否存在尚待考证,但是笔者查阅史料检得全祖望在作文时曾参看《南/北略》,其在《淡巴菰赋并序》中有“梁溪明府,指为旱魃(原注‘见《南北略》’)”一句,可知全祖望曾参看《明季北略》并引用。全祖望所参看是否是康熙年间的刻本,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参见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此后,该二书始迅速刊刻流传,版本渐多,但都经过删削,并非计氏原稿。此外,另有并不常见的三件稿本:一为北京朱天明购自苏州的《北略》原稿本、顺德邓氏所藏《南略》精钞本;二为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旧钞本;三为常熟曹大铁藏钞本。③参见《国粹学报》1908年第4卷第4期,第128-131页。后中华书局以杭大钞本为底本,综合曹大铁藏本、通行诸本以及其他史书相互参校,补遗正讹,于1984年出版,是为迄今最为完整之版本。本文所据即此本。
有的研究者认为,计六奇在《北略》与《南略》二书中表现出对明末朝政的不满,对清朝政策的愤怒,对故国的哀思,对既成事实的无奈。计六奇作为传统士人,有着强烈的正统观,主张严夷夏之防,甚至类比于王夫之的思想,《南北略》载有满清的大量暴行以及军民的反抗斗争,体现了计六奇对他们的强烈不满[5]。这种思想的形成,主要根据有二:其一,书中出现大量“敌”“虏”“酋”“东酋”“东夷”等字眼;其二,书中大量记载了满清暴行与抗清斗争。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北略》与《南略》二书中确实存在,但笔者以为这跟计六奇引用参考史料的习惯有关。张崟先生详细考证了计六奇所做《南北略》的史料来源,其中不乏当时名人的笔记、史书,将满人称之为“敌”“虏”“酋”“东酋”“东夷”,是晚明以来极为常用的说法。计六奇采择史料,大都保留其原貌,原文照抄,略作字词修改及顺序调整。《北略》卷二四《辽彝杂志》:“辽东之破,余馆于邹平张师家。是日,忽大风蔽天地,觌面不相睹。广宁之破,余亦计偕在都,连日风霾,东望但见黑气蔽天而已。”[9]卷二四,720计六奇生于天启二年(1622),辽东之破在天启元年(1621),而广宁之破时,亦在计氏出生之年。可见此段话语应是计六奇直接抄自参考文献,这充分说明计六奇在进行历史书写时,往往并未过多删改史料。笔者查得《北略》卷二四,除《北略总说》一条之外,其余六条均摘抄自夏允彝所撰《幸存录》等六篇[9]。且基本上是原文摘录,仅有个别字词删改。这是传统史书的编纂习惯使然,并不足以代表计六奇的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只有从计六奇对于各种史事的评判按语之中,我们方可真正了解他的思想与价值判断。
第二,关于大量满清暴行与抗清斗争的问题,计六奇在书中确实多有记载,论者所列扬州十日等也都属实,但笔者以为以往研究者的解读并不全面。
首先,计六奇并非仅仅记载了满洲人的暴行,对于明军和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残暴行为也多有所记载。 比如明军烤食农民军[9]卷一二,205、马士英标兵过淮安劫掠妇女[9]卷二〇,457、李自成水淹开封城[9]卷一八,317-321、农民军屠害凤阳百姓之
事[9]卷一一,172-177、张献忠屠蕲水城[9]卷一九,375等等都如实记载。可见,计六奇对于明清鼎革之际各方军事力量对于下层民众的屠害都记载无遗,这充分说明他并非是站在华夏汉族立场之上,仅仅是痛恨满洲暴行而已。
其次,我们再分析计六奇如何记载扬州被屠之祸。扬州屠城常被视为满人入主中原暴行之代表,计六奇在书中记曰:“扬州初被高杰屠害二次,杀人无算。及豫王至,复尽屠之。总计前后杀人凡八十万,诚生民一大劫也。”[11]卷三,205在这里,计六奇亦揭示明将高杰首开杀戮之实,并未隐讳。如果计六奇仅仅是为表达夷夏之防思想,此处完全可以将高杰暴行隐去不载,将罪责全部推给满人。而且他在后面又加按语,来表达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认为自宋代以来,繁华扬州先后遭三次大劫难,即元兵长期围城,城中“死者枕籍满道”,明太祖军克城“止余居民十八家而已”[11]卷三,206,以及此次清军的克城之祸。 计六奇加此按语是将扬州之祸放在中国历史一个长时段之中去做纵向审视,即扬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故而兵连祸结之惨事一再上演。相比之下,清军入南京后并没有大开杀戒,对此,计六奇对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赞赏有加,认为多铎入南京有六事可取:一不杀百姓,二斩抢物兵八人,三骂李乔先剃头,四放妇女万人,五建史可法祠,六修太祖陵。所以,计六奇赞之曰“颇有古贤将风”[11]卷四,221。以此综合而看,计六奇将明清鼎革之际各方对于黎民百姓的屠害记载无遗,无非是感叹“斯民何不幸而罹此劫也?”[9]卷一一,177,因而对保民之举给予高度评价。因此可以说,在计六奇观念中,扬州之祸并非夷夏族群之间仇恨的结果。所以,脱离计六奇全书的情境,单独把扬州屠城之事拿出来放到后世的民族主义观念之下进行评判,就无法反映作者本身的思想。
最后,再来看计六奇如何看待抗清问题。《南略》卷四《王献之不屈》记载:“王谋,字献之,号春台,无锡人。……丙戌仲冬(顺治三年),公将起义……公皮靴步行,道复滑,萧守驰骑突追,遂被获……因下狱。此十一月十一日事。……予思当日驱市人围郡城,犹以螳臂当车,羊肉投虎耳,其迂戆固不足道。所难者濒死不屈,狱开不逃,虽古之烈士,何以加焉?”[11]卷四,238-239在这里,计六奇要赞扬的是王献之等人英勇就义、不避死难的壮烈行为,但他并不赞同王献之的抗清行径,称此举犹如螳臂当车、羊肉投虎,“其迂戆固不足道”。如果将称赞抗清斗士的话语看作是计六奇反满抗清观念的表现,这实在是对他原意的误解。
总体而言,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争、杀戮与暴力给计六奇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些都持一种极力批判的态度,在历史叙事上并没有为某一方做任何隐讳,而是秉笔直书,将所见所闻编入书中,只是尽到一位史家应有的责任,并没有借此表达忠明反清、华夷之辨思想。反倒是当代的很多研究者,用一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眼镜审视明清更替,对计六奇史学思想、政治观点的归纳也带有很强的先入为主的主观性,希望找到计六奇夷夏之防的思想。故而更加主观地采择史料,往往用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未能把握计六奇在书中所表达的整体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故意”误解了计六奇。
二、计六奇的史学思想
在明清鼎革这个巨大的历史变动时期,诸多杀身成仁的忠义之士,为“遗民”政治话语形成提供了足够多的素材。
“天崩地坼”之时,短暂时间内多个政权的建立使得士人在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时难以抉择。其中,最为后世瞩目的当然是那些殉节先帝、杀身成仁、誓死抗清的忠臣烈士。在他们眼中,殉节乃是为人臣子的责任,“人臣委身事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大义,非可以官之大小,并在朝在差、在籍南北作分别观也”[9]卷二一上,549。 譬如东阁大学士范景文在李自成入京前三天即已经绝食,城破之日当即自经,其时尚未传出崇祯自缢的消息。后世对其评价甚高:“公决然一死,不复狐疑,盖公素志定也”,此“可与宋室文山并美千古”[9]卷二一上,505。 与文天祥并举,可知范景文在清初舆论中的至高评价。又如刘宗周在清军进入扬州之后举义不果,遂绝食而死。后世赞曰:“公以宿儒重望为海内清流领袖,常以出处卜国家治乱,而终以节见。悲夫!其论学也,以为学者学为人而已,将学为人,必证其所以为人。”[11]卷五,283在后人看来这种不仕贰朝,不做贰臣的品行才是“所以为人”的基本准则。孙源文临死前说“家受朝廷特恩,死吾分也”[11]卷四,238,黄淳耀更是高呼“呜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知余心”[11]卷四,264。 再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遗民态度与抗清意志,无不为士人所称赞。
这样的忠义行为及由此而形成的“遗民”政治话语,迄今为止仍在影响着我们对历史事件、人物的价值判断。然而问题是,这些人的忠义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形成群体意志。明末清初汉人对满人入侵的抵抗,远没有南宋建立之初民族间对抗程度之激烈,毕竟在两宋之际出现了像岳飞、韩世忠这样大规模、成建制率军抵抗金兵的壮举,金军终究不得南渡。虽然也有不少归附金政权者,但南宋朝廷强有力地维持了对政权的领导力,即使是岳飞这种英雄式的人物面对朝廷的旨意也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而这是在南宋初年形成卫国抗金群体意志的一个重要前提。但在明末崇祯帝死后,南明朝廷根本就没有获得对明朝遗留军政力量的实际领导权,忠于明朝的群体意志已经荡然无存,也就无法再形成对个体的约束力。导致这种忠明群体意志丧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价值判断的异化,即为什么要保持对明朝的忠义?或者说明朝是否值得更多的人为她杀身成仁?清朝是否就一定不值得归附、无法让人安身立命?对于更多的下层士人和普通百姓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计六奇就是这样一位下层士人,笔者以为,他对明清更替有着不同于那些忠明大儒的思想,通过对《南北略》等书的编纂,他把对时局的认识贯彻其中。因此,从他的历史书写中我们或许可以透视下层社会对于明清更迭、清朝定鼎的态度。
1.博采众说,勾稽历史,褒扬忠烈
如张崟先生所梳理,计六奇撰写《南北略》,采择当时所能见到的大量史料,也访闻民间,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对重要的事情加按语评论,以一种非常可观的方式勾稽历史碎片,目的是在叙事中发人深省,总结明亡清兴的历史规律。在这其中,计六奇不惜笔墨,记载忠于明朝之士的忠义行为,贬抑失节迎降、弄权利己之辈,以图达到“贤奸之用舍……概可见矣”[9]1之目的。
举例而言,计六奇对于陈璧所作《论贼必灭有八》称赞其“论列贼之情势,无一语不确,虽讬空言,要皆实事”[11]卷一,37。对于那些批评权贵的士人则是赞誉有加,在《吴适论云雾山》中,称赞吴适不畏权贵,批评马士英倡言开采云雾山禁地,其“直言无讳,虽以此忤权相,身轻似叶,名重如山”[11]卷三,168。 殉节之士,六奇更是称赞。 在他看来“人世最重莫如身命,士大夫所以殉难者,亦以节不可失,名不可败,故不得已舍此而取彼也”[9]卷一九,386。 “献忠逼让城,(房)景春曰:‘吾头可断,城不可让也。’贼益攻,景春发砲殱贼,贼以棺覆首,四面环围。守门指挥张三锡为内应,城陷。杨道选巷战死,景春被执,劝降不从,命拽出斩之。子生员鸣鸾抱父尸哭骂,贼复手刃。仆陈宜亦被杀。朱邦闻与其家人俱不屈死”,对此六奇称赞“死忠死孝,日月光昭,景春、鸣鸾之节烈矣!至若道选、邦闻宁与令君同日而死,不与叛逆同日而生,岂非皆不二心之臣哉!”[9]卷一五,270而夏允彝赴池死,陈子龙投河死的气节,六奇称赞“卧子与夏彝仲同举进士,房艺一出,脍炙人口。东南士子称大名家必曰陈卧子、夏彝仲。是两公者生而文章名世,没而忠义传世者也,齐驱并驾,洵为邦家之光矣!”[11]卷四,266、268
褒扬忠烈的另一面,计六奇对弄权权臣、退缩将领和失节投降者进行了严厉批判。对于擅权弄国、无能之辈直斥为“小人”,马士英特举先朝魏党阮大铖,六奇批评道:“从来小人当国,止狥一人之私暱,而不顾天下之是非,止弄一时之威权,而不顾万世之公论。初不过快所欲为,而其后国事愤裂,身名未有不随之丧者。”[11]卷一,43对于马士英离间鲁、唐二藩则骂之曰:“马士英既断送南都,复离间闽、浙,小人之败坏国家事可恨如此!”[11]卷六,291清军毁方国安大军锅灶,方即败走。六奇痛骂:“国安拥兵众二十余万,以锅灶之碎遂未战而逃,小人之贱者也!可斩!可斩!”[11]卷六,291-292对于北京城陷从逆诸臣,六奇条例明目,让其传世以警后人。并言道:“一时出狱者甚众,从逆当不止此,恨不能悉知也。”[9]卷二二,641而对于昔日崇祯癸未年的馆选庶吉士更是嗤之以鼻,“癸未馆选三十六人,俱济济贼庭,列在刑辱者止万发祥一人耳”[9]卷二二,619。
不过,计六奇也认识到,相对于殉节、抗清的士人来说,更多人选择了奉迎新朝。在他的统计中,殉节崇祯皇帝的文臣只有21人,而变节逃逸、大节有亏者有227人之多。①另据陈永明统计,迎降者高达四千多人。参见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世人感叹“国家不幸,罹此凶毒,宗庙震惊,至尊以身死社稷,臣子殉难者,仅北都二十余人。而在差籍诸大臣,受国恩深厚者,曾无一人奋决”[9]卷二一上,549;“甲申之变,降臣颇多”[9]卷二二,648,毫不足怪也。
2.鞭辟事理,于叙事之中反思、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
计六奇所撰史书主体是明朝政权,其线索有两条:其一是明末政权及南明余绪的历史变迁,其二是农民军的发展轨迹。正如他在《北略》最后做的总结:记载明朝史事,先中央后地方,以凸显根本所在。记载农民军史事,按照其发展的时间顺序,以表明农民军的发展轨迹[9]卷二四,728。但还有一条线索计六奇虽未言明,但也暗含其中,即清朝势力的发展。对此笔者将在后文中详述。
明朝必亡,难以挽回,这是计六奇一再强调的问题。如卷一三《圣驾巡城》:“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图数十里之城,城亦安足恃哉?即有修葺,亦兵、工二部事耳,岂万乘所宜亲履者?且自天子以至军民,数十万众奔走两日夜,服用移绕于外。 乱亡之兆,已于此见矣!”[9]卷一三,220-221
在《北略》之末,计六奇用了很大篇幅探讨了几个对明朝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流寇何以乱天下、东夷边事问题、明季致乱之由、国运盛衰、门户党争等,这些是他对明清易代问题的集中反思。特别是对明朝之衰亡,他总结道: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与焉。一曰外有强敌。自辽左失陷以来,边事日急矣。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贫矣。且频年动众,而兵之逃溃者俱啸聚于山林,此乱之所由始也。二曰内有大寇。使东师日迫而无西顾之忧,犹可以全力稍支劲敌,而无如张、李之徒又起于秦、豫矣。斯时欲以内地戍兵御贼,则畏懦不能战;欲使边兵讨贼,则关镇要冲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剧贼益横而不可制。三曰天灾流行。假流寇扰攘之际,百姓无饥馑之虞,犹或贪生畏死,固守城池,贼势稍孤耳。奈秦、豫屡岁大饥,齐、楚比年蝗旱,则穷民无生计,止有从贼劫掠,冀缓须臾死已矣。故贼之所至,争先启门,揖之以入,虽守令亦不能禁,而贼徒益盛,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四曰将相无人。当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纲,将如汾阳、武穆,或可救乱于万一。而当时又何如也?始以温体仁之忌功而为首辅,继以杨嗣昌之庸懦而为总制,终以张缙彦之无谋而为本兵,可谓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诸将,不过唐通、姜瓖、刘泽清、白广恩之辈,皆爱生恶死,望风逃降者。将相如此,何以御外侮、除内贼邪?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乱天下,况并见于一时,有不土崩瓦解者乎[9]卷二三,682?
计六奇从内忧、外患、天灾、人事四个方面总结了明之所以亡者。“庸奸之列朝廷也,贪污之遍郡邑也,懦将悍兵之耗饷于营幕,而残贼猾寇之蹂躏夫海内也,俱天之所以开大清也。呜呼!天之所废,天之所兴,人孰得而止之?”[9]卷二三,681此诚可谓明之所以亡者。
至于南明,在计六奇看来,更是乱象丛生,难有作为。弘光一朝奸佞弄权,只知为己谋利。“是时士英卖官鬻爵,乡邑哄传。予在书斋,今日闻某挟赀赴京做官矣,明日又闻某鬻产买官矣,一时卖菜儿莫不腰缠走白下,或云把总衔矣,或云游击衔矣,且将赴某地矣。呜呼!此何时也,而小人犹尔梦梦,欲不亡,得乎?”[11]卷二,99其他小人则是阿谀权贵,所谓“立朝后一惟阿党是狥”是也[11]卷二,105。 御史游有伦曾上奏批评朋党:“今日国事淆乱,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明知君子进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甚至常人所不忍道者,渎于君父之前,其视皇上何如主乎?台省中微有纠劾,则指为比党,相戒结舌,真所谓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也。”六奇评论道:“是时陆朗、黄耳鼎、朱统金类頁疏攻姜曰广、徐石麒、刘宗周等,各予告去,故有伦奏此,可谓抗疏矣。不知句尤骂得马奸一班小人好!”[11]卷二,108-109其可见计六奇对当时朋党倾轧、奸佞用事愤恨至极。
此外各藩林立,各争大统,同室操戈,难成一统。“马士英既断送南都,复离间闽、浙,小人之败坏国家事可恨如此!然三月士英唆斩闽使,六月钱邦芑疏斩鲁使,两国自残而敌乘之以入,俱小人为之也。”[11]卷六,291鲁王罹隆武、清军夹攻,而发兵西征,计氏评道:“大敌在前而操戈同室,晋之八王可以鉴矣。夹两大间而与为仇难,以是求济,未之前闻,方、马真罪人哉!”[11]卷六,291计六奇分析当时全国形势,指责鲁、唐二藩不重情势,不懂唇亡齿寒:“天下之势,当论其轻重大小,昔七国时,势莫强于秦,苏季子合六国以拒之,得安者十五年。后秦日夜攻韩、魏,而齐、楚不救。及韩、魏亡,而齐、楚亦遂随之矣。清势重若泰山,即昔日之秦不足以喻,而鲁以新弱犹未及韩、魏。隆武虽不悦,而同舟之谊、唇齿之言,不可不思。姑以大度优容,连兵共拒,俟事势稍定,大小自分。不此之计而自相寻仇,则鲁势必折而入于清,而闽之亡可立待矣。昔晋灭虢而虞亡,秦灭韩、魏而齐、楚亡,晋灭蜀汉而吴亡,八王自相残灭而刘、石滋强,元灭金而宋亡益速,古今之势,大可见矣!”[11]卷八,324-325唐藩隆武更是不思进取,敲诈于民。郑芝龙“令抚按以下皆捐俸助饷,官助之外有绅助,绅助之外有大户助。又借征次年钱粮,又察括府县库积存银未解者,厘毫皆解。不足,又大鬻官爵,部司价银三百两,后减至百两。武劄仅数十两,或数两。于是倡优厮隶,尽列衣冠”。对此,六奇斥之曰:“国家新造,当内抚百姓,外御疆场,或可稍延。乃助饷卖官,较士英当国为更甚焉,安得不偾乎! 《易》言:‘负乘’,洵矣。”[11]卷七,311郑芝龙不抚百姓,反强索于民,实在是居非其位;而永历一朝则是东奔西窜,“举朝醉梦”[11]卷一二,420-421,难成气候。 六奇叹曰:“当时国势危如累卵,清势重若泰山,而举朝文武犹尔梦梦,欲不亡得乎!”[11]卷一二,421南明各藩种种乱象表明,“国势至此,有不土崩瓦解者乎?”[11]卷一二,425
对于明末的历史,计六奇经常通过把很多大臣的重要章奏完整记录下来的方式,以达到存史之目的。如计六奇记载了李自成初起时,陕西原通政使马鸣世曾上疏论陕西一带的形势,“以秦视秦,未尝以天下安危视秦,而且误视此流贼为饥民,至令势焰燎原,莫可扑灭。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饷,为一劳永逸之计,恐官军惊于东,贼驰于西,师老财匮,揭竿莫御”。马鸣世的这些建议当然没有受到重视,十年后,李自成势力由陕、山入燕赵,明朝危在旦夕。计六奇在书中抄录了马鸣世的这份奏章,并论之曰:“马生之言,若操左券。”[9]卷八,140明末不乏文韬武略者,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像马鸣世这样有见识的大臣在明末绝非少数,只是熊廷弼传首九边,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史可法孤战而亡,在一个缺乏基本决策能力的朝廷统治之下,又有谁能够有所作为?计六奇对当时历史的记载表明:朝廷决策能力、指挥能力的丧失是导致大明王朝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计六奇非常懂得这种存史的方法,也是一种寓论于述中的叙事方法,无须多论,其中的微言大义已经跃然纸上。
三、计六奇的政治认同及其对明清鼎革的历史构建
探讨计六奇的政治认同,必然涉及他的身份界定,即在明清鼎革之际,他是否属于“遗民”?有的学者将明清之际的士人分为遗民、降臣、贰臣[12],计六奇未曾入仕,所以谈不上是降臣、贰臣。而关于“遗民”的界定,学界也有很多分歧,或以1644年是否成年,或以是否参加清朝科举,总是难以概括全面、准确,此不赘述。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探讨个人的政治倾向,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关于计六奇本人的生平,学界已经有了研究。①计六奇属于下层士人,人物资料稀少,关于计六奇的生平,张崟、任道斌、魏德良等已经做了很多梳理和研究,本文主要借鉴以上几位学者的成果。计六奇,字用宾,号天节子,又号九峰居士。生于天启二年(1622),卒年不详。其父曾游历各地,闻得诸多传闻轶事,所撰“手记”为计六奇提供了许多史料参考。母胡氏,为同邑胡时忠妹。胡时忠是无锡人,为崇祯时进士,南昌府推官[13]。曾任御史,屡言时政得失,京师号为“冲锋”。后来朝廷曾拟派胡时忠巡按福建,但未果不行,于是胡时忠归隐养母,卒于康熙庚戌春。胡时忠为黄道周徒孙,即六奇所谓“道周为沈延嘉之房师,沈又为舅氏之房师也”。这一身份对胡时忠在明清之际的出处有很大影响,因之入清以后以遗民身份不仕清朝。计六奇妻杭氏,乃杭济之之女。杭济之也是一个对计六奇影响很大的人,计六奇自幼常读书于其岳父及舅父家中。19岁时“随内父杭济之先生读书于洛社”,21岁时“随内父杭济之先生读书于舅氏”。顺治六年(1649),27岁的计六奇“入城应试”,顺治十一年(1654),又再次参加科考,但两次均落第。以后计六奇余生皆以教书、著述为业。
虽然计六奇的舅舅是一个态度坚决、拒不仕清的明朝遗民,计六奇的学业也多受他启蒙,但计六奇两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行为表明他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致仕而在清朝有所作为,至少他是一个认同清朝合法统治的士人。
计六奇的这种政治取向在当时并不孤立。入清之后,虽然有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诸多海内大儒坚决不仕清者,但对于正值参加科举年龄段的士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效忠清朝以获得个人前途。而且,很多学者关注到,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顺康两朝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尤其博学鸿词科的实施,对扭转明遗民的政治认同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明代大学士陈邦彦之子陈恭尹在入清之初曾致力于反清活动,直到康熙初期仍对清朝持谨慎观望态度,与在朝为官的友人也保持距离、谨慎交往。但到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陈恭尹在诗文之中开始极力称颂清朝的合法统治,甚至颂称“相谓百年来,太平此时独”。他已经由一个有着强烈反清思想的明朝遗民,转而“几乎成了清政权的代言人,绝非前明遗民”[14]。即使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虽然他们个人仍坚持原来的政治立场,但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曾以布衣身份参修《明史》,而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在康熙时期官至大学士,孙奇逢的学生汤斌也官至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并一度被康熙帝延聘为太子之师,汤斌还以理学名臣的身份,得以从祀孔庙。陈永明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颇具启发性。他以魏象枢、魏裔介、王崇简和王熙父子等人为例,证明很多在清初入仕清朝并获得高位的明朝士人,对明朝并没有表现出留恋之情,而是完全投入到为清朝服务的事业中。他们不但没有受到诸如“叛明”一类的诟病,反而在士林之中、社会之上获得赞赏和肯定,成为令人艳羡的成功者[15]。
计六奇科场之上未获成功,没有机会跻身高官之列,但他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即撰写《南北略》等史书来表达他对清朝的政治认同。
第二,计六奇在史书中如何表达他对清朝的认识。计六奇虽然将全书的线索归结为明朝与农民军两条,但在笔者看来,还有第三条线索,即后金—清朝势力的发展脉络,也在他的书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我们应该注意到,计六奇撰写《北略》开篇不是明朝之事,而是“建州之始”“清朝建元”。其起始时间恰恰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这一年明朝加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为什么要以此为全书的起点?计六奇在《北略》书末有专门交代:
《北略》,纪乱之书也。然神宗践祚以来,西夏有哱拜之乱,播州有应龙之乱,朝鲜、辽东有行长、秀吉之乱,乱不一矣,俱不之载者何?以无关于天下之大也。而独始于二十三年者,见皇清封建之始,继明之天下已有其人矣[9]卷二四,727。
在他看来,万历时期明朝虽然有很多内忧外患,但大都无关大局,唯独这一年努尔哈赤被明朝册封,由于是要取明而代之,所以至关重要。可见,计六奇全书布局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清朝,而这才是计六奇编纂《南北略》的核心所在。此后,他也不惜笔墨记录清军在全国各地的行动,清朝在关外的发展、入关、入京及追击农民军,剿灭南明各政权,在计六奇书中都有记载,使清朝的发展壮大在全书中成为一条隐含在明末、南明诸多史料中的暗线。
关于年号纪元的问题。界定明朝遗民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他对清政权的排斥,遗民士人所撰史书大多不会用新朝年号,以表示自己对于新朝廷的不认同。计六奇在史书中,则多处使用新朝年号。比如在卷首自序中即言“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无锡计六奇题于社土夅王氏之书斋”[9]1。而正文中作者在补充说明时也常有“康熙某年某月于何处书”等等。再如《南略》中,自卷二始,纪年皆为南明纪元与顺治纪元同纪,直至南明政权覆灭后,直接改用清元纪年,即自卷十六“投诚安插”条起“以后清纪”。可知,计六奇并不避讳使用新朝纪年,乃至在旧朝无年可纪之时改为新朝纪元。而在其所著《滇粤纪略》中,则是于每卷卷首先书“大清顺治某年”,再书“故明隆武某年”,或“故明永历某年”[16]。可见,计六奇奉清朝正朔无疑矣。
对于各地民间抗清问题。计六奇虽然一再褒扬那些英勇就死的忠义之士,但他并不赞成与清军对抗,如前文所述,他对王献之起义做出“迂戆固不足道”[11]卷四,239的评价。 计六奇在《总论起义诸人》一条中更是总结道:“夫以国家一统,而自成直破京师,可谓强矣。清兵一战败之,其势为何如者!区区江左,为君为相者必如勾践、蠡、种,卧薪尝胆,或可稍支岁月。即不然,方清师之下,御淮救扬,死守金陵,诸镇犄角,亦庶幸延旦夕。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当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11]卷五,277-278时移世易,虽“赤心未改”,然“时事已非”[11]卷一四,443。 对这些人的看法也只能是“其志则可矜矣”[11]卷五,278。
在计六奇看来,当时清朝国势正雄,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南明节节败退,一统之势已然明了。“甲申、乙酉间,清兵南下,至兖、至豫,至淮、扬,以及入金陵,下苏、杭,所至(明军)逃降,莫敢以一矢相抗者”[11]卷五,288,“其势为何如者”![11]卷五,277这种不识大势的抗清举措,实在是“不足道”。
所以当一些地方的百姓在清军压力之下不得已归附清朝时,计六奇也认为可以理解。在清军准备进入南京城时,全城百姓跪求赵之龙,但赵之龙却劝导“扬州已屠,若不迎之,又不能守,徒杀百姓耳。惟竖了降旗,方可保全”,“众不得已,从之”[11]卷四,217。 计六奇对此并无恶评。
可以看出,计六奇在书中一直暗示清朝得天下、明廷该亡的必然性,甚至用一种神秘主义的手法来书写这一趋势。最具代表性的是张真人祈祷的事例。计六奇在书中记载,崇祯帝眼见天下大乱且灾异不断,曾邀江西龙虎山的张真人到京城设坛祈祷,事后奏云:“灾异妖孽,上帝已命北极佑圣真君馘斩收逐矣。国家绵久,万子万孙。”对此,计六奇认为张真人所谓北极佑圣真君就是指的“披发仗剑”的玄武大帝,而清朝崛起于北方,也是辫发入主中原,驱逐李自成,“颇似之”[9]卷二三,664。只是崇祯帝没有听懂这种隐语罢了。
在《明季南略⋅自序》中计六奇写道:“《南略》一书,始于甲申五月,止于康熙乙巳,凡二十余年事,分十六卷。虽叙次不伦,见闻各异,而笔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嗟嗟!祸乱之作,天之所以开皇清也。”[11]1
“天之所以开皇清”,这实际上是计六奇撰写《南北略》所得出的最终结论。表面上看,他把清朝的成功和明朝的衰亡归结为天命,然综观全书,计六奇所列举的种种史料,不过是在证明“庸奸之列朝廷也,贪污之遍郡邑也,懦将悍兵之耗饷于营幕,而残贼猾寇之蹂躏夫海内”[9]卷二三,681,这与其说是天命,不如说是在分析“人力”,是“人力”决定了这种历史必然性。
第三,计六奇撰写《南北略》的时代背景。从《北略》的序言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作者撰述时的时代背景。其《自序》云:
自古有一代之治,则必有一代之乱;有一代之兴,则必有一代之亡。治乱兴亡之故,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独怪世之载笔者,每详于言治,而略于言乱;喜乎言兴,而讳乎言亡。如应运弘猷,新王令典,则铺张扬厉,累楮盈篇;至胜朝轶事,亡国遗闻,则削焉不录。若曰“当苏君时,仪何敢言云耳!”愚谓天下可乱可亡,而当时行事,必不可冺。况清世祖章皇帝尝过先帝之陵而垂泣,为亲制诔文以哀之。即今上登极,亦谕官民之家,有开载启祯事迹之书,俱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书与求书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数十年来治乱兴亡之事,一笔勾却也哉!予也不揣,漫编一集,上自神宗乙未,下迨思宗甲申,凡五十年,分二十四卷,题曰“北略”,以讠志北都时事之大略焉耳。然于国家之兴废,贤奸之用舍,敌寇之始末,兵饷之绌盈,概可见矣。世之览之者,拱璧唯命,覆瓿亦唯命云。谨序[9]1。
从这段序中我们可以知道,计六奇撰写《北略》一书是有感于历代史书言盛多,言衰少;谈治详,谈乱略。针对明末清初这段乱世,并未有史书梳理清楚。而计六奇正是着眼于此,立志记述“数十年来治乱兴亡之事”,从而使得“国家之兴废,贤奸之用舍,敌寇之始末,兵饷之绌盈,概可见矣”,如此即可达还原乱世实相之目的。这种求真求实记录历史的态度在书中屡有呈现。在论及部分灾异所预示的世变时,计六奇也对许多书籍并未记载而发出“诸书不载,何欤?”[11]卷二,104的反问。此种事例较多,恕不赘举。
而促成他撰写两略的另外两个现实因素,一是“清世祖章皇帝尝过先帝之陵而垂泣,为亲制诔文以哀之”,诱发了计六奇撰写明末历史的想法;二是康熙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对松弛,即其所言“今上(指康熙)登极,亦谕官民之家,有开载启祯事迹之书,俱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加罪”。查康熙四年(1665)八月己巳,圣谕礼部:“前于顺治五年九月内有旨纂修明史,因缺少天启甲子、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以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查开送,至今未行查送。尔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着查送……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17]可知计氏所言非虚,其撰述史书之时,清廷确实并未太多关注书中词字。孟森先生早已说明:“清初,禁网尚疏,有志著作之人,裒集明代史实,并不甚知有忌讳。”[18]因此,计六奇才发出感叹,“是天子且著书与求书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而若《南北略》确如谢国桢与韦力两位先生所言存在康熙年间刻本,也就更加能够证明当时文化气氛的相对宽松。①康熙二年(1663)结案的“庄廷鑨《明史》案”,发案于顺治年间,只是延至康熙初年方才结案。此案的爆发有其特殊原因和背景,此后约50年才有“南山集案”的发生,因此并不妨碍我们对康熙初年文网作出相对宽松的判断。参见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原因之研究》,台湾华正书局1983年版,第36-41页。
这段序言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发是,计六奇于康熙十年完成《北略》的编写,也是在那时写了《论明季致乱之由》附于书后。此时,距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死于昆明已过去整整十年,明朝余绪再无波澜,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年轻的康熙帝已经亲政,正在竭力推行各种调和满汉关系、笼络汉族士人的措施,以使其统治更加稳定。这些信息提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计六奇,是站在历史的终点来回顾明清鼎革这段历史,这是他构建清朝必然胜出、明朝必定灭亡的历史脉络的现实出发点。因此,我们从《北略》《南略》中应该可以读出,计六奇清楚地认识到由明到清那种不可逆转的内在发展趋势。他没有从明朝遗民的角度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反对这种转变,更没有在书中因为夷夏之防而否认清朝的合法性,相反,他站在了明确认同清朝统治合法性的立场上。正因如此,阚红柳在《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中纠正了学界以往所主张的计六奇反满抗清的观点。该书把清初私家撰史者分为三类:明王朝维护者、清王朝支持者以及在新旧政权之间动摇者,并把计六奇划分为清王朝的支持者[19]。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可见,以往研究者将民族主义的观念,以先入为主的前置方式贯入对计六奇及其著作的解读,曲解了计六奇进行历史构建的苦衷,只是将其著作当作表达自己思想和理论的手段,从而进入一种“强制阐释”的误区[20]。只有去除这些预设的价值判断,我们才能认识真正的计六奇,洞悉计六奇之笔所串起的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碎片。
最后,我们可能还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计六奇一方面不惜笔墨褒扬忠明义士,另一方面又认同清朝,并在书中构建清朝走上历史舞台的历史必然性,难道这两者不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笔者以为,计六奇在表达自己对忠明之士的赞美之时,并不一定代表他对明朝的留恋,也不妨碍他表达对清朝的政治认同。计六奇完全是站在纯粹的“忠君”观念立场之上褒扬忠明之士,这种写史手法似乎也影响着后世对明清鼎革之际士人抉择的评判。乾隆之际,清朝将很多投降清朝的明朝文臣武将归入《贰臣传》,反而对很多效忠明朝的忠义之士予以褒扬,即是一证。
[1] 张崟:《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计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29-757页。
[2] 任道斌:《〈明季南北略〉作者计六奇传略》,《文献》1980年第1期。
[3] 魏得良:《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
[4] 胡晓彤:《〈明季南北略〉的写作原因和史料价值》,《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5] 葛星:《从〈明季南北略〉看计六奇的史学思想》,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6] 杨续敏:《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页。
[7]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2页。
[8] 来新夏、韦力、李国庆:《书目答问汇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7页。
[9] 计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 夏允彝:《幸存录》,《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1-52页。
[11] 计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12] 孔定芳:《明遗民的群体身份认同与群体聚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3] 于琨、陈玉璂:《常州府志》卷二四,《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5页。
[14] 王富鹏:《论明遗民对清政权的接受和认可——以陈恭尹交游的转变过程为例》,《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4期。
[15] 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8-102页。
[16] 计六奇:《粤滇记略》,《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35卷),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307页。
[17]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9-240页。
[18]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8页。
[19] 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20] 张江:《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兼论相对主义的历史阐释》,《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