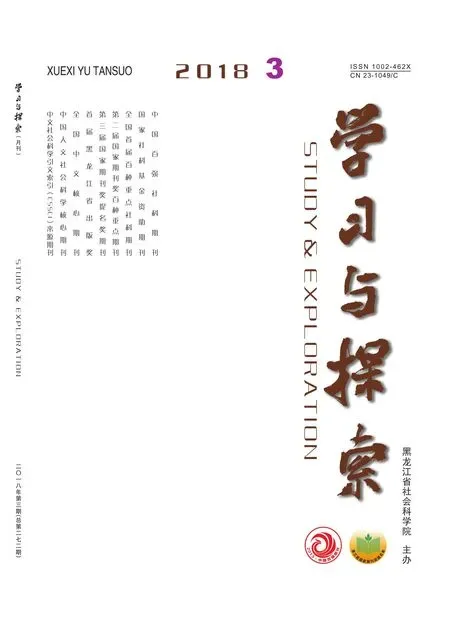中国现代诗论的一种总结
——论袁可嘉的诗论
2018-02-19廖四平魏玲玲
廖四平,魏玲玲
(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学院,北京100024;2.天门市教师进修学校,湖北 天门434000)
袁可嘉(1921—2008)从1946年冬到1948年底,先后在《大公报·星期文艺》《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文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二三十篇诗论;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论,虽然其中《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等诗论与其之前有不一致之处:如在评价诗歌时往往较多关注作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对艾略特不再一味地褒扬;但总体来说两者在一点上基本是一致的,即都指向新诗现代化。也就是说,袁可嘉的诗论是关于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它几乎涉及了中国现代诗论的所有核心问题,并超越了既有的论述,堪称中国现代诗论的一种总结。
一、“新诗现代化”概念的“勘定”
20世纪40年代,中国诗坛出现了一场“现代化”运动:一方面,“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的新诗”[1]3,它“代表新的感性的崛起”[1]10;而这种“感性革命的萌芽”在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等诗人的作品中已经出现过[1]4,穆旦等人的诗歌更是将之推向了成熟:“穆旦底诗分量沉重,情理交缠而挣扎着想克服对方,意象突出,节奏突兀而多变,不重氛围而求强烈的集中,即是现代化了的诗。”[1]48另一方面,“新诗现代化”也是诗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朱自清、唐湜等均论及过。例如,朱自清提出:“我们现在在抗战,同时也在建国;建国的主要目的是现代化……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加速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富厚些。”[2]唐湜还以杜运燮的《滇湎公路》作为他阐述“新诗‘现代化’”理论的依据,认为当时的诗坛上存在着“一个诗的现代化运动”,即在穆旦、杜运燮、绿原等参与的诗歌运动中,穆旦、杜运燮等为“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绿原等为“不自觉的现代主义者”[3]。
袁可嘉也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一方面创作了《沉钟》《进城》等“现代化”的新诗,另一方面还撰写了《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等诗论,对“新诗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针对当时有人把新诗“现代化”与新诗“西洋化”混为一谈,袁可嘉指出:“新诗‘现代化’并不与新诗‘西洋化’同义: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使它现代化的要求更与我们研习现代西洋诗及现代西洋文学批评有密切关系,我们却绝无理由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而为一。从最表面的意义说,‘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之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1]21
袁可嘉是朱自清、卞之琳、冯至的学生,与戴望舒、艾青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诗歌追求,与穆旦、杜运燮、唐湜、绿原等为诗友。袁可嘉曾坦言受到卞之琳、冯至等人的影响:“1942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的兴趣从浪漫派文学转向了现代派文学……我先后读到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4]573-574
但是,袁可嘉也受到了西方相关观念的影响。他曾明言其诗论“受到了瑞恰慈(又译为瑞恰兹、立恰慈、理查兹等——引者注)、艾略特和英美新批评的启发,而且是结合着中国新诗创作存在的实际问题”的[5]。同时,他是在与“西洋化”的对比中谈“现代化”的,其先在观念是“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加上他有创作诗的体验和经验,并善于归纳、总结,因此,其“新诗现代化”观点又超越了朱自清等人的观点。如朱自清既没有具体地界定“新诗现代化”,又没有就一些具体问题展开论述,“与唐湜相比,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谱系更具有一种历史感,他确认‘新诗现代化’的‘萌芽原非始自今日,读过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等诗人作品的人们应该毫无困难地想它的先例’”[6]。袁可嘉还认为不能“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而为一”,这比路易士的关于新诗从一产生即是来自西洋的“移植之花”[7]的观点更加科学。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一场“现代化”运动,“新诗现代化”自在其中。袁可嘉又参加了这场运动,他撰写许多见解独到的诗论,例如,他在《半个世纪的脚印·序》中指出:
(新诗)“现代化”的实质,说得简单一点,无非是两条。第一,在思想倾向上,既坚持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又保留抒写个人心绪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强调社会性与个人性、反映论与表现论的有机统一;这就使我们与西方现代派和旧式学院派有区别,与单纯强调社会功能的流派也有区别。第二,在诗艺上,要求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追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注重象征和联想,让幻想与现实交织渗透,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这又与诗艺上墨守成规或机械模仿西方现代派有区别[4]2。
显然,袁可嘉的这些观点与其四十年前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并有所发展和完善。首先,它从“思想倾向”和“诗艺”两个方面阐述新诗的“现代化”问题,且阐述得简明扼要;其次,它不仅阐述了“思想倾向”和“诗艺”各自的具体内涵,而且分别与西方现代派、旧式学院派进行了对比、区分,切中肯綮,因此比后者更具体、更全面、更明了、更科学,堪称是对“新诗现代化”这一概念的一种“勘定”。
二、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完善
袁可嘉“敏感地、富有针对性地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提供了自己独到的有时是相当精辟的见解……运用现代主义的诗歌知识,发现并论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课题,其中有的甚至关涉整个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趋向”[6],并“在有渊源、有背景的情况下,却不满足于变相编译或照抄,而处处都可见他的深入体会与独创性见解,这些体会与创见,甚至完善和完成了艾略特、瑞恰兹的理论”[8]56-57,从而完善了中国现代主义诗论。
(一)关于“纯诗”
所谓“纯诗”即“纯粹的诗歌”,也就是不含任何“非诗”成分的诗。袁可嘉认为,“诗歌作为艺术也自有其特定的要求”[1]5,“绝对承认诗有各种不同的诗,有其不同的价值与意义,但绝对否认好诗坏诗,是诗非诗的不可分”[1]7。
“纯诗”本是一个西方诗学概念,它的奠基者应该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但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是马拉美的得意弟子瓦雷里[9]。之后,西方还有一些人论及过“纯诗”及相关问题,如瑞恰慈认为,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或科学的真实,“《鲁滨逊漂流记》的‘真实’只是我们读到的情节合乎情理,从叙述故事的效果说来易于被人接受,而不是这些情节都符合亚历山大·塞尔凯克或别的什么人的实际经历”[10];艾略特则指出:“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非纯粹的文学标准所可决定,但它是否为文学作品则可诉之于纯粹的文学标准。”[1]7
在中国,也有不少现代诗人或诗论家论及过“纯诗”及相关问题,如闻一多曾阐述过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问题,并明确指出:“艺术最高的目的,是要达到‘纯形’pureform的境地。”[11]穆木天也提出:“我们的要求是‘纯粹诗歌’。我们的要求是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我们要求是‘诗的世界’。”[12]94王独清认为,“要治中国现在文坛审美薄弱和创作粗糙的毛病”就“有倡Poesie Pure的必要”,并认同穆木天的“纯粹诗歌”,称穆木天所主张的“‘诗的统一性’和‘诗的持续性’”“只有 Poesie pure才可以表现充足”[12]106-109;戴望舒认为“自由诗是不乞援于一般意义的音乐的纯诗”,“韵律诗则是一般意义的音乐成分和诗的成分并重的混合体”[13];朱光潜认为“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14];梁宗岱指出:“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的灵魂到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的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15]沈从文也提出:“诗必须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诗可以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16]
显然,袁可嘉的“纯诗”观受到了艾略特等人的影响,他认同艾略特关于“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非纯粹的文学标准所可决定,但它是否为文学作品则可诉之于纯粹的文学标准”[1]7的论断。同时,袁可嘉的“纯诗”观又比闻一多、沈从文的观点更紧扣“纯诗”、更“展开”[1]7,比穆木天、王独清、戴望舒、梁宗岱的观点更具体、更明了、更易于为人所接受。因此可以说,袁可嘉的“纯诗”观完善或超越了中国现代诗学中的“纯诗”观。
(二)关于“晦涩”
袁可嘉认为“晦涩是现代西洋诗核心性质之一”[1]22,现代诗的晦涩源于“现代诗人所处的厄境”或“传统价值的解体”或“现代诗人的一种偏爱:想从奇异的复杂获得奇异的丰富”,它的存在“一方面有它社会的、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也确有特殊的艺术价值”[1]100。
西方不少现代诗人或诗论家曾论及晦涩及相关问题,艾略特更是明确地指出:“就我们文明目前的状况而言,诗人很可能不得不变得艰涩。我们的文明涵容着如此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用于精细的感受力,必然会产生多样而复杂的结果。诗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涵容性,暗示性和间接性,以便可以强使——如果需要可以打乱——语言以适合自己的意思。”[17]32
在中国,穆木天把“朦胧”作为诗创作的自觉追求,认为“诗是最忌说明,诗人也是最忌求人了解”[12]106,应该表现那种“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12]98的诗的世界,此所谓“朦胧”实际上就是一种晦涩。20世纪30年代,诗坛上崛起了一种“主智”诗——注重智性或曰知性的诗,如冯至、卞之琳的诗,这种诗“以智为主脑”“追求智慧的凝聚”“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因而“必然是所谓难懂的诗”[12]262,难懂亦即晦涩的一种。
显然,袁可嘉关于晦涩的观点受到了中西诗学的晦涩观或中西晦涩诗的影响——它直接论及了艾略特、冯至等,它在晦涩产生的原因上与艾略特的观点相同;但又有所超越——它论及了晦涩的“特殊性”“普遍性”、产生的原因、意义、价值,比艾略特、穆木天等的观点全面、具体、切中要害。
(三)关于“象征”
袁可嘉认为“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1]7,其要点“在通过诗的媒介的各种弹性(文字的音乐性、意象的扩展性、想象的联想性等)造成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不定状态(Indefiniteness),从不定产生饱满、弥漫、无穷与丰富;它从间接的启发着手,终止于诗境的无限伸展”[18]。“诗的语言含有高度的象征性质……它的意义不止是它在辞书中的意义,而多半取决于全体的结构和当时上下文的次序……它的意义随时接受其他诸因素(意象、节奏、语气、态度等等)的修正和补充,所以整个诗创作的过程可以称为一种象征的行为”,因此“伟大的文学作品几乎无一不是”“有结构的象征系统”[1]229。
中国不少现代诗人或诗论家都论及过“象征”。例如,闻一多说:“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19]118-119周作人认为“兴”“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20]。穆木天指出:“一个有统一性的诗,是一个统一性的心情的反映,是生活的真实的象征。”[12]96梁宗岱认为“象征……和诗经里的‘兴’颇近似”,它有两个特性:“融洽或无间”和“含蓄或无限”,“所谓融洽是指一首诗底情与景,意与象底惝恍迷离,融成一片;含蓄是指它暗示给我们的意义和兴味底丰富和隽永……所谓象征是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或出神底瞬间瞥见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12]166-169。 卞之琳则认为“亲切(Intimacy)”与“暗示(Suggestion)”是魏尔伦的诗歌及其他象征主义诗歌的长处[21]。
袁可嘉的象征观与闻一多等人颇为一致,在象征与暗示、含蓄的关系上,两者更是相同。显然,前者是应该受到了后者的影响的,但也受到了西方诗潮的影响。袁可嘉认为“象征,指法国19世纪后期象征主义诗歌”[8]53,他“关于现代新诗象征诗艺的追求取法于里尔克的诗学观念和他的现代诗,里尔克认为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仿佛是两个分裂的世界,他要找到那种能同时表达内在与外在经验的象征。因此,象征成为里尔克沟通外在与内在经验世界的桥梁。同时他反对把感性对象表现为与对象分离的符号,而是把对象表现成它固有的象征物,从而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22]。显然,袁可嘉的象征观超越了闻一多等人,涵盖了诗歌的创作手法、语言和结构等方面内容,比后者更系统、全面,更符合诗的“实际”。
(四)关于“经验”
“所谓‘经验’,就是要让新诗接受和传达全新的人生体验的内容。”[23]“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都倡导‘经验’说,并把诗歌由表现情感、情绪到表现经验、理性视为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发展在诗质方面的重要标志。”[24]
瑞恰慈曾指出,能够实现“最大量”的“包含”的诗“通过拓宽反应而获得稳定性和条理性的经验”[25]226-227,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艾略特也说:“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而这些经验在讲实际、爱活动的一种人看来就不会是什么经验”[17]7-8,“当诗人的心智为创作做好完全准备后,它不断地聚合各种不同的经验。”[17]31
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王独清、梁宗岱等的纯诗理论,30年代的现代派诗论,40年代的袁可嘉的九叶诗友的诗歌观念,实际上都是认同“经验说”的。例如,冯至很看重经验对诗的作用,而路易士则明确说:“我们生于现代,我们有所体验,而我们的经验不同于前一二个世纪的,我们的诗,连同我们的文学,艺术,文化一般,自然也有我们这一时代的特色。”[26]
袁可嘉认为“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1]47,但“在生活里有生活经验与诗经验”[1]67。诗的经验“来自实际生活经验,但并不等于,也并不止于生活经验;二种经验中间必然有一个转化或消化的过程”[1]160;新诗“多数失败的原因——不在出发的起点……也不在终点……而在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1]24;“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1]3;“诗篇的优劣的鉴别纯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经验价值的高度、深度、广度而定”[1]6。
显然,袁可嘉吸纳了中西“经验说”的因子,但又超越瑞恰慈、冯至等人的观点——他的视野要宽广得多;而与穆木天、王独清、梁宗岱、路易士等人相比,袁可嘉则更直接、更具体地肯定了经验之于诗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五)关于“诗的戏剧化”
袁可嘉认为新诗的戏剧化有三个方向:一是里尔克式的,即“努力探索自己的的心,而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借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二是奥登式的,即“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诗人的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三是写诗剧,“现代诗的主潮是追求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而诗剧正配合这个要求”[1]26-28。
“戏剧化”“这个术语源于新批评派的肯尼斯·勃克(Kenneth Burke,1897—1993),意指任何非情节性的文学作品包括抒情诗都具有戏剧性结构,人生冲突在作品中像戏剧展开并得到象征性的解决”[27]185-186。艾略特认为现代诗里有三种声音:诗人自己说话的声音、诗人对听众讲话时的声音,以及“第三种声音——也就是诗剧的声音——所有的特殊性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即通过和含有戏剧成份——尤其是戏剧的独白——的非诗剧的声音的比较而显露出来的”[17]249-254。瑞恰慈则指出:“具有戏剧性结构的诗远远超出人们通常的想象。”[28]
20世纪20年代,朱自清的《小舱中的现代》、徐志摩的《海韵》、闻一多的《西岸》等都运用了戏剧的主要表现手段——对话。30年代,卞之琳写抒情诗倾向于“‘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出现了戏拟(parody)”[29]3,“常通过西方的‘戏剧性处境’而作‘戏剧性台词’”[29]15;柯可认为,“诗剧”为“中国新诗的形式方面的新方向”之一[12]267;叶公超则指出:“惟有在诗剧里我们才可以探索活人说话的节奏,也惟有在诗剧里语言意态的转变最显明,最复杂。”[12]33440年代,闻一多主张“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19]205
新诗也有与戏剧化的三个方向相对应的“案例”,例如:“里尔克式”的——辛笛的《弦梦》、郑敏的《金黄的稻束》、穆旦的《海恋》等;“奥登式”的——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杭约赫的《严肃的游戏》、袁可嘉的《上海》等;“诗剧”——穆旦的《神魔之争》《森林之魅》及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朗诵诗与秧歌舞”[25]226-227。
袁可嘉既自觉地接受了瑞恰慈、艾略特等人的影响,又对奥登欣赏有加。例如,他称奥登是一个“有名的诗坛的顽童”[1]28,认为“就纯从诗题材接触面的广度来说,奥登确定地超过梵乐希、里尔克和艾略特,只要一打开他的诗总集,你便得钦佩他在这方面的特殊才能”,赞赏奥登“对德籍犹太人,战时难民,及被压迫者的深厚同情”,明言“我们尤其不能忘怀他访问中国战场时所写的数十首十四行诗”[1]194。与此同时,袁可嘉还与朱自清等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且情趣相投,因此,其“诗的戏剧化”观点实际上是同时受到了中西“诗的戏剧化”诗潮的影响的。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诗的戏剧化”观点大致是历时性地出现的,且诗人、诗论家往往“各自为政”,因而较为零散,深度不够,内在逻辑性也不强。而袁可嘉的“诗的戏剧化”观点论及了“诗的戏剧化”的原因、方向、方法,颇为系统、全面,且有深度、理论性较强,如在朱自清等那里,“戏剧化”只是作为“理性节制情感”的审美原则下的一种具体的写作技巧[30],而袁可嘉则将“戏剧化”上升为一个完整的诗歌创作理念,从而超越了朱自清等的观点。
(六)关于“想象逻辑”
袁可嘉指出:“为击破传统的、狭隘的、平面的结构理论,艾略特本诸经验,首先提出‘想象逻辑’的名词。在他看来,作为诗的结构,常识意义的起承转合并不怎样要紧,重要的毋宁是诗的情思在通过意象连续发展后的想象的次序。”[1]37也就是说,“想象逻辑”即“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1]19,它遵循着“从矛盾求统一的辩证性……完全依赖结构上的安排”[1]37的原则,强调诗歌组织“高低起伏,层层连锁”[1]19的结构意识,颠覆了传统诗歌“概念逻辑”的结构安排,反对用“诗篇中最明白浅显的散文意义评判它的发展,看是否前后相符,首尾一贯”[1]19。
袁可嘉认同性地接受了艾略特关于“想象逻辑”的观点,并承认曾受到柯律勒治、瑞恰慈、克罗齐、玛里丹等人的影响:
柯氏说:“想象如此呈现它自己:在相反的不谐的因素的平衡调和之中;在同与异,抽象与具体,观念与意象,殊相与共相,新奇与陈腐,异常的情绪激动与异常的井然秩序的结合之中”……实际上柯氏及立恰慈(I.A.Richards)所谓“诗想象”也即克罗齐的“直觉”,法国当代哲学家玛里丹(J.Maritain)所说的“创造行为”[1]33。
与此同时,袁可嘉还受到中国现代相关诗学观点,尤其是李金发诗学观的影响。李金发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注重运用想象逻辑,朱自清在论及李金发的诗时所说的“远取譬”,其核心便是要遵循想象逻辑。但是,“对于想象逻辑,艾、瑞二人论述比较分散,也不够具体,而袁可嘉先生加以确切具体归纳,认为所谓想象逻辑,乃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对于诗歌十分重要,它可以结合不同经验,使意义加深、扩大、增重。他又用艾略特长诗作解,认为表现在这些诗里,是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突兀片断,或则扩大某一行或某一意象的蕴义,或则加深某一情绪的起伏、撼荡,或者加速某一观念的辩证引进。又比如他以瑞恰慈理论解释穆旦诗《时感》,说其中两支相反相成的思想主流在每一节都交互环锁、层层渗透,解释杜运燮《露营》和《月》二首,描述其感觉曲线,曲折变易,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都十分精辟而富于创见”[8]56-57。
除以上问题外,袁可嘉还论及了现代主义诗论的一些其他问题,如玄学、客观对应物、思想知觉化、最大量意识状态等,对既有的论述均有所修正、完善或发展,与上述内容组构在一起,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论体系,并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合法性,“重新树立中国现代主义的诗歌形象”;同时,形成了一种与现实主义诗论体系的对话基础,“澄清现实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的狭窄的理论定位”[6],堪称对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一种完善。
三、中国现实主义诗论的发展
袁可嘉的诗学理论也论及中国现实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一)关于“现实”
袁可嘉认为“现实”即“当前世界人生”[1]7,它“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也包括生活在具体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澜”[31];既包括“外在的现实”,又包括“内在的现实”;“绝对肯定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的人生现实性,但同样地绝对肯定诗作为艺术时必须被尊重的诗底实质”[1]5;“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生命”[1]220。
袁可嘉的这些观点一方面涵盖了既有的现实主义诗学现实观的核心内容,如作为“外在的现实”的“现实”;另一方面又涵盖了既有的现实主义诗学现实观所没有的内涵,如作为“内在的现实”的“现实”等。而关于诗与现实的关系的观点则颇为独到而又全面,因而超越了后者。
(二)关于“政治”
袁可嘉认为“诗的政治性是它的社会性的一面”[1]52,“现代人生……与现代政治如此变态地密切相关,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1]4-5;但“政治文学”“不能代替文学全体”,“即使承认文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工具既隶属艺术的范畴,自必通过艺术才能达到作为工具的目的”。因此,“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联系,但绝对否定两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1]4,“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和艺术的立场”。
在中国现代诗坛一直存在着两种强势的诗学观点:西化色彩浓重的现代主义诗学和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现实主义诗学。总的来说,前者倾向于否定诗的政治性,不主张诗歌为政治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主义诗学越来越影响诗歌和诗学的正常发展,受其影响的现代派诗歌“诗形僵死、诗思枯、未老先衰”[23],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合法性遭到质疑。现实主义诗学则过分强调诗的政治性,如阿垅认为诗需要的是政治内容而不是技巧[32],许洁泯认为“一切的战斗的现实的内容,也必须是政治内容”[33],诗“都是政治内容的”,强调“诗人的现实意识、时代感、历史感、政治意识,以及诗歌的社会功能的现实主义的解释”[6]。显然,袁可嘉关于诗歌政治的观点同时针砭甚至矫正了现代主义诗学和现实主义诗学各自的偏颇,发展或超越了既有的现实主义诗学中的政治观。
(三)关于“民主”
袁可嘉指出:“无论把民主定义为外观的文化模式或内在的意识形态,它都具有下述的几种特性:它是辨证的(从不同产生和谐)、包含的(有关的因素都有独立的地位)、戏剧的(通过矛盾冲突而得平衡)、复杂的(因有不同存在)、创造的(各部分都有充分生机)、有机的(以部分配合全体而不失去独立性)、现代的而非直线的、简化的、排他的、反映的、机械的和原始的。”“民主文化是现代的文化,民主的诗也必须是现代的诗。民主文化是辩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有机的、创造的,表现这一文化的民主的诗也必然分担同样的辩证、包含、复杂、有机、创造的特质。我们所要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包括民主政治的现代民主文化,我们所要争取的诗也必然是现代化的民主的诗。”[1]42-50
袁可嘉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现实”的一种回应——“民主”本是现实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诗学家们常常“将民主只看作是狭隘的一种政治制度,而非全面的一种文化模式或内在的一种意识状态;将诗只看作是推动政治运动的工具而非创造民主文化和认识的有机部分”,“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一方面在文学上坚持原始化,不民主化”[1]40-43。袁可嘉“关于现代诗歌的‘民主’内涵……直接代表了诗家对中国‘现代’问题的关注与回应”[23]。同时,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将在中国的象征主义实践与逃避现实的艺术倾向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一种本质特征,专断而巧妙地扩展定论为中国现代主义与逃避现实的艺术倾向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企图彻底否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合法性”,这是很不民主的——袁可嘉的“民主”观也是对此的一种回应;不过,也不仅仅是回应——“民主作为‘文化’的意义可以说是袁可嘉独特的社会发现,而他竟然又能从这一文化中读出与‘现代化’诗歌的‘直接的,显著的联系’……则更是诗家的智慧了”[23]。
(四)关于“人民的文学”
所谓“人民的文学”即“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的文学;它与“人的文学”相对——后者“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1]113-116。大致地说,在中国现代诗论发展史上,现实主义诗论认同并持“人民的文学观”,而对“人的文学观”不大以为然,现代主义诗论则相反。显然,两者均有偏颇、有欠科学。袁可嘉对此洞若观火,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民的文学”是“人的文学”的“一个部分”,“决不能独尊自己,以自己的尺度来限制全体,否定全体”;“现代文学终必在‘人的文学’的传统里溶化消解,得到归宿;终必在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中嵌稳本身的地位,找出本身的意义”。他之所以如此“折中调和‘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拒绝把两者推向现代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的极端,与其是由于他的丰富的‘文学史经验’,倒不如说是出自于他对无穷的历史变化和现实的复杂矛盾的一种积极的回应”[27]176。同时,也因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人民’使‘五四’时期所标举的‘人’有了更具体、更现实的内涵”,但是,“‘人民本位’的至上化与极端化却使其蜕变为民粹主义,丧失了基本的科学性、现代性”[34]。因此,这些观点同时针砭或矫正了“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的偏颇,更符合诗歌或文学创作的规律。
总的来看,袁可嘉关于“现实”等的观点不仅超越了中国现代诗论既有的观点,而且组构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颇成体系、颇具中国特色且针对性、实用性均很强的现实主义诗论,从而推动了中国现代诗论尤其是现实主义诗论的发展。
四、中国现代诗论范式的建立
中国现代诗论的正式建构大致始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又出现了胡适的《谈新诗》、闻一多的《诗的格律》、朱光潜的《诗论》、艾青的《诗论》等一些颇有建树的诗论。但是,中国现代诗论范式的正式建立,则始于袁可嘉的诗论。
(一)袁可嘉创立了一个完整的诗学概念
“在西方文艺思想的压迫性输入之中,现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与诗学家不得不将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应付、消化外来资源方面,由此形成了我们自身理论建设包括概念归结的严重匮乏,现代中国的几部体系完整的‘诗学’——包括朱光潜、艾青等人不无贡献的诗学——都未曾在推出新的诗学概念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虽然袁可嘉从不讳言自身诗学观念中所接受的外来痕迹,但他却总能自如地运行于所有这些外来诗学概念之上而予以新的组合和改造,并且形成自己的新的思想形式。”在此基础上,袁可嘉还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政治感伤、情绪感伤、民主的诗、包含的诗、客观对应物、新诗戏剧化、想象逻辑、思想知觉化、戏剧主义、诗境的扩展、诗境的结晶、最大量意识状态、文本的有机性、机智、似是而非与似非而是、讽刺感、辩证性、人民的文学、人的文学等具有特定含义的诗学概念,它们组构在一起自成一体,“既与现代西方的诗学思想形成了对话,又奠基了中国自己的诗学批评概念”。
(二)袁可嘉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诗学体系
袁可嘉的诗论虽是以论文的形式展开的,论文的撰写和发表也是直接针对诗坛现实的,带有很大的“随机性”——看似不成系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袁可嘉的诗论包括“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戏剧主义论”等内容,几乎涵盖了诗论的全部问题,且彼此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颇为完整而又逻辑严密的诗学体系。
(三)袁可嘉诗论完善了中国现代诗论的学理性建构
20世纪40年代的诗坛,对新诗进行理论思考的人不少,如朱自清、李广田、孙毓棠、陈敬容、萧望卿、楚天阔、朱英诞、查显琳、废名、林庚、路易士、郭绍虞等。但“鼓吹现代主义最力、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首推袁可嘉和唐湜。唐湜的新诗批评,走的是梁宗岱的印象主义批评的路子,注重个人的直觉和感悟的把握,充斥大段的抒情文字。虽然他声称‘我们应该接受欧洲人科学的批评方法、精明的分析与刻骨的刻画’,但是,他在‘批评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抑或两者兼具’这个问题上闪烁其词,所以,理性分析与诗化叙述时常混杂一处。”[27]169而“袁可嘉的诗论是心平气和的学术阐释,并非论战”,如《“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对于他深恶痛绝的感伤也绝不谩骂,而是指陈利害,说明感伤对文学本体的损害。他的文论是从文学内部进行探究,即使争议,也属于文学内部,而并不引渡到非文学的范畴”[35],这与胡适、朱光潜等的诗论风格一脉相承。有的则是一种新批评式的科学论文,如《从分析到综合》。总的来看,袁可嘉的“研究重于欣赏,制度化意味甚过一时的兴会感发……立论表现出智力与明晰”,颇具学理性,发展和完善了以闻一多、朱光潜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论的学理性建构。
具体来说,袁可嘉诗学观点的建构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袁可嘉“敏感地、富有针对性地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提供了自己独到的有时是相当精辟的见解……运用现代主义的诗歌知识,发现并论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课题,其中有的甚至关涉到整个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趋向。”“在有渊源、有背景的情况下,却不满足于变相编译或照抄,而处处都可见他的深入体会与独创性见解,这些体会与创见,甚至完善和完成了艾略特、瑞恰兹的理论……比如对于想象逻辑,艾、瑞二人论述比较分散,也不够具体,而袁可嘉先生加以确切具体归纳,认为所谓想象逻辑,乃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对于诗歌十分重要,它可以结合不同经验,使意义加深、扩大、增重。他又用艾略特长诗作解,认为表现在这些诗里,是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突兀片断,或则扩大某一行或某一意象的蕴义,或则加深某一情绪的起伏、撼荡,或者加速某一观念的辩证引进。又比如他以瑞恰兹理论解释穆旦诗《时感》,说其中两支相反相成的思想主流在每一节都交互环锁、层层渗透,解释杜运燮《露营》和《月》二首,描述其感觉曲线,曲折变易,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都十分精辟而富于创见。”再如,在瑞恰慈看来,能够实现“最大量”的“包含”的诗“通过拓宽反应而获得稳定性和条理性的经验”,“由平行发展而方向相同的几对冲动构成”;而袁可嘉则将之联系到“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经验’一词虽说是瑞恰慈诗歌批评的关键词之一……但将‘人生’连接于‘经验’之上,则完全是袁可嘉特殊命意”;并且,他明确地把“经验”同“热情”“说教”“感伤”“单纯”等“新诗的毛病”尖锐地对立起来,这可谓一个创见。中国新诗的经验论从初期白话诗歌的时代就产生了,但是直到袁可嘉那里才完全进入到了艺术本身的逻辑,同时,袁可嘉强调诗与意识的关系,而“把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同理查兹的‘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学诗学联系起来,可以说是袁可嘉最突出的批评贡献之一”,他“对现代主义的修正,是想建立一种与现实主义诗学体系的对话基础,其理论意图旨在表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并不排斥现实主义所萦萦系怀的诗歌问题”。
第二,袁可嘉接受现代主义诗学、美学的出发点是基于诗歌现代化的总命题。正是从这个命题出发,袁可嘉提出了“人本位”与“文学本位”的现代文化观念,从而接续了失落于历史断层中的“五四”人学与文学的启蒙精神。同时,袁可嘉又把现代启蒙话语与“人民”“政治”这些新语境特点做了创造性的整合,既坚持了现代启蒙立场,又给启蒙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袁可嘉不仅是现代诗学建设的先锋,也是现代文化建设的先锋。
同时,虽然从审美与政治的分裂与对抗的角度来看,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缺乏一种历史性的思考”,但总的来说,它超越了“新诗‘现代化’”“讨论热”中其他任何人的观点,如朱自清既没有具体地界定“新诗‘现代化’”,又没有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展开论述;“与唐湜相比,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谱系更具有一种历史感,他确认‘新诗现代化’的‘萌芽原非始自今日,读过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等诗人作品的人们应该毫无困难地想起它的先例’……所以,袁可嘉的批评不仅是对‘中国新诗’派的现代主义诗学的阐释,也是对整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诗学的阐释”。他认为不能“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而为一”,很显然比路易士的关于新诗从一产生即是来自西洋的“移植之花”的观点要科学。
此外,袁可嘉关于“新诗现代化”“人本位”“文学本位”的观点还颇具前瞻性—— “新诗现代化”在近半个世纪以后再次成为中国诗学界的热点问题,关于“人本位”“文学本位”的观点实际上对新中国自成立至改革开放开始之间极左文学思潮具有预警的性质。
第三,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将在中国的象征主义实践与逃避现实的艺术倾向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一种本质特征,专断而巧妙地扩展定论为中国现代主义与逃避现实的艺术倾向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企图彻底否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合法性”,“袁可嘉就通常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才会论及的那些问题重新加以阐释,至少可以获得两种批评效果:其一,澄清现实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的狭窄的理论定位;其二,重新树立中国现代主义的诗歌形象。即申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同样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也就是“让人们意识到象征主义并不代表中国现代主义的全部可能性,40年代还存在一种关注现实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而矫正了现实主义诗学的偏颇。
与此同时,袁可嘉既坚持“诗的本体论”,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既坚称诗不能脱离现实、政治,拒绝新批评派的理论把文本从社会背景和社会效果隔离开来之类的偏执,又明确地反对“诗是宣传”,从属于政治,认为诗歌必须遵循“客观性与间接性”原则,即与“象征、玄学”有机地融为一体……与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学观相比,袁可嘉的这些观点强调了诗歌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肯定文学对人生的积极意义;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诗学观相比,它们强调了诗歌对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因而比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诗学都要科学得多,也要成熟得多。
第四,“‘现实、象征、玄学’这一三维结构及其密不可分性质的整体,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特的现代诗学范畴。它以诗人强烈关注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现实为生命,以多种形式的象征为营造意象和传达情绪的手段,以抽象的哲理沉思与具象的敏锐感觉呈现为诗的智性基础,在‘放弃单纯的愿望’的‘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中,建造一种新的‘大踏步走向现代’的诗的世界……这一美学原则,淡化了二三十年代穆木天、梁宗岱等倡导的西方的‘纯诗化’理论的性质,强化了现实的社会意识与内在的自我意识融合的成分,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存在的现实主义深化思考潮流的冲击所带来的对于诗的现代性美学的调整。它在整体思考与实践操作上更体现了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趋向于民族化的努力。‘现实、象征、玄学’这一诗学范畴的产生表明,超越于戴望舒代表的30年代各种现代性诗学的探索,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原则的追求与构建的趋于成熟”[36]。
第五,袁可嘉关于“情绪感伤”“新诗戏剧化”等观点以及赞同艾略特“逃避个性”的主张,显然受到了闻一多、梁实秋、施蛰存等人诗学观的影响,但也有所超越:它比后者更科学、周全、系统。例如,“袁可嘉的戏剧化诗表现手法的探索使20世纪以来中外诗歌的重要特点,即通过象征、暗示、曲写的诗表现手法,更加突出,同时在理论上使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发展道路更加明确”[37]。同时,“作为现代‘诗经验’的新诗戏剧化追求,是袁可嘉第一次对它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解剖与阐述,正是通过袁可嘉的阐述,戏剧化才根本跨越了一般技巧的层面,成为连接思想与形式又不囿于思想与形式的‘思维方式’,作为诗歌基本思维方式的‘戏剧化’也才具有客观性、间接性、包容性以及富含张力、重视结构等基本特点……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所有的‘戏剧化’论述中,袁可嘉的思想具有更为清晰更为具体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无论他借鉴了多少外来的资源,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样的论述面对和回应了中国自己的问题,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创造性贡献……袁可嘉不仅针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问题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主张,而且还将努力尝试建立自己的诗学理论概念与批评方式。”
第六,袁可嘉对于新诗的“晦涩”所表现出的宽容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背景下,通俗易懂、刚强有力是时代对诗歌最主要的要求。“七月派”诗歌较充分地满足了这一要求,袁可嘉自己的作品,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也并不晦涩,而且他还认为批评要“见得到、说得出”“懂得清楚、听得入耳”。但是他却对晦涩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袁可嘉的诗论还有其他一些建树,如将西方诗学中国化、创作问题理论化等,它们组构在一起,建立起了中国现代诗论的范式。
[1] 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2] 《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3] 唐湜:《新意度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1页。
[4] 《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5]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6] 臧棣:《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7] 路易士:《新诗之诸问题(上)》,《语林》1944年第1卷第1期。
[8] 蓝棣之:《九叶派诗歌批评理论探源》,《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 曾思艺:《比较文学视野中诗的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
[10] 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7页。
[11] 《闻一多全集》(第3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38页。
[12] 刘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13] 《戴望舒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95页。
[14] 《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15] 梁宗岱:《谈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16] 《沈从文文集》(第12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51页。
[17] 《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18] 袁可嘉:《现代英诗的特质》,《文学杂志》1948年第2卷第12期。
[19] 《闻一多全集》(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20] 周作人:《〈扬鞭集〉序》,《知堂序跋》,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98页。
[21] 卞之琳:《〈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译者识》,《新月》1932年第4卷第4期。
[22] 王芳:《论袁可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3] 李怡:《“新诗现代化”及其中国意义——重温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思想》,《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24] 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25] 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6] 路易士:《新诗之诸问题(中)》,《语林》1945年第1卷第2期。
[27] 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8] 邵朝杨:《论新批评理论与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9] 卞之琳:《雕虫纪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30] 钱理群、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31] 辛笛、袁可嘉等:《九叶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2] 陈旭光:《永远的“哈姆莱特”》,《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3] 许洁泯:《勇于面对现实》,《诗创造》1947年第2辑。
[34] 邵瑜莲、符杰祥:《论袁可嘉现代诗学体系的文化意义》,《东方论坛》2001年第4期。
[35] 张同道:《探险的风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36]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页。
[37] 王芳:《论袁可嘉的现代主义诗学理论探索》,《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