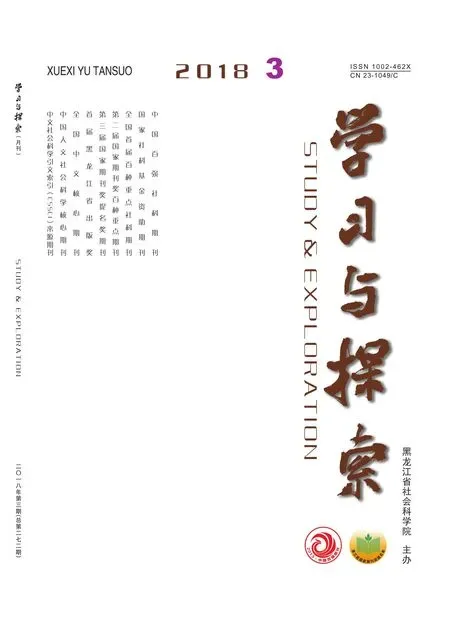法官管理制度与司法行为理论
2018-02-19傅爱竹
傅 爱 竹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8)
至少到今天为止,人类尚未发明一种司法“自动贩售机”——只要把案件事实输入进去,它就会自动给出判决结果,并且在可预期的未来我们也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因为司法三段论的诸前提从来就不是给定的,无法通过电脑而只能依靠人脑来识别。换言之,裁判工作必然由人亦即法官来完成。因而有人说,所谓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官之治”。现实主义法学早已证明,法官的个人特质包括才学、品德、癖好、偏见等,必然会渗透到司法运作的细节中去,并很可能会影响裁判的过程与结果。因此,如果不能对法官的个人特质进行有效的规制——扬其长者,避其短处——司法的质量也就无从保障,法治也将沦为法官的“专断之治”。这种规制主要以制度化的方式展开,是为法官管理制度。完善的法官管理制度乃是维护司法公正、避免法官专断之治的前提条件。而问题在于,如何构建完善的法官管理制度?这是本文的核心关切。
法官管理制度是个集合性概念,其下囊括了众多具体而微的制度,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做逐一的探讨。由此,本文将以法官管理制度中的绩效考核制度作为典型,反思探讨如何构建完善的法官管理制度。构建完善的法官管理制度的难题在于保护法官的三种动机,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只停留于制度表面的研究,必须深入制度内置的理论,而司法行为理论是法官管理制度构建的先决条件。据此,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从“角色期待”的视角提出评价法官管理制度优劣的标准;第二部分借助心理学中的“动机拥挤效应”找出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症结所在;第三部分反思当前法官管理制度所内置的司法行为理论即“经济人”理论之错谬;第四部分在吸取“经济人”教训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建构符合法官管理制度研究所需的司法行为理论,即“社会人”理论。
一、“好法官”与三种动机
去法院打官司希望遇到什么样的法官呢?回答这一问题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首先是专业技能一定要过硬,不胡乱判案;其次是谨守职业道德,不徇私枉法;最后是待人以礼,不冷漠市侩。这三个方面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好法官所应具有的品质。那么这些品质又如何获致?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需要法官相应地具有三种动机。
第一种是智识性动机,即法官对于裁判技能以及挖掘与运用自身智力资源的兴趣与追求。法官的工作是适用法律,亦即将案件事实归摄于法律规范之下。完成这项工作首先要求法官熟悉法律规范与法学原理,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培养康德所谓的“判断力”,即“分辨某物是否从属于某个给定规则之下”的能力[1]135。判断力越强,法官就越能迅速地联想并精确地定位到与案件事实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与法学原理可以通过书本或教学习得,但判断力却不能。康德指出:“实例乃是判断力的学步车”[1]136。具体说来,判断力之养成需要主客观两个条件:客观条件是要有大量的个别的、特殊的案件、情事和问题,即经验素材;主观条件则是要通过长期而专注的学习,将经验素材充分理解和内化。主观条件的成就离不开行动者对知识本身的兴趣以及挖掘与运用自身智力资源的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种动机能提供行动者长期不懈专注实践的内在推动力。因此,只有那些对裁判工作本身怀有热情、严格训练自己、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法官才可能练就高超的裁判技能。因此,智识性动机对于法官专业技能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种是伦理性动机,这既包括普通人所具有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意识,也包括法官所特有的职业伦理。法官所处理的案件,并不都是事实与法律规范都比较明确的所谓“简易案件”。在很多时候,无论是事实还是规范,都有可能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规范方面,经常存在多种可以适用之规则,或同一规则存在相互冲突的解释;在事实方面,对事实的认定也往往因“前理解”上的分殊而存在彼此对立且都具有正当理由的观点。正因为如此,裁判活动往往存在多种可能性,需要法官经过利益权衡和价值选择方能做出决断。法官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倾向经常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司法的整个过程之中。因此,法官个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水平就显得格外重要。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有言:“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2]
借用美国法学家朗·富勒关于两种道德的区分,①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参见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8页。史先生所言乃着眼于法官违反“义务的道德”之危害。然而我们还需注意到,法官如若丧失对“愿望的道德”的追求,则裁判的正当性基础殊为可虑。因为在法律规范并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法官需要通过德沃金所谓的“建构性阐释”找出所有可能的法律解释中最佳的那个。怎样判定何者为最佳?这就要求法官透过对法律制度中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等政治道德的理解来权衡与抉择。“他的决定不仅将反映出他对于正义和公平的观点,而且还会反映出他的更高层次的信念,那就是这些理想在相互抵触时应如何妥协。”[3]此处的公平、正义等政治道德便是富勒所谓的“愿望的道德”。②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富勒借助边际效用经济学来阐发“愿望的道德”的特点。边际效用经济学强调权衡既有的资源做出最有效率的分配,从而实现我们为自己确立的任何目标。这与“愿望的道德”平衡各种价值以求至善的特点颇为相似。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23页。因此,若想妥当地完成建构性阐释,法官就必须对“愿望的道德”怀有深刻的体悟。然而,对“愿望的道德”的理解与追求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对公平、正义无欲无求、漠不关心的法官必然缺乏对这些政治道德的感受力,因而也不可能对政治道德抱持深邃的洞察力。由此可见,法官一旦缺失追求“愿望的道德”的动机,就无法妥当地完成对法律的“建构性阐释”,因而其所做裁判的道德基础就是不稳固的、可质疑的。这种危害是潜移默化的,丝毫不逊于丧失坚守“义务的道德”的动机所导致的徇私枉法。总之,对于法官来说,伦理性动机的有无事关裁判的合法律性与正当性。
第三种是交互性动机,即法官对于人际间的沟通与交流以及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视。法律确定主义者如德沃金认为裁判存在唯一正解,只不过需要像赫拉克勒斯那样的“超人法官”才能够发现,而普通法官并不一定能够找到。这种说法多少给司法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但在这个祛魅的时代,法官身上早已褪去了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特质,人们不再相信法官能像启示性宗教里的先知那样具有发现唯一正解的“特异功能”,哪怕唯一正解确实存在。换言之,传统的法律确定主义与“唯一正解”命题已然无法为裁判提供合法化资源了。合法化资源的缺失,意味着司法缺乏权威性与公信力,法治也就随之岌岌可危了。因此,现代司法必须发掘新的合法化资源作为替代。
20世纪以来的主体间性哲学启示我们,当代社会的裁判合法化应着眼于沟通与交互性。一方面,裁判不应只给出判决结果,而必须注重程序与论证,在程序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论辩,在判决书中充分说理,力求以理服人;另一方面,法官也必须重视与当事人的交流与沟通,以礼相待,让人感觉是在真心实意地解决纠纷,而非应付差事、敷衍塞责,力求以诚动人。若想做到后一方面,就需要法官有意愿正面且积极地参与到与当事人的互动过程之中。一旦缺失这种动机,法官就不再重视“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工作态度显得冷漠与市侩,对当事人缺乏同情心和人情味,令当事人感觉自己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瓶罐头”。当身披神圣法袍的法官们在当事人及公众的眼里不过是些与凡俗无异的普通之辈时,当事人又怎会自愿服从、社会又怎会普遍接受法官的裁决呢?
通过前面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专业技能过硬、谨守职业道德、待人以礼的法官,需要相应地具有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这三种动机。其实,评价一项法官管理制度完善与否也可着眼于此,即看它是否能够保护、鼓励法官的这三种动机。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这个标准检视一下我国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
二、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心理学考察
(一)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特征
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又称法官质效考核(或考评)制度,是指通过一套客观化的指标来衡量法官工作努力程度以及工作能力(即审判水平)的法官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很早就已经应用在其他领域,如企业和行政部门,但在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建立还是比较晚近的事。200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中首次提出要“建立科学、统一的审判质量与效率评估体系,在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办案的情况下,确立科学的评估标准,完善评估体系。……根据法官职业特点和不同审判业务岗位的具体要求,科学设计考评项目,完善考评方法,统一法官绩效考评的标准和程序,并对法官考评结果进行合理利用。”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考核指标体系。各地法院又根据自己的情况对指标设定有所调整。常见的考核指标包括结案率、上诉率、二审发回重审及改判率、申诉率、调解率、撤诉率、信访投诉率、重复信访率、裁判主动履行率,等等。部分地方法院甚至与软件公司合作,细化出多达上百项的考核指标[4]。虽然在这一轮司法改革启动之初中央政法委及最高人民法院都下文要求各地取消不合理的考核指标[5],但很多指标仍在各地的考核中继续发挥作用[6]。绩效考核制度对法官之影响,就在于考核结果的使用。各地法院大都将考核结果同法官个人的评优评先、晋职晋级尤其是工资福利直接挂钩。①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对于累计两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次的,在所在级别对应工资标准内晋升一个工资档次。累计五年以上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次的,在所任职务对应级别范围内晋升一个级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次,且符合规定的其他任职资格条件的,具有晋升职务的资格;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晋升职务时优先考虑。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当年给予嘉奖;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记三等功,享受年度考评奖金。参见沐润:《法院绩效考核机制的评析及其完善》,《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2期,第141-146页。这就使得绩效考核变成一种“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激励制度。这种做法与其他同样引入法官绩效考核机制的国家大不相同。
以美国为例。早在1975年,阿拉斯加州就率先建立了司法绩效评价机制(Judi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简称JPE),此后很多州跟进引入类似的制度[7]。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司法绩效评价的结果可以用作选任法官以及改进法学教育的参考,但不得作为对法官个人进行定级排名的依据,未经法律许可也不得用于追究法官的纪律责任[8]。因此,对美国的法官而言,它只具有某种督促作用,并不具有强制性,与工资、奖金的增减更是完全无关。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如德国、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只是将法官绩效考核的结果作为法官选拔与晋升的参考,而且仅是众多参考因素之一[9]。
如此看来,将考核结果同法官个人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似乎只是我国法官管理制度的特色。为什么其他国家不采取类似的做法呢?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法官在《法官如何思考》一书中明确指出:“全面拥抱绩效考核,将之作为激励或约束法官的方法之一,还为时过早;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给高分的法官发奖金,这样的提议(没有任何人这样提议)则完全荒唐。”[10]139为什么波斯纳法官直斥这种做法是荒唐的呢?
对于以上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做出回答。但本文关心的是绩效考核制度能否保护与鼓励法官的三种动机,因此,本文以下将尝试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解答。
(二)经济性激励与动机拥挤效应
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有两个基本命题:命题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11]。命题二,价格的抬升会提高供给。由这两个命题还可以推导出第三个命题,即命题三,当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时,经济性激励的加入会对人们的行为意愿和绩效产生积极的提升作用。
命题三的提出为众多“激励导向型”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便属其中之一。我们可以推想,该项制度的初衷是通过加载一些激励机制来增强法官的行动动机,尤其是经济性动机,进而提升法官工作的质量与效率。但是,其能否在增强经济性动机的同时保护并鼓励法官的智识性、伦理性以及交互性这三种动机呢?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命题三。其实,这个命题若想成立还需满足另一个条件,即当经济性激励被引入时,行动者既有的非经济性动机是保持不变的[12]。但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个条件其实是不成立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经济性激励的介入很可能侵蚀和削弱行为人非经济性动机[13]。这种现象被称为“动机拥挤效应”(Motivation Crowding Effect)。
1970年,英国学者 Richard Titmuss在《礼物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14]一书中首次描绘了动机拥挤效应。这本书以英美两国的献血制度为考察对象。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推测,为献血者提供货币补偿的商业化献血制加载了无偿献血制所不具备的经济性激励,因而运行效果应该更佳。但事实上,情况刚好相反。美国的商业化献血制无论在血液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逊于英国的无偿献血制。Titmuss认为,这是由于经济性激励往往会侵蚀个人的公共责任意识,因而降低甚至摧毁了公众献血的意愿。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瑞士。瑞士政府打算建造两个贮存核废料的仓库。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符合共同利益的项目,但是没有哪个社区打算让仓库建在自己附近,这就是所谓的“NIMBY”问题。①Not in my backyard,指某些有助于提高社会总福利、但对建设地附近居民的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项目,如危险废弃物处理设施、机场等。1993年,Bruno Frey等人就该项目做了一个调查,所有的受访者都被问到是否允许核废料库建在自己社区所在的地界。起初,超过半数(50.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44.9%的受访者反对,其余4.3%的受访者则对此表示无所谓。但当瑞士政府决定对核废料库所在地社区中的所有居民提供经济补偿之后,支持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急速下降——只有24.6%的受访者愿意接纳该项目。换言之,约有1/4的受访者改变了看法。研究者认为,很多人原先愿意接纳这种NIMBY项目是出于公共责任意识,但是外在干涉即经济补偿引发了居民们对有害设施给他们造成的损失的关切,这就降低了居民们接纳该项目的非经济性动机[15]。在该案例中,非经济性动机所发挥的作用其实是大于经济补偿的,外在干涉导致“此长彼消”,居民的接受度因而下降。
近年来,动机拥挤效应已经吸引了众多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的关注,经验性证据不断呈现,理论解释也日趋成熟。学界在其实存性上已基本形成共识。它的发现揭示出经济性激励的潜在破坏作用,即对行动者非经济性动机的排斥与压抑。很显然,法官的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这三种动机都属于非经济性动机。既然如此,我国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由于加载了较强的经济性激励,便很可能挤出上述三种非经济性动机。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表明,非经济性动机一旦因经济性激励的介入而被挤出,即使经济性激励后来被移除,非经济性动机也经常无法复归;①Janssen & Mendys-Kamphorst, supra note 17, at 377-395.即便可以复归,也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并且很难达到外在激励被引入前的原初水平。不仅如此,当经济性激励被移除后,行动者的工作热情和动力在中、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大幅滑坡,甚至比原初水平还要差,亦即导致“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②Benahou & Tirole, supra note 16, at 289-520.所谓棘轮效应是指一个行为在经过一个阶段之后,就很难返回从前。棘轮效应通常被用来解释消费行为的不可逆性,即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随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如此看来,我国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对于法官的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动机的破坏是深远的,因而不适宜用作法官管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政法委的决策是正确的,该项制度理应予以修正。
三、制度内置的司法行为理论
(一)法官管理制度与司法行为理论
在法官绩效考核制度运行的十数年里,不乏大量的批评之声。但为什么这项制度在近几年来又呈现出“蓬勃”之势?这其中固然有路径依赖问题,但仅就学术研究而言,对该项制度的批评深度严重不足恐怕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原因。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中有关法官绩效考核的所有文献,发现绝大多数批评都采取相似的模式,即首先指出制度运行中产生的弊病,然后给出改进的思路或方案。此类文献中最常出现的词汇便是如何能让该项制度变得“更科学”“更健全”“更完善”。这种“哪坏补哪”的对策性思维,使得对该领域的研究沦为纯粹技术性的雕琢,反思力度严重不足。法官绩效考核作为一种制度性实践,必然是“理论内置”(theory-embedded)的[16]。 换言之,法官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是在某种理论的指引之下形成的,而这种理论对于法官绩效考核这种实践而言具有“构成性”(constitutive)意义。③制度设计者或实施者或许由于缺乏反思性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不存在。如果理论有缺陷或不适用,那么制度必然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病。因此,对制度的批判如若忽视了理论层面的检讨,就不能说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失效源于其所依凭的激励理论之错谬。研究如果没有深入到这个层次,就不可能命中这项制度的要害。以此观之,既有的那种仅评价实践效果而对实践目标缺乏体认的批判不过是在零打碎敲,显露出一种理论无意识。
因此,当我们试图回答如何建构完善的法官管理制度这一实践问题时,我们必须先找到制度背后的理论问题,这是此项研究展开的先决条件。那么,这里的理论问题究竟又是什么?
法官管理制度的任务是对法官的个人特质进行规制,因为有些特质关系到裁判质量。那么,究竟哪些特质会影响到裁判?它们又是以什么方式影响的?这些便是“司法行为理论”(Judicial Behavior Theory)要回答的问题。
所谓司法行为理论,是指研究法官在决策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哪些因素影响的理论。只有对这些影响因素具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哪些因素需要规制,又该以何种方式规制。因此,司法行为理论乃是研究法官管理制度的理论根基——它是制度内置的各种理论中最基本的那个,其他理论都必须在其基础之上展开。对“司法行为”的理解正确、全面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法官管理制度的“建筑质量”[10]5。
受法律现实主义的影响,“二战”之后,“司法行为”问题在美国一直是研究热点,业已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文献。但是本文却不打算直接借用这些研究成果,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国情不同。中美两国在司法制度、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差异甚大。司法制度方面,中国为科层型,美国则为协作型[17];中国法官为职业制(career),而美国法官则为旁门制(lateral-entrance)[10]120-121。 法律体系方面,中国属大陆法系,法律形式以制定法为主,美国则属普通法系,除制定法外,还强调遵循先例。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在法院内部相对统一,美国法官则自由与保守泾渭分明,激烈对抗。因此,很多影响美国法官裁判的因素并不见得同样影响中国的法官,而很多影响中国法官裁判的因素又未能在既有的理论中呈现出来。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既有研究的旨趣与本文的需要并不相符。美国学者研究司法行为,其意主要在于解释与预测,即解释司法决策的过程以及预测个案中法官将做出什么样的判决结果。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产生出大量高度复杂与精细的司法行为理论。根据波斯纳法官的归纳,现有的司法行为理论依类型划分有九种之多[10]17-52。但是本文所需要的司法行为理论乃是服务于法官管理制度之建构,旨趣不同则视角各异,因此现有理论所提供的洞见大多无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帮助,无论它们如何复杂与精细。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必须对司法行为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即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出发,建构符合法官管理制度研究所需的司法行为理论。当然,我们也并不完全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过往的司法实践可以成为生动的教材。我们仍可以利用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失败继续进行深入的分析。作为法官管理制度之一,该项制度也必然内置了一套司法行为理论。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的理论提炼出来并找出其缺陷,也就知道改进的方向了。
(二)司法行为的“经济人”理论
前文提到,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特点是将考核结果同法官的物质奖惩等直接挂钩。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激发法官的经济性动机。换言之,该项制度假定法官的工作动力主要来源于经济利益,亦即将法官视作“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经济人”假设属于典型的经济学分析方式,即假设人是理性自利的,一切行动都围绕着如何增进自身福利,然后以此为前提构建理性选择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很显然,将法官视作“经济人”就等于认为影响法官裁判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性的。我们可以将这种内置于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司法行为理论称为“经济人”理论。
众所周知,经济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势头颇为强劲,不断向其他学科渗透,因而也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在法官管理制度领域,经济学早已成为主流的分析模式。这里的“首功”,当记在将经济学引入法学的波斯纳法官身上。随着波氏著作的不断引入,国内学者如苏力、艾佳慧、王雷等,纷纷采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波斯纳一道追问:法官最大化什么?①参见苏力:《审判管理与社会管理——法院如何有效回应案多人少?》,《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176-189页;艾佳慧:《中国法官最大化什么》,《法律与社会科学》2008年第3卷,98-151页;艾佳慧:《法院需要什么样的人事管理》,《法律适用》2008年第10期,25-30页;王雷:《基于司法公正的司法者管理激励》,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建构。因此,“经济人”理论就不单纯是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所内置的司法行为理论,更代表了法官管理制度领域内的主流研究范式。然而,这些学者忽略了重要的一点,“经济人”作为一种司法行为理论(或范式),虽然在美国也是主流之一,其功用却主要是解释与预测美国法官的司法决策行为,而非用于美国法官管理制度的建构。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晏子春秋·杂下之十》)。“经济人”理论(或范式)漂洋过海之后,摇身成为我国法官管理制度研究的基础理论(或范式),而其原本的解释与预测功能倒鲜见有中国学者运用。“经济人”理论(或范式)真的适合法官管理制度领域的研究吗?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其加以评估。
在理论层面,“经济人”理论(或范式)犯了过分简化的错误。经济学之所以风头日劲,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其理论的简洁性:它能够将纷繁复杂的现实简化为几个要素以方便分析。“经济人”理论(或范式)也承继了这种简洁性,但这种简洁性是有代价的,它可能遗漏掉一些关键要素,致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出现重大偏差。“经济人”理论(或范式)的问题恰恰是将现实过分简化:它仅仅关注到法官的经济性动机,而基本无视法官的非经济性动机,致使我们对司法行为的理解过于片面。
在实践层面,依“经济人”理论(或范式)建构的法官管理制度无法培养出优秀的法官。通过我国法官绩效考核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依“经济人”理论(或范式)建构的法官管理制度过分强调经济性激励,很容易触发动机拥挤效应而挤出法官的非经济性动机,而某些非经济性动机却是好法官的必备品质。因此,“经济人”理论(或范式)不适合用来指导司法实践。
简言之,“经济人”理论(或范式)的错误不仅在于把法官视作“单向度的人”,更堪忧的是,由这种理论谋划出来的制度最终真的将法官驯化成“单向度的人”。
然而,“经济人”理论(或范式)毕竟提供了一种对法官的规制模式:它启示我们,可以利用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一面,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引导与约束法官的决策行为。如果我们放弃“经济人”理论(或范式),就间接放弃了这种规制模式。这就使我们似乎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无法保护法官的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非经济性动机,要么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活动进行有效的管控。反对废除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声音之一就是,一旦废除,没有其他可以约束法官的机制作为替代。然而,如果我们细加考察,这个所谓的困局其实并不存在。假使我们的法官管理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与鼓励法官的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非经济性动机,这些敦促自身不断提升裁判技能、谨守职业伦理、待人真诚以礼的动机,事实上既是法官行动的内在动力,也是司法行为的内在规制——法官会自觉主动地规范自己的裁判活动。换言之,如果说依“经济人”理论(或范式)设计的法官管理制度提供的是一种“他律”机制的话,那么这些非经济性动机则能够为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一种“自律”机制。如此看来,只要我们能够建构一种有助于保护、鼓励法官的这些非经济性动机的司法行为理论,我们就能同时为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一种新的约束力来源。
四、重构司法行为理论
在探寻符合法官管理制度研究所需的司法行为理论之前,我们需要申明这种理论的功能与限度。无论是用于解释与预测,还是用于制度建构,司法行为理论都始终是一种描述性理论而非规范性理论。换言之,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法官决策活动的视角,但不能直接给出应该如何操作的方法。尽管这种理论不能告诉我们更多,但它依然是重要的。正如前面“经济人”理论(或范式)所展示的,一个错误的视角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将我们引向歧路;相反,一个恰当的视角却能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洞见,让我们知晓制度建构可以从哪方面入手。因此,当我们想要构建一种能够保护与鼓励法官的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非经济性动机的司法行为理论时,我们不能寄希望它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具体如何建构法官管理制度,而只能期望它提供给我们合理看待这些动机的视角。想要找到合理看待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动机的视角,就需要我们对它们的性质有所把握。仅仅了解它们是非经济性的,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进一步探明这些动机是如何产生的。社会学理论表明,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一切情感、需求、动机都必然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化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理论中寻找答案。
当我们谈论法官时,我们不是在谈论某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在谈论一种身份、一种社会角色。从社会角色理论看,每一种社会角色都是由一系列“行为期待”(behavior expectations)——即他人对角色扮演者应当如何行动所提出的要求——构成的[18]。例如,对母亲的行为期待是关爱子女,对商人的行为期待是童叟无欺,对工匠的行为期待是技术过硬,等等。本文第一节所谈到的好法官的三个标准,就是站在社会角色理论的视角提出的。我们可以看到,行为期待事实上对角色扮演者提出了某些规范,或者说施加了某种约束。角色扮演者既不能无视也不能拒绝这些规范与约束力,否则就会招致制裁。制裁既包括积极意义上的,也包括消极意义上的:违反行为期待要么会遇到某种障碍,要么无法获得应有的支持或便利,并且这些规范的影响并不总是外在的。在长期的角色实践过程中,角色扮演者会通过观察、模仿、教化等方式逐渐将行为期待“内化”(internalization),亦即将行为期待所负载的规范与要求内化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这样,角色扮演者就会自愿而主动地按照行为期待行动。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G.Dahrendorf)将这样的角色扮演者称为“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19]。
很显然,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这三种动机也是通过上面这种方式形成的。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动机来源于法官的行为期待所负载的规范,即裁判技能过硬、谨守职业伦理、待人真诚以礼。作为角色扮演者的法官将这些规范内化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也就形成了上述三种动机。
从“经济人”的角度看法官会忽视这三种动机,但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从角色扮演者,亦即“社会人”的角度来观察法官,则可以投射到这三种动机之上。因此,如果仿照“经济人”理论建构司法行为的“社会人”理论,我们就可以将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动机纳入到视野中来。这相比“经济人”理论来说是一个进步。那么,“社会人”理论是否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呢?我们仍可以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来进行评估。
在理论层面,司法行为的“社会人”理论能够全面解释法官的各种动机,亦即能够多维度、全方位地观测影响司法行为的各种因素。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理解法官,就意味着将法官个人视作各种社会角色的集合体:他是一名法官,但可能同时扮演着父亲或儿子、丈夫、领导者或下属、政党成员、宗教信徒等多种角色,每一种角色都会向他提出各种规范与要求,也因此塑造了他各种各样的动机。而其中的某些动机便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带入到他的工作中,对裁判活动造成影响。这里面当然也包括“经济人”理论所特别强调的经济性动机,我们完全可以用负有养家糊口义务的父亲、丈夫等角色来解释这种动机的来源。换言之,“社会人”概念可以包容“经济人”概念,并且它更为开放,能够解释更广泛的现象域。因此,司法行为的“社会人”理论提供了一个比“经济人”理论更为全面的观察司法决策活动的视角,它能够将包括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动机在内的各方面因素纳入观测范围。
在实践层面,司法行为的“社会人”理论对于法官管理制度的建构与改革,尤其是在保护、鼓励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动机方面,均能提供理论上的助益。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司法行为的“社会人”理论可以借助其背后的社会角色理论为制度建构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虽然“社会人”理论本身只提供一种观察司法行为的视角,而不能直接给出制度建构的方案,但其所依托的社会角色理论却是“门类齐全”的,其中包含了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十分可观的对策性研究。例如,从角色理论看,如何鼓励法官的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动机是“角色学习”(role learning)或“角色适应”(role adaption)的问题;如何防范上述动机受到压制或排挤则是“角色紧张”(role strain)或“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的问题[20]。而对于上述问题,既有的角色学研究已经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①See William J.Goode, “The Role Strain Theory”,25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1960,pp.483-496; Neal Gross,Ward S.Mason& Alexander W.McEachern,Explorations in Role Analysis:Studies of the School Superintendency Role,New York:John Wiley& Sons 1958;Robert K.Merton, “The Role-Set:Problem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8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7,pp.106-12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也有不少国内学者应用这些理论对于中国法官的角色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并且给出了相应的应对建议。①参见江国华、韩玉亭:《论法官的角色困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15-28页;张晓冰:《法官角色紧张及其消解》,《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186-190页;吴英姿:《法官角色与司法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黄湧:《基层民事法官如何办案——从一则案件的审理看法官角色混同》,《法律适用》2007年第1期,75-80页;瞿琨:《论法官角色与公正司法》,《学术界》2006年第1期,79-84页;史美良:《法官角色的矛盾辨说》,《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177-179页;秦策:《法官角色冲突的社会学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35-40页。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献也都提到“社会人”这一概念,但含义相对狭窄,往往用来与“自然人”“法律人”“单位人”之类的概念进行对照分析。而本文所使用的“社会人”,源自拉丁语词homo sociologicus,沿用其原初含义,使之完全可以包容上述各种“人”概念。国内外的这些角色学研究都可以成为法官管理制度建构与改革的理论指南。“社会人”理论本身虽然不是制度建构的“工具箱”,却是开启“工具箱”的那把钥匙。
其次,司法行为的“社会人”理论为司法行为的“语境化”研究打开了空间,从而有助于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官管理制度。司法行为的“经济人”理论(或范式)假定人都是理性自利的,因而无论是中国的法官、美国的法官、伊朗的法官还是埃塞尔比亚的法官,在这种理论面前都不过是“经济人”,没有实质性差异。换言之,依“经济人”理论(或范式)建构的法官管理制度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在全世界推而广之。这就抹杀了时代、文化等因素对司法行为的影响。“社会人”理论则相对灵活开放,它会观照某一社会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诸多文化因素,考察它们对于司法行为的影响,这有助于因地制宜地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管理制度。
由此可见,司法行为的“社会人”理论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优于“经济人”理论,更适合作为法官管理制度研究的基础范式。
结 语
当前,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引得学界各路名家纷纷登场,一时有百家争鸣之势[21]。本文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加入这场讨论,关注的是制度背后的基础理论问题。
任何一种法官管理制度都内置一套司法行为理论,若想建构完善的制度,就必须先建构妥当的理论。现有的法官管理制度研究背后隐藏着一个“经济人”影像。这种研究范式将法官视作“单向度的人”,致使其所谋划出来的制度容易触发“动机拥挤效应”,从而驯化出“单向度的法官”。“单向度的法官”具有强烈的经济性动机,缺乏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对“好法官”来说不可或缺的动机,而当下的法官绩效考核就是要通过一种行政管理上的“规训技术”改变司法规律意义上的“法官的自由逻辑”,这正是该制度失败的原因之一[22]。相比之下,司法行为的“社会人”理论则从多个向度来理解法官,不仅能够全面观测影响裁判活动的各种因素,而且在法官管理制度的建构与改革,尤其是在保护、鼓励智识性、伦理性与交互性等动机方面,亦可提供理论上的助益。因此,笔者认为,应以“社会人”理论取代“经济人”理论作为法官管理制度研究的基础范式。
建构完善的法官管理制度需要一整套复杂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而司法行为理论在这个体系中发挥着近似于基石的作用——体系中的其他各种理论如规制理论、激励理论,都必须建筑于司法行为理论之上。找到妥当的司法行为理论,并不意味着建构完善的法官管理制度这一难题就能一劳永逸地得以解决,它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必要的起点,是构建理论体系的第一步,我们还需要一系列与司法行为的“社会人”理论相配套的、能够提供具体规制模式的规范性理论充实到这个理论体系中来,如此浩繁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予以完成。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引起学界对于法官管理制度背后的理论问题的关注,提升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反思性与理论自觉意识,以此激发相关后续理论研究,共同打造符合法官管理制度研究所需的理论体系。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史尚宽:《宪法论丛》,台北:荣泰印书馆1973年版,第336页。
[3] 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4] 刘炜:《法官绩效考核之忧》,《民主法制时报》2012年6月11日,第A4版。
[5] 《中央政法委:取消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考核指标》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22/c1001-26428720.html;《最高法决定取消对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考核排名》,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2-26/6916495.shtml。
[6] 《法院仍“晒”不合理司法考核指标》,http://china.caixin.com/2016-02-25/100912438.html。
[7] Rebecca Love Kourlis& Singer,Jordan M,“Using Judi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to Promote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90 Judicature, 2007,pp.200-207.
[8] 么宁:《美国司法绩效评价机制概览》,《人民检察》2012年第3期,第67-71页;罗灿、兴成鹏:《美国法官如何面对绩效评估》,《法制日报》2014年8月26日,第 11 版;Sharon Paynter& Richard C.Kearney,“Who Watches the Watchmen?:Evaluating Judicial Performance in the American States”, 41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2010,pp.923-953.
[9] 苏永钦:《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382页。
[10] 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 Roland Benahou& Jean Tirole,“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70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3,pp.489-520.
[12] Maarten C.W.Janssen & Ewa Mendys-Kamphorst,“The Price of a Price:on the Crowding Out and In of Social Norms”, 55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4,pp.377-395.
[13] Bruno S.Frey& Reto Jegen,“Motivation Crowding Theory:A Survey of Empirical Evidence”, 15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1,pp.589-611.
[14] Richard M.Titmuss,The Gift Relationship: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New York:Random House,1971.
[15] Bruno S.Frey & Felix Oberholzer-Gee,“The Cost of Price Incentive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otivation Crowding Out”,87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pp.746-755.
[16] 陈景辉:《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法学的知识框架即法理学在其中的位置》,《法学》2014年第3期,第 50-67页。
[17] 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第72-105页。
[18] Ralph Linton, The Study of Man, New York:Appleton-Century 1936,pp.581-582.
[19] Ralf Dahrendorf, “Homo Sociologicus:Ein Versuch Zur Geschichte,Bedeutung Und Kritik Der Kategorie Der Sozialen Rolle”, Vs Verlag Fu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0, pp.1-162.
[20] 秦启文、周永康:《角色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129页。
[21] 李拥军:《司法改革中的体制性冲突及其解决路径》,《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
[22] 李拥军、傅爱竹:《“规训”的司法与“被缚”的法官——对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困境与误区的深层解读》,《法律科学》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