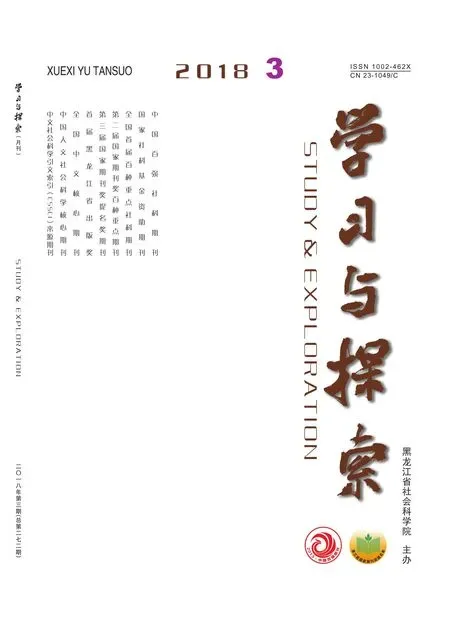对State政治共同体内涵的历史阐释
2018-02-19顾春梅周春生
顾春梅,周春生
(1.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2.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上海200234)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汉语“国家”一词来翻译、诠释英语中的State概念。但细细想来,问题还不少。在古代中国宗法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理念下,“国”与“家”其实是一体的。学人当然不会从这层意思来翻译、理解西方的State概念。即使抛开古代的含义,认为今人一般所用“国家”一词已经包含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国体和政体的内涵,这种想法也需要做些说明、解释,因为关键的问题是学人在谈及西语State概念的内涵时还有诸多模糊之处。
一
回溯西方的历史,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理论家尚未使用State或相类似的词来撰写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层面的政治著作。在西方的政治学理念中,State是近代才使用的关系到国体、政体等方面的概念,其内涵包括民族特性、地域划定、主权地位等。这里先做个提示,在上述内涵中隐含着一个核心的因素——政治共同体,这一核心因素很容易在使用中文“国家”一词时被忽略。马基雅维里最初提出State的概念,人们在理解马基雅维里的State内涵时多半向政治体制和政治治理如何稳定、如何有效用的方面着想。虽然这种理解和诠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事实上马基雅维里在阐释State问题时始终没有忘记其中的核心因素——政治共同体及其结构。这样说来,中文“国家”一词的词义必须加入政治共同体的内涵才能与State概念相契合。(本文出现“国家”一词时有不同的上下文语境,这里先做个提示。)当然,我们更不能一味从阶级暴力、政治控制这些统治的层面来片面理解、诠释State等。
政治思想史上与State或中文“国家”对应的英语词汇还有 Republic、Commonwealth、Community、Nation等。仔细考订这些概念会发现,它们都带有共同体的意蕴。英语中Commonwealth作为“共同体”来使用可以从洛克等人著作的诠释中找寻。17世纪英国政治家与政治思想家巴科斯特著有《神圣共和国》一书[1]。另外还有一个词即Community,此词的用途比较广,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各个层面的共同体内涵都可以通过这个词来表达。因此,Community的指称范围要广泛得多,它可以指一个社区,也可以指历史上的一个行会,当然还可以指一个自治政府。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是通过社区、行会、自治政府等管理自己[2]。其中在政治学意义上分析国家政治共同体时,Community仍是重要的概念。今天的“欧盟”除了European Union外,也可翻译成European Community。有些政治思想家认为Commonwealth与Community之间还是有点区别,认为Community意义上的共同体要比Commonwealth的社会层次更低些[3]81。例如,上面所说社区、行会等就是比Commonwealth低一级的共同体。这些情况只要注意具体的使用状况,其不同的内涵很容易辨识。Nation一词则典型地反映出近代民族共同体的内涵。那么State这个词的政治共同体内涵如何加以理解呢?西方近代的State与古代史上的城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用State来翻译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关于国家政治的书籍、观点时都必须做些必要的说明,否则会导致诸多误解的发生。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思想家在涉及高于个人、家庭和社会团体的政治结构时多使用“Polis”“Republic”等词汇。State这个词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4]。但有一点是西方古今相同的,即政治思想家在使用“Polis”“Republic”“State”“Commonwealth”等概念时都注意到了政治共同体的内涵。就这一层面而言,我们有时用State来指代上述其他政治共同体概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考查西方的政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我们首先在柏拉图那里发现其对共同体问题所做的阐释。柏拉图在涉及与汉语“国家”相类似的观念时,多用“城邦政治制度”这一概念。柏拉图的那本政治著作希腊文作“πολιτεια”,也就是“城邦制度”的意思。现在中文将柏拉图的共同体译成“国家篇”会引起一些误解。英文通常将那本著作译为“Republic”[5],这是比较合理的译法。因为城邦政治本身就是众人的政治,即政治治理的共同体。柏拉图的哲学认为,一物之所以为此物,必有其存在的结构或道理,只不过我们难以从终极的意义上认清这个结构罢了。与哲学家从整体的角度去设想那个事物存在的理念一样,政治思想家的任务就是要把政治共同体的性质搞清楚。于是柏拉图做了理想化的共同体构想,后人据此译作《理想国》。柏拉图《理想国》指出,“我们的立法不是为了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6]柏拉图设想:城邦按正义原则运行;城邦由法律维系着;城邦里有阶级的分层;每个公民经过教育后适应城邦的政治生活,各按其地位行事,如此等等。一幅政治共同体的图景。
现在我们通常将亚里士多德议论城邦政治共同体的那本书译作《政治学》(Politics),其实希腊文的原意还是指城邦制度,确切地讲是指城邦政治共同体。《政治学》开宗明义论道,“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事——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 ‘城邦’ (πολιs),即政治社团 (城市社团)。”[7]1因此一定要用国家来指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的话,也应当确切地理解为城邦国家政治共同体。显然,城邦政治共同体要高于和先于个体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假设,任何政治都与这样一种本性相关,即整体先于个体,整体大于个体总和,“就本性来说,全体功能先于部分”[7]8-9。按此推论,“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7]8。城邦共同体是个体的完成和完整形态。比如说一粒稻谷当其长成一束稻穗的时候,真正意义的一粒稻谷的意义才显示出来。那一束稻穗就是城邦政治共同体。公民是城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到了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出现,政治就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既然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那么决断城邦事务的准则就不应该代表个人和家庭的局部利益,而应是整个城邦或全体公民的利益。那么通过何种政治手段来维系城邦的利益呢?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谋而合,都提出既合乎理性又关涉现实利益的法律手段,“法律是以合乎德性的以及其他类似的方式表现了全体的共同利益,而不只是统治者的利益。”[8]89-90“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部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7]168亚里士多德说:“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智的体现[7]172。“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7]169。这样,亚里士多德已把城邦治理准则、法律的特性、自由公民平等人格等政治要素都归结为理性本性的驱使。亚里士多德还首次提出对全体公民都适用的自然法思想,“政治的公正,或者是自然的,或者是传统的。自然的公正对全体公民都有同一的效力,不管人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出于自然的东西是不能变动的,对一切都有同等效力”[8]102-103。综观亚里士多德的一生,对城邦政治共同体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百余篇关于不同城邦政治体制的著作中,现残留的只有《雅典政制》一篇。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著述还具体展示出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各方面内容,例如公民通过多种途径来感受城邦政治制度并参与城邦政治实践:公民登记制度、参与公民会议、与体现公民权利义务的各种机构打交道、参军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途径。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政治共同体的所有上述想法对以后西方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学说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或者说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构架。
城邦政治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单纯是政治思想家的发明,其背后也有现实的社会发展需求。以古代希腊为例,古希腊特定的地理环境使它不断处于与周边不同文明的交流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邦政治体制就是民族迁徙、文明碰撞的产物。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阿卡亚人向希腊半岛迁徙,公元前1200年左右,又有多利亚人的大举侵入。大迁徙打破了血缘关系,使地域为基础的城邦体制孕育而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大殖民运动。在大殖民过程中,小亚细亚沿岸、爱琴海诸岛、黑海周边地区及地中海各处相继建立起新的城邦。在这些新的城邦内,一部分外来民族面对着另一陌生区域的民族,两者间缺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于是,以广泛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新的政治统治形式出现了,它们又反过来影响母邦政治结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权利问题及如何完善与此权利相应的政权结构问题凸显出来。在雅典方面,梭伦改革对公民身份予以法的确认,并规定公民的各项权益,建立最高权力机构“四百人会议”。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对打击贵族统治、确保公民权益又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克利斯梯尼改革则重新划定行政区域,设“五百人会议”,使之成为最高立法和决策机构。全体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任何官职对公民敞开,各种官职的任期一般为一年。同时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对分立。例如,公民大会为立法机构,“五百人会议”和“十将军委员会”掌握行政、军事等权力,原来的陪审法庭成为司法与监察机关。当然这种三权分立在权限上并非十分明确,而且此提法也是后人赋予的。尽管如此,伯里克利时代在公民权利及相关的政权机构建设方面达到了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顶峰。所有上述历史因素汇聚起来,形成了政治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
罗马共和政治体制的产生亦有类似于古代希腊的历史事实。针对共和政治体制,西塞罗写了《共同体篇》或《共和国篇》即Republic,就是指的“大家的”意思。在西塞罗的著述中,最高的、最理想的政治体制仍旧是公民共同参与的城邦政体,他称其为公众的或公共的政治团体。“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①参见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译者就这段文字做了个注解:“国家”的拉丁文是Res publica,意思是“公共的事业”,Publicus(公共的)一词是源自Populus(人民)。西塞罗的这一重要的国家定义的拉丁原文是:Est res publica res populi,populus autem non omnis hominum coetus guogue modo congrecatus,sed coetus multitudinis iuris consensus et utilitatis communione sociatus.进一步阐述完美的共同体应当是“法的联盟”,“既然法律是公民联盟的纽带,由法律确定的权利是平等的,那么当公民的地位不相同时,公民联盟又依靠什么法权来维系呢?要知道,公民们不愿意均等财富,人们的才能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起码应该在权利方面是相互平等的。”[9]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的法学家开始用万民法的理论构筑罗马帝国的共同体。①参见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篇“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关于万民法的问题还可参见周春生等:《欧洲文艺复兴史(法学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帝国在经济与政治制度上很难以共同体的形式来同化被征服地区。当时在公民权的授予问题上就存在着罗马本土与各行省之间的冲突。在精神层面,罗马人可以用军事和拉丁语征服地中海世界,但罗马人无法用思想意识同化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后来罗马人对基督教世界发生了态度上的根本性转变,试图找到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纽带,但为时已晚。
二
到了中世纪,情况发生了诸多变化,庄园成了基本的经济、政治单位。庄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共同体,其中有各种庄园法在维系着共同体的生活。中世纪也是家族政治主导的时代,那时取得王位的家族势力、其他家族的势力、教会的势力、地方乡绅的势力、城市市民的势力等都在相互博弈之中。中世纪英法等国的议会就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博弈并取得相对平衡的结果。因此,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中仍存在着特有的政治共同体内容。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制度、机构等逐渐成为近代国家的雏形。即使后来的君主专制时代也没有摆脱共同体的性质。之所以存在着上述政治共同体的特征,还与城市的兴起有关,因为正是市民、商人等的出现,需要政治机构按经济的实力而不是按政治的特权进行从形式到内容的调整。近代西方的王权正是在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关系调整过程中强大起来的。所以,从表面上看,早期近代西方曾出现过强大的王权,并以此为象征出现了近代的国家。但从实质来看,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发育过程是各种权势集团的利益调整过程,从而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或者这么说,在中世纪表现为王朝政治共同体模式;到了近代则呈现为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模式;至文艺复兴时代,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整体功能开始显现,谁的民族国家整体功能发挥得充分,谁的经济、政治、国际地位等优势就更为明显。那时的王权已经转变为国家的象征而非家族势力的象征。因此,在英法等国,政治思想家特别在意与主权相关的君权问题。那时主权与君权是通用的概念。
谈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就要牵涉基督教的问题。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家所阐释的基督教教义中,同样包含鲜明的政治共同体概念。从宗教社会的角度看,基督教会的理论与实践是西方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共同体社会。我们可以通过阅读阿奎那的著作来了解此点。阿奎那的城邦政治理论的许多方面来自先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例如人是合群的动物;在一个自由人组成的城邦社会中必须以城邦整体的幸福为宗旨,如此等等[10]43-46。阿奎那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城邦高于个人和家庭,并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10]106。阿奎那认为,“一个营共同生活的社会是比较完善的”[10]47。无论是哪一种统治,都必须顾及公共的幸福,即使君主进行治理的时候也应当“念念不忘公共的幸福”[10]47。如果历史真那么简单点的话,基督教世界作为政治共同体是有成功可能的。但基督教出现在一个世俗的社会之中,世俗社会的各种权势与基督教会进行了政治上的博弈,最后基督教退出世俗社会的权力争夺,回到了其精神的领域。所以基督教会的帝国政治共同体实践只是一个插曲。在后来文艺复兴时期,萨沃纳罗拉、卡尔文的政治实践虽然在城邦的范围内进行,然而其框架只是基督教社团的放大,当然最后以失败告终。胡克的思想中也有浓厚的基督教政治共同体的特点,他在《教会政体法》(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中系统地阐述了教会作为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理论,进而为近代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结构和运作确立一个总体的框架。②See The Works of Mr.Richard Hooker,arranged by John Keble,revised by R.W.Church F.Paget,Burt Franklin,1970.全书共3卷,近2 000页的篇幅,其中《教会政体法》是主要部分,训诫文也占了相当篇幅。
到了欧洲近代社会的早期,民族政治共同体出现后,古代政治共同体基本框架又复活了,只是具体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民族政治共同体打上了主权的烙印。博丹的主权说关联君主统治的关系,但这种统治的基础是建立在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之上的。在16世纪,君主统治是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达到某种平衡的象征,即君权所维护的是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所以君权也成了这个共同体的象征。如果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近代意大利,甚至近代西方的政治思想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态问题。就此而言,近代国家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多重政治权益的调整过程:这里涉及国家与个人、国家与集团、国家与国家、国家机器自身各个部件,等等。
意大利的情况比较特殊,中世纪意大利的许多城邦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种城邦国家有些是历史遗留的,有些是新兴的,但无论是哪一种,城邦政治生活都经历过市民社会的发育过程。因此,意大利城邦国家能够更清晰地传达出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特点。意大利早在中世纪时代就到处是城邦国家政治共同体,特别是行会与行会、家族与家族等的政治共同体。但在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发展方面,它落后了。也就是说,意大利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功能还没有得以表现。另外意大利又与神圣罗马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即当柏克等人在关注国家主权、君权等问题时,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仍在关心早已存在的城邦国家共同体结构、国家治理功能等问题。尽管如此,他们对世俗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种种思考将近代西方国家政治的诸多本质问题勾勒出来。那时意大利特别有政治敏感力的政治思想家也意识到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是一种国家发展趋势。像马基雅维里这样的政治思想家,经历了漫长的外交实践生涯,对刚刚显露强大政治共同体功能的民族国家产生了十分敏感的意识。所以,他的政治思想阐释任务非常明确:一是把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特征等讲清楚,二是呼吁意大利尽快在一位称职的君主领导下实现统一。后来的许多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都将民族统一视为意大利国家发展的方向。在但丁的政治理论中,罗马人就是由许多共同体组成的更大的共同体。①See Dante,Monarchy,Prue Shaw,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41.英文在翻译低一层共同体时用了Collegiate Body一词,而高一级的共同体则用了Community,大致相当于Stato或Public的概念。详细可参见拉丁文与意大利文对照学术版《君主统治论》。Dante Alighieri,Monarchy,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2001,pp.250-251.在这个共同体中,有一些人扮演治理者的角色,而公民及公民的自由则是共同体的核心。法律、君主等都是为了共同体的秩序和公民的自由,而不是相反[11]。这些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观点在后来马基雅维里的著述中有更详备的发挥。
三
现在就来阐释马基雅维里的State理论。马基雅维里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Stato这个意大利语词汇,Stato的原意并不是指国家,而是稳定地站着。引到政治统治的方面,就是城邦政治的治理如何实现效用和稳定的问题。在马基雅维里及当时政治理论家的心目中,State的政治运作即如何统治的含义凸显了出来,也就是如何让城邦政治共同体更有效地运作。基于政治共同体的这种有效统治和管理形式,有些城邦中君主个人的势力强一些,就是君主统治的共同体。无论是古代罗马还是近代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他们都喜欢用君主统治和大众统治这样一些概念,有时我们简单翻译成君主国和共和国等,以为君主国就是君主说了算的国度,而共和国就是由公民共同说了算的国度。其实这里有点误解。在马基雅维里的时代,那些君主势力比较强大的城邦同样具有其他城邦政治共同体的一些制度,君主同样不能违背这些制度的规约。君主国中的政治共同体构成要件如法、各种市民会议、公民身份等仍然存在,只是君主更强势些而已。不要误以为在当时意大利的君主国里存在着与共和国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国家政治制度。后来洛克总结道:“‘Commonwealth’一字,我在本文中前后一贯的意思应当被理解为并非指民主制或任何政府形式而言,而只是指任何独立的社会。拉丁人以‘Civitas’一字来指明这种社会,在我们的语言中同这字最相当的,是‘Commonwealth’一字。”①参见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1页。此言出自第10章“论国家的形式”,英文原文是“Of the Forms of a Commonwealth”,参见 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Second Trea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354。 其完整的意思应当是国家政治共同体。顺便指出,柏拉图的《城邦政制》即《理想国》的拉丁文译名就是civitas,也是指的共同体。可见,政治共同体是最根本的因素。洛克还就此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当人们最初联合成为社会的时候,既然大多数人自然拥有属于共同体的全部权力,他们就可以随时运用全部权力来为社会制定法律,通过他们自己委派的官吏来执行那些法律,因此这种政府形式就是纯粹的民治政制;或者,如果把制定法律的权力交给少数精选的人和他们的嗣子或继承人,那么这就是寡头政制;或者,如果把这权力交给一个人,那么这就是君主政制;如果交给他和他的嗣子,这就是世袭君主制;如果交给他终身,在他死后,推定继承者的权力仍归于大多数人,这就是选任君主制。因此,依照这些形式,共同体可以就他们认为适当的,建立复合的和混合的政府形式。”[3]80-81可见,作者将共同体视为内涵丰富的政治学概念,无论哪一种政权设置形式,其实质都是共同体。但是,不同的立法主体和法律制度则使这些政治制度表现出根本性的差异。“如果立法权起初由大多数人交给一人或几人仅在其终身期内或一定限期内行使,然后把最高权力仍旧收回,那么,在权力重新归属他们时,共同体就可以把它重新交给他们所属意的人,从而组成一个新的政府形式,政府的形式以最高权力即立法权的隶属关系而定,既不可能设想由下级权力来任命上级,也不可能设想除了最高权力以外谁能制定法律,所以,制定法律的权归谁这一点就决定国家是什么形式。”[3]80-81从根本上讲,政治共同体的特征在君主国和共和国里都存在,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君主国和共和国的不同并不是共同体层面上的本质不同,只是制订法律的最高权力归属有差异。许多学者对于当时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政治共性及各自的差异等做过具体的分析。②See L.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Alfred A.Knopf,1979.学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即无论是怎样的城邦国家统治都不能违背共同体的基本政治要求。斯塔西指出,“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如同对博丹和斯宾诺莎一样,国家是公民体(Civic Body)的一种类型”[12]。在马基雅维里的心目中,像法国这样的君主威势很大的国家,其实也还是一个共同体。那里有完善的法治、政制、军事等,是政治共同体各种要素的强大铸成了法国的强大,而非一个君主的能力有多大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即马基雅维里在讨论君主国、共和国问题时,有时是从政治结构的特点出发进行比较说明、有时是从权力运作的角度比较得失的。就权力运作而言,马基雅维里更注重政治治理的效果,似乎马基雅维里并不计较政治共同体方面的国家结构问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马基雅维里不赞成独裁。在君主国里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等都不能随意被抛弃。他在《君主国》第3章“混合君主国”中特别提到了遵从先前君主国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逐渐达成一个共识,即马基雅维里是主张共和国政治体制的思想家。更具体地讲,马基雅维里政治理论的核心课题是如何运作城邦政治共同体的问题。马基雅维里一生所思考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城邦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基础和统治方式问题。为此,他在《李维史论》③还可以参见李维本人的著作。Livy,The Early History of Rome,BooksⅠ-Ⅴof The History of Rome from Its Foundation, Penguin Books, 2002; Livy, Rome and Italy,BooksⅥ-Ⅹof The History of Rome from Its Foundation,Penguin Books,1982.一书中特别研究了罗马共和国的权力人物,罗马共和国的国家机构设置,罗马共和国的权力制衡,罗马共和国的军事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社会运作机制,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综合协调方法,等等。马基雅维里共和政治体制理论中的几个核心课题包括公民自由、权力制衡等。其中,那个理想的罗马共和国的立国之本是保护公民的自由性[13]。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护这种自由,就必须按照权力牵制的理论设置相应的机构。例如,就有必要在共和国里设置一个能够充分表达公民意愿的议事机构,同时执政官秉公行事,贵族与平民的权力则处于相互制约之中。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任何出于一人之手的政府总会出问题。理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由君主、贵族和平民相互制约,并各自明确其政治权利与义务的政体[14]16-17,115,唯其如此,才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由法律确定的自由基础上所建立的政府[14]254-260。正如布克哈特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看到他如何地希望建立起一个温和的民主形式的共和国以为美狄奇家族之续。”[15]84而这个共和国应当是自由、法制的社会[15]84。对于上述政治体制的具体样式,马基雅维里曾举例说明,古代有斯巴达的勒库古斯(Lycurgus)政府等;近代则有法国政府等。马基雅维里对他同时代的法国政府赞不绝口,“法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组织得最好、统治得最好得王国之一。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看到法国国王的自由与安全赖以维持的优越的制度无数之多。其中主要的一个制度就是‘议会’及其权力。因为建立这个王国的人知道权力者的野心和他们的傲慢,认定有必要在他们的嘴上套上制动机来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因为君主知道人民由于惧怕贵族从而怨恨贵族,君主便设法使他们感到安全,但是,他又不想把这种事情作为君主特别照料的事情,于是,为着避免自己由于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同时为了避免由于袒护贵族而受到人民的物议,国王就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这个裁判机关可以弹劾贵族、维护平民,而用不着国王担负责任。对于国王和王国说来,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更审慎,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16]上述话语充分反映了马基雅维里政治理想的核心,也就是完全从政府的稳定与有效运行来考虑共和国的体制。
近现代西方国家制度的建设都是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协调推进的。公民是一个承担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成员。因此,成熟的公民意识会对国家的政治建设提出内在和合理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完善过程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过程,只有以公民为基础才谈得上所有的治理和国家稳定。与共和国相关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也是马基雅维里考虑的重点问题。根据马基雅维里在不同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公民的权利、公民的义务及其责任的彰显是其理想社会的重要特征,依此建立的共和国则是以公民的发展为基础的、能够充分体现整体功能的国家。同时,公民在国家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并由公民来做最后的断定。公民自由的实现除了与国家的自由相关外,还与法律的性质、运作有关。法是国家权力的基础[17]。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模棱两可,就会导致一个人的政治命运乃至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的损毁。所以,政治家应当一切从法律出发谈政治治理、谈公共的和个人的关系。一个君主,如果他还记得以前暴君统治的一切后果的话,那么他就会用法律来维系新的国家。当然,君主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只有在法律的前提下,才能既照顾到个人的利益,又兼顾共和国的利益[15]113。马基雅维里在分析佛罗伦萨的历史时已经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些。
马基雅维里对State的全面阐释使我们厘清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即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仍没有脱离古代就有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治理轨迹。在这个共同体内可以由君主来当政,可以由具有一定资质的公民群体来治理,也可以由贵族群体来治理。统治的内容可以有些变化,但政治共同体的政体形式却始终不变,从本质而言,State、Republic、Commonwealth 都是政治治理的共同体。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有许多思想家在其著作中涉及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内容。其后,法国启蒙思想家、美国建国前后的思想家等都有关于国家政治共同体方面的论著,其中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及国家代表公共意志的理论影响巨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等具体的国家政治实践都是上述理论的具体体现。这些已经成了学术界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建国历史就是一部共同体发生、发展、完善的政治史,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的自治奠定了美国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基础。①See Louis B.Wright,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1607-1763,Harper & Row,Publishers,1962.因此,美国的政治思想家在谈及State一词时都要特别强调其中的共同体内涵。①See J.Appleby and T.Ball,Jefferson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可见,西方政治思想家谈及State、Republic、Commonwealth之类政治共同体概念时都包含一些基本的要素,如尊重法律、各种要素之间的平衡等。在西方曾出现“君主专制”的情况,但这种君主专制只是共同体这一政治框架内的政治统治现象。例如,伊丽莎白的君主统治就是在英国中世纪长期形成的制衡政治结构中的统治现象,只不过伊丽莎白将共同体中的各个平衡因素掌控得更得心应手些。无论是古罗马的帝王还是近代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独裁,都违背了共同体的基本要求,独裁统治的最后命运就是垮台。我们用汉语“国家”一词去翻译、诠释那些概念时不要遗忘了其中的共同体的特性。总之,国家就是国家政治共同体。
四
这里就近代西方国家政治共同体做个总体的概括。第一层含义:国家是体现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政治共同体,涉及公民的身份认同,包括公民的国家身份认同、权利与义务认同等;②里森伯格曾从历史的角度梳理过西方传统中的公民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关系。See P.Riesenberg,Citizenship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2.但此书中更多的是一种学术史的梳理。涉及法治等问题。③凯尔森在《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一书的第2编“国家论”中谈到了国家与共同体、法律秩序等的关系问题。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层含义:国家是保障各种政治力量权势的政治共同体。第三层含义:国家是权力机构有效运作、发挥整体功能的政治共同体。
在不同历史时期,上述问题又比较复杂。到了近代,共同体中涉及的自由、民主等内容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起了各种讨论,主要体现在如何限定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在先原则”到卢梭的“公意理论”、黑格尔的“国家客观精神”理论[18],这些都存在着可能放大国家权力的危险。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着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各种权力机构职能如何与政治共同体个别权益相匹配的讨论。在一年一度的牛津大学政治讲座中,学人可以看到不同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④See B.Johnson,Freedom and Interpretation: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 1992,Basic Books,1993; S.Shute and S.Hurley,On Human Rights: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 1993,Basic Books,1993.在美国,罗尔斯的《正义论》与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等著作在此问题上甚至有过许多争论。罗尔斯在考虑正义原则的实现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每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一种合作体系,没有这种合作,所有人都不会有一种满意的生活,因此利益的划分就应当能够导致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们”[19]13。从这个假设出发,罗尔斯构筑了一个由权利发生、权利分配为环节的正义原则体系。那些运用机会较好、获利能力较强的人的权益会受到国家的干预。这种干预不是国家命令富者拿出一些钱来给贫者,而是国家在安排整体财富时向那些运用机会较差、获利能力较弱的人做出某种倾斜政策,以求得平等原则的补偿[19]95-96。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倾斜”和“补偿”是否是以侵犯政治共同体的另一部分人权益为代价的呢?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评就是以上述问题为核心展开的。诺齐克的价值政治哲学出发点与罗尔斯的正好相反。诺齐克强调个体性原则。诺齐克指出,“对行为的边际约束反映了其根本的康德式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他们若非自愿,不能够被牺牲或被使用来达到其他的目的。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20]39因此国家在未征得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实行某种“倾斜”政策和“补偿”措施必然会侵犯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诺齐克竭力批评罗尔斯的国家超强性治理功能学说,认为这势必会侵犯到天赋人权,等于将人当作手段而不是当作目的看待。诺齐克倡导一种“最弱意义的国家”,即“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守夜人似的国家,其功能仅限于保护它所有的公民免遭暴力、偷窃、欺骗之害,并强制实行契约等,这种国家看来是再分配的。我们至少能设想一种介于私人保护社团体制与守夜人式国家之间的社会安排”[20]35。诺齐克这种“最弱意义的国家”的设想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似乎有这样一种国家治理功能,其效果正好使绝对的个人权利得到了保护。其实,罗尔斯与诺齐克争论的关键就是国家权力的运用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罗尔斯必须说明:与政治共同体相关的个人权利究竟有哪些基本内容?而诺齐克必须说明:个人的权利是不是绝对个体化的?这种争论其实就是国家政治共同体引发的问题。
总之,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实践的具体过程都需要首先弄清楚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实质。我们又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之。以近代西方的社会历史为例,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还是与近代城市兴起相关的法国、英国等,都有一个城市市民社会的发育过程。在近代美国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更典型地体现出底层市民社会自治的发展、完善过程。因此,西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理论说到底是一种历史现象。
[1] R.Baxter,A Holy Commonweal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 J.Hale,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New York:Atheneum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4,ChapterⅨ.
[3] 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4] 奥本海:《论国家》,沈蕴芳、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页。
[5] The Dialogues of Plato,Vol.3,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2.
[6]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9页。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8]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9] 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10]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1] 但丁:《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 18-36页。
[12] 斯塔西:《马基雅维利的自由国家与不自由国家》,《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4期,第76页。
[13] V.B.Sullivan,Machiavelli’s Three Romes:Religion,Human Liberty,and Politics Reformed,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p.4.
[14] Machiavelli,The Discourses,C.E.Detmold,tr.,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9.
[15]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6]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0-91页。
[17] A.Bonade,Corruption,Conflict,and Power in the Works and Time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105.
[18]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4页。
[19]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0]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