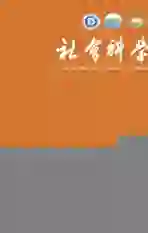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
2018-02-12沈洁
沈洁
摘 要: 科举停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性大事件;而肇兴于晚清上海的书业革命,引发了印刷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促成了思想与商业、启蒙与生意的多元复杂互动。学制改革与印刷业的根本转型,这两个事件交逢在近代“中”“西”“新”“旧”世道迁折的时局中,两者并非引发与被引发的单一因果关系。技术与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是真正将这些思想变局实现并固定下来的本质性力量。书业革命,正是这样的一个“枢机”——承载了、呈现出思想与市场、制度与技术变迁之间繁复而又具体的轨迹。
关键词: 废科举;晚清;印刷革命;书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12-0130-16
科举停废是晚清中国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性大事件,学界相关研究已很多。与废科及近代新学问题相关联,对晚清出版、印刷业的研究也很多。但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制度改革、技术革命与文化转型的互动中,讨论科举制度与书业革命关系的,尚鲜见。关于石印业,历来的研究都强调废科举导致石印衰落乃至终结,但废科与书业变迁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其中的多重原因,尚无有力论证。另外,从四堡、建阳到上海,出版中心的空间位移也不仅是一个出版史的问题,此前的成果基本停留在对出版机构、出版类目的具体研究层面,缺乏一种综合的整理与说明 ① 。
因此,本文着重讨论书业 与科举改章、停废的互动关系:废科事件怎样从政令、从教育取仕一隅扩散至社会,学制变迁如何与印刷、阅读乃至整个士林风习蟺变交互影响,旧书业如何在制度、技术与文化的综合作用下式微、更递,上海取代传统时代的印刷重镇,成为新式出版业的中心,空间位移中又包含许多繁复的经济因素。以书业为窗口,探讨此一时代之学术与公共舆论、书籍与市场、知识与生意,包括技术革命与知识形态变迁的贯连,这是思想史的另一种研究路径;主旨,则是在制度改革与技术革命的脉络中,整理、分析晚清中国的文化潮动,勾勒思想变动时代那些更细微和更本质的东西。
一、“印刷为之枢机”
印刷与教育的关系,是晚清时论中至为常见且一论再论的话题。1898年8月《申报》上有题为《论改试策论后士人家塾诵习课程》的论说:“今之势固急经济而缓词章也”,所以,除传统必读之书,古近名人论经济的文章亦不可不读;而《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之类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时务书,更应“次第阅识”,在家塾中或令初学者取报章分别句读,“以清纹理”。 经济文章成为圣贤文章之外的必读书目。士人更新阅读的需要成为转型出版业的内在动力。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中对晚清的革新运动与出版业的关系有过明确归纳:
我們现在谈到科举的废除,学校的创设,不能不归功于革新运动,而革新运动有此成绩,我们却又不能不归功于当时的出版业。
商务印书馆的庄俞也有类似说法:“戊戌变法之议兴,国人宣传刊物日繁,学校制度既定,复须新课本以资用,胥赖印刷为之枢机。”书籍是知识与思想的载体,而出版则成为启蒙与革新的重要媒介。“枢机”一词是精准的概括。新书业昌隆首先启之于朝廷改革科举的制度性变更,但另一方面,更多读书人投身于出版业,加上书商的配合,书业发挥的媒介作用为晚清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能并创造了基础。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以报刊阅读为例,据姚公鹤回忆,中国刚刚出现报纸的时候,每天发行之报,不过数百份,“社会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勖者”。报刊的阅读和传播还是很窄的,只是少数绅士、商人的消遣品。那时候的报纸发行主要就是集中在上海,少量的外埠订阅托信局邮寄,本埠则雇专人发送,有将报纸免费赠与商家,“然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饷之者”,送报之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 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可见,报刊阅读在彼时不惟不普及,尚且是等而下之的。1901年科举改革正式启动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学堂时代,学习声光化电,肄习师范、法政,并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从制度上为西学传播扫清障碍。如马叙伦所言,庚子丧乱后,国人盛谈新学,“诟旧学如寇仇,斥古书为陈腐” 。出版业亦因此而迎来更新良机,并在更新中快速走向繁荣。《时务报》经理汪康年说,自科场变后,来购者纷纷 。沪上各报也在改试策论以后开始大销:
当戊戌四、五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士子多自濯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侔利。盖巨剪之业,在今日用之办报以与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则名山事业且无过于剪报学问也。
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这固然是批评之论,但也说明,改试策论使得报刊成为应科考者必要的参考文本。《张棡日记》也记录了变法后书报销售大增的情形:
此次变法,与戊戌迥然不同。两宫一心,专心兴学,书院改学堂,科举重策论,翰林加甄别,宗室派游历,八旗官学变章程,八股永无再兴之日矣。京官稍有才学志趣者,争阅新书,将来衡文之选,皆出其中。沪上书报,销售之广,过于往年不止百倍。……若人自购报,家自置书,焉得有此力量?为体恤寒士计,于彼乎,于此乎,此事理之万万不可中止者也。
1901年《申报》上登载《振兴新学宜严杜邪说议》一文,政变后被视为“逆”的康、梁学说亦在报章间大行其道,成为书贾“射利”之工具:
明诏迭颁,此后科场一律废八股而试时务策论,一时各省书估争选,刊讲求时务之书,主持选政者学识未必兼长,且每以速成为贵,势不免拉杂敷衍,踳驳支离,就余所知,有将康逆所著《日本书目志》、梁逆所著《读西学书法》以及《时务报》、《湘学报》更易其名,翻印射利者,有将各报中或排斥康梁或阿附康梁诸论说,不顾以矛刺盾,贪多务得,并付石印,以冀风行者,阅者苟无成竹在胸,则欲求学问之翻新,或反被奇袤所蛊惑……
康梁学说虽被视为“奇袤”,却依然成为“欲求学问之翻新”的士子们争相阅读之选,时务策论成为科考内容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将《新民丛报》与康梁学说视为“科举利器”的说法不一而足。比如朱峙三日记中所载,《新民丛报》《中国魂》之类,已然成为20世纪初年一般士子们的“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 。王理孚也回忆说,“其时清廷科举未废,一般学子多携此册(指壬寅《新民丛报》——引者注)入场,藉以获隽者,不乏其人”。甚而有不读《新民丛报》何以通过入学考试的议论:
入学考验,将以察来考学生之程度果与已校相合否,以定去留者也。然今之入学考验,则异是。一似来考者无所不知,不妨苦以所难也者,英文算学,取则于人,笑柄尚鲜,国文一科,怪状百出,如某校高等小学科最近招考,题为“论钱荒之可贵”,又见有“自由必先自治说”、“论金贵之理由”、“性善说”等,均某某官立高等小学入学考验之题也。试问十二三岁之儿童,知钱荒金贵者有几人?而不读《新民丛报》又何从解自由自治之说哉?
有关晚清士人阅读《新民丛报》并受其影响、开始关心国是、寻求救亡的事例相当多,但或许都不如这则“入学考试”的议论来得直截,它告诉我们,梁任公和他的《新民丛报》是如何在实际意义上成为普及读物的。李剑农《中国近三百年政治史》中提及《清议报》《新民丛报》,也说到他们在改革后科举考试中的巨大影响力,称梁启超为“言论界的骄子”:
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從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
梁启超和他的《新民丛报》在改试策论后成为应试者“以为时务策论揣摩之资”的记载在清末民初的阅读、科考回忆中屡见不鲜。有些新式学堂还把《新民丛报》“学说”栏的一些文章列为教材 。《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成为这一时期国内畅销报纸,这自与其所传播的新词、新知、新思有莫大关系,也多多少少与科举制度的改革紧密相关。严复讲“任公笔下,殆有魔力”,这是思想史的角度,而从传播和阅读史的角度来看,像《新民丛报》这类新学书刊的巨大辐射力亦成就于晚清学制改革的现实机缘。柴萼《梵天庐丛录》记说:“梁氏之《新民丛报》,考生奉为秘册,务为新语,以动主司……学者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2-1033页。
风会迁流,新式书刊杂志开始成为士人的阅读日常。读报成为风气,这在报刊的数量上也可体现。在1898年以前,包括香港在内一共只有12种报纸,但到了1898年,已经有了至少35种日报,其中25种是在上海出版的。而在1902到1911年间,“中国,已发展成为一个有报纸读者的国家”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171-173页。 。新学书刊在晚清的兴起与兴盛当然由众多原因合力造就,但废八股、改策论则无疑发挥了至为关键的影响力。科举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时势,时势便又催生新的需要,而印刷,会逢其适。
190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图书有限公司,其《缘起》对于书业与教育之关系,亦有妥贴论述:
教育者,国民之基础也。书籍者,教育之所藉以转移者也。是以数千年之国体,传于经史,五洲各国进化之程度,佥视新书出版之多寡以为衡。今者科举废,学校兴,著译之业盛行,群起以赴教育之的。然而书籍之不注意,何也?书籍之组搆,由于编辑,由于印刷,由于发行,而后乃得流传于世,是编辑印刷发行者,所以组搆而成书籍者也。故编辑印刷发行之权在我,则组搆书籍之权在我,而教育之权亦在我。编辑印刷发行之权在人,则组搆书籍之权在人,而教育之权亦在人。……夫教育权之宜巩护,书籍之宜视为重要,编辑印刷发行事业之权之不可旁落。……早自为计,则上可以保国权,下可以免侵略,中国图书公司之所以发起者以此。
中国图书公司是清末废科举后由张謇主持集资开办的,它的教科书出版规模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对这些投身革新事业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而言,“启蒙”与“生意”的关系必须是殊途同归的。教育是国体之根柢,而印刷则为教育之基础。编辑、印刷、发行的事业,可以“保国权”,可以“免侵略”;这是较之于口号式的“文明”“进化”更为切要、更为实际的行动。印刷事业不同于一般逐利之场,是士人可以为更新教育、保护国权承担的责任,也是士人实现其启蒙理想最为关键的一种载体。吴稚晖民国元年为商务印书馆所出《新字典》撰写序言时,更将书商的事业奖誉为“营业之道德”:
营业者两利之事,职兼贸利与改良,二者完,即营业之道德也。西方商品之改良,月异而岁不同者,以单纯贸利之品物。扶持营业道德者所勿善,故不登于市场。然其得果,品物日良,而营业益利。皆道德最后之报偿。印刷业为文化之媒介,印刷之品改良,尤重于物物。商务馆愿以改良之品物,不计贸利之微薄,补助于文化。斯重营业之道德,以求营业之发达者欤?
吴稚晖说,书贾所从事的,乃是“名山著作之事”,不能以通常营业视之,也不应指其为单纯的取求报偿和获得劳务费。书业作为文化之媒介,是晚清中国启蒙与革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从新知的广泛传播到科举改革的最终实现,1901至1911年十年中间,印刷业的投入功不可没,这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制度、社会与政治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启蒙是如何传播的;在朝廷一纸政令之外,科举改革又是如何实现的。至此,印刷与教育便发生了切实的关联,是谓“书籍者,教育之所藉以转移者也”。
二、新书业肇兴
因改试策论,“新译西书,争睹为快”的时论在晚清更是常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在1901年以后才出现书局林立、书业繁盛的景象。
早在1898年,刚被任命为管学大臣的孙家鼐就说过“学堂教育人才,首以书籍为要”。孙诒让在这一年撰写的《〈中西普通书目表〉叙》也描述了改革科举后士人急需时务书的情形:
光绪戊戌秋,朝廷始更科举法,以策论易《四书》文,将以通识时务励天下士。于是乡曲俗儒昔所挟为秘册者,一切举废,则相与索诸市,求所谓时务书者。顾问以篇目某某,则愕眙不能应。黠估或示以断烂朝报,即大喜急持去。噫!讲时务而求之书册,所得几何,乃并所谓书册者亦不能举其名。科举之陋至是,其为世所垢病,不其宜乎?
戊戌年间,废除八股取士的政令在一夕之间颁下,埋首于孔孟之道的读书人不及反应,慌乱索求时务新书的情境跃然纸上。维新变法期间,江标督学湖南,命题课士“博古之外,兼取通今”,“三湘人士,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律本末》等新书就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也” 。而到1901年以后废除八股真正成为制度固定下来,西学新书的推广则更成为一时急务。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01年的《亚洲课本》广告中说:“泰西国势之强,由于人材之盛,人材之盛,实源于教法之良,彼新书日出,民智日开。顾为中土植人材,首在书之有善本,次在教之有善术。”赵惟熙《西学书目答问略例》中则将科举改革与西学盛行之间的关系表达得更为明确:
光绪二十七年诏变科举法,以中外史志、政艺各学试士,诸生鲜识西书门径,时来问业,不佞于中学应读诸书尚百不逮一,遑论鞮译之语、佉卢之文,顾修史余闲亦稍从事于涉猎,兹就所已知者仿南皮张孝达前辈《书目答问》之例,胪列西书诸目于篇,用谉来者。
《申报》1901年9月发表的《劝各郡县广购中西有用书籍以兴实学说》同样讲述了废除八股取士以后,士人为猎取功名而竞购中西新书的情景:
自废弃制艺之诏下,海内人士知朝廷敦崇实学,咸思研究经济,以收实效而宏远谟,而学究之为训蒙计者,亦知时文试帖不足以猎取功名,亟思改弦更张,别谋补救,于是竞购中西各书籍,为研摩玩索之资。……夫今之言培养人材者,动言开设学堂,然学堂之设,建讲舍、延教习、招生徒,其费非数万金不办,且寒素之士或须以教读为生者,即有学堂,亦未必能入内肄业,故事虽极美,而泽或难周。若筹款购书之事,苟得千金,即可办理,既可补学堂之不逮,即可免贫士之向隅,兴学之效固无有急于此矣。
《泰西新史》、《西学丛书》之类成为士人案头必备的举业参考书,而《时务统考》、《洋务经济统考》、《五大洲各国政治通考》之类,占到了西书出版比例的9.73% ,这些书几乎都是针对策论考试编制的。沪上各书局、书肆纷纷应景,印制此类新学书籍,比如相对传统的著易堂,光绪间共印书148种,其中有一半以上为铅印新学书籍;富强斋印书100种,几乎全部为时务新书。《申报》时务书广告中有言:“自科场改制之诏下,坊肆所出近人策论几于充栋汗牛。” 冯自由《革命逸史》载:“在辛丑、壬寅(1901至1902)两年为上海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盖其时留东学生翻译之风大盛,上海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新民丛报支店、镜今书局、国学社、东大陆图书局等各竞出新籍,如雨后之春笋。” 此外,《日知录》、《明夷待访录》、《通鉴》等史论书籍也因为改试策论而畅销起来。胡思敬《国闻备乘》中记:“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又废科举改学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三书盛行于世。” 章士钊说顾氏《日知录》的重获盛行,即与科考策论有极大关系:
顾氏《日知录》者固国闻中之良书也。数年前石印,书贾发行之数,不下十万,其所以然者,乃以其言蕴藉而且殚洽于试场之吞剥,与国中治国闻者之级数,毫无比较之关系。
而章太炎的《訄书》,章士钊认为其价值与顾氏之书不相上下,然而由于文义艰深,更重要的是与时务策论关系不大,因此不获流行。陆费逵也回忆,因为科举改革,要考史鉴策论,“于是《廿四史》《九通》《纲鉴》以及各种论说,又复盛行—时” 。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夫之《读通鉴论》和《历代通鉴辑览》,也在广告中称“二书于考试学堂需用皆急,特坊間并无佳本,士林憾之” 。据商务元老高凤池回忆,商务印书馆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书中,销路最好的即属《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二本四五集,《国学文编》,《亚洲读本》,《初学阶梯》(3),《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几种,其中《通鉴辑览》初版印一千本,立刻销完,再版一共销至万余部 。汤寿潜所辑《三通考辑要》也在科考改革之际为沪上书贾印行,并且销售甚广,章士钊称其为“不胫而走天下也” 。吕思勉《庚子日记》中提及汤氏《三通考辑要》,同样视其为科举骤变,“士子用为怀挟之书”。
众多的新学丛书更是书贾针对策论而编制的。比如“是编搜罗西学,择至切要者以备策问,博雅君子,庶有取材”(《西学大成》例言);“科场改式学堂,变制士子需西书研究,苦其浩无津涯”(《西学三通》例言)。有的丛书更直接在书名上便标明编书目的,如《新政应试必读》。
而沪上报刊中遍布的新书出版广告则更大程度展现了废八股、改策论对读书人阅读世界的影响。如《石印殿版直行二十四史全书出版广告》所称:
方今朝廷废八股讲实学,考求政治,学者非研究历史不为功。是以去秋各省乡场及□□会试题目一以史书为根柢,转明秋闱,又届多士讲学,必须平日渊博贯通,方足争于风帘,短曩之间,取青紫如拾芥也。本社不惜重资,印刷全史,早已出版,有志功名争购不遑,余书无多,购者原班带转,全史可立而待,非若徒托空言,出书无期。 《石印殿版直行二十四史全書出版广告》,《申报》1903年9月2日。
《新撰石印时务策论总纂初集》广告:
先生博古通今,无书不览,因见西学盛行,风气为之变,三场参用时务,已明降谕旨,考生临场对策,断不能枵腹从事,时务一书,实为当今所急需。爰即搜求各学堂、各书院时务制艺,分类纂辑,已竭数年之精力,详细校对,汇编成书,缩印精本,便于携带。计六十卷,订成二十四本,价洋六元。现因秋闱伊迩,一时不及赶办,先出书三十六卷,订十四本,价洋三元六角,俾诸君子得先睹为快,其余二十四卷随即续出,特先登报以告有心时务者,业已出书,各书坊皆有寄卖。 《新撰石印时务策论总纂初集》,《申报》1897年8月15日。
《出售新學汇编》广告:
今裒集论说纯载之属,凡足以振兴中国者,成新学汇编四卷,钦奉谕旨,废时文而试策论,是书适告成功,大可为先路之导。 《出售新学汇编》,《申报》1898年7月19日。
《芸缃阁书局发兑书籍西学大成》广告:
格致制造之学,主试者每以命题,今又奏准乡会两试第三场策问为选擢,观光者苦于门类纷繁,编简散列难稽,兹特将西学新译最要之本,网罗汇编,区为十二门,每门溯源探本,自算学、天文以及汽、电、光、声各学,绘图列编,无不详明备载,名曰西学大成。 《芸缃阁书局发兑书籍西学大成》,《申报》1898年3月11日。
上海是晚清出版业的中心地,时务新书的编译出版当然极盛;在上海以外的地区,同样受到废八股、改策论影响,刻印、翻印时务新书也成为一时风气。湖南是维新运动最早开展的省份,据统计,从1894年到1911年,湖南有书肆、书局163家,其中经营“新学书”的27家,官办、官绅合办的书局有3家,兼营出版与发行的书局有101家,编译社2家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出版》,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另参见郭平兴《近代早期(1840-1919)湖南图书出版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6页。 。1903年山西举人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应会试,在当地的书摊上发现“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在四川,时务新书原本很少见,然而,“自变法谕下,坊间辑刻蒙学新书甚夥,各坊以志古堂为最备,如王寅伯之启蒙歌五种等书,皆已出板。王君诸人现又集款四万购买印机铅字,广译新书以备开办学堂之用” 。在安庆,皖省风气晚开,士人每束时务书不观,而自改试以来,士人“均须从事于此”,因此考棚前各书铺生意异常拥挤,尤以四书经史策论销场为大 。在湖北,各书店也因科举改制而“销场固旺”,严译《天演论》《原富》等篇亦渐有购阅者。在扬州,“石印书坊只有三家,自废除八股后,人皆争购时务新书,近又岁试在即,买者愈众,以致石印书价值飞涨,该三书坊皆利市十倍云” 《商务:石印畅销》,《集成报》第18期,1901年10月。 。在铁岭有新开新华书局,“专卖学堂新书,获利什倍”。市场的变化反映的其实是需求的变化;1901以后时务新书的畅销正说明了科举改革对新书业产生的巨大影响。
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中的记录,1896年,市面上可读之西学书籍,总共不过三百余种,而短短几年之后,据《译书经眼录》作者顾光燮统计,仅1902-1904年间,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就达到533种。另以江楚编译局为例,其出版事业主要以译刻新书为主,《官书局书目汇编》统计,译刻新书60余种,占所刊行的全部70多种书籍的85% 。而在官书局以外,致力于译印西书的,除了商务这样的综合性出版机构,更出现了许多专门的译书团体和机构。比如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强学会改设的官书局等,较为著名的是1897年梁启超等维新同人集资,在上海创办的大同译书局。梁启超拟《大同译书叙例》:
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育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
翻译出版事业成为维新人士通往其政治抱负的重要途径。同一年,上海又有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的译书公会的设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气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 蔡元培尝言甲午士风,“朝士竞言西学”,至戊戌,他还与友人合力设立了东文学社,专门学读和文书 。1898年前后,上海又创办了多家新学书局,诸如,“以子史百家为经,以时务诸书为纬”的经济书局、以印行数理方面书籍为主的算学书局、出版“专言西国政治”《西政丛书》的慎记书庄,以及专售自然科学书籍的六先书局,等等。
进入20世纪以后,新的编译出版机构发展更快,主要还是集中在上海。盛宣怀也在1902年向朝廷上陈南洋公学翻译诸书时急呼:“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严复在《天演论》出版后给张元济的一封信里也说到,听闻南洋公学设译书院,张元济将安研其间,“不觉为之狂喜。大者则谓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喜提倡之有人” 。杜亚泉也说,当时的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 。编译西书事业自甲午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相当热度。在1901—1911年间,以“译”字为报刊或书社名称者,多达二三十种。有学者初步估算,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国至少有40家官办或私营出版机构从事西书译印工作。张晓灵《晚清西书的流行与西学的传播》一文中以飞鸿阁、纬文阁、十万卷楼、申昌书局、善斋书庄和宁波汲绠山庄六个书局为例,对晚清上海西书市场做了一些统计,在20世纪最初的一、二年间,出版的西书比例已经达到32.76%。即便是相对保守的十万卷楼,从《上海十万卷楼发兑石印西法算学洋务书目》和《上海十万卷楼发兑经史子集》两个书目的统计看,也出版了119种西书,占总数679种的17.52% 。可见,当时的西书出版已经略成规模,而且西书出版比例的不断提高是与其销售量的与日递增成正比的。以1902年广学会的新书销售量为例,“旨在广为译著有益书籍”的广学会在1893年出售书刊仅817本,次年即升为2286本,1896年为5899本,1897年为15455本,1898年高达18457本,1899年有20379本,1902年达到售书量的最高点,有48306本 。而其售书额,则在五年中“陡增二十倍不止”西学书籍销售量的增长与销售渠道的拓宽,与当时的士林风气密切相关。1931年李泽彰对三十五年来中国出版界的研究中,曾以海关洋纸输入的统计看晚清出版业的发展:自西学东渐,印刷方法也改用新式机器,以用洋纸印刷为原则;而洋纸的用途最大部分则是用于出版。中国虽已能仿造洋纸,但产量极低,因此,就洋纸的输入可以间接窥见出版业发达的状况。根据民国二十年出版的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入口货总值分类统计表”,洋纸输入在1903年为260余万两,至1906年增加二分之一,至1911年加到1倍以上,虽其间有数年比较以前1年或数年稍有减少,但大体上都是增加,并且增加得很快。九年间,平均每年购纸白银达从3796111.1两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新书业发达的概况。
时务新書大量出版,既成为商人的获利之源,也极大影响着读书人的科举之路;不仅更新其知识,亦改变其思想。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凭着这零星、混沌的新学知识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比如马叙伦的回忆:通过课外看《天演论》《法意》《黄书》《伯牙琴》《明夷待访录》等书,其考试文体也“大变了色彩”。黄炎培则更是因为早先接触西学,而在1902年的江南乡试中“榜上有名”。这一年的江南乡试,出题“如何收回治外法权?”,黄炎培因为读过《万国公法》,因此说了一些一般人不尽能正确分析的道理,就在这上边“得了便宜”。他说这一科乡试,一同赴考的南洋公学同学,共中选十二人,全部都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优越条件”:在公学阅读西书,学习策论,经过了一年半的锻炼,比起一般整天在八股文中打转的儒生,当然没有什么困难 。对士子而言,时务新书是启蒙,是应对科举的利器;而对坊肆书贾而言,时务新书则是生意,是射利之具。于是,启蒙成了生意,生意又反过来推动启蒙。1901年的废八股、改策论遂成为晚清新书业肇兴的重要推力。
三、旧书业的式微
“新”与“旧”、“现代”与“传统”消长起伏,是晚清中国的“大历史”。实则,也是一个学术史、思想史与印刷史上的通例。日本明治维新之际,亦颇有“欲废汉学”时风。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藏书”一诗“铁壁能逃劫火烧,金绳几缚锦囊苞。彩鸾诗韵公羊传,颇有唐人手笔钞。”注云:“变法之初,唾弃汉学,以为无用,争出以易货,连樯捆载,贩之羊城。”杨守敬1880年赴日访书,亦曾见闻:“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他还忆及数年前,一蔡姓书贩,一次性就从日本贩了一船的宋、元珍藉到宜昌。同样是“维新”,同样就是弃旧从新、全面拥抱西方,明治日本汉书古籍的遭际几乎是中国的提前预演。
书业变迁,首先便体现在旧籍市场的日益萎缩。
甲午特别是庚子以后,中国开始“弃旧如屣”,全面趋新。有关国人尊新学、“弃国学若弁髦”的议论不绝如缕。若章士钊感叹的:“今之业新学者,竟敢诋国学为当废绝”;“今也不然,科举废矣,代科举而兴者新学也。新学者,亦利禄之途也,而其名为高”;“夫科举时代,昌明绝学犹较易,新学溃裂时代,而含种种混杂之原因,而国学必至于不兴,则亡中国者必新学也” 。邓实所说:“自外域之学输入,举世风靡,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而无用。” 亦为俞樾所沉恸的:
今士大夫读孔子之书,而孜孜讲求者则在外国之学。京师首善之地,建立馆舍号召生徒,甚至选吾国之秀民至海外而受业焉。岂中国礼乐诗书不足为学乎?海外之书,译行于中国者日以益增,推论微妙,创造新奇,诚若可谓可喜,而视孔子之书反觉平淡而无奇闻。彼中人或讥孔子守旧而不能出新法,如此议论,汉唐以来未之前闻,风流会迁,不知其所既积,故曰孔子之道将废也!
连喜读新书的孙宝瑄也曾感慨过:
谈新旧不论是非,今日浮浪子一大弊也。夫是非之所在,公理之所在也。无是非,则无公理;既无公理,则此世界成何世界?我辈所以痛心疾首于今之世界者,谓其有势利而无公理也。讲明公理,尚不足敌势利之焰,况不论公理乎!
如果说,西学与中学尚为不同类型之判分,那么新学与旧学实际上已经包含明显价值判断。而在晚清,如孙宝瑄所说,已不再讲求是非,而惟以新/旧作为决断标准。“庠序中人均以拘守帖括为耻”,读西书、新书不仅是科举改革过程中读书人的进身之阶,更成为一种“高”的、符合“公理”的文化选择。鲁迅1908年发表《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对学术思想上的新旧转移已经有过深刻洞见,他把此时中国人对旧学的批判称之为随“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 ;“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谬而图富强也” 。
这一变化趋势具体反映到书业,就是“故书旧籍”,已经“无人留心” 。
梁玉泉研究了1898年到1901年四年间《申报》的书籍广告,这四年,是戊戌变法失败到新政改革开始的中间,新学经戊戌启蒙已有所传播,但由于科举改革尚未真正实现,时务新书只为少数趋新者所求。因此,旧学书籍的广告在比例上仍略高于新学。但是从统计中却可以看到,旧学书籍的出版呈现逐年下降态势:这四年总共2043个书籍广告中,属旧学书籍的1036个。其中,1898年376个,占56.2%;1899年280个;占52.93%;1900年162个,占50.31%;1901年218个,占41.68%。 旧籍市场处在日益萎缩当中。
经书大减,时务大兴:“自学堂以兴,教科书为重,四书不读矣,五经不讲矣,六经弃若弁毛,十三经束诸高阁。” 汪大燮感喟,所刊书籍皆为旧学,“出售不易,祗能送人耳” 。即便是在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以后,将国学旧典完全抛弃的说法也是夸张,但儒学读物销路大减,则确是事实。1903年《国民日日报》上刊登《进士之倒运》一则,讲述了一个不察时势的陋儒,贩卖旧书而大赔本的故事:
杭城进士王某不知何处集得多金,开一元记书坊于青云街,所售皆腐败不堪之书,王自负以进士之声望作市侩之生涯,自必利市十倍,乃场事毕后结算诸帐,则得失不敷,不得已克扣诸寄书代售之钱,倾入私囊,现为人查悉,争闹不止,可谓之进士倒运矣。
故事真假如何已不可考,但至少也说明了一种时势,以及在此时势中报人对此“腐败不堪之书”的嘲讽。1909年,《申报》上有《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一文:
凡原有之私塾固无论矣,间尝与各地老书肆中人过从相谈,询其旧书之销路如何,彼等尝曰,自有学堂,《论语》、《孟子》诸书销路大减,至停罢科举后,其减益甚,一二年前稍稍增多,年来已复其旧矣。
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改革对于旧籍市场的打击,几乎是倾覆性的。市场天然善于审时度势,考试内容变更促发书商们出版方向的转移:由课艺书到史书策论,再到时务新书;国学诸书因其不再适应考试制度逐渐被淘汰,有人感叹说,士夫汲汲谈新学倡学堂,“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南中开通早,士多习于舍己从人之便利,日为卤莽浮剽之词填塞耳目,欲求一国初以前之书于市肆,几几不可得”。鲁迅也曾经说过:“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
这是指内容上的新旧淘汰。而书业变迁,更关键的还在于机器印刷正式取代传统的手工雕版印刷业,中国亦就此进入印刷资本主义的时代。雷启立指出:雕版、石印、铅印等不同的印刷技术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面对的读者主体是不同的,因为印刷速度、价格成本等不同使得同为纸质印刷媒介生产出了不同的传播方式和读者市场,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各有偏向,生产和消费的目的也很不同;由于有了印刷技术和读者市场的支撑,媒介技术变革有力量改变原有社会文化的价值结构,从而直接导致了新文化状态的形成
这段话,概括了技术革命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同样也是芮哲非在《谷腾堡在上海》一书中着力论证的。由此可见,印刷,以及科举、新教育制度、新的文化形态,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与整个社会结构息息相关的一个环节,各自以辐射性的力量发散其功能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个领域,互相作用,互相影响。
发生在晚清上海的书业革命,既有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性因素,也有印刷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就技术而言,铅印术实则早于石印传入中国,但它并没有普及开来。原因在于,西方活字铅印技术的中国化过程十分困难,中文活字铸造不便,对于机器及成本的要求也较高,所以,反倒是后传入的石印更快占领市场。石印技术在1832年传入中国,而直到1880年代石印书坊才在上海广泛建立,从甲午到1905年,是石版印刷业最兴盛的时期。石印因其印刷速度及印刷数量、质量上的优势,迅速取代雕版印刷。
1880年代出版界的“石印热”,是由科举改革和译、阅新学的双重原因带动的。由于石印技术简便易行,印书往往能获巨利,一时书商纷起仿效。1889年《北华捷报》刊《石印书业之发展》一文,大体介绍了石印书业在上海的兴起过程:
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各地零售书店的增多,可以看出大家需要这种书籍。《康熙字典》售价各种版本不同,自一元六角至三元,字很小,木版大字的售价自三元至十五元。购买石印本的人,大半是赶考的举子,年青目力好,他们不要宽边大宇,而喜欢旅行便于携带的小书,举子们需要赶路,又喜欢带书。上海石印书局大量批发,供给远方省份,北京琉璃厂也设有分店,尤其是在四川商业中心地重庆,其他各城市也有分店,如广州等。但印刷中心地则在上海。上海是最早采用铅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机印刷的地方。
同光年间的石印书坊,大都以印行课艺书为主要业务。石印业相对于雕版印刷,有许多优势。雕版书字不能太小,而字大,书就贵,照相石印可 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石印技术印刷周期短、印量大、成本低,能满足印刷时艺课本量大利厚的要求。石印制版容易:“大抵刻版粗笨,成书不易,而刻工嘉者殊鲜。坊间刻本字迹类多模糊,且一书之版多至叠床架屋。读者、藏版者往往苦之。然有(石)版则可随时刷印,不计多寡,非其利欤?活版则排印甚速,字迹清明,价值又廉,流传甚广。” 更重要的,石印非常高效,“印速甚快”、“制作甚奇”,比如文明书局,机器全部开足运营,每日能印书20余万页。印刷革命使得从前那些不便流传、少量流传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在市场。早期,石印业的主要业务就是课艺书,印刷诸如《康熙字典》、《策学备纂》等士子应试书籍,由于印刷便捷,并且能印刷袖珍本,携带方便,“石印术翻印之古本,文字原形,不爽毫厘,书版尺寸又可随意缩小,蝇头小字,笔划清楚,在科举时代,颇得考生之欢迎”,更有不少应试考生借以作挟带之用。一时需求量大增,而石印书局也因此获利甚丰,并愈发引起聚合效应,光绪年间,上海的石印书局超过八十家。周越然也记录过这种场屋用书:“当清末科举时代,书肆中有所谓铜板四书者,高约三寸,广约二寸,可谓书本之至小者矣。此种书专为场屋之用,字小如蚁,不用显微镜,不能读其正文或注释。” 而且,石印成本也较木刻便宜许多。姚公鹤《上海闲话》中记点石斋《康熙字典》盛况:“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而罄。书业见获利之巨且易,于是宁人则有拜石山房之开设,粤人则有同文书局之开设,三家鼎足,垄断一时,诚开风气之先者也。”
据韩琦、王扬宗等人的研究,石印业在兴盛期内出版的读物,还包括经史子集、书画地图、报章杂志、西方科技、政教、史地等,对传播西学新识和维新思想作过很大贡献,甲午战后兴起的新学丛书热潮,主要就是由石印书业推动的。但它的出版大宗仍是科举读物。同文书局在1885年所印的《加批四书味根录》每部洋贰圆,获利十倍乃至二十倍之多,1885年的石印书目中,所列石印古籍除《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以外,共计60种:其中如《各省课艺汇海》之类的石印本32种,亦占总印量一半之多。扫叶山房在光绪年间印行的书籍主要都是时文制艺类书籍,所印103种石印古籍中,诸如,《四书院课艺》《紫阳课艺》《清朝文录》《直省乡墨》之类的书籍共55种,占总量的一半以上。1885年9月,《申報》上还刊登了扫叶山房迎考市在内地设分店的广告:“今当大比之年,除江浙两省届时往设(临时分店)外,湖北武昌亦往(设)分店。” 课艺类书籍的畅销程度可见一斑。而1905年前印制的《上海鸿宝斋分局发兑各种石印书籍》书目显示,经部、史部及时文类、诗赋类、试策类,与科考相关的书籍达到半数以上。
所以说,虽然也有印制新学丛书的业务,但石印书局最主要的营业还是与科举考试相关的。陆费逵回忆上海石印业“印书多而营业盛”,因为科举时代携带便利的缘故:
平时生意不多。大家都注意“赶考”:即某省乡试某府院考时,各书贾赶去做临时商店,做两三个月生意。应考的人不必说了,当然多少要买点书;就是不应考的人,因为平时买书不易,也趁此时买点书。——夏清贻著《金陵卖书记》即记赶考情形,形容书贾及赶考士子淋漓尽致。——到考期完了,各店要收歇而去时,颇有便宜书可买,比新出时竟有差至一倍以上的。
这一时期石印书业的营业额,据陆费逵估算大概能达到每年一二百万元。然而到了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石印书局只能转向翻印和影印古籍,在“新学猖狂”的年代里,业务自然江河日下。随沪上商务、文明等大型新式出版机构的设立,石印书局更是越来越无法适应市场,绝大部分都以倒闭收场。陆费逵总结中国近代六十年以来的出版业与印刷业,谈到石印书局的衰落,主要原因就是废除科举,考市消失:
三十年前,清朝废科举,于是石印书一落千丈。考试的书,原售一二元的,此时一二角也无人要。大的石印书庄因考试书的倒霉,都关门了,只剩几家专印古书或小说的小石印书坊了。
1918年扫叶山房编辑石印精本书籍目录,序言中对晚清以降石印书业的萌芽与中衰都作了回顾:
自泰西摄影术入中国,而印书开一新纪元。维时风气初开,疑信参半。信者喜其成书之速且精美异常也;疑者虑其不能传久,纸墨或易渝也。故四五十年前出板之书,大都密行细字,便场屋舟车之用,善本精印十不得其一二焉。其时官私刊本流布颇广,石印书亦实不能于其中分一席。此所谓萌芽时代也。科举即废,新政聿兴,革装书籍,挟新思潮以输入,活板印刷盛极一时。故籍陈编,束諸高阁,而石印书亦受影响。此其中衰时代也。
可以看到,石印时代的结束与课艺书的衰落是同时而来的。晚清的石印书局大都集中在上海一地,所以因科举改革而衰落的书局、书坊也同样主要在上海。像点石斋书局,总在科举考试前印刷出版投考士子所必读的科艺书,销路特别好,科考废除以后,这些书籍则根本无利可图了。时人言,时文废弃,则“坊间所刊所印之《大题》《小题》《文府》《文海》《文选》《文抄》皆一概顿成弃物矣。此等书册,浩如烟海,何止汗牛充栋,珍而宝之者多年,摒而弃之者一旦” 。
鸿文书局的失败则是废科后出版业新旧轮替的最典型示例。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中记鸿文书局兴衰的历史:
开设鸿文书局者,为江苏震泽人凌陛卿孝廉,家世丝商,资本雄厚,与点石、同文等局并驾齐驱。惟所出者多科举时代考场所用之书,如《五经戛造》、《五经汇解》、《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等类,不下数百种,当时非不风行,士子辄手一编,迨科举既废,不值一钱。民国初立,亦尝集合名士编成初小教科书数种,而资本短缺,推广无术,巧妇无米自难为炊,刊行之书终亦束诸高阁而已。
正是因为“大宗以科举书为多”,其“失败之基即由于此”,鸿文书局未能跟随潮流及时转型,以至一路衰落最终倒闭,“前功至是尽弃”。成立于1887年的蜚音馆同此命运。蜚音馆由扬州人李盛铎创办,也是晚清有名的石印书局,业务规模相当大,蜚音馆利用石印可放大缩小的技术,专门印制一种小开本的适应科场考生携带方便的“巾箱本”书籍,当时称这种书为“场屋夹袋书籍”,深受科举考生的欢迎。废科举后,业务蒙受巨大打击,损失很重,不久歇业 。
在中心地上海以外,也可以看到废科举对传统书业的巨大影响。最典型的,便是传统时代的书业重心之一——福建四堡。包筠雅指出,对四堡的雕版印刷业衰退造成最猛烈打击的,即是废除科考。四堡的书籍贸易在盛时的18、19世纪,“经生应用典籍以及课艺应试之文”,包括四书、四书集注、五经、各类课艺书、时文指南、童蒙读物始终是其出版大宗。但科举改革及其废止使得四堡的主要出版物变得毫无价值。教育体制改革和新课本的引入,被更高效、机械化的上海出版社垄断,大大降低了四堡库存的那些突然显得过时的蒙书的价值。雕版不能像活字印刷的模板那样分解,然后重新组合,以适应新的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的要求,也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新的阅读大众的需求。因此,在新的环境下,曾经盛极一时的四堡雕版印刷业自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经历了持续的萎缩和它最后的衰落。
再如江南官书局,辛丑以后归入江楚编译局兼管,丁未年淮南书局也归入江楚,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新学萌芽,视旧藉无足轻重,故以印售旧书之事,归入译著新书之局” 。湖北官书局命运相同,1908年,因为新学盛行,生意大为减色,总办以下各委员又坐食薪俸,月须赔款一千元。官书局业务难以为继,因此入禀鄂督请求停办。后来由绅士李绍棻等人承办,官书局改为商办 。四川的传统书业也深受晚清新学浪潮的影响。近代前期的木版书业,因紧密为科举制度服务,当时多印行经史典籍以及注疏考证一类书籍;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营业日衰,加上铅印书业的出现,相比之下成本过高,故无法生存而纷纷倒闭。如四川沪州宏道堂开设于康熙年间,自设印刷作坊,道光初年在成渝,道光三十年在宜宾、乐山先后设置分庄,后来还利用长江水运之便,在宜宾、汉口、南京、上海等地开设分庄,成为集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大型木刻书坊。民国初年,业务渐渐萧条,各分庄纷纷倒闭。南京的木刻书坊李光明庄书坊,以印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读物著称,也印行了不少经史子集。据它所刻《书经》刊叶目录所载,共刻印167种书籍,计经部41种,史部6种,子部3种,集部52种,启蒙读物24种,其他41种,颇具规模。它除在南京三山街大功坊秦状元巷设有总号外,并在状元境口状元阁开设分号。后来也因废科举,推行学校教育,采用新编教科书,而不能跟上形势逐渐被淘汰。
书籍的制作者受到影响,售卖者同样受到影响。1907年《盛京时报》载铁岭一兴源德书铺,“今虽设立学堂,彼仍卖《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合讲》《五经备旨》《八铭》《七家诗》等书,终日无过局者。”与此相对的,西门内新开新华书局,专卖学堂新书,则“获利什倍” 。随着改革课本、编译新的适合于学堂教育的教科书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课艺书正式退出市场。随同课艺书消亡,亦见国学旧籍日益衰微。北京的琉璃厂书肆可视为典型。雷瑨《嬾窝笔记·纪京城书肆之沿革》中记:
至光绪甲午以后,朝廷锐意变法,谭新学者,都喜流览欧西译本;彼时新会梁启超氏有西学书目表之辑,学者咸按表以求。而京师书贾亦向沪渎捆载新籍以来;海王村各书肆,凡译本之书无不盈箱插架,思得善价而沽。其善本旧书,除一二朝士好古者稍稍购置外,余几无人过问。此亦厂甸书肆变迁之大略也。
进入民国以后,琉璃厂的古籍更加乏人问津,“向售旧书各肆,叹息咨嗟,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张锐涵《琉璃厂沿革考》记厂甸书业,自乾嘉以来多为江西人经营,相传最初有一江西人赴京会试,未中,便索性在京城呆下来于厂甸设肆贩书,自撰八股文、试帖试,镌版印刷出售。后来者以同乡关系,颇有仿此而行者,年深日久,形成为集团。到清末废科举,琉璃厂的江西帮也就在无形中取消了。瞿兑之讲述厂甸旧事:
琉璃厂的铺家有两三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旧日卖缙绅,卖闱墨,替新科翰林卖字、替会试举子制办书籍、文具的。这种铺家一自科举废而帝国亡,于是改为贩卖教育用品,于是变成一种不新不旧、不伦不类的奇异现象。
有竹枝词《琉璃厂》,慨叹厂肆式微、国粹罄尽:
大雅于今已式微,海王村店古书稀。
如何碧眼黄须客,卷尽元明板本归。
这既构成思想史上的“权势转移”,同样也昭示了制度改革、技术革命与思想变迁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石印衰落虽与科举有莫大关系,但并不是唯一关系。因为,即便在考市消亡的情况下,石印在图像、新闻等领域仍然占据重要的市场份额,并且还进一步在图像生产上拓宽市。
除了新闻和图像生产,石印业在古籍出版领域也还存在一定的活力。叶德辉《书林余话》中,附有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说〈四部丛刊〉》,论及虽科举废、编译新著,但石印翻印旧书一风仍然兴盛:
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当时多密行细字之书,只便考试携带,不甚翻印善本。清亡,科举全废,编译新著,都用活版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書肆出石印书甚夥,翻印旧书之风气亦渐盛。于是一时不易得之书,亦得取求如志。而商务印书馆所印之《四部丛刊》,尤有价值。
实则,在石印业兴起的早期阶段,这个格局已经存在:既印行了大量课艺书,科举、策论参考书,西技、西艺、西政等新学书籍,也因其可以实现“精准复制”的技术优势而翻印了许多古籍。石印业在保存古籍与传播新知方面,均起过作用。
进一步讲,印刷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引入中国,恰逢萌发新思想、实施科举改革的这一时代,所以,造成了一种科举改制导致石印衰亡的表面逻辑。但其实,不管是石印取代雕版,还是铅印取代石印,与废科事件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废除科举的制度改革与印刷技术革新之间的关系,不可被绝对化;更确切的说,是科举改革为印刷业变迁带来了一种新的机遇。翻印兔园册子与译印新学丛书,均为书业市场对考试经济的迎合。
造成石印衰落的真正原因,首先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石板笨重,搬运不便,在印刷机上的运动速度慢而且只能平铺往返运动;同样由于石板的笨重,石印从根本上制约了印刷的尺幅(巨大的石头无法操作);印刷压力控制不好,印刷质量不稳定;印版附于石板,难以保存。此外,石印需要的印机、石材、油墨,成本消耗很大,没有相对大而稳定的市场是很难维持的 。这就解释了,考市消失,以科举读物为大宗的石印业必须面临转型;而与此同时,市场萎缩,行业转型必须的成本却无从而来,式微也就成为了一种合理的逻辑。
自身局限之外,则是印刷技术的改良和新技术的应用,这最终导致了石印业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需求,遭遇淘汰。当汉字活字的铸造难题被攻克之后,铅印技术得到了相关机械、动力等各方面的技术支持,并依据汉字特点不断改良,在之后的机械化大规模印刷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印刷能力也极大提升。随印刷机器的更新换代,与其配套的其他印刷材料、印刷用具也相应变迁。以纸张为例,中国的手工纸无法跟上印刷新技术步伐,相应的,进口机制纸价格却一再下降,开始代替原先的连史纸成为印刷首选。机制纸的盛行,又带动了书籍装帧的变化。而在1900年代,亦正起留日风潮,日文汉译新书取代西学新学译书,留日学生在译著、印刷、出版方面的积极推介和活动也加快了洋装书在中国的流行 。
再从空间来讲。1890年代之后,中国的出版中心发生了非常大的位移,明清时代的几大书业中心,诸如江南,福建的四堡、建阳,均迅速衰落,上海取代他们,成为晚清以降中国唯一的出版中心。整个出版业空间格局的位移,这是一个更加复杂、宏大的命题。为什么会汇聚到上海?上海是晚清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所以它可以先于其他地方引进并拥有新的印刷技术。上文已经论述过,印刷技术革命,不同的技术时段所使用的纸张亦不同,连史纸淘汰后,印刷纸张越来越依赖进口,而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口岸城市,这同样促进了印刷产业向上海的集中。与之相关,四堡、建阳之所以是传统的印刷中心,与他们靠近纸张原材料产地紧密相关,而随着印刷用纸的变迁,这些靠近旧的原材料产地的书业中心,也自然衰落下去。
晚清民初,石印取代雕版,进而石印时代结束、石印为铅印取代,是一个合力作用的结果。此亦正如废科与印刷,其间有此伏彼起、新旧消长,但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制度、技术、思想与社会,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运行,终而共同造就一种结果、一种时局。
学制改革与印刷业的根本转型,这两个事件交逢在晚清中国“中”“西”“新”“旧”世道迁折的时局中,两者并非引发与被引发的单一因果关系。在所谓“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的朝局之变与人心之变中,技术与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其实是真正将这些思想变局实现并固定下来的本质性力量。这正是本文通过具体论说,想要重建的一种多面的历史,以及其间的因由与经过情形;将思想史研究实体化,将我们所习惯的新、旧替换认知“去熟悉化”。书业,或许正是这样的一个“枢机”——承载了、呈现出思想与市场、制度与技术变迁之间繁复而又具体的轨迹。
The Reforms and Abolishment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Book Industry Revolu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Shen Jie
Abstract: The aboli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is a watershed eve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hile the book industry revolution which sprang up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Shanghai, had resulted in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print capitalism” and the multiple and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hought and commerce, and enlightenment and busin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form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ting industry, meeting in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new” and the “old”, was not just cause-and-effect.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patial pattern are the essential forces which actually promoted and realized the thought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the Abolishment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Evolution of Book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