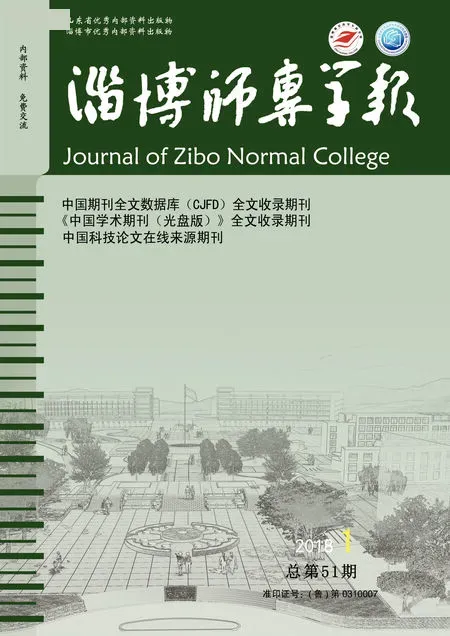论《诗经》中的亲情诗
2018-02-09曹芙蓉
曹芙蓉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诗经》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诗序》中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孔子在《论语·阳货》也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足以见出诗的教化作用。长期以来,研究《诗经》中爱情诗、农事诗、战争诗的有很多。尽管在中国古代的亲情诗品类繁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但目前有关于亲情诗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我们认为,亲情诗源于《诗经》而后不断发展。作为礼仪之邦、重视人伦道德的中国,自《诗经》开始就收录了大量描写亲情的诗歌。据统计,在《诗经》中就有三十多首描写亲情的诗歌,在这些作品中,大致可分为父母之情、夫妇之情、兄弟之情三种。《诗经》中的亲情诗主要分布在风诗和雅诗中。风诗是采集于民间下层民众之手,是当时当地的带有浓重地方色彩的歌曲,大多数是民歌;而雅诗则是上层贵族所作的诗歌。风诗中的亲情诗和雅诗中的亲情诗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一、父母之情
孝道是我国古代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基础,尊老、恤老文化则是封建家庭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下的积极产物。孟子认为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伦中,父子之情为首。在《诗经》中描写父母之情的诗,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描写因无法侍奉父母的悲伤与愧疚,第二类是对于父母亲情的思念。
《邶风·凯风》就描写了子女对于不能孝顺辛勤抚育自己的母亲而发起的自责之情: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母氏圣善,我令无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晛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第一章“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这句诗作者运用比的手法,描写出了长春万物的南风,抚育着多棘而又难长,却又十分稚弱且尚未长成的小木,尽管小木长得很好,母亲却已经病苦。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明诗人写此诗的目的,母亲虽有七个子女,却仍然不能安其室家。因此这七个子女写了这首诗,用凯风比喻母亲,孩子年幼之时比作棘心。盖曰母生众子,年幼时养育他们。母亲非常辛苦,本其始而言,这是孩子们做以自责的缘由。“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甚善,我令无人。”南风,吹拂着那多棘且难长,但心又稚嫩未长成的小木,母亲是那样的甚善,然而我们并没有尽到作为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前两章先是指出了母亲抚育自己的辛苦,后两章又表达了诗人因为不能侍奉自己的母亲,使母亲的生活劳苦,不能使得母心慰悦的自责。闻一多的《诗经通义》中指出:“名为慰母,实为谏父”,这是一首儿子歌颂母亲辛勤的养育之恩并且做以自责的诗。但是在《毛诗序》中提出:“《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气志尔。”《毛诗序》认为《邶风·凯风》这首诗仅仅是赞美孝子的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我们认为,这首诗的写作目的不仅仅只是赞美孝子,更多的是在描写面对母亲的无比圣善和无比艰辛的抚育、作为子女不能侍奉母亲而产生的自责之感。《凯风》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刻,现在我们经常用寒泉之思来表达子女对父母的思念以及感恩之情,用凯风来表达伟大无私的母爱,用寒泉来象征子女对母亲深切的思念。大文豪苏轼也有“凯风吹尽棘有薪”的诗句。古乐府《长歌行》诗歌中也写有:“远游使心思,游子恋所生,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鸣想追,咬咬弄好音。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其中用来象征伟大无私的母爱的意向皆出自于《凯风》之中。
在《孔丛子·记文》中记载道:“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小雅·蓼莪》: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糜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我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榖,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榖,我独不卒。
诗中把作为子女不能对父母行孝的遗憾与悲痛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刘沅在《诗经恒解》中评论道:“悱恻哀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与《蓼莪》皆千秋绝调。”第三章中连续的九个动词,把诗人不能使得父母终养的悲痛绝望的心情展现得一览无遗,感情更加饱满充沛。《毛诗序》中指出:“孝子不得终养尔”。朱熹《诗集传》也指出:“人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而作此诗”“言父母之恩如此,欲报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无穷,不知所以为报也”。清人方玉润称在《诗经原始》提到《蓼莪》为“千古孝思绝作”。诗歌的前两章作者深知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而感恩于父母对自己的抚养。诗人用重章叠句的手法,改动了上一节中的最后两个字,使整首诗感情更加充沛。“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我没有了父亲,还能依靠谁?没有了自己的母亲,我又能依靠谁呢?用问句的方式表达没有了父母的孩子将永远失去依托。在下一节中,感情的抒发可谓“千秋绝调”。《蓼莪》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我们用瓶罄罍耻这个成语来比喻不能使得父母终养,是作为子女的耻辱。用顾复之恩来比喻父母养育的恩德。“蓼莪”成为后世用来表达对父母悼念之情的常用意象,曹植的《灵芝篇》:“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唐代诗人牟融的两首诗中都运用了蓼莪这个意象。有《邵公母》:“伤心独有黄堂客,几度临风咏蓼莪。”另一首出自《翁母些》:“独有贤人崇孝义,伤心共咏蓼莪诗。”清代诗人杨贞《闻鸦喧忆亲抒怀》:“三复蓼莪诗,叹息欲废书。”用“蓼莪”的意象表达诗人们对于父母的感情,也源自于《诗经》。
在《诗经》中有很多类似于《凯风》和《蓼莪》这样的诗来描写对于父母的感情,《唐风·鸨羽》写儿子因在外服役而不能亲自侍奉自己的父母所感受到的痛苦与不安,《小雅·四牡》《周南·葛覃》这些作品都是上乘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并且《唐风·鸨羽》《小雅·四牧》这两首诗也可被认为是后世思亲诗的开山之作。
《诗经》中父母之情的第二类就是描写对于父母的思念之情,《魏风·陟岵》就是其中的一首。对于这首诗《毛诗序》的解释是:“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这首诗总共有三章,每章只改动数字,但抒发的感情却又似排山倒海般袭来,在行役中绝望无助的时候,诗人想到的是父母;他登上高岗向远处眺望,想到的还是自己的父母——父母的谆谆教导与暖心的关切全都浮现在脑海之中。此诗的反复咏叹更能震人心魄、感人肺腑,展现出了对亲情的殷切希望。
二﹑夫妻之情
在《诗经》中,描写夫妻之情的诗歌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诗歌类型就是描写夫妻婚后生活其乐融融的幸福场景,如《郑风·女曰鸡鸣》《王风·君子阳阳》,在傅斯年先生的《诗经讲义稿》中就这样写到“君子阳阳,室家和乐之诗”以及“女曰鸡鸣,此亦相悦者之词”。描写夫妻之情的第二类诗歌则是丈夫行役在外,在家的妻子思念丈夫所作的诗歌。这类诗歌在描写夫妻之情的诗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如《周南·汝坟》《王风·君子于役》《周南·草虫》《周南·殷其雷》《秦风·晨风》等,对于《汝坟》这首诗歌,傅斯年先生在他的《诗经讲义稿》中这样写道:“妇思其夫行役在外,未见时,‘惄如调饥’;‘既归’则曰‘不我遐弃’。卒章欢息时艰”,曰‘王室如毁’,则已是幽王丧乱后诗”。对于《草虫》这首诗,傅斯年这样解释:“女子思其丈夫行役在外,未见则忧,既归则悦,与《汝坟》同”。对于《君子于役》,这样解读:“丈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通过这些诗歌,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背景,战争频发,国家分崩离析,男子都要去征战,导致妻离子散。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导致了此类诗歌的出现。第三种我们认为应该属于弃妇诗。弃妇诗也是写夫妻之情,它不似前两种诗歌中描写夫妻之间真诚笃定的感情,而是从弃妇的角度出发来描写,来表现夫妻关系、夫妻相处中出现的问题。《卫风·氓》就是《诗经》中很著名的一首弃妇诗。当然,弃妇诗在《诗经》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小雅·我行其野》《郑风·遵大路》《小雅·谷风》《小雅·白华》都是弃妇诗中的名篇。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讲求夫妇有别,夫妻之间要遵守礼法的约束。长期以来夫妇之间厚重和深沉以及相敬如宾的感情和他们敬业乐群的生活态度,事实上则来源于中国人民淳厚勤劳的文化性格以及长久以来的男耕女织的生活理念。例如《郑风·女曰鸡鸣》就很好的验证了这一点: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闻一多在《风类诗钞》中提出:“《女曰鸡鸣》,乐新婚也。”闻一多认为《女曰鸡鸣》这首诗是在乐新婚,但我们认为,闻一多的这个观点并不能完全概括出这首诗总体表达的内容。在这首诗的第一章中,先是妻子和丈夫的对话,妻子催促丈夫起床去打猎,但是丈夫以“昧旦”为理由进行推脱。第二章中就描写男子涉猎、妻子烹调、妻子弹琴、丈夫鼓瑟的幸福场景。最后一章丈夫感受到妻子对自己是“来之”“顺之”“好之”而进行赠佩这一举动。我们认为这首诗是在赞美夫妇和谐的生活、诚笃的感情以及夫妇之间美好的人生心愿。朱熹《诗集传》中就指出:“射者,男子之事也;而中馈,妇人之职。故妇谓其夫:既得凫雁以归,则我当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饮酒相乐,期于偕老,而琴瑟在御者,亦莫不安静而和好,其和乐而淫,可见矣。”
但是,并非所有的感情都是如此和乐笃定且又美好。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战争对人民大众的影响是极为残酷和深刻的,它甚至会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男子出征,十去九不回,剩下的就只有女子在家无尽的思念,《诗经》中有很多首诗歌很好地描写出这个场景与感情,如《卫风·伯兮》。该诗深刻地描写出了思妇对于远征的丈夫深深地思念之情,表现出了该思妇对于丈夫感情的专一与忠贞。诗的第一句交代了整首诗的背景,写出了丈夫“为王前驱”而自己独守空房,在第二句诗人巧妙地用“首如飞蓬”,写出了思妇内心深处的失落与悲哀之感。“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丈夫都不在身边,“我”化妆给谁看呢?继而诗人又写道“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思念之情步步加深,可谓刻骨铭心。《卫风·伯兮》中思妇对于征夫思念之情的描写,在后世的诗歌中被广泛应用。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中写“起来人未梳头”,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徐干《室思诗》“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柳永《定风波》“终日恹恹倦梳裹”。这些都写出了思妇“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内心苦闷与惆怅,也体现出了思妇对征人的思念之情。当然“女为悦己者容”的观念也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民的心目之中。
与《卫风·伯兮》表达的感情相一致,《君子于役》这首诗也写出了思妇思念行役的征人,用情至深,感天动地。丈夫因为徭役而长久在外,他的妻子因为思念而发出了“不知其期,曷至哉”的感叹。这首诗中,诗人触景生情、见景怀人。“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体现出中国人“最难消遣是昏黄”的国民心理。“如之何勿思”发人肺腑、感人至深。“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融入诗人深深地祝愿,更可见情之深、思之切。而这种表现手法也被后来的历代文人所引用。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黄昏的时候,诗人触景生情,表达出了自己断肠人的悲苦之情。
《诗经》中描写夫妻之情的部分诗歌,以他们相濡以沫的情谊,不断影响着我们,也让我们从中领略到了上古家庭中夫妻生活的场景。而弃妇诗,则从另一种角度出发来写出我国夫妻的相处之道。这些诗歌大多都出自于女性之手,以写实的手法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女性形象。这类诗歌有着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从中我们也可以洞窥那些遭受欺辱的下层女性的不幸生活,也可以获悉当时的婚姻状况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弃妇诗的研究已经很多,本文对此不再进行详细论述。
三﹑兄弟之情
描写兄弟情深的诗歌也是属于《诗经》亲情诗的重要部分,《小雅·常棣》就是写兄弟亲情的诗篇。在《小雅·常棣》这首诗中,“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句属于整首诗点题之笔,既直接表达出了诗人对兄弟之情的赞颂,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人伦观念。钱钟书《管锥篇》中指出:“盖初民重‘血族’之遗意也。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则人伦耳;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家室之妇。”上古初民的部落家族,以血缘关系作为生存的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这首诗的主旨是至亲不如兄弟,在第二章中写了遭遇意外不测的事情,来表明真切的兄弟之情。三四章表达的也是相同的意思,遭遇急难时兄弟救助,遭遇外辱时兄弟齐心协力。更是运用了比较的手法,拿“兄弟”与“良朋”进行了对比,更能显出兄弟情深。第五章为此诗的一个转折点,自成一层意思,前四章中作者高扬理想中和乐的兄弟之情,第五章“丧乱既平”以后的兄弟“不如友生”,诗人有感而发,发出沉痛的叹息。六七章又转而接到第四章的意思上来,指出兄弟和乐的种种好处。最后一章卒张显志,意在告诫劝慰人们要牢记上面所说的道理,这样才能家庭幸福、妻子和乐。《常棣》对于后世文人的创作影响也极为深刻,“脊令”本是生活在原野中的一种水鸟,唐玄宗李隆基有《鹡鸰颂》。也有明代唐寅的《败荷鹡鸰图》来描写兄弟之情。吴潜写“去岁尚传鸿雁信,今年空念鹡鸰诗”,来思念远游的兄弟。孟浩然著有“共有脊令心”的诗句。杜甫也写有“浪传乌鹊喜,深负鹡鸰诗。”宋代诗人范成大更是写到:“把酒新年一笑非,脊令原上巧相违。”黄庭坚也在他的《和答元明黔南赠别》中也写到了:“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常(棠)棣”“脊令”已经被用来代指兄弟,并被历代文人广泛使用。
在《诗经》中还有一首诗歌是劝谏君王不要疏远兄弟的诗,就是《小雅·角弓》。这首诗以父兄的语气切直地表现出对于君王疏远兄弟而亲小人做法的不满,要求君王要以身作则,亲兄弟而远小人,这样人民群众才能效仿。《毛诗序》中写道:“《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而作诗也”。朱熹在《诗集传》中也写到:“此刺王不亲九族,而好谗佞,使宗族相怨之诗”。这首诗的内涵与《常棣》一诗一致,在《常棣》中前四章所描写的是理想中的兄弟相处之道,第五章写现实中的兄弟甚至“不如友生”,最后三章对人们进行了规劝,劝谏兄弟要和睦相处、互帮互助。而《角弓》所描绘的是因为兄弟之间相互不信任而产生的矛盾以及对于这种和乐场景的希望与殷切的寄托。通过对这两首诗歌的了解,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因为人们对于骨肉亲情意识的淡化,所以作者才写出这样的诗歌进行规劝。
自《诗经》以后,历朝历代描写亲情的诗歌蔚然成风,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歌。其中有很多的诗歌都饱含了中华民族历来所追求的至情至性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屹立在时光的隧道之中。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诗经》是我国亲情诗的发端,它对我国亲情诗的影响非常深远。《诗经》所体现出来的人伦亲情,以及所建构的伦理道德观,贯穿于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之中,也在中华文化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后代亲情诗歌的创作中,不论是创作手法“赋比兴”的运用,创作意象的运用,还是在复句沓章表现手法,还是抒情方式上,诗歌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诗经》的影响。
四﹑在风雅中的异同
在《诗经》中,同样是描写无法再对父母尽孝的诗歌,风诗与雅诗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有所差异。《国风》多出自民间,更加直接地描写,代表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如在《邶风·凯风》中直接抒发出了因为不能报答母亲辛苦的养育之情而发出的自责,是一首歌颂母亲而自责的诗歌。在语言方面,《凯风》诗中各章前二句,以凯风、棘树、寒泉、黄鸟等意象起兴,作比喻,构成了一幅生动清新的生活画面。后二句反复叠唱的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无不是孝子对母亲的深情。此诗中的民间用语,朴素自然、清新活泼而富有生活气息,且篇幅较短,章法不甚严谨、形式自由。在雅诗中,是从周代文人写诗的角度出发,真实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生活。如在《小雅·蓼莪》中,《诗集传》写道:“人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而作此诗”。《毛诗序》也提到此诗是“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根据史书记载可知,在周厉王、周幽王时期,君王暴政,赋税、徭役加重,大多数男子都要离家去征战,因此很多人都不能在父母跟前尽孝。这首诗典雅庄重,讲究句法﹑用韵,篇幅较长,结构严谨。赋比兴交互运用的手法更是这首诗歌的一大特色。丰坊《诗说》云:“是诗前三章皆先比而后赋也;四章赋也;五、六章皆兴也。”赋比兴这三种手法的交互运用,使得诗歌情感更加饱满,回旋跌幅,更加深刻地表现出孤子哀伤的情思。在后面一章中诗人连用了九个动词和九个“我”字,感情真挚,发人肺腑。这也是雅诗的整体特点,在雅诗中,多文人之典雅庄重,讲究句法押韵,且雅诗的篇幅较长,布局严谨,结构完整,组织周密。
对于描写夫妇之情的诗歌,则主要集中于风诗中,《王风·君子阳阳》《郑风·女曰鸡鸣》《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都以质朴﹑清新的语言,运用写实的手法,把现实生活中的生活场景入诗,描写出了夫妇生活的场景,或是思妇对征夫的思念之情,或是夫妻幸福和乐的生活画面,或是弃妇所遭遇的种种不幸。《诗经》中描写夫妻之情的诗歌大多反映的都是下层民众的真实生活、真实情感,或感人肺腑,或感到幸福和乐,或发人深思。
描写兄弟之情的诗歌,都出自于《小雅》,以一种劝谏的口吻来说明亲疏之分,兄弟乃是天伦也。《常棣》和《角弓》两首诗虽然描写的角度和创作的背景不同,但是作者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在劝谏要亲兄弟,要与兄弟和睦相处。
《国风》多出自民间诗人之手,内容更加深广,思想性相比较而言更加强烈。其中的亲情诗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雅诗的思想性虽然不如《国风》,且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但是他从文人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讽刺诗在雅诗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雅诗中的亲情诗,也大多都是通过描写亲情来怨刺社会政治,表达出诗人的一种希望。
《诗经》中的诗歌都是一首首现实主义的作品,描写的都是人民大众的真实情感,不似《庄子》《离骚》写作充满了奇幻和浪漫主义,使用夸张﹑虚构﹑想象等手法。《诗经》都是通过描写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场景和生活面貌,表达时代最真实的感情。描写亲情的诗歌在《诗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诗歌自然也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我们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先民们对亲情人伦的重视,以至到后来社会动荡时期先民们对亲情的呼唤以及期待。在现代社会中,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和谐的家庭,这些诗歌对于我们处理亲情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中可以学习到孝顺父母,以孝为本,也可以学到夫妻和乐、兄友弟恭。这些诗歌逐渐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历经千万年所流传下来的精髓,将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使之成长,促进中华民族走向更加繁荣富强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闻一多.风诗杂抄[M].上海:上海书店,1991.
[4]聂永华.诗经亲情诗的文化蕴含与文学母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5]傅斯年.诗经讲义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白景民.《诗经》中的亲情[M].聊城大学学报,2008,(2).
[7]雷红姜,何尊沛.论《诗经》中的亲情诗及其影响[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10,(2).
[8]武丽霞.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9]詹志红.唐代亲情诗研究[D].陕西理工学院,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