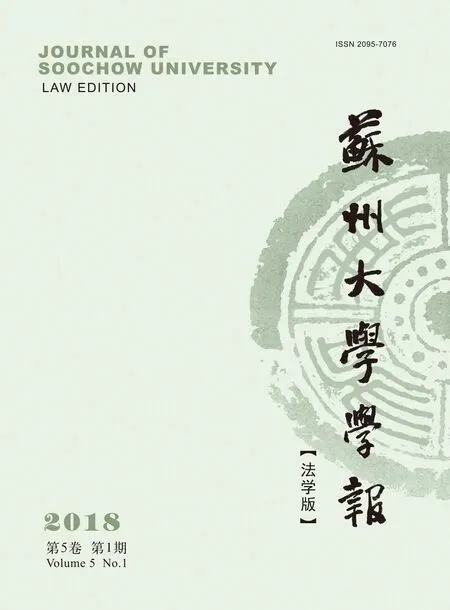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瑕疵婚姻制度的立法建议—以《民法总则》之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婚姻家庭编中的适用为视角
2018-01-31田韶华
田 韶 华
民法典分则婚姻家庭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结婚制度,而对瑕疵婚姻的规制则是结婚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瑕疵婚姻的制度设计不仅关系到法律对不符合结婚要件的婚姻缔结应有的态度,也关系到《民法总则》中的瑕疵民事法律制度对于结婚行为的适用,从而最终关系到民法典及其婚姻家庭编的体系性和科学性,应当引起学界和立法界的重视。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对瑕疵婚姻已有所规定,但如果从立法的科学性和体系性这个角度观察仍然存在不足。婚姻家庭编应在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立法经验以及总结我国现行立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此予以进一步的完善,其中既要考虑到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内在的体系性,也要顾及婚姻关系不同于财产关系的特性。本文以《民法总则》之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结婚制度中的适用为视角,对瑕疵婚姻制度的构建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对民法典分则婚姻家庭编的制定有所裨益。
一、目前我国瑕疵婚姻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立法对于瑕疵婚姻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婚姻法》第10至12条以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7至16条,这些条款分别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事由、程序以及婚姻被宣告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等问题予以了规定。上述规定虽然弥补了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之前有关瑕疵婚姻的立法缺陷,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瑕疵婚姻与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法律适用关系模糊不清。瑕疵婚姻在本质上是瑕疵结婚行为导致的后果,由于结婚行为属于身份行为,而身份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故民事法律行为实为结婚行为的上位概念。就此而言,瑕疵婚姻的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与民法总则中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关系问题。但从目前的立法来看,这一关系并未从根本上予以厘清。从《婚姻法》上的瑕疵婚姻制度来看,其对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实际上采取了选择性适用的态度,如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区分、受胁迫缔结婚姻的可撤销性的规定实际上就是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婚姻法上的适用;而相当一部分民法总则中的规范,如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等无效行为的事由,欺诈、重大误解等可撤销行为的事由则未在婚姻上予以体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选择的依据何在?是否具有逻辑上以及价值判断上的正当性?尤其是,对于婚姻法未予规定而造成的法律漏洞,能否由民法总则的规定予以补充?这些问题并不能从现行立法中找到答案。
2.瑕疵婚姻制度的内容不完整。例如,《婚姻法》规定结婚时需要当事人共同到一方户籍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但对于在未办登记或者登记存在瑕疵的情形下如何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却未设明文。特别是对于登记存在程序瑕疵的情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只能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撤销结婚登记。然而,行政程序只能解决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并不能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关系予以认定,由此造成的法律漏洞导致了司法实践的困惑。例如,面对当事人未共同亲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形,法院的观点即存在分歧:有的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①参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2015)铁民初字第611号民事判决书。有的法院则认为此种瑕疵不影响婚姻的效力。②参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民五终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
3.瑕疵婚姻的制度设计未能充分体现出身份法的特色。与财产法相比,身份法的特色在于其重视婚姻家庭关系的安定性以及女性、未成年子女等家庭成员的保护。但从目前瑕疵婚姻的立法情况来看,这一特色未能予以充分体现。反观域外,为保护既定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的利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瑕疵婚姻的后果方面都有着不同于财产行为的制度设计:或规定婚姻的撤销不具有追溯力,或承认婚姻的瑕疵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治愈,或为无效婚姻及可撤销婚姻中的无辜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救济等,但这些规定在我国婚姻法上或付诸阙如或有所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婚姻家庭法功能的实现。
鉴于目前我国瑕疵婚姻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婚姻家庭编的编纂应当在厘清瑕疵婚姻制度与民法总则的适用关系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与《民法总则》的衔接立法以及结婚行为的身份法特色,使瑕疵婚姻的制度设计更具科学性和体系性。
二、厘清瑕疵婚姻制度与民法总则之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适用关系
《民法总则》规定了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这些制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结婚行为,或者说,瑕疵婚姻的制度设计应否以及如何体现《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决定了瑕疵婚姻制度的逻辑起点和基本框架体系,是一个首先应予回答的问题。
关于《民法总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规范能否适用于婚姻家庭法,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持否定说,认为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各种规定,旨在重视对交易安全之保护;对仅有纯粹身份意义之婚姻、协议离婚、收养以及收养之协议终止等关系,并无适用的余地。③陈棋炎:《亲属·继承法与民法总则间之疑难问题》,载戴东雄编:《民法亲属继承论文选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9页。有的学者则持肯定说,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总则的内容,而婚姻法是民法分则的内容,故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婚姻关系。①王利明:《婚姻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学》2001年第3期。还有的学者持区分说,认为在婚姻家庭法有规定时,适用婚姻家庭法的规定,而在婚姻家庭法无规定时,则以不违反社会妥当性为限,可适用民法总则有关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②杨立新:《论亲属法律行为》,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对此,笔者认为,民法总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规范能否适用于婚姻家庭法,这一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民事法律行为规范能否适用于身份行为的问题,就此而言,上述观点中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均过于绝对。一方面,由于民法总则与分则的编排体例,在解释上应认为总则的规定对于分则有适用的余地。而且在民法理论上结婚、收养、协议离婚以及协议解除收养等行为被归于身份行为,而身份行为是与财产行为相对应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亦即是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存在的,故不能完全排除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对于身份行为的适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法律行为制度主要是以财产行为为中心构建的,而身份行为毕竟不同于财产行为,故应当承认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对于身份行为的适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③苏永钦:《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编纂若干问题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当然,区分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两种学说的缺陷,但其只是解决了在婚姻家庭法无规定时身份行为与民法总则的适用关系,并没有解决婚姻家庭编身份行为制度设计本身与民法总则的适用关系,故不能为相关立法提供理论依据。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鉴于身份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在民法总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规范能否适用于身份行为这一问题上,既不能过于强调身份行为的特殊性从而割裂其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也不能过于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涵射性从而导致其在身份行为中的不当适用,而应同时兼顾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体系性与身份行为的特殊性予以判断。这意味着婚姻家庭编应当对民法总则中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予以选择性适用。至于选择的标准,则应以是否有悖于身份行为的特质为判断。对于那些不违反身份行为特质的法律规范应予以适用,而对于那些有违身份行为特质的法律规范,则不应适用并应根据身份行为的特殊性予以制度创新。
由于结婚行为属于身份行为的一种,故上述结论对于结婚行为也同样适用,即瑕疵婚姻的制度设计亦应同时兼顾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体系性与结婚行为的特殊性,并对民法总则中的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依上述标准予以选择性适用。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婚姻家庭编中的瑕疵婚姻制度应重点在瑕疵婚姻的类型体系、瑕疵事由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予以完善。
三、注重瑕疵婚姻的制度设计与《民法总则》的衔接
(一)增设婚姻不成立制度
《民法总则》虽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不成立未设明文,但其区分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对于“不成立”这一后果均须予以承认。而从《婚姻法》的规定来看,由于在其规定的结婚要件中未予区分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在违反结婚要件的后果上也只规定了无效和可撤销,故“婚姻的不成立”这一瑕疵类型并未得到立法的认可。笔者认为,婚姻家庭编应当对婚姻的不成立予以明文规定。这一方面体现了与《民法总则》的衔接,另一方面也能够将那些虽然违反了结婚要件但无法被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涵盖的行为纳入到法律的调整范围,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依据。④王礼仁:《婚姻登记瑕疵中的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认定》,载《人民司法(应用)》2010年第11期。而且,在立法上规定婚姻的不成立也具有比较法上的依据。例如,《葡萄牙民法典》以及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均专节规定了婚姻的不成立,并对不成立婚姻的情形及其后果予以了规定。《德国民法典》虽未明确规定婚姻的不成立,但学者认为这一评价在实际法律效果上是存在的。⑤[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上述规定及见解值得借鉴。至于婚姻不成立的事由,依民法基本理论,应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未达成结婚的合意。例如,当事人在不知情或无合意的情况下被办理了结婚登记;二是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且不构成事实婚姻。对于第二种情形,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属于无效婚姻。①曹贤余:《登记瑕疵婚姻效力分析》,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3期。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结婚作为一种要式行为,登记应为结婚成立的形式要件,违反这一要件的婚姻应评价为不成立,而根本不存在的婚姻则谈不上无效。
(二)维持婚姻效力瑕疵的双轨制
现行《婚姻法》对于效力有瑕疵的婚姻采取了同时承认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一设计不仅与《民法总则》的规定相衔接(《民法总则》中的效力待定行为规则由于有违婚姻关系的确定性而不适用于结婚行为),而且也具有逻辑上的正当性——毕竟,违反公益要件和违反私益要件导致的法律后果应有所不同,②夏吟兰:《民法典之婚姻家庭编立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故这一制度设计应在婚姻家庭编中予以维持。但也有学者从比较法的角度提出了应当采取单一无效制或单一可撤销制的观点。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待商榷。从立法例来看,的确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家庭法未区分婚姻的无效和可撤销,而是采取了仅规定无效或仅规定可撤销的单轨制。如德国、葡萄牙等国的民法典只规定了可撤销婚姻(德国称之为可废止的婚姻),法国、瑞士等国家则只规定了无效婚姻。但应当看到的是,即使在这种单轨制模式之下,仍体现了立法者对于违反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的不同态度。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316条的规定,违反亲属编强行性规定的婚姻(如未达法定婚龄、违反禁婚亲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缔结的婚姻等),有权申请废止的主体是配偶任何一方以及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同时规定除非婚姻的废止会对当事人及其子女造成过于严苛的后果,行政机关应当提出申请;而对于受欺诈、受胁迫以及错误情形下缔结的婚姻,则申请人只能是配偶。再如,《瑞士民法典》虽然采取了单一的无效婚姻模式,但却把无效婚姻分为两类:即诉请无效无时间限制的无效婚姻和有时间限制的无效婚姻。对于前者,主管机关及其利害关系人均可提起无效之诉,而对于后者,则只有夫妻一方可以提出。由此可见,即使在单轨制模式之下,立法者仍然认为应对违反公益要件的婚姻和仅仅违反私益要件的婚姻区别对待,由此导致制度设计的复杂性。故笔者认为,在《民法总则》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已经有了清晰制度架构的基础上,婚姻家庭编没有必要另起炉灶采取仅规定无效或仅规定可撤销的单轨制,否则徒增制度设计的复杂性。
(三)体系化婚姻无效及可撤销的事由
1.关于婚姻无效的事由
《民法总则》规定的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事由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行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第144条);二是通谋虚伪(第146条);三是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第154条);四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第153条)。笔者认为,婚姻家庭编对于无效婚姻事由的认定,原则上应以上述规定为依据,并在充分考虑结婚以及婚姻关系特殊性的基础上予以设计。一方面,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安定性出发,应只将那些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并有违社会公益的行为确定为无效;另一方面,基于立法技术考虑,可在婚姻家庭编中仅明文列举与违反结婚要件有关的无效婚姻类型。至于违反民事法律行为一般生效要件的,可在个案中于不违反身份行为特质以及社会妥当性的前提下,适用《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文的主旨,笔者对此将另文探讨)。
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在目前《婚姻法》所规定的无效婚姻的类型中,重婚的、存在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这三种皆属于违反结婚要件中公益性要件的情形,同时由于这些要件均是婚姻法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将其作为无效事由也是《民法总则》第153条在婚姻家庭法上的体现,对此婚姻家庭编可予以保留。除此之外,笔者建议删除“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这一无效事由。虽然确定该事由的依据是《婚姻法》第7条第2项关于结婚的禁止性规定,但笔者认为婚姻家庭编不应再将其作为婚姻无效的事由。一方面,结婚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以患有某种疾病为由宣告婚姻无效直接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主权。虽然患有某种疾病会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但除非疾病导致当事人丧失行为能力,其他疾病是否影响结婚的决定应当属于家事自决权的范畴,国家没有必要干预。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以及对人权的重视,究竟哪些疾病属于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在科学上很难界定,事实上,时至今日,在医学上也没有哪一个文件明确规定何种疾病属于禁止结婚的疾病,这也导致此项无效事由在实践中难以适用。①孙若军:《疾病不应是缔结婚姻的法定障碍》,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婚姻家庭编应当删除将特定疾病作为婚姻法定障碍的规定,也不应将其作为婚姻无效的事由。但鉴于某些疾病会涉及到当事人及其配偶的利益,在解释上可作如下处理:如果当事人在结婚时患有导致其丧失行为能力的疾病,可以通过“欠缺结婚行为能力”这一规范认定婚姻无效;如果当事人在结婚时患有严重影响婚姻生活的疾病但不涉及行为能力问题,则在构成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下,可通过该制度对遭受不利益的一方予以救济(对此,笔者将于后文详述)。
(二)关于婚姻可撤销的事由
《民法总则》规定了四种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事由,即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在这四种理由中,“显失公平”因带有明显的财产法色彩显然不可作为婚姻的撤销事由,而其他三种事由能否全部适用于可撤销婚姻,则颇值探讨。有学者认为,由于现实生活中欺诈情况较为复杂,被欺诈结婚与受欺诈方对另一方审查不严有着直接的关系,故欺诈婚姻不应作为可撤销处理,而是应承认其婚姻的效力,将其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情形之一。②傅强、谢唯伟:《论非真意的婚姻》,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笔者对此并不认同。一方面,当事人因受欺诈或重大误解而结婚,皆非真实意思表示,财产行为尚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允许撤销,更何况比财产行为更重内心真意的身份行为?另一方面,从否定说的理由来看,其之所以反对将欺诈婚姻作为可撤销婚姻,主要是基于实务操作的考虑而并非严密法理论证的结果。而从法理上分析,欺诈、重大误解这些概念并非仅为财产行为而设,其在结婚行为中的适用并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然而,从立法例上看,虽然各国及地区的民法一般均将欺诈、胁迫、错误作为可撤销法律行为的事由,但对于可撤销婚姻事由的规定则颇不一致。如《德国民法典》规定的事由包括欺诈、错误、胁迫以及违反强行性规定等;③《德国民法典》中的可撤销婚姻实际上称为“可废止的婚姻”,其与传统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区别在于不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 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的事由包括欺诈、胁迫、违反法定婚龄等,但并未规定错误;《葡萄牙民法典》规定的事由包括错误、胁迫以及违反禁止性规定等,但未包括欺诈;而我国《婚姻法》中可撤销婚姻的事由则只规定了胁迫。在笔者看来,各国及地区立法中反映出来的上述差异恰恰说明民法总则中的“欺诈”、“胁迫”以及“重大误解”在婚姻的缔结中都是有可能存在的,而排除其中的一项或几项并不具有逻辑上以及价值判断上的正当性。故无论是基于与《民法总则》的立法衔接,还是基于回应实践的需要,婚姻家庭编均应将欺诈、重大误解作为婚姻可撤销的事由。除此之外,还应将结婚行为能力的欠缺增补为婚姻可撤销的事由。虽然《婚姻法》上只有对法定婚龄的限制,并没有对结婚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要求,但结婚行为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应为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对该规定的违反只涉及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故不宜将不具有结婚行为能力的人缔结的婚姻界定为无效,而是将其界定为可撤销更为妥当。其中结婚行为能力的欠缺既包括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也包括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对结婚的法律后果并不存在认知、理解的情形。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认定可撤销婚姻中的“欺诈”“重大误解”以及“胁迫”?从各国及地区的立法例及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均对上述行为采取了不同于财产行为的认定规则。例如,对于导致婚姻可撤销的“错误”,《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第2款第2项将其限制于“配偶一方在结婚时不知道事情关系到结婚的”;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508条第1款b项将其限制在身份认识错误。对于导致婚姻可撤销的“欺诈”,《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第2款第3项将其界定为:配偶一方因受恶意欺诈而作出结婚的意思表示,并且该方在此前知悉实情并正确认识到婚姻的实质就不会缔结婚姻的。但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欺诈所涉及财产关系或者是在婚姻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形下由第三方所为的情形。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能够被法院认定为“民法”第997条中的“诈欺”行为的,则均系夫妻一方有身体或精神上的重大恶疾,致难以期待他方无视其恶疾之存在而继续婚姻关系的情形。①詹森林:《民事法理与判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上述法条及司法实践说明,在判断结婚行为是否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时,应当采取符合结婚特点的认定标准,即能够认定为欺诈或重大误解的事由应限制在与婚姻的缔结有实质决定意义的事项,如身份资格、重大疾病等,至于对财产关系、社会关系、收入状况等的欺诈或错误认识则不能导致婚姻的撤销。
至于对导致婚姻可撤销的“胁迫”的认定,原则上与财产行为中的判断并无二致,即胁迫人威胁被胁迫人,其有能力向其施加恶害之不利。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往往会利用对方的危难之际迫使其同意进行某种身份上的行为,例如,乙或乙的家庭正在遭受他人施加的恶害,甲承诺若乙与其结婚则不会遭受此恶害。此种利用他人的危困状态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总则》中只有在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时方可撤销,由于显失公平规则不适用于身份行为,于此情形,如何对乙提供救济便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葡萄牙民法典》第1638条第2款规定:“一人借承诺使结婚人不会遭遇某种意外之恶害或不会遭受他人施加之恶害,而有意识及不法迫使结婚人作出结婚意思表示者,等同于不法威胁。”该条实际上对结婚行为中的“胁迫”作了扩张解释,笔者认为这值得我国借鉴。
四、突出瑕疵婚姻制度设计的身份法特色
由于婚姻关系对于当事人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瑕疵婚姻制度的设计也应符合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取向,即尊重既存的身份关系、努力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并保护特定主体如女性、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等。就此而言,瑕疵婚姻的制度设计除了要注意与《民法总则》的衔接之外,还应突出其身份法特色,以与财产行为相区别。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婚姻瑕疵的治愈事由
即使婚姻存在瑕疵,但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及稳定婚姻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除非损害公共利益,应允许此种瑕疵可因一定的事由而得以治愈。事实上,我国目前的《婚姻法》对此已有一定程度的承认。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8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实际上是将“无效婚姻情形消失”如已达法定婚龄等作为了婚姻无效的治愈事由,对此值得肯定。但上述规定只局限于婚姻无效领域且并不全面,笔者认为应作如下完善:
1.关于因欠缺结婚合意而导致的婚姻不成立的治愈事由。当事人事后达成合意或形成实质夫妻的情形下,应当认为这一瑕疵已被治愈。例如,在当事人未按规定共同去登记机构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形下,只要当事人已经形成实质夫妻关系,则应推定其存在结婚的合意,不能再认定该婚姻不成立。
2.关于婚姻无效的治愈事由。对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8条的规定固然值得肯定,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重婚一方当事人前婚已经因离婚或另一方死亡而解除,那么,重婚的后婚是否仍然无效?质言之,“重婚当事人的前婚不复存在”可否作为无效婚姻的治愈事由?对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为打击重婚这种违法行为,不应认可此种瑕疵治愈事由。而笔者认为,在重婚一方的前婚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形下,从尊重既成身份关系的角度出发,应认为法定无效的事由已经消失,不应再认定后婚无效。①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如何理解“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载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对此,也有我国澳门地区的民法典以及《俄罗斯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可资借鉴。②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506条规定:“重婚者的前一婚姻被解除(包括配偶一方死亡或双方离婚)或者被撤销的,其后一婚姻(重婚)则成为有效婚。”《俄罗斯民法典》第29条规定:“在审理确认婚姻无效案件时,如果法律不准结婚的条件已经消除,法院可以认定婚姻有效。”
3.关于婚姻可撤销的治愈事由。目前《婚姻法》并未规定婚姻可撤销的治愈事由,只是规定受胁迫的当事人应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对此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无异于赋予了受胁迫方在法定期间内的无限撤销权,这固然有利于对受胁迫方利益的保护,但忽视了对既成身份关系的尊重,故应当予以完善。《德国民法典》第1315条第4项规定,在当事人发现具有欺诈、重大误解事由或胁迫事项消失后,表明其愿意延续婚姻的,当事人不得再为撤销行为。此项规定值得借鉴。此外,为充分尊重欠缺民事行为能力者的意思自治,对于欠缺结婚行为能力者缔结的婚姻,当事人取得结婚行为能力(即可撤销事由消失)并不当然使婚姻成为有效,只有当事人取得结婚行为能力并且对婚姻予以承认的情形下方能使瑕疵得以治愈。
(二)对婚姻无效与撤销的溯及力予以区别对待
《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这实际上规定了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具有溯及力。对此,笔者认为,无效婚姻多为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故使其自始无效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但对于可撤销婚姻而言,其并不属于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的行为,也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在当事人已经形成了长期的身份关系和人伦秩序的情形下,为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利益,婚姻的撤销不应具有溯及力,而只能对未来发生效力。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各国及地区多规定婚姻的撤销并不具有溯及力,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借鉴。③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98条,《日本民法典》第748条,《葡萄牙民法典》第1633条等。此外,对于《德国民法典》第1313条关于婚姻可废止的规定,在解释上一般认为其只是令婚姻面向未来地被解除,原则上不具有追溯力。
(三)增设对瑕疵婚姻中无辜当事人的法律保护
依我国《婚姻法》第12条的规定,婚姻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后,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在协议不成时,由法院本着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判决。该条款将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的关系归于“同居关系”,基于此种定位,即使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不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其也只能在分割财产时获得一些照顾而并不能主张夫妻离婚时享有的一些权利(如经济帮助请求权、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请求权)以及继承权等。此外,依该条的规定,瑕疵婚姻中的无过错当事人除了在分割财产时得到一定的“照顾”之外,并不能向有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这使其得到的救济尚且不如瑕疵财产行为的无过错方,显然有失公平。④瑕疵财产行为中的无过错一方可依《民法总则》第157条的规定向有过错的一方请求损害赔偿,而我国《婚姻法》并无相似的制度,这使得瑕疵婚姻中无辜当事人一方的损害难以得到救济。例如,在江苏省沐阳县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重婚案中,宋某与沈某虽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40年,并补办了结婚登记,但仍然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婚姻,而沈某对宋某的已婚状态毫无不知情。婚姻被判定无效的后果使其失去40年之久的夫妻名份,导致继承等重要身份利益的丧失,而其利益依现行法律无从得以救济。案情载http://sqz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5/id/1288477.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月2日。而从域外立法例来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设明文对此类当事人予以救济:或者对善意的当事人提供与有效婚姻相同的保护①如《德国民法典》第1318条规定,对于结婚时不知晓婚姻废止原因的配偶一方,或被欺诈或胁迫的配偶一方,婚姻被废止后发生与离婚相当的后果,如仍然可以请求配偶之间的扶养以及仍然享有继承权等。,或者对于无过失者赋予损害赔偿请求权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99条则规定,无过失的当事人一方因结婚无效或被撤销受有损害者,得向他方请求赔偿。,或者二者兼采③根据新《巴西民法典》第1561条规定,婚姻不管是可撤销的,还是无效的,如夫妻双方是基于诚信缔结的,在撤销判决日之前,此等婚姻对他们及其子女都发生完全的效力;如在缔结婚姻过程中双方均为恶意,其民事效力仅给其子女带来利益。第1564条规定,当婚姻因夫妻一方的过失被撤销时,他方有义务弥补无过失的他方所有已获得利益的丧失,并有义务履行自己在婚前协议中所作的承诺。。相比较而言,第三种模式对无辜当事人的保护更为全面,值得我国制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借鉴。具体而言,对善意的当事人,应使其有权主张婚姻解除时作为有效婚姻的当事人有权主张的权利,包括继承权、经济帮助请求权、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请求权等;对于无过失的当事人,应赋予其对恶意一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即请求赔偿其信赖婚姻有效而遭受的财产上及非财产上的损失。④徐国栋:《无效与可撤销婚姻中诚信当事人的保护》,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