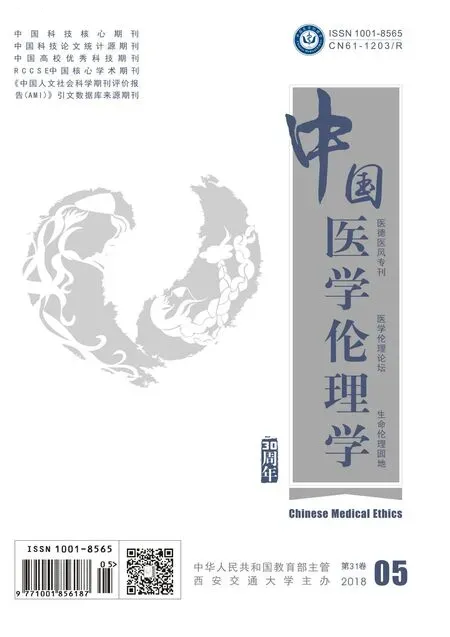人的不朽渴望与生死安顿
——唐君毅对不朽论的辨正及完善不朽论的设想*
2018-01-30何仁富汪丽华
何仁富,汪丽华
(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8,herenfu@163.com)
“死亡”似乎总是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而又是无法相离的孪生姐妹而存在的。一方面,“死”就不再“生”,或者说,“死亡”是对生命存在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恰恰是因为“死亡”的存在,确证着生命之为“生命”。这种生死存在的“吊轨性”是有自觉意识的人类最大的纠结之一,也由此而有了“终极关怀”的言说。人类的智慧在于,为了突破这种存在的吊诡性,发明出了“不朽”这一概念和论说,力图用各种各样的“不朽”将生死的辩证对立转化为生死的存在互渗与逻辑连接,以安顿人自己的生死,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的“不朽论”。因此,“不朽”“不朽渴望” “不朽论”,乃是现代生死学研究或者说生死哲学研究必须要正视和面对的基础性问题。人可能不朽吗?人为什么要追求不朽?人的不朽渴望是合理的吗?是可能的吗?人类思想史上的各种关于不朽的思想真的能够帮助人们实现“不朽”的渴望吗?这正是唐君毅在《论不朽》*《论不朽》一文,唐君毅撰写于自己刚刚经历了“几欲自杀”不久的24~25岁,1933年2月1日初稿,1934年3月27日改稿,1935年11月发表于“学术世界”第一卷第六期。后收录于1943年出版的唐先生第一部著作《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附录中。该文可以看作唐先生对生死哲学的最为明确的问题意识表达。概括言之,唐君毅在此文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其基本逻辑包括:人生终不免一死;人无不悦生恶死;人既无不悦生,而又终不免乎一死,于是便有了各种不朽的学说;感生死事大者既多,为不朽之论者兹众,但不朽果真可能吗?如何可能?一篇经典文献中讨论的核心话题,也是其一生都在追问的问题,并以此建立起一套现代儒家生死哲学系统。唐君毅将中西各种思想中出现的不朽论归纳为十种,并逐一做了理论上的辨正,指出了各种不朽论的不合理之处及可以借鉴的地方,并进而提出了自己“完善不朽论”的初步设想,为其建构的现代儒学生死(哲)学作了初步的理论奠基,也为现代人的生死安顿指出了一条哲学的出路。
1 物质性不朽论辨正
在唐君毅看来,物质不朽论、生物不朽论,大体可以归类为以“物质性渴望”为主要内容的不朽论,是最直观、最直接也最没有合理性的不朽论。
物质不朽论认为,人的生命机体是由物质的聚合而形成的特殊形态的物质体;人的死亡,只不过是人体的形态消散而重新回归另一种形式的物质存在。人的生、死,是物质的聚散,只不过是改变了物质的存在形态而已。神奇化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都只是物质存在形态的变化,犹如气的流行。物质常住,气运不息。所以,何死之有?何朽之有?持这种理论立场的,主要是以科学常识为支撑的各种“唯物论”。
唐君毅对这样一种“物质不朽论”的主要辩驳在于:首先,所谓的“物质常住” “气运不息”,都只不过是我们人过去的经验曾经昭示的,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保证,日月云雷等自然万象将会永远存在并运行不止;也没有绝对的理由保证物质存在在某一日不归于消灭;不能确知是否一定不会有宇宙虚空之日。其次,物质宇宙本身,并没有告知我们,它将长此终古;我们人类之所以相信此物质宇宙将长此终古,是因为我们相信,物质宇宙中有某种逻辑原则运乎其间,因此可以借由过去推知未来;但是,可以凭借过去的存在推知未来的存在的逻辑原则本身,并非物质存在;凭借一套非物质存在的逻辑原则推论出物质宇宙存在的永恒性本身即表明,宇宙唯物说的建立是无根据而不可能的。再次,即使我们承认,借助于逻辑原则建构起来的物质宇宙论成立,日月云雷等物质万象如此这般永恒存在、长存不毁,我们也不能否认另外的可能性存在,哪怕只是偶然的存在,即:万一遭遇到宇宙运行中其他大的流星的碰撞,地球破裂,一切生物,同为灰烬;在此种情况下,尽管从气的运物法则来看,与当下万物并育文化鲜明的情况下的法则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却不可能说,这两种存在状态的世界是一样的,无所谓好坏善恶之别。如此,我们也不可能说,生与死,毫无价值的等差。
唐君毅从过去经验并不绝对可靠、宇宙存在的逻辑并非物质、物质聚散并不等于人的生死三方面否定了“物质不朽论”的可能,论证是有力有理的。唐君毅认为,即使持此唯物论立场的人,只要平心静气而论,就不可能随意地说,也不可能真正相信:人的物质身体形散之后,因为物质犹存,所以生死无分。
生物不朽论认为,人诚然没有不死的,但是,人有生殖能力、生殖行为,通过生养后代而接续其后。因此,尽管人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死了,却还有子女存在,子又有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自从现代遗传学提出生殖细胞与身体细胞分别之论以来,我们就懂得,我们的身体里有无限年代祖宗的细胞,而我们身体的细胞可以传至无限年代后我们的子孙。何况,生物之所以有死,正由于其有生;有生必有死。既然有新生,何以还必须有旧老继续存在下去呢?在自然界中也确实存在诸多以自己的死成就新生的“自然行为”,比如一些低等动物,雌性动物完成生殖新生命后自己就死亡;另一些,雄性动物在完成交尾的生殖行为时便立马死亡。如果生物世界都老而不死,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一定是禽兽充塞、人满为灾。所以,造化安排,有死正所以为了有生。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那么,子孙绕膝,寿终正寝,也就是理所宜然;而所谓“不朽”之义,也正在于此。这种不朽论不仅是基于遗传科学的变种的“物质不朽论”,在经验事实上,也是很多常识中的人所坚持的“传宗接代”式的生命不朽论的基本信念依据。
但是,在唐君毅看来,这样一种以子孙的无尽延续来证明个人生命的不朽,有两个方面值得怀疑:首先,人并不必然都有子孙,而有子孙者也不必不中断。历史经验如此,历史逻辑也如此。如果必须要有子孙而且还必须延续不断才是不朽,那么,那些无子孙或有子孙而中断者,则依然面临“朽”的命运。而且,人之为人,求生命之不朽,也不应该只是求有不断的子孙的不朽,而还有求自身生命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不朽。其次,即使有子孙而且延续不断,可是,子孙未必真能够肖之;纵然其形肖,也不必一定心肖;纵然其心肖,也不必能够全肖;纵然能够全肖,可毕竟他们只是子孙,与自己并非为一。既然子孙不能肖,肖而不能一,那么,死者最终还是死,而且也没有绝对可以承续其生命的。如此,死者最终还只能是长朽而不是不朽。
唐君毅这里强调,一方面,生物不朽论无法安顿那些没有子孙者的生命;另一方面,即使对于子孙延续不断的个体生命而言,同样面对子孙的延续并非就是自己生命的不朽这一基本的生命事实。
2 社会性不朽论辨正
既然试图通过物质存在和生命繁衍的方式无法实现个体生命的不朽要求,那么将个体生命融入社会生活中的不朽论又如何呢?社会不朽论、曾在不朽论、价值不朽论,大体上都是从个体生命的现实存在性出发来诉求个体生命的不朽渴望,在唐君毅看来,也多是不合情理的不朽渴望表达。
事业不朽论特别体现在中国文化中的“三不朽”论。叔孙豹所言人有“立德”“立功” “立言”三不朽,这是一种以个人在现实世界中所成就的事业来论证个体生命的不朽的不朽论,其影响,尤其是对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甚至成为一般读书人安顿自己生死的基本选项。
但是,唐君毅认为,“三不朽”的事业不朽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与前面的“生物不朽论”有同样的问题。首先,立德、立功、立言,只可能是少数人所能实现的生命状态。尧舜仁政、秦汉武功、周孔文章,虽然都足以炳耀千古;但是,历史长河中存在的千万人中,能做到如此这般立德立功立言的,实在只是十分有限的一些个体生命。如果真是如此之后才能生命不朽,那么,不朽的权利,便只掌握在这样一些能够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少数人手里;此不朽之论,便也只能是安慰这一些少数人的不朽论。其次,德、功、言,其实都不过是立德、立功、立言者的生命足迹。但是,立德立功立言者的生命之所以高贵难得,并不只是因为其生命足迹,而是其生命本身。尽管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见其所立之德、功、言,犹如见其生命;但是,不管是客观存在上还是主观体验上,其迹虽存,其人确实已去。再次,即使认为立德、立功、立言者其生命之高贵就在其所立之德、功、言本身,但是,尽管一个人所立之德足以“德泽万世”,却不能保证万世之后仍能够无穷无竭;其所立之功尽管可以“功被千古”,但千古之后不能保证其不枯竭;所立之言或可以“言教百代”,但百代之后却也不能保证其不断绝。
很显然,唐君毅对于“事业不朽论”的辨正是极具冲击力的。一方面,他通过分析生命存在与生命足迹(其实就是哲学上所谓的体与用)、足迹不灭并不代表存在不朽、足迹不朽有朽的可能等逐层的剥离结构,对此不朽论的辨正确实是有力的;另一方面,此“事业不朽论”却又是大多数中国人自发或自觉地用作安身立命的不朽信念。所以,唐君毅如何在其所要建立的“完善不朽论”中化解此冲击,确实值得期待。
社会不朽论试图以社会的不朽来标明个人的不朽。按照社会不朽论的理解,社会可以在两个方面或者层面保障或满足个体生命的不朽渴望。一方面,客观上说,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人的言行无一不受社会的影响,同时又影响社会。另一方面,个人存在于社会,犹如细胞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尽管细胞有新陈代谢,但我们的身体却依然故我;相应地,个人有死生存殁,但社会却不会因此而生灭。
唐君毅认为,不管是通过个人的社会表现(用的层面)还是小我存于大我(体的层面)的方式来论证个体生命的不朽,社会不朽论都存在着如下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并非人的所有行为都具有社会性。人的行为尽管无不直接间接影响社会也受社会影响,但是,如果从人的行为影响存在于社会,就由此而证明人的行为不朽,那么,就必须明确,人的行为影响是否全部都在社会。因为,如果可以因为人的行为影响在社会就证明人的不朽,那么,也可以从人的行为影响有不在社会的方面而证明人之朽。其次,很难说社会是不朽的。社会的不朽存在,只不过是人的祈盼方向而已。事实上,古代若干文明古国都已经完全沦丧,很明显说明社会之朽。再次,社会纵然不死,但个人确实是必死。我们不可能因为个人之死而说社会有死,同样,也不可能因为社会的不死而说个人也不死。
唐君毅通过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具有社会性、社会也并非真的可以不朽、即使社会不朽也不能说明个人不朽三个层面结构了社会不朽论,也为我们探寻真正的生死安顿留下了新的思考向度。客观上说,人活着,就在社会中,也只有在社会中才真正呈现出其人之“生”。那么,个体生命在社会中所打上的个人生命烙印,到底可以如何安顿自己的死亡呢?这也需要唐先生在其“完善不朽论”中给以说明。
曾在不朽论认为,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就不可能变成非存在,而是与宇宙存在本身一起长存。人的言行颦笑,即使不影响别人,其自身也是不朽的。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一颦时,则此颦已呈现存在于宇宙;有一笑,此一笑也已经呈现存在于宇宙。虽然当我们眉开之时颦即消逝,但原先已经存在的颦,则未尝消逝;虽然敛唇之时即消亡,但曾经存在过的笑,则未尝消亡。由是可以推论,人之生也不会有死。
唐君毅认为,这样一种以其存在本身来说其不朽的观点,“似较顺理”[1]351。因为,一事物既然曾经存在,那么,即使是万钧之力,也不可能让它改变或者不存在;过去已经有的事,一旦有了,则不可能为无。尽管如此,唐君毅认为,以此种证明来说明人的不朽,仍然是不恰当合适的。首先,人之求不朽,不是仅仅期求人存在于宇宙。如果说人之求不朽仅仅是期求人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于曾经存在的宇宙,那么,人根本就不需要求这种“不朽”,因为,这样的“不朽”与现实世界人们感受到的“朽”,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被称为“朽”的行为,必有其行为主体“朽者”;既然有一个作为主体的“朽者”,那也就表明,此“朽者”必然曾经存在。其次,人期求不朽,不是仅仅期求人曾经存在。根本上说,人期求不朽,既是期求曾经存在,而且是期求现在继续存在。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不是仅仅期求继续存在于过去,而且是期求继续存在到现在以及未来。曾经存在的人虽然曾经存在,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曾经存在虽然继续存在于过去,但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于现在及未来了。
在唐君毅看来,这样一种“曾在不朽论”,尽管看似有理,实际上却是所答非所问。唐君毅在自己的“完善不朽论”中尝试借鉴了“曾在不朽论”的合理因素,但根本上并不是通过“曾经存在”来说明个体生命的不朽。
3 精神性不朽论辨正
价值不朽论、智慧不朽论、伟大人格不朽论、大我精神不朽论,都是基于个体生命的精神性而建构生命的不朽渴望,在唐君毅看来,尽管理论并不完备,但都具有一些合理要素。
价值不朽论认为,客观上说,我们人的心身诚然有死亡;但是,现实存在的人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之道,则是不会最终消亡的。人生在世,所思所行之道,无外乎真、善、美、神圣的价值存在。何者为真,何者为善,何者为美,乃至何者为神圣,都是自在天地之间,浩浩不穷。此自存于天地间的人间大道,既不随人的身心之生而存续,也不会随人的身心之死而断灭。因此,客观永恒存在的价值世界是人渴求不朽之真正所在。主张这种不朽论的,以哲学家居多,尤其是典型的中国哲学家。朱熹曰:“夫谓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正以道未尝亡,而人之所以体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2]象山曰:“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3]阳明也主张:道,天下人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也不为少。柏拉图则强调:至善的真理永远存在于理念世界。
唐君毅认为,尽管这种以价值不朽来说明人之生命不朽的观点多为哲学家所主张,尤其充分的理性证明,但是,“仍不足以餍人求不朽之心也”[1]351。首先,价值不朽论所谓不朽的“价值”,指的是抽象的价值共相,而不是存在于个体生命中具体而特殊的价值经验。抽象的价值共相是否能离开我们个体生命中的具体而特殊的价值经验而单独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形而上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先验自明的经验事实或逻辑事实。其次,即使抽象的价值共相能够脱离具体而特殊的价值经验单独存在,也不能以其长存不灭代替生命的长存不灭。因为人之为人所期求的“不朽”,并不是要特别追求这样一种价值共相的不朽,根本上是要追求生命的不朽。所以,在唐君毅看来,价值不朽论仍然是一种所答非所问的似是而非的不朽论。
智慧不朽论认为,作为个体生命,人确实不得不死亡;但是,人的智慧则不会随着人的生命存在的死亡而死亡,而是不亡。因为人的智慧明白清晰,可上通于神灵,对神灵施爱,并进而与神灵合一;而不像肉体、情绪的存在,污浊卑下,不可能及于神灵而不朽。在唐君毅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能动智慧和理性神的思想,斯宾诺莎关于智慧之爱的观点,都属于这种智慧不朽论。唐君毅认为,智慧不朽论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诸种从精神性角度提出的不朽之论,都有诸多合理可取之处;而且,这类不朽论都明确指出,不朽问题根本上在于期求人的精神或人格的继续,因此,其相关的论述也就自然切近问题的本质。
但是,智慧不朽论和其他精神性不朽论一样,其结论终有让人遗憾的地方。首先,说智慧的存在是不朽的,没问题;但是,人要期求的不朽,并非仅仅求智慧的不朽。人固然期求智慧的不朽,但同时也期求情绪的不朽。人固然期求与神合一的智慧能够永远与神灵契合无间,但同时也希望人间世的恩爱,同样能够地久天长。其次,尽管我们也可以说,期求情绪、情感、恩爱不朽的价值不及与神灵契合的智慧不朽,但是,客观上,人也有对于情绪情感不朽的要求,这是确实无疑的。既然有此要求,那么,仅仅是智慧的不朽,就不足以满足人全部不朽的要求而满意解决不朽问题。因此,在唐君毅看来,智慧不朽论并非能够满意解决不朽问题的“完善不朽论”。
伟大人格不朽论认为,世间存在的一般庸庸碌碌之人,对于宇宙世界来说,有之不多,无之不少,对于世界的价值不能有增加,因此不免与草木一样死灭腐朽.但是,伟大的人格则因其为世界价值的赋予者,其人格有特殊的构造,可以抵抗死亡。因此,伟大的人格决不能与庸庸碌碌之人一样死灭腐朽。唐君毅认为,歌德的人格论、费希特的自我论,都属于这类的伟大人格不朽论。
在唐君毅看来,伟大人格不朽论的问题,犹如事业不朽论一样。首先,这种不朽论忽视了人全部的不朽要求。因为,伟大人格的不朽,永远只是具有伟大人格的少部分人的权利。将不朽的权利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便只足以安慰这少数人的不朽心愿。但是,就人的生命存在来说,庸俗之人与伟大人格之间,并没有截然绝对的区别,就其潜能而言,无外乎程度的不同而已。其次,客观上说,伟大人格如果不能不朽,此事确实值得人悲痛,因此,确实应该立不朽之论以化解我们的悲痛之心。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即使是一个卑贱的乞丐因饥寒而死,同样也是值得我们悲痛的事。尽管因为资质、环境的各种限制,乞丐未能将其自己与圣人同有的一点良知良能扩而充之,因而未能充分尽其性,以至于饥寒以死;但是,正因为如此,如果让其一死而永无复余,永无超拔之日,则恰恰是更加值得人悲痛悲悯之事。就此而言,唐先生认为,如果要满足人全部不朽的要求,就应该立同样的不朽之论以济此悲痛悲悯。
大我精神不朽论认为,我们每一个具体生命作为“小我”的精神虽然死亡,但是,大我的精神却仍然存在。在唐君毅看来,按照印度梵志(外道)的比喻,人犹如瓶中的一个小虚空,梵则犹如一大虚空;因此,人之死,犹如瓶碎而还入大虚空。西方思想史上的“泛神论”,近代黑格尔为代表的以绝对精神为归旨的绝对唯心论,在这一点上是持相同的主张。唐君毅认为,大我精神不朽论与前面的各种不朽论相比,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大有不可同日而语者”[1]353。一方面,宗教家多以此作为自己立论和信仰的前提;另一方面,哲学家也对此多有详细陈述的论据。近代绝对唯心论哲学,便用超越逻辑为此不朽论作了详细而深入细致的辩护。
但是,在唐君毅看来,尽管哲学家们的辩护多有鞭辟入里之论,其结论却不足以安慰人的期求不朽之心。首先,所谓大我精神虽然不朽,但毕竟我们每个具体生命的小我精神则已朽;大我的精神虽然永存,但小我精神最终却只能是暂存。所以,大我精神的不朽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小我精神的不朽。其次,如果认为小我精神为大我精神的一个部分,大我精神的存在也就等同于小我精神的存在,那么,其中就将面临如下问题:一个个体生命的死亡,是全部没入于大我精神呢还是有自我个性的保存?如果有自我个性的保存,很显然是大我精神不朽论所不允许的;如果没有自我个性的保存,则小我精神实际上是已朽的。如此,唐君毅认为,在根本上,我们是不能以大我精神的不朽来抚慰小我精神朽坏之悲痛的。
4 轮回性不朽论辨正
前面九种不朽论,分别从个体生命的物质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角度来说明生命的不朽。通过唐君毅的精微辨析,我们发现,基于物质生命的不朽论根本上是不成立的;基于社会生命的不朽论往往是答非所问,不能解决普遍个体生命的不朽期求;而基于精神生命的不朽论,从价值不朽论到智慧不朽论、人格不朽论、大我精神不朽论,尽管仍然存在一些不够自圆其说的内容,但却越来越具有更加真切地满足个体生命不朽期求的内涵。因此,对于唐君毅来说,个体生命的不朽渴望的满足,个体生命的生死安顿,不能建立在物质生命和社会生命的不朽上,根本上只能建立在精神生命的不朽上。但是,这种精神生命的不朽,不是个体精神生命的直接不朽,而是借助于轮回性不朽论的合理要素所呈现的精神不朽。为此,唐君毅对个体流转不朽论做了更为深入的辨正。
唐君毅认为,个体流转不朽论是以个体生命人格的流转轮回来诉求和表达生命的不朽,这种建立在个体灵魂流转基础上的生命不朽论,与大我精神不朽论一样,是不少宗教家与哲学家的主张,而且论据相对来说最为丰富。它能把握住人求不朽的心理,并以个体灵魂流转投胎的方式,对于此种求不朽的心理予以最大的满足。
但是,在唐君毅看来,个体流转不朽论尽管对小我的个体性十分尊重和重视,但恰恰是因为对于个体性的实际存在过分执著,以至于认为灵魂本身只是独自存在孤立无依的东西,由此就不得不面临人的灵魂流转中的一些基本困难。首先,由于这种不朽论认为每一个个体灵魂都是独自存在、孤立无依的,因此,最后势必假设,任何灵魂都没有向外呈现自己和相互联系的窗户,都只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犹如莱布尼兹所说的“单子”。由此,任何一个灵魂要认识外界,都成为不可能。其次,由于必须假设灵魂无窗户而自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因此,任何一个个体灵魂与其他灵魂的共同知识,也就成为不可能。再次,由于假设各个个体灵魂封闭而独立存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不仅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由此,必然导致人的灵魂为有限数的结论。如果人的灵魂有一定的数量,那么,就会出现十分可怕的结果:一旦人的灵魂都投生为人之后,势必会导致男女配合不能生殖的一天(因为所有灵魂都已经转世投胎,不再有须要投胎转世的灵魂)。这样的后果,是十分令人不可理解和接受的。
除此之外,唐君毅认为,个体灵魂不朽论还将面临人以外的其他生物灵魂投胎的难题。因为,如果人有灵魂,则应该承认其他生物也有灵魂;人的灵魂虽然可以全部投胎重生为人,其他生物也可以投生为人。如此,此种不朽论又不得不面临如下难题。首先,如果其他生物的灵魂也有定数,那么,也势必将有其他生物虽然雌雄配合而不能生殖的一天。如果世间真有男女雌雄配合都不能生殖之时,那么,我们实在不敢想象,此事到底将何时降临,是否于最近降临亦未必然。其次,其他生物如果投生为人,是否仍能够保持其原来的灵魂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仍然能够保持其原来的灵魂,则由其他生物投胎转世为人的灵魂中,便有来自于犬或者猴等动物的。可是,犬、猴之类动物的灵魂只能形成犬猴等动物的身体;如果犬、猴的灵魂投入人胎仍只能形成犬猴的身体,则人就应该有的生犬、猴之类动物。可是,这样的事实是不可能的,除非生物学根本不成立。如果除了保持原来灵魂外,尚须增加一部分人类灵魂,那么,这部分人类灵魂从何而来?又如何与犬猴等的灵魂相结合?这样的问题实在是无从解答。再次,其他生物如果有灵魂,那么,其他生物的生命单位存在之不可确定状况,就成为完全无法理解和解释的情况。比如蚂蟥,无论将其身体分裂为多少,其每一部分都可以单独成一蚂蟥。由此可见,主张其他生物有灵魂,对于个体流转不朽论来说,不仅不能救其难,反而是给自己增加了若干无法解决的难题。
5 不朽渴望的合理性及“完善不朽论”的期许
经过综合辨正,唐君毅认为,传统不朽论或者基于个体生命的物质性、社会性,或者基于个体生命的精神性,或者基于个体生命的轮回性,来试图说明生命的不朽,以此解决生死问题。所有这些不朽论,都有理论上不圆满的地方,因此也导致其所彰显的人的不朽要求具有一定的非正当性。也正因为如此,又出现了各种试图通过“取消”不朽问题来“解决”不朽问题的理论或者论说。不过,唐君毅认为,一切希望通过取消不朽问题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的努力,也都不可避免地陷于失败。
实际上,在唐君毅看来,这些不朽论特别是“智慧不朽论” “伟大人格不朽论” “大我精神不朽论”和“个体流转不朽论”,其持论者们都提出了不少积极的主张和论证,对于人“要求不朽”的正当性,也已经有不少具有启示性的探讨。综合来说,人的不朽要求既具有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又具有逻辑论理意义上的合理性。从道德上说,道德行为的本质,即是为了实现价值、保存价值。生命的存在,无论哪一种派别的道德学说,都必须承认其本身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本身的存在价值,也必然具有使用的工具价值。因此,作为“保存价值”的生命不朽要求,完全可以被称为正当的要求。从论理上说,人的思想行为的本质便是在变中求常,从变动不居的现象中试图把握处常不变的本质规律。既然我们能够从自然界、社会界、历史界等等各种变动不已的现象中求到常,并建立起各种各样的代表人类文明的学科,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从人的生活之变、生死之变中,求我们自己生命人格之常,自然应该是我们作为人在理性上应该有的权利。因此,人求其生命的不朽、不断灭,实质上具有伦理上的应然性和正当性。
既然人的“不朽渴望”具有道德和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那么,如何建构出能够帮助人实现其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不朽渴望”的“不朽论”呢?唐君毅提出,需要建构一套“完善不朽论”。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完善不朽论”,唐君毅基于对各种不朽论地辩正,特别提出了“完善不朽论”必须具备的八个基本条件:
①必须以人格之不朽为对象。②必须以普遍人格之不朽为对象。③不能以抽象之大我不朽漠视小我之不朽。④不能将小我视作有定数之实体。⑤应将小我只视一生命经验之焦点。然亦不能谓此焦点于死时立即散去,使小我未遂其志即消灭,而谓只有一混沦之大我生命经验存在。须同时说明生命之超过个体性及个体性如前文所举。⑥须承认个体流传有限度内之可能,并说明于何种限度内可能,且须说明投胎时与父母精神肉体之各种关系,而不悖乎各种科学所证明之事实。⑦须说明其他生物朽或不朽之原因。⑧须说明此不朽之生命经验与物质世界之关系。[1]363
“完善不朽论”的八个条件大致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和对应的答案。首先,是什么不朽?“完善不朽论”必须保证每一个个体自我的人格不朽。条件①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讲,不朽论必须建立在“人格不朽”论的基础上,以此克服物质不朽论和社会不朽论的不足;条件②进一步将这种不朽的“人格”界定为普遍的亦即所有人的“人格不朽”,而不能只是部分人的人格不朽,以此克服社会不朽论及精神不朽论的不足;条件③进一步提出不能漠视“小我”的存在,以此克服精神不朽论中最高层次的“大我精神不朽论”的不足。其次,不朽的依据何在?必须充分说明个体自我的个体性与超个体性的存在及轮回。条件④说明小我的无限性,而不能将其有限化;条件⑤说明生命存在的超个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而不能将二者对立;条件⑥强调对于个体轮回的限度、条件的科学说明,而不能没有根据的流转。最次,不朽如何具有普遍性?必须充分说明非人生命及物质世界与个体自我的关系。条件⑦强调非人生命不朽的说明,而不能只停留在人的生命不朽;条件⑧强调生命不朽与物质世界关系的说明,而不能只是生命不朽的抽象论证。
很显然,在唐君毅的期许中,“完善不朽论”应该是能够化解所有已经有的不朽论中的各种不合理及矛盾之处,能够以个体生命人格的不朽为基础而兼及普遍人格、其他生物及整个物质世界的不朽,而在“不朽”的方式上则表现为个体生命人格的有限流转。当然,唐君毅也非常清楚,要同时符合这样八项条件,是十分艰难甚至是天底下“最难之事”。因为,要完全符合和满足这样八个条件,必然引起无量的矛盾观念;如果这些矛盾观念不能完全相互契合,此不朽论便不可能是“完善”的。可是,另一方面,唐君毅又特别强调:“如果不一一经度此八条件,终难造成完满之不朽说。”[1]363因此,即使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也必须要去经历和面对。
当然,提出这一“完善不朽论”期许的唐君毅,还只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而且是一位刚刚经历了“几欲自杀”和失去父亲的生命困顿而从中超越出来的智者。此时的唐君毅,尽管智慧和心气都已经非常人所比,但他自己也依然不敢说就可以承担此天下重任,而只是提出期望,发出疑问:“孰有愿本此八条件以建立一不朽说者乎?予企望之矣!”[1]363但是,正是这一发问和期望,让唐君毅本人的全副生命和理论思考都始终围绕在这一“完善不朽论”的建立上,并以其全副生命和理论思考做出了精彩的回答。从《人生之路》十部到《人生之体验续编》《病里乾坤》,再到《哲学概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唐君毅逐步完成了他的生死哲学的形上理论建构,在立足于儒家生死观的基本立场基础上,整合佛教及西方哲学的生死理论,并为了解决现代人的生死困顿,提出了以实现“不朽要求”为目标、以“心灵生命”为基石,以“立三极”(人极、太极、皇极)、“开三界”(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人文世界)、“存三祭”(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为归旨,以“生死呼应”、“生死感通”为根本的一套性情化的生死哲学理论,完成了其“完善不朽论”的理论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