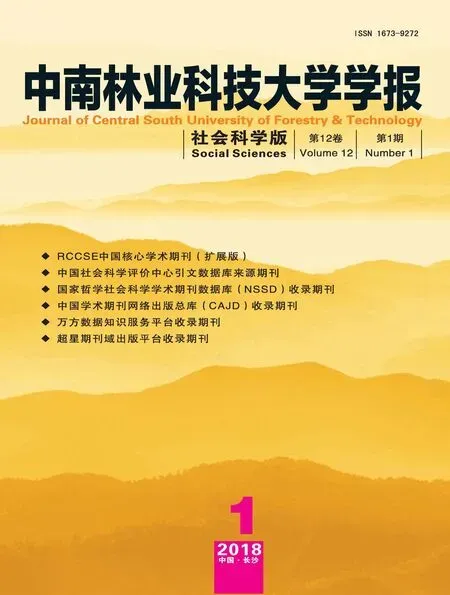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
——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2018-01-25王仁祥郭联邦
王仁祥,郭联邦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017年1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该文件在招商引资方面,不仅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以制定优惠政策,还鼓励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积极承接外资产业转移。自2004年中央首次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到2017年湖北自贸区、河南自贸区挂牌成立,中部地区发展始终是国家层面的重点战略。历次战略无一不强调中部要提高承接国际和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落实好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系列任务及要求。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日益突出,愈发成为国内外的关注焦点。在地方政府竞相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是否会为了提高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而主动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接纳更多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入?特别是我国中部地区,较东部有更低廉的地价和劳动力,较西部有更便利的交通及更大的市场,是东部和海外产业转移的理想选择。本文使用我国中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提出了“产能准入环境成本”的概念,基于其和环境监察两个角度测算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环境规制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原因吗?它们之间存在动态影响吗?政府如何制定环境规制才是真正有效的?
一、文献回顾
解释产业转移现象的经典理论有产品生命周期论和边际产业论等,比较优势原理和HO理论是基本分析范式。随着工业化加深,污染物在空间上的迁移态势受到广泛关注。由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活动是工业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因此这类产业的区域间转移成为了学界探讨的焦点之一。“污染避难所”效应(Pollution Haven Effect, PHE)认为,环境规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要素禀赋,如果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存在环境规制上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将对重污染企业建厂择地产生边际影响。因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加重了企业的环境成本,降低了产品的比较优势。所以,若贸易壁垒下降,那么污染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向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转移[1-3]。
许多学者尝试验证污染避难所效应在污染产业国际转移中的有效性。Levinson等[4]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发现,美国环境规制的相对提高致使进口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污染产品增加。Mulatu等[5]对欧洲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国家吸引了污染产业转入。但是,Ederingtor等[6]研究指出关税壁垒降低没有刺激美国的污染产业向海外转出。Marconi[7]考察了欧盟与中国的贸易结构,认为没有证据支持中国成为了欧盟的污染避难所。
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规制上存在一定差异,污染产业的区际间转移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一些研究发现省际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刺激了污染产业转移[8-9]。然而,部分研究并不支持污染避难所效应[10-11]。此外,也有学者指出PHE效应只在我国中部存在,东西部没有体现[12]。
之所以上述研究结论各异,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一方面,对环境规制的测量角度单一且欠缺准确,尤其没有考虑王勇和李建民[13]指出的省际间可比性偏差;另一方面,将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假设为线性关系,忽略了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总之,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仍未确定,污染避难所效应在我国区域间的检验并无定论,并且对具体区域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产能准入的环境成本和环境监察两个角度衡量不同省份的环境规制水平,在可比性偏差调整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其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为政府合理运用环境规制工具,以及污染产业的有序转移提供建议。
二、变量、数据与计量模型
(一)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分类
污染密集型产业是工业污染物排放集中的部门,环境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企业。遵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傅京燕和赵春梅[14]使用我国制造业的排污数据计算得出各行业污染强度值,确定了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制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5个大类行业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古冰和朱方明[15]、赵细康和王彦斐[11]通过计算污染排放强度认为,除制造业以外,采矿业门类中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亦隶属该类产业。笔者采用了以上划分结果,上述10类两位码分类行业属于我国现阶段的污染密集型产业。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用各省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值占污染产业全国总产值的比重(Y)来衡量产业转移。某种产业区际转移的结果必然是转出地产值的减少并转入地产值的增加[8]。虽然某地区产业产值的增长不一定来自于国内转移,也可能是新建企业产能、老企业扩大产能,或来自境外转移,但笔者认为后三者是一种隐性的产业转移,说明该地区具有某些吸引企业落户、产能增长的比较优势或区位因素。数值愈大表明该地区污染产业的分布集聚愈明显。数据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各省的环境规制水平。环境规制是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干预,它体现于政府对企业减排及承担环境负外部性成本的要求上,反映了政府为了减少污染物排放及改善环境所作的努力[16]。如何恰当地衡量环境规制是学界广为关注且饱受争议的问题。使用地区单位工业产值的污染治理投资额以表示环境规制是最常见的方法[17]。但由于不同地区间产业结构及产能分布存在很大差异,该方法存在严重的省际可比性偏差。因此,本文构建了两个指标,分别从产能准入的环境成本和环境监察的角度衡量各省的环境规制力度,具体说明如下:
一是产能准入的环境成本(ERI_a)。当今,环境影响评价是世界各国环境管理体系的基本制度之一,被视作控制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手段而广泛应用。近年来,作为环境行政审批的重要环节,环评制度在我国的覆盖面和受重视程度逐步加大,污染产业的大多数新建产能和扩建产能,都必须由环保部授权的专业机构进行完整的环境影响评估。《中国环境年鉴》披露了每年各省份环保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和环保投资额,由于后者对企业的生产及排污环节起直接作用,所以环保投资额占项目投资总额之比可以衡量各省的产能准入成本。但是,考虑到环评制度不仅要求于污染密集型产业,轻工业、城市基础设施等非污染密集产业也被要求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由于省际间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如果某地区以轻工业为主,则环评审批时对环保投资的要求就偏少。若不对指标进行修正,则会低估非污染密集产业集聚地区的环境规制,反之亦然。因此,笔者借鉴了王勇和李建民[13]的方法,用各省污染物排放量占当年全国总量的比重对分子进行平减,从而得到一个去量纲的值,公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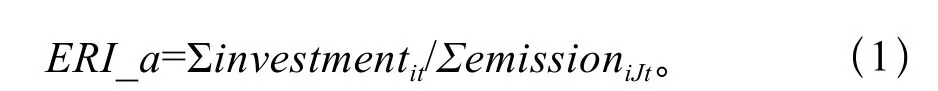
Σinvestmentit为t年i省所有通过环评审批的建设项目中的环境保护投资额占建设项目投资总额的比重。
ΣemissioniJt为t年i省J类污染物(J=1,2,3,分别代表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排放量的平均比重。
这一变量站在企业成本的角度,考察了政府对企业降低排污及执行清洁生产的要求。数值愈大,表明该地区行政上的产能准入成本愈高,即环境规制愈强。同时,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许会呈现出“U型”或“倒U型”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引入产能准入成本的二次项(ERI_a2)以进一步考察。
二是环境监察力度(ERI_b)。环境监督执法是政府环保部门的重要职责,政府对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违反环境保护规定事件的监察惩处力度是环境规制的重要体现。《中国环境年鉴》披露了每年各省份环境监察部门的本级行政处罚案件数,本文用它表征环境执法力度。同样地,由于各地区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分布集聚存在差异,并考虑到产业集聚效应,本文选取了规模以上污染产业企业单位数进行修正。即:

数值愈大,表明该地区环境监察越发严厉,即环境规制愈强。同样地,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引入环境监惩力度的二次项(ERI_b2)进行解释。以上两个环境规制变量的数据均源于历年《中国环境年鉴》。
3.控制变量
除环境规制外,还存在许多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经济因素。为减少统计偏误,本文将一些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从扰动项中分离出来单独控制,具体说明如下:
(1)地区市场容量(GDP)。由于不同地区间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差异较大,市场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发展,也决定着地区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因此,本文用各省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
(2)地区基础设施(BID)。“要致富,先修路”,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条件左右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企业的原料和成品的物流速度和物流成本,因此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对企业建址布局选择起关键作用。本文用各省交通密度来衡量基础设施状况,即:(公路里程数+铁路营运里程数+可航运内河里程数)/土地面积。
(4)地区劳动力价格(UAW)。因为用人成本是企业所背负的主要成本之一,所以若企业转入劳动力较低廉的地区,则可于一定程度上节约成本,进而赢得更高的收益。本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衡量指标,并使用平均实际工资指数对通货膨胀进行修正。
(5)地区科技研发水平(RD)。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但能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扩大收益,而且还是降低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实现清洁生产的根本手段。一方面,转入产业可在某种程度上吸收、利用当地的技术创新成果;另一方面,一些产业转入落后地区也可能为后者带来技术溢出。本文用各省R&D投入强度作为衡量指标。
控制变量数据均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计量模型
参照相关文献和理论体系,并根据上述定义的变量,面板回归模型如公式(3)所示: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度;μi表示省际间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而变的异质性,即个体效应;γt为不同年度间中部地区所共有的不可观测因素,即时间效应;εit为扰动项。由于现期产业转移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期众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即自变量的时间范围为2004-2013年,因变量为2005-2014年。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与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序列不平稳导致的伪回归,本文首先进行文献中广泛使用的LLC和Fisher-ADF面板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由表1可见,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均已平稳,此时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进行协整检验,考察可能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首先,笔者借鉴王恕立和王许亮[18]的方法,对因变量和所有自变量进行KAO检验;其次,再对因变量与核心自变量进行Johanse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协整检验
由表2可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假设检验强烈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因变量与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可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
(二)计量回归及结果分析
理论上,不同省份、不同年度间一般具有众多不可观察的异质性,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加以控制。统计上,本文先后进行了F检验(原假设为混合估计模型, p值为0.00)、Hausman检验(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 p值为0.00),即分别强烈拒绝了原假设,支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另一方面,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等问题,本文先后进行Wald组间异方差检验(p值为0.00)、Wooldridge序列相关检验(p值为0.00),以及Breusch-Pagan LM截面相关检验(p值为0.10),结果表明均不同程度上存在上述问题,其中异方差及序列相关尤为严重。因此,笔者使用Driscoll & Kraay[19]提供的修正标准误进行回归以处理上述问题。模型1至4即为使用D-K标准误的回归结果,模型5为O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的确,CBA联赛23年,山东男篮的东家一直都是总部位于济南的企业,绝大多数时间,其主场也一直位于省会济南,城市与俱乐部的关系密切、深厚。

表 3 计量回归结果†
总体来看,不同模型中,各变量的符号均保持一致,系数的显著性差异较小,方程整体非常显著;并随着解释变量的增多,R2逐步增大,模型设定良好。
基于产能准入成本的环境规制(ERI_a)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中部六省存在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效应。结合二次项系数发现,产能准入成本对污染产业转入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曲线形式,现阶段中部地区位于曲线极值点的左侧。即随着地方政府提高产能准入成本,污染产业仍将继续转入;当越过极大值点后,污染产业转入开始放缓停滞,进入关停或转出阶段。之所以出现这种倒“U”型关系,是因为就中部地区而言,现阶段环境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处于较低水平,生产运作有利可图。所以即使提高新增产能的环境成本,污染产业仍将继续转入。但如果政府不断提高这一环境规制,使得环境成本成为了重污染企业的明显负担,那么污染产业将不再转入并逐渐停产。
基于环境监察力度的环境规制(ERI_b)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再次得到印证。结合二次项来看,环境监察对污染产业转入的影响表现为“U”型曲线关系。目前中部六省位于“U”型曲线的左侧,即随着环境监惩力度的加大,污染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关停或转出;当越过极小值点后,污染产业仍将继续转入,使得中部地区再度成为污染的“避难所”。这说明了,由于我国环境监察的标准较低,且环境执法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技术条件较差、治污能力较差的产能,所以对于成规模的产能并无有效的威慑作用。虽然当前的监察力度起到了污染治理的效果,但未来仍需执行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
地区市场容量(GDP)系数为正但较不显著,表明市场因素对污染产业转入具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日趋式微。作为一种传统的区位因素,市场容量与有效需求密切相关,对重污染企业的选址布局起到一定影响。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中部地区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国内贸易方便快捷,所在地市场规模因素对企业的作用逐步下降。
地区基础设施(BID)系数为正且尤为显著,说明转入地的交通条件对产业转移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基础设施是工业活动的血液,原料、成品的境内流动均依赖于交通运输网络。并且随着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生产要素在省际间的流动加快,原料、市场等要素禀赋的重要性趋于弱化。
地区产业结构(IND)系数为负且尤为显著,印证了产业发展的一般经验规律。地区的服务业越发达,则对具有重工业特征的污染密集产业的依赖度相对越低,地方政府的招商压力较小,同时也会趋于制定更高的环境规制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劳动力价格(UAW)的系数为负,虽然在一些模型中显著,但这一结果并不稳健。随着我国劳动力价格的整体提高,劳动力成本始终是企业选址和产业转移时考虑的一大因素。但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成本负担较低,因此其对这一成本相对较不敏感性,这也是导致显著性结果不稳健的原因之一。
地区科技研发水平(RD)系数为负且显著,这一结果与预期相背离。虽然在现代经济学中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本文却发现地区科研优势与污染产业转入此消彼长。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科研投入强度大的地区高新产业发达,对重工业依赖度低,同时政府为了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而提高环境规制。另一种原因可能是污染行业企业在转移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所在地的技术溢出效应,研发和应用未能衔接。这也说明了技术进步对污染产业整体发展的贡献很小,后者可能仍然依赖于资本积累驱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使用2004-2014年我国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其他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中部存在显著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对环境规制力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存在非线性动态影响。基于产能准入成本衡量的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产业转入呈倒“U”型关系;而基于环境监察力度衡量的环境规制则与其呈“U”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地区科研投入强度与产业转移负相关,污染密集型产业吸收技术溢出效应的效率较低。
(二)政策建议
1.提高环境成本标准,加大环境监察力度
现阶段,环境成本占企业真实成本的比重仍处低位,政府可进一步加大产能准入成本,虽然短期内环境成本的上升仍将驱使污染产业转入,但越过倒“U”型曲线极大值点后,重污染企业将因所在地环境成本优势丧失而放弃转入。具体来说,政府有下述几点可为:首先,严格保证污染产业新建、扩建产能的环境影响评价实现百分百执行,捍卫环评制度的贯彻实施;其次,环保部门可适当提高环评标准,在技术水平可行的条件下,要求重污染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如引进新设备提高二氧化硫、氨氮等关键污染物的去除率;进而,坚决关闭落后产能、非法产能,打击权力寻租行为,将其中的生产要素转移到符合环境标准的企业中来,从而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及保证中央政府决策落实到实处;再次,现阶段仍需继续加大环境监察力度,但必须清楚认识到,关停、罚款并非一蹴而就,支持企业引进治污设备、加大环保研发才是根本手段。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企业的总体成本负担较重,提高环境成本的同时,政府需加快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等非必要成本的步伐。
2.兼顾不同的规制手段,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力度
从普遍性出发,政府需充分利用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的区际转移加以控制和引导,避免中部地区沦为重污染产业的“避难所”。并针对污染密集型产业中不同子行业的特点,兼顾具体子行业的特殊性和各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差异,制定相应的环境规制水平,使各行业对经济发展的边际贡献不低于其边际环境负外部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发现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经济效果具有动态影响,这也许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1]Walter I, Ugelow J 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Ambio,1979,8(2/3):102-109.
[2]Copeland B R, Taylor M S. Trade,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42(1):7-71.
[3]张友国. 碳排放视角下的区域间贸易模式:污染避难所与要素禀赋[J]. 中国工业经济,2015(8):5-19.
[4]Levinson A, Taylor M S. Unmasking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8, 49(1): 223-254.
[5]Mulatu A, Gerlagh R, Rigby D, et 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y location in Europe[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0, 45(4):459-479.
[6]Ederington J, Levinson A, Minier J.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llution havens[J].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2004,4(2):1330-1330.
[7]Marconi 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Europe: is China a pollution haven[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20(3):616-635.
[8]侯伟丽,方 浪,刘 硕. “污染避难所”在中国是否存在?——环境管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3(4):65-72.
[9]何龙斌. 国内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路径及引申——基于2000—2011年相关工业产品产量面板数据[J]. 经济学家,2013(6): 78-86.
[10]杨仁发.产业集聚能否改善中国环境污染[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25(2):23-29.
[11]赵细康,王彦斐. 环境规制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转移吗?——基于广东的阶段性观察[J].广东社会科学, 2016(5):17-32.
[12]彭可茂,席利卿,雷玉桃. 中国工业的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基于2002—2012年工业总体与特定产业的测度与验证[J].中国工业经济,2013(10):44-56.
[13]王 勇,李建民. 环境规制强度衡量的主要方法、潜在问题及其修正[J]. 财经论丛,2015(5):98-106.
[14]傅京燕,赵春梅. 环境规制会影响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吗?——基于中国面板数据和贸易引力模型的分析[J]. 经济学家,2014(2):47-58.
[15]古 冰,朱方明. 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动机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2013(3):66-70.
[16]黎 敏. 协同治理视域下企业环境管理机制创新研究[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4):13-16.
[17]张 成,陆 旸,郭 路,等.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124.
[18]王恕立,王许亮. 双向FDI的生产率效应研究——基于中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29(5):883-890.
[19]Driscoll J C, Kraay A C.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80(4):549-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