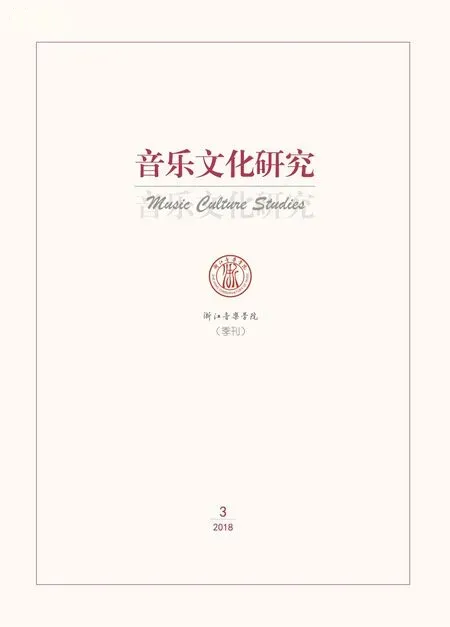南宋临安市民音乐文化的形成机制研究*
2018-01-24王菲菲
王菲菲
内容提要:南宋临安的音乐经历了由从北宋到南宋的过渡,其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世俗性变化和世俗化特征,影响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了宫廷对音乐的掌控能力、城市格局的变化、商业的发展、社会阶层、地域环境、政治时局、民众心理等诸多方面。
南宋是临安作为都市发展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的音乐发展过程中,南宋临安的各类音乐形式呈现出了新的区别于北宋的变化,甚至可以说获得了质的飞跃,而整个南宋时期临安的音乐所体现出来的更是融合性、叙事性、程式性、当代性、现实性等世俗化的特点。这些我们视为宋代音乐的世俗化转型的标志几乎都在南宋临安得以完成。而影响南宋临安音乐世俗化转型的主要因素包括了宫廷对音乐的掌控能力、城市格局的变化、商业的发展、社会阶层、地域环境、政治时局、民众心理等诸多方面。
一、宫廷音乐规模的缩减及宫廷对民间音乐的宽容态度
经过了宋金战争的极大破坏、偏安江南行在之后,南宋政权开始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此时对宫廷内外的音乐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内极力恢复雅乐古制,取消宴乐机构而改向民间雇用,对民间则给予了更大的自由度和宽容度,改官方组织而变为民间自发组织音乐活动,同时也允许民间音乐跟随民间艺人们进入宫廷。这样的政策和态度无疑是南宋临安音乐文化世俗化转型的绝佳契机。
(一)南宋宫廷音乐规模的减缩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载:“(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败盟,分兵两道入,诏革弊事,废诸局,于大晟府及教乐所、教坊额外人并罢。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取汴,凡大乐轩架、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虡、九鼎皆亡矣。”这段记载可以说是南宋宫廷音乐自北宋以来发生巨大变故的真实而全面的写照。随着北宋政权统治的结束,其宫廷音乐歌舞机构和力量也几乎一并消亡了。在南宋建国之后的恢复和调整中,音乐实践、音乐制度、音乐管理等层面都出现了新的格局。
1.宫廷乐人、乐器、乐章的散失与恢复
经过了北南宋之交宋金战争的洗礼,宫廷乐人、乐器和典章大量散失,这对南宋宫廷音乐的重建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和阻碍。宣和七年(1125年)12月,金国破坏盟约,分兵两路入侵,宋徽宗下诏改革弊政,废除各局,在大晟府以及教乐所、教坊里的额外人员全部都被罢免了。①北宋遗留的宫廷乐人、乐器、典章,除了在战乱中大量流失民间之外,另一方面又被金廷掳去了相当数量。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载,攻破宋都开封之后,金人数度来索人、物无数,并将其押解至金之南京,即现在的北京,从掳去的清单来看可谓事无巨细,无一不收。
南宋之初,宫廷开始着手音乐组织和制度的恢复,其中的重点就是恢复礼乐制度,但是由于战乱的破坏,南宋的雅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处在残缺不全的状态之下,因而期间也遇到了不少人力和物力上的缺遗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三:
一是乐器的阙少。“绍兴元年,始飨明堂。……太常卿苏迟等言:……今亲祠登歌乐器尚阙”,“十四年,太常寺言:‘将来大礼,见阙玉磬十六枚。’”在这样的情况下,太乐局只能寻找一些应急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比如祭典中缺少乐器,就借用军队中的军用大鼓;登歌、宫悬的乐器数量不足,就让登歌的乐器同时作为宫悬的乐器;并且从太常下至两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至广东西、荆湖南北,搜集过去所用的雅乐乐器。
二是文武之舞容的遗失和舞工的缺少。由于靖康、建炎的战火纷乱,雅乐乐舞艺人流离失所,乐舞图也随之消亡。因此文、武二舞的舞容几乎失传。“十年,太常卿苏携言:‘将来明堂行礼,除登歌大乐已备,见阙宫架、乐舞。’……丞周执羔言:‘大乐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将下任道,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深知舞仪,宜今赴寺教习。’”②学会了舞容之后,舞工的数量又成了问题,太常寺就曾出现向钧容直借用舞工的情况,“绍兴十二年钧容直所言:‘准太常寺差借钧容直九十八人充登歌二舞执色人祗应。’”③
三是乐工的匮乏。“嘉定二年,明堂大飨,礼部尚书章颖奏:‘太常工籍阙少,率差借执役。’”④解决的方法一方面是寻找旧有的乐工,即“乃访旧工,以备其数”⑤,另一方面则是所说的“率差借执役”,也就是派差借用民间的乐人来服役,而且只要“行止畏谨之人”⑥都被收罗其中。
从恢复的情况和措施不难发现,南宋礼乐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了。乐器和乐工不再具有雅乐专属的性质,因为他们有的来自军中,有的来自民间各地,就算是前朝宫廷的乐人也是在民间混迹多年很难保持雅乐的纯正,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宋宫廷雅乐很有可能沾上浓重的俗乐意味。
2.宫廷音乐机构的重建与废止
南宋在江南建立伊始,仍然保留了太常寺管辖下的太乐局和鼓吹局以及钧容直,但是它们在建炎的离乱中已元气大伤,数量骤减。如钧容直的人数由北宋时的二三百人,降至此时仅存的九十余人。此后,太乐局一直维持到南宋末期的德祐二年(1276年)。钧容直则无此幸运,绍兴九年(1139年),殿前副都指挥使杨存中请求收补钧容直人员,权以旧管之半即二百人为额,寻闻其召募骚扰百姓,降诏止之,绍兴三十年(1160年),复诏钧容直可省蠲。⑦
而负责宴乐表演的教坊及其监督管理机构钤辖教坊所则从南宋一开始就干脆被减省了。“高宗建炎初,省教坊。”⑧“绍兴、乾道教坊迄弛不复置云。”“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⑨直到绍兴十四年教坊复置,“凡乐工四百六十人,以内伺充钤辖。”其官属及隶属关系与北宋略同。然而好景不长,绍兴末复省教坊,“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即日蠲罢,各令自便。”⑩《宋史·乐十七》又记:“绍兴末复省。乾道后,北使每岁两至亦用乐,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原教坊的乐工则被遣散到德寿宫或临安府衙前乐等处供职。此后,教坊对于南宋来说已成昨日黄花,再也没有被设立过。南宋宫廷教坊体制存在的时间也只在绍兴十四年(1144年)至三十一年(1161年)这18年间。而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皇帝还命罢专演宫廷队舞的小儿队及女童队。⑪
教坊虽已省蠲,但宫廷中仍有不少需要使用宴乐的场合,那么又由谁来承应呢?其实,南宋废教坊,只是罢其职名,分散了乐工,每有宴席表演都是临时点集德寿宫、衙前乐和民间艺人临时排练。据《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记载:“绍兴三十一年,省废教坊之后,每遇大宴,则拨差临安府衙前乐等人充应,属修内司教乐所掌管。”可见此时的教乐所只是一个负责召集人员的行政机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机构,其属性从实践音乐表演而变成了组织音乐活动。
(二)南宋宫廷对自身及民间音乐的态度
1.对宫廷音乐的俭省、复古的态度
南宋的皇帝对于宫廷用乐的态度大多比较克制,崇尚的是“俭省”的原则。高宗南渡,经营多难,感伤颠危,曾一度禁作歌舞。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庚辰,“以二帝未还,禁州县用乐”⑫;二年(1128年),复下诏曰:“朕方日极忧念,屏远声乐,不令过耳。”⑬即便到了南宋中期,偏安局面已然形成,礼乐之事再度兴起,但统治者信奉的仍是“一切多简”的原则。“帝尝以时难备物,礼有从宜,敕戒有司参酌损益,务崇简俭。……令登歌通作宫驾,其押乐、举麾官及乐工器服等,蠲省甚多。”⑭而宋孝宗更是出了名的“务从省约”,这从孝宗年间的太常卿洪适的请奏中就可窥见其端倪:“圣上践祚,务崇俭德。……今乐工为数甚伙,其卤簿六引、前后鼓吹,有司已奏明,诏三分减一,惟是肄习尚逾三月之淹。夫驱游手之人振金击石,安能尽中音律,使凤仪而兽舞?而日给虚贵,总为缗钱,进二钜万。老从裁酌,用一月教习,自可应声合节,比至阙事。”⑮
南渡之际,雅乐受到了重创,“渡江旧乐复皆毁散”。直至四年后的绍兴元年(1131年)才恢复雅乐,“始飨明堂”⑯。随着偏安局势的形成,南宋宫廷开始逐渐恢复礼乐之事,其中最受重视的则是雅乐的登歌与宫悬,并掀起了雅正古乐的复古潮流。绍兴四年(1134年),国子丞王普进言,明确提出恢复雅乐先章后谱的古制,曰:“盖古者既作诗,从而歌之,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自历代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崇宁以来,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乞复古制。”⑰绍兴十年(1140年),太常卿苏携进言:“将来明堂行礼,除登歌大乐已备,见阙宫驾、乐舞,诸路州军先有颁降登歌大乐,乞行搜访应用。”⑱其后,礼部侍郎施垧奏曰:“礼经蕃乐出于荒政,盖一时以示贬抑。昨内外暂止用乐,今徽考大事既毕,慈宁又已就养,其时节上寿,理宜举乐,一如旧制奏。”⑲南渡后用以陈设礼乐之器,举行阅习仪式的太常寺,也得以重修增葺。20
相对礼乐的恢复,南宋宫廷对于宴乐则采取不设专门的机构、由教乐所临时召集应承的政策,凡皇帝寿诞和其他喜庆日子以及接待外国使臣、举行乐舞活动之际,一律采取向宫廷外雇请演员的办法,把地方官伎和民间伎人集中起来排练一段时间,以便届时供奉御前供应。
2.对民间音乐控制力的减弱和宽容度的增加
南宋宫廷对于民间音乐的宽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放弃宫廷操办的方式,改由民间自发组织南宋临安的民间音乐活动;二是以“和顾”的形式允许南宋临安的民间艺人大量进入宫廷演出,从而将民间的音乐一并带入。
南宋节日的庆贺与北宋官方举办的方式不同,多为流动性舞队的演出,更重要的是这些舞队是由民间的演员演出、由民间力量自发组织的,朝廷在这里只起到监督和维护的作用,同时对民间的这些演员加以犒赏,表现的是一种支持的态度,这和北宋的官方组织有着显著的差别。《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载:“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至节后,渐有大队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于盛,其多至数十百队。天府每夕差官点视,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升旸宫支酒烛,北至春风楼支钱。终夕天街鼓吹不绝……”
南宋民间艺人们被宫廷或官府应召称之为“和顾”,瓦舍勾栏中的民间艺人在节日、宴享或使节来访等情况下被召入宫廷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而,南宋时期临安瓦舍的隶属非常明确,周密《南宋市肆记》中说:“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这样使得宫廷能够及时而且方便地召集和组织瓦舍内的艺人们随时进宫承应。比如,“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而廷绅祝颂,务在严恭,亦明以更不用女乐,颁旨子孙守之,以为家法。”21这里的“杂攒”指的就是民间的艺人,他们被充作教坊的名号在宫廷中临时演出。又如,南宋时金国的使节来访时,宫廷也请了民间的艺人来应承。“乾道后,北使每岁两至,亦用乐,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22《梦粱录》曾记载一次教乐所的用乐情况,其中“和顾”人数最多,达157人,其次是“衙前乐”120人、“德寿宫”35人,最少的是“前教坊”和“前钧容直”,均为13人。
使用民间艺人演出在南宋甚至已经侵入到了雅乐的表演中,这引起了宫廷礼部的关注。嘉定二年(1209年),礼部尚书章颖上奏,请求重申绍兴年间、开禧年间已经实行的禁令,不许用民间的人顶替祭祀雅乐中的表演职司,明白地禁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使在祭祀时服役的人无论职位大小都严肃整洁,以便和精诚的祭祀相称。23
除了临时召集民间艺人入宫应承各类大小演出之外,还曾经出现过将城市瓦舍勾栏里的艺人完全调入宫中的情况。据《武林旧事》记载:“丁未年拨入构栏弟子,嘌唱赚色施二娘,时春春,时住住,徐胜胜,朱安安,陈伴伴等十四人。”如此一来由宫墙之外带入宫墙之内的世俗气息是越来越浓重了。
二、以商业为杠杆推动音乐的世俗化发展
临安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各个层面的变化是导致其音乐文化性质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城市商业在两宋期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入南宋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24南宋的临安成为一个偏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的消费型的商业城市。25在南宋的城市化进程中,对音乐文化造成最大影响的是城市化的发展所带来的音乐表演者、音乐欣赏者、音乐表演的性质、音乐表演的场所、音乐表演的时间等因素的变化。
(一)艺人和观众
1.适应不同阶层需求的艺人结构及专业分工组织的出现
从临安艺人的地域来源看,除了临安旧有的音乐表演者之外,随高宗南迁以及战争中逃亡而来的北方艺人也大量在临安城中聚集,其中包含了原北宋宫廷中的乐师、乐工,还有开封等北方地区各瓦舍中的乐舞艺人,如北宋名妓李师师靖康之变后流落江南,仍以卖唱为生。还有南方各地的艺人们也纷纷来到行在之所,例如苏州名妓钱三姐、七姐、文字季惜惜等,婺州张七姐、蛮王二姐、搭罗邱三姐等从江南诸州郡进入临安的艺人。26戏文由其发源地永嘉而来到临安并且流行开来,想必就是由于温州戏文艺人的流动而到来的。又如鲍老社会有福建和四川的地域之别27,也很可能是由于分别由这两个地域而来的演员组成表演鲍老的社会而得名的。这种艺人四方汇聚的情况下,一方面促成了南北音乐之间的极大融合,另一方面也把更多新的音乐形式带到了临安,从而促进了南宋临安音乐的发展。
就艺人的表演针对不同阶层人群的角度来看,南宋临安城市中的艺人总体上应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学习和表演歌舞、器乐、诗词演唱为主的乐伎,以女性为主,如“爱爱,姓杨氏,本钱塘娼家女。年十五,善歌舞”28。她们的表演常与宫廷、贵族、士大夫等阶层密切联系,场合多为宫廷、官府、贵族、士大夫等筵席之中,或者歌楼、酒馆等处。另一类是以演出说唱、戏曲等民间世俗音乐为主的民间艺人,其演出的对象往往是普通的市民百姓,场所主要是瓦舍勾栏甚至城中任意的热闹宽阔之处。由于音乐表演职业化和商品化的出现,以及受众的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南宋民间艺人的数量骤增,已经成为表演力量的主体。南宋临安城中艺人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记载最多的是周密的《武林旧事》,共记载各类艺人一千一百余人。
还有些民间艺人不在一定的勾栏内演出,任何宽敞热闹的地方都是他们的剧场,“如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岐人在此作场,尤为骈阗。又皇城司马道亦然,候潮门外,殿司教场,夏月亦有绝伎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场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桥药市、橘园亭书房、城东菜市、城北米市,其余如五间楼福客糖果,所聚之类,未易缕举。”29这一类艺人的演出方式在南宋临安被称为“打野呼”或称“打野泊”30。这些路岐人多半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不得不靠卖艺来维持最低的生活,因而其社会地位处于艺人的最下层31,这种现象也可以说是城市化发展中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必然,伴随路歧人行为的是社会人口和表演伎艺的巨大流动,这有利于不同的音乐样式和风格在南北、城乡间获得交流,例如说唱音乐陶真就是靠路歧“村人”在临安传播开来的。32
南宋音乐艺人专业化首先表现在分工相当的细致,《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中列有诸色伎艺人达五十五种之多,其中与音乐有关的条目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是艺术分工不断细化的必然结果,是行业自觉意识的重要表现,也是南宋临安音乐专业化高度发展的体现。音乐表演的组织称为“社”,是与工匠行会之“作”、商业行会之“行”“市”“团”相对应的,因而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它们与工商业的行会颇为类似。其主要功能,一是做好行内的协调,出现了“社条”行规33,制定行业规范,约束成员遵守职业道德,并有社首、班首等行会头领34;二是应付官府的差事与和顾,为宫廷、官府、驻军提供演出服务;三是参与和组织大型社会表演活动,如临安城中经常举行的节日舞队表演等。《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载南宋时临安的社会“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鞠)、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对艺术经验的交流、传授与艺术水平的提高起了良好的作用。
2.内涵广泛的观众结构
南宋临安城中,在瓦舍勾栏、茶楼、酒馆等演艺集中的场所参与观赏的观众几乎包括了整个城市居民结构中各个阶层的人们,上有南宋君,下有富家豪门,帮闲请客,士大夫和读书士子亦大量积于江南地区,“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于此地。”35而大批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一类的市民阶层,为数不少的西北驻军更是其间的中坚力量。就所属阶层的不同,这些观众的观赏聚集地也有所不同。
南宋临安城中的市民阶层是演艺欣赏者的中坚力量,以小商业主、手工业主、店员、手工业工人、各类役使伎艺人为主要成分的市民阶层空前地壮大起来,成为社会音乐活动、表演的主要参与者和欣赏者,为南宋临安娱乐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极大带动了娱乐消费。临安的人口在南宋时期急剧增加,最大的因素是大量的北方移民。靖康以来的北方人口南迁规模极大,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汉人南迁的第三次高潮,“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36。这些北方移民大大充实了临安的城市人口,城郊一再扩大,而这众多的人口为临安的音乐表演带来了一批批的欣赏者和推动力量。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妓乐”条,在述说了杂剧演出状况之后,说:“今士庶多从省,筵会或社会,皆用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处散乐家。女童装末,加以弦索赚曲,祗应而已。”可见当时临安的士家是音乐演出的主要欣赏者之一,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支持者,而他们需要演出则主要是依靠瓦舍等处的民间艺人。士庶文人除了将演出搬入自己府中,他们参与观赏音乐演出的地点主要是在酒楼、妓馆等场所。瓦舍勾栏虽然是临安城娱乐最为集中之所,但是士人似不太方便出入,然也有偷偷前往者,常常改装而掩人耳目,如宋人郭彖所载“士人便服,日至瓦市观优。有邻坐者,士人与语颇狎”37。
南宋时临安附近曾屯驻了大量军队,南宋军队(特别是前期)主要来自北方,如以一军人有家二口计,军人和家属约可达二十万人左右。38据说为了解决这些军士的闲暇娱乐问题,在临安城内、外建立了瓦舍,而这些瓦舍的位置常常被安置在军队驻地的附近,比如临安城赤山埠南步寺后军寨前就有赤山瓦子39。可见南宋临安城的驻军成为音乐娱乐的主要力量之一,而他们的观赏之地主要是瓦舍。
(二)音乐表演
1.音乐表演的商业性本质
所谓文艺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就是音乐歌舞的表演成为一种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并且要通过与金钱的交易来实现这个价值。也就是说音乐歌舞的表演不再是自娱性的,也不再是无偿的,观众要入勾栏观看演出就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这种现象在南宋临安城中是普遍而广泛的。
杜仁杰《庄家不识勾栏》中,以戏谑、调侃的口吻描述了一个乡下人进城看戏的境况,其中有“见一个人手撑着一个椽做的门”,“要了二百钱放过咱”等句子,说明看戏是需要买入场券的。另一种音乐演出的收费形式是在开场或演出过程中,由演员向观众逐个讨赏。“宋人凡勾栏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说大意,以求赏,谓之‘开呵’。”40《南宋志传》第十四回中,大雪小雪在南京御勾栏演唱:“大雪先唱一曲,名〈浪淘沙〉……小雪继唱一曲〈蝶恋花〉……大、小雪唱罢新词,台下子弟无不称赞。小雪持过红丝盘子,下台遍问众人索缠头钱。豪客、官家,各争赏赐。”41可见,在南宋时期音乐歌舞演出换得相应的报酬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规矩,也得到了市民大众的普遍认可。而宫廷采用“和顾”的形式,也就是出钱雇佣民间艺人到宫廷中作音乐表演,这和民间的商业化演出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南宋临安的音乐表演不仅自身是一种商业性的行为,它还参与和渗透到其他商业贩卖的活动中,无论是音乐表演还是商业贩卖,双方都获得了各自的利益,前者扩展了自己的市场、增加了影响力,后者则由于前者的精彩演出而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和买卖,而最终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库卖酒使用乐伎来做宣传和招揽。
国家“官卖酒”与乐伎扯上关系,开始于北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北宋只叫“娼妓坐肆作乐”42,南宋则有了一系列的套路,花样翻新,喧闹张扬。如耐得翁《都城纪胜》说:“天府诸酒库,每遇寒食节前开沽煮酒,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各用妓弟乘骑作三等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帬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裆袴者。前有小女童等及诸社会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呈,作乐,呈伎、杂剧,三盏退出于大街诸处,迎引归库。”
商业活动中使用音乐表演不仅仅是官方的特殊行为,在普通的商业贩卖中也是很常见的。南宋临安的茶坊、酒肆、食店,都特别讲究娱乐化经营,临安的茶坊中卖梅花酒时“因物制宜”的用同名的曲调来包装宣传:“暑天,兼卖梅花酒。……用鼓乐吹《梅花引》曲”43,这种销售方式在当时称为“歌卖”。44连临安城中小卖糖的也有唱曲儿、舞傀儡等招揽生意的招数:“又有虾须卖糖,福公个背张婆卖糖,洪进唱曲儿。卖糖又有担水斛儿,内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45
2.供求关系导致的迎合心理和竞争性
文艺演出既为营利性的商业行为,也就成为服务性行业,因而必须迎合顾客的需求,如此一来艺人成为商人,贩卖的商品是音乐,艺人与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牵制互相促进的关系,文艺演出需要遵照的则是商业化供求关系的规律。那么如何吸引观众保持较高的上座率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是摆在艺人面前的一大问题,因此他们做出各种努力以求在竞争中占得优势。
首先就是为自己的演出打起广告、做起宣传,且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有的靠大声吆喝、擂鼓筛锣招揽生意,如《庄家不识勾栏》中把门的:“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么末敷演《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的妆哈!’”有的利用在勾栏前张贴或悬挂“海报”来做宣传,此类“海报”在当时被称为“招子”,因其常为彩色的,故也称“花招子”,招子上写着所演戏名,也可能写上演员的名字,也有插挂旗牌、帐额之类的,在勾栏演出众多、观众无从选择的时候,此类显眼的标示就起到了很好的招揽和宣传作用。有的以观众的需要为最大的需要,因而采用观众直接点演节目的方法46,使得观众由被动的看客身份一转而成为主动者。当然最根本吸引观众的因素,还是精彩的表演和演员精湛的伎艺。
三、城市格局的变化为音乐的世俗化提供发展的契机
宋高宗于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并开始了对临安城市的改建和都城的建设。南宋临安城市的格局对于音乐的意义在于几个方面。一是坊巷制的建立,使得居民住宅与商业店铺可以交杂分布,共同的场所、无限制的演出时间,为音乐演出和民间艺人提供了更宽阔的平台。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的共同演出和实践带来了艺术上的融合、吸收与借鉴,有利于新的音乐形式、音乐风格的产生,也促成了艺人音乐素养和伎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南宋临安城内娱乐场所分布图显示,瓦舍、酒楼、茶肆、妓馆等各种演艺场所所在的位置,大部分处于商业核心的正中和四周,临安城内大瓦、中瓦、下瓦、南瓦等重要的瓦舍多位于城市的一类、二类商业中心区域47,这对于具有商业性质的演艺活动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三是城内城外统一建制统一划分区域,也就意味着城墙的界限被打破了,这不仅扩大了演艺活动的范围,增强了城市音乐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有利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流。四是由于不同场合的消费水平和活动特点的不同,勾栏、茶肆、酒楼等不同场所吸引了不同层面的人群参与其中的音乐活动,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一)多层次的场所
城市制度中空间的设置和布局与演艺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从南宋临安城中的一些地名中看出端倪,左二厢十八坊中有“众乐坊”,又称“南棚巷”,也许当时这里是艺人搭台表演、民众聚集观赏的所在,并因此而得名;左二厢中的积善坊又称“上百戏巷”,南宋时为傀儡戏集中地,每逢元宵灯节,“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艳丽”48,在这里表演精彩节目;此厢中的秀义坊又称“下百戏巷”,且与积善坊南北相邻,又同处于大瓦子东首,是当时临安城中百戏活动相当活跃的区域;左二厢的里仁坊中有“鞔鼓桥”,右二厢的教钦坊俗称“竹竿巷”,不知是否也和南宋临安的器乐演奏以及杂剧表演存在着关联。
1.以瓦舍勾栏为主体
最晚在北宋崇宁、大观(1102-1110年)间已经出现的瓦舍49,是一种新的商业集中点和娱乐场所,也是民间艺人表演的重要场所,发展至南宋临安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扩大和繁荣。临安瓦舍的设立虽晚,但是规模却不容小视,北宋汴京只设于城内的瓦舍,到了临安,随着城市格局的变化和城市范围的扩大,已经延伸到了城墙之外,所谓“城内外创立瓦舍”,连附郭之仁和县也有“瓦子巷”50,可见其延伸范围之大。除了空间上的扩展之外,瓦舍中勾栏活动的时间也最大程度的获得延长,并应时出现了专作夜场的勾栏,“独勾栏瓦市,稍远与茶肆,中作夜场”51。就数量而言临安一地,城内外的瓦舍就多至二十三处,其中仅北瓦一处就有勾栏十三座。52
关于临安瓦舍的确切数目,宋人在各书中记载不一,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梦粱录》卷十九《瓦舍》条说“杭城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西湖老人繁盛录》“瓦市”条说城内外有二十五个瓦子。《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列举了二十三个瓦子的名称及地点。《咸淳临安志》卷十九《瓦子》也列举了城内十七个瓦子的名称与所在地。其中较为正确的,也是目前多数学者所采用的是周密在《武林旧事》中的说法,即城内外共有瓦子二十三处。
起初,临安的瓦舍还只是作为军士们闲暇娱乐的专门场所,以后便发展成为面向普通民众的、融娱乐市易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游艺场。按照临安城内外瓦舍分布和具体的情况来看,临安城内的瓦舍规模很大,内容分类很细,往往位于城市的经济中心,多为普通民众的娱乐之所,而城外的瓦舍相对规模较小,往往位于军营或集镇附近,多是军士游艺之地。南宋时期临安瓦舍的隶属非常明确,周密《南宋市肆记》中说:“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修内司是宫廷内务部门,常负责营建和修缮工作,内设有教乐所,负责召集、培训民间艺人,供御前大宴宣唤,这样的设置应该是出于雇用民间艺人便利的考虑。殿前司为京师禁军统帅衙门,管理瓦舍属于兼掌,这也是由于驻军大都屯扎在城外和城内靠近城墙的地区,城外的瓦舍更便于为军士们娱乐服务的缘故。
2.以酒楼茶肆为补充
除了勾栏之外,酒楼、茶肆、歌馆也是城市中演艺活动较为集中的地方。南宋临安城内的茶肆为数不少,上下抱、剑营、漆器墙、子皮坊、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中子巷、狮子巷、后市街等处均有诸坊,著名的茶肆如八仙、连二、连三、清乐、珠子、潘家等,还有茶汤巷,是茶坊集中的地方,此巷就是因为茶坊多而得名的。
临安的茶肆尚有不同的类型,适合不同需要的人群聚集,如“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据《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这种花茶坊多是富家子弟、诸司下直等人寻欢作乐汇聚消遣的场所,而“非君子驻足之地也”53。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更有以某项伎艺为名的茶坊,如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毬茶坊”,可能是以蹴毬为主题的茶肆,来此的人群可能都是蹴毬的爱好者。中瓦内王妈妈所开的“一鬼窟茶坊”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等,则是士大夫聚朋会友的去处。富家子弟还在茶肆中以学习乐器、唱曲达到消遣的目的:“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54茶肆中还可以请旦,如戏文《错立身》第十二出云:“(生……看招子介)(白)且入茶坊里问个端的。茶博士过来。(净白)茶迎三岛客,汤送五湖宾。(见生介)(生白)作场。(吩咐请旦介)(且唱)[四国朝]听得人呼唤,特来次处。”茶肆中的请旦,由于场地局限,应该只是演唱小唱等小型的演出。
临安的酒楼大致有两种。一种为管库酒楼,这是南宋政府创办的酒库所附设的,临安的官酒库共有十三处,各库均设有酒楼,而其中“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55另一种为私人经营的酒楼,也称“市楼”,华丽可与官楼相比,著名者也有十余家,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南宋临安最出名的私营酒楼有南瓦子的熙春楼、新街巷口的花月楼、融和坊的嘉庆楼和聚景楼等,“皆市楼之表表者。……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擦坐’。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谓之‘赶趁’。……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56
(二)不同的音乐表演场合
1.日夜交替作场
随着临安城市格局的变化,商业活动在时间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延长,早市夜市是最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往往夜市甫一结束,早市就已开始,如此日夜交替地进行着,不受时间限制,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临安的早市和夜市延续北宋开封,且更加繁荣,史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57早市和夜市几乎没间断,而且“无论四时皆然”58。
纵贯南北的御街是临安城中最繁华的街道,“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毎日清晨,两家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59御街南段则主要为了供给宫内和主要中央官署日常生活的需要,因而是早市最热闹的地方,此地的夜市也十分热闹。御街中段特别是中瓦子所在的前一段,是街市最繁华的地段,《都城纪胜》“市井”条描述道:“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见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南宋临安城的北瓦中“十三座勾栏不闲,日日团圆”,并有夜间演出的明确记载:“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中作夜场”60,可见勾栏的演出时间相当饱满,利用率很高。南宋临安都市中夜场的兴盛和民众夜生活的普遍,为影戏的演出创造了条件并打下了观众基础。
2.周期性节日音乐活动
宋代是我国民俗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民俗事象极为多样,南宋一年四季的节日包括有帝后的圣节、官定的节日、节气性节日和宗教性节日等几类,分布于一整年的不同时日中间。每年的大小节日众多,以元旦、除夕、上元节(元宵)、立春节、清明节、上巳节(三月三日)、中元节(七月十五日)、中秋节诸节日为最热闹,几乎遍布一年的每个季节,由此循环往复。
以元旦为例。元旦是一年岁月的更始,南宋临安人对于这一节日尤为重视,认为“以年岁序,此为之首”,因此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不论贫富老少,无不尽情欢畅,“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61立春前一日,官府以旗鼓锣吹妓乐迎春牛,以求丰年之兆。立春时有迎春仪式和歌舞,范成大《立春日郊行》诗曰:“竹拥溪桥麦盖坡,土牛行处亦笙歌。”正月十五元宵节,除了花灯展览的习俗之外,还呈“奇术异能、歌舞百戏”,“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余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62
在南宋临安大大小小的节日中,又以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的音乐活动为最盛,在各类笔记史料中的记载亦最为众多和详尽。元宵佳节出自道家,道家奉天、地、水三元为天官、地官、水官之神,正月十五是天官圣诞之日,故以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上元之夜又称元夕、元夜、元宵。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曰:“正月十五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晨。”民间欢庆元宵祈福的风俗始于汉代,至唐更盛,往往接连数夜,通宵张灯。
3.宗教与崇拜中的迎神赛社
从南宋临安主要宫观寺院的分布来看,当时的宗教场所可以分为城内和城外两个部分,城内大多是沿着西湖发展的寺庙,城外则主要是靠近城墙地区大量的祠庙。63南宋时期临安城的迎神赛社活动正是在城外的祠庙中大量的存在,而城中的寺庙正如前文所述已很少作为娱神娱人文艺演出的场所了
迎神赛社又称神会迎或神赛会,为乡民祭神之仪,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条,就记载了临安钱塘门外霍山路崇仁真君的神庙前的露台表演,鼓吹、伎乐、舞队献艺,自早至暮,观众纷纷,其中娱神的意味逐渐淡薄,娱人的意味逐渐增强。陆游有《塞神曲》道:“击鼓坎坎,吹笙呜呜。绿袍槐简立老巫,红汕绣裙舞小姑。乌臼烛明蜡不如,鲤鱼糁美出神厨。老巫前致词,小姑抢酒壶:‘愿神来享带欢娱,使我嘉谷收连车;牛羊暮归塞门闾,鸡鹜一母生百雏。岁岁赐粟,年年蠲租,蒲鞭不施,圜土空虚。’束草做官但形模,刻木为吏无文书。淳风复还羲皇初,绳亦不解况其余!神归人散醉相扶,夜深歌舞官道隅。”64这正是生动地描述了南宋时城镇祭祀社神的场面。
南宋的迎神赛社活动的兴盛,甚至引起了士者和官府的关注与遏制,陈淳就写有专文反对“淫祀”和“淫戏”。南宋陈淳《上傅寺丞论淫戏》一文在论及我国南方农村无法扼制的南戏演出活动时说:“常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图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裒敛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滋炽。其名若曰戏乐,其实所关利害甚大。”
4.人生礼俗中的音乐
南宋时期音乐在个人成长礼俗中的运用主要是婚礼和丧礼。按照古礼,婚礼时是不用乐的,但是宋代的婚礼却开始普遍用乐,北宋元祐年间,哲宗大婚时曾经出现过用乐与不用乐之争,而南宋时期,据《武林旧事》卷八“册皇后仪”记载,皇帝婚礼奏乐多达十五次。
南宋临安城中的婚礼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议婚、订婚、完婚,尤其是完婚当日的迎亲过程,音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迎娶当日,男家派出一支迎娶队伍,由新郎带队前往女家迎娶新娘,这支队伍中须由吹鼓手和官私伎女等组成。《梦粱录》记载当时临安的情况说:“至迎亲日,男家刻定时辰,预令行郎,各以执色如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授事街司等人,及雇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请乐官鼓吹,引迎花担子或粽担花胜轿,前往女家,迎娶新人。”“其女家以酒礼欵待行郎,散花红、银楪、利市钱会讫,然后乐官作乐催妆,克择官报时辰,催促登车,茶酒互念诗词,催请新人出合登车。既已登车,擎担从人未肯起步,仍念诗词求利市钱酒毕,方行起担作乐,迎至男家门首。”新妇到男家门首下轿后,乐官、伎女、抬轿、鼓吹之人等,开始“拦门”讨“利市钱物”,“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65,乐官、伎女等拦门时,要念吉利诗句、讲吉利话,例如拦门诗、答拦门诗等。66
与古礼婚礼不用乐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南宋朝廷曾明文规定“丧葬不得用乐”67,然而民间确依旧是“丧家率用乐,人皆以为当然”68。在丧葬过程中,民间习惯聘请乐师奏乐,《司马氏书仪》卷六“丧仪二”中曾指出,当时有“初丧作乐以娱尸,及殡葬则以乐导车,而号哭随之”的习俗。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还曾经写道临安的丧葬过程,他说:“人死焚其尸,设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像前作丧歌,及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据称死者在彼世获有诸物,所作之乐,及对偶像所唱之歌,死者在彼世亦得闻之,而偶像且往贺之也。”69这段记载和南宋临安娱尸的习俗是相当吻合的。
四、特定的生存环境推动音乐的世俗化
南宋临安由于在时间、空间以及地方传统上的特殊性而融合成社会各阶层特殊的心理,这种社会风尚和社会心理进而又影响到了民众对于音乐的趣尚和审美,并且在具体的音乐文化中体现着人们的心理和情感。
(一)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
临安自吴越国以来一直保持的安定局面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五代进入北宋时,兵燹把其他大都会惨烈地破坏了,而杭州却太平无事,仍能够循序发展。自978年钱弘俶归顺北宋,杭州连续七十多年比较安定,未遭兵火灾乱,因而在北宋时享有“东南第一州”之美誉。70虽然南宋初期的战乱给整个江南带来了灾难,但临安是高宗的行在之地,因而并未受到重创。而且,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南宋向金朝割地、称臣,每年还要给金人大量岁币,这次和议虽然给南宋带来了巨大的国耻和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是客观上宋金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就此告一段落,江南地区再次进入和平环境,南宋得以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其后的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一系列和议的签订使得临安获得了相当长时间之稳定的局势和发展的空间。
(二)繁荣的经济状况
临安在北宋之时已经因其物肥水美而获得了“东南形胜第一州”的美称,南宋以来,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临安城市的社会经济更是获得了集中而迅猛的发展,对于临安这个城市自身来说所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机遇。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序中曾经说道:“自高宗驻跸于杭,而杭山明水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此番话语可能有言过其实之处,然而杭城人聚物美的景象却是事实,“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藩,市井坊陌,铺市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城外尚且如此,城内更是一派欣欣向荣:“大外至官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凡一切日常所需及金银首饰、杭锦织缎等,应有尽有。
(三)奢华娱乐风潮的兴盛
临安由于地处江南娇好的自然环境之中,人们的生活一直比较富足,因而自古就有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享受的风俗。南宋临安升为行在之后,奢侈之风愈盛。《太平清话》说:“钱塘为宋行都,男女尚妩媚,号‘笼袖骄民’。”《秦观雪斋记》也说临安的人民“羞质朴而尚浮华”。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条在描述湖上游船嬉戏娱乐的情形时,也感叹道:“日蘼千金,蘼有纪极。古杭城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可见,临安一地的风俗极为注重饮食、衣着、居住精致和铺张的追求。
除了物质享受之外,精神的慰藉和享乐也是临安人不容错失的事情,冶游山水、听歌赏乐,是其衣食住行等物质追求之外的又一倾力所为的赏心乐事。《梦粱录·卷四》“观潮”条中总结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整个城市陷于娱乐的状态,正如《坚瓠集》所说:“西湖之盛,始于唐,至南宋建都,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目为销金窝。”《苏轼表忠观碑》亦云,临安此地“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可见在和平环境的有力保障下南宋临安的人们尽情享受着他们的精神生活。
注释: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志四》,中华书局,2000。
②以上均引自[元]脱脱等:《宋史·乐志五》。
③[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七之二九》,中华书局,1957。
④[元]脱脱等:《宋史·乐志六》。
⑤同④。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三十《乐志五》:“乃从太常下之两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广东西、荆湖南北,括起旧管大乐,上于行都,有阙则下军器所制造,增修雅饰,而乐器寝备矣。其乐工,照依太常寺所请,选择行止畏谨之人,合登歌、宫驾凡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诣太社、太稷、九宫贵神。每祭各用乐正二人,执色乐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皆召募补之。乐工、舞师照在京例,分三等廪给。其乐工、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习;引舞、色长、文武舞头、舞师及诸乐工等,自八月一日教习。于是乐工渐集。”
⑦以上见《宋会要辑稿·乐五之三八》、同书“职官”二二之三至三二,[元]脱脱等:《宋史·乐志十七》。
⑧[元]脱脱等:《宋史·乐十七》。
⑨同⑧。
⑩同⑧。
⑪[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二。
⑫[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十四《高宗本纪》。
⑬[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三十《乐志》。
⑭同⑬。
⑮同⑬。
⑯同②。
⑰同⑬。
⑱同⑬。
⑲[清]嵇璜等:《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全文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20 楼钥:《重修太常寺记》,载[宋]楼钥:《攻媿集》卷五十四。
21 同⑧。
22 同⑧。
23 同④。
24 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第37页。
25 全汉昇:《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新亚研究所,1972,第295页。
26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妓乐》,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27 《西湖老人繁盛录》:“清乐社,有数社,每不下百人……福建鲍老一社,有三百余人;川鲍老亦有一百余人。”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28 [明]陶宗仪:《说郛》卷七十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9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30 [清]嵇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十八载:“今之艺人,于市肆做场,谓之‘打野泊’,皆谓不着所,今谓之‘打野呵’。”出处同⑲。
31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伎艺》:“村落百戏之人,托儿带女,就街坊桥巷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出处同26 。
32 《西湖老人繁盛录》:“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33 [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卷七》所载唱赚的社条规定:“如对圣案,但唱乐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词,切不可风情花柳、艳冶之曲;如此则渎圣,社条不赛。”载[日]长泽规矩也:《岁华纪丽书叙指南 事林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4 如熊保保,钱塘人,寡居,擅唱诸宫调,为杂剧班首、锦秀社首,死后行会为其立碑:“杂剧班首熊氏墓”,明代徐伟曾作诗悼之。见胡效琦:《杭州市戏曲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第334页。
35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3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7 [宋]郭彖:《睽车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8 吴松弟:《宋代靖康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载《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
39 周峰:《南宋京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16页。
40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246页。
41 《明代小说集刊》第二辑(1),巴蜀书社,1995,第111页。
42 汪拯:《燕翼谋殆录》卷三:“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民,设一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而散矣。又恐其不顾,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竞争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架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旧’。”
43 同29 。
44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茶肆》:“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奇桧等物于其上,装是店面,敲打响盏歌卖。”出处同26 。
45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46 杂剧《蓝采和》第一折。
47 [日]斯波义信:《宋都杭州的城市生态》,载《历史地理》(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69页。
48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元宵》。
49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谓其来时瓦合,出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出处同26 。
50 [明]沈朝宣:《(嘉靖)仁和县志》卷一。
51 《西湖老人繁盛录》,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52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53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54 同29 。
55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56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57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58 同29 。
59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60 《西湖老人繁盛录·瓦市》,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61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62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63 伊原弘:《南宋初起临安的形成——从寺庙分析入手》,载孙钦善等主编《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238页。
64 [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5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66 [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卷五《娶妇》,载[日]长泽规矩也:《岁华纪丽 书叙指南 事林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7 《燕冀诒谋录》卷三。
68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
69 [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352页。
70 宋仁宗:《赐梅挚出宁杭州诗》,引自《杭州历史丛编》编辑委员会编:《南宋京城杭州》序: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