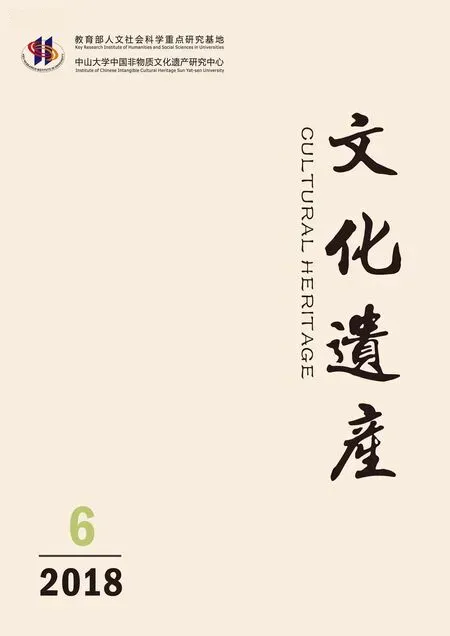现代日本社会的“祭礼”—以都市民俗学为视角*
2018-01-23王晓葵
王晓葵
导言
在日语中,祭(maturi)、祭礼,属于相关但是意义不同的概念。祭本来是祭祀神灵和祖先的信仰仪式,人们通过在神社等举行的祭拜和艺能表演等活动,祈求神灵或祖灵保佑全家平安、作物丰收、买卖兴旺。也藉此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也对祖先的敬仰与情感。祭的组织和举行,也常常成为地域共同体或信仰共同体通过现实可感的空间,确认和强化认同的过程。
而祭礼的产生是源于祭的仪式化和娱乐化。对此,柳田国男在《日本の祭》(1962)中,有一个简要的说明,他认为,祭主要是人与神灵、祖灵沟通的形式,以信仰和宗教的意义为中心。而祭礼是祭的一种变化形式,含有艺术表演的成分,以及有观赏者观看。这是祭礼不同于祭的最大之处。从祭到祭礼的变化,是日本祭的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柳田国男从发生的角度探讨了祭到祭礼的发展脉络,他说,
日本的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简而言之就是观赏人群的出现,也就是说参加祭的人们中,有些人并无共同的信仰,他们从审美的立场出发,来观赏祭的过程。这样一来,都市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也让我们对童年的记忆变得快乐。但是,这也慢慢侵蚀了以神社为中心的信仰体系,最终导致人们居住在村里,但是只是以观赏的心态去看待祭。这样的观念当然不是近世以来才有的。在明治以前,就已经渗透在村落之中了。村里年景好的时候,农民们总是要把“可看的祭”搞得华美热闹。而这个和他们原来固有的代代传承的感觉,对神灵和祖先的祭祀的义务责任并不矛盾。古老的习俗和新式的做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祭礼*柳田国男:《日本の祭》《柳田国男全集》13、東京:ちくま文庫1990年,第249页(作者译)。
柳田国男的说明,简单归纳起来,从祭到祭礼的变化,是从信仰世界扩展到人类生活中审美以及更广泛领域的一个过程,从人神沟通到和人人沟通的并存,这个变化虽然对原有的信仰形态有所影响,但是,让不具备共同信仰的人,在祭礼中通过娱乐和观赏产生共同性,是时代变化的一种重要现象。
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基本完成了都市化的转变,在都市举行的祭和祭礼也不断增加,而且在乡村地带举行的传统的祭和祭礼,也受到都市的影响,逐渐改变其方式和形态,因此,日本民俗学关于祭和祭礼的研究,也逐渐转向都市祭礼。民俗学家茂木荣对此做了如下总结,他认为日本民俗学通常把三类祭礼作为研究对象,第一类是在都市的神社寺庙举行的传统祭礼,特点是有各种祭神的活动以及牵引山车、轿台游行的活动,其组织者主要是神职人员或者当地街区的居民组织。第二类是在都市举行的非传统型的以祭冠名的节庆活动。这一类活动包含各种博览会、节日庆典等,通常在都市广场、城市干道、露天剧场等举行。其中有诸如游行、街市贸易、比舞赛歌等竞技以及各种表演。其主办者主要为当地政府、观光协会、青年组织、商工会议所、居民团体等。第三类是都市之外举行的非传统的新式祭礼,这一类是第二类祭礼在城市之外地区的翻版,在接受了城市文化洗礼的农林渔村地带举行*茂木栄:《都市とイベントー新しいマツリの抬頭》,東京:《都市民俗へのいざないⅡ情念と宇宙》1989年,第138-139页。。
茂木荣的总结基本概括了日本都市化完成后祭礼的现状。他认为,第一类的祭礼原本是民俗学一直关注的对象,也有很多研究的积累,而第二类和第三类则是今后都市民俗学的目标。
但是,都市民俗学在其诞生之初,就面临一个学术难点,就是如何把握城市中的传承性行为。众所周知,日本民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传承”,虽然这个概念从诞生至今几经修改,但是,其核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柳田国男把自己的民俗学定义为“民间传承”的研究。所谓传承,是指文化的时间性移动的概念,它是一个和传播(文化的空间性移动)对应的词语。它有两个含义,广义上指上一代通过语言或动作以及动作的结果传授、下一代通过听或看来继承这样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行为。前者(通过语言传授)是口头传承,后者(通过动作和动作的结果传授)是行为传承。关于口头传承,不仅传授行为,传授内容如神话、民间故事、民谣等都称为传承,甚至传授手段即语言也被传承下来。狭义的传承通常伴随着某种模式(或形式,惯例),亦即经过超越世代的反复延续而形成的一种模式(或形式、惯例),被延续下来就成为传承。传承当然是基层文化,但是属于上层文化的传统戏剧、武术、工艺等领域、也有传承的因素*福田アジオ等編:《日本民俗大辞典 下》,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年,第168页。。
从这个定义出发,传承的特征通常被认为有如下几个特征,1.是类型的而非个性的,2. 是反复的而非一次性的,3. 是集团的而非个人的,4. 是基层文化而非上层文化。传统的祭的形式和组织形态,都带有上述传承的特征。如茂木荣归纳的第一类,祭礼通常由神社的神职人员,或者当地住民组织主办并共同参与,其规范和形式在世代传承过程之中虽有损益,但主要部分则保持不变。而且过去这类祭礼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参加者基本是地域共同体成员,并不接受外人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承母体,或者是神社寺庙,或者是地域组织,他们是祭礼的施行者,也是信仰的主体。在以往的研究中,透过对祭礼从准备到实行的全过程的分析,便可以揭示这个传承母体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形态特征。
但是,第二类和第三类的都市祭礼的产生,以及第一类祭礼发生的变化,使得民俗学原来以分析传承母体和传承性事项的解释框架失效。因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祭礼,往往以开放的形式,允许外部人员参加,原有的传承母体的概念无法概括这些人群的特征,而且传承的内容和以前相比,保持与传达逐渐转换为创造与生成,因此,分析新时代的祭礼,不但是了解城市化社会日常与非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的需要,也是对民俗学向现代转型的挑战。
本文通过爱知县的花祭和起源自高知县的YOSAKOI祭,并联系几个相关的事例,讨论现代日本祭礼的基本特征,同时结合传承和传承母体这两个基本概念,探讨都市民俗学的可能性。
一、从地域传承到社会传承-花祭
“花祭”是日本中部爱知县北设乐郡等地传承了将近700年的祭祀活动的总称。其中北设乐郡的花祭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花祭据说源自镰仓室町时代的修验道的信徒们的仪式活动,主要是在一年中最寒冷的12月到1月之间,人们围着沸腾的水盆彻夜狂舞,这些舞分少年舞、青年舞以及鬼舞等。人们将烧开的水喷洒到身上,来去除身上的污秽。
举行“花祭”的时间各村不同,主场地由村内各家轮流承担,也有相对固定某个地点的。或者在神社举行。“花祭”举行场所称为“花宿”,人们认为,“花祭”期间神灵将会降临至此,“花宿”便成为一个神圣空间,神灵降临的时候会依附在剪好悬挂起来的纸片上,“花祭”参加者分为“舞子”和“宮人”、都是由当地的祭祀组织构成,过去“花祭”是禁止女性参加的,近年由于人口减少,为了维持这项活动的进行,以及适应时代的变化,女性也逐渐被允许参加。
长期以来,“花祭”一直是当地民众祈愿丰收、家族平安以及增强自身生命力,从而获得重生的祭祀活动。但是,这个延续了将近700年的民间传承,随着农村的凋敝,能够参与和承担祭礼各项活动的人越来越少,这项活动本身面临中断的危机。根据樱井龙彦的调查,“截止昭和25年(1950)奥三河地区还有21处“花祭”传承地,然而在历经60年的变化中,2010年度 (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的统计显示,现仅存15处, 由于人口稀疏化、老龄化问题,现今这15处传承地的“花祭”已面临濒死的危机,每年仅是勉强维持。例如,丰根村山内地区的“花祭”在2007年终止,当时该地区居住21户村民,人口计40人, 平均年龄超过67岁。另外,东荣町布川地区现有23户居民,其中12户为独居老人*樱井龙彦:《人口稀疏化乡村的民俗文化传承危机及其对策——以爱知县“花祭”为例》,《民俗研究》2012年第五期。。
由于过去日本的祭礼的传承母体是村落共同体,承担各项任务的相对固定的住户较多,比如主持花祭的 “花太夫”(祭神仪式、奏乐(鼓、笛子)的核心人物)及其辅佐“宫人”、以及扮演 “山见鬼”、“榊鬼”的人都是世袭制,为了能够让这个古老的祭礼能够传承下去,当地采取了诸如解除女性禁制,缩短时间、允许外部人员参加等措施。
樱井龙彦的调查提供了三个事例*樱井龙彦:《人口稀疏化乡村的民俗文化传承危机及其对策——以爱知县“花祭”为例》,《民俗研究》2012年第五期。:一个是东荣町布川地区的例子,该地区由于人口稀疏化、老龄化问题,无法确保足够的舞者。如今,部分舞者的角色已由名古屋市的中学生担任。2006年开始,名古屋的学生开始以参加“日式大鼓·舞蹈部”活动的方式加入其中。而每年,布川“花祭保存会”都会派人去名古屋进行指导。
第二个事例是东荣町御园地区与东京都东久留米市等地居民开展的“花祭”交流活动,1993年起,接受过御园保存会指导的东京儿童,开始参加“东京花祭”。御园地区的居民每年冬天前往东京,对孩子们进行音乐(鼓、 笛)和舞蹈方面的指导,东京的孩子们则利用暑假等机会来御园参加集训。1994年起,东京的孩子们直接参加御园的“花祭”,并和当地人一起表演舞蹈。 但是,正如“东京花祭”其名,孩子们的主要活动是在远离布川的东久留米市进行表演,尝试在东京市民中传播“花祭”文化。
第三个是在东荣町东薗目,一个外地的名为“志多罗”的专业鼓乐团因为别的原因迁至此地,开始协助“花祭”的笛、鼓演奏。1994年他们创作的“志多罗舞”成为了祭神舞蹈, 此后便一直为传统“花祭”注入新的剧目。虽然当地有意见认为,“花祭”是一种祭神仪式,不该引入专业的音乐演奏家。但是“志多罗”的加入得到了“花祭”保存会长等人的支持,如今他们已经不再被视为“外人”,而是作为当地居民的一分子积极参与进来了。
樱井龙彦的调查为我们提供的上述个案,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传承母体和传承行为的脱地域化,或者说是跨地域化。东京和名古屋的教师和学生们,每年参加“花祭”,并且将爱知的地方文化传播到东京和名古屋。原来在御园地方的祭礼,在异地东京和名古屋得到传承,和“花祭”的原生地毫无关联的东京和名古屋的孩子们和年轻人,在完全不同的空间传承这个祭礼,以及非本地出身的艺术家,被允许参加“花祭”的重要仪式的部分,可以理解为这个传承已经不再是当地人的专有物,而成为日本社会的共同财产。这个现象如果用从地域走向大众来描述的话,这个大众可以理解为新的传承母体。
从这个实例思考传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传承主体选择性,我们通常很容易把乡土社会的传承行为理解为习焉不察的、不知不觉的和带有某种强制性的规范。但是,随着都市化的推进,当地居民通过和外界的交往,开始有将自我的文化事项客体化的倾向,所谓文化的客体化,是指文化传承者自主将自身的文化作为可操作对象加以客体化,有可能生成新的文化,而且在客体化过程中文化传承人也有可能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太田好信:《文化の客体化 : 観光をとおした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創造》,《民族學研究》57(4),1993年,第391页。。
当地住民通过将“花祭”仪式开放给外部,进而使之得以传承,这既是传承主体的主体性选择的结果,也是一个传承主体扩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花祭”,既属于本地住民,也通过名古屋、东京等地的参入者的共同创造,成为日本社会共享的文化财产,而外部的参入者通过进入“花祭”的传承过程,将这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事项,变成自身享受和消费的文化要素纳入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这个现象毋宁说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
岛村恭则在分析大阪地区韩国侨民的生活文化时候,指出,传承行为是主体选择性行为,传达什么,继承什么,是由当事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生存状况选择的结果。他说,
在我的田野中,相等于传承的行为或者可以称为传承的事象不是不存在。我通过当地人生活中的各种事象,或者在他们与前辈之间,确实看到了某种传达、继承的关系。 (中略) 尽管存在这种情况,这些事象并不是 “自然地”、 “无条件地”传承下来的,而是只因为人们实践 “生活方法”时选择,所以才得以存在的*島村恭則:《“生きる方法”の民俗誌―朝鮮系住民集住地域の民俗学的研究》,大阪: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10年, 第301页。。
通过上述花祭传承现状的讨论,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传承和传承母体可以有更开放性的认识和理解,从本质性的地缘和血缘等纽带建立起来的传承母体的概念,扩展到自由选择性的“选择缘”的现代传承母体。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和保护的世界性潮流,从地域传承转变为社会传承,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这一点从祭礼的传承现状中尤为明显。
二、传承母体的开放性与“共同 想象”的地域-YOSAKOI祭
关于现代都市祭礼的诸特征中,脱地域性最为显著,所谓脱地域性,是指参加祭礼的人们,已经不在限于原有的以地域的信仰集团或者生产生活关联为核心的群体,而开放给任何愿意参加的人。但是,这样的脱地域性是否会导致传承母体的无条件的扩大,而导致传承的认同性被消解,本节就这个问题,以当代日本分布地域最为广泛的都市祭礼之一的YOSAKOI祭为例,讨论都市民俗学视角下的祭礼传承的问题。
YOSAKOI祭,是一个战后诞生的都市节庆活动。它起源于日本四国地区的高知县,YOSAKOI是“今夜请来”的当地方言的发音。每年8月9日到12日的4天,在高知市举行舞蹈表演。表演者在遵守一定的规则(如乐曲、舞蹈形式等)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创造表演形式。目前大约有150个团队、16000多人出场表演,观众达到100万多人。这个节庆活动后来逐渐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成为当代日本一个重要的都市节庆活动。
YOSAKOI祭始于1953年。为了摆脱战后的萧条,高知市工商会议所策划了这个活动。当时,相邻的德岛县有著名的阿波舞。高知希望创造一个能和阿波舞不相上下的节庆活动。组织者首先请日本舞蹈(花柳、若柳、藤间、坂东、山村等五个流派)的老师设计并传授舞蹈动作。同时,请专人谱曲作词编舞。创作了YOSAKOI舞曲。由于阿波舞是徒手表演的,为了凸显自身的特点,根据作曲者武政的提议,YOSAKOI祭跳舞时使用一种叫“鸣子”的木制道具。这个后来成为YOSAKOI祭的基本要件之一。第1次YOSAKOI祭于1954年8月举行。此后每年举行一次。早期的YOSAKOI祭节的舞蹈接近传统盂兰盆会舞蹈风格。1972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有采用桑巴舞和摇滚风格的曲子团队出现。新形式的YOSAKOI祭很快流行开来,形式也逐步多样化。
进入八十年代,YOSAKOI祭的音乐可以自由设定,对舞蹈的形式也解除了限制,和当地的团队不同,日常没有任何关联的人们组成的队伍激增,特别是年轻人,YOSAKOI祭成为他们相识并并共同度过激情时光的缘*平辰彦:《都市民俗学から見たヤートセ秋田祭の<祝祭性>―融合文化の事例研究―》,《融合文化研究》第14号 2010年1月,第25页。。
1999年开始,高知县开始举办YOSAKOI全国大会,当年有14个县外团队,约1000人参加,此后,外地参加团队逐年增加,到2005年已经增加到35个。参加的团队在2016年第63届时已经达到100个。其中大半来自高知县。1992年,北海道开始举行“YOSAKOIso-ran祭”标志着这个祭礼开始向外地扩散,此后,各地开始同样名称的活动。1996年开始,高知县开始派遣当地的舞者去参加表演和进行指导,并提供经费上的支持。高知县之外的YOSAKOI祭中,以北海道札幌的YOSAKOIso-ran祭、东北仙台的MichinokuYOSAKOI祭、中部名古屋的日本最中央祭规模和影响最大。每个地域在遵守一般性规则的同时,也加入了各个地方性的要素,比如神奈川县的小田原市ODAWAERA ESAHHOI祭就加入了当地的小田原提灯,兵库县的KINOSAKI温泉YOSAKOI祭,则突出当地的温泉特色、螃蟹造型等。
目前,YOSAKOI祭的基本规则就是原则上要拿着叫“鸣子”的乐器,使用当地民谣或民谣改变创作的曲目伴奏跳舞。舞者不仅参加本地的YOSAKOI祭,很多也参加其他地域举行的此类祭礼。为了强化和其他地域的差异,各地团队大多采取了强化本土特色的编排方针。关于这个祭礼的特色,长期研究YOSAKOI祭的矢岛妙子有如下总结:
1.维持祭礼的传承母体的全国性网络的存在。比如YOSAKOIso-ran祭,虽然在札幌举行,但是,参与者有东北地区的仙台、中部的名古屋、西部的高知、关东的东京、还有海外的团队。包括了来自不同地域的甚至不同种族的人。
2,具体的单位体现为地域、企业、学校等单位母体,而且这些单位母体也是开放的,在祭礼举行的过程中,各地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由此,上述的传承母体的具有松散的、结合原理的多样性、动态的、母体单位存在的重要性,以及参与者的全国性、竞争性导致传承力的强化*矢島妙子:《よさこい系祭りの都市民俗学》,東京:岩田書院2015年,第305页。。
矢岛等人的研究还表明,对YOSAKOI祭的全国性扩散,大学生的作用非常大。札幌、名古屋、仙台三地的YOSAKOI祭,分别是位于札幌市的北海道大学、名古屋市的中京大学以及东北出身的高知大学的学生,在参加了别的地区的YOSAKOI祭之后,萌发了在自己的所在地举办同类活动,将狂欢的激情和参与的感动和自己所在的城市的人们分享,进而付诸行动,先从同学中找到支持者,然后逐渐获得当地住民组织和行政部门的支持,逐渐扩展到现在的规模。
大学生群体的参加,对此类祭礼的维持和发展也有重要作用,在很多地方,由于少子化和人口流动等原因,由当地住民组成的团队的舞者的人数越来越难以保障,特别是要组成一个有感染力的舞队,需要将近一百人,从一般市民中要招到这个数量的舞者,难度越来越大。虽然舞队对任何地域都是开放的,但是,对外地人来说,经常来参加训练并非易事。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各地的市町村合并*平成以来,日本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强化财政基础。推动各地市町村合并,1999年(平成11年)3月统计的3232市町村数到了2008年4月1日减少到了1788个,9年之间减少了45%。之后,各地的地域认同也相对下降。而上述问题对大学生来说完全不存在。他们不但可以随时补充20岁前后的年轻舞者,练习的时间和空间都容易确保,很多大学还承认他们作为校外活动俱乐部的地位,他们不但有以大学为单位的舞队,还有跨学校组成的诸如北海道学生联合舞队、关东大学学生舞队、东京大学生舞队等。大学生的存在,是此类祭礼存在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民俗学的视角分析YOSAKOI祭礼,不可避免地要讨论传承和传承母体的问题。从上述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类新式的城市祭礼,其传承母体,已经不在局限在特定的地域认同,而民俗学的地域共同体论,通常以实体性的地缘为核心,福田亚细男的传承母体论,其中传承母体的条件之一是“占有一定的土地”,就是指特定的地域。而当传承行为扩展到全国甚至更广泛的区域的时候,传承的地域性因素是否可以放弃。变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对此,矢岛提出了“全国性参加的网络群体,就是都市文化的传承母体”*矢島妙子:《よさこい系祭りの都市民俗学》,東京:岩田書院2015年,第304页。的观点。对这个传承母体,她总结了如下几个特征,第一是松散性,亦即,参加团体不局限在特定的地域,而从更广域的范围内获取资源,其空间性呈现出差序性结构。第二,多样性的结合原理,也就是有多重形式的参入机制,而不是单一的诸如血缘或地缘的标准。这个保证了舞者可以相对自由地加入舞团。由上述的特征,衍生出第三个特点就是动态性,由于多样性的结合原理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因此,支持舞团的组织也不断改变修正,舞团也像一个生命体一样,有新生,也有消亡。第四个特点就是传承母体单位非常重要。很多支持舞团的母体单位,不仅仅在祭礼期间存在,平时也有活动。这些小单位的存在,是舞团作为传承母体存在的基础。而第五个特点就是全国性网络群体的存在,全国各地的参与者作为一个传承母体的存在是这个祭礼存续的重要条件。最后一个特点就是,通过互相竞争而强化了各自的传承力*矢島妙子:《よさこい系祭りの都市民俗学》,東京:岩田書院2015年,第304页-305页。。
他者的出现,往往是自我认同产生的前提。现代都市的开放性,为不同文化表象自我提供了舞台,这个表象的过程也是其主体自我建构和自我认知的过程。在这里,认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便成为重要的问题。矢岛认为,如果片面强调现代都市祭礼的开放性和超地域性,那么没有具体认同内容和对象的所谓传承母体,就很难把握。她的研究表明,来参加祭礼的舞者团体,都需要表演某个特定地域的民谣,这个民谣往往成为一个地域的表象,仙台的YOSAKOI祭主要是表演东北各地民谣,而名古屋的则是表演中部地区的民谣。另外,服饰的道具也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矢岛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回归地域”,换言之,在开放的城市舞台,参加者通过表演特定地域的民谣,将所代表的地域表象化,并以此建构参加团队的认同。来自不同的地域的人,通过表演,将在大都市生活中日渐疏离的身体感受实在化,这其实也是这个YOSAKOI祭的最大魅力。这里回归的“地域”并非原来实体的地域,而是被表象化的,参加者心意中的地域,它和现在实在的地域未必等同,比如札幌在表演中被表象为渔业文化的都市,而事实上札幌既不是渔港,也不是渔业生产的基地。渔港札幌,仅仅是参加表演的团队以历史记忆重现的地域印象*矢島妙子:《よさこい系祭りの都市民俗学》,第280-281页。。
现代祭礼中,不同地域、不同所属的参与者,在一个舞台上表演艺能,互相比较,决出胜负,这个环节往往是祝祭最为吸引观众的部分。比如广岛县内最古老的“西中国选拔神乐竞演大会”,从战后的1947年开始,到2007年为止,已经举行了60次,在西部日本,类似的竞演大会,这些大会逐渐定期举行,成为某些地域提高地方知名度,强化地域内部认同的符号。广岛神乐前汤治村,一年来客大约15万,虽然经济效益并不突出,但是对这个过疏化的山村地带,具有非常大的宣传效应。与此同时,竞演对艺能的传承也产生了影响。原本植根于各地祭祀活动的艺能,由于要在共同的舞台上表演比赛,为了有客观的可比性,表演团体之间逐渐形成了相对共通的表演程式或范畴。在此基础上突出各自的独特性。而各个表演团体在互相比较竞争的氛围中,逐渐萌发*俵木悟:《華麗なる祭り》《日本の民俗9 祭りの快楽》,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年,第92页。。
观光人类学的研究者山下晋司也通过各地的例子说明,“在关注当地人主体性基础上进行“传统”文化的再构建和再创造过程中,通过外部行为体与文化传承人的相互作用,有可能形成“地域身份认同”*参照山下晋司:《バリ 観光人類学のレッス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230页。。
通过上述的介绍和分析,我们或可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变化,通过祭礼的变迁有所了解,而民俗学在转向现代社会研究的时候,如何将原有的核心概念,比如传承和传承母体在重新加以界定之后,应用在分析和解释当代生活的诸多现象上,日本的民俗学界的努力和探讨,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余论:日本祭的研究与都市民俗学
日本研究祭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40年(昭和15年),当时日本正处在战争最为紧要的时期,为了弘扬日本国民的皇民国家意识,大量日本神社祭祀的记录和调查报告诞生。其中柳田国男的《日本の祭》(1942)就是这个时期问世的。
第二个时期是战后日本开始经济腾飞的1960-1970年代,这个时期是日本经济腾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期。日本社会全面进入城市化社会,家用电器和汽车的普及,农村社会逐渐衰退,生活文化全方位西化。由此产生的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矛盾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文化。祭和祭礼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表征,受到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关注。柳田国男热也产生于那个时期。
第三次祭的研究,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结束。战后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制度逐渐解体。日本社会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从公司、地域、单位等社会组织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重新个体化的人们,如何摆脱日常生活中的孤独和日常的无聊,重建新的社会网络,从中获得生活的幸福感和感动。新形式的城市祭礼,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以YOSAKOI等现代都市生活的祭礼研究为中心的成果涌现出来。
在诸多的成果中,松平诚为现代祭礼总结了五个重要的特征:
1.从地域走向开放;
2.观赏、参与、展示的多义性结构;
3.柔软的 内涵,开放的外延;
4.开放形的网络体系构和增殖性;
5.非日常/日常的结构变化,目标指向性的丧失与欠缺。*松平誠:《都市祝祭の社会学》,東京有斐閣 1990年,第34页。
这五个特点,具体而言,第一从地域走向开放,现代的都市祭礼,已经摆脱了传统型的参加者以特定地域的信仰集团和生活集团为核心的排他性构造,转而开发给任何希望参加的人群。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指参加群体的组织形态为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的机制,由此导致一个团体随之人员的变动,其特征在数年就发生激变。而这种开放性又产生了第三个特征,就是形成了沿着铁道沿线,干线道路的衍生群体,技能熟练的参加团队将表演技能传授给别的地区的团体,由此繁衍子孙一样的扩展出去,形成一个广域的网络体系。由于脱地域性和开放性的构造,使得参与者没有日常性生活、生产、休闲等方面的关系,很难形成牢固的生活共同体或者社会组织,参加祝祭所获得的开放感、情绪的宣泄和感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命的动力和活力,都还原到参与者的个体中,而不是他们的群体。这些特征,也基本上可以适用在本文讨论的祭礼上,
社会学者铃木谦介认为,不应将现代的“社区 ( community) ”看作过去由地理环境与固定的社会团体组成的 “共同体”,而应将其看做“虽有流动性”,但因“人们的自反性归属感”而产生的“共同体”。现代社区的共同性体现在社区居民共享着某种共通的东西,比如对家乡的眷恋,或者参与本地活动产生的“市民自尊 ( civic pride) ”*鈴木謙介:《ウェブ社会のゆくえ〈多孔化〉した現実のなかで》,東京,NHKブックス2013年,第195-196页。。
而战后在大都市产生的以高知县的YOSAKOI祭礼、名古屋日本正中央狂欢节等以大学生团体为组织主体的祭礼,则呈现出当代日本社会的新的人际关系构建的特征。也正是这种市民自尊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祭礼的演变,也是一个社会关系变化的晴雨表,通过对祭的过程的分析,能够揭示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构建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相邻学科的民俗学,除了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之外,也应该对其传承性加以关注。日本人类学家和崎春日把民俗学定义为“在传统性中探求现代性,同时在现代性中探求历史性”*和崎春日:《都市の民俗生成―京の大文字》都市民俗学へのいざないⅡ 情念と宇宙》,東京:雄山閣1989年,第116页。的学问。由此,他认为,都市民俗学就是要在都市的传统活动中探寻现代的意义,同时在现代都市中的各种现象中,寻找其和过去的关联和脉络,并面向未来,来思考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规律。
在中国,古老的庙会逐渐和现代的节庆商贸活动结合,以新的形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存续。以民俗学方法去分析和研究,得出解释力的结论,是未来中国都市民俗学的重责,日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相关的学术积累,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