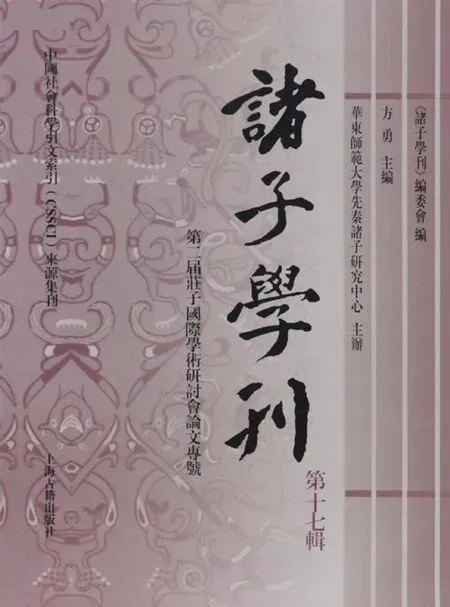自我與超我的蝶變*
——内向傳播視角下的莊子之夢新探
2018-01-23謝清果
謝清果
内容提要 《莊子》一書以夢喻道,托夢悟道,以啓迪世人認識自我,忘掉自我,成就自我。本文從内向傳播理論視角來觀照《莊子》一書中的夢文化,發現莊子學派以夢與醒的“物化”立論,教導世人當放下物質自我、社會自我乃至精神自我,以至於“坐忘”,才能找到真正的快樂逍遥的自我。同時,也激勵自我向超我(道我)努力,從而再將本我與超我貫通,做到即我即道,夢醒不二,進入無待的自由狀態。
[關鍵詞] 《莊子》 莊周夢蝶 内向傳播 自我 超我
引 言
認識自我,成就自我的永恒呼唤
認識自我,超越自我,成就自我,是人類作爲宇宙精靈的特殊之處。希臘阿波羅神廟牆上有箴言 γν俍θι σεαυτ傕ν (認識你自己;Know yourself),中國哲聖老子亦提出“自知者明”,便是例證。文藝復興時期法國思想家蒙田(Michelde Montagne, 1533—1592)説:“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識自我。”“在各種不同哲學流派之間的一切争論中,這個目標始終未被改變和動摇過: 它已被證明是阿基米德點,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動摇的中心。即使連最極端的懷疑論思想家也從不否認認識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斯特·凱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頁。人類一切認識出發點與歸宿點本質上都是因爲自己,依托自己,安頓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自我也應當是傳播研究的起點與終點。認識自我的重要性,可借羅洛·梅的名言來錨定:“人類的自我意識是他最高品質的根源。它構成了人類區分‘我’與世界這種能力的基礎。它給予了人類留住時間的能力,這僅僅是一種超脱於當前,想象昨天或後天的自己的能力。……是因爲他能够站到一邊,審視他的歷史;因此他能够影響他自己作爲一個人的發展,並且他還能够在較小的程度上影響作爲整體的民族和社會的歷史進程。自我意識的能力還構成了人類使用符號這一能力的基礎……使得我們能够像他人看待我們那樣來看待自己,並能够對他人進行移情……實現這些潛能就是成爲一個人。”(2)羅洛·梅《人的自我尋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6頁。人類能够學習,不僅從自己的經歷中學習,而且也從他人,從歷史的一切文本中學習,其實,學習,特别是那種思想領悟的學習過程本身是一個自我傳播的過程。比如筆者下文要開始的,對《莊子》一書中夢文化的禮贊,正是因爲莊周之夢開啓了一扇人類自我對話和隔空對話的大門。本研究的價值與意義可以表述爲:“個體的活動離不開自我,作爲個體活動的覺察者、調節者與發動者,它可以使個體的活動具有獨特性、一致性與共同性。不同的自我優勢,會引起相應的自我評價與自我追求,進而去尋找理想的自我實現。所有的自我行動,都是自我的外現,其意義在於保持個體的心理平衡,使個體與現實世界的關係和諧。”(3)李海萍《米德與莊子自我理論的現時代意義》,《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
近年來,筆者已發表了《内向傳播的視域下老子的自我觀探析》(2011)、《内向傳播視域下的〈莊子〉“吾喪我”思想新探》(2014)、《作爲儒家内向傳播觀念的“慎獨”》(2015)、《内向傳播視域中的佛教心性論》(2016)、《新子學之“新”: 重建傳統心性之學——以道家“見獨”觀念爲例》(2017)等系列研究華夏内向傳播的論文,試圖從内向傳播理論的視角重新解析中華文化,進而探索出一條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的可能路徑。本文即是從内向傳播視角來進行莊周之夢的新探索。
一、 夢: 一種内向傳播的特殊形態
内向傳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又稱自我傳播或人内傳播。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Donnar.R.Vocate曾在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Different voice, different minds一書的序言中提到,1986年查理斯·羅伯特向當時的口語傳播協會(SCA)提出成立一個内向傳播專業委員會的申請,還引起了不小的争論,從此内向傳播開始進入傳播學的研究視野。總的來説,内向傳播探討的是自我對話(self talk),此時自我作爲傳播者,既是發送者也是接收者(4)Donnar.R.Vocate.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Different voice, different minds. Psychology Press, 1994, p.3-31.。朱麗亞·伍德(Julia Wood):“自我傳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我們與自己進行的交流,或自言自語,或促使自己做某件特殊的事情或是決心不做。……自我傳播是在自身内部進行的認知過程。而且由於思考依賴於語言——用語言爲現象命名、用語言表示現象,因此這就是一種傳播。”(5)朱麗亞·伍德(Julia Wood)《生活中的傳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頁。國内學者郭慶光、陳力丹等對内向傳播都有一定研究,他們都把内向傳播作爲一切傳播的起點,也是一切傳播活動不可缺少的環節。例如,郭慶光在其《傳播學教程》中就認爲,内向傳播爲個人接受外部信息並在人體内部對信息進行處理的過程。國内華夏傳播研究著名學者邵培仁和姚錦雲認爲:“莊子發現了人類‘交流無奈’的内在之因,提出了人類交流理想的實現路徑。交流不在於外‘傳’,而在於内‘受’,思想學説的不可通約與其説是學理上的,不如説是主觀認識上的,即‘成心’。因此,交流過程需要付諸‘接受主體性’的努力,達到‘心齋’和‘坐忘’的狀態,從而恢復一個‘真宰’的精神世界,如‘天府’和‘葆光’一般。”(6)邵培仁、姚錦雲《傳播受體論: 莊子、慧能與王陽明的“接受主體性”》,《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第10期。兩位學者從人際溝通的角度探索人需要棄去成心以營造好的人際交往心理環境。而筆者則進而研究主體内部是如何憑藉自我對話從而實現内心的澄明、清静與徹悟。
(一) 解析與感悟: 中西論夢之别
陳力丹多次撰文闡述夢是一種内向傳播形態的觀點。他説:“每一個人的内心世界裏都有一些白天不知道的經驗和記憶儲藏室,夢則打開了這扇通往自己世界的門。大多數夢使用象徵語言編織而成。象徵語言的邏輯不是由時空這些範疇來控制,而是由激情和聯想來組織。這不是人們在清醒世界裏所通用的語言編碼。所以大部分夢就像是没有被啓封的信,讓我們好像在與自己交流,但又無法與自己交流。”(7)陳力丹《自我傳播的渠道與方式》,《東南傳播》2015年第9期。誠哉斯言!夢本是不同於一般邏輯思維的人類思維的另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的運用往往是在人的專注或焦慮之下産生。專注凝神下産生的夢可能如同門捷列夫發現苯六邊體結構的領悟之夢那個過程一樣,能够直達事物的本質,而焦慮之夢則帶來生理與心理的不安。而莊周夢蝶式的夢則是了悟萬化流行,不拘不滯,物我一體的人生至高境界。
概而言之,西方對“夢”的研究,注重的是作爲心理活動展現的一個視窗,“夢是對很多來自日常生活並全都符合邏輯秩序的思想的替代”(8)佛洛依德《夢的解析》,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07—308頁。。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學、精神病理學方面,往往把夢當成一種精神分析與治療的手段。因爲“夢”通常被認爲是人的潛意識的表現,是許多生理與心理問題的根源所在。如此,通過“夢”的剖析可以掌握個體的心理狀態與精神狀況,這是西方科技理性的體現。即便是對東方心理學有深刻理解的瑞士心理學家卡爾·榮格也説:“夢是一段不由自主的心理活動,它擁有的意識恰好用於清醒時的再複製。”(9)維蕾娜·卡斯特《夢: 潛意識的神秘語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4頁。與此不同的是,《莊子》書中的夢則更多視“夢”爲通向道境、悟境、化境的一個路徑,即坐忘、心齋之後的一種精神狀態。莊周之夢不是普通的生理、心理抑或精神方面的問題,而是境界的升華術,雖然《莊子》書中也有對夢産生的普遍性生理和心理有一定的闡述,但是核心不在於夢本身,而在於以夢喻道,以夢悟道。相對而言,儒家則更多强調的是通過夢來進行道德自律,孔子的周公之夢便是典型。著名學者劉文英説過:“在潛意識的層面上,由於自我意識不能控制,一切善的成分和惡的成分都會暴露無遺。由此,每天人都可以根據自己夢中的所用所爲,對自己的道德盡量做出客觀的評價。”(10)劉文英《孟子的良知説與道德潛意識》,《國際儒學研究》第10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31頁。概而言之,西方之夢研究重在解析,中國之夢研究重在感悟。從共通點而言,二者都希望通過夢的探討,更爲充分認識人的認知規律,並加以引導,以實現身心健康與人格升華。陳力丹就指出:“依然故我,是人内傳播的一種良好狀態,要能够始終知道自己是誰,自己要做什麽,想什麽,自己爲了什麽而做什麽。”(11)陳力丹、陳俊妮《論人内傳播》,《當代傳播》2010年第1期。
(二) 社會性與反身性: 中西自我對話旨趣的殊異性
米德作爲内向傳播理論的創立者,在於他創造性地將自我區分爲主我與客我。客我就是組織化的他者,是社會對自我期待的象徵性表達。而主我則是當下的鮮活的個體存在,具有能動性去召唤客我。從而,使此兩者在對話中實現自我的社會化。不過,應當注意到米德主我、客我觀本是基於社會心理學層面上的觀點。在中國情境下,客我(比如聖人)往往是先驗的、固定的,當然也與經驗相關,因爲没有脱離經驗的先驗,先驗只是在邏輯上存在,即邏輯的先在性。但在具體的情境中,先驗也是可體驗到、領悟到、感知到的“知識”,比如“道”,比如“聖人”。在任何時代下,聖人都是理想的客我,都是“道”在人間的體現,聖人是道的載體。世人通過聖人窺見“道”的意義與價值。這是因爲先驗的東西,離不開經驗的基礎,好比“道”作爲哲學範疇,離不開作爲路意義上的“道”,以及在具體事務中的“導”的功能。
相比於米德社會心理學意義上的主我、客我的自我觀,道家的自我觀則顯得有些吊詭,那就是它往往不滿足於當下的自我,它對主我在認知上既警惕又依賴。警惕的是,主我畢竟不是客我,也不是道我,它是存在不足的,是有七情六欲的,是還行進在通往聖人的路上的自我。但特别重要的是,自我要依賴主我,畢竟是主我主動地以客我爲參照來規範自我、修證自我;離開了主我,客我就没有意義。而且,任何人走向客我的道路都是獨特的,雖然方向是一致的。這就因爲主我注定是獨特的、具體的、有情境的。因此,米德更傾賴於主我,認爲主我富有主動性、創造性和獨立性。
米德認爲客我是建構性的,是主我不斷建構出來的。而道家認爲客我(道我)則更理想性和神聖性,甚至有着無窮的能力,等待主我去召唤,一旦召唤成功,主我就獲得了超越,個體得以成就。相比而言,米德作爲社會學家,關注的是自我的社會性。他提出的主我、客我的自我結構觀,目的也是關注自我如何在社會中自處,人如何與社會互動,進而自我内在進行互動,當然這兩個互動本身也是互動的,可以説是周而復始地進行的。而道家的自我觀的結構關心的是自我的精神超越,追求的是自我對社會的超然與超脱。因此,並不側重去追求社會價值的實現,而是追求個人性靈的安頓。這也正是源於其自我内在結構的設定的殊異性,道家認爲人與道是同構的,人具有道性是能够通達道,並成爲道的自我,且只有成爲道的自我——“道我”,人才是完美的人,才是超人、真人。這一點在《莊子》書中對真人入火不燙、入水不溺、逍遥自適的描述中可見一斑。因此,道家自我的修行講究的是對社會價值的超越與否定,從而在内心深處實現真正的完全的純粹的自由,否則就會成爲進道的障礙。
夢則是一種重要的自我啓示路徑,它啓發自我能够放下主我,關注客我,成就真我。夢,其實是自我内在結構中主我與客我矛盾張力的舒緩者、溝通者。因爲夢具有直觀洞察事物本質的功能。夢的直觀性有助於擺脱日常事項的干擾,直達問題的本質。夢境往往本身是問題的直接展開,因此夢境的感悟是破解現實自我困境的方式。笛卡爾也相信夢與現實一樣具有真實性,並不是一切都需要“眼見爲實”。或許夢中所見,亦是另外一種真實。要不執著於現實的真實,或許正是現實的真實阻礙了我們去瞭解和領悟另一種形態的真實,即無的真實。“人人都在夢中直接經驗和感受到過另一個我們並不能接受爲實體的經驗世界,夢使我們領悟到我們並不是在一個唯一的真實的實體世界中去感覺,我們同樣也在虚無的幻境中信以爲真地去感覺。”(12)高秉江《夢與自我意識確定性》,《學術研究》2004年第2期。
或許正如《駭客帝國》所呈現的那樣,我們夢可能被偷,從而活在别人精心設計的夢境中而不自知。《盜夢空間》以科幻表述夢,其實原型當在於中外傳統對夢的探索,只不過它用上了所謂高科技手段。因此,莊周夢爲蝶,還是蝶夢爲莊周,一時間成爲無解的問題。蝶有没有夢,是人没法體驗的,人所能體驗的是人的夢,蝶或有其自己的夢的形態,或許蝶與人之夢也可以通約,世界本存在無限可能,比如神龜可托夢於宋元君,龍王能托夢於唐太宗。
夢與醒的矛盾,困扰人類數千年。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題,始終還是離不開“我在”,他强調了“我”能够懷疑這一點是不能懷疑的,從而確證了我的存在。而道家對自我是否一定存在並不執著,在道家看來,也許人的最好歸宿是消融於道之中而不自知。因爲任何的“知”都可能會産生焦慮,只有不知之知,才是最後的了脱。有知還是“有”的狀態,無知才是“無”的境界。一切只爲找到真我,實現自我内在的統一,而不是人格分裂,人前人後不一樣。此時,“個體感到自己是獨一無二的、擁有充分的心理穩定性的、不因内部或外部變化而改變的整體”(13)維蕾娜·卡斯特《依然故我》,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87頁。。莊周夢蝶式的夢正是一種找回自我的方式,以夢的方式實現自我覺醒。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希·弗羅姆(Erich Fromm, 1900—1980)曾説:“沉睡之際,我們就以另一種存在形式蘇醒了。我們做夢。”(14)埃里希·弗羅姆《被遺忘的語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頁。夢能够折射自我的狀態,夢甚至可以領悟自我的成長,夢本是我之夢,是爲我而存在的。夢的屬我特性,注定我們必須正視它,利用它,與它共生共存。甚至在西方,學者也越來越意識到,夢是人類反省的路徑。“人們對於夢的認知有了重大轉折: 命運和上帝不再是決定性的因素,只有自身才是關鍵性的因素。夢屬於做夢者,並與其生活狀態有關,對於自我反省者來講,夢的作用不可忽視。”(15)維蕾娜·卡斯特《夢: 潛意識的神秘語言》,第14頁。
二、 莊子以“齊物”的方法重構夢境中的自我
如果説《逍遥遊》是莊門的境界和人生追求目標的話,那麽《齊物論》則應是莊門的心法,是通達逍遥的方法論。無論是“齊-物論”,還是“齊物-論”,其表達的含義是共通的,那就是要去掉“成心”,即去掉物我、他我之分别心和有待心,以“道通爲一”的心態與方法來處理彼此關係,具體可表述爲“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秋水》),“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德充符》),“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天地》)。總而言之,齊物是通道的方法。而齊物作爲方法,説到底是一種思維的技術,是在思維或靈府,或者説在潛意識、無意識中(如夢中),都能够無礙地處理好“物化”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講,莊子之“夢”作爲齊物的心路歷程,是内向傳播的一種特殊形式。筆者已在《内向傳播視域下的〈莊子〉“吾喪我”新探》(17)謝清果《内向傳播視域下的〈莊子〉“吾喪我”新探》,《諸子學刊》(第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中探討“吾喪我”的内向傳播意藴,本文則從“莊周夢蝶”等莊子的夢論中,繼續感悟其獨特的内向傳播智慧。
《齊物論》篇的思路大體如下: 莊周以“吾喪我”立論,提出物論紛呈,皆源於“我”執,當齊同而忘我。進而藉以天籟、地籟、人籟爲喻,指明人類因其紛繁複雜的心理活動,從而陷於“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鬥”的無限焦慮之中。進而點出,造成此焦慮的根源在於“是非”在作梗,而“是非”的判斷標準顯然在於我——“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人的身體百骸自有“真宰”“真君”治之,何勞我操心!而“我”所以操心,乃是因爲“我”有“成心”,即心不虚。而心所以不虚,乃是由人類的語言所帶來的,因爲語言本身是一種遮蔽。“言非吹”,語言畢竟不是“天籟”,能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因此,對待語言,應是“至言不言”,“終日言,未嘗言”。如何擺脱這種“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困境,唯有“莫若以明”,即“用空明若鏡的心靈來觀照萬物”(18)方勇、陸永品《莊子詮評》,巴蜀書社2007年版,第58頁。。這種“以明”的自在自主,本質上是“不用而寓諸庸”,是謂無所用心而心自定自主。具體説來,是“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這樣的心境是“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總之,以無滯於物的超然心境,收放自如地因應物我關係,物來則應,物去不留。
(一) 莊周夢蝶乃是“忘適之適”的夢境
莊子夢論的殊異性在於他石破天驚地提醒人們,夢與醒並非截然分明的。那種平常以爲自己是清醒的,或許自己正處於夢中;而自己處於夢中,尤其是祥和的夢中,正是天道的不可多得的敞開之時,也是自己心靈向道的敞開之時,此時的自我或許正是活得最愜意自然的時刻,正是這種時刻的超越性和創造性,莊子才感歎,大夢誰先覺。人們或許以爲夢是虚幻的,不真實的,覺醒時的自我才是真切的。其實,經驗也告訴我們,覺醒時的自我正因爲有我執、我見,遮蔽了對真常的洞察,正由於我們是使用語言等各種符號的動物,符號所編織的意義之網,時常網羅了我們自己,以致於看不到網外更廣闊的世界。“夢”反而是放下自己的一種方式,在夢中我們超越主體知覺的障礙,開啓了在無意識或潛意識世界的無窮追問,那種更深層的意識往往是不被自我發覺的,而改造自我、升華自我則必須深入這一層面。《莊子·達生》有言: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内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工倕的業務操作臻至化境,即“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此時是“道也,進乎技”,手指與對象之間已没有分别,到底是“指”指向物,還是物追求“指”,彼此已相互轉化,没有分别心於其中稽考。可知“化”境,是心泯,是心死神活的狀態。而“心”直白地講,即是當下自我的意識。而“心”最爲合適的安頓是“知忘是非”,“知”是小知,即間間,而忘是非之“知”是大知,則是閑閑的,亦即安適的。“心”的最高層面當是“忘適之適”,這時候的“心”的狀態是“靈台一而不桎”。鄭開對此解釋説:“‘靈台’即深層意義上的心,‘一而不桎’即非常地專注,没有束縛,非常活躍。”(19)鄭開《莊子哲學講記》,廣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3頁。“靈台”是人心最純粹自然的狀態,不過,“一”當是一心一意,即整體性的,整全的,通暢的,與物和諧遷移。這一境界《列子·黄帝》亦有載:“心凝開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這其中的奥秘就在於“不知”(即“忘”),而此時心則是凝而爲一的,自然天真,活潑自在,任我逍遥。此亦可謂“精通於靈府”,靈府乃精舍,是純粹的靈能,它不是機心所在,而是常心之所居處,正陶淵明所謂“形迹憑化往,靈府常獨閑”。這個靈府好比蜂巢中的蜂王,它是整群蜂的主心骨,但它卻時常安然不動而制群蜂之動。
蘇軾在《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詩》中慨然寫道: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
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
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
此真所謂以藝進道,道寓於藝!兩者相通處在於“遺身”,即忘身,是爲化境,我畫竹與竹畫我已分不清了,正是這種分不清,方可“無窮出清新”,仿佛自然天成。此意境乃是“莊周夢蝶”的翻版。
(二) “莊周夢蝶”喻示在“一成純”中快樂自我
莊子學派繼續了老子開創的“無”的智慧,不執於有,而以無的否定方式實現對自我的圓滿自足。這其實也是莊子内向傳播智慧的源泉所在。因爲衆人只看到正的一面,有的一面,而忽視了反的一面,無的一面。而究其實,此二者相反相成,不可缺少。如果我們把夢看作虚(無),而把醒看作實(有)的話,那麽,“莊周夢蝶”的意藴似乎就更清晰地呈現出來。虚虚實實,實實虚虚,不可執著。夢之虚卻有悟境之實效,而醒之實亦有“分”之區隔,而區隔正是爲了下一次的打破。未有醒之下的種種省思與追問,亦難有夢之中的超越與否定。縱觀《齊物論》,没有對人心之縵、窖、密等真實情境的把握,没有對人生“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困境的憂思,没有對“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的人類思維的反身性、對象性的思考,没有對道與物關係的洞察,没有對道與我關係的貫通追求,没有對人類認識(即“知”)有限性的自我反思,没有對“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的敬意,那麽莊周就只是一個漆園吏。而莊周注定成爲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巨人,就在於他有着“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的孤獨感,又有着一顆終結世間一切苦難的雄心,因此,他是神聖的,他仿佛就是人類自我覺醒的偉大導師,人類和諧相處智慧的奠基者。
在人類過於注重外求,過於注重索取的時代,莊子卻能反其道而行之,向内求,學會放下,學會舍去身心的負累,無論是有形無形的財富榮譽,還是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成見偏見和争强好鬥之心,從而獲得自由與快樂。而自由與快樂才是人生的底色與本質。人不能爲身外之物而迷失自我,逐於物而成爲物的奴隸。
三、 莊周之夢: 實現自我圓融自適的重要路徑
《莊子》書中9篇11處提到“夢”,不過限於篇幅,此處僅圍繞大聖夢、孟孫氏夢和莊周夢蝶這三夢來展開論述。夢其實是人認識對象的另一種表現,一定程度上也是認識自我的路徑。當然,《莊子·大宗師》明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這就是説,作爲道之究竟的載體——真人——是睡覺不做夢的,因爲他安心放心。這一定程度上也説明了夢是作爲意識活動的過程性和對象性,也是人向真人轉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此外,櫟社之夢、髑髏之夢、白龜之夢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教導世人當放下有用無用的計較心和以我觀之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標准觀,啓迪世人放下生死之别,安頓愛生惡死的執著心,指導人們當意識到人的認識的局限性,不要執著自我的理性,因爲理性皆有所困。
(一) 夢如鏡:“大聖夢”的自我鏡像
夢猶如鏡子,可於其中看到自己幼稚可笑,領悟人生苦短與世事無常。《齊物論》有“大聖夢”情節: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這個夢表達了好幾層意義:
其一,夢與現實並不一致,夢中飲酒縱樂,醒來卻因殘酷的現實而哭泣;相反,夢中悲傷哭泣者,醒來或許遇上田獵之快事。或許因此,世人常説夢與現實是相反的。其實也不盡然。就現實性而言,夢有一致有不一致,這也正是夢的奇妙處,也是現實的多樣性。
其二,更爲複雜的是,在做夢之中,不知自己在做夢,而且夢中還夢到自己在做夢,似乎在夢中能够占問夢之究竟。直到覺醒後,才知道是一場夢。經驗告訴我們,許多事情,醒着的時候未必想明白,然而在夢中想通了。由此看來,夢與醒着實是可以轉化的。其實,結合前文,我們可知,莊子其實已經設置了常人與至人的不同。常人則拘於自己的時空與教養,從自己的角度來判斷(自我觀之),因此未能把握正處、正味、正色。至人的神奇之處在於不僅保有外在的自由自在,即“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還“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傷,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而且其内在還可以“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换言之,至人之超越處在於他外生死,泯是非,忘利害,同尊卑。總之,道之境是“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齊物論》)。
其三,大覺而後能知大夢,愚者以爲自己是覺者,沾沾自喜以爲知道。這其實正是小知與大知的區别。愚者(小知)知其一斑以爲全豹。而能知此者,需要“大覺”。大覺是對醒的否定,是對覺與夢的雙重超越,既不自恃己之已知,又不否定夢可啓人感悟,人生便在於夢與醒之中流轉。大夢者,因夢而悟道者,大覺者,反省覺之局限、當下之困,而以夢啓我心智,不輕易否定夢的啓示,也不拘於夢的啓示,只是順勢而趨罷了。
其四,孔丘因拘於禮教而對有道聖人的狀態不解,以至於對其加以否定,從而堵住了自己的進道之階。從這個意義上講,孔丘的才智則如同夢一般,迷惑了他自己,而他卻不知道自己活在自己建構的知識的牢籠之中。而長梧子也自稱自己如此評價孔丘其實也是一種執著,一種判斷,凡爲斷言,便是迷誤。因此,他自稱與孔丘都在做夢,都有局限。這正如黄帝問道的情節中所言的那樣,知道是不知道,不知道是知道。
其五,莊子感歎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夢與醒的界限果真如我們平常知道的那樣嗎?果真不是我們知道的那樣嗎?要衝破這種思想的牢籠,是需要大聖大智,或許需要萬世之長如同旦暮之短那般的探索,方能解脱這一困擾,因爲“人之迷,其日固久”(《道德經》)。我們在語言的家園中生活,語言似乎成爲我們的空氣與皮膚,我們能離得開嗎?而我們不在一定程度上疏離於言語,我們又不能走出自我。豈不悲哉?!莊子開出的藥方是“和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説到底,就是要脱離“有待”的境地。有待便有所困,如同蟬對翅膀的依靠。而莊周夢蝶又何嘗不是一種不得已的隱喻,因爲蝶也需要依靠翅膀。而正在似乎“山重水複疑無路”之際,莊子卻又説出了“物化”的道理,可謂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物化者,陳鼓應先生解釋爲:“物我界限消解,萬物融化爲一。”(20)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2頁。方勇先生解曰:“一種泯滅事物差别,彼我渾然同化的和諧境界。”(21)方勇、陸永品《莊子詮評》,第96頁。總之,與物同化,不分彼此,方是了悟。
漢學家愛蓮心甚至認爲此夢似乎較“莊周夢蝶”更有豐富的内涵。故事的情節確實更爲豐富與曲折,喻義也更爲深刻,當然少了份夢蝶的詩意與快意。“大聖夢”顯得更爲高標而嚴肅,話題有點沉重。大道至簡,或因此故,夢蝶之流傳更廣泛深遠。
(二) 寥天一:“孟孫氏夢”的夢覺合一
《莊子·大宗師》中借孔子與顔回之口談論“孟孫氏之夢”:
顔回問仲尼曰: 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仲尼曰: 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耗精。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没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此例子亦是借“夢”言人當如何處理自我與外物的關係問題,關鍵是要表述如何順物化而不爲自我情緒所左右。莊子學派時常要走打破世人對夢與醒的執著,從而將自我從觀念的束縛中解脱出來的自我升華之道。借助詹姆斯的物質自我、社會自我和精神自我的見解,莊子學派眼中的物質自我主要指人的形體及與形體相關的各類財富;社會自我指人的各種身份和關係;精神自我比較特殊,不同詹姆斯所指人能够指導日常生活的精神理性和精神氣質,以實現對社會生活的應對。具體説來:
其一,不化的精神自我。莊子的精神自我是自我的歸宿,是一種精神,是對現實的超越。例如,生死不入於心中,最終實現的是自我對自我的負責,而不是對社會的負責。在莊子看來,社會的名位是對自我的傷害,只有回避社會價值,回到自我,自我精神才能得到安頓。以孟孫氏之夢的故事來看,與其説孟孫氏在處理喪事,不如説他是在安頓自我,以順應自然安頓自我性靈的方式來安頓亡靈,本身才是最好的安頓。孟孫氏母親過世,他“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這裏的哭泣其實也不是真的,因爲他只是“人哭亦哭”,因順人心,不給自己留下麻煩,此謂“人之所畏不可不畏”(《道德經》)。此是社會自我的順應。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道:“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莊子藉以告訴世人: 大化流行,人的知識有限,面對即將變化的情景,我們何以知道那不變化的情況?遭遇不化的境況,何以知道已然變化的情景?事物的變化多樣,這是事物的常態,也是道的常態。於此,孔子感歎他倆執著於禮教之悲傷情感,固執於名實之别,而未能化。因此,相比於孟孫氏,他倆更像是在做夢還没醒過來呢!爲何孔夫子明明跟顔回談論孟孫氏的事情,又何以説自己是在夢中呢?此處之夢更傾向於從常規意義上表述,那就是不真實的、虚空的,因爲他們只拘泥於形式,而没有把握本真。以人之規範束縛了自我的身心,是一種“困”、一種“累”,如同惡夢一般縈繞在其身上,使其不得歡樂,因此孔子希望速速從中“覺”起,此“覺”是一種破迷而悟的覺境。孔子後文又强調如同作夢化爲飛鳥而一飛沖天,化爲魚兒沉没於深淵,不知此時説話的我們是在夢中,還是在清醒狀態?因爲可能我們是做夢在一起説話,果真在一起説話了嗎?最後作者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適,本身是一種身心安適的狀態,這種狀態不用情緒去表達,一落言詮,便不自然;不期然而笑,笑得那麽自然,没有任何做作刻意安排於其中。總之,順應自然的安排去變化,如此便能進入寥遠天然的純一之境,無夢無覺,亦夢亦覺。
其二,“駭形旦宅”的物質我。我哭之時,旁人都以爲這就是“我”,他們哪裏知道那果真不是我。也就是説,旁人看到的是人的形,而不是我的神。而他哭所以“無涕”,乃是因爲他“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耗精”。形可駭(變化)而心無損,有軀體的轉化而没有精神的損耗。這種信念本是“通天下一氣”的表現。此爲莊子對形體我的態度,更不用説對財富名譽等均視爲浮雲了,此爲莊子的“物質我”。
其三,“是其所以乃”的社會我。孟氏的社會自我體現在“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常人的社會自我是有先後、生死所體現的利益關係的杯葛,而孟孫氏則“不知”,用現在的話説,他不把社會的規範内化我自己的規範。生死之哀不起,先後之得失不較,此時狀態就好比隨順事物的變化,以此處置那人力不可知的變化。
(三) 自我與超我:“莊周夢蝶”的“物化”啓示
《莊子·齊物論》結語曰: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1. “莊周夢蝶”: 在本我與超我之間的夢境
“莊周夢蝶”的情境是莊周式的,但做夢變爲某種生物,如鳥、魚、花之類,則是人類的常態。然而此故事寥寥數語,卻有着無窮意境,其根源當在於對人性的追問。蝴蝶其實是自我的鏡像,深入言之,是超我的表徵,蝴蝶不是當下的自我,而是自我的究竟,自我的了脱。顯而易見,“莊周夢蝶”直接表現的是莊周這個“自我”(ego),蝴蝶則應是超我的表徵。當然,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本我(id),作爲萬物之一的我。因爲莊周講究的是物我兩忘,當然,他反對以物役我,而是役物而不役於物,與物偕行。如此,我們就可以抽象地繼承佛洛依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自我觀,但在内涵上加以改造。那就是,在莊周看來,本我是一種作爲萬物之一的我,没有人的特殊性,而具有物的共性,没有人的優勢感與分别感。自我,則是處於社會情境中的我,是現實中操作的自我的提升與沉淪的我。超我,則是人作爲類的存在的高尚性體現,抑或人作爲文化的動物而産生的對終極真理的關懷與自我的永恒安頓的主體。其實,人作爲進化中的過程存在物,時刻是本我,自我、超我共處於一身,本我的快樂原則易於迷失於衆生之中,自我的現實原則則是在有時易於成爲有違道義的小人與有時易於成爲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人這兩端之間擺動,而端賴於自己的靈能如何驅使自我。“莊周夢蝶”則意喻自我的提升與超越。
有學者富有創意地將蝴蝶視爲本我,將莊周視爲佛洛依德的自我,並認爲本我有走向死亡本能,自我則有充滿愛欲的力比多,展示求生的本能。莊周力圖追求“本我”(id)對“自我”(ego)的戰勝,這便是逍遥遊(22)馬薈苓、王愛敏《從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解讀莊周夢蝶》,《湖南第一師範學報》2010年第5期。。不過,筆者認爲,夢蝶既然作爲追求自由的象徵,應當是“超我”的體現,而“莊周”則代表現實理性的自我。遊之類的逍遥在莊子看來是可以實現的,那就是與道爲一,也就是“物化”,亦即齊物。道是自我的消融,是本我與超我的貫通,但不能因此説自我是障礙,因爲超我的追求恰恰需要“自我”的操控,自我最終埋葬了自我,這是自我的最大歸宿。自我遵循現實原則,一直探討在本我的快樂原則與超我的自由原則的平衡。放縱快樂原則終究害人害己,而如果不能安撫本我的快樂原則,那麽超我的實現也就没有動力。本我與超我似乎是兩極,其實,在莊子看來二者是相通的,這個相能的橋樑便是“道”。道是“率性之謂道”,道是性的本然實現,不過性是“天命之謂性”,是天然的,是純粹的,而不是弗氏所强調充滿性欲的本能。進而“修道之謂教”,是需要在修持之中不斷去磨合自己的心性,將本我、自我與超我合一,並以超我爲主導。道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卻是人的意志可以感通的,因此就需要去“修”。這個“修”在莊子看來正是“心齋”“坐忘”,就是逍遥遊,就是萬物相和之境的“無死地”(《道德經》)。“莊周夢蝶”所以流行,正是其文本的象徵意義深遠,富有無窮的詮釋空間。本我是原始的,非理性的,本能的;而超我則是理想的自我,是道德理念,是富於升華的,悟性的,超越性的。若没有本我,又何來超我?“莊周夢蝶”表面上只有莊周與蝴蝶兩者,其實還有道,亦即道我。因爲一切都因爲有我才有了意義。没有“莊周”這一現實的自我,蝴蝶和高遠的道没有任何意義。因此,筆者認爲,蝴蝶與髑髏都是道的影子。
2. 夢: 通向覺醒之知的媒介
莊周與蝴蝶之間所以發生關聯是夢的接引。“夢”所以能接引而發揮媒介的作用,則因主體必有所求。“求以得,有罪以免”的欲望實現,如同蝴蝶的自由飛翔,而這一切的前提是要進入夢(道)。蝴蝶作爲物的存在是有限的,有形的,有名的,短暫的,而只有道才是永恒的,無名的,無形的,正如夢境一般神妙奇幻。物不化,則有阻隔。因爲莊周之爲莊周,他意識到物必有分,正因爲物之分,則物之爲物,而不能爲物物之物的道。
其一,夢——開啓深層自我認知的按鈕。“夢”的内向傳播過程何在,關係互動性何在?唯在一“化”中,蝴蝶本身就是由毛毛蟲轉化而來的,喻意“道”具有化腐朽爲神奇的功能。經歷由蛹到蝶的轉變,這個去繭的過程,是孕育新生命的過程,即化的過程。生命必須有所捨棄,才能實現超越。具體説來,“化”體現爲“坐忘”,可以是“心齋”,可以是“吾喪我”。在此類情景下,莊周易於夢爲胡蝶,易於進入自我超越之境。换句話説,在此心境下,自我易於退位,超我易於上位,本我則易於消隱轉化,進而呈現一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和諧場景。
吴光明在《尼采與莊子》一文中認爲:
通過反思他的夢,莊子獲得了一種覺醒之知: 我們不能知道我們不變的身份。正是這種知,使做夢者(我們自己)從被客觀實在論纏住的專横中解放出來。這是一種元知識,一種對自己無知的覺醒。這一覺醒的無知導致在本體論轉化之流中的逍遥遊。(23)愛蓮心《嚮往心靈轉化的莊子: 内篇分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頁。
莊周夢蝶之夢所以是好夢,因爲蝴蝶“栩栩然”生動活潑,而又“自喻適志”,即心靈似乎在盡情地訴説志向的舒適實現,即這種實現是没有代價的,是自然而然的。如同庖丁解牛一般,遊刃有餘,臻於舞曲之境。夢中之蝶已然不是現實中的蝶那樣有生有死,而是不生不死的永恒自在,此時,蝴蝶的快樂是没有條件,也是不需要等待的,是謂“無待”。無待,即消融了現實的我與理想我的界線,即無我而有真我。無待本亦是無的一種形式,無是一種否定,更是一種超越。鄭開亦解説:“‘無待’就是指我們所進入的獨立且自由的狀態。我們既不需要憑藉某種東西,同時,又將所有的外部條件統統去除,進而,將真正的‘我’釋放、發揮出來,這便是‘無待’思想的精義。”(24)鄭開《莊子哲學講記》,第207頁。或者,無待就是物我距離消融了,物我合一,蝶我合一,是謂“物化”,此時“出於無有,入於無間”(《道德經》),即謂“適志”,心想事成。依徐復觀所言“唯有物化後的孤立的知覺,把自己與對象,都從時間與空間中切斷了,自己與對象,自然會冥合而成爲主客合一。……此時與環境、與世界得到大融合,得到大自由,此即莊子之所謂‘和’,所謂‘遊’。”(25)徐復觀《遊心太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頁。
其二,醒——夢後的大覺。海外華人學者吴光明指出“莊周夢蝶”還包含着夢與醒之外的第三個階段——大醒。大醒即“從醒中醒”,即“莊周認爲他不是胡蝶爲‘醒’,莊周不確定他是莊周還是胡蝶則代表他從這個醒中‘醒來’”。(26)Kuang-ming Wu. The Butterfly as Companion[M].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217.這種深沉的“大醒”,會帶來“知不知”的認知轉化。“知不知”的瞬間感悟,如同瀕死體驗一樣,一下子便明白了活着時的迷昧、死時的明白。
莊周有名,成形了,則必有成心,而蝴蝶没有具體的名,故而是整全的,没有分化的,乃是永恒的。“胡蝶的精髓在於‘栩栩然’的翩翩飛舞——它從一個思想飛向另一個思想,從一個事件飛向另一個事件……它不否認夢與醒、現實與幻想、知與無知……它所能確定的,只是它從此‘飛’到彼的狀態。”(27)郭晨《吴光明與愛蓮心“莊周夢蝶”的闡釋比較》,《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蝴蝶是莊周力欲超脱的精神指稱,是精神形式的莊周,即自喻其適的莊周,而“蘧蘧然”覺醒狀態的莊周則是物質形式和社會形式的莊周。此二者統一於莊周一身,又是分離的。因爲精神狀態的“我”是可以超越或忘記身體或關係形態的自我,故有“缸中之腦”一説。飛是一種穿越,從夢到醒到大醒,即悟,即由覺而悟。蝴蝶顯然是莊周精神的投射。蝴蝶在别人看來可能是他者,但是蝴蝶在莊周看來則是從他者回歸自身,進而反觀自身,在這個過程中便是從與他者(蝴蝶)的對話(心靈感通)中,實現對自我與他者的同時“去蔽”,即同時實現對物化的順應,而齊一,最終通過關注他者而實現回歸自我的完整齊一,即靈與肉的統一。
正如漢學家愛蓮心所説的,蝴蝶這一意象的選擇,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它本身是“化”的現實表徵。蝴蝶從毛毛蟲到蛹,再到蝴蝶,實現了華麗的轉型(transformation),即“轉型爲胡蝶必須蜕掉原有的皮。這點表明僅有舊事物讓位於新事物時,轉型才會實現。且此種轉型是一種内部轉變,不需要任何外在媒介”(28)Robert E Allinson. 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Chapters[M].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p.74。
夢蝶中所提到的“物化”,在《天道》篇表述爲“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相似的表達亦現於《刻意》——“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既然天行與物化對舉,那麽其含義就應當是相對的。物化即天行,是天道自然而然的一種運動。人主動地進入天行物化之境,是聖人之爲,其境界是“天樂”,本然的快樂,而非人欲之樂。莊子在“寐”和“覺”的轉變中(其實亦即在“物化”中)體會到了自身的酣暢淋漓,此正所謂“大醒”。莊子並不停滯於對覺中的懊惱,而是於這一轉變中感悟到,自然之道不可違。唯有將自我與道相通,即主我與客我合一,才能形神俱妙,快意人生。因此之故,他以各類形體殘缺,但精神圓滿自足之人,來進一步展現“齊物”的奥妙。萬物與我爲一,“我”與萬物在大化流行中互爲主體,彼此相通相化,“物有分,化則一也”(29)馬其昶《莊子故》,引自錢穆《莊子纂箋》,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頁。。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學派在《知北遊》篇中亦有言“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似乎是否定“物化”,不過,此處表述是“與物化”,而非“物化”。羅勉道解得好:“外化而内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内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爲事物所撑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内不化也。”(30)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道藏》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頁。“古之人”是人心純樸之世的人,亦即莊子心中的理想人物,他們“外化而内不化”,是“承認並隨順外界的變化,與之一起遷移,但卻保持自己的真然本性,保持内心的真宰,保持内心之真,不‘喪己於物’”(31)奚彦輝、高申春《心理學視角的〈莊子〉自我觀探究》,《心理研究》2008年第2期。。
可見,“與物化者”是主體隨着他者變化,喪失了主體性,失去了自由與自在,不由自主。而“物化”則是表徵物的齊一性與貫通性,物與物、我與物都緊密無間,没有分别。“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32)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頁。。物化是物之常,道之常。“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天道》)人順道而爲,與物無傷。“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秋水》)
“莊周夢蝶”流露出莊子自我超越的意向,表達出對物我兩忘境界的追求與嚮往,同時也表達了對物我二分的常規思想的批判。正如弗洛姆所言,人的創造性工作是一種物我合一狀態:“在每一種創造性工作中,創造者同他的工作材料結合爲一,工作材料代表了整個外部世界。無論是木匠做一張桌子,還是金匠打一件首飾;無論是農民種莊稼,還是畫家作畫——在所有這些創造性工作中,工作者與對象都合二爲一,人在創造過程中將自己與世界結合起來。”(33)弗洛姆《愛的藝術》,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2頁。此所謂“道進乎技”。最徹底的創造性精神活動,便是自我的形與神的美妙統一,實現形之安順,神之靈妙,夢當是其最貼切的表徵。“莊周夢蝶”之夢不是精神狂亂之夢,身體狂躁之夢,而是形就神和之夢。此種吉祥之夢本身是身心放鬆的表現。
弗羅姆還認爲:“人——所有時代和所有文化之中的人——永遠都面臨着同一個問題和同一個方案,即: 如何克服這種疏離感,如何實現與他人整合,如何超越個體的生命,如何找到同一。”(34)同上,第14頁。在莊子看來,人源於道(齊一),因此人從本性上有着嚮往“道”那齊一且永恒安頓的訴求。人總感覺自身是被抛到世上的孤獨的存在者,生不能卻,死又不能止,即便他有親人,有朋友,他們也都只是共同通向“一”的橋樑,人在和諧的關係上更易於趨向本質上是以和諧爲特徵的“道”。莊子學派意識到人在内心深處有着拘於形體的現實自我,追求現實原則,又有一個追求超越,不滿當下,追求無形境界的超我。正因爲有對超我的追求,才體現了人的爲萬物之靈的高貴所在。一般人追求的是物與我的分别,於分别上顯示自我的殊異性;而聖人則反之,在物與我差别的消融中,展現自我的高貴性。上文已言的“大聖夢”啓示我們: 夢是實現超越的媒介。因爲(大)夢聯繫着醒(覺)與解。通常的睡與醒的反覆,如同處於鈞(製陶器所用的轉輪)之上,令人苦不堪言。而莊周夢蝶式的大夢,則産生了對睡與醒(覺)界限的消解,不認爲醒時才是真實的,而夢中是虚幻的;反而正是因爲有夢的觸媒,讓人放下了執著,達到“悟”的境地。夢真乃造化的神奇表現。不過,白龜之夢則既表明物我可以感通,但同時也説明了理性是有窮困之虞的。
劉文英指明蝴蝶夢狀態就是“與大道合二而一”狀態:“如果從藝術形象來看,我們可以把胡蝶夢中的胡蝶,視爲大道的一個象徵性符號,而‘夢爲胡蝶’則意味着莊子得道,與大道合二而一。若就思想境界而論,胡蝶夢中的‘不知周也’,亦即‘至人無己’的形象化,表明莊子自認爲他已達到至人的境界了。”(35)劉文英《莊子胡蝶夢的新解讀》,《文史哲》2003年第5期。故而,蝴蝶夢暗示主體精神的自由快適,蝴蝶夢的境界也就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境界,是物我齊一的物化狀態,是齊同物我狀態下逍遥自得、無掛無礙的自由境界,是物化的最高境界。
綜上所述,《莊子》書中的“夢”是通向自我内在結構(主我與客我)的消融的重要方式,也是實現自我升華的路徑。因此,引入内向傳播的理論視角,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剖析《莊子》的自我觀,並進而實現中西内向傳播理論的跨越時間的對話,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