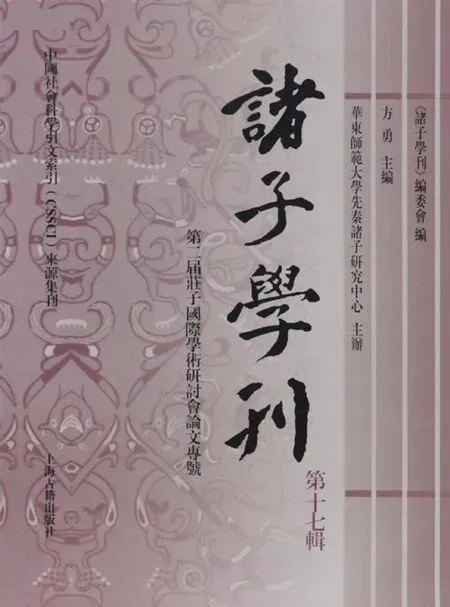《莊子辨解》中韓元震對莊子思想的理解
2018-01-23韓國曹玟焕
[韓國] 曹玟焕
内容提要 朝鮮儒家學者們通過理氣心性論來區分正學和異端,並以此批判異端,這當中包含着是否正確理解作爲“形而上者”的道和“本源上達處”。南塘韓元震爲《莊子》作注稱,這種標準適用於評判莊子思想,並把他的箋注稱作《莊子辨解》。韓元震把莊子思想規定爲“彌近理而大亂真”的具體内容,正符合於他對異端的認識。韓元震認爲《齊物論》中莊子把“一本萬殊”都看作是氣,即莊子所説的是“氣一分殊”,而“氣一”中的“氣”就是莊子所説的虚無的道。與儒家所説的“理一分殊”相比,莊子則説“氣一分殊”,那麽“理一分殊”與“氣一分殊”的根本差異就在於理和氣的差異。若要理解韓元震對莊子思想批判的核心,站在主張“理一分殊”的儒家立場來看,有必要考察以“虚無爲道,齊物爲宗旨”與“主張氣一分殊”的莊子思想中存在的問題。儒學和異端的不同在於——他們分别“把性和道當作什麽”,以及怎麽認識理和氣中哪個是使役者、哪個是施令者。具體而言,儒學以理爲“性和道”,異端以氣爲“性和道”;儒學主張“以理御氣”和“氣聽命於理”,而異端學主張“以氣役理”和“理反聽命於氣”。最後,韓元震通過把理和氣是當作“一物”還是“兩物”來展開對異端的考察。異端把理和氣看作一體,即“認氣爲理”。從這一點來看,老佛以來異端之説顯現的弊端,都是源於“認氣爲理”。“認氣爲理”和“認心爲性”是韓元震在《莊子辯解》中批判莊子思想的核心。在韓元震看來,莊子當作至道的混沌屬於前陽已滅餘下的“陰静”,因此莊子雖然以混沌爲至道,但他不知道這個混沌並非儒家所説的形而上者的道,實際上他所説的道是“天地未辟”、“萬物未生之前”的“一陰之静”,以此爲道實非真道。莊子的這種思維不僅不明白儒家所説的“陰陽無始”和“動静無端”的道理,也不理解“一陰一陽之謂道”,他也不清楚陰陽和動静之上更有太極之道。
[關鍵詞] 韓元震 莊子辨解 彌近理而大亂 真認氣爲理 認心爲性 認氣爲道
序 言
程頤和朱熹等宋代儒家學者在確定理學理論的過程中,受到佛教和老莊思想的影響。但是在堅持儒家道統論、强化正統的過程中,他們把佛教和道家當作異端加以批判和排斥。這種現象在實施崇儒抑佛政策、以儒學爲國教的朝鮮儒家學者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
鄭道傳(1342—1598)在《心理氣篇·理諭心氣》一文中,通過儒家的義理之正曉諭了道家和佛家,並指出了他們的錯誤,得出了“道家氣以爲道,佛家心以爲宗”(1)鄭道傳《三峰集》卷之十《心理氣篇·理論心氣》,“此篇,主言儒家義理之正,以曉諭二氏,使知其非也。理者,心之所稟之德而氣之所由生也……氣以爲道,心以爲宗。”的結論。對這個見解,權近(1352—1409)注釋稱“道家和佛家不知道形而上者爲何物”(2)權近對鄭道傳《三峰集》卷之十《心理氣篇·理諭心氣》之“氣以爲道,心以爲宗”作注:“此二家自以爲無上高妙,而不知形而上者爲何物,卒指形而下者而爲言,陷於淺近迂僻之中而不自知也。”可參。,李滉(1601—1670)稱儒家以“踐理”爲主,而老莊思想則偏向於“養氣”,結果帶來了“賊性”的結果(3)李滉《退溪全書》卷之十二《與樸澤之》云:“主於踐理者,養氣在其中,聖賢是也。偏於養氣者,必至於賊性,老莊是也。”。與此相似,朝鮮儒家學者們也通過理氣心性論來區分正學和異端,通過理氣心性論批判異端,這其中包含着是否正確理解作爲“形而上者”的道和“本源上達處”。南塘韓元震(1682—1751)(4)韓元震,字德昭,號南塘。他跟李柬發起湖洛論争,引起湖西地域學者的湖論。韓元震主張人具備所有的五常,與此相比,草木禽獸之類的物體只偏向其中一個,這就是人性和物性的根本區别。爲《莊子》作注稱這種標準適用於莊子思想,並把他的箋注稱作《莊子辨解》(5)韓元震《莊子辨解·序文》曰:“特于其本原上達處,有所未及者,而肆言之。故其弊遂至於異端賊道之甚者矣。學之不可不達本源也。”。韓元震在《莊子辨解》一書中通過“周之見(處)”這樣的表述來整理莊子所説的思維,通過“莊周”、“莊生”這種表述來輕視莊子,有時也稱“老莊”,對老莊思想進行總體批判,同時他也從比較的角度,通過“吾儒”的表述道出了儒學思想和莊子思想的異同點。
儒學主張“物之不齊”,這種“物之不齊”要求分别理解現實(6)《孟子·滕文公上》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韓元震認爲無分之説是異端之説的特徵。無分就是“人獸無分”、“儒釋無分”和“華夷無分”(7)韓元震《南塘集》卷之二十《答權亨叔(丁卯八月别紙)》:“自古異端之説,皆是無分之説也。老莊齊物,告子生之謂性,皆是也。今之學者,以人物之性,謂同具五常,是人獸無分也。釋氏曰心善,而儒者亦曰心善,是儒釋無分也。推尊許衡,以爲聖門真儒,即以爲真儒,則當學其人,是華夷無分也。此三説者,將爲吾道無窮之害,所恃而衛道者,唯高明也,把此題目明辨之,如何?”。這種“無分之説”也可適用於他的異端觀和人物性同異論。韓元震雖然承認莊子思想屬於高層次思想,但他也例舉了莊子思想是異端的理由,他認爲莊子思想公私不分、包含着有害于儒家以仁義爲根本的内容(8)《莊子辨解·大宗師》:“義而無意於爲義,仁而無意於爲仁,故曰不爲義,不爲仁。上文聖人之不失人心,不爲愛人,意亦與此同。然無所爲而爲仁義,仁義之真,而天理之公也。有所爲而爲仁義,仁義之賊而人欲之私也。真者,可謂仁義;賊者,不可謂仁義,則君子于此,當辨其公私之辨分而已。又何必惡其名而並去之哉?此周之學,所謂過高而爲異端也。”。同時他還對莊子的出世進行批判。韓元震説“‘學習孔子學的人’有必要清楚地瞭解莊子通過‘無心無迹’來‘全身遠害’”,他還把莊子比喻成鄉願(9)《莊子辨解·人間世》:“前段以知術御人爲不可,而此以無心無迹爲可,則似乎非知術者然。所謂無心無迹者,實要以全身遠害,而又没其痕迹,不使人覺知,則乃其用智術之深者也。……蓋此篇專以全身遠害爲至人之能事,則周之學,蓋無異於鄉願之媚世取容者,而其用意深微,托言高抗,使人莫覺其爲私邪鄙陋之學,則其爲亂德之深視鄉願,又不啻九萬里矣。爲孔子之學者,可不明辨而深辟之哉?”。他説,從儒學强調通過殺身成仁、克己復禮等利他的人生立場來看,莊子通過“無心無迹”來“全身遠害”的行爲並非正確的舉動。
韓元震特别通過《莊子辨解》闡明莊子完全不理解儒家提出的道的本質以及有關的“本源上達處”。他追求正確理解“本源上達處”,因爲在結局“下學”的層次上,這個“本源上達處”非常適用于人生現場。他還通過“彌近理而大亂真”的表述象徵性地批判了莊子思想的這一問題。
韓元震稱,在完全不理解“本源上達處”的“彌近理而大亂真”的話中,莊子思想與儒家的形而上學有相似之處。如果不理解這個相似點,在現實生活中就會出現無法判斷善惡的大問題。緊接着,他總結了莊子思想和儒學思想的不同,以及這些不同之處對實踐的人生和現實生活造成了哪些影響。因此,本文主要是探討韓元震通過《莊子辨解》批判莊子思想的具體内容是什麽。
一、 韓元震著述《莊子辨解》的動機
首先,我們來看看韓元震著述《莊子辨解》的動機。他曾讀過《莊子》並喜歡它的古奇,但因爲没能完全理解它的深意所以就没再讀過。後來他的朋友成君覺請他教授《莊子》,因此復取而讀之,經過反覆研讀,終於有所領悟——即他所説的莊子思想是“彌近理而大亂真”(10)《莊子辨解·序文》云:“余少也,讀莊生書,雖喜其文章之古奇,亦不能深解其意,廢而不復觀者久矣。今年冬友人成君覺請授是書,復取而讀之,反覆數遍,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始見其爲彌近理而大亂真也。”。“彌近理而大亂真”這句話是朱熹指摘作爲異端的老、佛學説時使用的象徵語。韓元震把莊子思想定爲“彌近理而大亂真”後,參照《莊子》既有的注釋開始重新揣摩莊子思想,結果發現既存的《莊子》注釋都是郢書燕説,曲解原意。在箋注《莊子辨解》之前,他對莊子思想持否定態度,因此起初他並不想給《莊子》作“箋注”(11)《莊子辨解·序文》:“既而又取諸家注説而觀之,蓋皆郢書燕説耳,殆如余前日之於是書也。於是盡棄其説,更以吾説授之。既卒業,君覺請録其説。余曰:‘余雖力微,不能焚絶其書,顧何忍爲箋注,雖甚不腆,亦何可甘心爲周之所謂萬世一遇之聖人與!’”。當成君覺請韓元震就其書而明辨之,要讓“詖淫邪遁”的莊子學説無所遁形于天下後世時,韓元震爲了正確理解和批判莊子思想,于是給《莊子》作箋注,並將其命名爲《莊子辨解》(12)《莊子辨解·序文》:“君覺曰:‘不然。是書之行於天下久矣。今不可以焚絶,既不能焚絶,則無寧就其書而明辨之,使其詖淫邪遁之説,無所遁於天下後世,亦豈不爲吾儒之一大快事也?’余曰:‘然。誠若子言,庶幾免于君子譏乎!’遂令執筆書之,盡内篇而止。蓋以内篇既明,余不待解説而明矣。録既成,名之曰莊子辨解。因略識其撰述之意。”。他得出結論説,莊子有“本源上達處”的問題,因爲他隨意表達自己的思想,所以類似於莊子思想的這種異端會對儒家所指向的道帶來極大傷害。
把莊子思想理解成爲“詖淫邪遁”,是推尊孔朱(孔子和朱熹)的朝鮮時代儒學者們的共識。韓元震整理《莊子》内篇,最終得出的結論是: 莊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以虚無爲道,以齊物爲宗旨”,他把莊子思想基本評價爲“彌近理而大亂真”。當然,他在《莊子辨解》一書中並不只是無條件地批判,對莊子文章的叙述方式和細緻用意他還是作出了肯定的評價。他説,莊子通過高遠的見識和奇異的文體展開論述,唯讀一兩遍是無法理解的。而且,如果單單認爲《莊子》文筆没有倫序、語言奇峭富麗的話,可以説根本没有讀懂該書(13)《莊子辨解·逍遥遊》:“夫謂莊周之文,無有倫序,而特其句語之奇而已者,可謂不知讀周之文矣。”,特别是因爲《莊子》大量使用寓言,所以不能僅僅糾纏於語言文字(14)《莊子辨解·逍遥遊》:“周之文,大抵皆寓言,讀者當看其主意所在,不可直就言語文字而求之也。”。
韓元震只給《莊子》内篇(七篇)作了箋注,因爲他認爲只要明白了《莊子》内篇,外篇和雜篇就都能自然理解了。此外,他還評價莊子的論旨展開很有條理,邏輯性很强。在《莊子辨解》中,他作箋注的方法是,首先在開篇説明“前篇的大旨”,然後把各篇的經文分成若干段落進行論述。同時,還把每一個句子包含的意思跟各篇的整體内容聯繫起來,進行詳細地分析。韓元震通過“前篇言……”的表述方式,即首先指出前篇所説的核心内容,然後再説明前篇與後篇之間有着怎樣的聯繫,把《莊子》内篇(七篇)解釋成了一個連續性的體系。
韓元震分析説,“至人之大道”(《逍遥遊》)與齊一萬物、齊一的作用有關(《齊物論》),如果是事物不損傷自己的齊物,就能養生(《養生主》);得以養生的話内裏就會得道,然後可以行世(《人間世》);如能養生和正確處世,德就會充實並符合内外(《德充符》);成就了德就是從根本上得道(《大宗師》);而從根本上得道就能成爲帝王(《應帝王》)。韓元震做上述的分析是爲了説明莊子很有邏輯地展開自己的思想。他特别肯定了《齊物論》的叙述方式。他説,《齊物論》雖然説的是“喪我”和“物化”,但“喪我”就是“齊物”之意,“物化”就是“物齊”,二者實互爲表裏(15)《莊子辨解·齊物論》:“此一段總結一篇齊物之意,與上文風竅之説相爲表裏,物化二字,又結一段之意,而與篇首喪我二字相應。喪我者,齊物之謂也。物化者,物齊之謂也。”又曰:“(《齊物論》)此篇篇首,即舉喪我二字,以示齊物之方,篇末復出物化二字,以證物齊之實,中間,又説道樞二字,以指齊物之本。”可參。。
此外,韓元震整理《齊物論》,稱其開篇的“喪我”提示了“齊物的方法”,結尾的“物化”證明了“物齊的實體”,而中間的“道樞”指的是“齊物的根本”。他説,《莊子》的文章似乎没有倫序、但指意非常有條理,不過若驟然一看仍然無法明白其中含義(16)《莊子辨解·應帝王》曰:“一篇之中,屢更其端,面目常新,若無倫序,而指意所存,卻自不亂,一串貫來,條理整暇,而變化出没,藏其妙用,使人驟看,莫覺其然,此政莊生爲文高處,手段能處。他篇仿此。”。具體而言,因爲《齊物論》借寓言來揭露真實,如果達不到得意忘言的境地則很難完整地理解這部書;也因爲文字神奇,所以只有熟讀才能明白其義(17)《莊子辨解·齊物論》:“此篇蓋周之文,用意最深者,故始合而分,至中而復合,既合而分,至末而復合,假寓言而談實相,語雖幻而意獨至,苟非得意而忘言者,難乎讀是書矣。若論其文字之體,則句句神,字字奇,熟讀可見。”。莊子的見處非常高,曾給《莊子》作注的人都没能完全理解他的見處和文字(18)《莊子辨解·齊物論》:“蓋周之見處亦高矣,其文亦奇矣。然自有周書以來,注家非一,而未有能識其見處,解其文字者,則周之自期於萬世者,亦可謂不誣矣。”。這一點跟韓元震著《莊子辨解》的動機有關。
當然,韓元震並不只是肯定《莊子》的文章,他也指出了莊子思想中包含的跟儒家思想相同的地方。例如,《養生主》和《人間世》所説的内容與儒學的修身和行己相同,《應帝王》所言跟儒學的治國平天下相同(19)《莊子辨解·應帝王》:“《養生主》《人間世》如吾儒之修身行己,《應帝王》如吾儒之治國平天下也。”,《莊子》内篇的結構與《大學》八條目的結構相應等。他認爲,尤其是在程朱學説未出之前,莊子對儒家六經的理解,以提綱式論説得極爲清楚,完全把握了儒家聖人的意思。韓元震從這一點上肯定了莊子學問的高深(20)《莊子辨解·序文》:“又按周生論六經之旨,曰《詩》以道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程朱未出之前,能以一言提其綱而論之,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然則周之學不可謂不深矣,其于聖人之意,亦不可謂不知也。”。站在哲學史的角度,他也對莊子充滿意味的發言給予了認證。莊子在《齊物論》中第一次提出“六合之外”這個新的空間概念,他的遠大境地也不是淺薄之人可比的(21)《莊子辨解·齊物論》:“六合之外,周之前未有言者,而周始言之。周之見處,亦自遠大,非淺夫之所可方也。存而不論之説,亦可謂知聖人之意。”。
如上所述,韓元震從兩個立場來理解《莊子》,一個是文學的立場,一個是哲學的立場。在這兩個立場中,韓元震著述《莊子辨解》,把莊子思想理解成“彌近理而大亂真”並對其進行批判,這一點與莊子思想對當時儒學支配下的朝鮮社會施加了某些否定影響有關。韓元震稱莊子思想是“彌近理而大亂真”並對此加以排斥,這與他指責莊子並未正確理解儒家的道以及無法達到儒家所追求的“本源上達處”有關。
二、 “彌近理而大亂真”的異端觀
韓元震把莊子思想規定爲“彌近理而大亂真”的具體内容,符合於他對異端的認識。如前所述,韓元震對莊子思想所做的解釋與儒家思想的理解雖然有共感上的一致性,但他最終是要確認莊子思想與儒家思想存在哪些差異之處並對之進行批判,這才是關鍵所在。對莊子思想最象徵性的表述就是“彌近理而大亂真”,那麽哪些内容是“彌近理而大亂真”呢?接下來,我們通過對《齊物論》的理解來探討這一問題。
莊子思想被規定爲“彌近理而大亂真”時,最大的問題是跟如何理解莊子所説的萬物齊同的《齊物論》有關。理解《齊物論》的方式從廣義來説有兩個,一個是“齊一萬物論”(即“齊物”論),另一個是“齊一物論”(即齊“物論”)。而選取這兩種解釋中的任何一種都會造成對《齊物論》理解的不同。韓元震選擇從“齊一物論”來理解。這種情況下,“齊一的是什麽”與相關的“主宰者”、“形而上者”是什麽就成爲問題。
韓元震通過“衆”來把握“物”,認爲“物論”就意味着“衆論”,而知識或言識就是“物論”。他認爲知識或言識都是通過後天學習獲得的,人類通過相同的知識和言識來區分是非善惡、表達自己的主張(22)《莊子辨解·齊物論》:“物論猶言衆論也。……知識言識,即所謂物論也。”。他還認爲這種物論由内心接觸事物而形成,因接觸事物的感動不同,導致“物論”也不同(23)《莊子辨解·齊物論》曰:“事物之日接於心,物論之所有生也。”又曰:“接物感動之不同,物論之所以不同也。”可參照。。“物論”有極其多的理由辨别是非,而辨别這種是非的根源就在於七情的感應(24)《莊子辨解·齊物論》:“物論至紛,而不過是非兩端,是非之興,又不過原於七情之感應。”。
對韓元震的這個分析,我們聯繫《齊物論》的“天籟”寓言來討論。他認爲“吹萬不同”的“寓言”就是作爲天籟的“衆口之言”,即物論(25)《莊子辨解·齊物論》:“吹萬言天籟,吹萬即衆口之言,即所謂物論也。”。韓元震把“齊一”的“一”作爲真宰的天來理解這個“衆論”,而且把它理解成莊子説的虚無的道(26)《莊子辨解·齊物論》:“吹萬不同,怒者其誰,借上萬者怒者而言。吹萬不同,言衆論之不同也。怒者其誰,言使之有是衆論者,一也。一者,即所謂真宰之天也。即周所謂虚無之道也。”。這其中包含着韓元震理解莊子思想的核心。他曾説過莊子思想的核心是“以虚無爲道,以齊物爲宗旨”(27)《莊子辨解·德充符》:“篇末無人情,即一死生忘形骸之本也。其文首尾,佈置亦有序,一死生外形骸,即所以齊萬物而一道德者也。蓋周之學,以虚無爲道,以齊物爲宗,故七篇之中,無非此矣。”,同時把它當作得道的要領。他認爲以虚無爲道,所以得道也是無心所得(28)《莊子辨解·大宗師》:“周以虚無爲道,以齊物爲得道之要。故其言知道,以無心無知言者,以虚無知虚無也。其言得道,以一死生外形骸爲言者,一死生外形骸爲齊物之極也。”。韓元震的《莊子辨解》從理氣論的觀點來分析莊子思想,從這個觀點來看,虚無的氣就是道。
韓元震認爲《齊物論》中莊子把“一本萬殊”都看作是氣,即莊子所説爲“氣一分殊”。“氣一”中的“氣”就是莊子所説的虚無的道(29)《莊子辨解·齊物論》:“前段大塊噫氣,萬竅怒號,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此段吹萬不同,怒者其誰,萬殊之歸於一本也。萬物出於一而復歸於一,故至人之體是道者,必萬齊物而爲一也。然在吾儒見處,則一本萬殊皆理也。在周之見處,則一本萬殊,皆氣也。理一於善,氣雜於善惡。”。與儒家所説的“理一分殊”相比,莊子則説“氣一分殊”,那麽“理一分殊”與“氣一分殊”的根本差異就在於理和氣的差異。儒學作爲以純善的理爲存在根據的哲學,“以理齊之”,那麽事事物物都以純善的理作爲存在根據,所以它能進入没有一毫邪念的正處。但老、莊作爲以善惡雜駁的氣爲存在根據的哲學,“以氣齊之”,那麽事事物物都會停留在真妄和是非錯雜混淆的狀態,萬物最後得不到正處(30)《莊子辨解·齊物論》:“故以理齊之,則事事物物之上一循天,則無一毫私意之間隔,而萬物真得其齊矣。以氣齊之,則事事物物之間,真妄是非,錯雜混淆,其所以齊之者,不過以私意强之,而萬物終不得其齊矣。此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
韓元震展示了“以理齊之”和“以氣齊之”適用於倫理論和修養論的特徵。這一點是《莊子辨解》與其他注釋的差别。依靠“純善的理一”分殊的側面,即使有惡,通過後天的修養可以恢復其性善,而且可能通過恢復性善來改變氣質。可是依靠“善惡混雜的氣一”分殊的側面,因爲氣自身善惡混雜,其所行必猖狂自恣。如果説氣質是盡善的,那麽聖賢爲什麽説要改善氣質呢?這就是問題所在,也就是朱熹所説的“彌近理而大亂真”的具體内容。
除此而外,韓元震在《莊子辨解》中稱自然界萬物的大小貴賤和人事的治亂是非是否依靠陰陽作爲,這並非“道的本然”。他稱,儒家和老莊的差異點就在這裏出現,也就是儒家的聖人以“理”爲道,因此“主善去惡”返回到“道之本然”。但是老莊以“氣和虚無”爲道,因此不能區分善惡返回到“道之本然”。話語雖然相似,但是實質的内容卻完全不同,由此二者完全不能並行不悖(31)《莊子辨解·應帝王》:“此一段始於混沌二字,以直指己之所謂道體,而總結上文,然實亦爲七篇之歸宿也。内外諸篇,皆當以此意推之。末段老莊見識本末,盡在此段,皆老莊見處,極於天地未辟,一番混沌之時,故便以此爲至道,又見其天地萬物,皆自混沌中分出來,而皆本同而末異。故便以萬物之有大小貴賤,人事之有治亂是非,謂皆道之當有,而不可以相無,人之爲道,亦當以齊物爲宗,以復歸混沌者,然後方可以得道,而人之有聰明知識,辨别是非者,爲喪道,是蓋不知所謂混沌者,乃在前陽既滅之餘一陰之静,而非形而上者之道也。萬物之有大小貴賤,人事之有治亂是非,皆陰陽之爲,而非道之本然也。聖人,以理爲道,故以主善去惡爲復其道之本然。然老莊,以氣爲道,故以不擇善惡爲復其道之本然。此其言道與復其本然者,語雖同而實則有薰蕕冰炭之不相入也。”。韓元震説儒學以“理”爲道,“主善去惡”;老莊以“氣”爲道、不分善惡。這就是韓元震在《莊子辨解》中爲什麽要做箋注的象徵性説法,同時也是“人物性相異論”的根據。
若要理解韓元震批判莊子思想的核心,站在主張理一分殊的儒家立場來看,有必要考察以“虚無爲道,齊物爲宗旨”與“主張氣一分殊”的莊子思想中存在的問題,即“虚無”的本質是什麽,以它爲道是否正確,什麽是“齊物”根源,具體通過哪種方式進行,通過善惡混在的氣來齊物的結果會給現實世界帶來怎樣的問題等等,都需要一一進行考察。
三、 區分正學和異端: 對“認氣爲理”和“認心爲性”的批判
韓元震對異端的認識在“辨異端、辟邪説”這句話中得到很好的展現,他通過理氣論來探討這一點。他區分了以理爲中心的“正學”和以氣爲中心的“異端”,並認爲這個區分適用於善惡的判别(32)韓元震《南塘集》卷之六《經筵説下》:“元震曰,小臣既論陸學之非,請復詳論自古正學異端之辨矣。天地之間,只有理與氣而已。理者純善無惡,氣者有善有惡。主於理者爲正學,主於氣者爲異端。正學異端之辨,只在於理與氣而已矣。”。
首先,儒學和異端的不同在於“把性和道當作什麽”以及理和氣中哪個是“使役者”、哪個是施令者。具體而言,儒學以理爲“性和道”,異端以氣爲“性和道”;儒學主張“以理御氣”和“氣聽命於理”,而異端學主張“以氣役理”和“理反聽命於氣”(33)韓元震《南塘集》卷之六《經筵説下》:“儒者以理爲性道,而理本無二體,故千聖論性,只是一致,而更無異論矣。異端之學,皆認氣爲性道,而氣則有萬殊。故諸子之言性道,各隨所見而不同。雖其言之不同,其認氣質爲性道則同矣。儒者之學,以理御氣而氣聽命於理,故所行無不合於道矣。異端之學,以氣役理,而理反聽命於氣,故所行必至於倡狂自恣矣。理則純善,而氣則淸濁粹駁,有萬不齊。此必須變化氣質,然後可以復其性初。氣質若果盡善,聖賢何以變化氣質爲訓乎,此處政當審察也。”。也就是説,理和氣的主宰性倒反過來的話,就成爲異端。儒學説性命,説“理氣不相離,理氣不相雜”,也説氣和“所以然者的理”。結果,儒學通過理來尋找善的根據,是實踐善的哲學。而莊子把萬物的根源放在氣(靈覺)中,從氣的善惡無分角度來齊一。韓元震跟儒學所説的一樣,主張善必須“以理御氣”才能實現。
因爲莊子稱氣自體是“澹一虚静”、“虚静虚明”,所以“氣之初定是善”,韓元震對這個見解提出異議,認爲此説不瞭解那個氣的本質(34)《莊子辨解·養生主》:“或曰,先儒有言澹一,氣之本,又有言氣之初,亦無不善。然則天地未辟之前,人心未發之時,氣之虚静虚明者,乃氣之本體,以虚静虚明爲萬善之本者,有何不可。”。因爲氣摻和着清濁粹駁,“澹一清虚爲氣之本者”,只是聚焦在“天地萬物未生之前”(35)《莊子辨解·養生主》:“此皆執言迷旨,自誤誤人之甚者也。蓋以澹一爲氣之本者,對攻取而言也。以氣之太初,澹一清虚爲善者,對糟粕煨燼之氣而言也。豈爲澹一清虚之中,更無清濁粹駁之雜,而有善無惡與性道無别耶?蓋如以陽明對陰濁而言,則陽明爲善,而陰濁爲惡也。豈謂陽明之中,更無毫髮邪惡之雜耶?此以澹一清虚,爲氣之本者,姑亦就此天地萬物未生之前而言也。”而言。在這一點上,韓元震認爲莊子不瞭解“氣御于理”,也不明白“動静和陰陽都是氣”。
如何看待人心也是儒學和莊子的不同之處。那麽韓元震是如何批判莊子所説的心的?他提起《齊物論》的“真宰乃道”、“真君乃心”,稱這個“真宰”如在“一身”,則心成爲真君,那麽心與道就合二爲一(36)《莊子辨解·齊物論》:“真君,即心也。……唯道齊之在萬物,則道爲真宰,在一身,心爲真君,心與道一也。邵子所謂心爲太極者也。然吾儒所謂真君之心,包性命而言,莊周所謂真君之心,指靈覺而言,性命一於善,靈覺無分於善惡,此所以語同而實不同也。”。他認爲儒家所説的“真君之心”包含“性命”,而莊子所説的“真君之心”則指的是跟氣有關的靈覺。這裏的性命於善始終如一,但屬於氣的靈覺則不分善惡,這一點也顯示了二者的差異。因此韓元震説莊子是“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問題是,如果像莊子這樣“無見於性”的話,就會發生氣質偏全上的差異,雖然計較是非善惡但卻出現了一個並無確定基準的問題(37)《莊子辨解·德充符》:“此以止水喻心,《應帝王》篇又以明鏡喻心。明鏡止水之喻,吾儒亦用之。周之於心,不可謂無見也。唯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所謂水所謂鏡,無所準,則或有時不得其監照之正也。蓋鏡雖同明,鐵之精粗不同,水雖同止,潭之大小不同,鏡之照物粗者或有所差,水之鑒形小者或有所遺,此即心雖同,静亦雖同,明其氣質之偏全粹駁,亦自有不同者,而應物之際,專任是氣者,不能無所差矣。”。
其次,韓元震通過儒家之道和老莊之道在内容上出現的差異來展開異端觀。他説,虚静構成老莊之道的内容,理構成儒家之道的内容。但老莊視作道的混沌虚静在“天地已滅之前”剩下“一陰之静”,然而這並不是儒家所説的道。也就是老莊以虚静爲道,這來自“氣之太初乃虚静”。韓元震從“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觀點批判這一點(38)《莊子辨解·養生主》:“若自一陰一陽之道説來,則澹一清虚者,即前陽既滅之餘,太極之静,而生陰者也。前陽爲此陰之本,而此陰又爲後陽之本,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互爲其本,而太極又爲陰陽全體之本,則安得以一陰爲氣之本哉。動静勢均,陰陽位敵,固未有善惡之偏,而以陰陽對太極而言,則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一而氣殊,則又安得以一陰爲純善者哉。”。
如果以“天地開闢之前”、“萬物未生以前”的混沌虚静爲道的話,那麽就只能説世間萬事和是非善惡本來都是從“混沌虚静”而來。莊子把是非善惡當作“道之全體”,認爲二者缺一不可,從而最終齊物萬事。但韓元震認爲儒家所説的道與是非善惡没有關係。異端之學所説的“混沌虚静”作爲“天地已滅之前”僅存的“一陰之静”,並不是儒家所説的道。儒家以理爲“性和道”,理本來並非兩體,因此很多聖人論述的性大都一致,没有其他的異説(39)韓元震《南塘集》卷六《經筵説下》:“老莊以虚静爲道,此蓋有見於氣之太初虚静者也。故以天地未辟萬物未生之前,混沌虚静者爲道,而世間萬事是非善惡,本皆自混沌虚静中出來。故又以是非善惡爲道之全體,而謂不可偏廢,遂欲並存而齊物。實不知混沌虚静者,乃前天地既滅之余一陰之静,而非真所謂道也。釋氏以靈覺爲性,此蓋有見於氣之運用靈妙者也。故以運水搬柴爲妙道,而不知運水搬柴,乃氣之靈妙者,而非真所謂道也。荀楊以惡與混爲性,此蓋生於末世,見善人少而惡人多,故遂以惡與混爲性。此則只見其氣之末流紛擾者,而不知有性者矣。陸王之宗旨,又不出於釋氏之外。異端之學,大概如是矣。儒者以理爲性道,而理本無二體。故千聖論性,只是一致而更無異論矣。”。這樣一來,像儒家這樣通過“純善”的理和道認識世界的話,當然没有問題,但像莊子那樣通過“混沌虚静”和氣來理解世界,就會招致善惡是非無分别的問題(40)《莊子辨解·養生主》:“周之見乎氣者,蓋限於今天地已辟之後,而僅能就此,推其未生者而謂之道,實不知其此天地未生之前,即是一陰之静,而此陰之前又是陽動,動静無端,陰陽無始,而動静陰陽之上,更有所謂太極之道也。故其論人心,亦指未發虚明而謂之道,謂之吉祥之本,而不知有所謂性善之理。然則論道論性,而近于周之説者,不可謂知性知天,而易以陷於異端之學矣。學者可不審所擇焉?”。
最後,韓元震通過把理和氣是當作“一物”還是“兩物”來展開對異端的考察。異端把理和氣看作一體,稱“認氣爲理”。從這一點來看,老、佛以來異端之説顯現的弊端,都是源於“認氣爲理”(41)《南塘集》卷三《經筵記聞録·太極圖》:“理氣一物二物之見,俱於道未有所見。而其爲吾道之害,則莫酷於一物之見。故老佛以來,異端之説,其見之蔽,皆坐於認氣爲理也。”。韓元震認爲,從根本上講,區分異端和正學就是分辨理和氣;强調應該注意分辨理和氣,認爲這一點也適用于心性論。也就是説,心“主於身”,“心即氣”;性“具於心”,“性即理”。儒學因爲“以理宰氣”,它基本上“本乎天”,可是莊子卻因“本乎心”、“昧其性”,屬於“以氣滅理者”。而異端就主張這一點。這裏批判“認心爲性”就是要“區分心和性”,那麽我們應該瞭解“認心爲性”之所以成爲異端的理由。韓元震對于“認心爲性”的批判同樣適用于佛家和陽明學(42)《南塘集》卷之二十七《雜著·王陽明集辨并跋》:“更按陽明答東橋書末,有拔本塞源之論,謂其于朱子之學,拔本而塞源也。噫亦痛矣,斯非所謂人得以誅之者耶?辨異端辟邪説,正須於拔本塞源,則吾請復爲拔本塞源之論也。夫學必主於心,而心則一也,何以有異端正學之别也,亦在乎理與氣之分而已矣。心主於身,性具於心,而心即氣也,性即理也。是故治其心而主乎性,以理而宰氣者,吾儒之學,所以本乎天也。本乎心而昧其性,以氣而滅理者,異端之學,所以遁乎天也。釋氏以靈覺爲性,陸氏以人心爲至善,此皆認心爲性而同歸於異端也。至若陽明之學,專以致良知爲主,而所謂良知,即是釋氏靈覺之知,而非孟子所謂仁義之良知,則亦不過爲循氣質之用而昧天理之真也。此又得陸氏之心印而傳釋氏之衣缽者也。學之所主,既在於氣,則其發之言語文章,見諸勳名事業者,固宜不純于天理而多發於人欲矣。且復就此而論之,陽明嘗論儀、秦之智術,以爲窺得良知之妙用,則其所云良知,固已可見矣。”。
“認氣爲理”和“認心爲性”是韓元震在《莊子辯解》中批判莊子思想的核心。他從形而上學的角度,通過“認氣爲理”批判了莊子思想未能達到“本源上達處”,通過“認心爲性”批判了莊子思想包含的人間善惡的顯現以及氣質變化論的問題。他認爲莊子完全不瞭解儒家“性命中正”的理,卻帶着“知覺機滅”的機和“善惡無分”的氣,想要説明自然原理和人間萬事,結果帶來的卻是是非善惡的無分(43)《莊子辨解·應帝王》:“四無爲可見老莊之術,專要避事畏罪,苟嶄兑禍,蓋鄉願之尤者也。無窮無朕,即混沌也。所受於天,天者亦以混沌言,言盡其所得混沌之道也。將隨之於事之既往也迎,迎之于事之未來也藏,滯而不化也。此與孔子四無語同。然在聖人,得順性命中正之道也。在老莊,則任知覺起滅之機也。性命純善,知覺有善惡,此聖人之道,一主於善,而有所不爲也。老莊之道,不擇善惡,而無所不 爲也。”。與講究天理的儒學相比,莊子講氣化。如果接受這種氣化的話,只能同歸于摇盪恣睢(44)《莊子辨解·應帝王》:“使物自喜,即使萬物各得其所之意也。然其如此者,在聖人則循天理之自然者也,在老莊則任氣化之所爲者也。循天理則己與萬物同歸于仁壽軌道矣,任氣化則己與萬物同歸於遥蕩恣睢矣。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也。”。
綜上所述,韓元震站在以老莊思想爲基本氣哲學的立場,通過理氣論闡述他的異端觀,他運用理氣心性論來理解、區分“作爲正學的儒學”和“作爲異端的老莊”(45)韓元震認爲儒學是正學,而道家、陽明學和佛家思想是異學。對於陽明學,他通過《王陽明集辨》批判,對佛敎則通過《禪學通辨》進行批判。,指出異端實包含着“彌近理而大亂真”之處。
四、 儒家對“認氣爲道”的陰陽論的批判
韓元震著述《莊子辯解》,通過“彌近理而大亂真”來批判莊子思想,因爲他認爲莊子所説的對道的認識,與儒學所説道的概念“似而非”。如前文所説,韓元震爲了説明對莊子思想所具有的“似而非性”的理解,通過性理學的理氣論展開異端批判論,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對莊子所説的與“無”相關的形而上學的理解。最大的問題是對《齊物論》中所説的“未始有物”的解釋,以及與此有關的“道”字和“物”字的解釋。
韓元震規定莊子“認氣爲理”,還規定他説了“認氣爲道”(46)《莊子辨解·大宗師》:“此段論道最詳,有情,以其主宰而言也,有信,以其至實而言也。主宰而又無所作爲,至實而又無有形體,故曰無爲無形。周之論道,可爲幾矣。然道上不得著情者。著此一字,亦可見周之認氣爲道也。”。他認爲聖人齊一萬物的理由就是要回歸到道之本一,這是莊子的意思。他認爲,《齊物論》中莊子所説的“始也者”是氣,“未始有始也者”是道,“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是“道在無中的根本”。莊子稱“天地未生之前”是道,但因爲莊子不知道“天地未生之前”就是“陰之物”,所以就這樣把道當作無。他如果明白儒學所説的“動静無端,陰陽無始”,“本無無物之時”的話,就不會把道當作無了(47)《莊子辨解·齊物論》:“始也者,氣也。未始有始也者,道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道之本於無也。有也者,事物也。無也者,道也。再言未始有無,言道之極於無也。蓋周以天地未生之前爲道,而不知此爲陰之物,故便以道爲無。若知動静無端,陰陽無始,而本無無物之時,則亦不敢以道把作無矣。”。
韓元震認爲: 莊子把“未始有物”看作道是因爲他没能完全理解儒家所説的“道”字和“物”字的意思(48)《莊子辨解·齊物論》:“未始有物,即周之所謂道也。有物即氣也。有封即天地也。有是非即事物之紛羅者也。自道而爲氣,自氣而爲天地,自天地而爲事物,有事物則是非彰,是非彰即道虧,道虧則愛成,愛成者,自私之謂也。有成故有虧,無成則無虧矣。有成與虧,末流之分也。無成與虧,本源之一也。”。他通過“陰陽無始”和“動静無端”的儒家“宇宙論”具體批判了這一點,即陽是事物,陽前面如果有陰的話,陰也是事物,動是事物,動前面有静的話,静也是事物,哪里有什麽“無物之時”?如前文所叙,如果没有“無物之時”,所謂的道就在事物中,更進一步説,就是它主宰了事物。通過這樣的道論和陰陽論展開宇宙論的就是性理學。
那麽莊子把“未始有物”當作道的話,會産生哪些問題?韓元震認爲,如果把“未始有物”當作道,就會出現“動而陽者”爲物,“静而陰者”爲道的理解。這樣看來,莊子所説的道不過是“形氣之粗”(49)莊子之所以不明道,是因爲他還没有從一陰虚静的形氣之粗中脱離出來。從這一點再往前走一步的話他就會明白道。《莊子辨解·大宗師》:“玄冥,無形也。參寥,無聲也。無形無聲,又讚歎詠歌之所不及,極言其微妙也。然亦不離乎天地形氣而爲言也。蓋言其形氣之始也。疑始,謂之始,而亦無可指以爲始者,故曰疑始,即所謂未始有始者也。周之所謂道也,言語文字,以道之所傳而言也。天地日月陰陽造化,以道之所存而言也。至於疑始,方指出道之本體,而實則不離于一陰虚静形氣之粗也。周於此處,又進一層,則豈不爲真知道者哉?”。因此,莊子並不明白《周易》所説的“一陰一陽之謂道”(50)《莊子辨解·齊物論》:“聖人之齊物,所以復其道之本一也,此周之意也。然周以未始有物爲道,則全不識道字,又不識物字。蓋動静無端,陰陽無始,陽爲事物,而陽前有陰,則陰亦事物也;動爲事物,而動前有静,則静亦事物也。夫豈有無物之時哉?既無無物之時,則所謂道者,亦在乎事物之中,而爲此事物之主也。今爲有無物之時,則是只知有動而陽之物,而不知此陽之前,又有静而陰之物也。以未始有物爲道,則是只以動而陽者爲物,而卻認其静,而陰者爲道也。然則周之所謂道者,即不過形氣之粗者,而不知此上面,更有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故周之語道,一則曰虚静,二則曰混沌。虚静、混沌皆是天地未辟、萬物未生之時,一陰之象也。一陰之中,輕清重濁、剛柔燥濕之氣,無不備言,分而爲天地萬物,高下散殊,而事物之是非善惡,亦皆由此以生。故周使以是非善惡爲皆道之當有,而其所以求道者,專以齊物以爲宗。故其學遂陷於倡狂妄行之域,所見一差,其害至此,可不懼哉!”。在這一點上,韓元震把莊子所説的道規定爲“混沌虚静”。莊子看到的混沌只是作爲“天地未開”和“萬物未生”的一陰之象。可是如果把這種混沌規定爲“一陰之象”的話會産生現實問題。“一陰”有清濁輕重之氣,這種“清濁輕重之氣”分離就産生天地萬物,成爲人類生活中是非善惡的根據。如果稱這種氣是根源的話,就會帶來無法分别現實中是非善惡的結果。莊子最後在“認氣爲道”的觀點中來理解道(51)《莊子辨解·大宗師》:“此段論道最詳。有情,以其主宰而言也;有信,以其至實而言也。主宰而又無所作爲,至實而又無有形體,故曰無爲無形。周之論道,可爲幾矣。然道上不得著情者。著此一字,亦可見周之認氣爲道也。”。這種思維是主張“理一分殊”的儒家思想絶對無法接受的。同時韓元震認爲莊子所説的“虚静寂寞”是“一陰之静”,這個陰只是“前陽”的根本,而不是萬物的根本。因此愚鈍無知的話,善惡就會混在一起,天理屈服人欲就不可能得到妙道(52)《莊子辨解·齊物論》:“不從事以下,皆愚芚不知之貌,與《天道》篇虚静恬淡寂寞無爲之語相表裏,彼以虚静寂寞爲萬物之本,此以愚芚不知爲妙道之行。周之見處,盡於是矣。然虚静寂寞,即一陰之静,而此陰又本于前陽,則安得爲萬物之本也?愚芚不知,即善惡之混,而天理常屈於人欲,則安得爲妙道之行也?所謂道者,至虚之中至實者存,至静之中至動者具,渾然而至善,粲然而至昭,則虚静寂寞、愚芚無知者,豈所以語道者哉?”。如上文所述,韓元震運用人性論批判莊子的宇宙論,這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
對莊子所説的混沌進行的批判與他從“認氣爲道”的觀點來理解莊子所謂的道的思維有關。韓元震非常重視《應帝王》的混沌寓言,這則寓言包含了《莊子》内外篇的主旨和老莊見識的本末(53)《莊子辨解·應帝王》曰:“此一段始於混沌二字,以直指己之所謂道體,而總結上文,然實亦爲七篇之歸宿也。内外諸篇,皆當以此意推之。”又曰:“末段老莊見識本末,盡在此段。皆老莊見處,極於天地未辟,番混沌之時,故便以此爲至道。”。莊子以混沌爲道體,韓元震認爲莊子所説的混沌内容有問題。他認爲老莊的見處在極於“天地未辟”的混沌之時,莊子不僅把這個混沌之時當作道,而且認爲天地萬物都是從混沌中生出。莊子認爲“以齊物爲宗,復歸混沌”是得道,而人類“用聰明和知識分辨是非”是喪道。在韓元震看來,莊子當作至道的混沌屬於前陽已滅餘下的“陰静”,莊子以混沌爲至道,他這個混沌並非儒家所説的形而上者的道(54)《莊子辨解·應帝王》:“又見其天地萬物,皆自混沌中分出來,而皆本同而末異。故便以萬物之有大小貴賤,人事之有治亂是非,謂皆道之當有,而不可以相無,人之爲道,亦當以齊物爲宗,以復歸混沌者,然後方可以得道,而人之有聰明知識,辨别是非者,爲喪道。是蓋不知所謂混沌者,乃在前陽既滅之餘一陰之静,而非形而上者之道也。萬物之有大小貴賤,人事之有治亂是非,皆陰陽之爲,而非道之本然也。聖人以理爲道,故以主善去惡爲復其道之本然。然老莊以氣爲道,故以不擇善惡爲復其道之本然。此其言道與復其本然者,語雖同而實則有薰蕕冰炭之不相入也。”。韓元震的這個批判與此前對“未始有物”爲道的批判是一致的(55)《莊子辨解·應帝王》:“未始出吾宗,即未始有物者,而周之所謂道者也。在吾儒見處,則爲前天地既滅,後天地未辟,而萬物未生之時也。”。
結果,莊子所説的道是“天地未辟”、“萬物未生之前”的“一陰之静”,以此爲道並非真道。莊子所説的“無”也不是儒家所説的“至無之無”(56)《莊子辨解·大宗師》:“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此三句雖略,周之見盡於是矣。萬物生於無,而死則復歸於無,故以無與死爲首尾。生者居其間,自無而適無,故謂之脊。然以一物之生死而言,則固生於無而歸於無也。若以陰陽之物而言,則前未嘗有無,後亦未嘗有無也,安得以無爲首哉?然則周之所謂無者,可見其指天地未辟、萬物未生之前一陰之静者也。以是爲道,非道之真,而其無亦非至無之無也。”。而且如果萬事萬物都是從無中生出來的話,就會産生無法分辨大小和夭壽等問題。韓元震用《齊物論》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來解釋這一點。他説,“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與張載的《西銘》雖然意思相同,但與《西銘》中的“理一分殊”相比,莊子的“廢分殊,亂理一”有其他的意思。莊子《齊物論》要説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廢分殊,亂理一”的思維(57)《莊子辨解·齊物論》:“言事物本皆自無中出,故推其本之無,則大小壽夭,無可分别者也。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與張子《西銘》之意同此。蓋周之見處,高於世俗一層者也。然《西銘》據理一而推分殊,周之齊物廢分殊而亂理一,所見有虚實故也。”。“廢分殊”從“亂理一”中出來,成爲“亂理一”的理由,因爲“理一”的“理”用“氣”來理解(58)這樣的話,韓元震説的“人物性相異”就不能成立了。。
韓元震認爲,莊子把“天地未生之前”看作是道,與他不瞭解“道不能成爲陰物”相符合。因爲道存在陰陽,但道卻成不了陰物。而且莊子把道當作無,這是他不瞭解儒家“動静無端”、“陰陽無始”的原理。那麽,韓元震所説的儒家的道是什麽?他認爲儒家的道是“至虚之中”“至實者存”,是“至静之中”“至動者具”。它是渾然至善,是粲然至昭(59)《莊子辨解·齊物論》:“所謂道者,至虚之中至實者存,至静之中至動者具,渾然而至善,粲然而至昭,則虚静寂寞、愚芚無知者,豈所以語道者哉?”。此外,莊子所説的太極也用這種思維來理解。莊子所説的太極被形容爲“形氣之極處”,但它並不是儒家所説的“無極而太極”的“太極”,因此説:“又安知無極太極之謂道耶?”(60)《莊子辨解·大宗師》曰:“子桑户一段,無極與上文所謂太極,皆以形氣言,非如吾儒所謂無極太極也。世之議周之失者,楊龜山説,每以道在太極之先爲口實,以周爲若道上求道者然,此無極者亦可作道字看耶?周雖不知道,亦未嘗以道爲有二層,以是詬厲,周豈服哉?且周於道字,本不見得,則又安知無極太極之謂道耶?特自撰出此名言,以形容形氣之極處,此無窮者耳。”又曰:“鬼神,以造化言。天地,該事物而言。太極,持天地有形之極處而言,非如孔子所謂太極也。六極,亦言天地有形上下四方之極也。……此一段發明道體,盡其幽妙,極其廣大,無一言不同於吾儒矣。然所謂道者,乃指天地未生之前,一陰虚静者,則其頭腦看起處,便自如吾儒不同矣。程子嘗論老佛之言,曰言言是,句句同,然而不同,正謂此矣。”
比如,莊子的道不同於儒家的道(61)《莊子辨解·大宗師》:“朝徹,朝明也。徹,通也,言胸中明通也。獨,道也。萬物未有無對者,而唯道無對,故謂之獨,見獨,見道也。無古今,道無古今之異也。入於不生不死,道無存亡之變也。殺生不死,殺物而不隨物而死也。生生不生,生物而不隨物而生也。其爲物物,道也。如《中庸》其爲物不貳之物。將送,其去也;迎迎,其來也。言物之去來成毁,無非道之所爲也。攖甯,攖,紛羅也;寧,有定也。言萬象紛羅而道有定體也。攖而後成,即象之紛羅,而見道之定體也。如《論語》一貫之旨。自見獨以下,論道極善,但其道,非吾所謂道也。”,韓元震專門從陰陽動静論的角度來説明它們的不同。儒家從根本上理解陰陽和動静時,陰陽則理解爲“陽中陰”、“陰中陽”,而動静則理解爲“動中静”、“静中動”。“陰陽無始”、“動静無端”是儒家的宇宙論,陰陽和動静之上有“一陰一陽之謂道”。可是在韓元震看來,莊子説起屬於“陰静”的“氣一”時既重視静也重視陰,莊子的這種思維不僅不明白儒家所説的“陰陽無始”和“動静無端”的道理,也不理解“一陰一陽之謂道”,他也不清楚陰陽和動静之上有太極之道。
結 論
朝鮮儒學者對《莊子》的理解有兩種傾向。一個是從文學角度進行肯定評價,即從《莊子》文章的展開方式、豐富的想像力和奇異的内容等角度對其作出肯定評價。另一種傾向則考慮到莊子思想運用於儒家思想支配的現實世界所産生的危害,並對之加以批判和排斥。本文通過韓元震的《莊子辨解》證實了這一點。韓元震批判莊子思想,基本上是通過以儒家的理氣論爲基礎的宇宙論和人性論進行批判的。因此,韓元震是否正確理解了“莊子爲何通過這一氣論來展開宇宙論與人性論的討論”的意圖?這也可能成爲一個争論的話題。
韓元震基本上主張“辨異端,辟邪説”,《莊子辨解》就是一個例子。儘管該書對《莊子》内篇(七篇)作了“箋注”,但“辨解”一語包含着他對莊子思想批判的辯論以及客觀理解的意圖。韓元震在當時朝鮮性理學核心論點“人物性同異論争”中堅持“人物性相異論”,這一立場也反映在《莊子辨解》一書中。
正如上文所述,韓元震具體通過理氣論、陰陽論和心性論討論了莊子思想,他的核心在於對“無分”的批判。這個“無分”並不單純地局限在理解形而上者,它也適用于現實的人際關係、人間善惡的判斷以及相關的行爲舉止。最後,韓元震在《莊子辨解》中表現的反無分理論也同樣適用於自身的“人物性相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