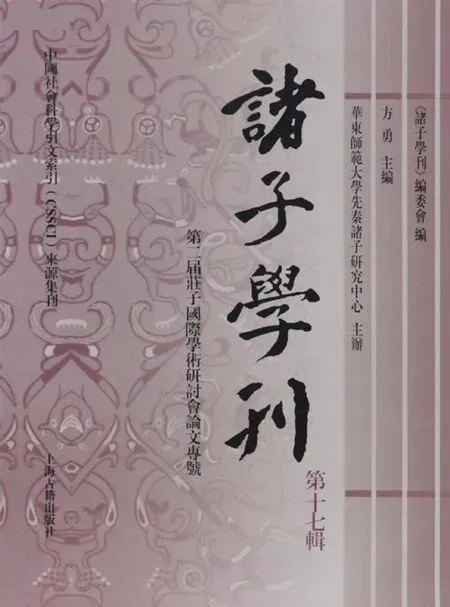桐城派《莊子》文學經典化建構及其文學史意義*
2018-01-23李波
李 波
内容提要 桐城派作爲清代最有影響、持續時間最長的古文流派,對《莊子》文學經典化建構做出了重要貢獻。桐城派古文家對《莊子》進行了全面的接受與廣泛傳播;將《莊子》散文及其思想作爲其學派構建文統的重要資源;通過文論、評點以及古文選本等形式對《莊子》文學價值進行了深入闡發。桐城派《莊子》文學經典化建構體現了其學派謀求自我創新、與時俱進的意志,在《莊子》文學經典化建構歷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關鍵詞] 桐城派 莊子 文學經典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興盛,《莊子》毫無争議地確立了其哲學思想經典地位。然而,《莊子》的文學價值並没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唐宋以來,隨着李白、蘇軾等文人對《莊子》文學的高揚,尤其是南宋《莊子》評點的興起,《莊子》文學價值不斷被開拓。到了有清時期,由於評點家、文學家以及批評家們以多種形式表達了對《莊子》文學的推崇,《莊子》文學經典地位遂而確立並鞏固。而桐城派作爲清代文壇上一支重要力量,對《莊子》文學經典化建構之貢獻尤爲引人矚目。本文試對此作一探討。
一、 桐城派古文家對《莊子》的接受與傳播
《莊子》之所以能够成爲思想經典,一方面由於它自身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獨特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因爲歷代文人學者對它的接受、闡釋與解讀。自漢代以來,《莊子》思想即已引起了文人共鳴,賈誼、司馬遷、揚雄、張衡等人的創作皆受到《莊子》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盛行,莊學思想高漲,《莊子》完全融入了士人心靈,與儒家思想一起共同塑造了中國士人的文化心理品格,從此成爲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後,《莊子》思想影響了一代代文人學者。作爲傳統儒家文人,桐城派的思想與行爲不可避免地帶有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身上儒釋道並重的特點,尤其顯示出較爲鮮明的《莊子》情懷。受時代影響,桐城派古文家對《莊子》的接受又表現出時代化特點。
第一,桐城派古文家對莊子思想的自覺認同。桐城派宗法程朱,面對漢學的壓力,始終堅持宋學,對抗漢學。但現實生活的種種挫折與失意亦使他們不得不尋求心靈慰藉,思想上自然而然地與莊子逍遥、齊物思想發生共鳴。因而此種情緒在他們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來,就連桐城派領袖人物方苞、姚鼐的思想中亦不乏此種傾向。方苞《遊潭柘記》《封氏園觀古松記》等文即表達出對世事無常的感歎與逍遥物外的嚮往。如《遊潭柘記》一文云:“昔莊周自述所學,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余困于塵勞,忽睹兹山之與吾神者善也,殆恍然于周所云者。余生山水之鄉,昔之日誰爲羈絏者,乃自牽於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邪!夫古之達人,岩居川觀陸沉而不悔者,彼誠有見於功在天壤,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況敝精神於蹇淺而蹙蹙以終世乎?余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妄意於此。”(1)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頁。姚鼐信仰程朱,清心寡欲,但漢學帶給他的巨大壓力以及辭官回鄉後的孤獨與失意亦使他主動親近老莊。《檥舊縣》一詩真切地表達了超然世外的思想:“清江静無風,曉岸初上日。高下雲影合,遠近山青出。連舫纜盡解,孤舟飯未畢。觕涉齊物旨,曠慕養生術。逐事偶在途,澹懷猶一室。復此對清遠,未應嫌遲疾。顧與漁父言,仰送飛鳥逸。又泛滄波東,聊作前遊述。”(2)姚鼎著、劉季高校點《惜抱軒詩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9頁。晚年的姚氏出入於佛道,流露出一定的消極情緒。
到了清代晚期,面對世事的無常以及社會矛盾的加劇,桐城派學者更自覺拉近了與《莊子》的距離,以期通過《莊子》來慰藉人生,淡化精神與肉體上的苦痛。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紓。他在《歲暮閒居頗有所悟,拉雜書之,不成詩也》組詩中寫道:“據案讀蒙莊,清風張胃脘。見獨或未至,朝徹已在眼。陶潛頗畏死,悟道一何晚。生生乃不生,所坐在煩懣。不攖胡得寧,萬擾奚我綰。微笑踞藤榻,蠟梅開欲滿。”(3)林紓《畏廬詩存》卷下,《民國叢書》第四編,上海書店1992年版,第4頁。“世亂得早死,此亦關福德。極力自排遣,轉眼復悲瑟。恍然思莊生,特覺豈無術。但能念旦宅,或抵寥天一。”(4)同上,第5頁。林紓自謂生於亂世,故將自己隱藏在莊子的精神世界裏,“自處於逍遥之域,深得莊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指”(5)朱羲胄述編《貞文先生學行記》卷二,《民國叢書》第四編,上海書店1992年版,第94頁。。顯然,在上述桐城派學者那裏,莊子“逍遥”、“齊物”思想成爲了他們逃避現實、尋求精神慰藉的良藥。
第二,桐城派將莊子“虚静”“自然”等理論吸收到儒家思想中,嘗試重塑新型的儒道合一的理想人格。外儒内道本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普遍人生態度,但清代中後期,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面對大動盪大變革的社會形勢,桐城派在曾國藩的帶領下一方面積極參與到社會政治改革中,另一方面又嘗試吸納莊子思想,欲構獨特精神境界,重塑新型人格理想。曾國藩篤好《莊子》,“悱惻神所獎,聊究莊生旨,齊物尋影響,行止皆有待,還以咨罔兩”(《贈李眉生》)(6)曾國藩《曾文正公詩文集》卷一,《四部叢刊》影印清同治本。。但他並非以消極的態度對待莊子,而是採用拿來主義,將莊子養生思想作爲個人身心修養與處世的重要内容。曾氏在《家訓》和《日記》中多次表達了此種看法:“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静虚,庶于修已治人之術兩得之矣。”(7)曾國藩《曾文正公家訓》“辛酉十月”條,清光緒五年傳忠書局刻本。“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遊心虚静之域。”(8)曾國藩《曾文正公家訓》“壬戌二月”條,清光緒五年傳忠書局刻本。“若遊心能如老莊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9)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辛酉八月”條,清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刻本。曾國藩將莊子虚静與自然的哲學思想納入立身之道,較好地處理了道家出世與儒家入世之矛盾關係,塑造了儒道合一的理想人格,體現了他歷經磨難、參透天人的獨特生命情懷。在曾氏影響下,曾門弟子積極學習《莊子》,在積極入世的同時,又能坦然地面對現實與得失,實現了對《莊子》經典思想的另一種解讀。
第三,桐城派古文家廣泛傳播並大力提高《莊子》的社會地位。桐城派古文家大都研究過《莊子》,且多有著作流傳於世,如姚鼐的《莊子章義》、劉大櫆的《莊子評點》等等,這無疑刺激了《莊子》在社會上的廣泛傳播,培養了大量的受衆群體。同時,桐城派還致力於《莊子》社會地位的提高,其中尤以桐城派後期人物曾國藩及其弟子最爲用力。曾國藩一方面主張將《莊子》作爲教科書引入課堂:“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説文》《水經》《文選》、宋五子及杜、韓、歐、蘇、曾、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一部焉。”(《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10)曾國藩《曾文正公詩文集》卷一,《四部叢刊》影印清同治本。另一方面,又頗爲大膽地將莊子與儒家聖賢並列,奉爲三十二聖賢之一,收入《聖哲畫像記》,這種打破儒道對立的傳統做法,無疑極大地擴大了《莊子》的社會影響。曾門弟子黎庶昌比其師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先是主張將《莊子》立爲學官,並命曰“亞經”:“竊謂《莊子》以下十一書,宜因私家肄習特爲崇異立入學官,使列十三經後,以《莊子》次《孟子》……各降一等,命曰亞經,俾天下人士益隆所習,咸馳騖乎通儒。”(《周以來十一書應立學官議》)(11)黎庶昌《拙尊園叢稿》,清光緒二十一年金陵狀元閣刻本。黎氏還直接上書皇帝,建議將包括《莊子》在内的諸子列入科舉考試:“科舉取士誠不可廢,唯今八比小楷最空疏無謂,應請罷去。……第二場周、程、張、朱、陸爲一科,孫、吴武經爲一科,管、荀、老、莊、董、賈、揚、文中爲一科。”(《上穆宗毅皇帝第二書》)(12)黎庶昌《拙尊園叢稿》,清光緒二十一年金陵狀元閣刻本。桐城派對《莊子》的推崇可謂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第四,桐城派古文家注重從經世致用的角度挖掘《莊子》中的實用精神和現實因素。清代中前期,桐城派自覺繼承了明末清初“通子致用”的社會思潮。方苞《書删定荀子後》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13)方苞《方苞集》,第422頁。爲桐城派諸子學思想奠定了基調,影響了桐城派對諸子的解讀。姚鼐即在《莊子章義》中發揮説:“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14)姚鼐《莊子章義》,清光緒五年刊《惜抱軒遺書三種》本。以儒解莊,歸莊于有用。清代中晚期,社會環境發生了不少變化,西學開始東漸,中西交流頻繁。桐城派學者開始求新求變,主動以西學會通諸子。曾門弟子中有海外經歷的學者,開眼看世界,他們的莊子學思想融入了新的時代因素。其中以薛福成的觀點最有代表性:“《莊子》一書寓言也,亦卮言也,而與近來泰西之學有相出入者。《外物》篇云木與木相摩則燃,金與火相守則流,此電學、化學之權輿也。《齊物論》篇云‘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秋水》篇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内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此天算之學、輿地之學之濫觴也。”(15)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五,清光緒十八年本。這種説法新人耳目,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極富時代氣息。
不同時代賦予經典不同的歷史使命,也使經典具有了新的時代内容。桐城派對《莊子》思想意義的接受闡釋,無疑賦予了《莊子》鮮明的時代精神,擴大了《莊子》影響,推動了《莊子》的廣泛傳播,亦間接强化了《莊子》文學經典地位。
二、 桐城派將《莊子》散文及其思想作爲構建文統的重要資源
《莊子》作爲經典文本,文與意交織在一起,不僅爲文人提供了創作靈感與源泉,也成爲理論家進行理論建構的重要思想資源,而文人與理論家對《莊子》的解讀又反過來不斷促使《莊子》的經典化,這是《莊子》文學經典地位得以確立的重要途徑。桐城派主要以古文名世,他們在構建文統的過程中,不斷學習、吸納《莊子》,有力地推動了《莊子》文學在清代的經典化。
第一,桐城派古文家在創作實踐中大量引用《莊子》資料,積極效法、學習《莊子》散文風格。首先,桐城派古文家在創作中大量引用《莊子》資料。桐城派古文家幾乎人人研讀過《莊子》,因此他們在創作中引用《莊子》經語或寓言故事來議論説理、表達感情是極其平常之事,像方宗樹的《贈馬雲序》《與馬君論周書年月考書》《贈譚麗亭序》《原理》,梅曾亮的《李芝齡先生文集叙》《論語説》,曾國藩的《慎齋詩草序》《養晦堂記》,張裕釗的《與黎蓴齋書》《湘鄉相國曾公五十有八壽序》《范月槎觀察六十壽序》,吴汝綸的《題馬通白所藏張廉卿尺牘册子》《朱嘯山六十壽序代》等文章,比比皆是。如梅曾亮《論語説》一文云:“莊子亦曰:‘山林歟,皋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人固有視富貴如脱屣,死生如旦暮,至於俯仰陳迹流連光景之代謝,事無與已而悲從中來,不能自已。”(16)梅曾亮著、彭國忠等注《柏梘山房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頁。所引莊子文字出自《知北遊》。又吴汝綸《題馬通白所藏張廉卿尺牘册子》云:“今廉卿死,通白亦裒輯所與尺牘爲一册,屬余題其後。昔莊子過惠子之墓,曰:‘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夫人亡,匠石輟斤者,其質死也。今匠石亡矣,求所謂成風之斤一運於人之鼻端者,當吾世殆無復有矣。雖其質之空存,曷益乎!嗚乎,悲夫!”(17)吴汝綸《桐城吴先生詩文集》卷一,清光緒刻《桐城吴先生全書》本。此處引用了《徐無鬼》“莊子送葬”的寓言故事。桐城派大量引用《莊子》的做法無疑大大加强了《莊子》文學經典化的建構。
其次,桐城派古文家對《莊子》散文亦情有獨鍾,創作出了不少深受《莊子》影響且具有《莊子》風格的文章。戴名世的《睡鄉記》就直接化用了“莊周夢蝶”的故事:“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蝴蝶至其鄉,復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也,相化而未有已也,於是睡鄉擾矣。”(18)戴名世著、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87頁。劉大櫆的作品受《莊子》影響更大,清《國史·文苑傳》云:“大櫆並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其氣肆,其才雄,其波瀾壯闊。嘗著《觀化》篇,奇詭似《莊子》。”如《顧備九時文序》《天道》等,世人分别評之云:“創意遣言得蒙莊神髓。”“此文欲合《莊》《騷》而一之,前面哀怨之音可續《天問》《卜居》,後面揮灑曠逸又渾似南華咳唾。”(19)劉大櫆《海峰文集》,清刻本。此外馬其昶、林紓等亦不乏此類之作。桐城派的效法模仿無疑使《莊子》文章成爲世人學習的範本。
第二,桐城派的古文理論對《莊子》思想多有吸納。桐城派雖然旗幟鮮明地以程朱理學爲宗,但他們在文藝審美追求上卻能够突破傳統“文以載道”理論的束縛,自覺地將藝術性與審美性擺在重要位置,因此,莊子思想自然成了他們建構文藝理論王國的重要哲學資源。
1. 道與藝合。在桐城派學者看來,作爲莊子哲學本體的自然之“道”就是作家文藝創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莊子悟道的方式和遨遊大道的精神就是文藝美學的最高理想。戴名世《與劉言潔書》一文云:“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即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夫……是故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壒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20)戴名世著、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第5頁。其對藝術創作心理與審美經驗的總結不僅是對莊子哲學思想的巧妙化用,且使莊子藝術精神得以較大提升。姚鼐的文藝審美思想亦帶有莊子那種超然世外的曠達與飄逸,如他在《左筆泉先生時文序》中云:“左筆泉先生之文,沉思孤往,幽情遠韻,澄澹泬寥,如人入寒岩深谷,清泉白石,仰蔭松桂之下,微風泠然而至,世之塵埃不可得而侵也。”(21)姚鼎著、劉季高校點《惜抱軒詩文集》卷四,第50頁。充分體現了其“道與藝合”(《荷塘詩集序》)的藝術理想,而這正是莊子哲學思想之神髓。
2. 法天貴真。桐城派作家在古文創作中頌揚了很多遠離塵世、超然物外的莊子式人物,表達了他們超凡脱俗的藝術精神。這其中以姚鼐最有代表性。他在《吴荀叔杉亭集序》云:“荀叔負雋才,而亦常頹然有離世之志。”(22)同上,第111頁。《贈程魚門序》云:“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23)同上,第126頁。姚氏以這樣一個獨特的群體爲審美對象,即因他們身上具有莊子一樣“全其真”的性格特點,顯示出鮮明的審美傾向。他在《贈陳伯思序》一文中云:“周衰而莊周、列禦寇之言興。蓋古帝王之時,民皆有淳德,聖人謂無以持之也,道以仁義,養以禮樂文章,使民始于忠信而成於禮。若周、禦寇所云大人之德者,聖人乃以爲教之質也。去古既遠,功利狙詐益用,二子始欲一返乎質,使人各全其真,其言雖不中,捄世之心,可謂切矣!自周及魏晉,世崇尚放達,如莊列之旨。其時名士外富貴、淡泊自守者無幾,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達之中,又有真僞焉,蓋人心之變甚矣!”(24)同上,第112頁。可見,法天貴真思想是姚鼐評判人物的一個重要標準。
3. 隨順自然。桐城派古文創作雖然有家法可言,但又試圖化家法於無痕,按照文學的審美規律進行創作,達到一種自然至美之域,因此他們往往借用莊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表達他們的古文理念。姚鼐于《答魯賓之書》一文中提出:“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25)同上,第103頁。張裕釗於《答吴至甫書》一文云:“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爲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常乘乎其機而緄同以凝於一,唯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唯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26)張裕釗著、王達敏校點《濂亭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頁。桐城派隨順自然的藝術追求與莊子哲學思想是一致的。
桐城派學習模仿《莊子》散文風格的做法無疑是對《莊子》文學經典地位的認同,而他們在文藝理論建構中大量吸收借鑒《莊子》經典思想的行爲,不但豐富發展了《莊子》經典内涵,而且使《莊子》的經典文藝思想得到了强化和升華。這不但對清代文藝理論發展有着重要影響,即使對今天的文化建設也有着積極意義與指導作用。
三、 桐城派古文家對《莊子》文學價值的肯定與推崇
在《莊子》文學經典化過程中,明清評點家、文論家和文人的評價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綿延二百多年的桐城派就是這支隊伍中的一支生力軍,他們通過多種途徑對《莊子》文學進行批評,不僅推動了《莊子》文學經典地位的確立,而且使之得到了不斷的鞏固和加强。
第一,桐城派文論對《莊子》文學成就進行了充分肯定。首先,對莊子文章的大力推崇。如戴名世《老子論上》云:“莊周、列禦寇之流,其言依仿老子,吾觀其書,大抵憫世之昏濁,爲洸洋自恣以適己志,此文人學士之雄者耳。”(27)戴名世著、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卷十四,第399頁。姚範説:“莊周之文如飛天仙人,絶世聰明語,不容第二人道得。”(28)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四,清道光姚莹刻本。方東樹《昭昧詹言·通論五古》云:“以六經較《莊子》,覺《莊子》意新奇佻巧;以六經較屈子,覺屈子詞膚費繁縟,然而一則醒豁呈露,一則沉鬱深痛,皆天地之至文也,所以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29)方東樹著、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5頁。《王李高岑》云:“大約太白詩與莊子文同妙,意接詞不接,發想無端,如天上白雲,卷舒滅現,無有定形。”(30)方東樹著、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卷十二,第249頁。梅曾亮《讀莊子書後》云:“《莊子》者,文之工者也。”(31)梅曾亮著、彭國忠等注《柏梘山房全集》卷一,第85頁。薛福成《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云:“《莊子》,諸子之英華也。”(32)薛福成《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庸盦筆記》卷三,清光緒二十三年遺經樓刻本。皆對《莊子》文章激賞有加。其次,對《莊子》文學風格的評價。劉開《與阮芸台宮保論文書》云:“老氏之渾古,莊周之駘蕩,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勁直,韓非之峭刻,孫武之簡明,可以使之開滌智識,感發意趣。”(33)劉開《與阮芸台宮保論文書》,《劉孟塗集》,清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曾國藩《與張廉卿》云:“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柳宗元。”(34)曾國藩《曾文正公詩文集》卷一,《四部叢刊》影印清同治本。張裕釗《答劉生書》云:“古之爲文者若左邱明、莊周、荀卿、司馬遷、韓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厲而氣雄,然無有一言一字之强坿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唯此最爲難。”(35)張裕釗著、王達敏校點《濂亭文集》卷三,第57頁。分别以駘蕩、陽剛、俊偉、氣雄等總結出《莊子》文學風格特點,頗爲精當。以上評論見解精闢,無疑加深了人們對《莊子》文學價值的認識,提高了《莊子》文學經典地位,引起人們學習《莊子》散文的濃厚興趣。
第二,桐城派《莊子》評點著作對莊子文章的賞析。桐城派既是文派,又有學派性質,致力于將文與學有機結合起來,他們通過評點《莊子》,表達了自己的藝術思想。如劉大櫆《莊子評點》、姚鼎《莊子章義》、方潛《南華經解》、吴汝綸《莊子點勘》、馬其昶《莊子故》、林紓《莊子淺説》等。這些評點大都引入了“義理、辭章、考據”三位一體的桐城派家法,深化了《莊子》研究。單從辭章方面而言,有以下幾方面的貢獻。其一,文章脈絡的梳理。桐城派繼承前人的看法,十分重視分析研究《莊子》文章脈絡。如姚鼎解《逍遥遊》篇“夫水之積也不厚”段云:“‘水之積也’至‘培風’,承‘以息相吹’,言空際皆實氣所居,無空缺也。‘背負青天’二句承‘天之蒼蒼’四句,言上下寥闊無邊際也。遊於此正焉,與天地一矣。”(36)姚鼐《莊子章義》,清光緒五年刊《惜抱軒遺書三種》本。林紓評《逍遥遊》篇説:“通篇用一‘大’字作起結,以篇首有‘鯤之大,不知幾千里也’,故惠子一發問即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呺然大也’,此大而抹殺莊子言之無當,莊子矢口,立破他拙於用大。”(37)林紓《左孟莊騷精華録》卷下,上海商務書局1935年版,第11頁。等等。莊子文章脈絡分明,一線貫穿的特點得以深化。其二,比喻修辭手法的闡釋。桐城派尤其欣賞莊文“喻中設喻”的修辭技巧。劉大櫆评《逍遥游》篇“風之积也不厚”段説:“又于喻中設一喻,以解積氣之厚。”(38)引自吴汝綸《莊子點勘》,清宣統二年衍星社排印本。方潛評《逍遥遊》篇“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句云:“以水喻風,喻中喻。”(39)方潛《南華經解》,清光緒二十二年桐城方氏刊本。以下所引方潛資料皆出此本,不再注釋。評“適蒼茫者”句云:“以適喻飛,亦喻中喻。”評“小年不知大年”句云:“以年喻知,亦喻中喻。”“喻中設喻”雖然前人已提出,但桐城派的大力發揮使這一特徵大放異彩。其三,以“法”析莊。桐城派爲學主張“義法”,因此解《莊》時亦體現出這一觀念。如方潛評《庚桑楚》云:“莊子文極詭變,而法極嚴密,通其法則其文可知,而其理可得矣。”林紓評《逍遥遊》篇“惠子謂莊子”段説:“此節割截内篇之《逍遥遊》,另作一小篇,然亦自成文法,所謂大陣中之小圖陣也。”(40)林紓《左孟莊騷精華録》卷下,第11頁。評《養生主》篇“庖丁解牛”段説:“文節節有條理,均合於古文之義法。”(41)同上,第15頁。其四,分析莊文之筆法特點。如方潛評《胠篋》篇云:“此篇言特放肆而筆自奇横也。”林紓評《齊物論》篇云:“子綦之論天籟,用疊筆,如洪濤巨浪,一瀉而下。”“《南華》之文,每於極淒厲處,音漸幽咽,幾於沉沉無聲矣。必有崛起之筆,響發於空際。”評《德充符》篇云:“堙跂、支離、無脤一節,用短接之筆,其中逐句變化,讀之精熟,不唯得練字法,亦解制局法。”(42)林紓《莊子淺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排印本。以上分析使《莊子》散文藝術性得到了具體揭示,對世人學習《莊子》散文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同時也使《莊子》散文的經典地位得到了極大的鞏固與提高。
第三,桐城派古文家破天荒地將《莊子》收録入古文選本中,實現了《莊子》文學經典歷程上的一次重要突破。自蕭統以“以立意爲宗,不能以文爲本”爲由,將《莊子》等先秦諸子排斥在《文選》之外以來,歷代選學家基本繼承了這一傳統,所著選集皆不收《莊子》,這不能不説是一個缺憾。作爲一個古文流派,桐城派亦非常重視通過編纂古文選本來宣揚他們的文藝美學思想,從方苞的《古文約選》至姚鼐的《古文辭類纂》都明顯地體現出了這一特點,由於受“義法”理論的束縛,他們的選本多重視唐宋八大家以及歸有光等人的作品,故仍沿襲了《文選》做法,將《莊子》拒之門外。此種做法到曾國藩時才被打破。曾國藩宣導宗法先秦兩漢和魏晉文章,從而突破桐城派傳統,大膽地將《莊子》散文選入其所編的《古文四象》與《經史百家雜鈔》中,實現了古文選本的一次歷史性飛躍。之後,弟子黎庶昌編纂《續古文辭類纂》,亦選入《莊子》。林紓節選《莊子》編入《左孟莊騷精華録》,並加以評點,進一步提高了《莊子》散文的文學地位。以曾國藩爲代表的桐城派文選家對《莊子》散文的主要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確立《莊子》散文之“論著類”文體。歷史上,首先對《莊子》文體進行評論的是劉勰,他認爲《齊物論》一篇“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文心雕龍·論説》),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對《莊子》文體特徵的評述。而南宋吴子良、元代郝經等人卻持反對意見。如郝經以爲《齊物論》“篇第之名”(43)郝經《郝氏續後漢書》卷六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並非文體學意義上的論説文。有清時期,《莊子》散文評點發達,評點家們從不同角度分析了《莊子》的説理特徵。前人對《莊子》文體的探討爲後人積累了經驗,最終由桐城派學者完成了《莊子》文體的定位問題。姚鼐在《古文辭類纂》“論辯”中説:“論辯類者,蓋原于古之諸子,各類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録,録自賈生始。”姚氏將“論辯”體歸之于諸子的做法啓發了曾國藩,他將《莊子》中的《逍遥遊》《養生主》《駢拇》《馬蹄》《胠篋》《達生》《山木》《外物》和《秋水》九篇選入《經史百家雜鈔》,歸之“論著類”。而曾門弟子黎庶昌又唱和其師,將《莊子》中的《逍遥遊》《養生主》《駢拇》《馬蹄》《胠篋》《秋水》選入其所著《續古文辭類纂》中的“論辯類”文體。在曾國藩及其門弟子的努力下,《莊子》文體地位正式確立,成爲散文文體大家庭中的重要一類,亦使《莊子》散文成爲世人學習的經典範本。
其二,《莊子》“詼詭之趣”的藝術審美。如果説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是按照文體分類編選的一部古文選本,那麽其《古文四象》則是完全依照藝術審美標準編纂的一部古文選集。趣味是曾國藩論文的一項重要標準,“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詼詭之趣,一曰閒適之趣”(44)曾國藩《曾文正公家訓》卷上“同治六年三月一十二日”,清光緒五年傳忠書局刻本。。他特别欣賞《莊子》文章的詼詭之趣,“詼詭之趣唯莊柳之文、蘇黄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詼詭,此外實不多見”(45)同上。;“姚公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恢詭處不逮遠甚”(46)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辛酉三月”條,清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刻本。。因此,他將《養生主》《駢拇》《馬蹄》《胠篋》《外物》全篇以及《齊物論》《大宗師》《天地》《天道》《秋水》《至樂》《徐無鬼》《則陽》《列禦寇》篇中的部分章節選入了《古文四象》一書“少陽趣味”中的“詼詭之趣”一類,不但實現了古文選本的又一次突破,而且使《莊子》散文真正獲得了與其他古文體同樣的文學地位,在經典化道路上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四、 桐城派《莊子》文學經典建構的文學史意義
《莊子》文學經典化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是由各種力量的合力交織一起共同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既有文人、學者、文論家、評點家等爲主體的個人力量,又有一些流派、學派的群體之力。由於時代背景、政治環境、文化政策以及讀者群體的不同,使得《莊子》經典化在不同時代表現出了不同特點。而有清時期桐城派對《莊子》經典的建構最爲引人注目,貢獻較大,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認識。
其一,桐城派中前期所處時代正是清代文字獄最爲酷烈之時,文人學者噤若寒蟬,稍有不慎,即遭滅頂之災。此時的乾嘉學派專心于朴學,遠離政治,而桐城派不僅繼續發揮《莊子》“通子致用”精神,而且在文學創作中通過發揮莊子思想流露出對世事的不滿,表現出積極干預現實的熱情。在桐城派中後期,社會動盪,列强入侵,西學東漸,桐城派更爲重視發揮《莊子》經世致用思想,並通過大力提高《莊子》地位,賦予《莊子》鮮明時代内容,以圖革新求變,對抗西學。桐城派以上做法不僅使《莊子》經典思想得以傳承和發揚,而且擴大了《莊子》社會影響,開啓了近現代《莊子》經典化的新紀元。
其二,歷代《莊子》文學的經典化途徑並不完全相同,但後人總是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有所發明與創新,最終完成了《莊子》文學經典化的歷史重任。桐城派對《莊子》文學經典化建構的貢獻即在於此。桐城派自覺扛起了清代《莊子》文學經典化建構的任務,不僅在學術上對《莊子》作了考證、義理與辭章的研究工作,而且在古文創作、古文理論方面積極學習借鑒《莊子》,並首次將《莊子》編選入古文選本中,使《莊子》成爲了構建桐城派文統的重要資源。桐城派綿延二百多年,代代讀《莊》、研《莊》,對《莊子》文學經典化的建構作出了巨大貢獻,清代無有出其右者。在桐城派的努力下,《莊子》文學在清代大放異彩,歷史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桐城派爲傳統《莊子》文學經典化歷程可謂劃上了一個較爲圓滿的句號,並開啓了近現代《莊子》文學經典化新篇章,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其三,桐城派構建《莊子》文學經典的過程也是其自身解放思想,謀求走出創作困境,力求理論突破,尋求道統、文統與學統如何在更高層次上合一的過程。我們知道,自方苞提出“義法”理論以來,桐城派學者就一直對前人學説不斷進行修正,如劉大櫆、姚範、姚鼎對方苞理論的修正,曾國藩對姚鼎理論的修正等等,而他們的共同做法之一就是利用《莊子》作爲理論武器,或在創作中學習模仿《莊子》,或在文藝理論上吸收借鑒《莊子》,或對《莊子》文學進行評論或評點,或將《莊子》選入古文選本表達其文藝審美理想等等。通過這樣的努力,提高了桐城派學者的精神境界,豐富了他們的文藝理論思想,提高了藝術審美趣味,從而努力使其作品的藝術性與思想性達到有機統一。雖然桐城派的創作有很多值得詬病的地方,但他們開放的胸襟、與時俱進的探索與創新精神是不能被否認的。因此,充分認識桐城派建構《莊子》文學經典的意義,對於我們正確評價桐城派成就、客觀看待他們對中國文學史的貢獻是有其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