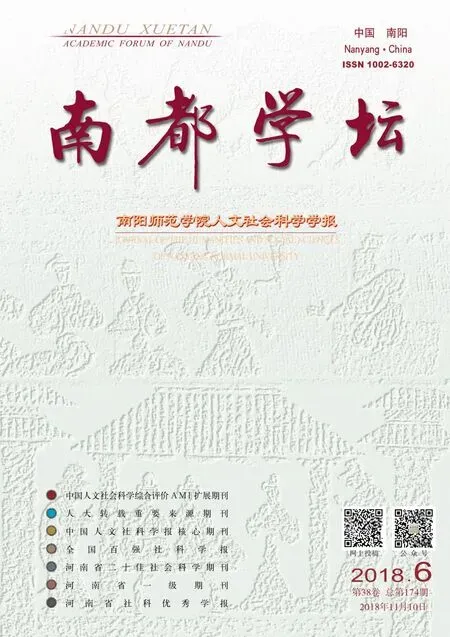伊尹新论
2018-01-23刘夫德
刘 夫 德
(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 西安 710061)
伊尹名挚,又称阿衡,相传是商代初年的大臣。他被认为是一位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杰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甲骨卜辞中称他为伊尹、伊,与商汤(大乙)等殷商的先公先王一同被祭祀。金文中则称其为伊小臣,并称颂他对于商汤的辅弼和翦夏的贡献。在早期以儒家为中心的文献中,他是一位贤能的宰相和帝王师,他主要的事迹除了助汤伐夏,还在商汤死后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为了教育太甲,伊尹曾将太甲放之桐宫,他代为执政,在太甲悔过自新后,又迎回太甲,交还王权,并继续加以辅佐。然而这是一面之词,出土于晋太康年间的《竹书纪年》则说他放太甲之后被太甲潜出所杀,其内容与传世的典籍相抵牾。虽然有许多的学者加以辩解,但是,由于《竹书纪年》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所以这一记载不容忽视。
一、前人对伊尹的认识
《竹书纪年》出土以前,人们对伊尹一致采取褒扬的态度,《尚书》《诗经》《左传》《史记》以及后来出土的甲骨文等都是如此。诸子百家中不仅儒家,像法家、兵家、墨家、道家、杂家等也都十分称颂伊尹。历史上伊尹被人称为“元圣”,历代都把他与周公相提并论,认为他是忠臣良相的代表。当然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是没有,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孟子·尽心上》里的公孙丑,从维护皇权的角度对伊尹的行为进行过质疑。但这在《竹书纪年》出土前是个别的例子。
在汲冢竹书出土以后,就太甲废立一事虽然人们的观点分成两类,但大部分人并没有改变既成的观念,仍对《竹书纪年》的记载持怀疑态度。据说曾注过今本纪年的沈约就认为太甲杀伊尹一段记述“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唐人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也辩说:“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杀之,则伊尹死有余罪,义当污官灭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复立其子,还其田宅乎?《纪年》之书,晋太康八年,汲郡民发魏安僖王冢得之。盖当时流俗有此妄说,故其书因记之耳。”
宋人柳开的《太甲诛伊尹论》针对《竹书纪年》所载太甲杀伊尹之事,根据大量史料进行了辩驳: “《周书·君奭》篇云:‘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是其君臣悉见其父子间保全令德也……苟伊尹为臣,能放其君,是其政在尹也,能制于甲矣,岂甲反能以不道害之乎?且尹之相汤伐桀,以成其功,民咸知尹而辅矣;复以其自立为君,而又七年以永其位,若是,何有甲之所能哉?既云尹乃自立,是因事而夺君位也,为逆甚矣。太甲能潜出以诛之,岂肯反用其子乎?必以反用其子,其子果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尽道而佐其甲乎?”(《柳开集》卷三)
清人崔东壁的意见与此大同小异。他在《商考信录·辨太甲杀伊尹之说》中,引用《孟子》等古籍中的有关资料,竭力证明《竹书纪年》记载讹误。他辩说:《孟子》中有“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的记载,说明太甲是悔过返都了的;《左传》中有“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声”的记载,说明他并未杀伊尹;沃丁礼葬伊尹后,《尚书》中的《沃丁》篇,赞颂伊尹的功德,说明伊尹系善终;《竹书纪年》中所载太甲杀伊尹后,又任其子伊陟、伊奋为相,杀其父又立其子为相,实属不可信。崔氏还继承孔颖达的观点,认为《竹书纪年》应是受战国之时多弑君杀主、世风败坏的影响,才出现伊尹夺位被杀之说。他坚持认为伊尹是心地广大、光明若天地日月的“圣人”,怀疑《竹书纪年》是否将这段史料抄错了。其实历史上杀其父而任用其子的例子不是没有,例如史上因治水失利杀鲧而用其子禹;刘秀杀真定王刘杨而用其子刘得为新真定王等。
近人怀疑《竹书纪年》的人也很多,例如金景芳先生说:
《竹书纪年》说:“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太甲,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这条记载……应出于后人意在强调君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为,不足为据。[1]
现在坚持太甲未杀伊尹一派的主要论据是出土的甲骨文中,伊尹与商汤(大乙)等殷商的先公先王一同被祭祀,如果伊尹作为逆臣真的被杀,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因为《竹书纪年》所述史事,经考证后,发现颇多可信,因此其史料价值极高,所以另一派意见则认为, “太甲杀伊尹”之说也当是可信的,伊尹是篡位后被杀的逆臣。伊尹改造太甲、归还国政之说只是儒家立论的说教而已。曾亲自检看过汲冢竹书的杜预对此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他不仅不疑《竹书》,反认为《尚书》记载的不同应是伏生的老迈昏聩所致。刘知几著《史通》,在其《疑古》篇以及《杂说》上篇中对于《竹书纪年》中所记伊尹的被杀等说法,认为是可信从的史实,并且揭露儒家书所言传贤禅让之说不实。此说体现出刘知几的史识能力,但却历来为许多卫道者所诟病,曾遭遇胡应麟、郭孔延、黄本骥等许多人的竭力反对[注]参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卷五、卷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郭孔延《史通评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黄本骥《痴学》第七卷《信古录》,收自《三长物斋丛书》,清道光(1821-1850)刻本。,甚至《疑古》篇的这一部分内容也遭到一些人的删削[注]如黄叔琳《史通训故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纪昀《史通削繁》,大东书局1932年版。。唐僧法琳在《决对傅奕废佛僧事》一文中也肯定《竹书纪年》的伊尹自立、太甲杀伊尹事,认为是“舋起萧墙。君臣无道” (法琳《广弘明集》卷十二)。明人祝允明则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祝子罪知录》卷一)。他显然意识到儒家的所谓放太甲迎太甲其实就是对伊尹篡位和太甲反击的粉饰。近人孙淼先生也认为伊尹篡位当有其事,所谓放太甲其实就是篡权,所谓迎太甲,“授之政”,实属牵强附会。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个昏君被改造过来,说太甲面壁三年,改恶向善,是后世儒家加工润色的结果。说太甲有“暴虐”“乱德”等行为,但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这个说法是妄加之词还是实有其事还是个问题[2]。
以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使不少人难以决断。清人梁绍壬就说:“耏野之师,桐宫之放,事为其创,功罪惧难言之也。圣人之意深矣。”[3]其实除《纪年》外,《御览》卷八三引《琐语》也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其观点和《纪年》同。可知伊尹自立之说战国以前是存在的,并不是《纪年》一家的妄言。
对于伊尹的思想,议论者很多,虽然不能完全脱离伊尹的所作所为,但主要是后人的借题发挥。《尚书》等文献中表现出的伊尹的政治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行“德”政,具体内容有敬天爱民、仁、善等。 这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伊尹在历史上应是一个靠立德上位者。
就具体人来说,最早议论伊尹的作为及其背后思想的大概要数春秋末年孔子的弟子子夏,而议论最多的大概要数孟子。子夏说:“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认为伊尹是仁的代表。孟子则继承了这种思想,他认为伊尹是“伐夏救民” 的仁人。孟子对伊尹议论和褒奖尤多,他不仅说伊尹推行尧舜之道,是仁的代表,还说伊尹是“先知先觉”,是“圣之任者”。孟子以民为本、仁政爱民的政治主张应该与此有关,这种思想认识也影响了后世许多人。柳宗元写《伊尹五就桀赞》,就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伊尹是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念,极其有责任心的伟大仁人。他说:“吾观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 ”程颐、朱熹等人也都是这样的思想,朱熹《孟子集注》也说:“伊尹之志,公天下以为心而无一毫之私者也。”这可以说是儒家道统的一条主线。
北宋徐铉在其《伊尹论》中以为,曲解圣贤至公之所为而达到自私之目的是极常见的现象,霍光之乱引伊尹放太甲之例,并不能归罪于伊尹。反过来,若天下归心于伊尹,则伊尹代太甲亦无可非议。伊尹对太甲的放而复立,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智谋,也显示伊尹的忠诚品格(《骑省集》卷二十四)。苏轼则写了《伊尹论》,称赞伊尹是“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节者”。
伊尹的形象在历史上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汉代霍光废昌邑之举,曾援引伊尹事。田延年对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资治通鉴》卷二四)董卓废帝,司马朗也说:“原明公监观往事,少加三思,即荣名并于日月,伊、周不足侔也。”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唐代罗隐在《伊尹有言》中说:“及商汤氏以鸣条誓,放桀于南巢,揖逊既异,浑朴亦坏。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则臣下有权始于是矣。”(《谗书》卷一)伊尹一生审时度势、深谋明智,往往被后人所肯定,宋儒(程颐、邵雍、朱熹等)的释《易》之作,以及清江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 )等人的著作中多有体现。 近代梁启超也曾借伊尹励志:“欲求国之自尊,必先自国民人人自尊始。 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余觉之而谁也。’”(《新民说》)
关于伊尹和商汤的遇合和交集,史料记载也有差异。一般有三说:伊尹负鼎俎干汤;伊尹为媵见汤;汤前往聘伊尹。这些可以看作是史料,也可以认为是古人对于伊尹事迹的认识和发挥。
由于伊尹的家奴出身与一代贤相之间的距离过于悬殊,因此也有一些学者对伊尹的家奴身份不予认可,而认为伊尹是夏代贤臣,有高度的政治智慧,丰富的从政经验,他的离夏从汤,是明主与贤臣的双向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机遇[4]。有人同样否认伊尹的家奴身份,而把伊尹设想成一位大巫式宗教领袖,有权有势,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助汤灭夏[5]。但上述观点论据薄弱。
近年来对于伊尹的研究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进展,由于国外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影响,有学者提出商代存在二头政治、二头轮流执政。美籍华人张光直先生从研究甲骨文入手梳理殷商王制,认为商代的王位是由十个以天干为标志的礼仪单位分成两组轮流执政,伊尹在其中一组之中。他进一步认为这种王位继承制度就是舅甥相承制[注]还可参见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证》,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5期,1963年版,第165-202页;《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商王制》,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73年版,第111-127页。[6]。此外,认为伊尹和商汤二头并政的还有江林昌先生,文中认为伊尹与商汤的关系实际上是氏族社会禅让制度的遗存,伊尹是二头政治盟主之一[7]。反对的意见则大多采取传统的观点加以驳斥。
二、伊尹即寒浞
要想解决伊尹的问题,首先需要把伊尹在历史上所处的时代背景搞清楚,不然就很难着边际。
陈梦家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作商世即夏世说[8]。他列举夏和商的诸帝相应的关系说:夒即喾;启就是契;相就是相土;芒就是冥;槐就是亥;不降是王恒;履癸即示癸。另外,刘夫德《上古史发掘》认为《史记》中的五帝时代也就是史上虞夏时期的重复[9]225。以这些观点推论的话,商汤伐夏桀,也应就是后羿代夏故事的异传。汤在甲骨文中名“乙”,应该就是羿,音同。在金文中汤被称为“成唐”(《叔夷钟》),这与唐尧有关,唐即尧,也即羿,尧、羿音通。伊尹被指是汤的“相”“臣”“小臣”(《墨子·尚贤》《淮南子·泛论训》《楚辞·天问》、《叔夷钟》铭等 ),那么汤的相或者臣也就是羿的相或者臣,那么羿的相或者臣是指谁呢?《左传·襄公四年》: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寒浞,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贿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享(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
又《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
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及夏之衰,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弃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伯明后以谗弃之,而羿以为己相。寒浞杀羿于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穷门。浞遂代夏,立为帝。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于过,封豷于戈。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初,奡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氏,收斟寻二国余烬,杀寒浞,立少康,灭奡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也。
汤的相应该就是指引文中羿“以为己相”的寒浞。伊尹于汤对应于寒浞于羿的身份,伊尹即寒浞。羿、浞的代夏也就是伊尹的助汤伐夏,这应是同一件史实的不同传说。
伊尹,《天问》称“伊挚”,《史记·殷本纪》《索隐》引《孙子兵书》:“伊尹名挚。” 挚,何许人也?据《左传·昭公十七年》《世本》(《路史》后记注引)《帝王世纪》和《通志》等均言挚即少昊。少昊字青阳,亦称玄嚣,金天氏。据郭沫若等人的研究,挚就是契[注]郭沫若认为:“少昊金天氏帝挚,其实当即是契。古挚、契同部。挚之母常仪,契之母简狄,实系一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页。,也就是玄鸟生商故事里的契。少昊也是以鸟名官者,他们是同一个“人”。
《史记·五帝本纪》称挚“不善”,看来挚是没有善终的。 另外,与伊尹和汤相对应的除了羿和寒浞之外,还有王亥和有易,有易就是羿[9]93,而王亥应该就是伊尹。王亥的被杀也可以看作是挚的“不善”。王亥在《太平御览》中又是鲧[注]《太平御览》八百九十九引《世本》做鮌,即鲧。,鲧也被杀了,因为那是同一件事情的异传。
严格说来,伊尹和少昊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少昊其实就是指夏后氏,是以太阳和鸟作为象征的一部。伊尹(寒浞、王亥、鲧)曾经是夏后氏集团的一部分,但他后来叛夏了,并且帮助汤推翻了夏统治者。
《左传·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扈即崇[注]《左传·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杜预注:“始平郡有户县扈乡甘亭,殷为崇国。”,就是崇伯鲧(伊尹)。《史记·殷本纪》《索隐》述赞:“旋师泰卷,继相臣扈。”“臣扈”虽泛指扈从,但本义即应源于“有扈”,即指伊尹。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扈民是分两部分的,依附于少昊(夏后氏)的是“扈民无淫者”,而另有一部分非“无淫”者,应该就是叛夏者,也就是到汤(羿)那里去了的伊尹。
传说伊尹生于“空桑”,《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
至于空桑在何处,则说法很多。有说在今河南省杞县[注]范成大《揽辔录》:“丙寅,过雍邱县(今河南省杞县),二十里过空桑,世传伊尹生于此。一里过伊尹墓。” 见《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页。;有说在河南省嵩县[注]《明一统志》:“空桑涧在嵩县南,有莘氏女采桑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长而相殷,是为伊尹。”;也有说其出生于伊水,伊尹故里在陈留东北二十里[注]《河南通志》卷七《山川上》:“伊水,在陈留东北二十里,环绕伊尹故里。”。
伊尹母身化为空桑,应该是附会伊尹生于空桑传说而来,人是不可能化为桑树的。而空桑应该是指穷桑,“空”“穷”音通,“空谷”“传音”一作“穷谷传音”,就是指曲阜地方。少昊挚邑于穷桑,许多传说少昊与空(穷)桑有关。《尸子》:“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 穷桑一说在鲁北,一说即曲阜。《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昊氏有四叔。”杜预注:“穷桑少昊之号也,四子能治其官,世不失职。济成少昊之功,死皆为民所祀。穷桑地在鲁北。”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 《帝王世纪》:“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 《曲阜县志》也记载:“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挚,黄帝之子玄嚣也。”曾都曲阜,陵也在曲阜。《淮南子·主述训》:“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诱注:“空桑地名,在鲁。”此空桑应即穷桑。曲阜是传说中夏后氏的政治中心。《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有学者认为穷石即穷桑。石与桑为同纽字,又阴阳可对转[10]。伊尹作为夏人的一部分,说他生于空桑实在没有错,其地应在鲁。
三、伊尹的社会地位及其“五就汤、五就桀”的原因
传说伊尹曾耕于有莘之野。《孟子·万章上》:“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汤三使往聘之。” 说伊尹躬耕和耕于有莘之野应该并不是信口而说,历史上伊尹确和农耕有关。
前述伊尹即扈,而有扈是少昊氏的农正。扈即崇,即崇伯鲧。《天问》中说鲧在西迁时曾沿途播种农作物:“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另外,有莘,一作有侁,字无定字,怀疑即高辛氏。高辛即帝喾,喾,音通杼、浞,就是伯杼、寒浞。前述伊尹就是寒浞,因此也就是高辛氏。另外,伊尹也曾封于高辛。伊尹即挚,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纪》云:“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于高辛。” 这样说来,说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并不是没有根据。
有关伊尹“负鼎干汤 ”的传说文献记载比较多。 《史记》:
伊尹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
《墨子·尚贤》:
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
《庄子·庚桑楚》 :
是故汤以庖人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
《战国策·冯忌请见赵王》:
伊尹负鼎俎而干汤,姓名未着而受三公。
《韩非子·难言》:
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
《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爟火,衅以牺猳。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圣人之道要矣,岂越越多业哉?
《鲁仲连子》 :
伊尹负鼎佩刀以干汤,得意,故尊宰舍。
《离骚》:“缘鹄饰玉,后帝是飨。”王逸注:
后,殷汤也;伊尹始仕,因烹鹄鸟之羹,修饰玉鼎,以事汤也。
《楚词·涉江篇》:
伊尹烹于庖厨。
《韩诗外传》:
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
《 淮南子·泛论》篇高诱注 :
伊尹负鼎俎,调五味以干汤,卒为贤相。
前述伊尹即鲧。鲧为崇伯,崇、重同音,崇就是重。《尔雅·释诂》:“崇,重也。”重即火神重黎之重。火神也即灶神,因此其有曾为庖人和负鼎调味之说。所以说伊尹为庖人以及负鼎操俎以干汤,也不是信口开河。重即句芒,《吕氏春秋》 高诱注:“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又《礼记·月令》 郑玄注:“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为木官。” 少昊即挚,伊尹也即挚,实际上伊尹也应就是少昊一部的重。“句芒”,又作“汪芒”等,“蓬蒙”是其对音,杀羿(汤)者。杀羿者有二人,一是寒浞,一即蓬蒙,寒浞是伊尹,蓬蒙也是伊尹,他们应是同一个“人”。
《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
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
何者为媵?《说文》:“送也。”指陪嫁者。《仪礼·士昏礼》注:“古者嫁女,必娣姪从之,谓之媵。”媵由此引申有臣仆义,如“媵臣”“媵从”“媵御”等。
另外,《韩诗外传》说:“伊尹,故有莘氏僮也。”也有的文献称其为“臣”“小臣”等。笔者觉得这种传说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伊尹在有莘(高辛)氏集团时,其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在社会分工上有别于神职和管理等阶层,是处于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一种地位,虽然那时未必有奴隶,这或者可以类比于印度的低等种姓。从《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关少昊氏的记载来看,其中有历正者,有司分司至者,有司启司闭者,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以及鸠民者夷民者,而扈民在这一集团中地位是最低下的。他是农正,是从事农业生产者,说他曾为“媵”为“僮”真的没有错,他的反叛可以说是最早的农民起义。“扈”在字典中有扈从义,可能就和当年扈民在少昊(夏后)集团里的社会地位有关。
有扈氏叛夏的原因,据说是启夺了益的盟主地位,因此不服[注]《史记·夏本纪》曰:“……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84页。。但从上述史料分析,是不是伊尹叛夏是为了挣脱自己的下层社会地位而做的努力?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被称为“盗跖”的人物,跖一作“蹠” ,字无定,音同“挚” ,疑是伊尹的化身。跖虽然在庄子书中被说成是春秋时人,但那应是托古。《史记· 伯夷传》正义: “蹠者,黄帝时大盗之名。以柳下惠弟为天下大盗,故世放古,号之盗蹠。”
盗跖在其他书中是和桀并称的。《荀子·荣辱》:“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淮南子·说山训》:“桀跖之徒,君子不与。” 又有成语“蹠犬噬尧”(《战国策·齐策六》)、“蹠狗吠尧”(《新唐书·孙伏加传》),可知他是尧时代的人。而尧,前述即羿,即汤。“跖犬噬尧”又作“桀犬吠尧”(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因为桀即契[9]232,即挚,益知跖即伊尹(挚)。跖在历史上是大盗的代称,“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庄子·盗跖》)。实际上就是农民起义。其声势很大,《荀子· 不苟》曾称赞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叶主绶《续山东考古录》:“樊县故城在滋阳西南二十五里,俗名顾王城……俗传盗跖所居。”明万历版《兖州府志·古迹》:“顾王城,在府城西南三十里,城北有墓,曰跖冢。”清康熙版《滋阳县志》:“柳下惠之弟展雄,孟子所称盗跖者,在邑西三十里筑城自卫,能周济邻里,号曰顾王,名曰顾王城。”为什么盗跖称“顾王”?顾即扈[注]见《说文解字》;又陈梦家认为顾即卜辞之雇,见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05页;王国维认为卜辞的雇即扈。见于其《说亳》载《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2页。,指“有扈”,就是夏之“扈民”,指伊尹。
孟子说伊尹是先知先觉,是“圣之任者”,《易·革·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换句话说,伊尹是一位助汤革命的伟大的先知先觉、顺天应人的革命家。
《孟子· 告子下》:“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赵岐注:“伊尹为汤见贡于桀,桀不用而归汤,汤复贡之,如此者五。”
《淮南子·泰族训》:“伊尹忧天下之不治,调和五味,负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汤,将欲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 ”
伊尹犹豫、徜徉于汤、桀之间,这个问题其实是解开上古史上一些问题的关键,关系到认识当时是三分天下还是两分天下的问题。
从上述《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的那段话来看,伊尹(有扈)这一集团的一部“无淫者”是存在于少昊(夏)集团之中的,而另一部分非“无淫者”,就是叛夏者,应该属于汤集团一部。这种分属两个集团的状况或者就是传说伊尹“五就桀,五就汤”的根本原因。这些所谓古人实际上应该并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些集团的代称。由于相互之间的纷争,一些集团的属性是在变化着的。例如《西山经》云:“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丕鸟】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山加鹞去鸟】崖。钦【丕鸟】化为大鹗……鼓亦化为鸟……”“钟山”应即“崇山”,音“通”。“鼓”通“顾”。这正是指崇山神鲧(伊尹)这一部,这一部因故化为鸟了。由此可知,伊尹确实改变过身份。
又如舜有两个弟弟,《大戴礼记·帝系》:“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而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舜只有一个弟弟象,司马迁只说他性格傲,敖在这里被抹杀了。其实敖是存在的,他和象在一起时被称为“象敖”,他和舜在一起时,他就等同于舜。敖其实就是黄帝之下留有姓名的二子之一的玄嚣,嚣也就是敖,“仲丁迁嚣”一作迁隞。敖在舜(桀、少昊)集团时,玄嚣就是少昊(《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帝王世纪》)。事实上敖就是伊尹,这是一个故事的分化,下面在谈及玄嚣一名时还会谈到这一点。
四、伊尹的被杀与否、其名字的来源以及当时的社会结构
《竹书纪年》是说伊尹被杀了的,而众多后世学者并不认可。但从《山海经》上述的记载,以及鲧和王亥的被杀等故事来看,伊尹是被杀了的。前述鲧即伊尹,王亥也是伊尹。王亥宾于有易而淫,寒浞也曾因于羿室,有易就是有羿。《天问》中说有扈的事应该也是指这件事[注]少康应即少昊。参看刘夫德《上古史发掘》,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少康“长颈鸟喙”(《路史》)与少昊的“以鸟名官”是一致的。此外发hao音的字如郝,客家话发音kok,近康音;发kang音的字如忼、邟的声母可以转化为h;其他如妔、吭、薧等字的声母也可以k、h转变。。
在王亥故事中,王亥是被有易所杀,上甲微曾为之复仇。太甲也应该就是上甲(微),也应就是复国的少康,也就是少昊[注]《楚辞·天问》:“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而少昊即挚,即契。因此《国语·鲁语》说:“上甲微能率契者也,商人报焉。”他的国曾经一度被汤(羿)和伊尹(寒浞)所灭。虽然王亥故事中,王亥是被有易杀害,但实际情况可能是有易(羿、汤)的势力是被王亥(伊尹、寒浞)破坏的,这一点在《左传》中有反映,是寒浞先灭羿,然后自己又被夏后氏的势力所扑灭。因为有易(羿)也就是益,所以这还是那个益启相争的故事。
史书对这段故事记载不尽相同,但伊尹(鲧、王亥、有扈、敖、寒浞、鼓)被杀是可以肯定的。实际上,伊尹还应该就是历史上被杀的蚩尤。蚩尤即鲧[11],也即寒浞[9]392-399,因此也就是伊尹。蚩尤冢在“阚乡”,肩脾冢在“重聚”(《皇览·冢墓记》)。“阚”音同“寒”;重即寒浞(鲧)。涿鹿之战之“涿”音同“浞”。《竹书纪年》说伊尹被杀时“天大雾三日”,《论衡·感类篇》也说:“伊尹死,大雾三日。”而《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 这都可以互证。又如史称蚩尤作兵,兵器制作与火有关,而传说伊尹亲为庖人、负鼎佩刀等,也是与火有关,因为他们就是火神重黎之重。其间汤就是炎帝、黎,而少昊应就是涿鹿之战中的黄帝。
总结一下,在伊尹故事的各种异传中,伊尹的被杀大致有下面几种版本:
伊尹被太甲杀(古本《竹书纪年》)。
王亥(伊尹)被有易(羿、汤)杀(《山海经》及郭璞注)。
有扈(伊尹)被启(契,夏后氏)杀,一说被相(汤)杀(《尚书·甘誓》)。
浞(伊尹)被夏的遗臣灭(《左传·襄公四年》《帝王世纪》)。
有过(顾、扈、伊尹)被少康(少昊、夏后氏)杀(《史记·吴太伯世家》)。
重黎(伊尹、汤)被喾(禹)杀(《史记·楚世家》)。
浇(伊尹)被少康(少昊、夏后)杀(《楚辞·天问》)。
丹朱(伊尹)被尧(羿、汤)杀(《庄子·盗跖》《韩非子·说疑》)。
蚩尤(伊尹)被黄帝(少昊)杀(《史记·五帝本纪》)。
钟山神鼓(伊尹)被帝戮(《山海经·西山经》)。
鲧(伊尹)被祝融(黎、汤)杀(《山海经·海内经》)。
鲧(伊尹)为尧(羿、汤)所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 。
从中可见伊尹被杀应该是事实。杀伊尹者有汤(羿、尧、祝融黎)和夏后氏(少康、少昊、契、启、桀、“帝”、太甲、上甲微)的区别,伊尹不应是指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指一个集团,所以其可能与夏后氏和汤两个部落集团都有过矛盾。
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它和《山海经》比较的话,《山海经》应该还是比较原始的。在《楚世家》中重、黎是不分的,重黎最终被喾杀。喾其实就是鲧自身一部,这里可以看作鲧子禹,音通(喾音通杼,杼一作予)。《山海经》也说过“鲧腹生禹”的话。《竹书纪年》的杀伊尹而用其子,也应就是杀鲧(伊尹)而用鲧子禹。
关于“伊尹”一名的问题,多说伊是地名,与伊水有关[注]参见《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其母居伊水之上。”;尹是官职[注]《史记·殷本纪》皇甫谧注:“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伊为人名,尹是官名。”。但是,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伊尹还有一个化身就是“关尹”,就是在老子故事中,陪同老子“具之流沙”的关令尹喜。但是,说关尹是关令应是后人对“关尹”的望文生义。“关尹”这一名字源于“环渊”,关环尹渊一声之转[12],这也是“玄嚣”一名的来源[9]353,关尹和老子实际上就是玄嚣和昌意的化身,也就是黄帝和炎帝、伊尹和汤的化身。黄帝即“轩辕”,音同“玄渊”,来源于“玄嚣”“环渊”。伊尹不是蚩尤吗?怎么又成黄帝了呢?这是因为伊尹(玄嚣)曾经存在于少昊(夏后氏)集团中,因此少昊氏也就有了玄嚣、玄渊(轩辕)之名。伊尹应该是少昊氏的先辈,也应就是所谓“虞”,所谓“太康”。而少昊即少康,也就是夏后氏。从这种意义上讲,伊尹(玄嚣、玄渊、轩辕、蚩尤、寒浞)其实才是真正的黄帝。而少昊氏的“玄嚣”之称可以说是“僭越”了伊尹的一个名号。《史记》记载的涿鹿之战中的黄帝则指的是少昊。
前述鲧也是伊尹,鲧字“熙”(司马贞《史记索隐》),与关令尹喜之“喜”应是同音的不同表记。他们是同一个“人”。因此“伊尹”也不是什么在伊水长大的一个官儿的意思,而是同“关尹”一样,是玄嚣一名的一个分化。这个名字分化出有十个以上的名字,除“关尹”“玄渊”“环渊”外,还有“娟嬛”“蜎嬛”“便嬛”“它嚣”“范蜎”“蜎渊”“娟环”“娟嬛”“便蜎”“范瞏”等[12],另外还有“宓喜”“宓牺”“伏羲”等,“伊尹”应是其中之一。伊在上古中原地区应发ji音,与现在客家语发音近似,与“娟”音是双声。伊即渠,发渠音的字,不少可以发ju音,如瞿、忂、苣、郥、岨、弆、跔、跙等。另外,伊即他、她,以上诸分化的名字中有一名叫“它嚣”,音同。而伊尹之“尹”和关尹之“尹”则是同一个字。
从上述有关伊尹的一些史料来考察当时的社会结构,伊尹作为一个集团是分作两部的。其一部存在于桀(少昊、夏后氏)之中,其另一部则和汤(羿)集团结合在一起。伊尹(鲧)在和汤(羿)一起被迫西迁时,被《天问》称之谓“并投”,是一种双子集团的写照。《山海经·海内经》 :“有嬴民,鸟足。有封豕。”这应该是这二部西迁后的景象。封豕即王亥(伊尹、鲧);嬴民,据吴其昌,就是摇民[13]。那么也就是尧,指羿(汤),摇羿音通。这显然是一个两合组织。事实上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重、黎二部。传说中王亥(寒浞)曾经贪欲过有易(羿)的女人(“浞因羿室”),从这一故事可以看出,在汤和伊尹的集团间似乎是存在有通婚关系,应该是两个通婚的兄弟部族。又因为伊尹曾经存在于舜(桀)集团,所以这一故事也被说成是舜贪欲象的女人。
关于我国古代的二头政长制,许多学者都有论述,例如郭沫若,他说:“又尧舜禹的传说,都是二头政长。在尧未退位以前是尧、舜二头,在尧退位以后是舜禹二头。尧时又有帝挚为对。均与西印度之二头盟主相合。”[14]
翦伯赞也有类似观点,大致认为伏羲、神农以至尧、舜,为中国历史上的蒙昧时期以至野蛮中期时代,而黄帝、颛顼、帝喾、挚、禹、皋陶、益等,依次两两成对,递相为母系氏族社会的二头军事酋长[15]。
除上述张、江二先生所阐发的商史上的情况之外,从周史上的弃和叔均兄弟二部、秦史上的鸟俗氏和费氏二部等这种二头组织的史料来看,我国古史上曾经存在过两合组织这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这是氏族社会一种通常的社会结构。西周时期的昭穆制度可能就是其孑遗。这种组织的存在,同时也必然存在其代表人物。不过,不能肯定上述汤、伊尹等就是真实的个人,他们只是集团的化身,因此说他们就是二头政长、二头军事酋长还为时过早。
综上所述,由于虞夏时期即五帝时代的重复,浞羿代夏即汤和伊尹的灭夏,这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传说,因此伊尹即寒浞。除此之外,伊尹在历史上异传很多,他其实还是鲧、王亥、蚩尤、有扈、重、跖、伯杼、柱、高辛、太昊、太康、玄嚣等,并且因为他曾经是夏后氏(少昊)集团的成员,他还可以看作是少昊、挚、舜、黄帝等,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历史“人物”,是中华三祖(炎、黄、蚩尤)之一的蚩尤,也是契文中三高祖(夔、王亥、乙)之一的王亥。他曾经是夏(少昊氏)集团的一部分,其后也确实和汤结成过两合社会组织,是当时多头社会之一部。他对夏集团的颠覆,可以说是最早的农民起义。他在历史上确曾被杀,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没有错。虽然如此,但很难说他是一位具体的个人,只能说他是集团的化身,他的被杀应该是指一个集团的覆灭。伊尹(鲧)被殛于羽山潜于虞渊,虞即驺虞,是神话中的月兽,而西方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布满象征月的蟾蜍纹、魍魉纹、十字纹、龙蛇纹等纹饰,其应即他被“杀而放之”后的文化遗存。伊尹在甲骨文中被分组祭祀,代表了时人对那段历史的一种认知。伊尹的那个时代距离甲骨文时代也已经非常遥远,作为追忆的历史也不能说是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