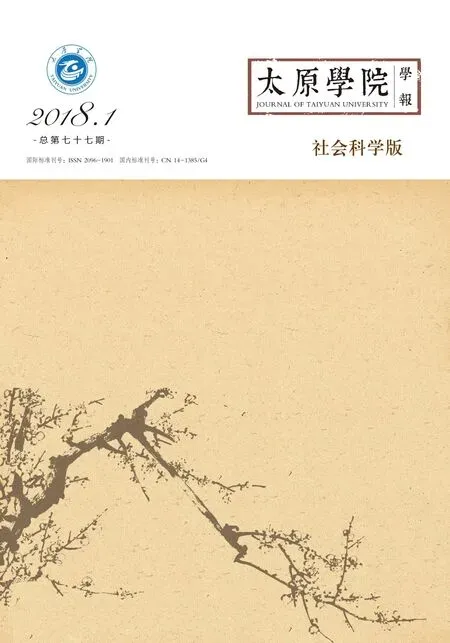《邂逅者》的地理空间叙事
2018-01-23胡
胡
(长江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0)
2014年7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去世,享年90岁。戈迪默生前著作颇丰,仅长篇小说就有十五部。在这些小说里,戈迪默建构了各种空间,尤其是地理空间,来反映社会背景、人物的思想以及各种文化,从而揭示南非的社会现实。出版于2001年的《邂逅者》*《邂逅者》是戈迪默的第十三部小说,原名为The Pickup。该小说被介绍到中国后,有学者将小说名译作《邂逅者》,也有译作《偶遇者》。本文作者倾向于将其译作《邂逅者》。论文中所引用的该小说部分译文引自漓江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梁永安所译的中文简体版《偶遇者》。被认为是戈迪默最好的小说之一。该小说讲述了一个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移民故事。南非富家千金朱莉毅然跟随非法入境的修车工阿卜杜来到他贫穷落后的沙漠故乡。在朱莉努力适应当地的环境并融入当地的生活和文化之际,阿卜杜却依然执着于移民他国。在故事中,戈迪默构建了三重不同的地理空间:人文地理空间、自然地理空间与理想符号空间。“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往往体现了作家的审美倾向与审美个性,以及他的创作理想与创作目标。”[1]作者在《邂逅者》中建构的地理空间隐喻了南非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失衡,同时指向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藉此,我们也窥见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审美空间的建构方法。
一、人文地理空间与人物塑造
戈迪默对故事中的人文地理空间建构颇具匠心。《邂逅者》的主人公来自两个国家。故事的前半部分是发生在朱莉的家乡——一个不知名的非洲都市,故事的后半部分发生在阿卜杜的家乡——一个边远的阿拉伯沙漠村庄。戈迪默通过主人公的生活轨迹呈现了三组对比的人文地理空间:街道、咖啡馆与家屋,再现了两位主人公各自的生活背景,揭示了人物性格的成因,为人物形象塑造做好了铺垫。
1.街道:社会图景的缩影
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示故事的前半部分发生在哪个国家,但是通过后文陆续提到的种族隔离、权力分配、经济发展等话题可以推测,这个颇为现代化的城市特征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极为吻合。戈迪默在《邂逅者》中对这个都市街道的刻画,几乎囊括了全球化时代这个国际大都市存在的所有社会问题。街道成为南非社会图景的缩影。
故事的开篇始于街道。“捕食者团团围住猎物。那是一辆小轿车,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子。”[2]1朱莉的车因为电池失灵抛锚在大街中央,各种车辆挤成一团,一群交通暴民的肆意辱骂让场面更加失控。在一个靠给人找停车位的黑人的帮助下,朱莉的车被推到路边,问题暂时解决。心有余悸的朱莉“感觉到了冰冷的鼻子,呼出的热气还有闪亮的牙齿就在她的脸旁”。[3]“猎物”的切实感受形象表现了她孤立无援、没有归属的生存境地。把朱莉比喻为猎物,围观的人群比喻为捕食者。作者用自然纪录片一样的表现手法描述此时嘈杂失控的场景,暗喻这个城市好似丛林般生机勃勃却又危机四伏。
这是一条极具嬉皮士风格的国际化街道,所呈现的林林总总都是新的,是年轻人享受自由、展示个性与爱好的最好去处。这里居住着“一些老去的嬉皮士和左派犹太人,一些20年代移民至此却没有发迹成为中产阶级的祖父辈”。[2]2街上有外国人开的小店,很多商店都以西方文字命名,处处都有西方文化的烙印。这里有白人,有黑人,还有来自沙漠小国的有色人种阿卜杜,有从乡村地区流入行乞的农民,还有来自刚果和塞内加尔的妓女。混杂多元的街道居民、消磨时光的年轻人以及淘金的异乡人,以及他们所隐喻的贫富悬殊、失业、色情、犯罪等社会问题,共同构成了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社会图景。作为前殖民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全球性与本土性在这里冲突与融合,多元、混杂的文化在此共存。
故事的后半部分发生在一个边远的无名小国,一个容易滋生恐怖主义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地方。按照阿卜杜的说法,他的国家是一个归属不明确、政治体制不明确的国家。但是,这并不妨碍朱莉对他的迷恋以及对他的国家的向往。如同一个异域游人对阿拉伯国家的美好遐想,朱莉想象阿卜杜的家乡有“棕榈树、骆驼,两边挂满地毯、摆满铜器皿的小街。独桅三角帆船”。[2]22她的幻想来自于她儿时看过的故事书《一千零一夜》中的插图,旖旎的伊斯兰风貌,充满异域风情。朱莉的幻想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东国家的构想,凸显了朱莉典型的消费者心态。然而,到达阿卜杜家所在的村庄后,朱莉没有看到自己想象的美好画面,而是年久失修的破旧房屋和随意丢弃的动物尸体。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广告牌和街道上飘荡着的西化的音乐昭示着经济全球化对这个边缘小国的影响。不难想象朱莉承受着怎样的心理落差。在市集日,满地随意摆放的廉价商品成为朱莉眼中“精彩的拼凑艺术”。[2]107家境优渥的朱莉是以游人的心态看待自己的所见,局外人的身份使她无法体会这个沙漠小国穷人生活的艰辛。
杨欣欣、杜明业认为,“文学作品中地理空间的建构问题绝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描述和反应意义上的地点,它对情节结构的设置和人物性格复杂性内涵及悲剧命运的展示都具有推进和渲染的作用”。[4]从繁华都市来到这个破落的小村,外部地理空间与想象地理空间的巨大落差带给朱莉极大的心理冲击。对陌生环境的猎奇感消失后,朱莉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当朱莉看到街上出售的破旧衣服、太阳镜和大哥大时,她开始质疑“为什么我们只把这样的狗屎卖到这里来?”[2]108她把这一切都归咎到自己身上,是“我们”把这些破旧的东西当作商品,倾销到这个贫穷的国家。作为优势主体的白人代表的是优势经济文化霸权。她认为,是以她为代表的白人的作为导致了这里的贫穷与落后。
作者把地理空间叙述从一个发达的现代国际都会区转移到了一个落后贫穷的中东小村庄,巨大的地理空间反差突出了白人所代表的欧洲殖民者所谓的优越性与文明性,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弱小国家的影响。朱莉在努力摆脱帝国文化与经济投射给她的身份的同时,也在努力反思这个沙漠小国在全球化中所受的冲击,以及作为优势主体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成为她向心之旅的开端。
2.咖啡馆:矛盾心境的象征
L.A.咖啡馆极具嬉皮士风格,是朱莉和她的朋友们日常聚集的地方。L.A.是Los Angeles的缩写。但是打这条街走过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名称的真实含义。店老板取这个名字或许是为了让客人体会到与自己生活相称的异域风格。如果店主想表达自己咖啡店的嬉皮士主题的话,那他肯定是把洛杉矶和旧金山弄混了。因为两地有其各自不同的历史。旧金山曾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嬉皮士精神的城市,而洛杉矶则要拘谨许多。店名与咖啡店主题的混淆表现了部分南非人想要融于国际,体现时代感,却对相应的文化背景一知半解。然而,咖啡馆名称的含混不清并不妨碍它成为各种人群聚集的地方。除了年轻人,一些老去的嬉皮士、左派犹太人或者来此淘金的老移民也是这里的常客。
“圆桌帮”是作者对朱莉和她的一帮朋友们的称呼,是因为他们总是在闲暇时聚集在咖啡馆里的一个圆桌旁消磨时光。圆桌意象在故事中一再被提及。它的物质特性有着深刻寓意。首先,圆形意味着平等与对话。“圆桌帮”是一个容量无限的圈子,总有新人加入他们,也有一些人会好久不见。成员们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每一个新成员的加入和老成员的离开。这些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男女 “都是一些想与自己的过去和家人疏远的人”。[2]20“圆桌帮”们一贯谈论的话题也都与种族歧视、权力分配不公、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有关。“向邂逅者敞开——这是她和一票朋友的信念,也是他们认为生活值得继续的部分原因。”[2]7对朱莉和她的朋友们而言,向陌生人敞开自己不仅表现了自己的阶级与种族立场,也是一种肯定生活价值的尺度。然而,“敞开”也意味着没有特定的归属。人的内心是空白的,任何可能性都有可能发生。任何外在的因素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和情感走向。这成了朱莉与阿卜杜故事的一个引子。其二,圆桌意味着循环。“圆桌帮”们的谈话没有特定的说话者,而且话语与心理独白交叉进行。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加入,一起“喋喋不休”地重复着“熟悉的蠢话”。[2]55而话题的循环重复意味着,他们所诟病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与约翰内斯堡的L.A.咖啡馆相对应,在阿卜杜家所在的阿拉伯小村庄也有一处伪装成咖啡馆模样的酒吧。之所以需要伪装,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酒吧是违禁场所。时不时地还会有穿便装的保安警察坐在暗处,进行监视。一群受过教育、期望改变现实的年轻人是这里的常客。尽管不能享受如同“圆桌帮”们一样的言论自由,然而这里的年轻人并没有像“圆桌帮”一样在咖啡馆醉生梦死、嘲讽社会,而是积极商讨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方法。他们都期待自己的国家能在政治上有所改变,建议国家政府利用网络扩大影响力,从而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阿卜杜经常参加与朋友在酒吧的聚会,却又担心自己会被朋友的慷慨言论激发斗志,“让他想要加入他们,一起密谋、一起进行煽动、一起去冒险,好改变这个地方——这个沙漠”。[2]153作为一个当地少有的拥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阿卜杜同感于国家的落后与贫穷,却又极力逃避作为国民所应具有的责任与义务,把逃离这个国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大卫·哈维认为,咖啡馆既可以是公共空间,也可以是完全的私人空间。要进入这一空间,必须要经过商业与消费主义的淘选。[5]291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向心空间,L.A.咖啡馆似乎可以接纳所有人,却用自己含混的店名宣告了自己的嬉皮士主题,无声地标示了自己的排他性。要进入这个咖啡馆的人不仅要有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而且还要有对特定区域亚文化的认同。“圆桌帮”们在咖啡馆圆桌旁平等共处,惺惺相惜,却仍然找不到彼此想要的温暖。他们批判社会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改变现状。双重矛盾囊括了南非的社会全貌,讽刺了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而在阿拉伯小村庄,表里不一的酒吧与阿卜杜的矛盾心情互为映衬,成为阿卜杜内在心境的象征。
3.家屋:游离心灵的归属
“圆桌帮”的成员们在少年时代或者年轻时代都经历过种族隔离之痛,也见证过南非的历史巨变:第一次黑人当权,第一次自由选举等。他们在享受着和平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安逸生活和充分自由时,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他们把L.A.咖啡馆当作自己的“家”,选择把“一群玩游戏的人”[2]141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互相安慰,一起在这样一个极具嬉皮士精神的咖啡馆里消磨时间、嘲讽社会。但是在朋友那里,朱莉也没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家的温暖。如Emma Hunt所言,“在全球化的城市里,尽管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人产生交集,人与他人之间却失去了一种联系感”。[6]“在家”,却又“无家可归”,这成为身处大都市的年轻人们的普遍感受。
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诗学》里把住宅称为“家屋”。他认为,“如果没有家屋,人就如同失根浮萍。家屋为人抵御天上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是人类存在的最初世界”。[7]31家屋因此有了两层含义,包括有形的物理空间和无形的心理空间。物理空间的疏远和心理空间的隔膜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圆桌帮”们的“无家可归”。朱莉的父母早已离婚并再婚。父亲在“市郊区”的别墅里有遮阴的露天平台,有各种用途的厅室。家里装饰着花卉、高级家具与油画,有权贵聚集的高雅社交活动以及各式美酒和美食。原本可以衣食无忧的朱莉却“决绝”地搬离了这个衣食无忧的家。带着阿卜杜再次造访父亲的豪宅时,朱莉仍然会“陷入一种熟悉的沮丧心情中”。[2]35“她打量过一个个房间,没有一个是她的;墙壁上没有她少女时代的明星海报,床上也没有父亲从机场给她买回来的长毛绒大熊猫。她现在所游荡、停顿与聆听自己心声的地方,已不是从前的房子。”[2]39父亲的豪宅里没有真正属于朱莉的,承载着她生活体验的独特空间。“地域和空间的独特性是居住者文化的独特性,也是居住者本身的独特性。”[8]129-130父亲豪宅房间的单调、雷同、结构一致性根除了朱莉在这个家的独特性。整齐划一的现代化居住空间形式毁掉了人的家园感,使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错置关系。空间隔膜因此产生。
汪民安认为,“理性化的城市设计,摧毁了地方的感受,摧毁了对人的认同感,摧毁了情感原则,摧毁了人们对环境的责任”。[8]130因此,搬家变成了一件毫不犹豫的事情,居住空间可以随意更换。从父亲家搬离后,朱莉租住在一个装潢成小村屋的仆役小屋里。小屋内空间不大,家具很少,并在有意无意地证明:闲适不一定要靠奢侈家具才可以营造。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蒂姆·克勒斯威尔(Tim Cresswell)认为,“我们或许会想藉由安排布置房间的家具,让房间在实际和体验上都舒适宜人,来使我们新近购买或承租的房间,对我们产生意义”。[9]16朱莉在努力营造属于自己的,有独特意义的居住空间。但是即便如此,朱莉仍然没有对小屋投入自己的情感。屋里的家务活有专门的清洁工定时来做。随意丢弃的垃圾和凌乱摆放的生活用品说明朱莉仍然缺少对这个小屋的归属感。这个房子不算是她的家屋,仅仅只是一个供她停留歇息的居住空间。
朱莉一心要逃离自己在南非的富裕家庭,却慢慢在阿卜杜的贫困家庭里找到对家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表现方式就是她与空间的良性互动。她和阿卜杜居住在主屋旁边的单坡小偏房里。房间条件简陋,仅有一张吱呀作响的铁床和一个洗脸盆。这个局促的居住空间与朱莉父亲的别墅和她曾经租住的装修精致的仆役小屋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朱莉欣然接受了这里有限的居住条件,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此外,朱莉还努力争取在厨房帮忙的机会,并以此作为融入这个新家的契机。在文学批评领域,厨房空间一向是被解读为女性低下地位的表征空间。然而,在《邂逅者》中,厨房却成为家庭权威的象征。在这个穆斯林家庭里,父亲的角色是失语的,母亲则是家里的权威。她主导着家里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氛围。每天,母亲带领着家里的女人们在厨房为全家人烹制饭菜。朱莉想要进厨房帮忙,却遭到了母亲的拒绝。为了找到与母亲交流的突破口,获得母亲的认同,朱莉甚至花高价从国外邮购了古兰经并认真学习母亲常常诵读的经文。她的努力为她赢得进入厨房帮厨的机会。通过与厨房空间的良性互动,朱莉获得阿卜杜家人的认同,并慢慢找到对家的归属感。在这里,厨房空间成为母亲家庭主导地位的表征空间。
朱莉在逃离了父亲的豪宅,也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装潢精致的仆役小屋,却格外珍惜这个贫困简陋的新家。朱莉对舒适居所的逃离和对简陋住所的珍视并不是对物理意义上居住空间的简单抗拒和接受,而是心理意义上的疏离与皈依。朱莉在这个沙漠村庄的住所因此有了家屋的含义。巴什拉认为,大城市里的房子缺乏纵深的私密价值,也缺乏辽阔的宇宙感。“因为在这里,房子已经不再是盖在自然的环境里,空间与家屋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人工关系。跟房子有关的所有事情,都变成机械性的,因为私密的居住生活,从每个角落逃逸。”[7]54相较而言,乡村生活“被安静地束缚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人们根据这片土地确定自己的认同,确定自己的语言、风俗和起源”。[8]124对于朱莉而言,被家族权威和宗教品质所铭刻的乡村居所既是物理意义上的家屋所在,也是心理意义上的家屋空间。阿卜杜家的居所才是她的家屋所在。
二、自然地理空间与故事发展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卫斯理·科特把类似于荒野这样的人类社会空间建构中遗留的剩余空间(space left over in planning)*该译法引自颜红菲.叙事理论的新视角:评科特的《现代小说的地点与空间》[J].《外国文学研究》,2012(3): 163-166,165. 原文出自Wesley A. Kort, Place and Space in Modern Fiction (Gainesville: UP of Florida, 2004), 152.归为边界地带。他认为,各类边界地带的不断出现为构建新型的人与地点关系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它是被边沿化了的空间,介于纯粹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边界地带,是人与自然及社会双向关系的纽带,既是最富于张力的空间地带,也是最容易产生新质的空间。”[10]在这个故事中,草原为朱莉与阿卜杜的心理交流提供了场所,而沙漠则成为两人各自的向心与离心之旅的诱因。主人公与自然地理空间的互动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1.“大草原”:平等交流的场所
与阿卜杜相处时,朱莉“尽量不走在这个汽车修理工的前面,就像他是一个仆人一样”。[2]7刻意维持的表面的平等并未真正改变他们的身份差异。在他们同居的小村屋里,两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生理层面的,而非心理层面的。[11]18而到了周末,两人一起到了大草原时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在人迹稀少的草原上,朱莉和阿卜杜可以抛弃所有对两人身份差异的顾虑,阿卜杜也抛弃了宗教戒律,“双重身份消失”。[2]30“他们会散步,卧看浮云飞鸟,交换所见所感,并像普通的情侣一样,对彼此所见所感的巨大落差感到差异和有趣。”[2]29两人平等交流,相互分享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享受着难得的亲密时光。在自然地理空间内,没有如L.A.咖啡馆的无形排斥,也没有“圆桌帮”的无声排挤,朱莉和阿卜杜开始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在心理上相互靠近。正如Dana所言,“草原给两个爱人一个抛弃城市差异的机会,也暗示着新的平等的可能性”。[12]
在草原上,朱莉与阿卜杜心理的距离拉近了,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两人身份的差异。他们会在草原上阅读。朱莉会带着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书,这些作家都是阿卜杜在大学课堂上没有听过的。阿卜杜会读报纸,“而且会抱着批判的精神琢磨报纸上报道的事实”。[2]30相较而言,阿卜杜的阅读更加务实,朱莉的阅读纯粹是消遣或者文学欣赏。两人生活境遇的巨大差异导致阅读内容的迥异。朱莉在草原上体会到了她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寂静之声”,[2]29然而附近高速公路上传来的隐隐的车声无形中否定了朱莉的判断。在阿卜杜看来,“只有沙漠才是真正的寂静”。[2]29实际上,朱莉眼中的“大草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草原,而是她对绿草地与山上的概称。这不仅意味着以朱莉为代表的南非年轻人与自然的疏离,也意味着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人类很难真正享有纯粹的自然地理空间。
2.沙漠:认知系统重构的诱因
龙迪勇认为,“空间是我们行动和意识的定位之所”,[12]它“必须被人感知和使用,被人意识到,才能成为活的空间,才能进入意义和情感的领域”。[13]在阿卜杜看来,家乡的沙漠代表着绝望,是他一心想要逃离的无用空间。但是,对朱莉而言,沙漠帮助她找到自己的定位,是充满希望的阈限空间。
朱莉经常一个人在清晨和黄昏之际散步到沙漠。坐在一处废墟上凝视沙漠,享受沙漠带给她的宁静。在一个阈限时间去往一个阈限空间,不确定的时空带给朱莉前所未有的平静。全新的自然地理空间带给朱莉巨大的心里冲击,“通过这一冲击,主体内在空间被完全颠覆,然后按照外部空间法则与逻辑进行重构”。[5]286她欣然接受了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努力融入这个新家,慢慢获得家人的认同和接受。在南非时,她逃避与父亲的联系,企图用朋友代替家人,最终也没能获得她想要的亲情与归属感。但在与阿卜杜家人的相处中,她慢慢体会到,“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一种很重要的东西,不,应该说不可少的东西”。[2]160朱莉找到了久违的亲情和对家的归属感。“不仅如此,朱莉还通过教授英语,参加妇女聚会等方式加强和当地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她用自己对这个村庄生态环境的认同和主动的人文交流行动表达了她对这个沙漠村庄的认知和亲近感”,[11]20是地理空间认同和精神皈依的合二为一。
文学地理学认为,人与其生活的地理空间是一种相互投射、相互渗透的关系。朱莉与沙漠的关系不是单一的接受与给予的关系。在享受着沙漠带给她改变的同时,她也在努力回馈自己置身其中的自然地理空间。与一位在沙漠中放羊的贝都因女孩的偶遇让朱莉心中萌发了建设绿色家园的梦想。和阿卜杜父亲一起对一个远房亲戚的拜访更加坚定了朱莉要实现自己梦想的决心。“看到这个沙漠中央生长着稻谷时,就表示这里是可以孕育出生命来的,表示它可以提供一种超越于一切意义之外的存在。”[2]182朱莉要利用父亲为她设立的信托基金在沙漠里种植水稻。她希望能向阿卜杜证明,“没有天国,没有涅槃。这地方是我们唯一能拥有的。”[2]182既然世界上没有理想的天国,人不可能在涅槃后迎来渴望的美好生活,那就积极面对这个地方唯一拥有的沙漠。改造它,利用它,从而让“生活变得有用,变得有意思”。[2]183因此,在这里,朱莉“观察到自己正慢慢形塑为另一个自我”。[2]167自然地理空间帮助朱莉重构了自我的认知系统,她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与最终确立凸显了人与地理空间的良性互动。
三、理想的符号空间与主题提升
杨欣欣、杜明业认为,“地理空间还往往是作为一种精神建构而存在,是关于地理空间建构与生活表征意义的观念形态”。[4]143戈迪默在《邂逅者》中不仅建构了人文地理空间和自然地理空间,以塑造人物形象和推进故事的发展,而且还通过对阿卜杜幻想中的理想空间的描述,揭示阿卜杜的精神失衡,以提升故事主题。
阿卜杜拥有大学学位,他可以利用自己所学为国家发展做贡献。此外,他从小就跟随舅舅学会了修理汽车,他也可以在叔叔的修理厂工作,靠着自己的双手过上富裕的生活,并且极有可能继承这个厂的经营。然而,他的理想是移民到一个富裕的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去过很多国家,用过很多假名。他在伦敦的餐馆里洗过盘子,在德国的啤酒馆里清扫过呕吐物,直到在南非的修车厂里当“油猢狲”并遇上了朱莉。阿卜杜本以为拥有了朱莉,“靠着她的关系、她的背景,就可以在她的国家获得他所一直无法获得的东西”。[2]117然而,梦想再次落空,阿卜杜不得不再次回到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国家,他用回了自己真实的名字:易普拉欣。然而,称谓的恢复并没有带给他自我意识的回归,他依然一遍遍地尝试申请移民他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美好富庶的大国一次次成为阿卜杜的移民目的地,作为符号的价值被阿卜杜不断提及,并被阿卜杜建构成一个“遍地都是可能性”[2]181的地理空间。去哪一个国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离开本身。阿卜杜对富庶国家的简单构想只是拼凑了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他并不清楚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
阿卜杜在梦想着移民他国的同时,也梦想着成为某个金融公司的高管,有着和朱莉父亲一样的豪宅和奢华生活。他梦想中的工作空间是在一栋摩天大楼里,如同朱莉曾经的办公室一样,有开阔视野的大窗户、定做的椅子、组合式办公桌、电脑、通讯器材和每个月更换的亚热带盆栽。他拒绝用自己所学为国家做贡献,也拒绝用自己的汗水来换取富足的生活,反而幻想着在摩登的办公室里指点金融。阿卜杜对理想空间的构想是基于他有限的空间体验。由于缺乏对其他空间的感知,他无法对自己的空间激起反思。因此,他所看到的自己的家乡就只有沙漠和贫穷。阿卜杜强烈的理想空间梦与朱莉的绿色家园梦形成巨大反差。在阿卜杜逃离故土,不切实际地追求理想空间的同时,朱莉在为改善当地的地理空间而努力。朱莉的坚持反衬了阿卜杜的理想空间注定只是符号式的存在,他一心要逃离的沙漠小国却是真实的存在。
阿卜杜在朱莉继父的帮助下获得移民美国的许可,前往美国。大嫂赫蒂安慰朱莉说,“他一定会回来的”。[2]227这句话不仅仅是安慰。人们通常会对自己的故乡产生强烈的寄托性情感,“失去了同它的经验性联系,就如同丢失了自己的身体一样”,“一旦被迫远离这个空间,人们的家园感和故土意识就反复被激发,返归的愿望就会喷涌而出。空间世代的居住,演变成了家族意识,家乡意识,历史意识和根深蒂固的记忆”。[8]127缺乏与本土文明相互联系的空间感,阿卜杜在异国他乡永远都只能是个夹缝人,遭受帝国文化的排斥,找不到家的归属感。对故土的眷恋最终会牵引着阿卜杜回到原点。他的移民行为注定是西西弗斯式的徒劳。
在《邂逅者》中,戈迪默将社会背景、人物内心思想、多元文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都融入了地理空间叙事。人文地理空间的建构帮助作者塑造了人物形象,自然地理空间建构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理想符号空间的建构提升了作品主题。然而,所有空间的建构都是没有特定的国名或者地名。这种非特定的地理空间位置隐含着一种共性,它引导读者去思考这种非特定的地理空间的代表意义。这些人文地理空间与自然地理空间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地理空间,主人公在头脑中建构的理想符号空间也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所共有的美好幻想。三重地理空间层层递进,相互交叉,由外及内,共同构建了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的地理空间,昭示了全球化时代人的精神困境。
参考文献:
[1]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J].世界文学评论,2009(1):41-46.
[2]纳丁·戈迪默.邂逅者[M].梁永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
[3]Nadine Gordimer. The Pickup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4]杨欣欣,杜明业.论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建构[J]. 社会科学家,2011(6):140-143.
[5]刘进,李长生.空间转向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6]Emma Hunt. Post-Apartheid Johannesburg and Global Mobility in Nadine Gordimer’s The Pickup and Phaswane Mpe’s Welcome to Our Hillbrow [J].Ariel,2006,37(4):103-121.
[7]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M].龚卓军,王静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7.
[8]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9]蒂姆·克勒斯威尔.地方:记忆、想象和认同[M].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16.
[10]颜红菲.叙事理论的新视角:评科特的《现代小说的地点与空间》[J].外国文学研究,2012(3):163-166.
[11]胡忠青. 论戈迪默小说《邂逅者》中的生态美学意识[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 39 (03):17-22.
[12]Dana C. Mount. “Playing at Home: An Ecocritical Reading of Nadine Gordimer’s The Pickup” [J].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2014,45(3):101-122.
[13]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