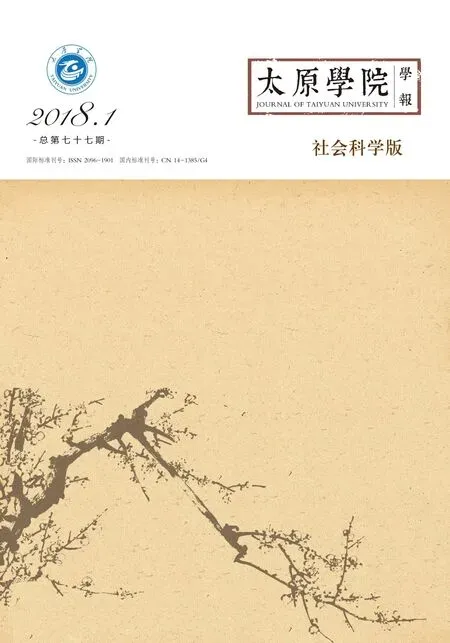《别让我走》中的反乌托邦设定
——克隆人的傀儡命运探析
2018-01-23吕曰文
吕 曰 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当代久负盛名的英国日裔作家、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以其细腻妥帖的写作手法、充满淡淡哀愁却又发人深省的人性探讨独成一家,作品一经面世就广受评论界的好评,石黑一雄本人也于2008年被时代周刊评为“1945年后英国最伟大的50位作家”之一。2005年,石黑一雄在新兴科技克隆技术的启发下写成出版的反乌托邦式科幻小说《别让我走》,透过克隆人凯茜·H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生命还未来得及绽放就已凋零的克隆人,他们在人类的控制和玩弄下度过了短暂、无助而又悲凉的一生。小说自出版以来就有众多学者对克隆人的不反抗、不斗争、自愿接受人类为其安排的人生轨迹的生活态度提出质疑,认为这有违常理。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如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理论[1]、后现代主体性的拉康式解读[2]、福柯的“监狱制度”理论[3]等。本文将从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统治”(强制)与“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这两个霸权形式切入,探讨人类如何通过强制统治和思想入侵使克隆人逐步丧失逃离和反抗的意识,从而将克隆人培养成惟命是从的傀儡,同时就小说的反乌托邦式故事设定进行分析,一探深藏在噩梦般故事情节下作者的真正意图:唤醒科技高速发展下,现代社会中的人内在的爱、道德和尊重,以及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审视,极力避免类似克隆人悲剧和反乌托邦式社会的产生。
一、政治社会的强制性统治
葛兰西从社会集团角度将上层建筑分为两个主要的层面,其中一个是“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或“国家”(state),即国家和政府政治活动领域。[4]国家是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通过“司法的”政府来行使权力,对其他集团进行“直接统治”。[5]70
1.强制性隔离
在小说《别让我走》中,随着克隆人的成长,作为统治阶级的人类将克隆人划分到不同的隔离区域管理,各年龄阶段所在区域的监管和隔离强度也有所不同。小说叙述者凯茜·H及其伙伴露丝、汤米的整个童年是在英格兰乡下的黑尔舍姆度过的,一般情况下,克隆人在黑尔舍姆所居住的时间较之日后待的任何住所都更为长久。与此同时,这里隔离强度最大,几乎与人类世界隔离,“黑尔舍姆位于一个四周都是高地的平整山谷中。”[6]31黑尔舍姆建在人迹罕至的乡下且地处高地的凹陷位置,如果不走近根本无法发现这里还存在着一栋住着克隆人的校舍,因此对鲜有与外界接触的克隆人而言,远远开过的一辆小汽车“有时就足以在上课时引起骚动”[6]31。强制性隔离是为了便于驯化和控制克隆人,克隆人是人类社会的科技产物,是实验室里、试管里创造出来的,是作为治疗疾病的“更科学、更有效”的途径——活体器官储存器而存在的,然而当克隆人与人类无异的外表使人类感到不安和恐惧,并开始思考克隆人是如何养育、是否应该创造出来的时候,却已经太迟了。随着克隆人的器官被不断地移植到人类身体中,人类早已认为癌症是可以治愈的,“怎能要求这样一个世界去放弃那种治疗的方法,要求它回到那黑暗的时代?没有回头路了。无论人们对克隆人的存在感到如何地不安,他们压倒一切的考虑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配偶、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朋友,能够不因为癌症、运动神经元疾病、心脏疾病而丧命。”[6]241因此,克隆人从小就被隔离隐匿起来,一方面为了掩饰人类无情、残忍的掠夺事实,避免人类因为看到他们而感到恐惧和厌恶,于是,除了每日出现在黑尔舍姆里的教员、好多天来一次的园丁、工人和每年为画廊挑选作品而只来两三次的玛丽·克劳德夫人外,便没有任何其他人类出现在黑尔舍姆了;另一方面,隔离能够更好地让克隆人在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的条件下,一心接受人类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意识,理所当然、心甘情愿地去捐献器官,为人类奉献年轻而健康的生命。为避免克隆人跑出隔离区域,统治阶级将分割人类世界和克隆人世界的林子恶意扭曲成充满阴森、恐怖故事的场所——“一个男孩和他的朋友大吵了一架,从黑尔舍姆跑了出去。他的尸体两天后在林子深处被发现绑在一棵树上,手脚都被砍掉了”[6]46;一个女孩因爬过栅栏去看外面的世界而不被监护人允许回来,她死后的灵魂一直在树林间游荡,渴望着再次回到黑尔舍姆。统治阶级通过舆论和谣言的方式强制克隆人老老实实地待在隔离区域内,从而获取大多数克隆人都自愿同意待在固定区域的假象。
经过黑尔舍姆整个童年的隔离式洗脑教育,克隆人会被分配到村舍、威尔士山区的白楼或者多塞特郡的白杨农场中的一处去,那里“不会再有监护人,所以必须互相照顾”[6]107,克隆人可以出去溜达,“只要能够在天黑前回来,并且在凯弗兹的花名册上登录回来的时间”[6]108,在这一阶段,克隆人的隔离不再那么严格,他们只需要学会互相照顾,为后期在康复中心照顾捐献器官的克隆人做准备。克隆人从被创造出来到他们生命的终结,人类社会为保持现有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有意识地将他们强制性地培育和隔离在正常人的生活外,真正意识到自己接触的是克隆人的正常人大体都是和克隆人有必要接触的工作人员,他们因工作性质的缘故也不会对社会安定造成影响。
2.强制性基因介入
作为统治阶级的人类为了更好地监管克隆人,避免他们因私自产下后代而造成无法掌控的后果,人类在创造克隆人的时候通过强制手段让他们的基因里存在一丝缺陷——无法生育。克隆人的存在已经在人类社会颇有争议了,一旦克隆人像人类一样能够生儿育女,有家庭伦理的关系和亲人之间的牵绊,又如何能继续为人类的利益而从容地接受既定的悲惨命运呢?人类又如何才能继续把他们看成科技创造出来的产品?尤其是当科学家詹姆斯·莫宁戴尔发现存在可以创造出有着“优异的智力,优异的体质,诸如此类”的“高素质孩子的可能性”[6]242。而万一这样子被创造出来的优秀的“人”取代了人类在当今的社会地位,又如何处置呢?这远远偏离了人类最初将克隆人当作活体器官储存器的预期目标。如若克隆人在人类不知道的地方产下后代,其无异于正常人的相貌和日后所接受的教育带来的影响将完全脱离人类的掌控。因此,人类进行强制性基因介入,将克隆人设置成为一次性产品,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有着代码和记录,生命的每一次重大经历都在统治阶级的引导和规划下完成。
统治阶级通过政治社会的强制性手段——隔离克隆人和破坏克隆人生育能力的基因,不仅保护和维持了其稳固的霸权统治,而且设法赢得被它统治的克隆人的积极实践,更是为市民社会中的文化渗透铺平道路。
二、市民社会的文化渗透
葛兰西划分的上层阶级另一个方面则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即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在葛兰西看来,“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是霸权的又一表现形式,即“在市民社会领域发生的,国家通过非暴力机器的意识形态使被统治阶级心甘情愿地接受控制和支配”[7],也就是狭义上的文化霸权。葛兰西十分重视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在阶级统治中的作用,他指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国家的暴力和强制职能依旧存在,但是,更多地通过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领导权’(hegemony)来行使”[5]74。小说《别让我走》中,统治阶级除了运用政治社会的地理隔离和基因介入等强制镇压手段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市民社会里掺杂欺骗的文化灌输来驯服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克隆人接受人类所传输的道德、政治、文化价值,使之潜意识里认可并支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而逐步丧失思考和选择的自主性,使命运完全脱离自己的掌控,最终成为人类肆意攫取的对象。
1.掺杂欺骗的文化灌输
在克隆人的幼年时期,黑尔舍姆的教员反复告知克隆人:“作为黑尔舍姆的学生,我们全都很特别。”[6]39“我们”享受了其他克隆人所没有的特权和机会,“我们”可以像正常人的孩子一样,接受艺术熏陶——学习绘画、素描、陶艺;朗读剧本、散文、诗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特权”在拍卖会上体现:桌上摆放的物件都是人类儿童所丢弃的破烂玩意儿。然而克隆人却把它们当作宝贝,一个个地精心挑选。一方面,克隆人接受的是和人类儿童相似的教育,学习的都是人类的高雅艺术;另一方面,小箱子里的收藏品却是人类弃之一旁的玩具,教员们精心挑选这些课程和玩具的粗鄙目的昭然若揭:时时刻刻宣扬人类的优越和先进,凸显克隆人的低下与卑微——就连用上人类即将进入垃圾桶里的玩具对克隆人而言都是一份“特权”和“殊荣”,从而通过非暴力的手段达到影响并塑造克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目的。极其成功的,在寻找露丝原型的过程中,同伴们都不相信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内工作的女人是露丝的原型。露丝也恼怒道:“我们都知道这点。我们是从社会渣滓复制出来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也许还有罪犯,只要他们不是精神病人就行。他们就是我们的原型。我们都知道这事”“如果你想在合适的地方找,那么你就到阴沟里去看看。你就到垃圾桶里去看看。低低头看看厕所吧,你在那里就能找到我们来的地方。”[6]152统治阶级通过使用压抑、欺骗克隆人的一系列观念和意识形态来维持自己的领导权,衬托自己高大先进的形象,使克隆人这样的下层阶级在不断的影响下服从于他们的统治,达到“为人类奉献生命”的最终目的。
在黑尔舍姆,被人类教员和克隆人提及最多的是“创造性”,“创造”得多棒不仅是评价一个克隆人是否优秀的标准,也是克隆人在同伴之间能否受到尊重的标准。有“创造性”的克隆人像帕特里夏·C,她画的月历牌生动精致,“你能从中辨认出某些学生和监护人的脸来”[6]84;克里斯蒂写得一手好诗而名噪一时,大家对她充满钦佩和敬畏。然而,被愚弄的克隆人并不知道这只是转移注意力的烟雾弹罢了,所谓的“创造性”只不过是人类检查克隆人是否有灵魂的工具而已。
但捐献器官作为克隆人被创作出来的根本目的却从未被黑尔舍姆的教员们仔仔细细、透透彻彻地讲清楚过。汤米也曾发现:“在我们待在黑尔舍姆的所有岁月里,监护人很可能不论告诉我们什么,都十分小心儿刻意地选择时机,以便我们总是因为太小而不能恰当地理解刚刚告诉我们的信息,可是我们当然会在某个层次上接收这个信息,这样用不了多久,这玩意儿就会全部进入我们的脑袋,而又不会恰如其分地去检验它”[6]75人类教员们总是会在谈论别的事情的时候插入捐献器官的话题,却又从不讲明为什么要去捐献、如何捐献,克隆人“被告知却没有真正被告知”[6]75。教员们利用这种模糊印象来让我们在六七岁的时候就“知晓”这些概念,“当我们长大了,监护人对我们说那些事的时候,没有一件事会让我们感觉完全意外,惊讶不已。那就像我们之前就已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所有的一切了”[6]75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逐步使克隆人认可人类所传达的文化价值和思想内涵,让统治阶级的霸权变成一种“常识”和“共识”。因而克隆人在似懂非懂之间,认为捐献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捐献的时刻到来时,你就在自己身上裂开一点儿,一个腰子什么的就会溜出来,你就可以把它给人了”[6]79。事实上,当克隆人真正经历过捐献才发现捐献并不是一件“裂开口,器官就会自己溜出来”的好玩事,而是“伴着痛苦和麻醉药、精疲力竭的不眠之夜”[6]5,甚至许多克隆人只完成了第二次捐献就完结了,露丝愤怒道:“我敢说这种事比他们告诉我们的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在我们的捐献间歇时间里把我们转来转去。”[6]206然而,就算克隆人现在发现了事实的真相,真真切切明白“被告知的事”到底是什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完了人类为克隆人预设的道路,离生命的终结也不远了。
在大多数处于麻痹状态的克隆人眼里,“黑尔舍姆,我敢肯定那是一个漂亮的地方”[6]5即使是做完第三次捐献,“躺在那儿输液,全身就像被鱼钩钩住了一样”[6]5的克隆人,一听到凯西讲述黑尔舍姆的点点滴滴时,几乎不能呼吸的脸上都会绽放出笑容。由此可见,黑尔舍姆不仅留下了凯西、露丝、汤米他们这些从小在此成长的克隆人短暂生命里最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是所有克隆人心目中最向往、最神圣的地方。这说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实践和扩散成功地将被统治阶级驯服,使其接受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离开这里的学生,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多少真相”[6]99。
2.克隆人反抗的不可能性
针对统治阶级对人民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欺骗,葛兰西提出了革命的新策略——阵地战,其首要任务就是夺回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被统治阶级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重建一种新的“整体文化”。在这场文化革命中,不仅仅要消灭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使被统治阶级文化实现真正的主体文化,从而使被统治阶级获得全面的自由。[8]《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群体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自小就长期接受人类的思想意识,视捐献器官为自己“应该做的事”[6]207。即使露西小姐告诉他们真相:他们生命的一切都是虚幻和骗局,捐献器官只是他们被创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克隆人们也只当“她是一时丧失了理智”或是“因为我们在走廊上太吵而训斥我们”[6]74,“讨论她所说的话确是惊人的少。如果这事被提及,人们就会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已经知道一切了。’”[6]74克隆人的态度表明他们在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中已经接受了人类的思想灌输,完全服从人类的意志要求,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无可厚非的,根本没有闹革命的诉求。另一方面,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然而克隆人的生命短暂,最长也无法超过中年,且捐献期间的频繁转院,使得即便有克隆人觉醒了,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支撑他宣扬自己的思想给其他克隆人,其他克隆人只会将他当作第二个“疯了的露西老师”罢了。在人类的洗脑统治下,克隆人既不具备奋起反抗的群体自发性,也没有充分的时间让有觉悟的领导者去传播思想意识,反抗斗争的不可能是必然的结果。
三、反乌托邦的设定及反思
1.反乌托邦的社会设定
《别让我走》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末的英格兰——一个与当前社会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平行时空,这里没有癌症是无法治愈的,人类死于疾病的概率大大降低,寿命也大幅度地延长。表面上看,人类社会日益进步,科学技术愈加发达,然而在这所谓“进步与文明”的背后却埋藏着人类令人震惊和发指的血腥勾当:将实验室培育出来的克隆人当作一具具盛放各种器官的活体容器。无论是地理上的隔离、监禁还是文化上的欺瞒、渗透,全部都是为了能在他们盛年时无所阻碍地一次次拿走他们的主要脏器,用鲜活的生命偷取人类自己在这世上多苟活片刻的机会,人类就是参与策划并谋杀克隆人的刽子手。石黑一雄笔下的科幻社会将人类自私、冷漠、残忍、暴力的丑恶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在这个克隆人生活的平行世界里,人类没有给予他们丝毫发自内心的关心、尊重,更没有爱,他们从小到大、由始至终都生活在欺骗和谎言,悲伤和绝望之中。
相较于乌托邦小说中所构建的完美社会,《别让我走》这种类型的反乌托邦小说则是将这种完美社会给读者带来的美梦和憧憬活生生地打碎,将读者置身于噩梦般的人间地狱之中。有学者这样定义反乌托邦:“反乌托邦(又称反面乌托邦、恶托邦)是对存在于另一个时空的、比现实社会更糟糕的国度或地方的描述。通常包括以现在推断未来,将现实社会的弊端推向极致,含有警示意义。”[9]是以,反乌托邦小说虽然故事背景遥远陌生,但是故事的内核依旧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社会紧密相连,高瞻远瞩地对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灾难进行理性推测。正如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言:“从本质上来说,反乌托邦总是一部关于‘不久的将来’的小说,它讲述一个关于迫在眉睫的灾难故事——生态问题、人口膨胀问题……核事故问题等诸多问题都一一等待来到我们自己的不远的未来社会。只是这一灾难提前进入到了小说时间而已”[10]虽然反乌托邦小说中含有科幻元素,但“它从作者所生活的现实出发,通过将现实生活中某一(些)社会问题放大,即通过对这些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虚构性表征,来达到现实批判和现实影响”[11]。
因此,作者将小说设定在一个反乌托邦社会中,不仅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和对精神世界的反思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忧虑和关切,更多的是通过给予读者心灵上的震撼与冲击,引发读者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批判:使读者联想到在现实社会中发生同样悲剧的潜在可能性,从而认清自身在社会里所处的位置,知晓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故而提高警觉,避免悲剧上演。
2.反乌托邦设定的现实意义
获诺奖后,石黑一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阐述他笔下人与人、人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同时生活在大小两个世界中。我们在个体世界里,努力地去实现自我,去寻找爱;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更大的世界交融在一起,而那个世界是一个被政治主宰的反乌托邦世界。所以我总是关注同时存在的大小两个世界,我们不能顾此失彼。”而乌托邦小说正好是一个作为阐释这种人性异化堕落,世界似是进步、实则落后的关系再合适不过的载体,因而作者立足当下,将对当前社会的不满、批判和反思,以及对更好的社会架构的理解置于地狱般的另一时空之中。
《别让我走》就是这一典型。随着1996年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在克隆技术和基因工程带人类走入一个新的科技时代的同时,石黑一雄对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与关切,作者并不是反对科学,也不是反对发达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而是反对科学的进步以人性的泯灭和沦丧为代价。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对他人的尊重和关爱,那么人类与其他生物又有何区别?只不过是一具具行走的躯壳罢了。因此,这些技术能否被人类正当、合理地使用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正如沃尔什所言:重要的不是“理性和富足的社会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问题,而是人类是否能够利用自己的理性和非凡的能力来创造并维护这样一种社会”[12]人类如何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中保持自己与人为善、与世界为善的本心,不被利益蒙蔽双眼,真正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是一个值得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深思的问题。
四、结束语
《别让我走》中的统治阶级将强制和同意以平衡形式相配合,形成“武力和同意,统治和领导权,暴力和文明”[13]双重权力结构,有效地控制了克隆人这一被统治阶级,通过对克隆人的压抑性文化渗透,阻碍了克隆人自我意识的萌发,使之一直处于麻痹和惟命是从的状态。由于克隆人的生物特殊性,他们无法控制自身的基因组成,因此自被创造出来后,就注定要受到心理、意识结构的禁锢,压抑和欺骗人的意识形态系统必将伴随一个又一个的克隆人像提线傀儡般走上预定的轨道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作者通过刻画这样一个反乌托邦社会,表达了对现代社会中科技异化人性的担忧与反思,为人类社会敲响警钟——避免社会在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中以人性沦丧为代价,从而指引人们最终到达充满爱与希望的彼岸。
参考文献:
[1]方幸福.被过滤的克隆人——《千万别丢下我》人物性格及命运解析[J].外国文学研究,2014(2):104-111.
[2]沈安妮.对石墨一雄《别让我走》中后现代主体性的拉康式解读[D].重庆:四川外国语学院,2012.
[3]李里,王晶.无处可逃的人生——评《别让我走》[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7-80.
[4]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杂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7-198.
[5]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石黑一雄.别让我走[M].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7]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7.
[8]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杂记[M].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16-317.
[9]刘宁.当代科幻小说研究与多丽丝·莱辛[J].文学理论前沿,2014(2):156-173.
[10]Jameson, Fredrick. The Seeds of Tim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56.
[11]王建香.反乌托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7.
[12]Walsh, Chad. From Utopia to Nightmare[M]. London: Geoffrey BLES Ltd., 1962: 16.
[13]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