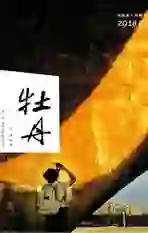后院的草
2018-01-22松小川
松小川
后院长满了草。去年开始我渐渐疏懒了那块空地的种植,原本推窗便可见的一垄一垄整齐可爱的蔬菜瓜果,现在是一片无序的杂草野花。有时走到那儿,会有一种被遗弃的沉默感,不过这里的沉默仍然平静、缓和,没有海洋般的深渺,也没有沙漠般的荒凉。前院人来人往,小跑车也嘀嘀嘀摁着喇叭宣告自己的存在和功用,因而我常常走着走着又转过身去:生活在召唤我,街市就在不远处。
一片野草。一种柔软而令人忧伤的无用激情,如同某种低语在某一块背阴处窸窣、摇晃。野草能成就什么呢?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它们所能述说的不过是生命自身的隐秘激情和被遗弃吧?我随时可以借用镰刀、锄头驱逐它们,然而还是放过了。或许从它们身上,我认出了自己,认出了自己的语言。在没有什么能够被真正种植的地方,任由风将草芥吹偏方向,任由词句散落荒凉僻静处,也没什么不好吧?
的确,安放在红袖添香中的三百多篇文字一夜之间蒸发这事让我难过了一阵。不过想想也不必哀伤,红袖需要向自己的消费者委身奉献,允诺点什么慰藉,比如萌妻出没、总裁与美女这些故事。而我的取景器里没有它们,把文字存放在那儿本来就错位了。一位多年爱护着我的朋友也终是隔膜了,他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那样拿枪的战斗姿势,也许是必要而且是对的,我却因此紧张而难受。这也是我的过错,我只愿听到走过草坡散步的声息。
我默默地将某些想法套在自己身上,再由自己将之轻轻甩掉。空荡荡的苏醒之后,天空依旧是蓝的。
起风了,寻常的,司空见惯的风。随着沙沙声的节奏起伏,忧郁密集的草叶在建筑背阴处发出簌簌声,缺乏与外界交流的能力。
刚刚有访客来看望我。我的一位姊妹,教会钢琴师。我想起自己有好久没去教堂了,我对上帝的疏懒让我的姊妹深切担忧。她认为我需要被教导被救赎。“感谢神!光,一个词,具有强大的威力。”她衷心希望能将我从这片潮湿草地连根拔出,引渡到上帝之光照中。我的姊妹对上帝的描述過于复杂,但依然孜孜不倦地尽努力讲述着她自己也模模糊糊的上帝之音。
我点点头。想起了一个生性羸弱、紧张而敏感的男人,一位痴迷光的画家。他几乎是带着甜蜜的爱的执着去描绘皮肤和皮肤表面流动的光辉。他说,要相信皮肤的光辉,皮肤就是女神,皮肤就是伊甸园。所以他画作中人体的皮肤里面没有住着真正的人。
神让艺术家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给他们光,一定还给了他们阅读混沌,阅读黑纸的能力。
画家知道一道裂痕便可能揭露开启风景之下的内核。天堂的手卷被上帝收起,从此生命的第一个迹象是血,基督流血并背负起十字架走去。这是一个命运中经常感受到威胁的男人的恐惧,他以绘画天才成就自己的信仰:为了更好的活下去,他必须在表面、布料和皮肤中开启激情之光。雷阿诺。
阳光下,钢琴师与我一样瘦弱得像根草。然而她是上帝的草,她笑着说着,面色红润,仿佛基督金色的话语给她抹了魔力香油膏。我想自己还是一根背阴处的野草,但我敬爱她,如同敬爱那位画家的皮肤之光。我也相信,只要钢琴师的手指滑过琴键,天堂的手卷便会重新打开。
夏天在生长,雨后的后院中充满着泥土和草木生长的气息,这些声息伴随着一只只蝴蝶的飘动在空气中回荡。
我在后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我的手臂和双腿似乎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触须与茎蔓,陷落其中。荒草在风中触摸我长长的发辫,野藤悄声抚摸我裙衫的破损处,我们望着彼此,仿佛有个回忆存在我们之间。我的心掉进了泥土里,那些曾被我用镰刀驱逐出去的与时间纠缠在一起的歌谣、梦境正在归来,它们要求收复失地一般打开了我身体的门。
我想要拥抱它们的散乱与柔软。
同一时,在我生活的地方,某家餐厅的老板娘开着采购小货车回来了,一条小狗摇着尾巴正穿过巷子向它的伙伴走去,夏令营的孩子们在露天帐篷里唱着营歌,有人在微信里转发一个暴力视频,画面里有体面人士借着正义的名义在揪打一个年轻姑娘,那姑娘屈着膝盖,叫嚷着,她那样叫嚷着,显然相信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懂得她所遭的罪吧?电视新闻中记者则拿着话筒向世界报道人间无私的爱:一名警察正在洪水中救助困在民宅中的老奶奶,他背起了老人……而我的邻人昨日猝死湖畔,此刻,常青园里山野菊的黄色与哀恸一般响亮。
生活的语词,生命的语词。大地与天空的对话。天真与复杂,温暖与痛苦、明晰与暧昧……一切都那么脆弱,短暂,却永远不能穷尽。
我渐渐能够平静地写下点什么了。在黯淡的光照中,以落下的方式,脸朝上。如同后院的草籽以自己的生长聆听上帝微小造万物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