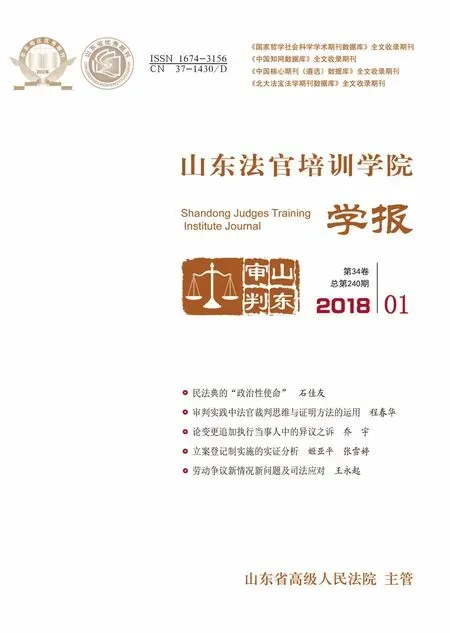刑事审判中被告人翻供的司法应对
——基于裁判者角度的思考
2018-01-22王金凤
王 海 王金凤 杨 琳
翻供是刑事审判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a魏中礼:《关于翻供问题的几点思考》,载《山东审判》2010年第3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既有据实翻供、又有不实翻供,而且从司法实务的角度以及实践经验判断,不实翻供、真假混杂的翻供通常占绝大多数。在司法实务中,经侦查审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在意志最薄弱的时刻心理防线被突破,从而全盘交待。而在后来的阶段,随着侦查审讯的压力逐渐减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趋利避害、最后一搏的心理逐渐加强,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翻供。尤其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当庭翻供现象更为突出。由于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庭前供述的真实性也可能大于当庭陈述。b龙宗智:《试论与当庭供证相矛盾的庭前供证的使用》,载《法学》2000年第1期。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翻供,已经成为侦查、起诉乃至审判阶段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维护程序正义的司法理念,避免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一)裁判者面临的现实窘境:惩罚犯罪与保障无辜的二难选择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传统中,往往将被告人的翻供与“不老实”、“不认罪”划等号。在当今的司法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通常都认为翻供具有双重属性,既有较强的抗辩性,又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在具体办案中,法官面对被告人翻供仍持两种不同的心理和态度。一方面,害怕自己所承办的案件中被告人出现翻供,这往往会给办案带来麻烦,增加查明事实的难度,甚至会令有罪的被告人逃脱法律的追究,而致放纵犯罪;另一方面,又担心被告人的翻供是有道理的,害怕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没有审查出真实的翻供,甚至会令无罪的被告人受到法律追究,而致冤枉无辜。相比之下,或是基于大多数被告人翻供均属无理翻供,抑或是基于办案压力和司法的惯性,法官在采纳被告人的翻供理由上更加偏向前者,其结果是大多翻供案件被法官驳回。在裁判文书中,通常表述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作出了多份一致的有罪供述,该供述取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与全案证据相印证,应予采信;而被告人的当庭辩解或翻供理由缺乏相关证据印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纳。然而,做法上的偏向并不一定代表其内心的真实想法。通过访谈发现,在心理上,与放纵犯罪相比,法官实际更担心后者,特别是在证据本身就比较薄弱的案件中,被告人翻供更是令法官犯难。这不仅是因为冤枉无辜要受到错案终身追究或是法律的制裁,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官内心深处要受到良心的不断谴责。这种实际做法和真实想法的不一致,充分折射出了法官对待被告人翻供的矛盾心理,使其内心倍受煎熬,不得不在惩罚犯罪和保障无辜之间做出二难选择。
(二)裁判者的应然态度:犯罪控制价值向正当程序价值的适度倾斜
1.以积极理性的心态正确认识和看待翻供
正所谓,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翻供的作用也不例外,需要正确看待。翻供固然增加了办案难度和法官的工作量,但从近几年所曝光的佘祥林、赵作海、滕兴善、呼格吉勒图等冤错案来看,正是由于被告人的翻供而暴露了案件的矛盾和证据的疑点,倘若法官能正确认识、因势利导,反而有利于及早发现问题避免冤枉无辜。在有的案件中,由于被告人对法律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盲目翻供并采取不正确的辩护策略,反而有利于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增强其内心确信。如张某强奸案,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与未成年人李某同在一都市会所上班。某日晚,张某邀约李某等人到外面饮酒,直至凌晨李某才扶张某回到会所,二人临时挤在客人的洗脚房内休息,张某趁机强行与李某发生了性关系。张某在侦查阶段前二次笔录中对发生性关系一事供认,但辩称系在李某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得知李某事后洗过澡、未提取到张某的精斑等实物证据时,张某开始翻供称只是借着酒劲对李某进行了抚摸和亲吻,并没有发生性关系。审理发现,李某陈述当晚将张某扶进房间后,张某就对其身体进行了抚摸,期间她接到一个同事的电话,但也没有向同事呼救。直至后来,张某剥去了她的衣裤,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后,她才哭着跑出房间,告诉了同事。由于担心名声被毁,李某没有报案,而是要和张某私了。因要求赔偿3万元没有谈妥,张某反而以受到敲诈勒索为由报案。公安介入之后,发现本案实际是一场因强奸案引发的纠纷,遂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认真分析,本案中由于张某的翻供,反而减少了认定案件的难度。倘若张某一直辩称双方系出于自愿,由于二人是同事关系,深夜共同进入一个房间,李某也称对其抚摸时没有反抗而是在接电话,认定张某强奸的难度反而较大,只能依赖二人没有谈恋爱、李某系未成年人、哭着跑出房间、处女膜破裂以及要求赔偿等间接证据来认定。但张某却选择了一个最笨的翻供伎俩,使案件得以顺利地认定。
2.维护程序正义,体现“天平倒向弱者”和“平等武装”的理念
从诉讼构造角度来看,法官处于等腰诉讼三角结构的顶端,面对被告人翻供时,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居中裁决本是其应有之义。然而,我国刑事诉讼的结构,从横向看,属于控辩裁“三方组合”的三角结构,从纵向看是公检法前后记起的线性关系。c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110页。这种相对复杂的双重结构,加之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特殊关系,导致在司法实务中,法官与公诉人的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在面对被告人翻供时,有时甚至过分偏袒控方,而失去了客观中立的立场。
如郝某受贿案,郝某庭审翻供称,其于5月9日被通知到侦查机关接受讯问直至11日才被刑事拘留,其是在人身遭受非法限制的情况下作出的有罪供述,属非法言词证据,应当排除。辩护人当庭提供了郝某的妻子、弟弟证言,证实郝某于5月9日下午电话告知妻子、弟弟前往侦查机关接受调查,后无法联系;证人兰某证实其于5月9日下午在侦查机关接受询问时,从声音判断郝某可能也在侦查机关;郝某的电话清单显示5月9日下午16时许接到了侦查机关的办公室电话。可见,关于郝某何时到案问题,辩方证据已经比较充足。但法官仅依据公诉人提供的郝某签名时间为5月10日的询问通知书、两名侦查员出庭证明郝某于5月10日凌晨到案接受调查,继而认定郝某到案时间为5月10凌晨,在无法说明5月9日下午16时许至10日凌晨郝某出于何种状态的的情况下,就作出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侦查机关对郝某采取了非法拘禁等违法取证行为的司法评价。如此偏向控方的认定,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法谚有云:“如果原告就是法官,那只有上帝才能充当辩护人。”d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倘若法官偏向控方,无异于将裁判职能与追诉职能混为一谈,被告人将陷入辩解无处、申冤无门的绝望境地,辩护权则根本无从谈起。我们知道,刑事诉讼的历史,是被告人的辩护权不断发展、不断扩张的历史。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程度,也是判断一个国家司法文明与进步的晴雨表和试金石。在刑事诉讼中,柔弱的个人权利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始终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庭审实质化的大背景下,法官不应再向过去那样简单地将自身定位于流水线上的一环,而是将整个诉讼程序看作为一个障碍赛,维护“天平倒向弱者”和“平等武装”的程序正义理念,e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从犯罪控制价值向正当程序价值适度倾斜,f[美]赫伯特·L.帕克:《刑事诉讼的两种模式》,载《争鸣与思辨——刑事诉讼模式模式经典论文选译》,虞平、郭志媛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并在与检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之间实现平衡。可见,法官在面对被告人翻供时,不仅要正确认识、理性看待,更要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居中裁决,惟此才是对待被告人翻供的应有态度。
二、认真倾听被告人的翻供理由,对翻供是否合理作出经验判断
(一)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做到兼听则明
认真倾听,是对人最好的尊重。在刑事案件中,胜诉固然是任何被告人都想要追求的结果,但能够得到一个倾诉的机会、发泄心中的不满同样重要。早在古代,我国就有“两造俱备、师听五辞”之说。在古代埃及,为了强调给那些身陷囹圄者以公正听审的重要性,更是流传着这样一则古老的诗歌:“如果你是一位领导者,请耐心听取申诉者所想;如果他要吐露心中委屈,请不要加以阻挡。可怜的人期待胜诉,更渴望向你倾诉衷肠。申诉一旦受阻,人们便会追问:‘为何他会冷若冰霜?’不是所有申诉都会成功,但好的听审能抚平心里的哀伤。”gJerry L.Mashaw,Administrative Due Process:The Quest for a Dignitary Theory,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 61,1981. 转引自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为了更好地应对翻供,做一名理性的倾听者,在案件受理后,法官要利用开庭10日前送达起诉书、开庭3日前送达传票,以及与公诉人、辩护人交流意见的机会,对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指控的事实有无异议等情况进行摸底,并对被告人是否翻供作出一般性的判断。在正式开庭前,要审查供述内容,了解供述的矛盾和疑点等。当被告人的供述存在反复或者在关键情节存在矛盾时,还要有针对性地拟定庭审讯问提纲,把存在矛盾和反复之处作为庭审的重点,避免在庭审中无法快速找到焦点或者对控辩双方争辩不知所云。
(二)运用“交叉询问”和“五听之法”,对翻供是否合理作出经验判断
在庭审阶段,两造俱备,法官居中裁判。面对控辩双方关于翻供是否有理的争讼,法官要居于客观中立、居中裁判的位置和立场认真倾听。倾听时,可以运用“五听之法”,对被告人翻供的言谈、举止、表情、心态、陈述的口气等进行观察,从直觉上对被告人翻供是否有理作出经验判断。为了便于倾听、查清翻供理由是否成立,法官还要充分发挥法庭讯问、举证、质证功能,运用交叉询问规则来帮助查明案件事实。h如英国学者迈克·麦考韦利认为“对质和争斗是发现事实真相的最好方法”。参见卞建林:《刑事证明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如美国著名证据法学家Wigmore所说,“交叉询问无疑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发现事实真相的最伟大的法律引擎’”。iJohn Henry Wigmore,A Treatise on the System of 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New York:West Pub.Co.,1904,p.1697.因此,法官可以充分引导控辩双方就翻供是否有理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不同意见,在控辩双方激烈的争辩中,发现被告人的前后口供存在的矛盾和疑点,并在全面掌握案件的基本事实上,对每一份供述进行认真的审查,最终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必要的情况下,法官还可以依职权对被告人就有关的问题进行发问,以此来打消其心中的疑虑。
(三)分析被告人的翻供心理,实事求是、因势利导
翻供不仅是证据战,也是心理战。认真倾听,不仅有助于疏导被告人的情绪,还可以深入分析被告人的翻供心理,因势利导。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被告人的翻供心理有很多,有的出于纠正原来虚假的有罪供述,为澄清事实而翻供鸣冤;有的纯粹是出于狡辩,为逃避法律的制裁而翻供抵赖;有的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对部分事实或关键细节翻供,意图浑水摸鱼、蒙混过关;还有的是因为受到侦查机关刑讯逼供或不公正的对待而翻供泄愤。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有弄清被告人的所思所想,分析其翻供的原因和心理,才能找准病灶、对症下药。
如胡某受贿案,检察机关指控胡某利用担任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166万元。庭审中,胡某对收到166万元的事实认可,但翻供称收钱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单位不太方便的为公支出,有18万元上交了镇财政,有148万元用于抗震救灾和支付给上访户,没有将这些钱据为己有,其选择的是一种非直接拒收和非直接上交的“礼金收交”方式,是一种拒贿保廉的主观动机,没有受贿的主观故意。胡某翻供时情绪激动,并以清朝清官于成龙“违令开仓放粮”的典故做比喻,辩称自己虽然违纪,但不构成犯罪。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胡某受贿166万元,另查明胡某以个人名义向镇财政中心上交18万元、为处理该镇拆迁移民问题向长期进京上访的村民们支付57万元,合计75万元;同时认定该75万元系胡某的个人行为,与公务行为无关,不应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胡某不服提出上诉,扬言得不到公正对待将终生上访。
经认真分析,胡某之所以翻供,其认为组织在调查期间向其撒了谎,称像他这种收到贿赂以后最终用于为公支出的人,可以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但其发现,组织不但将其移送司法,而且在起诉后甚至都没有考虑其为公支出这一情况,他要向世人证明,他与一般的贪贿官员不一样,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行为。二审中,检察员抓住了其自尊心较强、急于“正名”的心理,实事求是地从认定其为公支出符合案件客观事实,符合经验判断和常情常理,符合基层乡镇实际以及证据采信规则等方面发表出庭意见,认为一审判决割裂了受贿所得与赃款去向之间的关系,该75万元应作为受贿后的为公支出,在量刑时酌情考虑。检察员发表完出庭意见后,胡某一改愤怒状情绪当庭含泪表示认罪服判,并对司法机关表示感谢。最终,二审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量刑由有期徒刑五年半改为四年半。本案被告人之所以在一审阶段翻供、情绪激动上诉,并表示判决生效后将作为上访户长期坚持上访,却在二审阶段含泪认罪服判,主要是司法人员弄清了其翻供心理,采取“疏”而非“堵”的办法,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排除以刑讯等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防止可能的错误裁判
(一)启动非法口供排除程序
在被告人翻供的案件中,以受到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为由而翻供的,占有相当比例。作为法官,就需要对被告人是否受到了刑讯逼供进行审查判断,以及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
1.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启动和证明
一是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启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庭审时,审判人员认为被告人的口供可能系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要对收集该口供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同时,被告人以遭到刑讯逼供为由当庭翻供并请求法院排除该非法口供的,法院要让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二是非法获取口供的证明。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在庭审时,检察机关应当承担口供收集过程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在决定对获取口供是否合法进行调查时,可要求公诉人提供情况说明、出入看守所体检报告等证明口供取证过程合法的证据。在必要时,还可以采取当庭播放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要求讯问的侦查人员到庭说明情况等形式,对口供取证过程的合法性进行证明。
如张某受贿案,检察机关指控张某利用担任国有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贿赂人民币283万元、欧元3万元。在庭审中,张某对收受283万元事实认罪,但辩称没有收到肖某所送3万欧元,讯问笔录记载了张某未曾供述的内容。法官重点审查了该同步录音录像,发现讯问笔录中虽然记载张某供述其曾收到肖某3万欧元,但同步录音录像显示张某对该事实明确否认,表示在其印象中没有收到该3万欧元。由于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同步录音录像严重不一致,法院判决排除了该讯问笔录,对指控张某收受3万欧元的事实没有认定。
2.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
经审查,确认或者不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应当对该口供予以排除。法官在确认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方法获取口供时,要依赖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行判断。如果所获取的口供能够证明取证是合法的,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可以采信该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反之,如果证明该口供是通过刑讯方式取得,或者不能排除是通过刑讯方式取得的,要对该口供依法予以排除。如文某盗窃案,被告人文某当庭翻供称其遭到公安人员的刑讯逼供,且讯问笔录内容与其供述的关键内容不一致。庭审时,法官重点审查了同步录音录像,发现录音录像画面模糊、录制时间与讯问笔录的记载时间不一致。而且,文某手臂部分留有伤痕,检察机关没有提供入所体检表,公安机关虽出具没有刑讯逼供的情况说明,但综合分析仍不能排除非法取供的可能性,该有罪供述被依法排除,检察机关遂撤回起诉。又如邱某强奸案,被告人邱某与被害人陈某均为精神智力发育迟滞的残疾人员,在案证据中仅有邱某第一次有罪供述后便翻供,而该有罪供述存在较大疑点,虽然在第一次讯问笔录显示邱某承认强奸了被害人,但同步录音录像却显示,邱某是在经过公安机关“严肃”教育、反复讯问其是否有强奸行为后供认的,而且该同步录音录像还出现了录制中断、时间不能连贯等问题。公安机关尽管出具情况说明称,是录音录像设备出现故障,但依然不能排除公安机关有非法取供的嫌疑,加之案件其他客观证据亦存有瑕疵,证据链条无法形成,法院最终作出无罪判决。
(二)排除非法口供时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1.关于“重复性供述”
在排除了某一份或某几份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此之后作出的与被排除的口供内容完全相同的口供,是否也应当作为毒树之果予以排除,我国法律目前仅排除以刑讯逼供方法获取的重复性供述,对其他方法比如使被告人遭受精神痛苦或者通过非法拘禁方法获取的重复性供述并不排除。而且,即便排除通过刑讯逼供所获取的重复性供述,也设置了“侦查期间更换承办人以及逮捕、起诉和审判期间再次讯问,被告人自愿供述的”三种例外情形。对此,我们认为,对重复性供述应当重点考虑非法口供所涉及的波及效力,在无法保证被告人系自愿作出真实供述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再将该重复性供述作为证据使用。这主要是基于被告人在遭到刑讯逼供、精神痛苦或非法拘禁后,心理上会有所忌惮,害怕“不老实交代”会再次受到同样的对待。而且,从目前所曝光的冤错案来看,在司法实务中,被告人因翻供后再次受到刑讯逼供的案例亦不鲜见,这种情况下所作的供述亦难以保证其真实性。j高翼飞、高爽:《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和对翻供的审查》,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35期。
2.关于“毒树之果”
从广义上讲,重复性供述也是毒树之果的一种。除此之外,基于该非法口供而取得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亦属于毒树之果的范畴。对此如何处理,我国法律尚未有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应将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区别对待,对言词证据从严掌握,对实物证据适度从宽。在排除时,还要看侦查取证的违法程度,如果是轻微的违法则通常情况下不排除;如果是严重违法,必要时也可以排除。但无论是否排除,法院在定罪量刑时均应留有余地。
3.关于“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宽禁止、严排除”的立法模式,未明确规定对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而获取的口供应当排除。对此,我们认为,法官发现采用这些方法而获取的口供时,即便根据现有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不予排除,承认这些口供的证据能力,但也应当对该口供的证明力加以适当限制,在运用这些口供形成内心确信时,也要有所保留,毕竟这是通过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的非法方法而获取的口供。
四、根据翻供的不同情况,灵活行使庭审职权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除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外,法官还要针对被告人翻供的各种不同情况,采取灵活的处理措施。
(一)要求提供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材料,必要时通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对被告人翻供称,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所做的陈述与笔录记载的内容不一致时,法官在讯问被告人是否进行阅读、签名、捺印,以及签名、捺印的原因以外,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有关讯问程序合法的情况说明,或者要求侦查员出庭说明情况。如果有同步录音录像,也可以将该录音录像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进行比对,看关键情节是否存在记录不一致等情况。如陈某故意伤害致死案,被告人陈某一审当庭翻供称,其作出的供述与讯问笔录的记载在一些关键细节存在不一致之处,请求法官将讯问笔录与录音录像进行同步检验。然而,一审法官及公诉人对陈某的要求没有理睬,致使案件进入到二审阶段。二审检察人员在讯问陈某的过程中,陈某又提出了这一情况。二审检察员耗时2个工作日,终于发现陈某在录音录像中的陈述与讯问笔录的记载,在致命伤是否系其捅刺这一关键细节存在不一致之处。由于该细节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案件最终被发回重审。
(二)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传唤相关人员到庭对质
对被告人翻供称,同案犯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警察提供的证词等与犯罪事实不符或者存在重大矛盾时,依据在案证据难以查清的,可以根据直接言词原则,传唤相关人员到庭对质,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如吴某故意杀人案,吴某当庭翻供称,自己当时不在案发现场,而是与证人李某等人一起喝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当庭出示了证人李某等证明被告人在案发当时不在犯罪现场的证言,致使案件一度陷入僵局。经审查证人李某等人的证言,发现辩护律师在制作询问笔录时有一定的诱导性,辩护人问话的内容较长,而接受询问的人通常只是回答“是或者不是”。法官遂在二次开庭时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公诉人当庭先后询问证人李某某等人,案件发生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你还能够记清你们当时喝茶的具体时间吗?李某某等人均回答记不清楚了。公诉人又问,那你在辩护律师中制作的笔录中为什么说的如此详细呢?李某某等回答我只是向律师说在那段时间和被告人在一起喝茶,并没有明确具体时间,律师为什么那样记录其也不清楚。如此一来,辩护律师提供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在案发当时吴某不在现场的情节不攻自破,吴某不在犯罪现场的翻供理由得以查清。
(三)要求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供述笔录及相关证据材料
对被告人提出其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和起诉部门作出过翻供陈述,而在案证据没有提供的,法官可以要求公诉机关提供这些讯问笔录,以及其他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如在曹某受贿案中,曹某翻供称其曾在检察机关批捕环节、审查起诉环节对其讯问时即已作出不一致的供述,但是公诉人并没有出示这些证据,仅出示对其不利的供述而未出示对其有利的供述。公诉人当庭表示,曹某在批捕、起诉环节所作出的供述与起诉指控的事实不符,不具有真实性,依法不应采信。为查明这一事实,法官要求公诉人提供这些证据后再次开庭。经二次开庭,控辩双方对曹某在批捕、起诉环节的供述进行了举证、质证,虽然法官最终没有采信被告人的翻供理由并判决其有罪,但对塑造法官客观中立形象、疏导曹某情绪以及全面审查被告人供述依然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依法退回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必要时依职权核实
对直接证据中只有被告人供述,或者全案证据中被告人口供之间、口供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或疑点的翻供案件,以及被告人提出新事实、新证据的翻供案件,在现有证据无法查实的情况下,可以退回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在必要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核实。如张某合同诈骗案,检察机关指控张某向被害人陈某虚构其公司正在申请青海省一煤矿的采矿证,向被害人陈某提供了相关图纸等资料,并带领陈某到煤矿进行了实地考察。双方签订采矿合同后,陈某按约定支付保证金1000万元,张某收到款后随即将钱全部转给其本人及其他自然人。案发时,张某除归还陈某300万元外,尚有700万元没有归还。张某在侦查阶段的6次笔录,除第一次辩解收1000万元用于合作开发煤矿而不认罪外,其余5次对诈骗陈某的事实供认不讳,但庭审中张某翻供称煤矿真实存在,未申请到采矿证的原因是国家政策临时调整所致,700万元用于公司运营和归还前期探矿债务,不构成犯罪。张某的辩护人还提供了800余页的证据材料,其厚度堪比侦查卷宗,在证据总量上甚至形成了一对一的局面。对此,法官针对张某的翻供情况,逐一列出补查提纲,要求侦查机关详细补证。后经三次开庭、两次退查,案件的疑点得以澄清,最终对张某作出有罪判决。
(五)妥善运用庭审指挥权,依法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
庭审中,法官面对被告人翻供时容易形成两个极端。一方面,认为被告人翻供毫无道理,纯属无理狡辩,不容其供述清楚便予以制止,过于积极主动行使庭审指挥权,容易给人造成法官偏向控方的印象;另一方面,认为法官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对被告人的翻供几乎毫不打断、任其无限制地夸张表述,甚至在其过于重复的情况下,仍放任自由,几乎不用或放弃了庭审指挥权。之所以出现两种极端,实际上是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官庭审指挥权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关系。我们认为,庭审指挥权的目的在于把控整个庭审,使庭审顺畅有序进行;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目的是通过给予被告人说话的机会,认真倾听和采纳其合理辩护理由,二者从本质上说是不矛盾的。因此,面对被告人翻供时,法官应适时运用庭审指挥权,引导被告人陈述辩护理由,制止过于冗长和重复的辩解,使庭审既不流于形式,又不拖沓冗长,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五、综合分析全案证据,运用经验法则作出合理判断
(一)详细审查被告人供述的细节
在审理被告人翻供的案件中,不仅要分析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认罪、翻供的时间、地点、次数等,更要详细审查被告人每次供述的细节。对普通刑事案件,关注的细节通常包括作案的时间、地点、参与作案的人员以及每个人员具体实施了何种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结果等。对职务犯罪案件,如贪污案中,则通常包括公款套取的方式、手段、票据的金额、大小、具体的经办人员、赃款的处理等细节。一般情况下,如果被告人是真正的凶手或罪犯,那么他对这些细节交代的会比较清楚,供述的会比较自然、流畅,仅通过侦查人员的“诱供”、“逼供”则难以详细、自然地作出有罪供述。同时,在一些犯罪案件中,还可以通过审查被告人书写的亲笔供词,捕捉和分析被告人作案前后的那种恐惧、犹豫和侥幸心理,感受被告人的心理变化,以此增强法官的内心确信。
(二)结合言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
主要是将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犯之间的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进行对比,分析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对这些矛盾能否作出合理解释。如王某等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检察机关指控陕西王某电话联系四川张某称,其欲到四川购买毒品用于吸食和贩卖,并让张某帮助购买。后王某将此事告诉李某,并与李某一同驱车来川购买。当王某与李某买完毒品后,行至途中被民警抓获,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388克。庭审中,王某翻供称自己购买毒品的目的是为了吸食,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张某、李某翻供称,自己帮王某购买毒品是用于王某吸食,至于王某是否贩卖他们只是猜想,并不清楚。而公诉人却认为,三被告人均不同程度地供述了王某购买毒品的目的是贩卖和吸食,对购买毒品用于贩卖的目的是相互印证的,足以认定。经审查,王某在侦查阶段的三次笔录,第一次和第三次均供述是自己吸食,仅第二次供述购买毒品是自己吸,如果有人买就卖一点也不一定。张某在侦查阶段的三次笔录,前两次供述只是帮王伟购买,至于干什么用并不清楚;第三次供述王某想买点毒品来吃。李某在侦查阶段的三次笔录,第一次供述王某买毒品是自己拿回去吸,也卖;第二次供述是王某用于自己吸食;第三次则供称不知道王某要干什么,只是跟着王某来川办点事情。认真分析,三个被告人的供述并不稳定,认定三人贩卖毒品的证据实际上仅有不确定的言词证据证实,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故仅判决三人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
(三)将被告人的供述与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对比审查
法官要将被告人的多份供述与客观提取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进行比对,将被告人的每一份供述与现场勘查提取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详细辨明被告人供述与这些客观性证据的先后顺序,分析是“先供后证”还是“先证后供”,以及是否存在人为制造的“先供后证”等情况。一般而言,在排除非法取证的前提下,如果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提取到隐蔽性很强的实物证据,则被告人的供述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在有的案件中,公安机关在抓获被告人之前往往带着摄像机等设备,对抓获情况进行了录音录像。该录音录像会反映抓获时的一些细节,如果利用得当可以据此查出被告人翻供能否成立的一些蛛丝马迹。如文某、蔡某制造毒品案,检察机关指控文某和蔡某在蔡某家中制造麻古,文某提供制毒原料、工具并负责具体操作,蔡某提供帮助。公安机关在制毒现场将蔡某抓获,查获麻古780克。当晚,公安机关在文某家中将文某抓获。蔡某对其与文某共同制造毒品的事实供认不讳,但文某翻供称其是在受到公安机关威胁、吸食冰毒、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作出的有罪供述,内容不实、应当排除,且蔡某是在冤枉他。经查,文某在侦查阶段仅作了两次有罪供述后便翻供。第一次是被抓当日在派出所作出的;第二次虽在看守所,但系被抓次日凌晨2时许形成的,且大量复制、粘贴了第一次笔录内容。案发现场也没有提取到文某制造毒品的指纹等客观证据,证据较为单薄,被告人文某翻供一度使案件陷入被动。后经反复审查,发现卷中有抓获文某的视频光盘一张,该光盘显示文某在家被抓获时,民警当场讯问其知不知道为什么被抓时,文某断断续续地交待了因为制造“麻古”,麻古和制毒工具都藏在蔡某家中。这一重大发现,成为认定文某制造毒品罪又一关键证据,最终法院以文某、蔡某犯制造毒品罪定罪处罚。
(四)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
如前述郝某受贿案,检察机关指控郝某利用担任建设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通过低价购买房产的方式收受房产公司贿赂45万元。郝某翻供称,其供述是在人身遭受非法限制的情况下作出的,依法应予排除;其因该房地产公司对购房优惠一直未予落实,故未将剩余房款交至房产公司,郝某与房产公司之间仅存在民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而非低价购房的受贿行为。经审查,在案证据除郝某的供述外,有购房合同等证据证实郝某确实向该房产公司购买了两套商铺,合同总价80多万元,郝某仅支付了30多万元;有行贿人房产公司董事长赖某证实,按照与郝某的约定,郝某的房款已经付清,不存在欠款问题;有公司财务人员的证言及在交房资料的签署意见显示,该房“房款已清、发票已换、税费已收”;有郝某的购房客户档案也载明,郝某是一次性支付30余万元;有赖某及财务人员证实,虽然公司将郝某购房差额在财务上做挂账处理,但这是规范公司管理的一种财务处理方式,将来公司如要注销准备做呆坏账进行核销,与郝某无关,郝某也不知情;有不动产发票、房产证、国土证等书证以及赖某等人证实,在郝某仅支付30多万元房款的情况下,房产公司为其开具了票面金额为80万元的全额购房发票,并为郝某办理了产权证;自房产公司向郝某出具全额发票后,直至侦查机关调查前,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内,房产公司从未以任何方式向郝某催要过剩余房款,郝某也未向房产公司支付过剩余款项。综合分析,本案即便排除郝某的供述,在案其他证据足以认定郝某与房产公司之间已不是简单地民事纠纷,而是低价购房的受贿行为,郝某的翻供理由不能成立。
(五)审查被告人的翻供是否符合常情常理
如林某抢劫案,检察机关指控林某为抢劫敲开未成年人黄某的家门,准备采取用刀胁迫的方式实施抢劫,在黄某大声呼救的情况下,曹某为阻止黄某呼救,用刀刺向黄某咽喉、后颈等部位,致黄某两处二级轻伤,后林某逃离现场。经鉴定,林某患有抑郁症,但对本次违法行为评定为有刑事责任能力。庭审时,林某翻供称其受到了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其没有抢劫的意思,当时因琐事受到表叔责备,心情烦闷就想报复社会,刚好看见老爷爷、老奶奶出了门,就敲了被害人的家门对其进行了伤害行为。本案由于林某的翻供,到底是定故意伤害还是定入户抢劫存在分歧。综合审查本案的基本案情发现,林某的辩解不能成立。理由:其一,关于林某犯罪时的主观心态,虽然林某辩称当时并没有抢劫,只是想报复社会,但报复社会的方式有多种,既可以表现为盗窃、抢劫,也可以表现为故意伤害。因此,结合本案认定为抢劫罪并未超出林某所辩称的主观心态。其二,从林某的客观行为看,本案林某随身携带刀具,看见黄某的爷爷、奶奶下楼后,才敲开黄某的房门,随后用刀刺向黄某,造成黄某两处二级轻伤,如果其心态仅是出于故意伤害的故意来报复社会,那为什么黄某的爷爷、奶奶下楼时不去伤害,而在家里可能没有人的情况下去实施伤害?林某辩称对黄某进行故意伤害的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其三,认真分析,林某当时更多的是一种盗窃或者抢劫的主观心态,但无论哪一种,在进入被害人家中发现有未成年人黄某在家后,当场对黄某实施暴力并致其轻伤,均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其四,林某当庭翻供称在侦查阶段受到了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但从公安机关补充调取的入所健康体检表看,无法显示公安有刑讯逼供。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五次供述,除第一次供述没有交代犯罪事实外,其他四次均供述了其抢劫的犯罪事实,其当庭翻供的理由不能成立。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对林某定罪处罚。
最后,为更稳妥起见,还应将被告人的翻供情况与全案证据进行反向审查。即在正面审查被告人供述与全案证据是否存在印证后,将被告人翻供的情况与全案证据再次进行审查,分析被告人翻供或者辩解理由与全案证据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印证,或者与全案证据存在着矛盾,并审查这种印证和矛盾是否系自然形成,能否得到合理的解释。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审查印证,结合经验法则,对被告人翻供是否合理作出最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