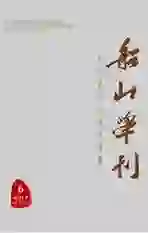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商榷
2018-01-03王夏刚
王夏刚
摘要:
夏剑钦先生在《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一文中,根据史实和相关文献对拙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第五章中谭嗣同致刘善涵十四通信函中的十一通的编年,进行了辨析订正,笔者除了认同一通信函的编年为误判,一通信函编年应更精确外,对夏先生认为编年不妥的其余信函,一一作了辨证,以夯实谭嗣同研究的文献基础。
关键词:谭嗣同;刘淞芙;书札编年
近日读到夏剑钦先生在《船山学刊》2016年第6期发表的《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一文,夏先生对拙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对“谭嗣同书札编年”一节中致刘淞芙函的编年提出不同意见。夏先生的一些见解对笔者很有启发,使笔者认识到自己在信札的编年方面,尚存在考虑不周的情况,需要加以更正。同时,对于夏先生的一些意见,尚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以下按照夏先生《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所列书札顺序,一一予以辨证。
一、被指误判为1894年所作的书札三通
此三通信函,前两封,我均断为于1895年所作,夏先生未能细查,认为我误判为1894年,然后加以辨证,不能不令人遗憾。
1.《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二,笔者转述黄彰健先生的看法,认为当写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夏先生断定为该信写于牛庄之役前的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夏先生的理由是信函中提到“昨接山海关来电,廿四、初六,宋帅连战牛庄,甚不得手”,书中所言宋帅即宋庆,并未参加牛庄之战,牛庄之战发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因此,此信系误传信息。但从牛庄战事发生时间和信末所署“十七日辰刻呵冻草叩”,夏先生推断该函写于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对此,笔者颇感困惑,既然是误传消息,就需要对此时间点存疑。退一步说,误传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人物误传,即宋庆未参加牛庄之战,谭嗣同误为“宋帅连战牛庄”,但写信时牛庄之战已经发生,那么,该信札的编年,似应以牛庄之战发生后的“二月十七日”为断,而不是牛庄之战发生前的“一月十七日”。一种是地名或事件误传,如宋庆军队确实与日军有交锋,且“甚不得手”,但并非“连战牛庄”,或者此函中所说的“连战牛庄”,并非发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的牛庄之战。
为解决以上疑惑,我们查看了当时的谕旨,发现在光绪二十年在牛庄一带,中、日之间已经发生了战事。如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丁酉,“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宋庆,李鸿章电奏,叠据善联、袁世凯营口局各电,宋庆二十四日接仗不利,退守牛庄,其本日战状,及宋得胜受伤情形,尚未据宋庆电报,殊深焦灼,现在贼氛正恶,宋庆兵力不敌,惟有联合前敌各部,及章高元等,坚守牛庄,兼顾营口,严杜西窜之路,是为至要。”①该谕旨中所称善联、袁世凯电奏“宋庆二十四日接仗不利”,当为十一月廿四日,与谭嗣同信中称廿四“甚不得手”是基本符合的,但从所引电文来看,是退守牛庄。次日谕旨表明宋庆是连日在海城与日军接战,而且牛庄一度失守。“宋庆电奏均悉,连日海城接战,伤亡甚众。宋庆率队回扎田庄台,并据袁世凯报,牛庄已失,览奏殊深愤懑。”②牛庄之战发生后,谕旨中的词汇就由“接仗不利”,变为“湘军溃退”。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壬子,“电寄宋庆等电均悉,贼扑牛庄,湘军溃退,现在营口已危,尤须紧防西窜锦州”③。
由上述资料,可初步推断,谭嗣同信中所言,并非指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发生的牛庄之战,而是指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发生在海城、牛庄一带的战争。
我们还可以在谭嗣同的其他信函中,寻找到一些线索。《上欧阳瓣姜师书》中叙述战事与《致刘淞芙》十二之二一一对应。《致刘淞芙》十二之二称:“昨接山海关来电,廿四、初六,宋帅连战牛庄,甚不得手。然则前廿五、六之捷,容有虚饰乎。”此信所提的疑问,在《上欧阳瓣姜书》可得到解答。谭在此信中称“宋帅连战甚不得手”的消息,来自魏光焘密电,并称以前所得的所谓捷报,来自黄佩豹,黄佩豹的消息则来自胡凤柱。“佩豹前说宋、蒋连战大胜者,据胡提督凤柱④之电,后接魏午庄密电,则云宋军连战甚不得手。”谭嗣同感慨当时消息歧异,“同时同地,歧异若此”⑤。
综上所述,谭嗣同信中所言“廿四”,当为十一月廿四,紧接“廿四”的“初六”,似应为十二月初六,所言多为近事,信中说“昨接山海关來电”,消息即为十一月廿四、十二月初六的战事不利,依照情理,信末所署“十七日”,似以十二月十七日为宜。因此,我还是赞成黄彰健先生将此信写作时间断为“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看法。
2.《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四,该信末署“廿三夜”,夏先生将此信与《上欧阳中鹄》之七联合考察,认为《上欧阳中鹄》之七末署“乙未除夕”,及其附言“致刘淞芙信乞交之”,确定此书作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不同意我将该书系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看法。
由于信函中信息简略,在断定年份时存在困难,采用其他信函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比对,厘清线索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这种比对,有时也会出现危险,因为要确定转交信函的唯一性,存在不少困难。而各种线索表明,乙未除夕谭嗣同托欧阳中鹄转交给刘善涵的信,并不是《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四这一封。
从写信地点来看,《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四表明,其时谭嗣同与刘善涵均在武昌,可以随时见面,信中约好第二天下午七点钟会面。“马医士言:明日下午七点钟可与罗教士会面。届时可先到马处。”此处所说马医士,当为马尚德,他曾经为谭继洵之妾魏氏治过病。谭嗣同与刘善涵计划和罗见面,据邝兆江考证,“想是要罗就开矿的问题向他们提供意见”⑥。
而从《上欧阳中鹄》之七来看,称“途中连上数书”,并报告已经到达湖北,家中安好。信中提及开办赈灾捐款事,以及采购杂粮和钱荒等事,并称“闻十九日湘雪三四寸,鄂亦同之”,可知,当时欧阳中鹄在湖南浏阳,谭嗣同在湖北。
从二信的内容和谭、刘、欧阳所在的地方来看,谭嗣同不可能在乙未除夕,将二十三日写就的拟定与刘善涵次日在武昌见面的信函,交给在浏阳的欧阳中鹄转交。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似乎不合情理。至于谭嗣同致欧阳信中所言“致刘淞芙信,乞交之”的信函,可能为写给刘善涵的另一封信。乙未除夕谭嗣同给在浏阳的欧阳中鹄写信,并托其转交给刘善涵信函一封,二信均于丙申年正月寄送,因此谭在《致刘淞芙》十二之十一中说:“月初由瓣姜师转致一笺,计达。”⑦endprint
如果《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四并非《上欧阳中鹄》之七所称转致的信函,我们就不能根据《上欧阳中鹄》之七的写作时间,来确定《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四的写作时间。
从内容看,信中提到“晏壬卿先生路费,应于何时致送”,并建议在次年正月俟其到县时补送。⑧因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谭嗣同等人设立算学社,聘晏壬卿为师,因此此信当写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以后。信中商议“回县度岁”事,并言及“晏壬卿先生路费”事,揆之情理,八九月份议论此二事,均嫌太早,似应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间。信中又提到次日见面事,则此信当写于谭嗣同、刘善涵同在湖北时。
从光绪二十一年谭嗣同的行踪来看,十一月十八日,他在浏阳写信给欧阳中鹄,称“章程草草拟就,暂秘不敢示人,故无与商议者”⑨。十一月二十日,他又在浏阳写信给欧阳中鹄说:“昨闻绅士请官出示晓谕,乡间遇有痞徒借荒劫掠者,格杀勿论。”十二月初三日,他在浏阳写信给欧阳中鹄,称:“顷又接家信,王方伯奏嗣同出洋”。十二月十七日,谭嗣同写信给欧阳中鹄,称“十五上船,十七开行。……俟到鄂详察情形办理。”⑩十二月廿三日到湖北。可以推定,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七日,谭嗣同均在湖南。
十一月廿三日,谭嗣同在湖南,不可能写此信。十二月廿三日,谭嗣同在湖北,可能会写此信,但从《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十一来看,光绪二十二年正月,谭嗣同收到刘善涵去年腊月二十四日所写信函。B11如果《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四写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廿三日,次日即腊月二十四日,他们约好下午七点见面,完全可以当面谈事,不必写信,即使写信,也会立即收到,不会延搁到次年正月二十前后才收到。可能的情况是:刘善涵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已归浏阳,并在腊月二十四日写信给在湖北的谭嗣同,谭于次年正月二十前后收到此信。
因此,我还是认为该信写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廿三日。
3.《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五,夏先生引用邓潭洲先生的遗墨,认为写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我仍然认为此信作于光绪二十年,不过需对此说予以修正,即该函应是光绪二十年乡试前所作,而非为乡试后所作。因为细绎该信,应为备考所作。一方面,多次应试落第,使谭嗣同对八股文的程式和文风,感觉无所适从,因此决定“不读一文,不立一义,我行我法”,但还是希望能够在科举道路上能够有所突破,“成功则天,转觉超然,无所绁绊”。同时推测当年的乡试,会更加离奇,“闱中之光怪陆离,殆有十倍于去年者”B12。一方面,又准备试作。“拟出各题,切实光大,亦有旧曾作过者,缓即把笔从事,并呈正之。”因为光绪十九、二十年连续两年乡试,所以才会有去年(光绪十九年)的“败鳞残甲”送给刘善涵指正的行为。光绪二十年,谭嗣同乡试落第后,编《仲叔四书义》,在自叙中宣告:“嗣同行与新学长辞,不复能俯首下心奉之”B13。不再从事时文写作的态度十分决绝,怎么可能在光绪二十年鄉试落第后,在与刘善涵的通信中,称“科举之文,古今所苦,事会如斯,未得而废,承不弃菲薄,与之商量,以此益思自奋”,还要就刘善涵所拟各题,“缓即把笔从事”B14!
二、被指考证更当精确者三通
1.《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八,我推断为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夏先生根据《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所载史事,推断为四月,我同意夏先生的判断。
夏先生根据该函中有“武冈贼平,而湘乡复有事”,指出分别指两事,即光绪二十年三四月平定的邵阳武冈、湘乡会党首领彭十五聚党众千余人起事和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湘乡县哥老会首领朱老八(名达聪)等立大营于武冈山门祭旗起事二事,因此此书应作于朱老八起事之后,即光绪二十一年阴历四月。
2.《致刘淞芙》十二之九,我认为写于光绪二十一年,夏先生认为这“显然是缺乏相关考证的错误”。
由于该信未署日期,夏先生由信中“昨有书答绂丞兄,兼致阁下”,联想到谭嗣同写于九月二十日的《报唐才常书》,认为此信写于后一日,即九月二十一日。但细绎两信,似乎没有关联。
首先从地点上来判断,“昨有书答绂丞兄,兼致阁下,计已见之”,昨天写信,今天估计已经见到,只有同在一地,方有此种可能,因此可以推断,谭嗣同写《致刘淞芙》十二之九时,谭嗣同、刘善涵、唐才常三人同在一地。谭嗣同在信中又说:“回湘别图,急切何能”,可知三人均不在湖南,可能都在湖北。而从《报唐才常书》的内容来看,谭在湖北,刘善涵、唐才常在浏阳,因为谭嗣同在信中说:“亦拟还县一游,日期急不能定,大要归则甚速耳。彼时当畅衍,此书其先声也。淞芙处亦欲作一详信,不识写得及否,乞以此书示之。”B15从地点上来判断,前一天在湖北写的信,第二天就断定身在浏阳的刘善涵已经过目,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讲通。
其次,从信的内容来看。刘善涵曾经给谭嗣同写信,欲归浏阳,谭嗣同回信劝导。从谭嗣同劝解的话语来看,当是战局紧张,刘欲归浏阳避乱,与甲午战争吃紧有关。欲归之意,可包括归湖南避乱和归隐不问世事两种想法。谭嗣同说“此时南洋安然无恙,毋乃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时夜,太早计矣”B16;“待到兵临城下,徐徐他去,未为晚也”,都与战事吃紧有关,似与刘善涵与唐才常在浏阳矿务官办、私办问题上的争执无关。谭嗣同分析刘善涵要离开湖北的三个原因,如侍奉双亲、提高收入、避乱,并一一予以否决。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归隐和用世的区别,认为对刘善涵而言,“不取科举,即为大隐”B17。《报唐才常书》分析了浏阳矿务官办、私办的争论,指出他们之间产生意见,“真儿戏耳”,认为“两君见识皆有未到,而淞芙又差一重”。从信中所言,欲隐退的是唐才常,而非刘淞芙,“足下不求与淞芙详剖天下之事理而进及于教务,妄欲引嫌退避,见识于此,亦差一著也”B18。
综上所述,我仍然认为《致刘淞芙》十二之九写于甲午战争吃紧的光绪二十一年。
3.《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十二,该信未署日期,相关信息甚少,我根据《上张孝达督部笺》,将其断为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夏先生认为是误判。这点我是同意的,该信当作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endprint
《上张孝达督部笺》中有“顷于十七,径达金陵”B19,信息过于单薄,需要与其他材料配合,夏先生根据刘善涵的《蛰云雷斋诗存》中的《谭复生太守丈乘楚材兵轮,由湖北之官金陵,余与黄颖初随行,至九江,舟胶累日,迄不得行,太守以诗见示,勉酬二律,借以自广,时十二月十四日也》证明此事,并指出了该《诗存》所录诗句的错失,“十月十日”当为“腊月十日”之误。刘善涵所提到的谭嗣同的诗作,当为《由武昌而建业诗》,诗前小序曰:“偕刘君淞芙、黄君颖初由武昌而建业焉,乘楚材兵轮,侧庐山而狂注,瞻望未罢,俄而胶三日,为作是诗。”B20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廿五日《上欧阳中鹄》十三,有“去腊在鄂曾上一笺,以事迟延至初十日始克启行,沿途兵船浅搁,至十七日到金陵”B21。出发的时间及到达的时间,均有佐证。因此,该信写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当为迎请刘善涵“本日登舟”之函。
三、余论
在谭嗣同研究中,如何对存世文献进行解读,是奥妙无穷的学问,需要熟悉谭嗣同所生存的时代,谭嗣同的师友交往,谭嗣同的人生经历,和谭嗣同的思想变迁。在阅读信函过程中,抽茧剥丝,发隐探微,是一件痛苦而快乐的事情。发现一个问题,或者确定一封信函的准确日期,是快乐的,但是稍不留神,也会造成一些失误,令人纠结。在信函日期的确定上,内证是关键,信函所述内容,是我们对信函编年的基础。在辨析信函编年的过程中,本文多次使用了这一方法。
由于资料短缺,遗存信笺不全,我们有时也会采取外证的方法,如用有明确日期标志的相关信函,推测信函的写作日期。对此,夏先生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如由《上欧阳中鹄》十三中所述离开湖南和到达金陵的日期,以及刘善涵的诗词,推断该信写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纠正了我的错误,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在使用外证的过程中,必须以内证为基础。如《致刘淞芙》十二通之四,该信末署“廿三夜”,夏先生将此信与《上欧阳中鹄》之七联合考察,认为《上欧阳中鹄》之七末署“乙未除夕”,及其附言“致劉淞芙信乞交之”,确定此书作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但仔细分析两封信的内容,发现二信了无关联。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九,夏先生由信中“昨有书答绂丞兄,兼致阁下”,联想到谭嗣同写于九月二十日的《报唐才常书》,认为此信写于后一日,即九月二十一日。但细绎两信,似乎亦无关联,因为无论从写信及收信人所处的地点,还是两封信内容的相关度来看,都是此信非彼信。谭嗣同师友间,经常转交信函,只是有些转交信件保存了下来,有些则已经不存。我们只有以内证为前提,仔细辨析信函之间的关系,方能避免发生在编年上的误判。
【 注 释 】
注释:
①②③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第56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6、608、710页。
④据《清实录》第56册,第607页,应为“吴凤柱”,吴为湖北提督。
⑤⑦⑧⑨⑩
B13B14B15B16B17B18B19B20B21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第3次印刷,第14—15、488、481、451、452—453、17、482、251、485、485、251、287、283、470页。
⑥邝兆江:《马尚德——谭嗣同熟识的英国传教医士》,《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B11谭嗣同在信中说:“月初由瓣姜师转致一函”,“昨奉去腊廿四日惠书,祇领一切”,并谈到赴俄赞使事及此事已作罢论,当写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谭嗣同《致邹岳生》一函中说:“致刘淞芙秀才信一件,纸包一个,务乞妥交。”所托转交的信件,当为此信,因此可推测此信当正月二十前后。(《谭嗣同全集》,第490页)
B12“殆”为推测语气,应是对当年即将参加乡试情况的预测。谭嗣同在去年(光绪十九年)参加了乡试,感觉“光怪陆离”,推测今年(光绪二十年)乡试的“光怪陆离”会愈演愈烈。如果谭嗣同已经参加了光绪二十年的乡试,对当年闱中的“光怪陆离”已经有真切体会,在表达上,一般不会采用推测的语气。
(编校:夏剑钦黄渊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