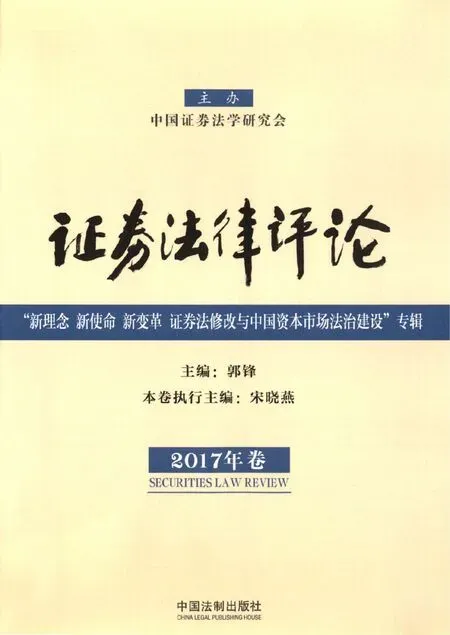对执法实践中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认定方法的反思与修正
2017-12-14张保生朱媛媛
张保生 朱媛媛
对执法实践中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认定方法的反思与修正
张保生*朱媛媛**
当前,对于最为常见的利好型内幕交易,在我国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均采取“实际所得法”计算违法所得。该计算方法使内幕信息公开且被市场消化后的盈利仍被认定为违法所得,并且未剔除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因素对个股价格的影响,将与违法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收益也认定为违法所得,既违反违法所得因果关系的基本法理,也有违行政处罚法的“过罚相当”原则与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本文认为,在认定内幕交易违法所得时,应当将卖出股票盈利的认定限制在合理时间内,并将系统风险因素和非系统风险的其他因素导致的盈利予以剔除。
内幕交易 违法所得 基准日 系统风险 非系统风险
引言
近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下称“告知书”),拟对张某涉嫌内幕交易“华闻传媒”股票进行行政处罚,认定:案涉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2年9月26日至11月29日,张某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华闻传媒”约740万股;2013年2月25日,“华闻传媒”股票复牌;截至2014年10月27日,张某将上述约740万股全部卖出,合计获利4200万余元。据此认定张某内幕交易违法所得为4200万余元,拟予以没收并处以三倍罚款。
证监会在该案中遵循了与以往同类案例一致的处理原则,即以实际买卖股票的差额认定违法所得。
本案中,张某全部卖出“华闻传媒”股票的时间距复牌日已长达二十个月,在此期间,“华闻传媒”不仅发布了一系列净利润大幅上涨的重大利好公告,并且公告启动了另一项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此外,这一期间大盘上涨34.77%,达到“华闻传媒”个股上涨幅度的53.13%。“华闻传媒”和深证综指在此期间的股价波动对比如下图所示:

显然,张某在复牌日后二十个月才卖出全部股票的收益,并非均建立于内幕信息优势地位之上,也并非均系内幕信息公开后对股价的影响所致。在行政处罚中,违法所得是指从事违法行为而直接获得的收益以及基于该收益而产生的孳息。〔1〕参见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二版,第295页。而本案证监会采用“实际所得法”认定的“违法所得”,由于期间过长和其他与内幕信息无关联因素对股价的影响,很难将“实际所得”与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存在畸重之嫌。
本文将以我国内幕交易最为常见的利好型内幕信息下的行为模式为研究对象,对违法所得“实际所得法”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和反思,并基于证券市场基本原理和认定违法所得的因果关系理论,对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提出修正性建议。
一、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实际所得法”在我国的实践
关于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计算原则和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证监会于2007年发布的《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第22条规定:“违法所得的计算,应以内幕交易行为终止日、内幕信息公开日、行政调查终结日或其他适当时点为基准日期。”
第23条规定:“违法所得数额的计算,可参考下列公式或专家委员会建议的其他公式:
“违法所得(获得的收益)=基准日持有证券市值+累计卖出金额+累计派现金额-累计买入金额-配股金额-交易费用;
“违法所得(规避的损失)=累计卖出金额-卖出证券在基准日的虚拟市值-交易费用。前款所称交易费用,是指已向国家交纳的税费、向证券公司交付的交易佣金、登记过户费、及交易中其他合理的手续费等。”
但是,遗憾的是,证监会在行政处罚决定中从未引用过该规定作为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计算依据,而且该规定的效力也一直广受社会质疑。〔1〕参见汤欣、高海涛:“我国内幕交易案件违法所得的算定及判罚——兼论域外法律实践及其启示”,载《证券法律评论》(2015年卷)。
根据内幕信息的性质,大体可以将内幕交易分为利好型内幕交易和利空型内幕交易。利空型内幕交易的行为模式是指在利空信息公开前卖出原持有证券以规避损失的情形。利好型内幕交易的行为模式,根据交易时点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在利好信息公开前买入,公开后全部卖出;二是在利好信息公开前买入,公开后部分卖出;三是在利好信息公开前买入,公开后继续持有。实践中,在利好信息公开前买入、公开后全部卖出的案件最为常见,占2011年至2016年期间全部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例的74.26%和全部刑事判例的55.23%。〔2〕参见张宠:“论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认定”,北京交通大学2016届硕士论文,第16页。
根据对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案例的分析,对于在利好信息公开前买入、公开后全部卖出的内幕交易,证监会和人民法院均采用简单的实际卖出金额减去买入成本及交易费用的方法计算违法所得(下称“实际所得法”),而不确定计算违法所得的基准日,而且对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以及上市公司自身的其他非系统风险因素对所得的影响,也均不予剔除。可见,对于上述行为模式下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认定,证监会和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已经形成统一的适用规则。相关审判人员认为,“这种方法便于计算,也为大多数学者及司法机关普遍接受”〔1〕参见赵靓(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内幕交易案件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解析”,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9月14日第6版。。
上述内幕交易“实际所得法”的理论基础有二,一是认为内幕交易是一笔整体的交易,而不能人为割裂为合法的证券买卖和非法的内幕交易;〔2〕参见赖英照:“内线交易的所得计算”,载《中原财经法学》2013年第31期。二是“违法所得”与违法行为的间接因果关系说,即只要没有实施违法行为,就不会产生实际所得时,就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即使是违法行为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所得,也是应由国家没收的违法所得。〔3〕参见肖泽晟:“违法所得的构成要件与数额认定——以内幕交易为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二、域外对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实际所得法”的修正实践
(一)美国
在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内幕交易“实际所得法”的修正已经超越了理论分析和被告人抗辩层面,而是得到了部分法院的认同。一方面,对于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认定应当限制在内幕信息公开后一段时间内。在United States v.Royer一案中,第二巡回法庭虽然将内幕交易的犯罪所得认定为实际且变现的利益,但将该利益限定在内幕信息公开后三日之内的实际收益;〔4〕United States v.Royer,549 F.3d 556,590-91(2d Cir.2005).转引自万志尧:“内幕交易刑事案件‘违法所得’的司法认定”,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2期。另一方面则是考虑了市场因素对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计算的影响。第十巡回法院在United States v.Nacchio上诉审中修正了本案联邦地方法院和第八巡回法庭在United States v.Mooney一案中采取的实际所得法,而采用了市场吸收法,〔5〕United States v.Nacchio,573 F.3d,1062(10th Cir.2009).转引自汤欣、高海涛:“我国内幕交易案件违法所得的算定及判罚——兼论域外法律实践及其启示”,载《证券法律评论》(2015年卷)。即当内幕信息公开并被市场完全吸收后,欺诈行为终止,此时其他因素对股价的影响不应再作为计算违法所得的基础。〔6〕United States v.Mooney,425 F.3d(2005).转引自汤欣、高海涛:“我国内幕交易案件违法所得的算定及判罚——兼论域外法律实践及其启示”,载《证券法律评论》(2015年卷)。
(二)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在“台开公司内幕交易案”中以违法所得计算问题三次发回重审,直到“高等法院”第四次审理时按照“关联所得法”对违法所得进行计算,本案才告终结。“最高法院”认为,内幕交易违法所得以信息公开后股价涨跌的变动幅度差额计算,应指计算内幕交易犯罪所得时点的股票价格变动必须与该内幕信息公开之间具有相当关联性。〔1〕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2007年台上字第7644号”(2007年12月25日判决)、“2009年台上字第4500号”(2009年5月25日判决)。转引自汤欣、高海涛:“我国内幕交易案件违法所得的算定及判罚——兼论域外法律实践及其启示”,载《证券法律评论》(2015年卷)。
(三)我国香港地区
我国香港地区在认定内幕交易违法所得时对“非内幕信息因素”的剔除持保守态度,只认为在“特殊情况”下,需要顾及其他因素,但是,对于这一“特殊情况”的适用,香港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且尚未公布明确的适用标准。〔2〕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v Shek Mei Ling(1999)FACV No.23 of 1995.转引自汤欣、高海涛:“我国内幕交易案件违法所得的算定及判罚——兼论域外法律实践及其启示”,载《证券法律评论》(2015年卷)。
三、对以“实际所得法”计算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缺陷的反思
不可否认的是,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采用“实际所得法”计算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非常简便,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是,“实际所得法”无论其理论基础本身,还是在监管逻辑上,乃至从结果的公平性而言,均存在难以自洽之处。
(一)采用“实际所得法”计算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使得并非违法行为导致的收益也被认定为违法所得,违反了违法所得因果关系的基本法理。
根据行政法学通说,违法所得是指行为人从事非法经营等获得的利益。〔3〕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二版,第311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6号)第10条规定:“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所得’,是指通过内幕交易行为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可见,无论是从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还是从两高的司法解释来看,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必须是不法的内幕交易行为直接造成的,即“违法所得”与违法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实际所得法”不考虑“实际所得”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将与违法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收益同样认定为“违法所得”,有违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和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
1.“实际所得法”未考虑行为人信息优势的时效性,将信息优势结束后的所得也一并认定为“违法所得”,违反了违法所得因果关系的基本法理。
禁止内幕交易的首要原因和价值在于维护证券交易的公平〔1〕L Loss and JSeligman,Securities Regulation,Third Edition,Volume VII,pp.3451-3454(1991);Shen-Shin Lu,Insider Trading and the Twenty-Four Hour SecuritiesMarket,pp.1719(1994);Gil Brazier,Insider Dealing;Law and Regulation,pp.5253,(1996).转引自杨亮:《内幕交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防止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公众对内幕信息的无知状态牟取暴利。因此,禁止内幕交易的核心在于禁止行为人不当利用信息优势。
而行为人信息优势并非永久存续,而是具有一定时效性。〔2〕参见王越、郭献朝:“内幕交易罪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22期。行为人较公众更早知悉利好内幕信息的存在,并基于此提前进场,以较低成本进行“原始积累”。随着内幕信息的公开,公众开始接触并消化这一信息,行为人的信息优势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在此之后,行为人的所得便不再来源于其信息优势地位,因此,该部分收益不能认定为“违法所得”。“实际所得法”并未对信息优势的时效性予以考虑,将信息优势结束后的所得也一并认定为“违法所得”,明显不当。
2.“实际所得法”忽视了市场对内幕信息的消化能力,将内幕信息对市场失去影响力后的收益,也认定为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违反了违法所得因果关系的基本法理。
从经济关系上分析,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必须是重大未公开信息价值的犯罪化兑现,即违法所得来源于重大信息所带来的金融商品市场价格波动。〔3〕参见刘宪权:“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司法判断规则研究”,载《中国法学(文摘)》2015年第6期。利好信息公开后,市场会随即作出反应,直到利好信息被市场消化,股价趋于平稳。此时,利好信息对市场的刺激作用消失,股价趋向于平稳。因此,当内幕信息转变为公开信息,其作为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对股价影响力的存续同样具有一定时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74条规定:“投资人损失计算的基准价格,是指为确定证券的真实价值,将投资人的应获赔偿限定在因证券市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而拟制的基准价格。……内幕交易的,以该内幕信息公开后10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格为基准价格。”可见,最高人民法院该司法解释起草组也认为,市场对内幕信息的反应存在一定合理消化期限,该期限过后,证券价格将回归理性。
显然,“实际所得法”将行为人在内幕信息作为“重大信息”对市场失去影响力后的收益也认定为“违法所得”,无疑忽视了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信息的消化能力,明显不当。
3.“实际所得法”未剔除系统风险及非系统风险因素对收益的影响,违反了违法所得因果关系的基本法理。
通常认为,在证券市场上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的除去证券欺诈行为之外,还存在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因素。系统风险,是指由于宏观因素发生变化而对市场整体产生影响,导致整个或某一类证券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所引起的风险,通常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等。〔1〕参见陈共、周升业、吴晓求:《证券市场基础知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非系统风险则是指与整个市场无关而发生于某个具体股票或债券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于公司内部因素。〔2〕参见贾纬:“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1期。
在内幕信息公开后,个股价格的上涨不仅受到该公开信息的刺激,还会受到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张某某等内幕交易“凯诺科技”案中,内幕信息公开后个股上涨14%,大盘涨幅则为22.55%,被告人辩称,对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认定过高,应剔除大盘涨幅对相关股票涨幅的影响。但是,对此法院并未作出回应。
显然,“实际所得法”未考虑系统风险及非系统风险因素对个股价格的影响,必将导致法律评价与内幕信息对资本市场的真实作用之间出现明显相悖。
(二)证券监管机构对利空型内幕交易与利好型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认定方法完全不同,监管逻辑不一致。
对于利空信息下的规避损失型内幕交易,证券监管机构则将利空信息对股价的影响期间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而非认为行为人任何时段规避的损失均属于“违法所得”。具体而言,证券监管机构以内幕信息公告日为基准日,以实际卖出金额减去卖出股票在基准日的虚拟市值(卖出股票数量×基准日该股收盘价)计算违法所得。〔3〕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主编:《证券行政处罚案例判解》(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我们认为,证券监管机构在利空型内幕交易违法所得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显然更为科学和合理。难免有学者质疑,为何在利好信息下获利型内幕交易中,证券监管机构却弃此方法不用,而改用直接计算买卖差价的简单方法,导致监管逻辑不一致。〔1〕参见彭冰:“内幕交易行为处罚案例初步研究”,载《证券法苑》2010年第三卷。
(三)采用“实际所得法”计算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既可能导致计算的违法所得畸高,也可能导致计算的违法所得畸低,甚至在明明存在违法所得的案件中将违法所得计算为零,明显不公平,有违行政处罚法的“过罚相当”原则和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实际所得法”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导致违法所得畸高,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导致违法所得畸低,甚至可能导致违法所得为零。例如,在赵建广内幕交易“ST黄海”案件中,赵建广在获悉公司利好的内幕消息后,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股票30万余股,但是在内幕信息公开后并未卖出,而是在两个多月后才开始卖出。但由于此时股市泡沫破裂,大盘从6000点急剧下跌,最终赵建广卖出股票亏损35万元。据此,证监会认定赵建广内幕交易没有违法所得,只对赵建广处以10万元罚款。但显然,赵建广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并不等同于最终的实际亏损,赵建广之所以发生亏损,是其坚持持有不抛售,自愿承担市场风险造成的。〔2〕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ST黄海赵建广)([2009]17号)。
此外,由于现行司法解释将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金额大小当作考量内幕交易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核心标准之一〔3〕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公通字[2010]23号)第35条规定:“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单位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单位,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三)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五万元以上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6号)第6条规定:“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三)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第7条规定:“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三)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七十五万元以上的;……”,因此,将利用内幕信息获取利益以外的收益认定为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可能导致不构成内幕交易罪的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也可能加重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1〕参见万志尧:“内幕交易刑事案件‘违法所得’的司法认定”,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2期。例如,在冯某某等内幕交易“德赛电池”案中,被告人上诉提出,实际获利不等于非法获利,应以复牌当日的收盘价计算,原审法院认定的涉案获利金额不当,导致判处其罚金刑过重。〔2〕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74号《刑事裁定书》。
四、对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认定方法的修正性建议
概而言之,“实际所得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割裂了“违法所得”与“违法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合理的计算逻辑应以“只有能够归因于违法行为的获益,才构成违法所得”为基本原则。我们认为,能够体现上述计算原则的计算模型主要有两种:一是确定基准日及基准价,将行为人的违法所得限制在“违法行为存续”或“股价受内幕信息影响”的合理期限内;二是在有系统风险因素或非系统风险的其他因素导致股价波动时,对该等非关联因素予以剔除。
(一)确定基准日
确定基准日的意义在于避免将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计算范围无限扩大,对于在基准日之前卖出的证券,以实际收益确定违法所得;对于在基准日之后卖出的证券,则应当以证券买入价与基准价之间的差额确定拟制所得。我们认为,根据证券市场的基本形态和原理,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确定基准日:
1.方法之一:将信息优势消除日确定为基准日
(1)对内幕信息公开后出现涨停时信息优势消除日的确定
在内幕信息公开后为公众所接受、理解的有效期后卖出证券,则此时行为人的收益已并非完全基于其信息优势获得,因此,在信息优势消除后的收益便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据此,可以将信息优势消除日作为确定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基准日。
我国证券市场设立了涨跌停板制度,通常重大利好消息对股价的影响会通过涨停板的形式体现,2007年A股个股曾创下连续42个涨停板的记录。在涨停板期间,假设行为人未取得信息优势,则行为人与公众处于相同的无法建仓的地位,因此,涨停板期间应当属于信息优势存续期。涨停板打开后,如市场累计卖出量未超过行为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的持仓量,说明行为人仍可通过其利用内幕信息提前进场的优势而获取利益,因此,这一期间也应当属于信息优势存续期。
据此,我们认为,可以将涨停板打开后市场累计卖出量超过行为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的持仓量的日期,作为认定信息优势消除的日期。此后,其他投资者得以无障碍进场,行为人的信息优势地位消失。
例如,在引题案例中,2013年2月25日“华闻传媒”股票复牌后随即连续两天涨停,直至3月4日涨停板打开,并且在当日市场累计卖出量超过张某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的740万股,因此,应当认定2013年3月4日为基准日。
(2)对内幕信息公开后未出现涨停情况下信息优势消除日的确定
内幕信息公开后股价未涨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内幕信息公开对股价的影响并不重大。〔1〕参见刘光明:“内幕交易犯罪违法所得应如何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16年第11期。因此,在内幕信息公开后未出现涨停的情形下,则应以复牌日为信息优势消除日。如果行为人在复牌当日将股票全部抛售,则应当以行为人的实际所得认定违法所得;如果行为人在复牌当日仅卖出部分股票或继续持有股票,则对于未卖出部分,应以复牌日当日的收盘价作为基准价认定违法所得。
2.方法之二:将重大信息消化日确认为基准日
如果行为人的平仓交易距离内幕信息公开已有相当长时间,内幕信息对股价的影响力已经耗尽,行为人不具有利用内幕信息经济价值获利的可能,则此时行为人获取的收益应排除在违法所得之外。
内幕信息公开后,市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该等信息消化掉,涉及复杂的测算规则。美国司法判例认为,应视公司规模和知名度判断,相较于知名度小的公司,知名度大的公司需要的时间更短一些。〔2〕参见程红:“论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6期。也有观点认为,内幕信息被市场消化的具体期间在个案中涉及多重诱因,应由法官自行判断。〔3〕参见李有星、杨楠:“论我国内幕交易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建构”,载《时代法学》2012年第10卷第6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的规定,以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认定为虚假陈述基准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读,这种方法的思路是当股票的换手率达到100%,即表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基本摆脱了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4〕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参考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将股票复牌后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认定为内幕交易基准日。
对于上述两种认定基准日的方法,我们认为,内幕交易行为之所以违法,其核心并非在于证券买卖行为,也并非在于根据信息对股价的刺激投资,而是在于行为人违反了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破坏了市场参与者基于平等信息地位进行交易的投资环境。因此,将行为人信息优势消除日认定为基准日,更符合禁止内幕交易行为的立法目的。
(二)确定基准价
在证券市场中,收盘价是最重要的一个数据,是盈利或亏损的基准,是市场参与者们所共同认可的价格。〔1〕参见罗开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如何认定内幕交易犯罪违法所得”,载《上海金融报》2014年2月15日第A13版。对于基准价的确定,我们倾向于认为,将复盘日至基准日期间收盘价的平均价确定为基准价较为合理。
(三)剔除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因素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9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可见,在我国证券欺诈民事审判实践中,已经允许行为人对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因素的存在及其对投资损失的影响进行证明和抗辩。
在认定是否存在系统风险因素时,应考查汇率、利率等金融政策、国内和国际的突发事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动等具体诱因的存在。在计算系统风险剔除比例时,我们认为,证券市场的指数波动则是最直观、最量化的参照标准,具体可根据个案情况,将大盘指数、行业板块指数或两者相结合作为系统风险计算的参照标准,或者参考同行业同类型个股或受同一政策影响个股的价格波动情况。
对于非系统风险因素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也应允许相关责任人作合理抗辩。比如,在行为人买入和卖出股票期间,上市公司发布其他重大利好消息,导致股价飙升。
(四)以基准日和基准价为标准计算违法所得,同时剔除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因素影响股价的因素
基于以上考量,对于利好型内幕交易,我们建议,以基准日和基准价为标准,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计算公式如下:
1.行为人在基准日之前抛售所持有证券的情况下,以实际所得确定为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累计卖出金额+累计派现金额-累计买入金额-配股金额-交易费用-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因素对股价的影响。
2.行为人在基准日之后抛售所持证券的情况下,以基准价计算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基准价×累计买入股数+累计派现金额-累计买入金额-配股金额-交易费用-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因素对股价的影响。
3.行为人在基准日之前抛售部分证券的情况下,应以基准日为界分别计算。
违法所得=基准日前累计卖出金额+基准价×累计买入但未卖出股数+累计派现金额-累计买入金额-配股金额-交易费用-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因素对股价的影响。
结语
诚然,对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认定在实践中存在一定技术性难题,但是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认定不仅决定了行政罚没的范围和行政罚款的数额,更是行政违法行为是否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的重要参考依据,依法合理认定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确有必要。随着金融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不断探索,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机构应当尽快确立更为科学的认定规则和计算方法,并以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基准日、基准价等关键指标予以明确,并允许行为人对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因素的存在进行主张和抗辩。
*张保生,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朱媛媛,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