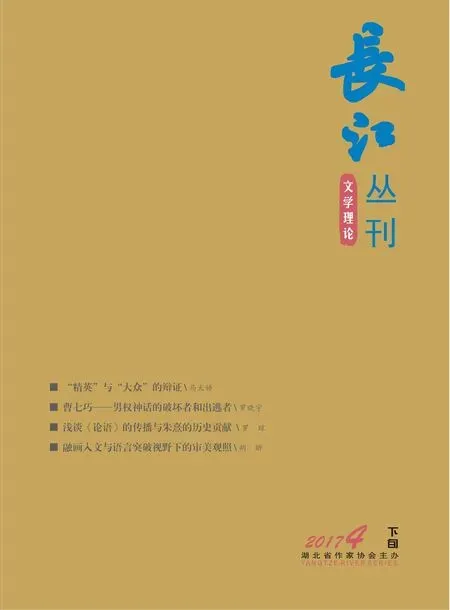融画入文与语言突破视野下的审美观照
——浅谈汪曾祺作品中的人性美
2017-12-05胡昕
胡 昕
融画入文与语言突破视野下的审美观照
——浅谈汪曾祺作品中的人性美
胡 昕
汪曾祺是一位连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为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他的散文体小说在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同时,不追求语言的华丽性和优美性,而是致力于用平淡质朴的文字营造浓浓的乡土文化氛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
汪曾祺 散文化 通俗化 乡土化
一、美在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段优美而简短的乐章。时而急促,时而舒缓。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小说长短上,更多的则表现在行文的句式上。小说大多采用短句,偶尔夹杂一些长句,长句的娓娓道来和短句的戛然而止结合,一收一放,使语言富有极佳的节奏感和层次感,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是一种"诗化的小说语言"。看他的《葡萄月令》: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
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
雪化了,土地是黑的。
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
葡萄出窖。
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芽苞…
再看他的小说,《中国大百科全书》论述道“以散体文的形式表现叙事性的内容,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关系、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人物活动的环境进行具体的艺术描写,是小说的基本特征…。”传统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皆认为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大要素,舍去其中之一,皆不能称为小说。作家们也一直谨遵这条戒律,可到了汪曾祺这里,这一切都全变了个样。他的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情节迭宕起伏和章回严谨的固有程式,有意减少戏剧性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不设悬念[1],在叙事性小说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都被汪曾祺舍弃了。他自觉地继承古典笔记体小说的诸多特点,融合散文隽永、淡雅的风致,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生活化的叙述方式表现。以他的《受戒》为例: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开头提到庵赵庄,然后分别解释这三个字,以介绍名字的来历。一短一长,起承转合之间安排得非常和谐,错落有致,读起来跌宕起伏,犹如诗词一般,干净清爽。汪曾祺深受老师沈从文散文化小说的影响,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这种独有的诗化语言读起来朗朗上口,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我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不大真实。”“我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分是一直都明显地存在着的。…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气氛即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2]…所以他创造了一种散文化的小说文体,或者说将小说写成了散文(诗),这种独特的行文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二、美在“融画入文”的叙事手法
汪曾祺本人就是一个画家,会中国画,因此对于色彩的感觉非常敏感。“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薄高雅的风俗画效果。”在小说叙事中插入一些风俗轶事的片断,一地一景、一人一事,娓娓道来。作者就是通过这种绘画的手法在小说中,把那些旧社会普通人的普通生活,鲜明、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又将朦胧、含蓄的底蕴留在读者的想象中,在汪曾祺小说中,取代了情节的中心位置,成为支撑小说的框架,以他的《鉴赏家》为例: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
简简单单几笔便勾画出了当地的一幅物产风俗图:这样,用水果标示一年的光景,将四季时节与水果联系起来,从立春到端午,从盛夏到入冬,好像把当地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风情画一幅幅地在小说中展现给读者看:美丽的景色以及丰富而诱人的特产,正是一幅幅风俗画。因而读汪曾祺的小说就有一种如同赏画般历久弥新的审美感受力,这种充满作者故乡高邮气息的民俗风情画,在作者的小说中几乎每篇可见。例如他的《大淖记事》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 。”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精妙的色彩搭配使他的小说具有了诗的意境和清新的民间神韵,强烈地展现出生命的活力,风习的传承,文化的血脉。这些都可以看出汪曾祺对高邮这片故土的热爱和熟悉,进而在他的文字里像画画一样表现出来,乡而不土,落犹不迫。
三、美在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美
汪曾祺处于传统文化的话语环境,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主张打破浪漫主义的虚无和缥缈,在掷地有声的现实里开出一片花来,沈从文对其影响不可不谓之深沉,有了《边城》,汪曾祺便领略并清楚了那种自然、健康、纯粹的情感。以致于他的小说题材大都选自于民俗风情,在日常生活里插科打诨,用白描手法简单勾勒图画,用质朴文字描写家长里短。没有刻意雕琢,没有辞藻堆砌,只有清新的文风、悠然的表达。他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文体自觉的先声。
例如:“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说:“要——!”
“快点划!”
人对于爱情是缺乏免疫力的,这种真挚的情感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和发展,它纯粹、自然、只要有那么一点春风拂过,即会春芽猛长,春暖花开,这是人性的本初,更是人性的光明面,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逃脱爱情的巨大力量。无论是未受禁锢的常人,还是清心寡欲的出家人,都拥有着最原始的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和对精神生活的渴望。所以在那个美好的年龄,小和尚明子的青涩拘谨和小英子的率性天真,这场纯美的初恋,是汪曾祺作品中最真挚的情感表达。
[1]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三章“奇书体的结构诸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6.
[2]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M].北京出版社,1981.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