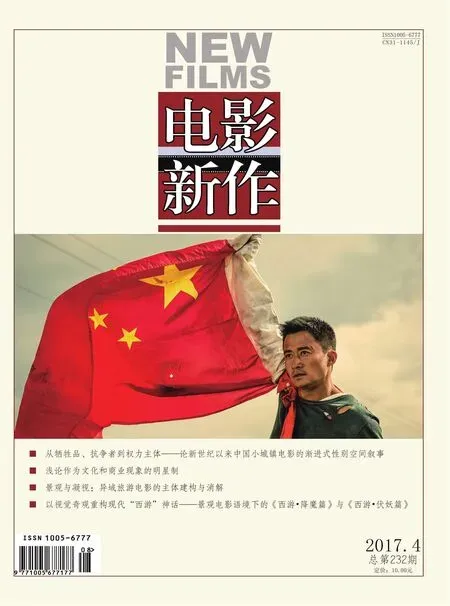三重时空,一场幻梦
——电影《七月与安生》中的成长与身份认同
2017-12-02张璐
张 璐
三重时空,一场幻梦
——电影《七月与安生》中的成长与身份认同
张 璐
电影《七月与安生》关注的焦点是女性的成长及其身份认同,然而其表现的“成长”和“身份认同”,本身就值得商榷。影片采用现实、小说和依附于小说而展现的回忆三线并置的叙事模式,形成三重话语时空。电影中,流浪作为实现成长和进行自我身份体认的方式,得到的是一种狂想式的展示,真正的远方与未来反而是缺席的。电影所展现的实则是一场背离现实主义的幻梦,最终达成的也只能是一种虚假的成长和想象性的身份认同。
《七月与安生》 成长 身份认同 流浪
现代主义宛如一场成长洗礼,它既是对19世纪社会巨变的反应,也引导着个体对“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和“宗教信仰的泯灭”①这两大变化做出反应。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在成长中都经历着自己的“现代主义”剧变。生活的迷向,未来的惘惑,反叛、破坏、独立……这些词以及它们的反义词,共同构成了成长这一过渡时期的关键词。
《七月与安生》首先是一部成长电影,再是一部青春电影。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的选择与挣扎,其有别于普遍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对这两大命题的热切关注使《七月与安生》从当代一众大打怀旧牌的青春片中拔地而起。然而,电影是否体现并实现了真实而现实的“成长”和“身份认同”,这本身就构成一个问题。流浪作为电影中实现成长的方式,得到了极为浪漫的却是一种狂想式的展示。远方成为一个少女式幻梦中的逃离现实的匿名地,引导出一条想象中的逃逸路径,不确定地点,不确定名称,因为逃离现实而抹拭了现实的厚度、削弱了现实的重量,真正的远方与未来在电影中反而是缺席的。一方面逃避“必须”,一方面追求“不可得”,电影《七月与安生》所展现的实则是一场背离现实主义的幻梦,最终达成的也只是一种虚假的成长和想象性的身份认同。
一、三重叙事时空:亦真亦假
电影《七月与安生》自一开始就设置了两明一暗的三线叙事结构,即现实、小说和依附于小说而展现的回忆。三条线交织错置,甚至彼此掩盖,形成了三重时空,导向了不同的后果,而电影的最后30分钟则将三重话语空间层层打开,顺应人物情绪的发展而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亦真亦假的结局。
电影开篇,金色光线下的树林里,两个小女孩相互追逐对方的影子。这是两人的回忆,也是小说里的内容。随之银幕黑掉,伴随着键盘敲击声,一行字出现,“七月第一次遇见安生是13岁的时候”。电影正式开场,而电影中的那部网络连载小说也就此开篇。按照惯例,充当叙事工具的小说会使影片构成一种戏中戏的叙事模式,比如去年闪耀威尼斯电影节的《夜行动物》。但《七月与安生》的特别之处在于电影中的小说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回忆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相互交融,从而增添了叙事的复杂性。其次,小说也是导演设置的一个障眼法,它的作者之谜,为之后电影情节的反转埋下了线索。

图1.《七月与安生》
如前所述,电影《七月与安生》的复杂性集结在最后30分钟。这30分钟是三重叙事话语的交错空间,彼此互文,相互纠正,以至于让人错觉无论是回忆还是现实,甚至整部电影,都亦真亦假,形如幻梦。在电影的第77分钟,小女孩作为引导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出场,她联系了男主人公家明,并导致随后安生与家明迫不得已的再次相见。其间插叙的则是小说中的内容:七月离家之后,四海为家,到北京寻找安生,发现安生这时有了未婚夫老赵,生活终于安顿下来。也就是从这段插叙开始,电影开始打破多线并置的状态,松懈叙事空间的界限,为稍后接连的故事反转做准备。在随后的第89分钟,故事实现了第一次反转——安生与家明再次见面,家明终于得知小说的真实作者不是七月,而是安生。家明追问“小说都是假的,七月在哪儿呢”,安生看着他,陷入回忆。也是在这里,回忆第一次以非附着于小说的形式出现。安生的回忆承接着之前七月到北京找她的时候,因为蜕去小说的虚构外壳,而进入真实的界域。但这段回忆的真实再次局限于有限时间内,止步于林七月生产之前……家明询问七月的去向,安生隐忍着撒了谎。直到回到家中,安生大声痛哭,才又继续未讲完的真实的回忆,说明了七月的真实结局。回忆线至此终结。然而连载小说却还没完结,需要一个结尾。安生接着写。她为七月设计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也正是她讲述给家明听的那个结局。七月独自走向远方,继续流浪,并且“从不去想她将走到哪里,还会走多久,只想自由自在地一直走下去”。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里,七月一个人缓缓走向遥远的灯塔,而这个结尾其实是安生笔下的小说的结尾。
三重叙事时空交错织就电影的三个结局,有着杜撰成分的小说,有着留白的回忆,有着刻意隐瞒的现实。导演用这种繁复的叙事结构最终将电影打造成了一场仿佛镀上迷离光晕的幻梦,真实与虚构,回忆与现实,亦真亦假,难以分辨,而这更像是一种因为无力呈现现实而做出的艺术化的妥协。因为缺乏处理残酷现实的策略,而代之以电影叙事上的模糊不清、真假不明。
二、两个自我:镜中人像
贝尔将现代文化置于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领域间断裂的图景中进行考察,认为人的困境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②,因为人存在于二者的缝隙之中。现代社会中,个体面临的各种两难矛盾与选择正是源于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同运转原则,经济领域要求的是具有功能理性的以满足效益为首要目标的组织形式,而现代文化则标榜个体的完全自由与自我实现,七月与安生恰好代表着这一冲突下的两种相反的典型人格。她们从在中学军训上初识,就已经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如果说七月是拥有并且竭力维护“安全”的利益占有者,那么安生就是“自由”的忠实信徒。然而她们的性格中却都有对方的影子,互相投照相互映射。她拥有她的安全,却也羡慕她的自由;她挥霍着她的自由,却也渴望她的安全。安全与自由,爱与怕,本来就是现代人所遭遇的核心困境。电影用两个人物形象将这一本来存在于个体内部的两难矛盾具象化,加剧了其间的角力与冲撞的张力。詹明信说,“踏入后现代境况以后,文化病态的全面转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明: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③,并没有夸大其词。
分裂的自我如何实现身份认同?电影用最后30分钟,进行了一场交换人生的实验。就自我认同而言,拉康的观点是:“主体认同是在他人身上并一开始就是在他人身上证明自己”,最终使自己对自己并使他人对自己形成一种“想象性的认同关系”。④而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当代,充溢整个社会的“差异和他性”已经成了身份/认同必不可少的构成因素。只要当性格中不同于日常一面的另一面得到认同,即使是想象性的认同,个体的身份认同才算得到最终的实现。七月在告别了过往的一切之后,如曾经的安生一样,走上流浪之路,旅店,舞厅,游轮……漂泊在大海上,七月发现自己“曾经赖以生存的稳固的生活,像陆地一样离她越来越远了。她才发现其实自己特别习惯摇晃与漂流”;而安生则如曾经的七月,找了一份稳定工作,过起都市白领的平淡生活,“安生仿佛变成了安稳的七月,七月也变成了流浪着的安生”。七月与安生,正如同一个人的两面灵魂,她们分别做出的改变与尝试其实是一个人努力适应人格中的差异与他性,进行身份认同的体认的过程。

图2.《七月与安生》
电影结尾前,安生站在巨大的落地玻璃前,看着自己的镜像,镜头横移,镜中的人影竟是七月,两人相视而笑,就像一个人从窗玻璃里看见了自己一样,镜像般的存在关系,哲学性地暗示七月与安生正是两面一体,同时也暗合现代社会分裂与暧昧的时代精神。这种刻意的混淆甚至蔓延到了银幕之外,分别扮演七月与安生的马思纯与周冬雨,在惊人地共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之后,反复声明七月与安生就是同一个人……这种打破第四堵墙的仿真与拟象,甚至比影片内容本身更具说服力,引导了观众对电影的判断与评论。导演在表现两个人物角色上的指意不明,两位主演在戏外的有意效仿,观众对此的认同与买账,无不透露出现代人内向的怯弱与外向的跟风。真正的自我在没落,自我认同则始终处于缺失的境地。
三、一场虚无幻梦:流浪狂想
现代文化里,流浪被改造成为一个充满了波西米亚式浪漫气质的行为,其现实依据则源于工业革命与交通革命,“现代世界的剧烈运动和文化变迁打破了旧有的时空顺序和整体意识”⑤。而纵身投入充溢着不确定性的广袤社会之中,个体似乎更能适应并掌握令人不安的现代性的变化之流。然而无论是在个人的幻想还是在艺术作品中,流浪始终是现代文化滋养生成的产物,它不仅与现实背道而驰,而且根本没有能力具体化任何现实。然而电影《七月与安生》却极力“鼓吹”流浪。从被迫走上流浪之路的安生,到成年后主动选择流浪的七月,流浪成了实现人生成长、进行身份体认的方式,经历流浪,便能对人生大彻大悟,寻觅到人生的真谛,找到自己的最终归宿……然而流浪,始终脱离现实。在电影所展现的流浪中,充斥银幕的是用MV式快速镜头极力打造的浪漫与美化,消失的是那些繁琐而现实的生活细节,那些与基本生存相关的沉重日常。我们忍不住问,她们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她们流浪到底去了哪里,与原有世界又保持着怎样的联系或距离?从这个角度说,《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既“轻”又“浅”,轻在缺失现实的厚度与重量,浅在止步于幻梦式的远方,无关真实的未来。这如同一个文艺少女的浪漫狂想,永远停留在青春期,永远未成年,捧着一颗自怨而自恋的心,在大脑里走遍千山万水,经历生离死别,演绎着在现实世界中永远无法存活的故事,因此最终完成的只能是虚假的成长和想象性的身份认同。

图3.《七月与安生》
流浪是一种对自由的失重想象。电影中的远方,那些七月与安生都分别流浪过的地方,极寒雪地,寥廓大海,始终面目模糊,一闪而过,犹如幻梦中的海市蜃楼,它们坍塌而降落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所对应的难以挣脱的沉重现实。去远方流浪,其首要目的就是逃离现实。安生在寄给七月的明信片里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不会腻味的感觉”。她不满足,她渴求变动,追求新鲜,寻求刺激……贝尔将之称为大众社会的感觉革命,现代社会剧增的“相互影响”把每个人与更多的人联系起来,“增大的相互影响不仅导致了社会差别,而且作为一种经验方式也导致了心理差别——它造成对变化和新奇的渴望,促进了对轰动的追求,导致了文化的融合,凡此种种都十分突出地表明了现代生活的节奏”。⑥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大众文化的视域下,流浪会显得格外有魅力。

图4.《七月与安生》
抛离过去,拒绝重复,生活的方向便只剩下将来,而将来本身却蕴含着最终的虚无。“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⑦,七月与安生最终交换人生,灵魂的两面就此完整,但是其后呢?电影以七月走向远处的灯塔作结,看似寂静美好,却完全陷入了没有未来的虚无感之中。这并不是一个现实的解决个体内部二元冲突的方案,电影甚至没有勇气就这一问题给出确凿而响亮的回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两生花》同样探问了个体的双重性的问题。《七月与安生》表现着个体之“异”,《两生花》则细心描绘着个体之“同”。“异”最终通过交换构建出“同”,然而,两面“同一”的个体在未来的漫漫长路中将如何平衡自我,又将最终去往哪儿,一切都未可知。《七月与安生》的故事甚至无法避免“空洞”的质疑。两个女孩的嫌隙,争吵,以至分离,都与男主角苏家明有关,然而这个男性角色在电影中却始终是一个功能性的符号化存在,没有自主性。将戏剧冲突凌驾于一个缺乏“实在感”的空洞符号之上,未免失于避重就轻。
电影《七月与安生》所表现的成长和身份认同,其属性犹如云烟,其内核的虚假薄弱在现实语境中更是将持续遭遇严重的危机,不得不缴械投降。没有面向真实未来的勇气,就无所谓成长;只能在想象中完成的身份认同,就不是真正的认同。再美的梦,如果缺乏现实的出口,那也只是一场幻梦。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94.
②[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前引书:60.
③[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M].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447.
④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122-150.
⑤[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前引书:14-15.
⑥[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前引书:137.
⑦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6-97.
张璐,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