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可夫斯基电影场面调度的空间叙事
2017-11-29峻冰高娜
峻冰 高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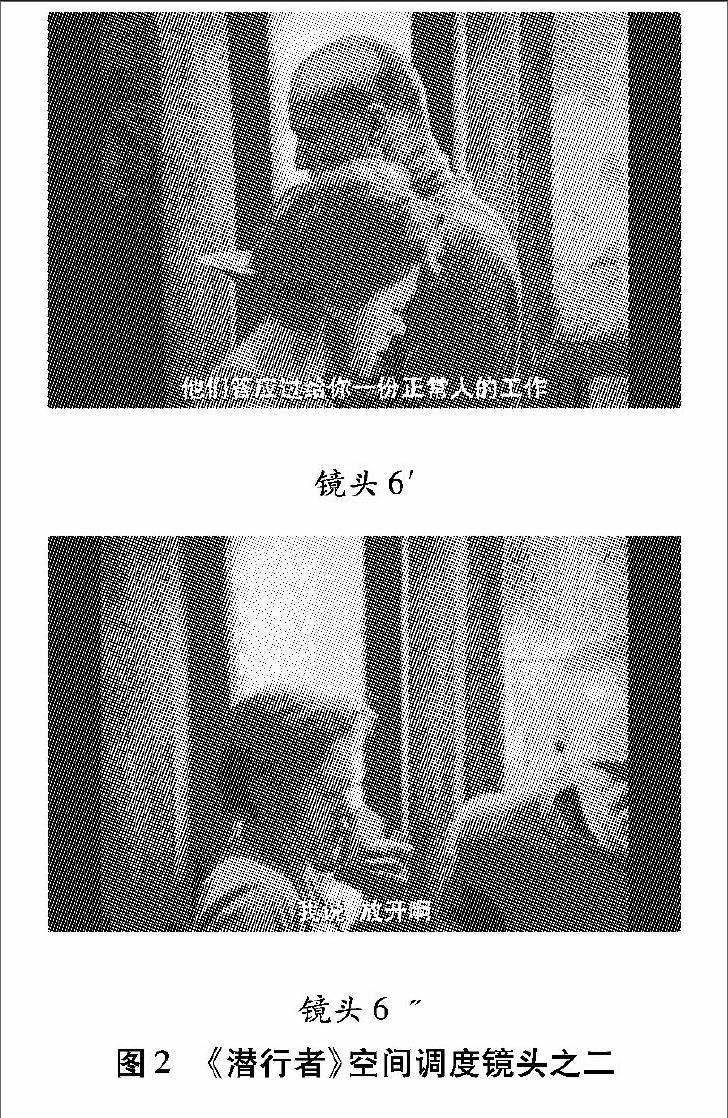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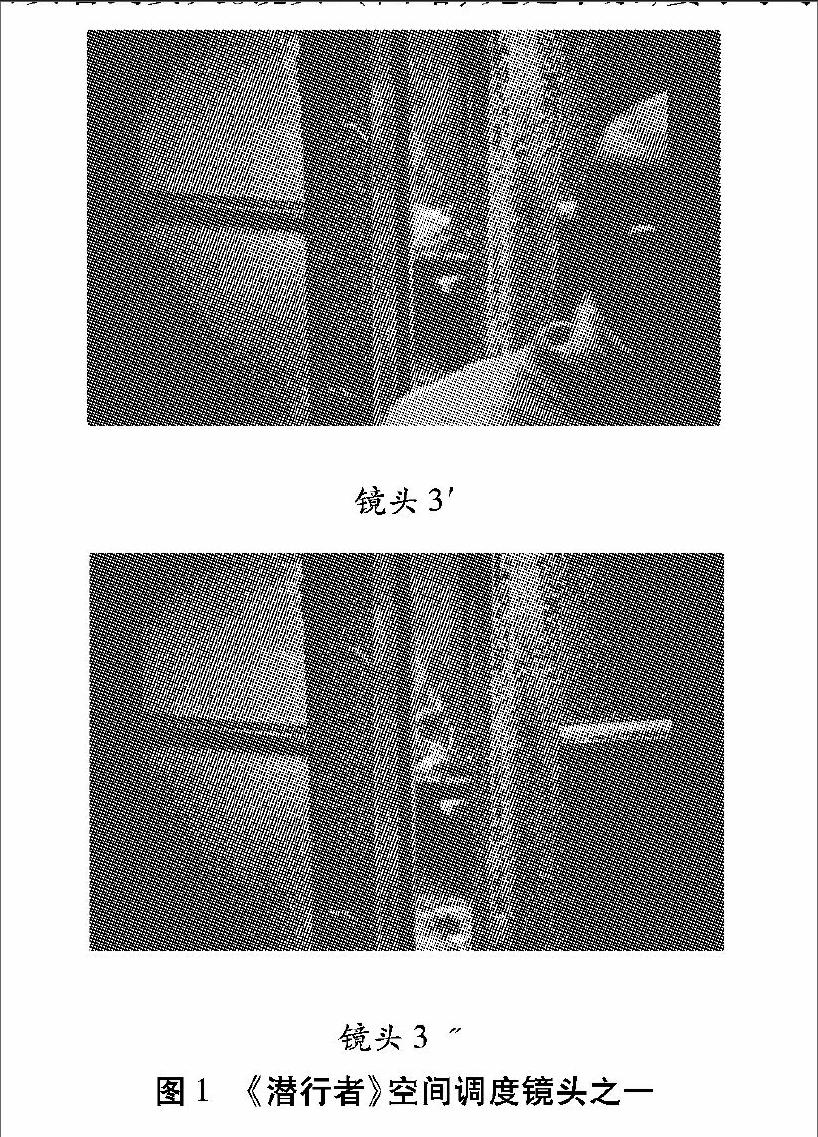
关键词: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潜行者》;场面调度;空间叙事
摘要: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以其电影独特的“诗性推理”闻名于世,他将苏联时期“诗电影”的艺术性提升至新的高度,尤其体现在电影场面调度的行云流水般的诗性镜语上。在其代表作《潜行者》中,充满诗意且富有个性色彩的场面调度(尤其是空间调度)比比皆是,它们基于导演电影观念,从演员调度、演员与摄影机之间的调度、空间感的营造、空间象征等方面共同彰显了影片场面调度中空间叙事的审美魅力。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7)05-0035-06
The Spatial Narration of MiseenScene in Tarkovskys Flims
—Take Stalker as an example
JUN Bing, GAO Na
(College of Literature &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Key words: Andrei Tarkovsky; Stalker; miseenscene; spatial narration
Abstract: Andrei Tarkovsky is known for his unique “poetic reasoning” films in the world. He promotes the Soviet “poem film” artistic quality to a new level,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the poetic lens language in the film miseenscene. His masterpiece Stalker is full of poetic and individualized miseenscene (especially space scheduling). They are based on the directors film concept to highlight aesthetic charm of the spatial narr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actors scheduling, actorscamera scheduling, creation of space sense and space symbol etc.
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1932~1986)作为俄罗斯杰出电影导演,一生作品不多,但其揭示战争扼杀儿童天性悲剧的《伊万的童年》(1962,获第3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再现历史、艺术和心灵的苦难史的《安德列·鲁勃廖夫》(1971,获第2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协会奖),探讨科学研究中保持对人性尊敬的《飞向太空》(1972,获第2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以及对母亲进行诗性与哲思性回忆的《镜子》(1974)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浸润着对人类命运的追问和对人类本性的反思,以及通过消除人类的罪恶来实现人类救赎的潜在意识。导演运用享誉电影史学界、电影评论界的独特的“诗性推理”和场面调度行云流水般的诗性镜语,将苏联时期“诗电影”的艺术性提升至崭新的高度。
卡尔·巴特曾说:“对于启示在圣经中的上帝的三位一体理解导致这个独一的上帝不是只被理解为非位格的统治,即不只是作为权柄,而是作为主;不只是作为绝对的圣灵而是作为位格,即作为一个以他的思想和意志存在于他自身而存在的我。这就是他如何是作为父、子和灵的三重的上帝(thrice God)。”〔1〕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上帝代表三圣中的任何一位,而三圣中的任何一位也可以是上帝。塔尔可夫斯基与费德里科·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并称“圣三位一体”。持“自然神论上帝观”的他,认为上帝对自然界无法干预、应尊重自然规律,上帝只是自由的化身。这种对自然的膜拜式尊重无疑可溯源于俄罗斯传统文艺精神——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生存的制约在塑造出顽强、坚忍的人物个性的同时也彰显出自然的无比伟大。正如塔尔可夫斯基所说:“我们电影艺术的传统不仅导源于苏联电影的那些先行者,而且导源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诗歌、文化。当我们谈论电影时也不应忘记这点。值得回想一下,我们的电影是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深厚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内部的。”〔2〕美国影评家J.何柏曼也说:“安德烈·塔科夫斯基……其图像炽烈,如黑泽明;郁卒折腾,如安东尼奥尼;刚愎执著,如布雷松;对于民族神话之专注不移,则犹如约翰·福特。”〔3〕毋庸置疑,这种认识潜移默化地促成了其影片充满诗意的场面调度——现实世界和人类向往凝聚于电影影像,现实透过影像散发出人性诗意。
塔尔可夫斯基说:“对于我来说,电影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道德行为。”〔2〕《潜行者》(1979)作为其代表作,改编自斯特鲁加茨基兄弟(阿尔卡季·斯特鲁加茨基与鲍里斯·斯特鲁加茨基)的中篇小说《路边野餐》。片中富有个性色彩的场面调度(尤其是空间调度)比比皆是。该片讲述一位经验丰富的“潜行者”斯塔凯尔不顾妻子的阻拦,带领一位科学家和一位作家穿越一片有着千变万化陷阱和圈套的死亡之地——“区”,意图帮助科学家和作家找到“区”中可实现梦想、赢得尊重、收获尊严的“房间”的故事。影片“主题是关于人的尊严,关于一个人因缺少自尊而痛苦”〔2〕。斯塔凱尔每次进入“区”的本质目的实际是对自我生存意义的探寻,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他于妻子、孩子面前已失去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了,他的幸福、自由及一切与尊严有关的东西都在此“区”里——他不收任何报酬地带作家、教授等来到“区”,实欲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赢得他人认同。影片结尾,斯塔凯尔认识到这个“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其内心深处真正渴求的是爱:来自妻子的爱和来自孩子的爱(其实隐含着爱与被爱两个方面)。作家、教授在“区”里也深刻觉悟到自己到此之前的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功利目的也是实现不了的,人首先要自我肯定,而后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显然,影片是以滞缓的画面节奏、具有哲思性的镜头设计来探究人类的欲望和灵魂本质的。endprint
适值导演逝世30周年之际,聚焦个例,细致探讨其影片场面调度的空间叙事,认真揣摩大师的导演技法,于当下乃至今后的国产电影创作不无裨益。
一、寄寓电影观念的场面调度
无疑,电影观念是电影创作者(特别是“作者”)创作的依托与基础。“时间”作为物质世界中一种主观抽象的、处于精神层面的概念,是塔尔可夫斯基一直关注的对象;而电影作为一种留存时间的方法,是真实时间的模型。正如塔尔可夫斯基所言:“时间,复印于它的真实形式和宣言中:此乃电影作为艺术的卓越理念,引导我们思考电影中尚未被开采的丰富资源,以及其远大的前景。我的实际工作和理论假设都是建立于此一理念之上。”〔4〕在塔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时间是事实形式的时间。其电影观念中的“纪实”不仅是电影用来客观记录现实的手段,而且是电影呈现时间刻痕于现实的方式。影像不仅是一种反映现实的手段,它还能透过现实的片段与变迁把握作用于其上的时间。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曾经说过:“初看塔科夫斯基的影片仿佛是个奇迹。蓦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房间门口,过去从未有人把这房间的钥匙交给我。这房间我一直都渴望能进去一窥堂奥,而他却能够在其中行动自如游刃有余。我感到鼓舞和激励:竟然有人将我长久以来不知如何表达的种种都展现出来。我认为塔科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3〕现实世界和人类向往凝聚于影像,现实透过影像散发出诗意,因此,塔尔可夫斯基以“雕刻时光”命名自我著作,无疑涵盖了两层含义:电影是对“事实形式的时间”的挽留与影像化;“雕刻”过程中蕴涵着追求与向往。
“如果把二十年前典型的好莱坞影片与现代影片比较一下的话,那么摄影机富于机动性这个事实也许是唯一最惊人的区别了”〔5〕,电影理论家李·R·波布克如是说。“场面调度这个一开始用于舞台剧的概念后来也意指导演对画框内事物的安排。”〔6〕作为影片拍摄的中心环节,导演拍摄每一场景都必须考虑摄影机的位置、演员在摄影机面前的运动等问题。也即导演要在特定空间里遵循导演意图安排演员、摄影机及画面中的一切。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导演要安排的对象可以是构成镜头场景的几乎所有事物,包括镜头构图本身、取景框、摄影机的移动、人物、灯光、布景设计和一般的视觉环境,甚至那些帮助合成镜头场景的声音”〔7〕。在塔尔可夫斯基那里,“场面调度是演员和环境以及其他演员之间关系的安排和设计”〔4〕。至于场面调度的不同手段,电影学教授尹鸿在美国电影学者路易斯·贾内梯的基础上将其分为20项内容,并概括为三大部分:“场面的空间调度、场面的时间调度和场面的视点调度。”〔8〕审慎探察,可见塔尔可夫斯基电影场面中的空间调度带有独特的个性色彩,充满诗意。
显而易见,场面调度是将现实影像化的过程与方式,沟通电影拍摄现场和银幕影像。在塔尔可夫斯基电影中,场面调度不单纯局限于电影创作的表达手法,而是涵盖演员、摄影机、剧本的选择、剪辑的观念、影像呈现等诸多方面。导演尤善段落镜头的运用,摄影机多用拉、移、升,并与摇结合;在拍摄方式上其多用活动摄影机拍摄活动对象——尽可能不要过多的镜头剪切。在拍摄现场,导演通过演员、摄影机及其与空间的关系等的安排和布置,使现实世界在摄影机面前获得一种选择性的注视——它截取了永恒流動于时间中的事实片段;电影的拍摄成为勾连这些片段的方式。在银幕影像中,原有事实片段又以一种流动的方式呈现于观众面前。现实的时间之流在拍摄时被中断,而又在影像中重组。电影由此迸发出诗性之美——是温和,也是暴力;是优美,也是崇高。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诗性美就是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所说的艺术的存在方式,“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9〕。
二、空间调度中的演员调度
“电影空间的本身形态是一个前窄后宽的,向远方扩展的三角形”〔10〕,包含再现空间和构成空间。再现空间借摄影机的记录功能,逼真地再现某一真实场景或写意场景〔11〕;构成空间借蒙太奇手段将零散拍摄的一系列个别场景组合成一个统一的完整场面,暗示出纵深空间〔11〕。电影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不同体现于自身的层次与深度,并使导演在演员调度方面具有灵活性与差异性。演员调度在画内空间中涵盖前后、左右、上下三个向度。导演利用演员的位置变化进行空间调度,多拥有较大的自由创作空间。塔尔可夫斯基善于利用演员在不同空间(多为再现空间)中的不同位置关系来揭示人物关系或主题,演员调度控制着观影节奏,而节奏的控制也是将流动的时间赋予静止和恒久的方式之一。
1.“潜行者”斯塔凯尔与妻子的二人调度
在《潜行者》开场第一个场景中,导演仅用8个镜头的空间调度就完美地为观众呈现了“潜行者”斯塔凯尔与妻子的关系。其中,镜头3~镜头6关于斯塔凯尔与妻子空间关系的调度尤为出色。
在镜头3(见图1,运动镜头)中,镜头先由全景跟随男人的运动向右摇,摇至窗户:一是交代了镜头2中左侧光线的来源,二是提示画面左侧画外空间的存在。男人出画,从室内空间离开并掩门:此时男人所在空间与孩子、妻子所在空间分隔。该镜头中男人和女人并未同时出现在画面中,男人离开室内空间后,隔着门框的景深镜头的后景处显示妻子坐起:这暗示二人的隔阂,也为接下来的争吵作铺垫。男人关门后出画,切到下一镜头。镜头4(图略)是固定机位的全景,男人从画右向左移动,点火打开水阀洗漱,头顶的电灯从微闪到闪,男人
回头看到女人。镜头5(图略)先是中景,妻子手拿
东西对男人说话,妻子向前走成特写,边走边说:这里导演有意将男人和妻子分处两个独立空间,并不用全景交代二人的空间关系。镜头6(见图2,运动镜头)里,近景观照下的男人低头漱口,抬头看女人说话。男人向右侧走动,摄影机跟随男人由画左摇向画右;同样是特写观照下的女人从左下角入画,走到男人旁边站住,说话;男人端着盘子,边吃边与女人交谈,两人目光无任何交汇,各自望向不同方向;男人转身背对摄影机,女人遂靠在男人背上哀怨;男人欲走,女人从男人手中抢夺手表,二人争执。此时摄影机顺势向右微摇,向后微微拉开,男人从画面左侧出画,女人哭泣。镜头5和镜头6中,妻子主动闯入男人的空间,一番交锋后,男人从二人空间中逃离,并与妻子再次处于两个空间。endprint
这组镜头的空间调度暗示出“潜行者”斯塔凯尔与妻子之间的隔阂:妻子是斯塔凯尔去往“区”探寻精神世界的阻碍,但男人最终摆脱阻碍,义无反顾地奔向目的地(可视为对现实的反抗)。片尾,妻子来酒吧找从“区”中返回的斯塔凯尔,导演先把斯塔凯尔和妻子分置两个空间;之后,斯塔凯尔主动走进妻子所处的空间:在此段落镜头中,一家三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共处一个空间。这暗示斯塔凯尔在心理上对家人的理解和接受,并暗含对现实的屈服,照应开头对家人的逃离、对现实的抗争。
2.“潜行者”斯塔凯尔、教授、作家的三人调度
导演在片中对“潜行者”斯塔凯尔、教授、作家三人的画面空间关系进行了冷静、客观的艺术处理。三人的多次空间调度都以三角形的不无象征意义的构图方式存在。若将教授看作追求真理的自然科学的意指,那作家则意指追求自我意义的社会科学;而作为引导者,斯塔凯尔无疑指向游离于二者之外的“他者”。稳定的三角形状态象征三人所标识力量的平衡;在某种意义上,斯塔凯尔是这一平衡的维持者。故当作家试图脱离这一平衡关系独自前往“房间”时发生了意外——“区”的警告迫使作家回归三人空间,人物关系的平衡得以重构。教授走失并重聚后,三人对“区”的探索暂告一段落,并分置不同的空间小憩。斯塔凯尔昏昏睡去,而教授与作家则针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辩论。
在进入被称为“绞肉机”的恐怖管道时,作家被分割到一个独立的空间,他开始对更深层未知世界的独自探索。这一过程虽充满孤独、无助及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但其仍义无反顾地前行——这显然可被看作是对人类心灵深处潜意识和非理性欲望的探寻;对此未知领域,“理性”的教授的退缩也在情理之中,契合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的深层文化心理:“扭曲和异化的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技术文明与精神危机的两极分化下,形成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和冲突”〔12〕。对物质文明和理性的过度强调使得世界被规则与理性所占据,人类内心逐渐被理性所侵扰。在《潜行者》中,“区”被视为人类内心欲望和情感的隐喻与表征,进入“区”亦可看作是对理性侵扰的逃避。
三、空间调度中演员与摄影机之间的调度
贝拉·巴拉兹特别强调摄影机的创造性运用:“摄影机能提供新的表现方法,主要是因为它能自由移动,不仅时时给我们展示新的事物,而且还不断地变换角度和距离,所以才形成了电影的这种富有历史意义的新特点。”〔13〕他指出,“摇镜头这一特殊手法在所有电影表现手法中最受欢迎,它既可以使画面显得特别真实,而且能使观众在与摄影机一同移动的时候,产生身临其境感。”〔13〕其实,巴拉兹所阐释的这种摄影机的“自由移动”“摇镜头”,即摄影机的空间调度——主要体现于演员与摄影机空间关系的处理上。塔尔可夫斯基对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持保留态度,这其实是对“再现空间”与“构成空间”的认同倾向不同所致。“爱森斯坦关注的是画面的叙事性,即画面与画面之间的上下连接,他在画面中发现了意义的单向性,并将这种单向性的意义强烈地凸现出来。而塔尔可夫斯基则更重视画面本身的造型感,即画面意义的含混性、多向性和发散性。”〔14〕塔尔可夫斯基的这种理念在其充满“诗性内涵”〔15〕的演员与摄像机之间的调度上体现得较为充分。
《潜行者》在展现进入“区”之前的现实生活时,镜头运动以简单、缓慢的推、拉、摇、移和固定镜头为主——这也被用于主要人物在“区”以外的空间调度中。这种单调重复、小范围移動的摄影机调度暗示当时现实生活的枯燥无味,进而表现人在现实中所受到的种种压制与束缚。镜头在人物进入“区”后展现了一个开放的迷人的充满活力的自由空间,曾多次进入“区”的“潜行者”斯塔凯尔躺在草地上长舒了一口气——人获得自由的一种隐喻。此后,镜头运动自由、多变,并借与演员调度的完美结合实现了契合导演意旨的“诗性推理”。
在影片放映50分钟左右的一个段落镜头的场面调度中,镜头起幅为一辆废弃的汽车,前景是不知名的野花和锈迹斑斑的金属片;镜头缓慢前推,目之所及全是生机勃勃的绿草野花与灰暗锈蚀的金属之间强烈的视觉反差;镜头透过汽车门窗继续推进,斯塔凯尔入画,废弃的汽车变为前景,后景草地上堆满废弃的钢铁部件;随着镜头的继续前推,教授、作家先后入画,完成三人关系的构建,由汽车车窗形成新的方形画框;镜头推进停止,人物开始对话交流;当探索继续进行时,人物相继出画,随着镜头继续推进,后镜内容(一块块废弃坦克和装甲车的钢铁部件)逐渐清晰,成为画面的主导内容。导演通过不断变化着的画面空间,使画面内涵最终得以揭示:不仅通过对纵深空间的多层次展示完成其诗意叙事,也暗示出物质文明的产物在“区”这一特殊空间中毫无用处。镜头落幅对废弃装甲车和坦克的强调也是塔尔可夫斯基电影空间调度的特点——当观众觉得镜头的主要内容已经表达完毕时,导演又借镜头的进一步运动揭示新的题旨。如影片放映至65分钟19秒处,教授、作家和斯塔凯尔依次出画进入画外空间继续探索,此时镜头逐渐上摇,使原本不在画内的“房间”凸现出来,展示人物与“房间”之间的实际空间距离,借此从时空关系上进一步说明,即使目的地近在咫尺,也要怀着虔诚之心完成探寻、发现之旅。这一主要内容外的叠加意义使影片充满诗意,令人咀嚼、回味。
四、空间调度中的空间建构
用道具的布置形成画面内部构图是场面调度中电影空间创造的一种方式。“电影创作者常使用建筑的一部分来把人物的行动‘框起来,并以此赋予其额外意义。常用的建筑部分包括门、窗和镜子。”〔8〕《潜行者》中门、窗常被用来建构新的空间。
影片的第一场戏中,“潜行者”斯塔凯尔利用卧室的门将自己和家人分隔于两个空间,从后面的情节可以看出家人是其前往“区”追寻理想精神世界、赢取自我尊严的主要阻碍。“门既是入口也是出口,当然也是阻碍行动的潜在障碍。”〔8〕斯塔凯尔借掩门这样的举动来防止家人成为自己行动的障碍。显见,这种调度既合乎情理,也隐喻人物关系。
斯塔凯尔带领作家、教授进入“区”后,在展示废弃车窗的镜头中,导演利用车窗构成新的画框,并由人物的相继入画营造了新的空间。此时,画外更广阔的现实世界被车窗隔绝在“区”之外。此后,三人才算真正进入“区”的空间。在进入“区”的核心空间前,三人在一小房间内停留了一会儿,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此时摄影机被置于房外,借门框形成新的画框,画内空间相对狭小,仅能容下两三人。教授时而出离画框,被分割在新建构的狭小空间外,使新空间内的“潜行者”和作家位置极为突出。处于运动中的教授成了空间内流动的元素,使画内人物数量处于对比性的流动中。endprint
“潜行者”斯塔凯尔从“区”中归来回到酒吧后,其妻来此地找他。酒吧的门把酒吧内和酒吧外的空间分割开来,斯塔凯尔通过门走出酒吧(进入现实空间)。由酒吧空间走进现实家庭空间的过程,意味着人物在心理上对家人态度的转变及家庭关系在“爱”的统摄下于某种层面上的重建——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达成了某种无可奈何的流溢出淡淡哀伤情调的妥协。
五、空间调度中的空间象征
象征最初多被运用于文学和绘画。随着电影的发明和电影语言的演进,象征也逐渐作为电影创作者表情达意的手段而被广泛运用。在电影中,“一样东西被用来代表和意味着另一样东西,那么它就是一个象征。它代表的常常是一段感情、意义、传统或者其他相同的联想。”〔8〕如鸽子象征和平,飞鸟象征自由,狐狸象征狡猾,松树象征坚持与坚强,红色象征生命与激情等。这种具象与意象、意义的象征关系,赋予电影艺术以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的特性。克里斯蒂安·麦茨指出:“如果将电影的声画关系看作能指,其所表达的内容则为所指。”〔16〕通过符号的“外延的能指”和“外延的所指”构建“内涵的能指”,从而确立“内涵的所指”,即象征义。
电影空间既是叙事环境,也是主题的载体;既体现影片的视觉风格,也体现造型风格,故它具有很大的表现性和形成象征的可能性。塔尔可夫斯基在影片空间调度中,常通过对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处理来构建其特有的“能指”与“所指”、“外延”与“内涵”,揭示影片独特的空间象征意义。
《潜行者》在叙述日常真实生活时使用了黑白画面,背景多为后工业时代的铁路机车、火力发电场的巨大烟囱、破败的房屋、潮湿泥泞的道路,随处可见的工业管道和机器轰鸣的废弃厂房等。在虚幻迷离、充满象征意味的“区”中,影片使用彩色画面展现另一图景:举目望去尽是绿色的植被、不知名的野花、潺潺的溪流,以及远处被朝霞染红的天空,一切都显得温暖而宁静。通过黑白画面空间和彩色画面空间的强烈对比,暗示出当时苏联现实生活的压抑、晦暗、枯燥及物质文明的发展所导致的人性异化:人的情感和欲望被压抑,个人空间变得狭窄甚至完全失衡,人与人之间变得难以沟通。由此来看,片中关于人的现实生活空间的描写与存在主义相通,所以让-保罗·萨特也颇推崇塔尔可夫斯基的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区”这样一个彩色空间不正是主人公内心所向往的温暖、光明的美好生活吗?
当“潜行者”斯塔凯尔回到现实后,影像仍是黑白的画面空间,这寓示探寻的徒劳无功。“潜行者”回到了那个阴暗狭小的家中,仍然没能摆脱象征现实束缚、精神障碍的妻子和孩子,但导演为人们留下了希望和期盼。影片最后彩色的回归及孩子的“超现实”行动显示了现实空间中的“奇迹”,而这种奇迹在象征理想精神世界的“区”中却无法出现。这种显然充满期望的结尾映现出塔尔可夫斯基批判现实后人文关怀的一面,昭示着导演将美好的希望寄予了下一代,期盼能改变现状的奇迹在他们身上发生。对于“潜行者”斯塔凯尔,导演同样给予殷切的希望和同情,作为“区”的坚守者和其他人进入“区”的引导者,他将分别意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家和作家从黑白画面空间引至彩色画面空间。这象征着导演希望通过《潜行者》这部影片给被“异化的人”打开通往追寻内心向往的大门;当然,探寻“区”的过程也可视为塔尔可夫斯基通过影像所进行的自我救赎和对艺术信仰坚守的象征。
参考文献:〔1〕
Karl Barth,Church Dogmatics(Vol 1)〔C〕∥G.W.Bromiley T.F.Torrance,Trans.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the God.Edinburgh:T.﹠T.Clark,1975:349.
〔2〕李宝强,编译.七部半: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世界〔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348,351,355.
〔3〕李泳泉.仿佛梦境,仿佛倒影——我的私密的塔科夫斯基〔C〕∥安德烈·塔科夫斯基.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1,1.
〔4〕安德烈·塔科夫斯基.雕刻时光〔M〕.陈丽贵,李泳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3-64,20.
〔5〕李·R·波布克.电影的元素〔M〕.伍菡卿,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74.
〔6〕戴·波代尔.电影镜头:场面调度〔J〕.宫竺峰,译.世界电影,1984,(2):172-188.
〔7〕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M〕.郭青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9.
〔8〕尹鸿.当代电影艺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15,121,121,117.
〔9〕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85.
〔10〕叶明.关于电影的场面调度〔J〕.电影艺术,1963,(1):12-21.
〔11〕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170,170.
〔12〕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0.
〔13〕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37,142.
〔14〕黄文达.外国电影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27.
〔15〕黄文达.外国电影发展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0.
〔16〕克里斯蒂安·麦茨.电影符号学的若干问题〔C〕∥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383.
(责任编辑:杨珊)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