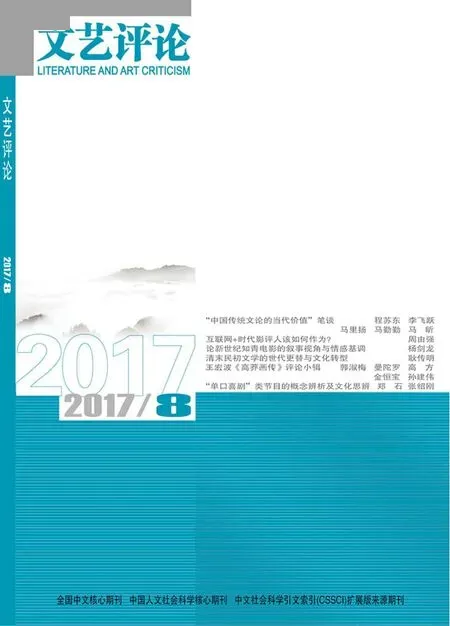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单口喜剧”类节目的概念辨析及文化思辨
2017-09-28张绍刚
○郑 石 张绍刚
“单口喜剧”类节目的概念辨析及文化思辨
○郑 石 张绍刚
喜剧的发展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从柏拉图开始,历史上每一个时期的哲学家、文化研究者等都对喜剧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思考。广播、电视的兴起使喜剧不再固守于舞台,而是走进了千家万户,互联网时代更是将喜剧的传播和创造进一步扩大。在诸多喜剧的类型之中,对“单口喜剧”的探讨一直相对沉寂,当大众依然认为这种表演形式仅是舞台之上的小众之好时,却不知电视和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单口喜剧的影子,其自身或变形而生的节目早已受到了广大受众的喜爱。当下,喜剧类节目的热度逐渐升温,作为其分支的单口喜剧类节目则必然需要重新审视,进而探究更为可能有效的创新。
一、“单口喜剧”的历史发展及概念辨析
“单口喜剧”翻译自英文“Stand-up Comedy”,也可被译为“独角喜剧”“立式喜剧”“站立喜剧”等。单口喜剧类节目在我国电视及网络上出现的频次较低、时间较晚,但一经播出,该类节目均受到了广泛的热议及关注。但受众对单口喜剧一直保持着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认为单口喜剧即是“脱口秀”(Talk Show),节目生产者也未对该节目类型进行有效地分类,大而化之地将其与脱口秀节目或中国传统曲艺单口相声等节目画上等号。其实,单口喜剧是一种独立的表演形式或曰节目类型,其自身有源自于历史、深植于文化的独特属性和含义。
单口喜剧发端于欧美,最早出现在18至19世纪英国的音乐厅中,二战之后,电视和广播的发迹给这种停留于舞台的表演形式带来了巨大冲击。直到20世纪70年代,音乐厅表演作为一种大众的娱乐形式逐渐式微,大量的单口喜剧演员开始转向电视和广播谋求发展。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开始逐步发展起单口喜剧表演模式。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早期的单口喜剧演员通常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俱乐部、酒吧、夜总会等场合演出,表演内容多围绕政治、种族和性等话题展开。时至20世纪70年代,单口喜剧演员开始向电视及电影领域拓展,诞生了《今夜秀》《周六夜现场》等单人喜剧电视节目。20世纪80年代之后,单口喜剧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占据一席之地,并衍生出许多崭新的节目形态,也逐渐成为深受美国观众喜爱的节目类型之一。
根据英国肯特大学艺术学院的奥利弗·道布尔(Oliver Double)的调查发现,用“单口”来定义一种喜剧表演模式源自美国(自1948年出现之后,该词在20世纪50年代的商业媒体中得以通用)[1],而英国的商业媒体直到10年后才开始出现“单口”这一词语。可见,美国最早将这一表演形式进行命名,实践上也占据优势。经过长久的探索,美国的电视单口喜剧节目不断得以完善,并成为了其他国家争先效仿的样本。
我国最早开始电视单口喜剧节目生产应追溯至1990年的香港,演员黄子华将这一表演形式引入华人社会,并为其取名为“栋笃笑”,其后香港主持人、导演林海峰将其称为“是但噏”。我国大陆地区对该类节目的发展相对较晚,其中比较知名的节目有《壹周立波秀》《今晚80后脱口秀》《吐槽大会》等。
单口喜剧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其发端于剧场,繁荣于电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或曰节目类型,其形态具有以下特征:在传统单口喜剧形式中,演员在剧场中直面观众进行表演,在其长时间的发展中,它不再固守于表演者在实体空间点对面的表演形式,而是走向电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作为一种节目类型,“一个人、一支麦”为其基本形式,笑话与段子为其表演内容,引人发笑为其终极目的,只有具备以上三种基本要素,才能真正构成单口喜剧节目形态,这也是它其区别于脱口秀、单口相声和单人脱口秀的节目的根本所在。
首先,脱口秀是单口喜剧的一种衍生形态。早期的脱口秀发迹于广播电台,自二战之后逐渐走向电视媒介,1953年,史蒂夫·艾伦(Steve Allen)在NBC主持《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首次开创了“六段式”(six-piece format)脱口秀模式,即开场段子、喜剧环节、嘉宾访谈、音乐嘉宾、乐队伴奏、观众互动。此后,脱口秀便逐渐在此基础上繁荣发展。脱口秀打破了单口喜剧中单人表演的核心形态,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嘉宾访谈、喜剧表演等诸多环节,随后又衍生出了访谈类、对话类等节目形态。可以说,脱口秀在某些程度上依然具备单口喜剧的特性,但在六十余年的发展中,脱口秀已经逐渐与单口喜剧相分离,并逐步固定为一种独特的节目模式。
其次,我国的传统曲艺单口相声也与欧美的单口喜剧有着本质的区别。单口相声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与单口喜剧有相似之处,即一人表演且置景单一,但细微之处仍见巨大差别。舞台构成上,单口相声需要一张覆盖帷布的桌子,表演者始终站立其后,桌上摆放醒木、折扇、手帕等道具,这些道具均是辅助表演的重要构成要素,且舞台不需要灯光的配合。但单口喜剧则完全没有对道具的要求,“一个人、一支麦”便可以完成对演出的需求,有时仅需辅以一把椅子,在舞台上则需要一束追光即可,但这些也都不构成必须要素,且表演者可以在舞台上随意走动甚至走下舞台与观众交流。叙事内容上,单口相声要求表演者以“说唱”的方式叙述事件,叙事结构严密,多以单一故事讲述为主,并在叙事情境中呈现冲突和矛盾进而展现“包袱”。而单口喜剧表演者则多进行主观叙述,在讲述中表达自我态度和独立观点,叙事结构不需完全严密,叙事段落之间无需具备关联性。
第三,单口喜剧也不同于单人脱口秀。单人脱口秀节目多以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其讲述者或评论者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不再具备表演性质。该类节目虽然保留了“一个人、一支麦”的形式,但就其观念来说,该类节目以观点表达为主体,不再以“引人发笑”为终极目标,完全区别于单口喜剧节目的内核和实质。
二、“单口喜剧”类节目的文化思辨
深植于西方文化的单口喜剧,其内在属性无不深刻折射出西方喜剧思想的文化传统。西方的喜剧思想可追溯至古希腊祭祀酒神的民间滑稽剧,其中大多是关于对政治和社会的讽刺,民众广泛参与、畅所欲言。尼采将古希腊的喜剧精神归结为一种酒神精神的传统,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到:“在酒神颂歌里,人受到鼓舞,最高度地调动自己的一切象征能力;某些前所未有的感受,如摩耶面纱的揭除,族类创造力乃至大自然创造力的合为一体,急于得到表达。”[2]尼采还在《偶像的黄昏》中说到:“在酒神状态中,却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于是情绪系统一下子调动了它的全部表现手段和扮演、模仿、变容、变化的能力,所有各种表情和做戏本领一齐动员。”[3]在酒神精神的感召下,人们打破了日常的伦理禁忌、道德规范,完全释放本我的冲动,回归到自然之质。可以说,古希腊喜剧就是酒神精神的象征和外化体现,西方各个国家的狂欢节,以及不断发展演变而来的喜剧表演形式均受到了该种精神和传统的影响。单口喜剧的发展虽然受到了来自社会、文化等语境的话语规制,不断舍弃了酒神精神狂放的外衣,但就其表演形式、表演内容及表演观念来看,却依然内含着酒神精神的力量,秉持着传统的喜剧遗风,比如:公共空间内的狂欢、打破等级秩序的大众讨论、自我观点的表达和本我欲望的释放等,而这些在当下依然展现着独特的文化活力和价值意义。
第一,就表演内容而言,单口喜剧使得私人生活话题公共化、社会化。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公共人的衰落》中认为,“西方关于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观念之一就是将社会本身当做戏台……人间戏台的各种形象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演练的图像。这种演练是一种表演的艺术,演练这种艺术的人是在扮演‘角色’”[4]。单口喜剧表演发生在剧场、舞台或演播室内,但其表演内容的基础和背景却是更为广大的公众与个体所处的生存空间。就西方的单口喜剧传统来说,政治、种族、性等均是单口喜剧演员所涉猎的话题,在某种技巧性的创作中,对这些话题观点进行主观地、幽默地表达,技巧的核心即在于不吝惜将私人话题展现,并私人生活与公众经验相融合。此时,单口喜剧的表演者是在“人间戏台”之上扮演着展现人间故事的讲述者之“角色”。理查德·桑内特还认为:“其他将人间的事情当做喜剧的作家也持有这种信念,他们认为从人类的行为出发,既无法认识到人的本性,也不能给道德下什么确凿的定义。”于是乎,在一种“角色”扮演的名义之下,表演者无需讳言对社会、文化、他人乃至禁忌话题的观点。表演者从自身出发,讲述发生在自身或假设发生在自身的故事,将这些私人性的话题公之于众,“人间戏台”的其他演员——广大的观众们便可以在其中得到某种满足与自得,从此该种话题便揭除了神秘和禁忌的外衣,对内心隐秘的压抑得到了释放。以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对脱口秀的观点来看,“它们使不可谈论的变得可以谈论,使让人感到羞耻的东西变得体面起来,并将丑陋的个人隐私变成引以为荣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成了去除妖魔的仪式——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仪式”[5]。
第二,单口喜剧类节目中蕴含着源自大众的抵抗性力量。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认为,“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在社会控制之外始终存在着大众文化的某种因素,它避开了或对抗着霸权力量”[6]。大众作为精英文化或霸权文化的从属者,似乎一直以来都在被动接受着来自上层文化的规训,自社会地位不均等的关系之中,大众无法在主流/高雅文化栖居的媒介之上建构出其自身认同的文化资源。但单口喜剧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其表演形式中却蕴含了大量的抵抗精神,试图建立出一套关于大众接受的快乐文本。约翰·菲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的观点,准确地说是关于大众“快感”生成的观点中隐匿着巴赫金“狂欢”理论的思想,“在狂欢仪式上,等级制完全被打破,插科打诨的语言、俯就的态度和粗鄙的风尚主导了所有诙谐的游戏”[7]。大众广泛参与的“狂欢”仪式,无需顾忌主导/从属、上层/下层、官方/民间的等级制度,而是在打破一切的观念之中,用游戏、冒犯乃至释放压抑的话语来制造快乐。单口喜剧中沿袭了这一传统,表演者通过讽刺、揶揄的语言将精英/霸权文化以及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传统价值观念中的弊病、丑陋适当表达,即使是转瞬即逝或有所限制,但依然能在其中制造出符合大众心理诉求的抵抗,并制造出了社会性的快乐。
第三,单口喜剧类节目具有自觉、自省的批判精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一切的大众文化都趋于一致。依靠现代科技手段生产出的文化产品具有同质性和可预见性的特点,而这种类似工业体系的生产方式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服务,而非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目及我们当下的媒介文化环境,文化产品的生产已经产业化和模式化——从风格到形式,从整体到局部均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特点。文化被“物化”为了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所带来的影响则是大众对社会和文化的顺从。单口喜剧则不同,它释放了文化所应具有的创造力和革命性。单口喜剧删繁就简,完全舍弃形式上的修饰,将演员的表演放置于焦点。从其历史传统来看,单口喜剧不讳言、不逃避社会和文化的公共话题,表演者个人观点在公共空间内的表达彰显了一种自觉的意识,即拒绝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的询唤,以此唤起了观众的思考。另外,意识形态/精英文化所控制的媒介在文化工业体系下所建构出的世界越发地蒙蔽大众的意识和判断,迷糊了幻象和现实的界限,并强迫大众接受和认同媒介上的世界即是现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单口喜剧的快乐文本似乎并不纯粹,其中夹杂着对文化工业体系下所建构出来的世界的自省式的批判,在表演中不断解构其建立的幻象和话语权,将其自身拉下“媒介神坛”的荒谬神话。正如《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所提到的,“艺术越是把与其水火不容的生活严肃地表达出来,就越会发展成它的反题,即生活的严肃性;艺术越是依据自身法则致力于自身的全面发展,就越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减轻它的负担”[8]。单口喜剧幽默言辞的外衣之下是犀利的观点,它利用其独特的表演方式,将客观、严肃的生活适当还原,否定将生活现实等同于文化建构出的形象或曰幻象,让受众在表演者的嬉笑怒骂间保持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驯化以及媒介建构的世界的理性思考。
三、冒犯:当下我国“单口喜剧”类节目的一种文化观念
就我国的具体语境而言,为数不多的“单口喜剧”类节目虽诞生较晚,但《壹周立波秀》《今晚80后脱口秀》等节目在电视上一经播出便全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当前网络上“现象级”的单口喜剧类节目——《吐槽大会》,则在短短的3个月内收获了近十五亿次的点播量,其中单期的最高播放量达到了2.1亿次。可见,时下单口喜剧类节目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受众需求,而其自身也释放着崭新的文化意义。现如今我国的媒介环境,多元文化交融并举,异次元、二次元文化异军突起,每一种文化群体都亟待发声,谋求其生存的空间,确立文化主体。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是推动着主流/非主流、官方/民间的两个舆论场的形成,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一个群言时代已经到来。
大到媒介文化,小到媒介作品都在寻求着突破和改变。笔者认为,当下文化,具体到“单口喜剧”节目中,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观念是“冒犯”精神,而这也构成了当下大众文化审美转向的一个维度。
冒犯是一系列言语和行为的集合,如:批评、詈骂、嘲讽、憎恶、贬损、威胁等。依据不同的语境、心态,冒犯语言和行为不仅是负面情绪的宣泄,有时也具有情感的表达、身份的认同及道德的评判等功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里,这些言语和行为所包含的攻击性和反叛性给统治阶级或曰主流/官方意识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而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群体企图为大众文化施加规训,尤其在以“礼治”“德治”“人治”的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中国文化的古典语境中,来自底层、民间的“冒犯”更需被禁止。然而逃逸的、被压抑的大众文化的冒犯力量却一直活跃,其深埋的抵抗精神时而彰显于身体,时而彰显于语言。冒犯是一种对抗性的体现,它将丑/美、私人/公众、欲望/伦理的矛盾集中展现,其出发点是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传统价值观念规训的怀疑,其目的是对自身文化和身份意识的捍卫。
诚如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所说,“大众文化制造了从属性的意义,那是从属者的意义,其中涵括的快乐就是抵制、规避或冒犯支配力量所提出的意义的快乐”[9]。可见,从大众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冒犯是诞生快感的来源之一,是大众文化突破主流文化以维护自身地位和霸权地位的安全阀门的快感。具体到“单口喜剧”类节目而言,冒犯精神作为其内核观念则在更大程度上激活了大众文化的活跃。在单口喜剧类节目中,传统的发言人/言论者的形象演变为表演者,聆听者/围观者的形象则变为了参与者,个人崇拜被消解,发声者的理性、权威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表演者用言语来嘲讽、贬损和戏弄社会及文化现象,而观众也可用嘘声、笑声及骂声来表达对表演者及其观点的评价,行为和言语为冒犯赋形。而在网络时代,民众参与单口喜剧的渠道变得更加丰富,民间舆论场的话语也更加多元。以《吐槽大会》为例,从主持人到嘉宾的表演以及“弹幕”的使用时刻彰显着冒犯的精神。首先,主持人和嘉宾都在单人表演时间内,用调侃的语言冒犯各自身上的槽点。该种冒犯不是一种语言的恶意攻击,而是一种自我态度的彰显。戏谑的语言使得每一位舞台之上的公众人物、明星偶像褪去神秘的光环,言辞中不复以往的夸赞和逢迎,而是将他们还原成大众一员,以俯就的姿态看待他们的过往人生,将高举的明星生活和工作降维成全民性、平等性的公众话题,包裹以幽默的外衣并公之于众。这类似于西方传统的狂欢仪式上对“国王加冕”仪式的戏仿,仪式的最后是给国王“脱冕”:国王的帝服被扒下、皇冠被摘掉,民众在这种具有相对性的象征仪式中获得快乐。其次,弹幕的使用让观众被压抑的快乐得到充分释放。据统计,《吐槽大会》的有效弹幕数近六千万条,可见这是一种民间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场域,观众以发弹幕的形式参与到节目中,不仅在发表言论、表达观点,也在无形中构成了节目的生产要素。时而冒犯性的话语激活了观众参与和观看的快感,也成为了个体与大众之间讨论、交流的切入点,在节目播放的同时,亿万观众在网络上自发聚合,围绕着节目中的嘉宾表现、段子笑话各抒己见,促成了一种虚拟的“狂欢仪式”。
就外在形式而言,单口喜剧类似于传统部落中的“游吟诗人”的演唱,即叙述与交流还原成讲述者和听众之间的二元关系的最初始状态。约翰·菲斯克和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在《阅读电视》中提到,在一个社区中,电视(笔者认为,此处“电视”这一相对的小概念可扩展至“媒介”的大概念)类似于一种“吟游诗人”的功能,不过该种“吟游诗人”的叙事形态在单口喜剧中得以变形,传统的史诗颂歌变成了笑话和段子,占据主导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程度上被表演者消解和解构,相同的是,表演者的个人形象和魅力作为叙述的一种原初动力得以保留并持续扩大。但无论如何变化,单口喜剧与“游吟诗人”演唱一样,都将回归和保留在最简单、最传统的叙事场景、模式之中,而其魅力也恰恰彰显于此。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
[1]Oliver Double.The origin of the term stand-up comedy[J],Comedy Studies,2017.
[2][3]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第320页。
[4]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2页。
[5]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6页。
[6]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7]汪安民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8]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9]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