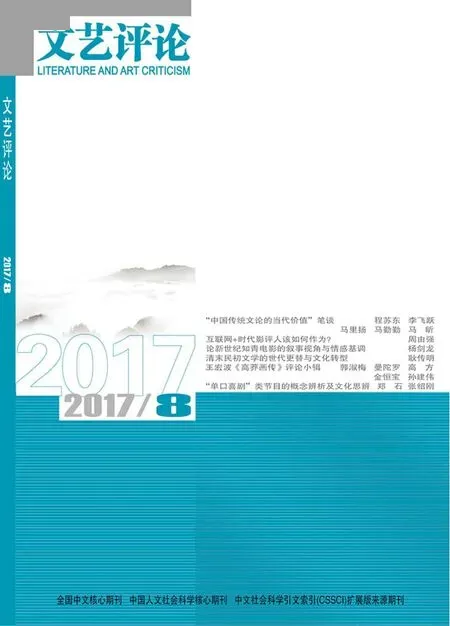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上官体”生成原因探析
2017-09-28○李巍
○李 巍
“上官体”生成原因探析
○李 巍
“上官体”是唐代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风格称号。上官仪在贞观时期就已崭露头角,“绮错婉媚”之风已基本形成,为何“上官体”在高宗朝才风靡一时,且对龙朔诗坛的进程及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研究“上官体”的生成原因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地位之贵显是“上官体”形成的外因
上官仪在贞观初年及第,开始入朝为官,但是一直官位平平。《旧唐书·上官仪传》云:“贞观初,杨仁恭为都督,深礼待之。举进士。太宗闻其名,召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时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常预焉。俄又预撰《晋书》成,转起居郎,加级赐帛。”[1]
贞观朝上官仪的官职并未有大的提升,由从六品下之弘文馆直学士升为从六品上之秘书郎,后转官起居郎也只是从六品上,升迁调动不大。弘文馆学士深受礼待,“给以五品珍膳”[2],太宗还经常让上官仪“视草”,甚至“依靠他润饰自己粗糙的诗稿”[3],作为皇帝身边的贴身文人,可谓十分荣耀,但由于官低位卑,“显而未贵”,并无实权。
按照闻一多先生的说法,上官仪生于608年,[4]贞观元年(627年)20岁,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已42岁,人生的黄金期都在贞观时期度过,其诗才已经展露头角,且现存诗作中作于贞观时期的诗作占了很大的比例,“绮错婉媚”之诗风基本形成。他虽然也很见重于太宗,但并未引起一场诗风新变,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上官体”的形成及在诗坛上产生影响是在高宗朝他的地位显贵之后。关于此事文献多有记载:
《旧唐书·上官仪传》载:“高宗嗣位,迁秘书少监。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如故。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5]
《新唐书·上官仪传》亦载:“仪工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显,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6]
《唐诗纪事》卷六亦云:“工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人效之,曰‘上官体’。”[7]
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上官体”之形成是在他“贵显”之后,也即在龙朔至麟德元年(661年—664年)之时或之后。为何上官仪在高宗时地位陡然“贵显”,2013年8月至9月,上官昭容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团。《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简称《墓志》)详细记载了上官仪所历官阶的基本情况:“皇朝晋府参军、东阁祭酒、弘文馆学士、给事中、太子洗马、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赠中书令、秦州都督、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8]除了“晋府参军、东阁祭酒”外两《唐书》本传都有记载。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上官仪与高宗李治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高宗即位前被封为晋王,而上官仪曾担任过“晋府参军”,也就是说上官仪在太宗朝太子之争中属于李治一党(按:太宗朝太子之争主要有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李治即位之后重用、擢拔上官仪是理所当然之事。
正由于唐高宗即位后上官仪地位之“贵显”,人们纷纷效仿其体,方被称为“上官体”。在他没显贵之前,虽然“绮错婉媚”风格基本形成,只不过人们没有或者很少仿效而已,可见,上官仪之“贵显”是其诗体形成的外因。
二、“上之所好”是“上官体”形成的动因
高宗即位后仍然继续沿袭太宗朝制定的各项政策,加之贞观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等共同辅政,国家出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史称“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9]。更为重要的是平定高丽,大破西突厥,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家版图为唐代最大。为了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高宗携武后同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天勒碑而还。
高宗在永徽年间有“贞观遗风”,由于贞观熏旧遗老的存在,他的政绩显得相对暗淡,随着他们的离去,偶然因素继承皇位的李治迫切需要文人对其治绩进行讴歌颂扬,以彰显其功绩,进而向世人证明自己皇位的合理性。永徽六年高宗不顾大臣反对而极力废王立武的事件,就是以此彰显自己至高无上权威的体现。另外,从永徽六年之后一系列的乐舞制定中也可看出高宗的喜颂好谀心理。
《旧唐书·音乐志一》载:“显庆元年正月,改《破阵乐舞》为《神功破阵乐》。”[10]
同卷又载:“(显庆)六年三月,上欲伐辽,于屯营教舞,召李义府任雅相、许敬宗、许圉师、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于阗王伏阇、上官仪等,赴洛城门观乐。乐名《一戎大定乐》。”[11]
《破阵乐》前加“神功”二字,名异实同,以彰显自己扫除寰宇、一定天下的卓越功勋。《一戎大定乐》又名《大定乐》,取名大定,象征着平定高丽后天下也会随之大定。此乐是由太宗时期的《破阵乐》踵事增华而成,人数由太宗时期的120人增至140人,阵势更加雄壮,声势更加浩大,显而易见,高宗整改阵容是炫耀自己的赫赫声威,彰显自己的功德。
“永徽之治”使高宗产生喜颂好谀心理。正所谓“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帝王喜好是文学风尚的方向标,直接促成文学风气的演变。因此上官仪探索诗艺、提高诗技有了动力,文人们学习与提高诗技也有了途径与方法,以至一时间追攀摹仿,形成一种精研的风气,一种创作的高峰。
三、类书之编纂是“上官体”形成的契机
“上官体”之形成与当时的文化建设事业相关。史载:“龙朔元年,命中书令、太子宾客许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等于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制赐物三万段,敬宗已下加级、赐帛有差。”[12]这部书凡3年方修成,“(龙朔)三年十月二日,皇太子弘遣司玄太常伯窦德玄,进所撰《瑶山玉彩》五百卷上之,诏藏书府”[13]。
《琼山玉彩》选择的标准是采摘“古今文集”中的“英词丽句”,编纂的体例是“以类相从”,纂集的目的不外乎创作时便于查找,以提高诗艺水平。除了《琼山玉彩》外,上官仪还参与过《芳林要览》等大型类书的编纂活动,涵咏其间,精研不辍,一定收获颇多。上官仪在参撰的《芳林要览》序中云:
且文之为体也,必当词与质相经,文与声相会。词义不畅,则情旨不宣;文理不清,则声节不亮。诗人因声以缉韵,沿旨以制词,理乱之所由,风雅之攸在。固不可以孤音绝唱,写流遁于胸怀;弃徵捐商,混妍蚩于耳目。[14]
《芳邻要览序》中明确了上官仪的纂集标准,也是他倡导的作诗标准即要注重声律,靠声律来使诗作音韵协调。参与修撰的学士们在编纂期间和闲暇之余向上官仪请教作诗的技巧方法,上官仪一方面为学士们请教的促使,一方面也是长期编纂类书有所领悟,加之自己创作经验,总结出一整套的作诗技巧和方法,在长期的互动交流中,上官仪的诗学理论逐渐被学士们所接受并运用到实际创作之中,“上官体”逐渐形成并产生很大的影响。
深受上官仪影响的一批人,或者说追捧上官仪的一批人,如元万顷、郭正一等,他们近体诗律化程度很高,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上官体的诗歌理论的可操作性及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上官仪诗歌理论与创作脱节的原因是由于诗歌多创作于贞观时期,而偶对的总结是在高宗朝编辑大型类书的过程中在已有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以往的佳言名句提炼升华而成的。其诗作的律化程度没有后学诗人高是可以理解或者说是正常的。
四、偶对之总结是“上官体”形成的关键
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外,“上官体”形成更重要的原因是上官仪总结了一整套简明扼要、行之有效的作诗方法,使后学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使诗艺有较大的提升。上官仪的诗学著作早已散佚,《宋四库阙书目·文史类》载有上官仪《笔花九梁》二卷,日本小西甚一认为此即《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所录之《笔札华梁》二卷,且古字“花”与“华”同字,“九”与“扎”乃书写讹误,二书应为同一本书。王梦鸥先生在其《初唐诗学著述考》中也认为伪题魏文帝《诗格》,实即《笔札华梁》之删节本。[15]王利器先生和卢盛江先生在整理《文镜秘府论》中也认为《笔札华梁》是上官仪所著,此从其说。
虽然《笔札华梁》已经失传,但其相关理论散见于《文镜秘府论》所引各书中。上官仪的诗学理论表现在声病理论上提出“八病”之说,表达诗歌情感意绪的“八阶”“六志”之说,更重要的是提出对偶理论的“六对”“八对”之说。前两者学人论述较为详备,此就对偶理论展开论说。
南齐周颙发明了“四声”,沈约等人据此提出讲求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律的诗韵要求,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作家创作了大量“永明体”诗歌。他们的诗歌理论主要侧重于韵律。齐梁之际,刘勰的《文心雕龙·丽辞》从对偶方面探索诗艺:“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16]不但总结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种方式和其中的难易优劣,且强调“自然成对”。上官仪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诗歌的属对理论进行了拓展和延伸,提出“六对”“八对”之说。《诗人玉屑》卷七《属对》引《诗苑类格》云:
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是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17]
“六对”是从最基本的字词之间的对偶来阐释对属理论,是初学者入学之门径。前两对“正名对”“同类对”是从词义角度进行例说:“正名对”是指类似于“天地日月”之类的专有名词,侧重于单词之对;“同类对”即同一属类事物之对,较“正名对”多了修饰成分,因此由单字对扩而为词对,且“花”“草”和“叶”“芽”又两两相对。中间三对主要从语音的角度例说:“连珠对”从字音的角度两字相同连绵成对,“双声对”“叠韵对”分别从双声和叠韵的角度连词成对。
最后“双拟对”的例句“春树秋池”,模棱两可,似乎不知所云。《文镜秘府论》有诗证为我们作了注解:“春树春花,秋池秋日;琴命清琴,酒追佳酒;思君念君,千处万处。”[18]可见“双拟对”是一句之中同一个字间隔出现,八对中也有“双拟对”,其例句云“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很显然是一句之中隔字相对。“双拟对”是从侧重结构的角度阐释为对的方式。
“八对”是将“六对”中的基本字词对法运用到句联之中,对“六对”理论进行演绎和延伸,有所提高和深化。“的名对”和“异类对”是从词义的角度进行阐释。“的名对”例句“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送”“迎”和“去”“来”都是反对,且是动作方向对,“酒”与“琴”是宽泛的同类对,“东南”与“西北”是方位名词两两相对,是正名对。“的名对”是将“六对”中的“正名对”和“同类对”进行简单的应用,是作诗最简单的构句之法。“异类对”则在此基础上有所变化和延伸。例句“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风”与“虫”是不同属性事物的名词对,“织”与“穿”是不同的动作对,“池间”与“草上”是不同位置的方位名词对,“树”与“文”更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之名词对,上下句中都属于不同类属的词义对,构成两联的异类特点,造成迥异之感。“双声对”和“叠韵对”是从语音的角度构句,与“六对”分类一致,但是内涵有所差别,“六对”是一句之对,此是一联之对,也即将双声、叠韵在具体的诗句中进行运用。“连绵对”和“双拟对”是从结构的角度构句,但有所差别,前两对也可以说是反复对,一联之中某个字反复出现,只不过出现的位置不同而已。“连绵对”是同一个词连续出现,而“双拟对”是同一个词间隔出现。“回文对”和“隔句对”虽然也是从结构的角度构句,但是突破了两句之间同位相对的简单模式,上升到句式的变化,是从结构角度对句的变式,但又不是简单的结构变化,还考虑到句间语义之衔接,意脉之相承,情感之升华,特别是“隔句对”的示例可谓是一首完整的五言绝句,不但有相同“复”字的隔句相对,还有“夜夜”“朝朝”不同联绵词的隔句相对。在意脉上一脉相承,将相思相盼相顾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也称得上闺怨诗的上乘之作。
“六对”“八对”由词到句,由联到篇,由浅入深,是一个简单易行的作诗范式,不但对初学者来说是入门之法,对于有一定基础的人来说也是提高诗艺行之有效的法则。
另外,这“六对”“八对”并不是只考虑到语音、语义、结构等方面词句的对应,而且在音律上也很讲究,每种例对都力求做到平仄相应。“六对”中“花草叶芽”是平仄仄平;“萧萧赫赫”是平平仄仄;“黄槐绿柳”是平平仄仄;“彷徨放旷”是平平仄仄;唯独“春树秋池”是平仄平平,平仄不是特别严格,但是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做到了平仄相对。
“八对”中“的名对”是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平,除第三个字外严格相对;“异类对”是平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除一二字外严格对仗;“回文对”是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除第三字之外严格对仗;“隔句对”是平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平平平仄平。上官仪总结的声律规律成为作诗者遵守的规范,为近体诗的定型铺平了道路。
“六对”“八对”不但总结如何炼词成句,而且在调声上也讲求平仄相应、清浊相对、缓急相异,使一句一联至四句乃至全篇词义相对、韵律和谐。上官仪总结的作诗范式简要但不简省,简易但不简略,简便但不简约,“六对”“八对”对属范式的理论和范式的提出,对初学者来说不但直接而且有效,如登云之梯,不但平缓而且入云,成为作诗之不二法门,对推广、普及、提高近体诗有很大裨益。
要之,与高宗的特殊关系使上官仪官位日显,为“上官体”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高宗武后的喜尚颂美心理,使上官体研究诗艺有了动力;《瑶山玉彩》等大型类书的编纂为上官仪精研诗艺提供了契机;上官仪“绮错婉媚”诗风创作实践和一整套作诗的理论和技巧的总结是“上官体”形成的关键。龙朔文士为了能使自己诗艺大增,势必对上官仪的诗歌及其理论心琢手摹,希冀早日“成才”,加之上官仪的理论和技巧简单易行,这些文人更是将之奉为圭臬,对其人大加尊奉,对其诗作奉为“标杆”,他的诗歌理论成为作诗之不二法门,广为普及流传。因此“上官体”风靡一时,他们学诗之目的并非修身养性,更非个人单纯的爱好,而是为了巴结逢迎,为了讨好献媚,为了最终身显位高,为了在政治的舞台上有其光彩耀眼的时刻。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1][5][10][11][12]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3页,第2743页,第1046页,第1047页,第2828-2829页。
[2]吴兢编著《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5页。
[3][美]斯蒂芬·欧文著《初唐诗》[M],贾晋华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4]闻一多《唐诗大系》[A],《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6]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35页。
[7]计有功撰《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73页。
[8]李明、耿志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J],《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
[9]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70-6071页。
[13]王溥撰《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年版,第657页。
[14][18][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 1582 页,第707页。
[15]王梦鸥《有关唐代新体诗成立的两本残书》[A],《古典文学新探》[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3-244页。
[16]刘勰著《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4页。
[17]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9页。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青年项目“中国唐前天人思维叙事模式研究”(编号:16ZWC02),哈尔滨商业大学青年创新人才支持项目(编号:2016QN0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