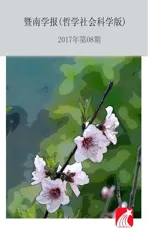“赠柳”词与汪懋麟的词事追求
——兼论王士禛词坛影响之另一面
2017-09-12戴健
戴 健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200)
“赠柳”词与汪懋麟的词事追求——兼论王士禛词坛影响之另一面
戴 健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200)
题赠柳敬亭的《贺新郎》、《沁园春》两词,是汪懋麟康熙九年的代表作。它们表达了词人对柳敬亭的致敬之情、劝谏之意,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同时也是其稼轩词风确立的标志,曾得到曹尔堪、周在浚等并世名家的唱和与肯定。“赠柳”之作不仅显示出了汪懋麟的文学个性——在“评柳”的问题上敢于与师相左,而且反映出其词学创作姿态之积极,终使其成为广陵词坛“后王士禛时代”的代表作家。但自康熙十五年《锦瑟词》刊刻出版后,汪懋麟即较少涉足填词,在“诗”与“词”的文体抉择中最终淡出了后一领域。这既是其师王士禛“避词”态度长期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王氏神韵诗论成为主流话语后影响力所及的具体表现。
汪懋麟; “赠柳”; 柳敬亭; 《锦瑟词》; 王士禛; 广陵词坛
汪懋麟(1639—1689),字季甪,号蛟门,扬州府江都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九年正月授官,历任内阁中书、刑部主事,曾入史馆修纂明史,二十三年因蜚语罢官,此后家居。汪氏一生居止以扬州与京城为主,词坛影响亦与此关联密切:既是广陵词坛的后起之秀,又是京师词坛的主将之一,词事追求颇能反映出这一时期南北词坛的风尚变迁,以及文士心态的微妙变化。同时,其师王士禛对词事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对汪懋麟的文学选择亦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其“赠柳”词作为考察切入点,原因有二:一是作为代表作,它们足以反映汪氏的词学成就,如严迪昌先生曾在《清词史》中评曰,“(汪氏)《贺新郎·赠柳敬亭和曹升六韵》、《沁园春·再赠敬亭和升六韵》等都属《锦瑟》一集中的力作”;二是作为唱和之作,它们与当时之词坛有深广联系,解读意蕴丰富。
一、“赠柳”意旨
“赠柳”即题赠柳敬亭之作。柳敬亭是明末清初著名说书家,因说书技艺精湛、经历奇崛而大受文士追捧。尤其是其曾入幕左良玉军中、见证南明党争与覆亡的经历,在易代之变中具有“故明记忆”的象征意义,故汉族文士多与其交往。顺康间,“赠柳”之作多不胜数。以康熙九年(1670)柳敬亭献艺京师为例,一时名流多与其交接,龚鼎孳、梁清标、曹贞吉、白梦鼐、汪懋麟、周在浚、曹尔堪等皆有诗文题赠,贰臣、新贵、名士等不同身份的人士在柳敬亭的说书技艺中沉醉,在题赠酬答中映照自我。汪懋麟别集中关涉此事者有二词一诗,此中不仅有对题赠对象的恳切赞赏与深深同情,更有对柳敬亭的劝谏——对其晚依豪门的劝止,以及破惑见真的引导,此等内容皆为同类作品所无,故而汪词“映照”意味独具一格。
先看其《贺新郎·赠柳敬亭和曹升六韵》之作:
何物吴陵叟。尽生平、诙谐游戏,英雄屠狗。寒夜萧条闻击筑,败叶满庭飞走。令四座、欷歔良久。说到后庭商女曲,怅白门,寂寂乌啼柳。天付与,悬河口。 可怜漂泊宁南后。记强侯,接天樯橹,横江刁斗。亡国岂知逢叔宝,世事尽销醇酒。叹满目、烂羊僚友。心识怀光原未反,但恩仇、将相谁知否。少平勃,黄金寿。
词作上阕总括柳敬亭失意豪侠的形象。将其与朱亥、聂政、樊哙等历史人物相埒,渲染柳敬亭的豪侠气质。转笔“令四座、欷歔良久”则从现场感受着笔,突出同情之意。“后庭商女曲”与“怅白门,寂寂乌啼柳”,所选皆与金陵相关之典,且紧扣柳敬亭曾长期在金陵卖艺作场、亡国后此又为伤心地的事实。下阕从柳敬亭入幕左良玉军中说起,阐述对南明历史的看法,以此点醒柳氏。对左良玉的评价见于“记强侯”和“心识怀光原未反”两部分,汪懋麟既批评其跋扈——“接天樯橹,横江刁斗”,兵谏之举确有不顾大局之狭隘,也批评其短智——用晚唐“泾原兵变”之典说明,左良玉因轻妄而让自己史留骂名,着实糊涂。此外,还涉及对南明君臣的评价:“亡国岂知逢叔宝”批判弘光帝荒淫误国;“烂羊僚友”讽刺南明官吏滥竽充数;“少平勃”句,反用陈平、周勃平定“诸吕之乱”的典故,意在批判南明朝中无贤。
通过对历史环境的批判来细数柳敬亭的生存痛苦,表达同情与惋惜,乃《贺新郎》一阕之表达重点,作家的劝慰之意现于《沁园春·再赠敬亭和升六韵》中:
狡黠淳于,抵掌而前,似此奇哉。任毁三骂五,河山尘芥;谭玄论白,富贵蒿莱。临槛狂呼,仰天大笑、舌上青莲何处来。从他语,学伯伦作达,荷锸须埋。 当筵谩道俳谐。看此老前身是辩才。记灵岩山畔,天花曾落;远公社里,锡杖常陪。慷慨逢场,悲凉说法,较胜雍门乐与哀。余生事,但楞严系肘,麯米盈杯。
上阕仍聚焦于对柳敬亭形象的描摹。以淳于髡、李白、刘伶三位来揭示柳敬亭的性格:博学多才、能言善辩、高度自信、任诞纵情。这样的刻绘故意疏离了柳氏说书人的底层身份,而是慨其抑郁牢骚之气,揭其心性聪敏却高蹈失意之一面。下阕援佛说理意在劝慰。“看此老前身是辩才”句,意指有二:一指柳氏乃北宋高僧辩才禅师转世,精通佛法、功德圆满;二指柳氏乃佛教中善于说法之人,《楞严经》:“虽知一切法远离文字,不可言说,而常说法,辩才无尽”,意其讲法道理圆通、言辞流畅、毫无障碍。顺承此意,“天花曾落”、“远公社里”两句,皆引佛门高僧故事正面肯定;“楞严系肘”则荐以佛典《楞严经》,劝其依性起修,速达破惑见真之境,在各种善恶因缘的纠葛中得到解脱,以获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上述劝慰仍属婉转,相关诗作更为明晰。在《柳敬亭说书行》长篇歌行中,汪懋麟详细描绘康熙庚戌冬(九年,1670)柳敬亭为其献技之经过。诗之后部有:
君不见原尝春陵不可作,当日纷纷夸养士。鸡鸣狗盗称上客,玳瑁为簪珠作履。此老若生战国时,游谈任侠羞堪比。如今五侯亦豪侈,黄金如山罗锦绮。尔有此舌足致之,况复世人皆用耳。但得饱食归故乡,柳乎柳乎谭可止。
诗中的“原尝春陵”是指战国四君子——平原君赵胜、孟尝君田文、春申君黄歇、信陵君魏无忌,皆以礼贤下士而著称。可在汪懋麟看来,他们的时代早已过去;如今的豪门权贵毫无养士之心,根本不必再为其卖命。柳敬亭有说书之技,世人有耳,普通民众的娱乐需求,足以让其舌耕自给。这样的观点亦可见于汪氏所作《郭猫儿传》中。郭猫儿乃扬城“善象生”者,即口技表演者。他因艺闻名,“尝有贵人过此,欲挟以去,猫叩头请命,欲老死故乡”,作者因之赞曰:“噫嘻,猫之技不惟可喜可悦,而其所守亦有足尚者”。此与柳敬亭之谋生方式正好相反,汪懋麟的褒贬态度亦可知。同时,若联系柳敬亭入清三十多年一直不肯剃发改装的事实,则汪懋麟此处的叶落归根、老依故土之劝就更显睿智:在京城这样的敏感之地抛头露面,不是柳敬亭这等遗民装束者的明智之举。
汪懋麟与柳敬亭同为南直隶扬州府人士,乃名副其实的同乡。康熙九年,居官京城的汪氏看到比自己年长五十多岁的柳敬亭仍在风尘漂泊、居无定所,还沉浸于明亡的痛悼中,内心是甚为疼惜的。故此,在“赠柳”词作中除了常见的对柳氏才华之激赏、人品之推重外,汪懋麟还说了一些体己话:劝止其依附豪门的谋生方式,开导其放下善恶因缘的纠葛。这些话语一方面反映出汪氏对世事的洞明,同时也体现出其善意,对前辈同乡赤诚的关心与爱护。正因有此内容,汪氏“赠柳”之作别具格调与境界。
二、“赠柳”的词坛影响及于汪氏之意义
汪懋麟的“赠柳”词作在当时甚有影响,并世名家曹尔堪、周在浚皆有和作,足见推重。有一个背景必须先作说明:《贺新郎》“赠柳”词的首倡者并非汪懋麟,而是曹贞吉。故有疑问:曹、周二人为何不步首倡之韵,而接和者之韵?是曹贞吉的原作未为二人所知,还是另有原因?先看时人曹禾之述:
柳生敬亭以评话闻公卿,入都时邀致踵接。一日,过石林许曰:“薄技必得诸君子赠言以不朽。”实庵首赠以二阕。合肥尚书见之扇头,沉吟叹赏,即援笔和韵。珂雪之词,一时盛传京邑。学士顾庵叔自江南来,亦连和二章,敬亭名由此增重。
据此可知,曹贞吉的《沁园春·赠柳敬亭》、《贺新郎·再赠柳敬亭》曾“盛传京邑”,同为秋水轩唱和群体成员的曹尔堪、周在浚不会不知。且据上引文字,曹尔堪和作之前是明确知道首倡之人的,故此,“不知说”难以成立。欲明其中真正原因,尚需从词作本身入手。为便于对照,现将四人作品全数征引如下:
曹贞吉《贺新郎·再赠柳敬亭》
咄汝青衫叟。阅浮生、繁华萧索,白衣苍狗。六代风流归抵掌,舌下涛飞山走。似易水、歌声听久。试问于今真姓字,但回头、笑指芜城柳。休暂住,谭天口。 当年处仲东来后。断江流、楼船铁锁,落星如斗。七十九年尘土梦,才向青门沽酒。更谁是、嘉荣旧友。天宝琵琶宫监在,诉江潭、憔悴人知否。今昔恨,一搔首。
汪懋麟《贺新郎·赠柳敬亭和曹升六韵》
何物吴陵叟。尽生平、诙谐游戏,英雄屠狗。寒夜萧条闻击筑,败叶满庭飞走。令四座、欷歔良久。说到后庭商女曲,怅白门,寂寂乌啼柳。天付与,悬河口。 可怜漂泊宁南后。记强侯,接天樯橹,横江刁斗。亡国岂知逢叔宝,世事尽销醇酒。叹满目、烂羊僚友。心识怀光原未反,但恩仇、将相谁知否。少平勃,黄金寿。
周在浚《贺新郎·次汪蛟门舍人韵为柳敬亭作》
矍铄庞眉叟。问沧桑、几番阅历,白云苍狗。今古兴亡堪指掌,老向燕台浪走。寻筑客、沉埋已久。忽漫骑驴归去疾,莫攀条、长叹嗟衰柳。从此去,须钳口。 如今寥落时人后。忆当时、纵横舌战,气吞牛斗。百万连营看握麈,月夜临江命酒。羞碌碌、古人为友。太息信陵门下士,且藏身、傭保君知否。年望八,不言寿。
曹尔堪《贺新郎·赠柳敬亭次汪蛟门韵》
八十庞眉叟。见从来、衣冠优孟,功名刍狗,炯炯双眸惊拍案,似听涛飞石走。叹此老、知名已久。大将黄州开广宴,倒银缸、击节频呼柳。排战舰,下樊口。 长江浪息风清后。束轻装、归舟一叶,帆移星斗。画角牙旗频入梦,犹在辕门使酒。诸巨帅、皆为吾友。白发瘦驴燕市月,少年人、能识苍颜否。歌未阕,起为寿。
《贺新郎》又名《贺新凉》、《金缕曲》、《乳燕飞》、《貂裘换酒》,定格为一百一十六字,前后段各十句、六仄韵。对比曹氏原倡与汪作可知,用韵大致相同,只略存小异:一是同是仄韵,曹作全用上声,而汪作结句用去声,即“一搔首”与“黄金寿”之别;二是依律平仄通用时,汪作多用仄声,如“当年处仲东来后”与“可怜漂泊宁南后”之例。故此可知,汪作在声调上更为激越、铿锵。此外,意味上亦有区别。首倡的曹作苍凉而沉潜,“尘土梦”、“憔悴”、“今昔恨”等词语描摹的柳敬亭,是落魄者的形象;词作下阕涉笔左良玉故事时,只以东晋“王敦(字处仲)之乱”隐喻,未有明示,故此,蕴藉有余、透辟不足。汪作则豪横而雄肆,刻画柳敬亭形象时不作今语、近绘,避免今昔对比之黯然;下阕直指宁南旧事,且以“记强侯,接天樯橹,横江刁斗”略作铺陈,雄健纵横之意鲜明。再看两首和汪之作。周词中“忆当时、纵横舌战,气吞牛斗。百万连营看握麈,月夜临江命酒”,与曹词中“大将黄州开广宴,倒银缸、击节频呼柳。排战舰,下樊口”诸语,明显是写柳氏入幕左军之事,而且在铺排气势、雄健程度上更有提升,豪纵之色尽显,与汪作之豪雄更为接近。
后人在评述曹贞吉此作时,最常提及的是王士禛之评:“赠柳生诗词牛腰束矣,当以此为压卷”,以其推崇之甚而意为无可匹敌。但是,从周、曹两位行家的和韵选择来看,恐非如此:同时代行家用实际行动给出的褒贬选择,足证汪懋麟填词实力之不可小觑。且以汪氏之个性,绝非自甘落后之人。曹禾曾在为曹贞吉所作的《词话》中有言:“蛟门自负诗歌不可一世,独以文章让予,填词推实庵,三人每酒酣争胜,气不能下”,可知汪懋麟在填词上甚有与曹贞吉争雄之心,意气风发、姿态昂扬。
以赠柳词为代表的豪放之作是汪懋麟词事追求上甚有价值的部分,它首先是词人风格多样的重要组成部分。“沁园春”与“贺新郎”皆为长调,从格律角度而言,前者“格局开张,宜抒壮阔豪迈情感,苏、辛一派最喜用之”,后者声情沉郁苍凉,宜抒激越情感,“大抵用入声部韵者较激壮,用上、去声部韵者较凄郁”,亦即,二调宜显豪放风格。汪懋麟的两首赠柳词,皆现豪放之相:使事用典,纵横史乘;大开大阖,气象恢弘;参透世变,意境苍凉。故由此可知汪懋麟词风之一斑,而此一点对认知作家风格至为重要。因早年追随王士禛,故汪懋麟常被归为其师花草之派;又因其《锦瑟词》中“沉眠周柳”、“不令人不销魂”的香艳之作不少,故其词风确有婉约之一面。但是,作家风格并非一成不变,后期词作、尤其是长调作品显示出的是汪懋麟对豪放风格的着力追求,以及非凡实力。曹贞吉言汪词“直以龙门笔意作草堂致语,大奇”,可谓到位之评:寻绎出的是汪懋麟史学修养、史家意识在词作中的得体展露,及使词体面貌为之一新的独特。徐釚所说:“《锦瑟词》排荡奡兀,中有一种葱茜之色,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则从整体倾向的角度推崇其激荡、傲岸之作。这种变化在作家本人处,亦得珍视,如在《锦瑟词》卷首《锦瑟词话》中,置首者乃曹尔堪 “豪迈壮往,读之兴会飙举,逼真稼轩”之评,足见认同;周在浚“直与稼轩、后村并驾,非柳七辈所能望也”、肯定其豪放成就的评语,亦收录在册。
须知,这一转变,既是对顺治十七年至康熙二年“虹桥唱和”婉约风格的超越,同时也是对康熙五年“广陵唱和”豪放风格的继承,故为清初词风流变的具体折射。
汪懋麟是广陵词坛中本籍词人的代表,同时也是成功进入京师词坛的广陵作家。故此,赠柳词作获得同道首肯,这不仅是汪氏个人融入京师词坛、立稳脚跟的标志,而且更是广陵本籍词人在“后王士禛时代”积极追寻出路的成功尝试。故其词坛表现深得本籍前辈肯定:
吴薗次曰:词家旧推云间,次数兰陵,今则广陵亦称极盛。闻之程村曰,陈善百《半豹吟》,巧于言情;宗定九《芙蓉集》,精于取境,乃刻意避香奁语,岂畏北海无礼之诮耶?近如《锦瑟》、《溉堂》,亦足旗鼓中原也。
吴绮此语中为广陵词事“树宗立派”的意图十分明显,历数陈世祥、宗元鼎、汪懋麟、孙枝蔚诸家词集的目的,不仅在于欲比肩云间派、毗陵群体,而且着眼于抗衡中原,视野与气度皆不凡。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中,汪懋麟无疑被前辈视为广陵词坛的新晋主力,对其词学追求既有肯定又有希冀。词评家徐釚亦有相似看法:“广陵诸子如善百、园次、梅岑、鹤问,各自名家。今又得蛟门吐华振藻,浸浸乎轶苏黄而驾周秦矣”,亦在广陵词人群体中确立汪懋麟之献替。
三、“赠柳”所示与王士禛之相左见解
汪懋麟乃王士禛之弟子。顺治十七年汪氏即“因小试,得以诗为质,先生加奖焉”,从此进入王士禛门下。有关师生二人在词学上的关系,学界已有论述中言“同”多、辨“异”少,反映出在二人词事研究中尚存偏失,亟待纠补。
具体到“赠柳”事件,首先反映出的“异”是对柳敬亭的评价与态度不同。王士禛亦有“论柳”文字:
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破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作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苏昆生者,一善说评话,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左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余曾识柳于金陵,试其技,与市井之辈无异。而所至逢迎恐后,预为设几焚香,瀹岕片,置壶一、杯一;比至,径踞右席,说评话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复强之也。爱及屋上之乌,憎及储胥,噫,亦愚矣!
其中贬义明显。王士禛不喜柳敬亭的原因,从上述文字来看主要有二:一是不愉快的观演经历,让王士禛视柳氏为“浪得虚名”之辈;二是厌弃追捧柳氏的文化氛围,王氏认为,“名卿遗老”实际是将柳敬亭视作东林党之遗存而念念不忘,寄托的是自家的“悼明”情结。这段带有鄙夷色彩的文字曾引发历史上“拥柳派”的反击,如泰州人康发祥在《伯山诗话》中斥其为“谰语”,甚为愤慨。那么,这段话真的是诬赖、无据之评吗?其实不然。由一次不愉快的观演经历而全盘否定柳氏技艺,做法当然欠妥;但是,揭示出柳敬亭身上的“故明象征意义”,王士禛却是洞若观火、一语中的。由此亦可知,王士禛“倒柳”的真正目的是反对清初“名卿遗老”不能与时俱进、无视改朝换代事实的倒退做派,以及不满于彼时社会中所弥漫的“悼明”氛围。这亦与王士禛入清后积极拥抱新政权的仕宦心态甚是契合。
尽管恩师“倒柳”的态度鲜明,但汪懋麟并不附和趋奉,而是从自我感知出发,抒写“惜柳”之意。其“惜柳”又非遗老心态,而是从“人”之角度,理解与同情柳敬亭这一个体在历史沉浮中的苦痛,并助以解脱之道。
更进一步说,汪懋麟在词作中已反映出对南明史实总结、评述的意图,远比王士禛一味鄙弃遗老思维的做法更有意义和价值。如其《贺新郎·赠柳敬亭和曹升六韵》中有:“可怜漂泊宁南后。记强侯,接天樯橹,横江刁斗。亡国岂知逢叔宝,世事尽销醇酒。叹满目、烂羊僚友。心识怀光原未反,但恩仇、将相谁知否”,从君荒臣腐、文争武哄等多个角度分析国事糜烂的原因,显示出一定的史家意识。这既与汪懋麟的学识、气度有关,同时也是历史认知的某种必然。甲申之变时汪懋麟尚在童稚,但扬州屠城之惨、仲兄被戮之痛,都使他对易代之变有切肤之痛——如其诗文《告先考文》、《刘庄感旧》、《董妪传》等篇中皆有反映,这是他能深切体会柳敬亭痛苦的情感基础。可毕竟事过境迁,当汪懋麟考虑仕隐出处时,明亡已有十多年,因此仕清的心理负担不太沉重。而回溯前明兴亡史实时,岁月的磨洗与沉淀,都让这份总结的理性成分增多、感性成分减少。再加上汪懋麟颇具史才,曾被荐入值史馆:“崇祯朝无实录,曹侍郎溶进邸抄五千余册,君与乔君石林辈辑为长编,作史者始有所考据焉”,故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认知更为深刻,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原因,从而提供史之镜鉴。这种创作手法在其后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可以找到明显的继承痕迹:大到创作主旨、人物定位,小到遣词造句等,皆有迹可循。
其次,师生之间在词体创作上也有分歧。王士禛居官扬州时建坛立坫,借词而声名早著,确立起了自己的文坛地位。但北上京师以后,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时人蒋景祁谓其有“弃词”之举:“王詹事阮亭精研诗格,《衍波》以后禁不作词”。关于王士禛入京后是否“弃词”,学界尚有争论,如严迪昌先生言其“是”:“王氏词学活动在他离去扬州时也就告终结了”;李康化先生言其“否”,“其实并不准确”。依本文之见,“弃词”之说确有不妥,言其“避词”则更恰当。事实是王士禛入京后仍有填词,但只在推却不了的场合才偶一为之,其后又旋扫痕迹,不愿外传。如康熙十一年,龚鼎孳、梁清标、曹贞吉、汪懋麟等一同观赏宋琬《祭皋陶》杂剧的搬演,雅集诸人皆作《蝶恋花》词以抒胸次。王士禛不仅作词,而且是首倡——这从同集诸人词作标题中皆有“和阮亭先生韵”所示可知,但此作并不见于王士禛著述中,可作的推论是词人自己事后删去了此作。正因如此,同时代之人有的只是其“禁不作词”的印象。至于以《居易录》中有其康熙二十八年所作《点绛唇》而驳“禁不作词”之真实性,则尚有不察之憾:蒋景祁《刻瑶华集述》成于康熙二十五年,早于《点绛唇》三年成文,因此所述并无瑕疵。而此又可证“避词”之说更为合理。
身为王门弟子,汪懋麟对其师在词事上的回避态度不会不知,但汪懋麟没有亦步亦趋。赠柳词作写作于康熙九年,已是王士禛“避词”之时。与对柳敬亭的评价一样,汪懋麟在词体创作上也是自有主见:入京为官后积极参与群体唱和活动,除赠柳唱和外,还曾参与秋水轩唱和、《祭皋陶》观剧唱和等,逐渐成为京师词坛令人瞩目的人物。以秋水轩唱和而言,汪懋麟的参与主要有三:一是作词两首:《贺新凉·送周雪客还白下》、《贺新凉·寄栎园先生》,皆为豪放之声;二是为《秋水轩唱和词》集作序,与王士禄之《题词》、杜浚之《词引》并列,且在概括秋水轩唱和特点上,最是清晰明了、要言不烦:“词非一题,成非一境”,被今日治词史者征引最多;三是成为唱和主题之一,汪懋麟曾于康熙十年在京城纳妾,龚鼎孳、曹贞吉、杜首昌、周在浚、纪映钟、龚士稹、王豸来、陈维岳、王士禄、徐倬、梁清标等名流皆作“贺汪蛟门舍人纳姬”之词道贺,共得十二首,乃此次唱和中以主题划分、得词最多者,足见汪氏人气之高。
四、汪懋麟词事追求消歇与王士禛之关系
康熙十五年,汪懋麟将自己的《锦瑟词》刊刻出版,集中收录词作164阕,并配有3篇“词序”、16首“赠词”、29则“词话”。相较于同一年刊刻的曹贞吉《珂雪词》所收:“序文”3篇、“词评”6则、“词话”8则、“题辞”6首,则《锦瑟词》在“题赠”与“评点”的呈现上皆更“隆重”。《锦瑟词》付梓后,汪懋麟较少涉足词事,故其在词集中罗致同道评述的举动,甚具总结的意味,可视为一种郑重的道别。
汪懋麟为何放弃对词事的追求?作家本人未有明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就在《锦瑟词》刊刻的第二年,王士禛编纂《十子诗略》,汪懋麟与曹贞吉、宋荦、曹禾、田雯等同列,“称诗辇下,时号‘十子’”。此事意义重大。裴世俊先生曾言:“这是一次‘开山采铜’创立派别的尝试”,即《十子诗略》的刊布乃王士禛创立“神韵派”的重要举措,为其诗名上达帝听的先决条件。两事关联来看逻辑约略可成:汪懋麟在诗学成就得到王士禛首肯后,最终放弃了词事上的特立独行。
这一联系不是没有依据。在门人与自己词事态度相左一事上,王士禛并非全然豁达。虽然此事隐晦,因当事人不落言筌而很难找到“夫子自道”,但在王士禛所作《汪比部传》中,还是流露出了真实态度。此文在涉及对汪懋麟的文学成就评价时,只字不提词作;在著述介绍中,称其“所著诗文集合二十四卷,行于世”,故意省略词集。参看他人所作传状:冯溥《汪君蛟门传》,“诗、古文、词亦益工,每一篇出,不胫而走四方”、“所著《百尺梧桐阁集》文八卷、诗十六卷、诗余一卷行世”;徐乾学《刑部主事季甪汪君墓志铭》,“君所著《百尺梧桐阁集》文八卷、诗十六卷、诗余一卷行世”;方象瑛《汪蛟门墓志铭》,“所著有《百尺梧桐阁集》文八卷、诗十六卷、诗余一卷行世”,皆言其有“诗余一卷”,即肯定《锦瑟词》的存在,与王士禛的“抹杀”形成鲜明对比。《汪比部传》乃汪懋麟身故后、王士禛受其家人拜请而作,是汪氏一生行迹的盖棺之论,对后世影响之巨,王士禛不可能不知。文中故意不提汪氏的词事成就,用意即在:既然汪懋麟在康熙十五年后已不涉词事,故当年师生间的这份分歧亦无必要让后人知晓。
这种避谈词事的态度,贯穿于王士禛后期的文学著述中。如其晚年自述平生文字交游时,也尽量抹去词学的痕迹:

今人在言及其与邹祗谟的交往、扬州文事时,大书特书的《倚声初集》编撰、广陵唱和等,皆不在王士禛的自我陈述中,其避谈词事的主观倾向可明。
而这在当日对汪懋麟的影响,是加重了词人的思想负担,并最终导致其放弃词学追求。首先,与王士禛文学观点相左,汪懋麟在当时承受了不小的舆论压力。如其曾言,“今之名诗人者,往往诟懋麟之学,谓与先生异,则当在所弃必矣”,所说乃因诗学观念与王士禛不完全一致而承受的压力,而推及到词“作”与“不作”这样有更大分歧的问题上,则其所遭受的非议应该是更甚的。其次,词事上“压”、诗文上“扬”,王士禛对汪懋麟的文体选择有明显干预。关于前者,只要翻检《锦瑟词》即可知王士禛之冷淡态度,总共只有“欧晏正派妙处,俱在神韵,不在字句”一句评语,而此语既缺乏明确的对象感,同时又未明褒贬,泛泛而论,敷衍之意甚浓,在《锦瑟词话》中是诚意最欠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诗文上王士禛对汪懋麟甚是器重。诗事之外亦认可其古文,多次委以重任。如康熙十一年,嘱其为《蜀道集》作跋、为《游山诗》作序。此外尚邀其为至亲骨肉作传,如康熙十四年的《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孝节王先生碑阴记》,乃为其兄长王士禄而作;康熙十五年,《王宜人传》为其亡妻而作、《王御史传》为其叔父王与允而作,如此等等,皆可见信任与厚密。再加上汪懋麟是“遇知己,倾肝腑向之”的个性,故综合种种,恩师在词事上的否定意见无论怎样都不可能一直置于不顾。故经历近十年的酝酿发酵,汪懋麟在《锦瑟词》刊刻出版后作出了选择:放弃对词学的追求,以自己的妥协来化解矛盾。而王士禛对此应该是持欢迎态度,转年《十子诗略》中收录汪懋麟之作即是这一态度的外化表现。
当然,汪懋麟放弃词事追求,亦有自身原因,究其根本乃在其文体观念。试看其在《十五家词原序》中所述:
夫声音之道,上自雅颂,以至汉魏、六朝,唐人乐府诸篇皆所以被管弦、奏朝庙者也。若宋之词,下矣;元之曲,愈下矣。大雅之士思起而振之,古乐既已失传,世俗沿袭之曲荒秽杂乱、不能遽革,求其稍为近古、不悖于声音之道者,于诗余其有取乎?
由此可知,汪懋麟在词体正变观上接受的是王士禛早年词乃“乐府之变”、“古诗之苗裔”的论调,这一理论虽可从文体升降代变,亦即文学统序上为词体争得一席之地,但难免文体代降、词体卑下的逻辑推论,故实难将“词”与“诗”、“古文”作等量齐观。汪懋麟曾自言,“(填词)同于博弈耳,未敢自位于古人也。愿卒业于古文焉、诗焉,源深而流远,殆茫茫乎未见其所止矣”,即其所持乃传统文体尊卑观念的体现。这正是历史人物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真实状态:当就填词一事而言时,可能姿态积极;而当“词”与“诗”作对比选择时,则另当别论了。
这种文体尊卑观念本就势力强大、根深蒂固,再遇王士禛这等文坛巨擘的实践引导,词体创作受到负面影响就是自然之理了。对此,清人其实早有揭示:“渔洋复位高望重,绝口不谭,于是向之言词者,悉去而言诗、古文辞,回视《花间》、《草堂》,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只可惜今日治词史者重视不够。言及王士禛对清词复兴的影响时,不谈其“避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既妨碍了研究的客观与全面,同时也存在悖论:既然王士禛的文坛影响巨大,那么为什么“避词”这么重大的举动会没有产生社会反响?
康熙十五年前后的京师文坛,其实正酝酿新变。就诗词而言,一方面词坛呈消歇之态:龚鼎孳、宋琬等谢世,曹尔堪、周在浚等离开,汪懋麟放弃,曹贞吉大量减产;另一方面诗坛勃兴,最耀眼者乃王士禛正以神韵理论成为王朝新的诗歌领袖,而背后的推手是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
康熙丙辰,某再补户部郎中,居京师。一日杜肇余(臻)阁学谓余曰:“昨随诸相奏事,上忽问:‘今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文者,孰为最?’首揆高阳李公对曰:‘以臣所知,户部郎中王士祯其人也。’上颔之曰:‘朕亦知之。’”明年丁巳六月大暑,辍讲一日,召桐城张读学入,上问如前,张公对:“郎中王某诗为一时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上举士祯名再三,又问:“王某诗可传后世否?”张对曰:“一时之论以为可传。”上又颔之。七月初一日,上又问,高阳李公、临朐冯公再以士祯及中书舍人陈玉璂对,上颔之。又明年戊午正月二十二日,遂蒙与翰林掌院学士陈公同召对懋勤殿,次日特旨授翰林院侍读。
从康熙十五年开始被君主留意,至康熙十七年“由部曹改词臣”;并由此而主盟清初诗坛、引领诗歌一体步向“盛世元音”,王士禛的荣显之路充分说明,京城的文学风尚从来就不是完全由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而是与时代政治和文化背景关联紧密的。由此审视这一大背景之下汪懋麟在诗词上的重新选择,正是“诗”盛“词”弱、代表皇权意志的神韵诗歌话语更具强势力量的具体表现,故其于文学史而言,亦存“一叶知秋”的解读意义。
[责任编辑 闫月珍 责任校对 池雷鸣]
2016-12-14
戴 健(1969—),女,江苏江都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清宴集与戏剧生态研究》(批准号:15YJA751005)。
I206.2
A
1000-5072(2017)08-01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