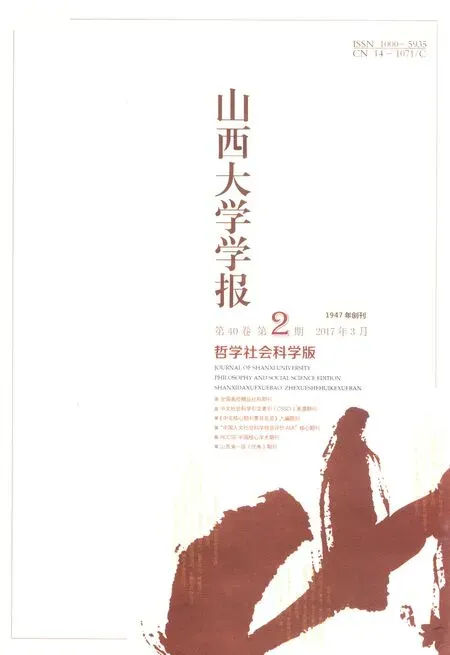论“启蒙”及其教育学意蕴
2017-06-01杨兆山
陈 仁,杨兆山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论“启蒙”及其教育学意蕴
陈 仁,杨兆山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基于不同的文化历史语境与实践情态,“启蒙”展现出来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通常以“启蒙运动”代替“启蒙”发生的内在逻辑的做法,是对“启蒙”本质、内涵与价值使命的片面化。教育与“启蒙”存在着本质性的联系,二者都关注如何使人成之为“人”的问题。立足于教育“培养人”的价值前提,廓清“启蒙”的教育学意蕴,不仅有利于在理论上完整地认知“启蒙”,也有助于纠偏实践中的认识论偏差,更好地助推教育价值转型、落实使人成之为“人”的启蒙目的与使命,最终促进人的理性与自由。
启蒙;教育;理性;自由;自我启蒙
在全球史语境中,“启蒙”是在不同地域以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态发端的,因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情态。由于“启蒙运动”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影响,它甚至改变了人们对“启蒙”的本体性体认与历史叙事。实际上,以“启蒙事件”为中心的历史认知,虽为人们理解“启蒙”提供了极其生动可视的历史参照,但往往也会造成“启蒙就是启蒙运动”的观念误导。其直接的一个后果是,“启蒙历史主义”借助启蒙运动的魅力而掩盖了启蒙发生的内在逻辑与价值进路。因此,超越启蒙的地域中心论,突破“历史主义”的惯性思维,从而真正廓清“启蒙是什么”,已构成一个亟待解决的观念命题。特别是,随着对启蒙的关注不断深入,“如何理解启蒙”与“理解启蒙是什么”越来越表现出同一性的特点,这就需要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来还原“启蒙”的本来面目。本文的理论旨趣在于,基于“启蒙”的哲学本体把握,从“培养人”的价值前提出发,以“人”的历史形态与发展诉求作观察,尝试在教育学的层面揭示“启蒙”的本质、内涵与价值使命,对“启蒙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体系化的建构,最终的目的是进一步推进和落实教育使人成之为“人”的实践命题。
一 启蒙的隐喻及其三种哲学本质

“启蒙”进入社会及个体的观念实践史,得益于“启蒙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助推。1783年12月,德国神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约翰·弗里德里希·策尔纳在《柏林月刊》上撰文,发现“在启蒙的名义下人们的心灵(都太经常地)陷入混乱”,于是便在文中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注脚中提出:“什么是启蒙?这个就像什么是真理一样重要的问题,在一个人开始启蒙之前就应该得到回答!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它已经被回答!”[3]这一“什么是启蒙/启蒙是什么”的追问,不仅要求剥掉“启蒙”的隐喻学特征,更是要求抵达“启蒙”的深层本质。1784年,策尔纳的提问得到了门德尔松和康德的回答,并由此引发了长达10年的关于“启蒙是什么”的讨论。其中,以康德的论断最为著名——“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4]200年后,福柯以同样的篇名对康德进行了反思,指出“启蒙”不应该被视作某个历史事件,直言“‘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人们变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5]542,试图纠正启蒙运动导致的“启蒙”的认识论误判。总体而言,在观念与实践史上,对“启蒙”内涵及其哲学本质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启蒙作为确证“人”的本质的实践。就人类而言,不经“启蒙”而成为“人”缺乏足够的、自明的前提。这就意味着,启蒙与“人”的本体存在具有等同地位,从而构成了人类使人成之为“人”的自明性实践。虽然启蒙的主题与观念随人类总体生存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但以“启蒙”表征人的自明性存在的事实却从未改变;不同时代的“启蒙”虽也导致了不同的实践图景,但总体反映为对“人”的不断趋近。其中,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确证“人”的关键性历史事件,体现着“一种普遍的关于生活意义的‘自我意识’”[6]。作为人类自明性的实践,“启蒙”在以下方面确立了进步的价值尺度:(1)以人和社会的进步为内生性目标,因而民主政治、开明文化、自由自主的国家公民都是其实践的追求;(2)倡导具有共性意义的价值原则与现代精神,如理性、民主、科学和平等等进步观念,就主要来源于“启蒙”的普遍的反思与合理化过程;(3)基于人类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创造人及社会向前发展与进步的可能性,从而为人及社会的转型准备相应条件。
第二,启蒙作为理性与自由的精神品质。人的理性与自由,是人自身最为本质的精神倾向。理性是一种“引导我们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特性的理智力量”[7]11,而启蒙从一开始就内含着理性的自我要求,它并不是出自理性之外的价值诉求,而且从最高的确定性定义了“自由”的原则,“赋予了自由以理性的性质”[8],客观上为人的自由实践提供了前提。黑格尔指出,“人之为人的本质——是自由”[9],它甚至构成人精神存在的唯一真理。在启蒙实践中,理性与自由愈来愈趋于融和、相互促进,共同为“人”提供本体意义的支持:只有通过理性和自由的高度发挥,人“才能达到存在的真理,达到最高和谐和无限丰富的实在”[7]30,从而为“人”立法。近代以来,追求人的理性、自由与解放,成为一个重大的现代性课题:(1)追问社会存在秩序的合理性,致力于人理性的行使和自由的实践;(2)以促成自由的实践为目的,建立自由、平等、合乎人性的发展共同体;(3)在启蒙的指引下,使人依靠自身得到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超越。就此而言,“启蒙”在确证人的理性与自由的同时,也使其自身成了人类总体实践的内在品质——一种基于理性与自由的启蒙精神。
第三,启蒙作为反省与超越的生活态度。启蒙运动几乎是以社会进化论为支撑,展开了近代的启蒙实践。但仅仅以“启蒙运动”去确证“启蒙”,也就极可能在肯定“启蒙”作为人类的自明性实践及其内在精神品质的同时,以时间线性逻辑置换了启蒙进化的可能性与多元性。福柯指出,“同‘启蒙’联系起来的纽带并不是对一些教义的忠诚,而是为了永久地激活某种态度,也就是激活哲学的‘气质’”[5]536。因此,多元的、不同时空的“启蒙”,并非只是某个历史事件,还应包含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品质——反身性思考与批判的态度。(1)“启蒙” 的反省与超越态度,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然性”,丧失了这种生活态度,也就否定了人对“意义”的把握方式——反思与批判的思维意识;(2)“启蒙”需要反思自身宣扬的价值在“人”的内部是否能够是自成目的性的,能不能真正为人的发展提供价值跃升的可能;(3)从启蒙的实践史来看,“启蒙”必然包含“再启蒙”的过程,是某一时空范围内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需要对“自反”的危险抱以警惕;(4)“启蒙”的反省与超越的态度,体现着精神祛魅的诉求,它要求自觉更新自身的观念文化和精神面貌。
从隐喻存在的意象勾描,到哲学本质的追问,实际上难免不会被诟病为是简单的而且是试图用碎片黏联所谓的整体——在浮光掠影的阐释中,“启蒙”的意涵显得破碎、游离。但这种兼顾“观念”与“实践”的阐述方式,试图达成两个层面的目的。其一,就观念史而言,明确知识、理性和真理之于“启蒙”的合法性及其基础地位;其二,在实践目的上,就是明确“启蒙”对于个体及社会的解放意义,这种意义本身是在对自由、民主、人性的实践中生成的。“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动因不是主观动机,不是离开人的物体,也不是抽象的人类主体活动,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构成的社会实践的能动创序结构”[10],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历史情境生成的启蒙经典事件,不仅有了动态生成而非僵死且彰显人类主体活动为前提基础的历史意义,也同时使得在哲学本质的意义上对待“启蒙”的认识问题,有了更动态的生成空间。
无论是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还是在实践史的框架内,“启蒙”之于教育既是社会实践的“历史构境”,也是社会实践的“思想构境”。前者所揭明的是,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等关键历史事件,构成了辨认“启蒙”内涵的基本历史语境,也是确认教育作为启蒙的实践及其现代精神生成的重要历史基因:“启蒙是一个时代,即一个自指的时代,一个自身提出其自身座右铭、箴言的时代,一个要求自身应做之事的时代。无论对于思想、理性和知识的一般历史,还是对于其现在、对于认识、知识、怀疑、幻象的形式,为了一些制度,等等,启蒙在制度内部善于重新认识自身的历史环境。”[11]后者提醒,“启蒙”也并非单纯局限于历史,必然还要“实践”,涉及“观念—物质”的转化过程,但观念的持续性变革是造成实践变革(包括教育变革)的思想条件,而且这一思想变革的核心就是“人”的引出,即使人成之为“人”,这构成了人性化的变革力量:在实践的逻辑和出发点上,“启蒙”的意义就在于“人”的发现,从而把启蒙的思想根基及历史前提转向了“人”的存在。
二 教育的启蒙性与“人”的确证
教育与“启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本质性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在柏拉图旨在促进灵魂转向的“洞穴理论”中找到部分根基,“而且从最原初的意义上讲,教育即是一种‘启蒙’的实践”[12]。近代以来,伴随着对“人”的使命性追问的哲学传统(它至少可以追溯至斯多葛学派)、精神趋向,启蒙运动把“启蒙”与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凸显出来。某种康德意义上的将“启蒙”定界为“勇敢地去认识你自己”,从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这是“启蒙所要求的自我思考以及由此在启蒙中的不断进步乃是出自于人的使命自身的要求”[13]。但根本地讲,人类实践都是对“人”的本质确认,“是一切人类确定性的历史先验”,而这种“人的确定性永远无法归于天资和环境影响”。[14]48教育自其一产生,就彰显了“启蒙”之于“人”的本体意义。换言之,人们将教育与“启蒙”观念性地联结以前,“启蒙”就已经在教育中事实地发生了,只不过启蒙运动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视觉化而且持续影响至今的历史镜像。
近代以来,“启蒙”构成了人类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目的,也成了教育绝对领先的实践内容。基于人的“启蒙”,教育在对人进行本质确认的同时,进一步生成和丰富人之为“人”的规定性,而这一使人成之为“人”的过程,实际遵循的是教育“培养人”的价值前提与实践规定,它关注的是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可能性。因而,这不仅是哲学追问的人性命题,更是切切实实的实践命题,具体包括:(1)教育通过知识启蒙,“传播以真理性知识与日常知识为核心的人类知识为其主要职责,它需要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知识的真理性和有效性,从而使知识理性得以内在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原则”[15],从而给予个体自由以理性的内在支撑;(2)通过德性启蒙,培养个体的道德知识、道德情感和道德精神等,涵养个体德性,形成个体实践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与价值规范,不断提升个体的道德实践能力;(3)通过价值启蒙与观念祛蔽,实现个体的“灵魂觉醒”,促使人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和价值实现,实现精神世界的自由。一言以蔽之,教育中的启蒙就是对个体知识、观念、道德和精神等进行“祛蔽”、指引和充盈的过程,“教育的本质和最高境界即是一种‘启蒙教化’的形式”[16],而“启蒙”就意味着“对一切个体进行教育,从而使尚未开化的整体获得自由”[17]33,教育与“启蒙”最终得以合二为一、互为促进。
作为“启蒙”的教育,使人成之为“人”就是其存在合法性的价值宣示。可以说,教育使人成之为“人”的概括,既构成了教育中“人”的发现、生成及其完善的精神意向/内在目的,也构成了教育的实践基点与内在使命,彰显出了启蒙运动以来教育的人性化趋向及“属人品性”。这意味着:(1)教育首先应当具备“启蒙”的意识,紧契使人成之为“人”的“启蒙”使命;(2)教育应当是合目的的、合人性的“启蒙的教化”;(3)作为一种“启蒙的教化”,教育应尽可能在“人的启蒙”的基础上,通过对个体的知识、观念、素质结构和精神面貌等进行“祛蔽”、指引和充盈,将人不断推向自由与解放的发展,最终使人自由、全面地占有“人”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积极介入公共实践,推动“社会启蒙”。就人性的事实与社会发展历史而言,启蒙确实造就了关于“人”的本体认识与积极观念,并使站在“人”的立场去确证“人”,成了难以逆转的价值转向。立足于“人的启蒙”的实践内容与价值使命,教育既丰富了“启蒙”的人性内涵,同时也彰显出了自身应有的精神品质。
第一,教育自其诞生起,即是一种培养人的专门活动,其首要目的是使人脱离“蒙昧”,体现出了明显的“启蒙”意味。由此,教育在其原初意象上,就是一种“启蒙”的实践,它解决教育中“人”引出的各种价值问题,通过促进人的社会化,最终使人占有“人”的本质而真正成为“人”。历史地看,“启蒙通过巨大的社会变革、制度安排和现代教育,给予了人类及其价值努力许多仅仅是现代才可能有的珍贵赠礼。独立而不再是依附性的个人及其自由权利,平等、正义的观念和宽容的胸怀,幸福追求的正当性”[18]。正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历史事件显示,对人性觉醒与人性复归的努力,主要依靠群体启蒙来完成,体现为“社会启蒙→个体启蒙”的思路。在当代,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愈趋紧密,它以其制度化、民主化和大众性的特征,已经逐渐承担起“启蒙”的主导角色。因此,在当今的开放社会中,教育必须面向的是“所有人”,对所有人有目的、有计划地施加全面而系统的影响。可见,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育坚持的是“为人”和“属人”的价值立场,因而与传统的启蒙路径、观念与方法所不同的是,教育呈现的是“人的启蒙→社会启蒙”的实践逻辑。
第二,在制度化教育中,个体启蒙的主要载体是“知识型启蒙”,其主要内容是知识传递、道德培养与人格塑造,是基于“人”的目的施加的影响,而并不是别的什么“非教育”目的。人类实践史上的启蒙,主要包括权力型、救亡型和知识型三种。其中,权力型启蒙是指以掌握权力或具有权力优势的精英群体实施的启蒙实践。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中国民国初年的启蒙思潮等等,基本都是由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推动的。相对而言,救亡型启蒙是出现在民族危机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启蒙型态,中国清末以来至抗日战争期间主要以这一型态为主。知识型启蒙具有稳定的知识内容与价值体系,教育即以此型态为主。相较而言,权力型启蒙和救亡型启蒙是由工具主义支配的,知识型启蒙则强调“人”的立场。在教育领域,知识型启蒙并不局限在“知识”的层面,而是以整体性的影响促进人的价值观念、素质结构和精神面貌等的积极变化,这既符合“启蒙”的本来意涵,也符合教育发展的事实。“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17]1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之所以成为一股撬动世界革新的主要力量,就与教育作为知识型启蒙的影响密不可分。更为重要的是,追求知识真理/科学理性,实现人的理性自由,乃至达到个体的整体发展、自由与解放,才是教育作为知识型启蒙的真正价值旨归。
第三,立足“人”的立场进行启蒙,是对人性理念的实践贯彻,因而坚持“启蒙的教化”即是教育人性化发展的价值限定。作为教育培养对象的人,起初是“未完成”的人,他具有可塑性,也具有能动的创造性与自我发展的开放性,不必要强制地把社会的“规范”附加于他,甚至把未完成性看成是人之为“人”的阻碍条件,而应当以开放态度,赋之以教养性的理解,推动其生发出“自我教育”与主动提升的内在动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作为一种影响人的“中介”,教育也就与主体的人完成了内在的互构。一方面,人得以在教育的启蒙影响下成为理性的、主体的与自我完善的存在者,“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着,就是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性之外还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19],因而也就为其走向自由与解放准备了教育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教育的目的就是‘人的本性自身的目的’”[14]124,教育通过启蒙的实践,建立了人与世界互动、联结的纽带,但同时将人的主动与开放性发展视为这种联系的基础,由人自身在启蒙影响下决定自己的方向,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教育向“人化教育”的转型。
总而言之,教育与生俱来就具有“启蒙”的基因,是指向“好/更好”的价值实践(Education as Betterment),因为“Betterment本身就有价值,有一种往上提升的味道”[20]。由此,经由“启蒙”的过程,人不仅上升为了“人”,教育同时塑造了将自身升格为“启蒙的教化”的价值合法性。但还需注意的是,“教育依据人的观念而培养人。人的观念是教育理念的一个规范性限定。……教育所理解的人的观念或对人的命名,意味着教育将培养什么样的人,意味着我们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教育。”[21]因此,这一对“人”的本质确证的命名过程,必须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教育的人性化,以实现使人之为“人”的启蒙目的,并真正保持教育作为“启蒙的教化”的实践价值与精神品性。
三 启蒙的异化与教育的“自我启蒙”
启蒙展示了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却不等同于作为现代性事件的“启蒙”,但它又以现代性历史事件表征其对世界进程产生的榜样性影响。作为与人类历史相伴生的自明性实践,启蒙不仅反映着人类对于理性与自由的追寻,也体现着一种反省与超越的精神态度以及试图生成有意义的可能生活方式的价值愿望,因而不存在“启蒙的终结”的问题,也并不存在“对启蒙的超越”的问题。而之所以能够发起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是对作为现代性历史镜像的“启蒙运动”的伪古典式的怀旧。应当认识到,启蒙本身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实践机制:“启蒙作为内生的‘人’的觉醒状态,它有一种自我澄清和自我发动的机制。只要启蒙任务没有完成,或者再启蒙的形势形成了,启蒙的任务就会再一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不是主观宣告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也不是借助所谓批判启蒙的武器就可以彻底瓦解的事务。”[22]换言之,启蒙有着“自我启蒙”的内在诉求,唯有这种自我更新与超越的品质,才有助于推动“再启蒙”的任务。
在当代,启蒙日益暴露出了许多隐匿或衍生的弊端,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对宗教和传统的祛魅破坏了人类自我约束的根据及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工具理性凸显导致人性的萎缩和社会的市场化,原子式个人主义的高扬引发社群的疏离乃至破毁,极端自由主义盛行致使社会公正无从落实,普遍的怀疑心理和制约动机通过剔除社会政治中的道德因素和信赖感而造成民主的劣质化,作为个人中心主义之放大的族群中心主义激发了层出不穷的国际冲突;最为严重的是,僭妄的工具理性主义,攫取和占有性的个人自由主义,反宗教、反传统、反自然的个人—人类中心主义”[23],而这种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逐渐使启蒙偏离了人文主义传统,启蒙的精神文化甚至走向了专制、排斥与粗暴。可以说,现代社会景观中的“启蒙”,始终处于紧张之中。越来越多人也开始反省,启蒙并没有使得人类成为万能的存在者与自我主宰者,人类依然无知、对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悲观主义。在战争、暴力、极权主义、毒品、堕胎、克隆、自杀以及核辐射等“现代病”中,启蒙乐观主义成了人类狂妄自大的代名词。
正如历史所展示,启蒙具有极其强大的实践生命力,对人类摆脱各种局限性并迈向自由与解放,达到康德意义上的“成人”状态,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现代性异化的现实已经发出严重警告,正是源于对启蒙的信仰与过度迷恋,我们走上了与“祛蔽启蒙”原初目的相反的道路,我们因“启蒙”而自我解蔽、又因迷恋“启蒙”而自我遮蔽。因此,在保持启蒙价值合法性与进步性的同时,必然要审慎对待其边界/价值可能性:(1)启蒙促进了世俗化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形成了以启蒙理性为内核的观念价值体系,从而带动了哲学、文化与教育等实践的自我理解与变革,但不能将启蒙理性唯一化和绝对化,毕竟它并不是人的绝对本质且唯一能够给予人的价值的东西;(2)启蒙的主体与主体性启蒙的一致性,是启蒙展开的主体因素,但启蒙主体如何在有效性、真理性的问题上深入个体情感及经验世界,难以通过理性标准衡量,而启蒙在对待“理性”与“感性”时,走上了两条对立的道路,并加剧了启蒙自身价值的内部冲突;(3)由于启蒙在民众中的权威地位,启蒙往往会强调针对“对象”的启蒙而在实践中忽视“自我”的启蒙,极可能将自身推向决断与狂妄的危险境地。
虽然启蒙现代性异化的困境,并不意味着“启蒙已经失败”,或者宣告“启蒙已经终结”,但也不是要刻意回避问题。特别是,作为一项与“人”相关、直接关注“人”的存在本质与根基的活动,教育也同样发生了“现代性异化”的现象。这既是启蒙现代性异化的总体实践状况在教育领域的反馈,同时也反映着教育自身确实存在着与使人成之为“人”的启蒙目的相违背的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1)将“启蒙”的目标片面化,即教育目标取向上是以“职业人”的培养取代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具体是指按照工业生产、市场资本与文化产业等需求培养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特定类型的职业人越多则越有利于生产效率与管理秩序的维持,体现了浓重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2)基于工具理性主义的目标设定,教育内容的安排都几乎以科学知识、技能训练等实用性课程占据强势的主导地位,以理性代替“全面”、以分数代替“素质”、以“实用”代替“人文”,追求知识的“真理性”也变成了对知识占有情境性的取代,教育离个体精神世界、生活世界越来越远,沦为了“在一种创造便利的意义上被期望于用来促进乃至加速实践性——技术性的文化进程”[24],“标准化”而非生命的多样性与意义建构,成为教育的普遍追求;(3)教育方法仍然停留在“传授/灌输”的层面,重“权威”而轻“民主”,无法真正实现提升个体创造性、关注个体情感与经验世界的价值诉求;(4)伴随工具主义、消费主义的崛起,教育在其精神气质上变得平庸化,“不再关照人性或灵魂的健全发展,而是专注于发展受教育者竞争社会地位和获得资本货币的能力,专注于培养受教育者的消费品质和消费能力,为资本社会和市场社会服务”[25],不仅难以传播真理性知识,而且导致个体精神世界的同质化与平庸化,背离了个体自由与解放的启蒙宗旨。
“启蒙精神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反思精神,其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服从于其他功用”[26]。这种气质,是一种反身性的批判精神,一种不沉溺于“真理”、面向当下生活以及未来的自我变革态度,一种能够对自己发起“审问”并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独立精神品格的价值文化。对教育而言,这种气质就是“自我启蒙”的内生性基因,启蒙本身就蕴含着反思与革新的精神。一方面,它要求坚持启蒙旨在促进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目的;另一方面,更是要求教育从启蒙现代性异化的困境中自我突围,时刻保持自身作为“启蒙”的清醒姿态,能够以果决勇气进行自我革新,实现教育的价值转型,从而为推动教育的启蒙实践夯实基础。“启蒙”永远不会终结,它是人类永恒面对的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么启蒙”。用“启蒙”的本真态度启动“再启蒙”,这是教育自我启蒙的核心,教育需要回归“启蒙”的本体与价值使命,能够积极主动纠偏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时刻防止自身异化与“反启蒙”的倒退。
首先,“自我启蒙”意味着观念的自我更新,教育需要坚持个体自由与解放的启蒙目标。“‘启蒙’作为通过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启蒙的核心是使用理性,理性启智是让人摆脱封建专制机器上的零件状态,进入自由和解放之中的成人状态”[27]。通过理性启蒙实现人的理性自由,使人能够运用理性自主判断、决策和自由行动,这是启蒙致力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重要路径。事实上,人类至今几乎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理性启蒙的积极影响。但理性本身却是自我纠缠的矛盾体,它以价值法官的强势地位驱逐了人的“感性”。换言之,启蒙在树立理性权威的同时,却也忽视了个体发展的另一面——人的感性发展。“人”不断在完善与发展的同时却也陷入了异化与片面化的泥潭,“被理性启蒙的世界不是一个人性得到真正发展,自由得到全面实现的世界,而是一个普遍异化的世界”[28],人性的完整性被肢解,人的自由与解放仍然举步维艰。在教育中,理性启蒙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才导致了这些问题。教育需要更新观念与目标,把感性启蒙纳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核心议题,实现理性与感性的协调。
其次,“自我启蒙”基于人的全面性发展诉求,教育应尊重个体完整经验世界,注重内容的情境性与方法的开放性。由于理性启蒙处于优先的位置,“知识—能力”的内容输出模式备受推崇,因而“从内容到结果”的价值期待往往是单向的、结果主义的。“结果主义”的价值模式背后,隐藏的一个知识逻辑就是“理性权威”的中心地位,它强调的是客观性、确定性,排斥个体生命与生活经验的参与,以科学理性为根本的法则。教育的自我启蒙,需要正视个体完整经验发展的内在诉求,在关注个体理性的同时,也需要对个体的情感、人格与审美等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人并不是绝对理性的存在,而且有着个体经验与自我感知的存在,是以认知、道德与情感等全面参与和体验世界的存在。因此,教育应“涵盖知育、德育、美育,即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三个方面,唯此才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全面而协调的发展,使人能为‘整全的人’”[29],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自由发展的前提。同时,正如杜威所言,“生活就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30]教育应回归个体的生活世界,注重其情境性与发展的可能性,从“结果主义”转向“生成性”的发展。
最后,“自我启蒙”是教育内在的精神品质,教育需要重塑自身的人文价值关怀,回到“人化教育”的精神本性。作为“启蒙的教化”,教育意味着它应当是“好的”教育(Education as Betterment),虽然它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教育结果,但它在最大程度上承认了“好的”教育对人的全面、系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只能在“培养人”的价值框架之内产生。因为,教育首先是一种培养人的实践,只有人的自由与解放而不是别的什么“非教育”目的,才是教育安身立命的根本。真正立足于“人”的发展并一切从人的发展出发,这是教育之为“启蒙的教化”的人性基础。教育自身进行的“自我启蒙”,就是为了保存和不断夯实教育的“启蒙性”,实现向“人化教育”的价值转型。雅斯贝尔斯指出,教育首先应“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而不是导向由原初派生出来的东西和平庸的知识”[31]。教育要真正达到“自我启蒙”,就必须重返“人的启蒙”的实践本体,不断完善自身的人文品格,致力于提升个体的精神世界。
[1]姚中秋.中国式启蒙观:《周易》“蒙”卦义疏[J].政治思想史,2013(3):40-65.
[2]邓晓芒.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J].广东社会科学,2003(4):36-45.
[3][美]詹姆斯·斯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和20世纪的对话[M].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
[4][德]康 德.什么是启蒙?[J].盛志德,译.哲学译丛,1991(4):3-6.
[5]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6]孙正聿.属人的世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12.
[7][德]恩斯特·卡西尔.启蒙哲学[M].顾伟铭,杨光仲,郑楚宣,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8][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社会理论与真理伦理学[M].郑丹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3.
[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8.
[10]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J].学术月刊,2009(7):13-23.
[11][法]福 柯.康德与启蒙问题[J].于奇智,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32-47.
[12]陈 仁,杨兆山.教育作为“启蒙”的实践规定性——基于教育学几个经典命题的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02-107.
[13]方 博.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天意与人的启蒙[J].哲学研究,2014(3):68-76.
[14][德]底特利希·本纳.普通教育学——教育思想和行动基本结构的系统的和问题史的引论[M].彭正梅,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5]陈 仁,杨兆山.理性、道德与个体的灵魂觉醒——教育何以作为“个体启蒙”的实践[J].基础教育,2015(2):5-9.
[16]陈 仁,杨兆山,周国斌.启蒙现代性及其问题视域:教育学立场的反思与建构[J].教育科学,2015(6):1-5.
[17][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8]王 葎.幸福与德性:启蒙传统的现代价值意涵[J].哲学研究,2014(2):73-78.
[19][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0.
[20]欧阳教,李彦仪.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2):65-75.
[21]金生鈜.国民抑或公民:教育中的人如何命名[J].高等教育研究,2014(5):17-24.
[22]任剑涛.启蒙的自我澄清: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J].学术界,2010(10):5-16.
[23]胡治洪,龙 鑫.“启蒙反思”的理据、指向与限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5):43-51.
[24][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 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
[25]金生鈜.资本主义教育精神:教育的现代性困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6):1-7.
[26]邹诗鹏.启蒙及其理性的边界问题[J].哲学动态,2015(11):13-21.
[27]张一兵.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从不被统治到奴役的同谋[J].哲学研究,2015(7):79-86.
[28]衣俊卿,尹树光,王国有,等.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32.
[29]王元骧.审美教育与人格塑造[J].美育学刊,2013(4):1-6.
[30][美]杜 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4.
[31][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 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
(责任编辑 徐冰鸥)
On the Implication of Enlighte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dagogy
CHEN Ren,YANG Zhao-shan
(DepartmentofEducation,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Based o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 and practice modality,the connotation of “enlightenment” is extremely rich. It is common to see that “Enlightenment Campaign” instead of “Enlightenment” occurs in the internal logic,however,it is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its nature,meaning and value. There is an ess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both of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how to make people into “human”. Based on the value premise of education “cultivating human”,gett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 of “enlightenment”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the complete cognition of “enlightenment” in theory,but also to the correction of bias in the practice.Moreover,it will better boost the value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carry out the purpose and mission of enlightenment which is to make people into the “human”,and ultimately promote human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rationality; freedom; self-enlightenment
2016-12-2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现代性视域下中国教育启蒙问题研究”(14ZZ2102)
陈 仁(1985-),男,广西北海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杨兆山(1963-),男,黑龙江甘南人,法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2.014
G40-02
A
1000-5935(2017)02-009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