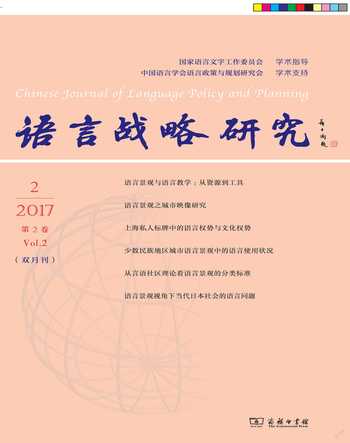上海私人标牌中的语言权势与文化权势
2017-05-30苏杰
苏杰



提 要 本文主要探讨上海的城市语言生态系统中的私人标牌所体现出的语言权势与该城市生态系统中的文化权势的关系。研究发现,官方领域语言景观能够较准确地体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语言权势与所对应的群体的社会地位,而私人领域的语言景观中的语言权势则与群体社会地位存在错位,这种错位主要是由文化权势的影响造成的。在分析文化权势时,由于现实条件所迫,应避免过度追求对标牌作者内心动因的深入研究,而应从文本入手进行诠释,尝试结合现实社会语境进行分析。同时,在通过私人标牌的语言权势分析文化权势时,要注意文本中所包含的对应其他文化的文化先例所体现的文化权势。
关键词 语言景观;语言生态学;语言权势;文化权势;文化先例
Language Power and Culture Power of Bottom-Up Signs in Urban Shanghai
Su Jie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guage power embodied in the bottom-up signs and the culture power in Shanghais language ecosystem. It reports on a linguistic landscaping research of Shanghai urban catering business. Data collection includes photographing linguistic signs displayed in and out of some 100 restaurants and interviewing restaurant owners or worker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top-down signs can accurately reflect language power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sign makers, while the language power of the bottom-up signs is not directly corresponding to social status of the sign maker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ismatch in the bottom-up sign cases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impacts of culture power of the investigated languages. The author further argues that sign producers original motivation is not the focus of this linguistic landscaping study; rather, this study emphasizes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positions the texts in its social contex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ulture power reflected in the linguistic sign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take extra caution in interpreting culture power embodied in the “Прецедентный феномен (precedential phenomenon)” while analyzing languages of bottom-up signs.
Key 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 language ecology; language power; culture power; precedential phenomenon
一、引 言
自Haugen(1972)提出了“语言生态学(language ecology)”这一概念,这种将语言与其所属环境视作一种生态模型的隐喻性研究范式便成为了研究语言认同、语言兴亡、多语问题等议题的新视角。语言景观研究则旨在通过分析景观文本所体现出的语言权势差异来推测其背后所蕴含的群体地位和认同。本文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将语言景观的文本放入一个特定的语言生态系统(亦有学者称之为“语言世界系统”)中,探寻文本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上海作为国际化水平领先的国内城市,其语言生态系统的构成较为多元,在语言景观方面也有相应体现,因此本文将以上海的城市语言生态系统中的语言景观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二、研究背景
赵蓉晖等(2010,2012)对上海的外语生活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上海各领域“使用语种”的比率是极不均衡的。除汉语、英语以外,使用较多的为日语,其他语言的使用比例都较小。此外,还进一步划分了领域进行详细调查。在市政设施中,语言使用形式较为多样化,但主要使用汉语及英语,有少量的日语、朝鲜(韩国)语等。
尚国文、赵守辉(2014a)指出,语言标牌一般可分成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两类。前者又称自上而下的标牌,是政府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如路牌、街牌、楼牌等。后者又称自下而上的标牌,是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用作商业或信息介绍的标牌,如店牌、广告牌、海报等。按照这个分类,上文中的调查结论可以整合成:自上而下的语言标牌中均出現汉语,而外语则基本为英语,偶见日语、朝鲜(韩国)语;自下而上的语言标牌中亦以汉语和英语为主,并出现少量日语、朝鲜(韩国)语等。在笔者对浦东机场的确认性实证调查中发现,官方语言景观出现外语的比例较高,中英双语标识占91%,日、朝鲜(韩国)语标识大多只出现在地点指示标识上(其实直接观察指示符号也能获得其信息)。而通知性标识则基本不出现日语、朝鲜(韩国)语,唯一出现其他语种的多语标牌为通信运营商制定,并不能完全归为官方标牌(如图1左)。
官方语言景观由于主要集中在交通等政府、事业部门,较为容易调查,而私人标牌由于所属行业复杂、数量巨大,调查难度较官方语言景观大很多。俞玮奇等(2016)从族群研究的视角对上海古北韩国人聚集区进行了语言景观调查,然而由于论文特性,只统计了三种语言,并不能体现上海整体私人标牌的特点。
自上而下的语言景观所体现的语言权势可以折射出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语言地位差异、现有的语言政策以及其背后的族群地位与认同;而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则能更好地体现市民生活中真实的语言权势及其对应的族群地位的差异。因此,本文将通过对上海的私人标牌进行实证调查和分析,进一步讨论其语言权势与对应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基于私人标牌的特点,我们选择按行业调查,而不是按地理范围调查,以防出现地理分布不均衡(少数群体聚集区、特色商业街等原因)而造成的误差。本文以餐饮行业为调查重点。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我们认为在采样时应该尽量选择语言生态系统中的活跃个体。基于这一原因,我们依据某餐饮论坛的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样本总量为510家):总体评价3星以上、食客消费评价数量50条以上、最新留言日期在三个月以内。经筛选后共随机抽取100个有效样本(排除连锁店的其他分店、标牌中语言使用不明确等误差情况),其中中餐馆46家,非中餐馆(无法归类则被排除)54家,非中餐馆包括法国菜(12)、英国菜(1)、美国菜(2)、日本菜(18)、韩国菜(3)、拉丁菜(12)、东南亚菜(3)、中东菜(2)和创意菜(1)。
本文使用回访调查法,在前期调查时主要采集语言景观数据,主要进行定量分析;回访调查时带着定量数据分析得出的初步结论对各家店铺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对店铺业主(或侍应生)和消費者进行访谈。
Scollon & Scollon(2003)的场所符号学理论认为,语言标牌中的语言之间存在主次关系,可以通过语种布局、凸显关系、字体大小、材质等方面进行考察。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区分了多语标牌中的首要语言、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为控制变量,本次调查只对餐厅的门头和暖帘(作为整体)进行统计,而内部装饰和菜单等语言景观只部分作为印证性参考证据。
在质性研究中,我们对100家餐馆中的80家进行了田野调查,每家抽取一个周末午市中的一小时和一个工作日晚市中的一小时,观察消费者中有效样本共计4170人。
四、研究结果
(一)前期调查的结果
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
Landry & Bourhis(1997)认为,语言景观具有象征功能,即语言景观中能体现出的不同语言的语言权势,也可以折射出该语言的族群的社会地位。尚国文、赵守辉(2014a)指出,Backhaus在研究东京的语言标牌时发现私人标牌与官方标牌不同,很多私人标牌不含日语,有40%的私人标牌以其他语言为主导。本次调查从总体上看确实也存在非汉语主导标牌比例较高的现象,从总出现频数来看,汉语出现频数最高,达到68次。能体现出作为通用语的汉语在上海城市语言生态中的主体地位,而汉族也是上海城市中的主要民族,但是其作为首要语言的频数只有44次。英语出现了46次,占第二位,能体现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地位,也与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的特征相符。但是,使用这一观点分析其他语言时则存在一定的问题,按照《2014上海统计年鉴》 ,上海市居留许可外国人(非英语母语)按国别人数排序为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国籍旅游入境人数按国别人数排序为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从调查结果来看,只有日语的出现频数能够与其社会群体的势力相符。另外,从总体上把握第二、第三语言的数据也较困难,因此,我们在私人标牌的研究中进行了更细化的多因素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
1.在私人标牌中,对语种选择和主次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商户的文化属性。在100家调查餐厅中,73家选择菜系所属国的语言作为首要语言。因此,并不能直接将私人标牌中的语言权势推及所属社会的语言权势。
2.私设景观中的英语地位超过了官方语言景观。在官方语言景观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主导语言全部为汉语,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中汉语的地位,而英语作为主要外语,虽然地位较其他外语高,但是只出现在次要语言中。在私人标牌中,英语作为首要语言的有22个,这种以外语为标牌首要语言的行为本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这种违法现象的存在也体现了英语的地位在官方和非官方情境下的差异。另外,在中餐馆的样本中,有22%(N=10)使用英语作为首要语言,另有30%(N=14)使用英语作为次要语言,也体现了英语的语言地位和价值之高,与官方语言景观截然不同。
3.作为首要语言的其他外语包括:日语(13次)、法语(8次)、西班牙语(7次)、意大利语(4次)、巴西葡萄牙语(1次)。朝鲜(韩国)语和泰语只作为次要语言(第二、第三)出现,体现了其他语种间存在地位上的鲜明差异,但这种差异与语言权势并不对应。
可见,私人标牌体现出的语言权势与官方语言景观有较大的差异。官方语言景观与现实族群地位的对应较为吻合,而私人标牌则有所偏离。
(二)回访调查的结果
为分析上文所述三个问题的原因,我们进行了二次调查,即主要基于质性研究方法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并通过定量、质性相结合的方法来处理数据。Fairclough(1992)指出,文本在话语实践层面可分为话语生产、话语分配和话语消费三个部分,那么访谈对象便应着眼于作为话语的语言景观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1.在调查中为避免引起被试的怀疑和排斥,我们仅通过口头问询和外貌、服饰、语言等多种族群特征来区分调查对象的族群。虽然可能是这种客观条件下最好的方法,但可靠性仍旧较低,只能尽量做到准确。消费者大致上区分成中国人、韩国人(27)、日本人(108)、英语国家消费者(292,包括印度等前殖民地国家人以及全程说英语的不确定族群)、非英语国家人(91)。我们发现,在所有餐馆中,语言景观文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绝大多数为中国人,占87.6%(N=3652),外国人占12.4%(N=518)。外国人并不集中于对应国家的餐馆中,其中中餐馆内外国消费者共计211人次,占外国人总体的40.7%;法国餐馆中出现了韩国人、日本人、英语国家人和非英语国家人全部类型;日本餐馆中外国消费者主要为日本人,但也出现了韩国人、英语国家人。其他餐馆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对话语生产者的调查同样也存在这种问题,即中餐馆基本是由中国人开设,非中餐馆经营业主也主要是中国人,只有20%(N=16)的非中餐馆的业主为外国人。
2.在访谈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挑战。首先,对话语生产者的调查过程中,80家商铺中同意进行访谈的业主只有12个。而关于“为何使用这几种语言制作招牌?”和“这几种语言的位置、大小等为什么这么设计?”两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都是“不太清楚”“这个不是我设计的”“我们是分店,软装和门头不归我们管”“你问这个干吗,我们这个是文字画,不是字”等答案。
对消费者的访谈中,只有少部分访谈对象给出了“这个名字看起来很洋气”“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应该是西班牙(语地区)那边的菜吧,想试试”等回答,绝大部分消费者都语焉不详。但是,在正面回答“你知道这个店的招牌怎么读?是什么意思?”问题的14位被试对象中,只有2人回答正确。
五、分析与讨论
(一)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语言景观
中国以地理区域为范围进行抽样的实证研究都得到了如下类似的结论:该社区的私人标牌中体现的语言权势与当地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有密切关系。例如俞玮奇等(2016)指出:在北京望京和上海古北的“亚社区”里,这些外籍侨民都趋向于维护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并将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带进社区之中,于是造就了外侨聚居区的多语景观。张媛媛、张斌华(2016)在中国澳门的四个地区抽样、统计后指出,澳门民间语言使用与政府语言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官方语言使用符合语言政策不同的是,民间语言使用更注重经济性。澳门官方和非官方的语言景观差异为非官方少用葡文,涉外商业区域和本地居民生活區域的语言景观差异为后者少用英文。即其抽样结果也表明私人标牌中的语言权势与社会事实相符,与样本的族群人数有密切关系。
为何以行业对城市整体进行抽样调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们认为,语言生态学着眼于整个的语言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中的各组成部分应互相影响、互相联系,不存在孤立的个体。外国人聚居区在内部形成了一个语言生态系统,这毫无疑问,但是这一子系统与城市语言母系统内的其他成分并没有密切关系,如“古北韩国人聚集区”这样的子系统中的文本,很可能在话语空间内并不与主流的上海市民所处的语言生态系统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调查对象选择上就要求其具有一定的活力(经济活力、文化活力)等,因此可以被认定是城市语言生态中的有效组成部分。
回访结果1恰好印证了我们在前期调查中的结论,即这种生态系统中的活跃组与孤立的子生态系统具有鲜明的差异。俞玮奇等(2016)调查表明,孤立子系统中的多语餐馆都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高比例为对应语种母语者的现象。而这些活跃组中的多语店铺大多数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主体都由中国人充当。也就是说,这种多语店铺的语言权势与所对应的语言群体的权势不具有主要关系。
(二)语言景观的创作者身份
回访结果2,这是语言景观研究中非常棘手的问题,语言景观制定者的身份问题一直以来受到大量指摘,许多语言景观的制定者对语种选择和放置的原因闭口不答。不仅如此,Malinowski(2009)曾指出需要区分作者身份和制作者,他认为语言景观的场所符号学特征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所以很难进行研究。
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可以从“文本”的视角进行考察。语言景观作为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文本,与社会产生了密切联系,文本在建构社会事实的同时也受社会事实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便有了其独立属性。从罗兰巴特开始,作者对文本的权威性便被质疑着。对于文本的创作者,Foucault(1969,转引自Bouchard 1980)区分了两个层次:真实作者(作者个体)和作者功能。创作文本的人被他的写作行为和创造出的文字所放逐,由真实作者变成了文本所在的书页上的一个名字,成为一种“作者功能”。写作过程中作者的主体消失,成为他创造出的文字的产物,是一种话语后的非个人的工具性存在。
作为文本存在的语言景观有两个存在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创造过程的阶段,这一阶段中“真实作者”的意图是重要的,直接导致了不同文本的诞生,但是这个阶段的文本是没有参与知识建构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于“语言景观和社会事实”的交互关系之中,即可以不在语言景观的研究中作为重点。第二个阶段是作为完成的文本的阶段,在这个时候,真实的作者已经消亡,而作者功能成为文本的动因发出者。按照社会建构论的观点,语言景观的文本的建构也应是社会性的,并非个体的、内在的。人际互动、社会协商与共识决定了知识和知识类型。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所采访到的语言景观的“创作者”只能认为是“真实作者”,他们对语言景观并不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权。更进一步地说,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连“真实作者”的地位都不完全具有。在某个连锁店的采访中,店主给出了该店门头的较为直接的设计理由,比如“只用英语也没见着中国人就不来了……我们这么设计(店外招牌)就是方便外国人也能看懂……现在(同类型的店铺)都是这样(的设计方法)”。但是,作为一个连锁企业,科层制的特点便使得一个个人无法对这一完整的设计负责,即使科层制产生了寡头统治铁律,这些“少数人”的身份也必然不是语言景观的实际创造者,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真正具有“真实作者”地位的是该企业的科层中流动的权力本身。
伊格尔顿(1987)指出,“后现代文本观”与“新批评”时期不同,“读者”的身份变得重要起来。Hoggart(1997)也认为读者在意义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读者在文本的消费过程中建构了符合当下历时语境的恰当含义。调查中,语言景观文本的消费者所提出的“看起来洋气”之类的说法,本身便点出了他们所感受到的这些外语作为首要语言的语言景观中体现的语言权势差异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差异。而研究者也同样是文本的消费者,因此我们认为,现有的通过研究者自我解读来归类、分析语言景观创立动因和其所反映的社会事实的方法并不是绝对主观的、片面的方法。通常这种方法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主观主义”,但是研究者作为读者,进行了具有社会共识性的诠释,反而可能是最容易趋近“功能的作者”的动因的方法,比起那些或含糊或真真假假的语言景观创立者的访谈数据,这种符合历史语境并且能够获得广泛共识的结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以上讨论认为真实作者的动因在这里并不重要,而社会背景对作者功能产生的影响才是研究的重点。结合消费者的访谈内容,我们猜测,这种多语语言景观的话语生产与消费特点并不是来源于对族群的认同,而是来源于对文化的认同。
与“语言权势”对应,我们可以使用“文化权势”这一概念来指称语言权势背后所存在的文化地位与认同的差异。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并不相同,中国人可以因为对日本文化感兴趣而产生对日本文化的认同,但不一定产生对日本人群体的认同。上海城市生态系统中不同文化的权势高低正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官方语言景观与私人标牌语言差异的“错位”原因。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将这100家店铺的相关信息整理后,请8位关键文化顾问进行分类。他们的身份包括时尚生活类杂志编辑、餐饮杂志编辑、潮流爱好者、社交名媛、4A公司员工、高级白领等,均为上海户籍或长时间在上海工作的青年,其身份大致符合布迪厄(2015)定义的“文化中间人”形象,工作与社交中具有提供文化的展示与再分配的相关功能。请他们按照自己的看法将这些店的消费期望分为“白领及以上文化阶层”和“白领以下文化阶层”,经统计后发现,绝大部分的店铺都能获得明确的划分,每家店铺的分类都至少获得6位以上顾问的同意。在只包含汉语和英语的44家中餐馆中,汉语单语的20家中餐馆中只有30%(N=6)被归类在白领及以上,首要语言为汉语、次要语言为英语的14家中有64%(N=9)被归类在白领及以上,第一语言为英语的10家中有90%(N=9)被归类在白领及以上文化阶层。在外语为首要语言的餐厅中也存在这种现象,汉语为首要语言的9家非中餐廳中只有2家被归类到白领及以上文化阶层,而外语为首要语言的45家非中餐厅中,有40家被归为白领及以上文化阶层。可以看出,在上海,私人标牌的语言首要关系确实与对应的文化权势有关,不同文化的经济水平、文化影响力各不相同。英美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化权势,而日本文化在上海具有大量爱好者,其对应的日语也体现出了较高的文化权势。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所对应的族群在上海人数较少,但是在餐饮方面具有非常高的文化权势,因此,这几种语言在餐饮业的私人标牌中也体现了较高的文化权势。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点注意几种语言,第一为朝鲜(韩国)语。韩国人在上海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族群数量在外籍族群中可排进前三,但韩国文化在中国人群体中文化权势较低,因此语言景观制定者在选择语种上更倾向使用英语和汉语这种相比文化权势更高的语言作为首要语言。不仅在标牌上如此,其内部语言景观也存在这种现象,如图2所示,该韩餐馆(目前在上海韩国餐馆总体评价排名第一)内部的语言景观中有一部分只使用汉英双语,而在出现朝鲜(韩国)语时也是作为第三语言使用。
图2 韩国餐馆的内部语言景观
在一些餐饮文化权势较低的餐馆中,我们也能发现其文化对应语言通常不作为首要语言出现,包括德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等。我们调查的中东餐厅中,土耳其餐厅使用了英汉双语,摩洛哥餐厅使用了英语单语,二者都以英语作为首要语言出现,如图3。
(三)语言景观中的文化先例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一个初步的猜想:私人标牌的语言权势受到了其对应的文化权势的影响。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语言权势和文化权势具有对应关系呢?
图4是一家中餐厅标牌,使用了汉语单语。我们能发现“很高兴遇见你”其实是来自于“Nice meeting you”的翻译,并不是汉语的原生语句。在调查中,大多数顾客都能反应出这个语句所对应的英语,因为,这个单语标识不仅体现了汉语所对应的汉文化的文化权势,同时也反映了英语的文化权势。
在上海的私人标牌中,我们发现有两家韩国面包房,他们的标牌中使用了中文,但是文本中出现了“巴黎”这一词,看上去是体现了汉语对应的文化权势,但同时将法国(擅长面包制作)的文化定型体现了出来。
上文提到,在对私人标牌的话语消费者的访谈过程中,许多被访者表示并不能朗读、理解店名,但是却可以从中体会到一些文化特质,比如“花水木”“酒吞”“da Ivo”“La Casetta”“Al borgo”等,这些文本直接体现了一种文化特质,其文本本身的信息传递功能则已经消失。又如,汉语语言景观中的“日本料理”中的“料理”是“菜”的意思,但是这里使用和制汉语词也是为了添加一定的日本文化特质在里面。因此可以说,许多汉语标牌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日本文化权势在内。
六、结 论
在城市语言生态系统中,私人标牌所体现出的语言权势并不能直接体现所对应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而是受该系统中的文化权势的影响。权势高的文化会使对应的语言获得高于其对应群体社会地位的语言权势,而权势低的文化会使对应的语言权势降低,甚至其主体地位会被其他强势语言取代。上海的城市语言系统正是如此,英语所对应的社会群体地位低于汉语所对应的主体群体,但是在私人标牌中,由于英语对应的文化权势过高,英语的语言权势也获得了过度的提升,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汉语。同时,我们发现在通过语言景观分析文化权势时不能认为单语与单一文化、多语与多元文化是一一对应的,单语中所包含的对应其他文化的文化先例本质上也体现了另一种文化的文化权势。
注 释
① 参见http://www.stats-sh.gov.cn/tjnj/tjnj2014.htm。
参考文献
皮埃尔·布迪厄 2015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尚国文、赵守辉 2014a 《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6期。
尚国文、赵守辉 2014b 《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特雷·伊格尔顿 1987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俞玮奇、王婷婷、孙亚楠 2016 《国际化大都市外侨聚居区的多语景观实态——以北京望京和上海古北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张媛媛、张斌华 2016 《语言景观中的澳门多语状况》,《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赵蓉晖等 2010 《上海世博會外语环境建设研究》(综合报告),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赵蓉晖等 2012 《上海市公共场所外文使用情况调研报告》,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Bouchard, Donald. 1980.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by Michel Foucaul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airclough, Norma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a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nd Blackwell.
Haugen, Einar. 1972.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San Francisc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oggart, Richard. 1997. The Tyranny of Relativism: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Society. St. Loui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Landry, Rodrigue and Richard Y. Bourhis.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1), 23-49.
Malinowski, David. 2009. Authorship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 Multimodal-Performative View. In Elana Shohamy and Durk Gorter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New York: Routledge.
Scollon, Ron and Suzie Wong Scollon. 2003.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London: Routledge.
责任编辑:姜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