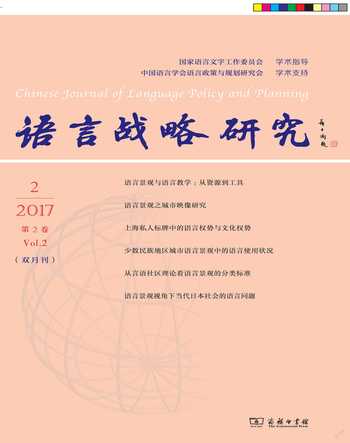论当今普通话的民族性及其他
2017-05-30侍建国
提 要 本文根据中国六十多年来推广普通话的全民实践,提出当今汉民族语口语的乡音特色反映了说话人的本族语意识,体现了整个民族自觉地将共同语视为全民交际语。在当今的中国语境下,民族语不完全等同个人母语,后者指个人早期自然获得的方言,前者则是依靠文化传承所习得的全民交际语。鉴于个人母语跟方言和民族语有交叉,本文使用民族母语。当前汉民族之间通行的、带乡音特色的“普通话变体”是民族母语的常见口语形式,它与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有着本质的不同。
关键词 民族母语;方言;普通话变体
On Putonghua and Its Han Ethnicity
Shi Jianguo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outcomes of the nationwide use of Putonghua promoted for over 60 yea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an speak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or with different dialects are aware of their local accent, thinking that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ir ethnicity or regional identity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regard the common language as a nationwide lingua franca.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in China, national language is not synonymous with individuals mother tongue. Whereas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dialect being acquired naturally, the former is a result of heritage transmission by oral communication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differentiate Putonghua variation, i.e., Putonghua with an accent, which is widely used among the Han people, from interlanguage, second language or foreign language.
Key words native language; dialect; Putonghua variation
一、当今普通话的全民性
(一)普通话由六十年前的北京话成为当今全民交际语
普通话是中国语境下的一个特定概念,作为中国各方言区之间通行的交际语已经存在了六十余年。就其早期形式而言,从1913年由各省选派代表参加的“读音统一会”算起,政府推行的以北京音为基础的汉语共同语流行至今已有一百年了。这一百年里,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对推广普通话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五四运动”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继而“新文学的发展也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巩固了白话文的社会基础”(王本朝2013:159),从根本上奠定了“国语运动”的社会基础;二是1955年开始的全民推广普通话运动;三是电视的普及促进了普通话标准音的传播;四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各方言区人口的流动,这也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通话的普及。
然而,普通话所指的对象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已经悄然变化。六十年前说的普通话主要是以北京话为主的标准语,全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说普通话;当今广大人民说的普通话则是带各种方言特色的与标准语有差异的“普通话变体”。可以说,当下的普通话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民的基本语言能力。
(二)当今普通话的语言学性质——普通话变体
因此,当今普通话的语言学性质还有待探讨。学界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普通话只有标准与不标准的差别,二者没有本质的不同。这种观点以羅常培、吕叔湘(1956)为代表,他们预测当时的共同语将会被规范的共同语替代。另一种观点主张把当下的标准普通话与全民交际语区别开来,但二者的名称各不相同,有的叫规范普通话—大众普通话(姚德怀1998),有的叫国语—普通话(戴昭铭2000),有的叫广义普通话—狭义普通话(李贞2002),有的叫标准语—通用语(侍建国、卓琼妍2013)。下面先讨论二者是否应该分开。
罗常培、吕叔湘的观点是基于当时普通话的两大不足提出的: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大多数人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二是当时书面语的规范还不明确。经过六十多年的全民推普实践,现在这两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大多数人都会说普通话,书面语的规范也很明确。回过头看,如果当时将标准语与全民交际语分开,普通话的现状可能不是这样,会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流行的蓝青官话。在缺乏普通话规范音的概念并且很少人会说普通话的情况下,不把标准语与全民交际语分为两种不同的普通话,这对确立标准语的规范地位和推广普通话来说是有益的。我们在讨论二者是否应该分开时,不能脱离历史。
再看普通话的现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0年、2010年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已有超过70%的人能用普通话沟通,九亿普通话人口中大部分人把普通话看作超越方言的全民交际语。2000年的调查材料中,入户问卷有两个问题是针对被调查人说普通话的动机以及对普通话交际的满意度的,即“您为什么要学(说)普通话”和“您希望您的普通话达到什么程度”。对于第一个问题,选择“工作和业务需要”以及“为了同更多的人交往”共占74.54%,选择“为了找更好的工作”只有2.97%。从中可以看到国人主要把普通话当作交际语,“工作和业务需要”也可看作交往目的。如果说普通话能跟好的工作机会直接挂钩,应该有更多的人选择“为了找更好的工作”。交际满意度的调查是根据被调查人的主诉,设有四个选项:1.能流利准确地使用;2.能熟练地使用;3.能进行一般交际;4.没什么要求。数据显示选择3.和4.的共55.1%,选择1.和2.的共44.9%。因此可以认为,在多数国人看来,普通话作为交际语只要能沟通就令人满意了。
从普通话运用的现状看,经过六十多年的全民推普实践,当年罗常培、吕叔湘预测“规范的共同语”(即标准语)将为全民所使用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不能苛责学者的预测。语言运用的前景难以预料,它受到社会变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标准音的推广力度也并非不够,电视的普及(包括电影、电视剧、儿童片的宣传)大大加强了标准音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这是以往任何推广手段都无法比拟的。
二语习得的实践说明,一个人掌握自己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且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较长的时间。况且也不是依靠练习人人都能说一口标准音。我们看到周围不少人,经过很长时间练习依然发不准标准音。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是认为学习语言的能力特别是发音能力是无限制的、无代价的,事实上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任何语言能力的获得或者添加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我们不应强求全民语言的口语形式都达到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以德国为例,德语经过五百多年的标准化,至今只有很少德国人(大概人口的五分之一)把标准德语作为母语(Mattheier 2003:237-238),而能说标准音的人口则更少(Davies & Langer 2006:118)。①德语的词有丰富的形态变化,标准化工作主要在正字法和语法上,不在正音上。②作为音素文字的德语尚且如此,对于方音之间既有对应又有不同历史演变的汉语大家庭,加上其表意文字的属性,自然难以提高大众口语的发音门槛。因此有学者(如徐杰、董思聪2013)提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应该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
比较六十年前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状况,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推普初期标准音作为一个不常听到的语音形式,需要大力推广才达到今天的普及状况。六十年前将“规范的共同语”作为推普目标,是政府的语言规范行为,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今天的普通话现状来说,无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今标准音比比皆是,手机、网络上唾手可得,人们不仅对它有清晰的概念,而且还能模仿发音。实际上,当今的共同语已经演变成为六十年来在标准音指引下的融合各地方音特色的“普通话变体”。以下讨论标准普通话和各地普通话变体的分合。
郭熙(2006)在比较普通话标准语和华语时说,普通话的标准是国家语言权力机构对语言干预的直接结果,而华语是自然形成的。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汉民族标准语和当下的汉民族共同语:制定普通话的标准是政府的语言规范行为,由六十年的推普实践而形成的普通话变体则是全民运用规范的自然结果。这两种语言形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后者是在长期规范指引下形成的语言形式,从语言性质上,应该给予它合适的“名分”,即将普通话变体从普通话标准语概念中分出来。从已有的名称看,有两种分法:一是将标准语分出来,二是将普通话变体与共同语对应,保留现在“普通话”的标准语概念。根据六十年来的普通话定义,标准语一直是该定义所规定的语言形式,而普通话变体的语音形式并不符合标准音,所以将普通话变体与全民共同语对应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做法。
(三)汉语的规范式和运用式并存
以上區分对于标准语在新形势下的地位并没有影响。首先,只有在标准语存在的条件下才能有共同语的健康生存空间,标准语与共同语反映了汉语的规范式与实际运用式的两种形式,二者在中国语境下互依互存。其次,中小学语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推广都需要标准语。然而,为语文(即民族语)教育设定的语言标准是为了树立典范,实际的运用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化程度,这也是“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目的,它对促进使用标准语有指导作用。
再看语言结构的其他方面。先说普通话书面语。由于教育的普及,加上广播电视带来的普通话标准语的传播,无形中也推广了书面语的规范,可以说现在普通话的书面语与六十年前的情况比起来,其规范程度比普通话口语还高。然而,目前网络语言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规范,语言学家需要适应这种时代潮流,从传统的规范观念中另辟途径。
再看词汇和语法。在比较方言与标准语的异同时,经常强调二者的不同。从历史的角度看,“方言间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照例是大部分相同的”,包括标准语,它们都是“同一语言的继承和发展”(袁家骅等2001)。比如“得意”,《管子·小匡》云“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现代书面语里有“十分得意”;粤语还引申出可爱义,如“个细佬好得意”;东北话可说“我得意你”(也写作“德意”),是“我喜欢你”,当动词用,还带宾语。其实,从数量上看,方言与标准语在词汇和语法上的相同点大于不同点。拿粤语与标准语相比,就人体的词汇或者亲属称谓名词而言,粤语方言词占36%,其余的都跟普通话相同;如果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词汇,二者的相同数量高达90%(欧阳觉亚1993)。
因此,标准语跟方言之间的主要不同在语音上。鲍明炜(1955)根据汉语书面语的形成和发展提出“标准语问题实际上只是标准音问题”。笔者进一步提出:鉴于方言和标准语并非对立,二者具有较整齐的对应关系,根据语音系统对应的整齐与参差,当今的汉语标准化除了有国家标准,也应该接受区域变体和场合变体。这里有三个概念:一是国语,即标准音;二是区域变体,指特定方言区域内通行的普通话变体,如粤港澳地区流行的普通话变体就是带粤方言特点的普通话区域变体;第三是场合变体,指不同场合使用的普通话变体,如两个不同方言区的人日常对话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场合变体也包括一个能说标准语的人跟家人、朋友对话的语言形式。Labov(2012:13—14)比较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三种不同言语场合里“尾g省略”,发现奥巴马从最正式的场合(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接受总统提名的有讲稿的发言)到一般的正式讲话场合(父亲节仪式上回答记者的政治性提问),再到随意场合(父亲节在白宫草坪烧烤时跟大厨的聊天),其“尾g省略”的情况成比例增长,最正式的场合“尾g省略”只有3%,正式讲话里出现33%,随意场合里出现72%。据此,笔者认为当今的汉语标准化应该是一个跨方言区域、多场合交际的融合过程,一个人的共同语口音越接近标准音,其跨区域交际和多场合交际的可懂度就越强。
二、当今共同语的民族母语性质
(一)普通话变体的文化因素——共同语的民族性
汉民族运用共同语的自然规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使用的公民性,二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民族母语性。语言使用的公民性可理解为公民在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利时应该具备的国家语言能力,汉民族共同语的民族母语性指中国汉民族人民的母语能力,二者可分别称为国家语言能力和民族母语能力。既然这里的语言运用指全民交际语的使用,这两方面就具有相关性,即现今的共同语就是两千多年来形成的民族母语。国家语言能力的设定应该充分照顾大多数公民的语言能力。当今汉民族共同语的成因有二: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另一方面是语言学因素。民族母语流行的社会成因比较容易被觉察,它的语言学成因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体现在对普通话的性质以及所谓“地方普通话”③的认识上。
众所周知,一个人能否较快地学会另一种语言,其中一个因素在于第一语言跟目标语在类型上是否相近。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方言之间的互懂度只是一个方面,各方言与标准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结构要素之间的对应性以及语言使用的社会政治因素是另一方面,后者在语言身份的识别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孙宏开(2013)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讨论语言身份识别,必须综合考虑语言结构要素以及社会政治因素,他说(2013:457):
本民族对母语间的差异是最敏感的,哪些语言能够通话,通到这[什]么程度,他们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们对语言内部的差异比较敏感,一般一个语言内部存在方言或土语差异的,一开始互通可能有困难,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慢慢地沟通。
这段话是针对中国民族语言的情况,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区域身份识别功能亦是如此。
再看国家语言与公民的民族母语关系。单语国家公民的国家语言能力与公民的民族母语一般不发生冲突,国家语言就是民族母语,公民的国家语言能力可以通过提高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来实现。但在多语言、多方言甚至多区域文化的国度里,如果某种语言形式被规定为国家语言,那公民的国家语言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公民的第一语言跟国家语言之间的相似度有关,这种相关性可从文化认同和语言结构两个方面考察。
先说文化认同。如果各地不同的区域文化都是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不同区域的人对于国家认同以及对于国家语言自然就产生认同感。中国公民的区域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发生矛盾,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他既属于这个国家,也属于他生长的那片乡土。国家语委200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大多数公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方言,这一现象说明方言依然是汉民族人民区域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记,这既是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个人的区域身份主要由语言来体现。语言认同是一种最直接也最易获得接纳的身份认同,这是乡音对于汉民族人民的情感维系,它具有一种赤裸裸的乡土归属感,一种内心深处不可或缺的文化慰藉。
再看汉族人民对汉字的崇敬。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里,文字形式的語言(包括它的语音)一直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它也是儿童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西汉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两位汉代学者说的古者八岁入小学,必须先辨认汉字字形和学会读音,说明以汉字表达的语言对于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后来的《三字经》等儿童启蒙读本也是为了学习民族母语的书面语及其语音形式。
因此,在汉语这个语言大家庭里一直延续着一种现象: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不同区域流行着不同的方言口语,但整个民族的书面语(包括它的读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一致的,它的书面语音是超方言的。这就自然形成了汉民族特有的民族母语观:日常生活使用方言口语,重要场合使用正式的语言形式,后者能以汉字完整地记录下来。这种正式语言的读音也随着时代而变化,它的名称亦不断变化,最早称“雅言”,后来称“通语”,此后在“雅言”或“雅音”之前冠以地名如“洛阳音”“金陵音”“中原雅音”,明清时称“官话”,清末称“国语”,现在叫“普通话”。
(二)个人母语(母言)和民族母语④
从文化和民族的角度看,汉民族母语两千多年来一直延续着两种显而易见的形式:一为摇篮里学会的言语形式,可称方言、母言;一为接触启蒙读物时的书面语形式,可称民族母语。母言指各方言区的方言口语,民族母语则是整个民族的、主要以汉字表达的语言形式,即汉语书面语。⑤汉民族对于文字所记录之语言的崇敬,不仅是因为书面语的准确性,还因为它是先哲以语言形式传承下来的民族瑰宝。它不但具有语言的魅力,更有民族文化的魅力。这种民族母语观是汉民族文化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个人而言,它是一种在世世代代文化浸濡下形成的精神实质。李宇明(2003:56)把这种民族精神称为民族忠诚,他说“母语是个民族领域的概念,反映的是个人或民族成员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者说是民族忠诚”。
此外,汉民族母语观还来自每个人的母言(方言)能力。汉语的母言和民族母语之间存在着语言结构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从三个方面分析汉语方言的母语性质。首先,民族母语是书面的,也是语音的,这种语音形式是儿童在接触了民族母语的文字形式后通过耳濡目染习得的。其次,从时间顺序上最初获得的语言形式是第一语言,一般叫方言。方言与标准语之间在词汇、语法、语音上具有较严格的、可追溯的对应关系。第三,在汉语方言和标准语长期共存的过程里,不少词具有两种不同的读音,一种是方言读音,一种是标准语读音,如扬州话的“街”有[kε]/[t?iε]两个读音,前者是方言的,后者是标准语的。⑥赵元任(Chao 1947:6-7)提出汉民族语言里存在一种叫“wenli”⑦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书写的,也是传承智慧的、朗读的、背诵的,是各方言共有的部分。赵先生所说的“wenli”可能代表了民族母语意识,他晚年用了十几年时间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大概就是为了实现这种民族母语意识。
三、“普通话变体”不是“中介语”
(一)“中介语”是外语学习者的个人语言
当今汉语方言区的人所说的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变体,常被称为“地方普通话”。不少学者关注过它,也做了不少分析,但这些研究大多把“地方普通话”等同外语(或者第二语言)学习过程的中介语。中介语是二语习得理论的术语,它指第二语言学习者自己形成的一种发展目标语的能力,它会将第一语言的规则不适当地运用于目标语,从而产生不符合目标语规范的偏误。中介语和“化石化”的概念自从1972年提出以后,就被广泛地运用于二语学习偏误。我们必须承认,普通话变体的某些特征与中介语确有相似之处,如普通话变体有方言规则的负迁移,也会发生标准语规则的不适当运用,即所谓“矫枉过正”,这些相似点使得普通话变体看起来属于中介语。
中国学者近几十年来也开始注意到方言区的人所说的带区域特征的“地方普通话”这一特殊的言语形式,并将这种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与标准语比较,分析当地人在学习北京音时易犯的错误。如陈章太(1983)在分析普通话口语的第三等级(最低级)时说这种普通话带有较浓的方言色彩,该文从语言规范的角度为“地方普通话”提出了具体的衡量指标:语音上不合《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不应超过6项,词汇上不应超过所用词汇总数的7%,不规范的句子不应超过所说句子总数的6%。陈章太虽然承认不同方言区的人使用这种语言形式彼此都能听懂,但还是把它定性为不合规范的学习偏差。陈建民、陈章太(1988:115)以社会语言学观点对“地方普通话”提出新的界定——过渡语,认为它属于中国交际语言的一种形式,“是方言向普通话过渡的产物”,“是介乎方言与标准普通话当中的过渡语,在推广普通话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该文明确提出要研究各地过渡语跟标准语的差异,为的是“怎样使它更好地向标准普通话过渡”。
李如龙(1988)的“过渡语”概念虽然还未脱离中介语的藩篱,但已经开始注意到“过渡语”的特性。他提出过渡语是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相互影响的中间环节,一个方言区里多数人所说的过渡语具有“大体一致的系统性”。这里所说的“多数人”可视为“过渡语”的普遍性和认可性,而“大体一致的系统性”可视为这种形式具有相对稳定的语言结构。
还有另一种中介语的解释,认为地方普通话“实际是一种中介语,一头联系着标准普通话,一头联系着方言”(李蓝2001:19),但这种言语形式是地方普通话还是接近普通话的方言,难以界定。国家语委2000年对语言调查员的指引是“两层皮,一刀切”,所谓“两层皮”,指说话人的地方普通话跟说话人的方言在音系上已经形成明显差别,属于两种音系;“一刀切”指“不管这种普通话规不规范,只要音系已基本转换成普通话的声韵调,就算是普通话”(李蓝2001:19)。
(二)“普通话变体”表现了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转化
有学者从另一角度观察“地方普通话”的语言性质。劲松、牛芳(2010)对长沙人戏称的“塑料普通话”进行了调查,发现在高学历的年轻群体中流行一种长沙普通话——固化的地方普通话,并认为它与一般的长沙普通话有本质的不同。⑧该项研究调查了42個高学历的年轻人,他们都能熟练地使用较标准的普通话,但在公共场合却主要使用一种固化的长沙普通话。说话者认为这种“地方普通话”可凸显自己的地域身份和社会地位,并且在公共场合运用它能产生一种区域认同感和友好感,而使用标准语则缺乏这种由身份认同而产生的示好功能。显然,跟上世纪把“地方普通话”归为“不合规范的学习偏差”或者把它看作暂时的过渡形式这两个观点比起来,这种代表区域身份特征的普通话变体理论为汉语语言学提出了新挑战。虽然劲松、牛芳仍将这种言语形式归为固化的中介语,但其实它已超出中介语范畴了,因为中介语不包括已经掌握了目标语却仍坚持使用有偏误的形式,即我们不能说奥巴马在白宫草坪烧烤时跟大厨聊天时所用的英语“发音有偏差”。
固化的长沙普通话例子代表了“地方普通话”的一种情况,此外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从未受过正规普通话训练并且在上学期间老师都用方言授课的低学历(初中)中年人在跟外地人交际时所使用的言语形式。笔者过去三年曾指导硕士研究生对江苏泰兴、江苏南通、海南文昌、山西太谷、广东东莞这五个方言区的普通话变体进行调查,分析说话人的方言向标准语转化的语音规律。五地的调查报告一致认为,普通话变体既区别于当地方言,又区别于标准语;它与方言和标准语在语音系统上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说话人都能运用这种对应关系。运用手段有两种:“沿用”和“转化”。“沿用”指将方言语音成分(声、韵、调)直接搬进普通话变体,“转化”指说话人在方言与标准语之间所做的自发性对应。这两种手段可以让不懂自己方言的人大致理解说话人的意思。调查报告还显示,说话人对于标准语具有一定程度的感知,因为说话人的实际发音是朝着标准音的方向转化的。研究者认为,这种自发的转化能力只能从方言与标准语的对应性上得到解释。
当然,如何具体分辨“自发的转化”和有意识学习过程中的偏差,普通话变体理论还需更加深入。但无论是自发转化还是学习偏差,汉语方言与标准语之间在语言结构要素上的共性占据主导作用,而外语学习过程的中介语在学习者的个人母语和目标语之间基本不存在语言结构要素上的任何共性,这是当今普通话变体与中介语概念的本质不同。下面举个例子说明什么是语言结构要素的共性。国人初学英语,记不住英语单词发音,就以方言词语帮助记忆,比如,英语的“thank you”至少存在南北两个地方口音版本:东北人说“三块肉”,吴语区的人说“生果油”(指花生油)。“三/生”的声母[s](齿龈擦音)对等英语“thank”的开头辅音[θ](齿间擦音),“块/果”的声母[k‘](舌根送气塞音)对等英语“thank”的收尾辅音[k],“肉/油”音节直接对等英语的“you”,因此,如果不计音节数量(英语是两个音节,汉语是三个音节),“三块肉/生果油”与“thank you”之间存在一定的语音相似度。然而“三块肉/生果油”在东北话和吴语里并没有“谢谢”的意思,如果没有人告诉学习者该短语是英语“谢谢”的意思,学习者自己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方言里这个词语在语音上接近英语的“谢谢”,因为英语和汉语方言之间不存在任何语言结构要素的共性。
再看汉语标准语的动词“打”与各地方言读音的差距。“打”的声母从古到今都是[t],没有变化。根据曹志耘(2008)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打”的韵母在汉语方言里有三类读音:官话区读如假摄的[a/A, , O, o, ?]等;江浙一带读如梗摄的[a?/A?, an, ?/, ?i/i]等;少数不读如假摄或梗摄的方言,其发音为[a/, ε/?, O, o, ai]。所以现代方言“打”的韵母实际发音要么是口腔元音,要么是元音加鼻音。从“打”的历史来源看,中古音韵地位是开口二等上声梗韵端母,拟音为[ta?]或[t??]。读[ta]应始自敦煌变文(都兴宙1985),韵尾鼻音脱落。由此看出现代方言“打”字读[ta]或者[ta?],它们与标准音[ta]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方言区的人学习标准语的“打”不需要记忆,凭借类推就可以了,因为方言跟标准语在语言结构要素上具有共性。
四、结 语
全民语言能力应建立在汉民族人民本族语观的文化传承和语言自信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任务,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公民的语言能力无疑是公民文化素质最基本、最便于实现的一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国民都能对自己所说的共同语具有自信心,自然会增加对国家语言的认同感。因此,提高国家语言的认同成为培养公民文化自信的任务之一,汉语的语音规范也关系到公民社会里如何提高公民意识和文化自信的任务。历史证明,汉民族的方言和标准语相互依存、和谐共处,普通话作为当今全民共同语的标准形式是民族母语的代表,在国家语言体系中具有主导地位;而各地人民日常生活的方言无时无刻不在为全民共同语包括它的标准语增添新鲜养分,这正反映了汉语方言和标准语之间“和而不同”的本质。
注 释
① 德语标准化从15世纪的城镇化开始,到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以东中部德语方言的区域书面语翻译德语版《圣经》,使得该区域书面语成为一种超区域的书面语,路德称之为“语言模范”;再到德国印刷中心(如Saxony、Leipzig等地)所采用的语言形式,后期再加上规范语言学家的推广而形成(参见Davies & Langer 2006:74)。现代标准德语的发音最接近德国北部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的语音。从语言结构上,现代标准德语的词汇、语法、音系主要来自高地德语方言,而标准音的语音特点却更多地受到低地德语方言(指德国北部——笔者注)的影响(参见Barbour & Stevenson 1990:50)。
② 印欧语的正字法并不完全为了发音规范,它也有词形上(视觉上)的分辨功能,如法语的同音词pin,pain, peint有不同的词形(Lodge 1993:105)。
③ “地方普通话”的概念早已有之。王力曾提到的上海普通话、广东普通话就属于一种区域普通话(王力1954)。因那时以方言冠名的普通话缺乏标准语的基础,缺乏全民参与的社会环境,因此半个世纪前的“方言普通话”跟当前的“地方普通话”属不同概念。
④ 本文“母言”不同于“母语”的概念也参考了英国作家、语文学教授约翰·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native language”不同于“cradle tongue”的观点,他于195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参见Tolkien 1955/1963:36)。他的“native language”指不同于第一语言的、由本族传承下来的语言能力。
⑤ 香港人的母言和母语意识与内地人不同是有历史原因的。英殖民统治时期,港人的日常口语是粤语,中文书面语也是粤语语音,所以老一辈的港人有很多受过中文教育却完全不会说一句普通话。回归以后,香港的中小学逐步用普通话教中文,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
⑥ 这样的一字两读也叫文白异读。方言、共同语的不同读法是形成文白异读的主要因素。
⑦ 赵元任说wenli是西方学者根据中文造的英文词。
⑧ 劲松、牛芳(2010:46)认为一般的长沙普通话使用者还未掌握标准语,所以语音偏差因人而异,缺乏一致性;而固化的长沙普通话在语音上一致性很高,与标准语的相似度也高。
参考文献
鲍明炜 1955 《略论汉族共通语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语文》6月号。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建民、陈章太 1988 《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中国语文》第2期。
陈章太 1983 《略论汉语口语的规范》,《中国语文》第6期。
戴昭铭 2000 《汉语研究的新思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都兴宙 1985 《敦煌变文韵部研究》,《敦煌学辑刊》第1期。
郭 熙 2006 《论华语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劲 松、牛 芳 2010 《长沙地方普通话固化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李 蓝 2001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況调查”中的汉语方言问题》,《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学报》(综合版)第4期。
李如龙 1988 《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过渡语》,《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李 贞 2002 《共同语和标准语——对普通话定义的思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李宇明 2003 《论母语》,《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罗常培、吕叔湘 1956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北京:科学出版社。
欧阳觉亚 1993 《普通话广州话的比较与学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侍建国、卓琼妍 2013 《关于国家语言的新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孙宏开 2013 《关于语言身份的识别问题》,《语言科学》第5期。
王本朝 2013 《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王 力 1954 《论汉语标准语》,《中国语文》6月号。
徐 杰、董思聪 2013 《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应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语言科学》第5期。
姚德怀 1998 《“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58期。
袁家骅等 2001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语文出版社。
Barbour, Stephen and Patrick Stevenson. 1990. Variation in German: A Critical Approach to German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o, Yuen Ren. 1947. Cantonese Prim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Winifred V. and Nils Langer. 2006. The Making of Bad Language. Lay Linguistic Stigmatizations in German: Past and Present. Frankfurt: Peter Lang GmbH.
Mattheier, Klus J. 2003. German. In Ana Deumert and Wim Vandenbussche (eds.), Germanic Standardization: Past to Present. Amsterd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Labov, William. 2012. Dialect Diversity in Americ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Lodge, R. Anthony. 1993. French: From Dialect to Standard. New York: Routledge.
Tolkien, John Ronalol Reuel. 1955/1963. English and Welsh. In Angles and Britons (ODonnell Lectures).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責任编辑:姜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