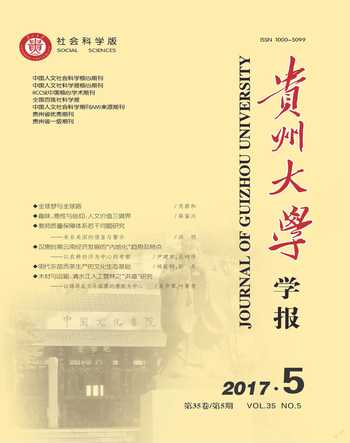莫言《四十一炮》中的乡村书写及其意义
2017-05-30魏家文
魏家文
摘 要:《四十一炮》是当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对欲望的变态追逐使得整个乡村日益陷入道德沦丧与人性迷失的失控局面。对此,作家并没有将之简单归结为外部的社会原因,而是从人性弱点的角度探讨其深层原因,着重探讨人类生存的困境与出路问题。从总体上看,莫言的乡村书写接近赵树理的立场,但与赵树理纯粹的农民立场不同,莫言摆脱了单纯的农民立场的局限,将一种来自现代的外在视角和源自民间的本地视角融合在一起,从而建构了一种乡村书写的新范式。
关键词:
《四十一炮》;乡村书写;欲望;乡村立场
中图分类号:I206.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5-0146-04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5.24
莫言是当代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莫言眼里,“社会生活、政治问题始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可不关注的重大的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也永远是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最主要的一个题材。” [1]莫言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小说极少从政治层面对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从民间立场出發,立足于人而非阶级的、政治的立场来关注当下社会中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变化,将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通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以隐喻的形式表达他对现实的针砭。
《四十一炮》就是这样一部体现莫言个人风格的小说。小说通过一个身体已经长大但精神依然停留在儿童时代的罗小通的诉说,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及其所在村庄的变迁史,展示了1990年代改革之初,一个名为屠宰村的村庄在商业化浪潮中农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蜕变过程,在揭示人性裂变与扭曲的同时,也写出了在非理性欲望的刺激下,整个村庄日益陷入道德沦丧与人性迷失的失控局面。
一、社会变革中的乡村图景
在传统社会里,农村和城市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两极,彼此之间是一种并置和静态的关系,城乡之间虽然有差距,但这种差距是自然形成的,二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这种情况到了现代之后发生了改变,城乡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并置、静态转向对立和动态。由于现代文明首先在城市登陆,城市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乡村则意味着愚昧和落后。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乡之间的差距和隔阂逐渐加大。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农业集体化大生产、统购统销、工农产品剪刀差以及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全面实施后,广大农民逐步成为落后愚昧的“乡下人”、沦为“城市发展祭坛上的牺牲品” [2]。
莫言出生在1950年代,饥饿与贫穷是他与同时代人共同的人生记忆之一。对长期处在饥饿与贫穷中的人而言,贫穷与饥饿强化了人的欲望,人一旦有了摆脱这种境遇的机会,他们长期受压抑的欲望往往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为了欲望的满足往往不择手段。对《四十一炮》中的村民而言,这一切除了受时代的影响之外,还与城市人对农村人的伤害有关。
不可否认,在农村实行大规模的改革之前,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由于物质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人在城市人眼里被视为贫穷愚昧的“乡下人”,进城的乡下人往往受到城市人的嘲笑和歧视。村长老兰在省城一家饭馆吃饭时,因为拿着菜单不会点菜受到服务员的嘲笑,称乡下人只配吃由别人吃剩下的菜放在锅里“咕嘟咕嘟”煮成的“大烩菜”。当老兰对一道“青龙卧雪”的菜提出异议时,服务员则讽刺老兰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土鳖”。这件事极大地伤害了老兰的自尊,虽然老兰对此非常愤怒,但因为当时人穷志短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他因此在心里默默许愿,将来有机会,一定会加倍偿还城市人给自己的伤害。老兰的经历并非个案,类似的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在当时一再上演。城市人对农村人的伤害必然会造成城乡之间的对立,激起农村人对城市人的怨恨。可以想象到,农村人一旦有了报复城市人的机会,他们就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屠宰村人也不例外。
屠宰村原本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村民们一直过着物质贫穷但精神相对富足的生活。改革开放之后,屠宰村人在村长老兰的带领下,很快放弃了辛苦而收获菲薄的农业生产,开始成为远近闻名的屠宰专业村,为城市人提供肉食品。村民为了谋取暴利,在村长老兰的示范和带领下,注水在屠宰村大行其道,牲畜不论死活,不论牛、羊、猪,全都注满了污水,甚至有时候鸡蛋也难以幸免。后来,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屠宰村人用活畜注水法代替了死畜注水法,屠宰村的造假事业达到了顶峰,最终到了唯一没有注水的就是井水的疯狂状态。与此同时,靠注水富起来的屠宰村人,一改过去对城市人的羡慕和尊敬,开始用鄙视和敌意的眼光看待城市人:“城里人器官退化,根本分不出牛肉的好坏。真有上等的肉,也不应该让他们吃。好东西进了他们的嘴巴,等于白白地糟蹋。” [3]245农村人把注水的肉食品销往城市的时候,他们收获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对城市人报复后的快感。
二、乡村的沉沦与人性的堕落
屠宰村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是当时中国非正常欲望极度膨胀的社会现实的投射。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莫言对乡土中国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人性的异化和乡村的整体沦陷忧心忡忡。莫言认为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高度的欲望化,疯狂的金钱欲,变态的食欲,夸张的性欲,我觉得这是社会普遍的堕落。” [4]莫言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直接发表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而是通过主人公罗小通充满狂欢色彩的诉说来再现现实。尽管罗小通的诉说虚虚实实,真假难辨,但在1990年代中国社会非正常欲望极度膨胀的大背景下,乡村的沉沦与人性的堕落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小说除了对屠宰村全民疯狂造假的揭示外,农村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人物命运的前后巨大反差等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更是作家关注的重点。
首先是村民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屠宰村人过去由于贫穷而倍受城市人歧视,因而现在对金钱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现在这个时代,有钱就是爷,没钱就是孙子。有了钱腰杆子就硬,没钱腰杆子就软。” [3]184为了赚钱,村长老兰将他发明的注水法无偿传授给大家,成为黑心致富的带头人。在村长老兰的示范和带领下,屠宰村人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彻底革命,注水成为绝大多数村民的共识。当罗通对村长老兰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时,老兰的理由是:“罗通,我知道你对大伙往肉里注水有意见,但你睁开眼睛去四乡里看看,不光是我们村往肉里注水,全县、全省甚至全国,哪里去找不注水的肉?大家都注水,如果我们不注水,我们不但赚不到钱,甚至还要赔本。如果大家都不注水,我们自然也不注水。现在就是这么个时代,用他们有学问的人的话说就是‘原始积累,什么叫‘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就是大家都不择手段地赚钱,每个人的钱上都沾着别人的血。等这个阶段过去,大家都规矩了,我们自然也就规矩了。但如果在大家都不规矩的时候,我们自己规矩,那我们只好饿死。” [3]184-185老兰的活命哲学虽有诡辩之嫌,但当时社会上普遍盛行的拜金主义风气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不仅流行于成人世界,还影响了青少年的思想。罗小通对读书的厌恶和对老师的轻视,就是这种价值观影响的结果。当老师问他八个梨分给四个孩子的方法时,他的回答是“抢呗,现在可是原始积累时期,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拳头大的是爷爷。” [3]189在罗小通眼里,老师所教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老师还没有他知道的东西多,因此他认为在学校读书纯粹是浪费时间。在这种“反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罗小通对世界和人的认识显得狂妄而又浅薄无知。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人很多,但其实都可以用肉来划分,那就是:吃肉的人和不吃肉的人,能吃肉的人和不能吃肉的人。能吃肉但是捞不到吃的人,能捞到肉吃但是却不能吃肉的人。还有就是吃了肉感到幸福的人和吃了肉感到痛苦的人。” [3]293与此同时, 罗小通的自我评价则是病态和扭曲的,他以能够把班主任在课堂上气哭为荣,并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人。罗小通身上所表现出的知识无用论,实际上是1990年代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想在社会上普遍蔓延的恶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家对农村未来的担忧。
其次是村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在集体化农业生产时代,屠宰村村民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过的是一种简朴的乡村生活。打谷场是村民们日常生活和情感交流的主要场所。作为一个表征传统农业文明的特殊的“时空体”,“打谷场的时空体中存在着的,是月光、牛群、田野以及千百年来不变的稳定的生活和行为模式。” [5]生活在这种“时空体”中的村民还延续着农民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他们对外县来的牛贩子卖完牛后不是马上回家,而是进城花天酒地,将腰包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才回家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在村民们看来,这些牛贩子的所作作为根本不像农民,因为他们的习惯与派头与他们熟悉的农民不同。但当打谷场变成屠宰场、村民由农民变为商人后,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复存在,村民的工作不是下地劳动,而是白天给牲畜注水,夜晚将注水的牲畜屠宰后请肉类检疫站的人盖上章,趁着夜色将注水肉运进城。更有部分村民受城市奢华生活的吸引,不再满足于辛苦而危险的造假行为,选择到城市里做一名不劳而获的乞丐,袁七就是其中的代表。村民对此不是同情鄙视而是心生羡慕:“他自己说在十几个城市里都有家眷,他过上了走到哪里哪里有家的幸福生活。袁七吃的是海参鲍鱼,喝的是茅台五粮液,抽的是玉溪大中华!这样的乞丐,给个知县也不换。” [3]261
再次是主要人物命运前后的巨大反差,以罗通和村长老兰为代表。在农村大规模改革之前,罗通和老兰都是村里的明星人物,同时也是一对相互不服的冤家对头。在年青時的吃辣椒比赛和争夺农村美人“野骡子”的竞争中,罗通都占上风。成年后在屠宰村的打谷场上,罗通的大家风范与老兰的小肚鸡肠再次形成了鲜明对比。事情的起因是罗通凭借庖丁解牛般精准的估牛手艺和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赢得了牛贩子和屠户的一直好评,成为儿子罗小通心目中的英雄。老兰为了树立自己在村民中的权威,打压罗通,在打谷场上当着牛贩子和村民的面,故意用尿液来羞辱他,但罗通不为所动,表现出一种罕见的隐忍和大度。尽管罗通的表现让他年仅五岁的儿子罗小通和一些有血性的汉子们感到十分失望,但当老兰被疯牛攻击时,罗通还是不计前嫌出手制服了攻击老兰的鲁西大黄牛救了老兰的命。罗通的所作所为,颇有远古君子风范。罗通不是没有自己的行事底线,当老兰为挽回脸面故意对年幼的“我”说了些混账话后,罗通愤怒之中咬掉了老兰的半只耳朵,可见此时的他还是一个有血性的男人。但当罗通结束流浪再次回到屠宰村时,已经成了一个怯弱胆小的中年人。此时的屠宰村已经是村长老兰的天下,老兰成了村子里呼风唤雨的人物。在村里建立肉联厂实行机械化屠宰后,罗通的估牛本领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他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对村里的新景象和新生活感到无所适从,即使他想与妻子杨玉珍一起收破烂,妻子也认为他干不了。因为根据杨玉珍的经验,收破烂要脸皮厚,半偷半抢才能赚钱。最后,在村长老兰的恩威并用下,昔日村民中的英雄好汉只好忍辱负重担任老兰下属公司肉联厂名义上的厂长。当曾经的手下败将老兰在商场、官场和情场上春风得意时,不适应形势的罗通只能在“超生台”上寻求心灵的暂时安慰,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直到最后,罗通因无法忍受妻子的背叛,在老兰妻子葬礼上斧劈妻子而被捕入狱。
屠宰村所发生的一切,虽然带有荒诞离奇的色彩,却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现实批判意义。尽管作家对乡村沉沦和人性堕落种种乱象的描写入木三分,但作家不是以一种彻底批判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悲悯态度来关照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表现出一种书写乡村的新范式,这一切都与作家的乡村立场有关。
三、作家的乡村立场及其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乡村一直是作家书写的主要对象。但在书写乡村时,作家的立场并不相同。从总体上看,作家书写乡村的立场主要有三种: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立场,侧重于以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眼光审视和批判乡村文化的弊端;二是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反思现代文明立场,侧重于表达对古老乡村文明及生活方式的留恋和肯定;三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自我立场,侧重于以乡村护卫者和农民代言人的身份关注乡村的现实政治问题。从总体上看,莫言的乡村书写接近赵树理的立场,但与赵树理纯粹的农民立场不同,莫言摆脱了单纯的农民立场的局限,将一种来自现代的外在视角和源自民间的本地视角融合在一起,从而建构了一种书写乡村的新范式,《四十一炮》就是这一新范式的代表作。
面对屠宰村村民在潜意识欲望驱使下集体疯狂的造假行为,作家并没有采取高高在上的批判立场,对村民进行严肃的道德审判,而是从乡村立场出发,对村民对欲望的追逐行为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与理解。作为一个1950年代出生的农民的儿子,莫言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与理解:“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 [6]6莫言的饥饿记忆,使他不可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农民进行空洞的说教。在莫言看来,农民放弃传统的农业生产从事商业贸易,是人的天性中趋利避害本能的体现,其背后透露出的是当下农村現实的残酷与无奈。正如小说中的破烂大王杨玉珍说的那样:“现在的庄户人家不是从前了。从前的庄户人从土里刨食,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锅里有馍,碗里有肉;风不调雨不顺,庄家歉收,锅里汤,碗里糠。现在,但凡不是呆傻的,没人再去地里受罪。汗珠子浇透十亩地,赶不上贩上一小拖猪皮。” [3]107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欲望的合理存在与追求,对个人的幸福追求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屠宰村在老兰的带领下,很快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里的基础设施和村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罗小通流浪回来后,屠宰村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屠宰村已经被划入新的经济开放区,开发区内新建了众多的现代化工厂和大楼,在新挖的人工湖周围,新建了大批设计新颖、用材考究的别墅。至此,屠宰村已经从昔日贫穷落后的农村变成了一个生活富裕、景色怡人的度假胜地,宛如充满梦幻色彩的童话世界。
莫言在肯定欲望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欲望泛滥的负面性进行了批判。成名后的莫言坦言自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受到作家能一天吃三顿饺子的诱惑。出于对农民缺衣少食的窘困生活的同情,莫言对村民的活命哲学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莫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渐渐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饺子,也还是有痛苦,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并不亚于饥饿。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一个作家的神圣的职责。” [6]48通过非法手段富起来的村民并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是在对欲望的疯狂追逐中陷入精神的“贫穷”之中。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欲望,村民们可以不择手段,由此带来的土地荒芜、生态环境恶化、伦理道德沦丧、价值观错位等社会问题触目惊心。对这些问题的揭示,体现了作家身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忧虑。”[7]
莫言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乡村沉沦和人性堕落的原因,不是简单地归结于外部的社会原因,而是从人性弱点的角度来探讨人的非理性欲望的根源。在莫言看来,苦难的根源并不完全来自外部,“最深重的苦难来自内心、来自本能。”[6]175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欲望的奴隶,在欲望的诱惑面前,理性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无论是对屠宰村人在潜意识欲望驱使下集体造假行为的揭示,还是对“肉食节”上人们在欲望的刺激下的狂欢与迷醉的描写,都显示出,在欲望的诱惑面前人的理性力量的渺小。这不单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是整个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共同困境。在《四十一炮》中,莫言不是简单地站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探寻乡村沉沦和人性堕落的原因,而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人类生存的困境与出路问题。因此,莫言并不是将《四十一炮》写成一部单纯的社会批评小说或谴责小说,而是直面人的生存困境,把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情感的异化和理性的迷失作为自己关注的重点。作家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悲悯情怀,使得莫言的创作“在抒写时代现象时却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8]这正是莫言的创作受到世界认可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莫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 (1):120.
[2]安本·实.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J].刘静,译.小说评论,1991(1):93.
[3]莫言.四十一炮[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莫言.在文学种种现象的背后[C]//莫言对话新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01.
[5]管笑笑.当时间化为肉身:关于《四十一炮》的解读[J].小说评论,2015(2):106.
[6]莫言.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C].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
[7]张瑞英.一个“炮孩子”的“世说新语”:论莫言《四十一炮》的荒诞叙事与欲望阐释[J].文学评论,2016(2):201.
[8]刘再复.莫言了不起[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3:40.
(责任编辑: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