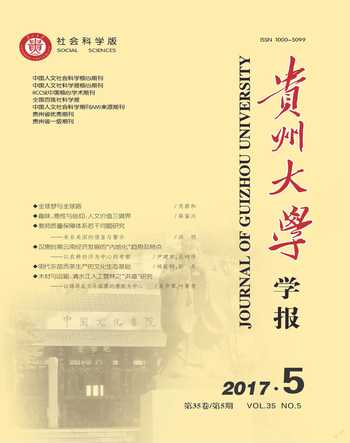“四个自信”的深层哲学意蕴与伦理自信
2017-05-30宋君修
宋君修
摘 要:“四个自信”理论思想不应该停留于一般理论探讨,而是需要深层哲学分析和概念奠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这是“四个自信”所“道—说”的理念。黑格尔的伦理实体概念所导出的伦理自信概念可以很好地释放出“四个自信”理论思想的深层形而上学真切意义。伦理自信不仅表明“我们”是一个有精神的伦理实体,而且表明“我们”必须以伦理的方式来看待和处理相关于这个伦理实体的一切。伦理自信的概念可以常识性地作为我们的方法论,来透入对“四个自信”理论思想的深入探讨,以激发和启示其中所蕴涵着的巨大的理论与实践力量。
关键词:
深层哲学;倫理实体;伦理自信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5-0006-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5.02
一、引 言
在中国改革开放长足发展的时代,在“一带一路”广为讨论和参与的今天,在进一步深层发展和社会问题伴随一道的当前,自信问题越来越凸显出其影响深远的意义,成为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时代命题,即“我们”“中华民族”究竟应该如何走向所必然需要的精神上的自信,以便在深层上催化激发我们所必然面对的古今中外的双重维度的真切文化,从而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可持续的深入发展,适配所必然需要的良性动能环境或框架的时代命题。
在这一问题视域下,作为“我们”时代问题的“四个自信”的深刻理论思想问题,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讨所能够真切承载的。固然,这种一般探讨很重要,然而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却是相应概念的深层内涵的奠基性探讨。这意味着,如果要让“我们”的时代问题真切地发挥出本应有的理论、精神与实践的生态力量或能量,那么与此问题相关的概念的奠基性深层内涵,就必须真切地获得系统性的分析研究,从而寻找到上述所说的那种“适配”的最佳的微观适配结构层面。
这种分析表明,“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在既有的改革开放的建设与发展成就现状下,继续保持必要的宏观研究方式的同时,卓力探究必然的微观研究方式。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关于“四个自信”这一论题的探讨,需要更为深入的哲学与形而上学理解的奠基。这即是说,在我们“中国”“道—路”的自信问题上,除了内在规定性的“中国”的政治之“道—路”的自信外,还应该让这种与自身理论与制度的自信一道的“道—路”自信链接/连接上更为广博的“文化自信”,从而让“中国道路”获得真切本己的“中国文化”的奠基,并进而形成更为“自强不息”而“厚德载物”的“中国”“道—路”“文化”的生态。这种生态的具体而现实的展开和生长,就是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理—论”。
尽管从“四个自信”的阐述顺序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依次顺序的,然而这却不能机械地来理解,特别在对此进行理论探讨的时候。事实上,从“我们”复杂而漫长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使命事业来看,在“四个自信”中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无不是相互间复杂而漫长地进行着生态互动的。这就是说,这四个方面的时间序列与它们的逻辑序列是不能简单地机械教条地合一的。
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命题,本质上必然要求我们深刻而深入地理解“四个自信”的理论思想,并进一步寻求其相应的哲学概念或者哲学形而上学的奠基,以及进一步追问其相应的终极意蕴奠基,从而为其生态地创造出更加普遍和普及的精神血肉。简言之,“四个自信”的理论思想应该化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社会”的日用而不必然知的精神、意识、心理、信念。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深入揭示并论述“四个自信”理论思想的日用而必然的意蕴。为其在理论必然以及必然理论上通透,“四个自信”的理论思想才能走出狭隘的政治或者政治学视域等,进入日常生活及其世界的生态系统,化为历史而逻辑地实践着的精神生态,而这种精神生态不是别的什么,正是这种历史而逻辑地实践着的精神的伦理,相应着伦理自信在此问题讨论中,笔者已完成一篇正在投稿中的专门论文《伦理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深层本质》,而该论文的基础是笔者的另一篇专门论文《伦理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见李崇富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二、四个“自—信”的深层“道—说”意蕴
“四个自信”理论思想集中突出“自信”。这里的自信不应该是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而更应该是或者必然是在真切纯正的“浩然之气”(孟子)意义上理解的。这意味着,这种自信应该是一种深层形而上学的精神,显明作为“自”的一种精神主体和作为“信”的一种精神“理念”(柏拉图)。仅仅这一个词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就已经显明着浓厚的伦理意蕴,更不说其所“道—说”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了。
应该说,“四个自信”内涵着四个“自—信”,而四个“自—信”“道—说”着“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这四个方面的理念。很显然,如果不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书写这四个方面的理念,那么人们很难感受并理解到这种书写方式的理念所本应该具有并释放出来的巨大而伟大的深层形而上学的精神力量。唯有以概念之锤的方式来敲碎(加连字符)积习为常而往往被人们不知不觉地固化或僵化了的这些词语,才能够以原子裂变的方式激发并释放出相应的精神能量。如果停留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自信”,那么这必将难以避免“四个自信”的这种精神力量的窒息或者弱化,因为这种“信”之所“信”只能够深沉地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觉醒以及相关现实与历史的觉醒,而这只能意味着这种觉醒本质上是一种伦理觉醒,指谓一种伦理自信。
很显然,在上述概念之锤的方式下,所“道—说”的诸理念词语立即深层共鸣着久远的精神历史记忆和印记,让我们能够瞬间共鸣通透相关的丰富意蕴,宛如虫洞或者时光隧道效用。这可以让我们更加历史、逻辑而现实地在以词语表征的方式融合生长并成长出自己的世界。因此,可以这样说:“四个自信”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有其天意所嘱,可称之为我们中华民族现代的天之道;这个“道”,需要显化为适应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不同事物、不同关系、不同层面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路”,以便人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世界能够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走向自己的人生幸福,并进而一起走在共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之“路”;这种“道—路”,需要显明为相应的“理”,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之“理”,并进而通过语言文字而凝聚为相应的“论”,以“方便法门”的方式承载这“道—路”之“理”,通向并宣化于不同人们的心和精神,以便人们能够真切地在各自的层面和方式上感受、理解并适当应用这种“道—路”之“理—论”;在具体的应用中,这种“道—路”及其“理—论”必然以生命生长和成长的生态方式显型为相应的“制”,以便所有人们都能够在具体应用时有统一的依据,由此构成为生态共同体,并以具体差异的方式显型为相应的“度”,以便不同的人们都能够以各自生态共同体的不同方式展开具体应用;这种“道—路”及其“理—论”和“制—度”,在具体显化、显明、显型以及具体应用中,需要进一步升华为具有“化育”(《中庸》)之功与力的能够化民与万物以善生、养生、用生而幸福的相应的“文”,以便超越人们的生命限度而流传不同的生命之“文—化”,在词语的固定和固化之间寻求保持足够的化育空间,让化育之“文”不僵化,而是生态地生长并成长为该生态本身所本性使然的精神,历史、逻辑而现实地实践着的精神。
在对“四个自信”理论思想的这一深层形而上学的解读中,不难发现,其中的所有方面都不是孤立的、割裂的,而是生态地结构的、环节的、层面的。这就是说,这里的所有结构、环节、层面都各自是各自,但是都不是孤立的割裂的,而是相互以生态方式构成为一个具有各自功能作用意义的生态结构、生态环节、生态层面,并且它们合起来共同构成的整体的生态也是一个具有自身功能作用意义的最大的生态整体系统。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此用生态来描述和阐述的对象,并非生态学对象,而是特殊的对象,因为这种对象是具有自身多姿多彩又复杂多变的精神的。
正是在這里,这种本性上有其自身精神的生态整体系统,与黑格尔所阐发的伦理实体,发生了奇妙的真切理论共鸣,因为这种具有精神的生态,毋宁恰恰是在亚里士多德意义的“形式”上,与这种伦理实体是同一的。这就是说,这种有精神的生态是逻辑同构于这种伦理实体的,因此二者的概念逻辑机制与形式是相同的,互相相通的。换言之,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相互诠释而生发出奇妙丰富的真切理论意蕴的。因此,黑格尔的伦理实体是可以被诠释为这种有精神的生态的,只不过在此所不同的是,这种有精神的生态不是什么别的生态,而恰恰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社会”“民族”及其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事业的生态。
因此,不论是这种生态还是黑格尔的伦理实体,其本质的本性的要义都在于其精神,而这也恰恰是“四个自信”的深层形而上学的真切意义所在。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反复突出宣明的“自信”意蕴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自觉而清醒地追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很显然,这种中国方案的具体描述恰恰是“四个自信”理论思想,并且这种方案不是单纯理论的,而是有着底蕴深厚、厚积薄发而情怀天下兆家安定幸福的“中国”“精神”的。这种精神,作为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伦理实体的精神,生态地适应、转变并示范着在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之“路”,或者称之为面向未来命运发展的后古代中国之“路”。换言之,“中国”之伦理实体正在凝聚千古的“自—信”“精—神”之力,重构底蕴深厚而与时俱进地适应转变的“自—信”“精—神”之礼,重构“我们”“中华民族”的后古代中国之伦理实体。这是“中国”“道—路”应该具有的本质内涵,也是“中国”“文—化”应该具有的本质内涵,否则难以避免庸俗化、平庸化的泥淖和陷阱。
因此,恰恰是在这种生态或者伦理实体的意义上,必须以“精—神”之视域来扫描并透彻理解“四个自信”理论思想,而这种视域,更具体地可以称之为伦理自信视域,简称为伦理视域。就此来说,伦理视域这个概念是不应该随便使用的,除非至少论述者自身是必须有那种生态或者伦理实体的“精—神”的。
三、伦理与伦理自信的视域
伦理视域或者伦理自信视域的内涵,可以典型地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获得阐发,并进一步确定地提炼为一种方法论。
根据黑格尔,伦理概念的理解应该区分于道德。从其所阐述的伦理和道德的概念来看,黑格尔是在对立统一的意义上界定和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根据黑格尔,应该认为道德其实是我们人类各自群体的伦理生活的一种造诣,因为他说“个别的意识,既然它直接以实在的伦常亦即民的生活为它的生存,它就是一个具有坚实信心的个别意识”[1]。又说:“一个人做了这样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事,还能就说他是有德的;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时,他才可以说是有德的;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2]黑格尔的这一论述表明,一个民族的伦常生活是该民族的伦理生活,而作为个别的意识的个人,就我们人类各民族自身的生存发展史来看,越是在起源的民族伦理生活阶段,越是与所在的民族伦常生活融为一体,而这正是原始部落时期我们人类各族群的生存生活的经验样态。在这个时候,我们人类在各自的族群中,实际上是没有“个人”和“自我”的,而所应该有的事实上是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族群部落。这个特点,原始地保持为我们人类不同群体的这样一种新生个体的特征,即一般来说,迄今为止,无一例外地可以发现,我们人类的所有不同族群或群体的新生婴幼儿,都有普遍共同的一个特征,即这样的新生婴幼儿是与其赖以生存的母亲或者抚养人融为一体的,直到有一天他/她可以不再因为母亲或者抚养人离开了其视线而哭闹。
在黑格尔看来,这样的群体或族群及其生活正是一个“伦理实体”:(3)“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3]在黑格尔的理论设想中,可以认为,伦理与实体两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或者伦理的实质或内容是以实体的形式或方式而达成的,而实体这一形式或方式表明,伦理的实质或内容即伦理生活不是简单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的行为、活动等的累加,而是这种累加构成为一个作为普遍物的整体即这样整个的个体——这就是黑格尔在例如上述引文(1)中反复强调的个别意识所具有的那种坚实信心之所坚信的。这就是说,黑格尔所说的这种坚实信心,并非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那种含义,而是特指作为个别意识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对其自身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民族伦理生活的坚实信心,亦即一种对自身所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族群、群体、民族、社会、国家之生活所具有的精神上的坚定信念,而这种精神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单纯抽象的精神,而是具有历史而逻辑的现实实践含义的精神,那种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历史而逻辑地能动的精神。显然,这种精神之所系的只能是黑格尔在上述引文(3)意义上的那种作为整个的个体的普遍物。黑格尔把这种普遍物称之为实体,或者伦理实体。
因此,正如黑格尔在上述引文(2)中强调的那样,对这种伦理实体的生活来说,除非我们个人所做的合于伦理的事是出于我们个人自身的秉性,否则的话,那是不能具有道德意义的,因此黑格尔在上述引文(2)中强调“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在此,一种深刻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意蕴共鸣立即发生,因为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存在中才能诞生例如道德等的社会上层建筑,而黑格尔的这一表述所表明的正在于具体的伦理生活(作为社会存在)的造诣或者心得体会等达成为一种德。这种类似的理论阐述,也可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一个人的现实活动怎样,他的品质也就怎样。所以,我们应当重视现实活动的性质,因为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现实活动的性质。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的习惯绝不是小事。正相反,它非常重要,或宁可说,它最重要。”[4]37亚里士多德进而援引柏拉图关于孩子教育的观点论证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起对该快乐的事物的快乐感情和对该痛苦的事物的痛苦感情”[4]39并得出结论:“德性成于活动,要是做得相反,也毁于活动。”[4]41
这就是说,根据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工具,我们应该且必须要说,伦理生活对于我们具体的个人来说具有先验性,即个人只能出生于特定的某个族群、群体、民族、社会、国家的伦理实体中。很显然,这种伦理实体的生活对该个人来说,是作为非具体的整个的个体的普遍物,与该个体相对立。该个体要生存和生活,就历史地必然地要对该伦理实体生活的相关伦常习俗、规章制度等等进行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上的内化,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对该伦理实体的坚定信心,从而与该伦理实体同呼吸、共命运,从而不再把自身作为相对于该伦理实体的异在之物。当该个体能够以自身秉性的方式而自然地信受奉行该伦理实体生活的伦常习俗、规章制度等等的时候,该个体就被称之为是有德的。
正是在上述伦理实体及其坚定信心和造诣的意义上,伦理本身即意味着自信。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把自信从伦理中剥离出去,那么伦理不再成其为伦理,因为这样的伦理不能够承载或提供给相应人们以一种赖以生存和生活所必须的精神普遍物,而人之为人的要害问题之一即是:人不能够没有精神地活着。因此,伦理自信必然是现实、历史而逻辑的。这就是说,伦理之为伦理,必定是历史、逻辑而现实地实践着的,必定是自信着的,这是伦理或者伦理实体的本性使然——伦理或者伦理实体可以被毁灭,但是一种没有自信的伦理或者伦理实体,正如一个没有精神的人,这是不可能的,除非那不是伦理实体,或者那是在乌合之众与一盘散沙的意义上的伦理实体。因此,伦理或者伦理实体,是可以发展为一种方法论的,而这种方法论本身意味着相应事物和问题的内在的伦理自信视域,尽管这难以避免一种泛伦理主义的苛责,然而这种苛责恰恰是狭隘伦理学或者狭隘学科观念下的。此外,相比于这种狭隘之物,更重要的是方法,这不正是现代世界诸领域的研究成果所表明或启示的吗?
显然,伦理自信的概念有不错的双重理论和实践意蕴。从伦理实体来看,我们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伦理实体是根本不同于欧洲或者西方的伦理实体的。这意味着根本不同的伦理实体生活,根本不同的伦常习俗和风俗习惯等。简单说,这意味着根本不同的伦理实体的历史、逻辑而现实地实践的精神的路径。尽管从概念上来说,这都是同一个概念形式的,但是问题关键不在于这种形式,而在于这种形式下的根本不同的内容。换言之,“我们”的伦理实体生活和“他们”的伦理实体生活是根本不同的。这意味着,我们在思考和研究“我们”的建设和发展问题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所说的“我们”与“他们”究竟不同在哪里,又究竟应该如何真正以“我们”的方式来思考、研究和处理“我们”的问题,因为经由近代以来的苦难艰辛曲折的学习和经验教训,“我们”的伦理实体事实上已经不再亦步亦趋地进行思考研究和建设发展了。如果能够普遍达成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在面对着“我们”当下的诸多建设和发展问题时,在面对着诸多来自于“他们”的问题遭遇时,能够真切地从“我们”的伦理实体生活的现实当下的具体问题和事情出发,去思考和研究相关问题。这既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质料的伦理的,也是形式的伦理的,从而构成为一种全方位的伦理视域、伦理实体视域、伦理自信视域。
显然,这一视域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和“我们”更能够自覺地意识到并普遍地理解到“我们”是一个伦理实体,并且我们和这个“我们”本就应该是同一的,而这种“我们”的伦理实体生活必然需要相应的伦理或伦理实体视域、伦理自信视域。这种伦理和伦理自信的方法论的构建,可以让“我们”更加自觉地有意识地以更加恰当的方式来直面“他们”的伦理实体所带给“我们”或加诸“我们”的各种影响,从而让“我们”的伦理实体更加以伦理和伦理自信的方式,更加有效地创造性地直面各种内外问题。
四、伦理自信视域下的“四个自信”
因此,伦理自信不仅表明“我们”是一个有精神的伦理实体,而且表明“我们”必须以伦理的方式来看待和处理相关于这个伦理实体的一切。在此,“我们”必须警惕那种非伦理的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没有或者缺乏精神的,而这种精神是这个伦理实体自身本性的,不是外在强加的。这就是说,在“我们”伦理实体的诸方面问题上,必须坚持、强调和突出这一伦理实体的自觉精神的“我们”之主体,即是说必须自觉而清醒地为了“我们”伦理实体而反思和实践。伦理自信意味着“我们”伦理实体的自觉,伦理地自觉,以这种伦理凝练的自信精神来建设和发展“我们”伦理实体,来面对可能的诸问题和困难。这恰恰是“我们”伦理实体的觉醒,或者“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觉醒。简单地说,这种伦理觉醒意味着,“我们”伦理实体有了自身本质本性上的精神、文化、信仰和守护,并进一步发展丰富。
这意味着,伦理自信的概念可以常识性地作为我们的方法论,来透入对“四个自信”理论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启示和激发其中所蕴涵着的巨大的理论与实践力量。综观“四个自信”理论思想,应该认为,道路自信在其中发挥着根基作用。应该这样伦理地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达成为相应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我们”伦理实体的轨道,而这一伦理实体轨道具体实现为相应于该伦理实体的理论、制度和文化。此外,文化还有另外一种囊括一切方面的含义,让我们的中国道路及其理论和制度涵化于自身,以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含摄力量的形而上学精神,而这必然普遍含摄着可资化育之用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具体文化,例如我们古代的诸文化。这本性上就要求“我们”从质料和形式的双重方面来伦理自信地观察、思考和研究。
此外,伦理自信地理解“四个自信”,必然本性地要求“自—信”的“我们”之历史的视野,因为伦理实体必然是有其自身的历史过程的,宛如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过程。这显然是一种伦理的历史视野,或者伦理自信的历史视野,因为伦理实体具有自身的生命,必然要求其自身作为其自身的生命历程和精神。
从“我们”新中国的发展史来看,应该说,相应的初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由此“我们”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也就应该进入向更加完善而精致的发展方向前进的阶段,而与此相应的宏观研究方式也就必然应该在保持必要的宏观研究的同时,突出微观研究方式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因为在这个历史使命阶段,在必要的国家宏观调控保持结构性和导向性的稳定前提下,关于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问题已经必然地转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和地方、不同群体等等,以至于必然转向不同个人的微观事务、行为、活动。如果宏观研究旨在这种建设与发展的骨架、筋脉和血肉,那么微观研究则旨在这种建设与发展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这里问题的要义在于,如果问题停留于宏观领域,那么相应的建设与发展则缺乏微循环生态,而这却是有深远的负面影响而足以致命的。这一方法论视域本身已经意味着应该且必须伦理而“自—信”地来看待“我们”新中国的发展,即这种发展宛如一个人的生长和成长过程那样,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但是所有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又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形成为一个伦理实体的问题域。这表明,不同时期的不同对象的不同任务或问题不能割裂地孤立地来理解,而必须放在对这同一个伦理实体来看的发展整体的过程中,伦理实体地来理解。
正是在这一情形下,我们党适时地指出了“四个自信”的理论思想,开启了由以往的学习借鉴向深入学习而自主创造转变的治国理政方式的大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表明,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伦理自信的觉醒状态,一改以往的不自觉地伦理不自信的状况。这意味着,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完成了吸收借鉴各民族文明优秀成果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步阶段,开始进入自觉而觉醒地吸收借鉴而创造地“摸着石头过河”的后续高级阶段。我们三十年来的艰辛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转变觉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坚定、坚实而保持伦理自信的国家肌体,尽管不乏肌体的营养不良或者营养不均衡等诸多问题,然而我们终究在复杂的困难中走到了现在。因此,这种适时的转变正表明,在我们党的创造性领导下,我们的国家肌体开始进入全面茁壮成长的新时期,进一步坚定、坚实肌体的同时,更加丰满肌体的血肉和神容。这一状况恰恰表明,我们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已经伦理实体地普遍地成为一种值得人们坚信的普遍物。换言之,“我们”已经由以前的自在的伦理实体阶段进入了现在以至于必定将来的自为的伦理实体阶段。这种伦理实体的普遍意识的觉醒,不论是作为内容来说,还是作为方法视域来说,都内在地要求并意味着相应的“自信”,而其历史、现实而终极的指向必定是伦理之自信。
在这种问题域背景下,“四个自信”中的道路自信本质上必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道”的“中国”“路径”,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应用所本然旨趣的。从国家哲学来看,以“认同感”为核心旨趣的意识形态,必然是贯穿于国家生活的诸领域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等。对于同时面对着既有的本己历史文化和碰撞中的西方它者历史文化的“中国”来说,如何让其“认同感”生态地扎根于这两种维度的历史文化,从而形成“中国”自身切己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国家”“认同感”,这是当下这种历史使命的紧迫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伦理地来看,这种认同本性上必然是伦理认同,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伦理实体下的诸伦理个体对所赖以生存和生活的该伦理实体发生相应的认同。因此,这种认同必然是直面这种伦理实体本身以及所处于的古今中外的双重伦理实体的环境,进而寻求这种认同所系的伦理实体的创造性的建设与发展。
这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历史步伐和发展现状已经表明,“我们”是不可能朔历史而上地回到传统的社会及其文化的,也不可能跳跃历史而出地投入到现代的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我们”唯一切己的选择只能够是在既有的古代的和现代的西方社会历史文化与同样既有的古代的和现代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双重生态下,生长凝练旨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的文化认同以及意识形态认同。就此来说,这种道路以及文化已经不是普通的观念问题,而是深刻、幽深的“精神”问题,即“中国”的“国家”“精神”问题。这种问题不可能是抽象的,因为“精神”在本性上必然是伦理的,因为至少从如前所引述(1)(2)(3)来看,黑格尔所论证的伦理实体的概念工具表明,相对于个人而言的民族生活必定是历史、现实而逻辑地有精神的,这达成为相应的伦常与道德,并且反过来说,抽离于这种精神的民族生活是不可能的,即作为整个的个体的普遍物的,除了精神,别无所是。这就是说,如果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不能普遍地成为我们党、国家和中华民族的伦理实体的历史而逻辑地实践着的精神之普遍物,那么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就难以避免流于和限于狭隘的政治理论的命运,从而成为一种单纯的灰色理论,但是问题在于这不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四个自信”理论思想的真切之意义。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这必然意味着其中的伦理自信,即旨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伦理实体生活的茁壮发展。
五、余 论
既然“我們”不可能回到我们曾经的历史中,也不可能跳跃出其外,那么“我们”唯有“自—信”而“仁勇”地守护着“我们”伦理实体的成长,让其成长在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外在难题及其文化环境时,伦理地或者伦理自信地适时地接通“我们”伦理实体的文化生命历程,以为其进一步成长筑基,筑就那伦理的精神之基,关照“我们”的伦理现实和伦理未来,生发其成长的理论和制度,因此“四个自信”理论思想最后以文化自信收束。
这意味着,在“我们”的伦理自信视域中,必然有古今中外的四重文化对象。同样地,这四重文化对象也必然应该以伦理自信视域来关照,其中我们的古代文化对象尤其是如此的,因为那是“我们”伦理实体的曾经的伦理自信视域。这种伦理自信视域在迄今仍然在流传不息的《礼记》等古典文本中,有着确凿而比较系统的记载和阐述。如果这种伦理视域曾经绵延不绝地成功实践了至少两千多年,而至今仍然在跳动着脉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深层而富有建设性地接通这个视域,以为重聚“我们”伦理实体自身的“文—化”生命母体,从而同样深层并富有建设性地重构“我们”伦理实体的当下现状,以更加深层地适应“我们”伦理实体被动而主动地进入的这个现代世界,并且更加富有深层建设性地面向“我们”伦理实体的未来。
然而,出于“我们”伦理实体自身考虑,上述“文—化”生命母体的的寻获,不可能寄希望以对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式的传统上的学术和学问的回归,例如对“儒学”“经学”等的回归,而必然本性上要求把包含这些学术和学问在内的一切传统上的文化视为面向“我们”伦理实体的并非“我们”伦理实体必须面向的“文—化”素材,进行重构和激活。换言之,这种“文—化”素材至少是曾经连续两千多年成功的深层相关于“我们”的古代的伦理实体的遗产,而“我们”伦理实体正是孕育并生长于该遗产中,既然“我们”伦理实体不可能摆脱掉这种遗产的深层“文—化”影响,那么就必须对这种“文—化”进行面向并适应“我们”伦理实体的再“文—化”。这是伦理自信及其关照下的“四个自信”本应该有的深层内涵意蕴。
因此,伦理自信不论是在质料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表明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精神的伦理实体,并且这一伦理实体以我们党为其自身精神的引聚生发源,同时在我们党的引聚生发领导下,这一伦理实体内部诸结构和层面又各有其自身精神的引聚生发源,由此而构筑一个广阔的可供人们自由而有序地施展其才华的伦理实体平台和框架,从而为这一伦理实体创生源远流长的各种“自—信”的精神动能。这种引聚生发源的本质使命正是内引外联地“文”而“化”之地透析各种“文—化”素材,以便在自身“文—化”生命母体基础上,实现千古以来的“文—化”生命的再次复兴和辉煌。
因此,“中国”“道—路”的国家哲学必然只能是“我们”“中国”的国家哲学,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国家哲学。然而,不幸的是,在类似问题上的深重问题在于,“我们”总是不知道或者忘记,所谓的国家哲学本性上就不可能是一般的抽象的。黑格尔的伦理实体的概念工具表明,国家本性上就必然是一个伦理实体,而且是最大的伦理实体。当我们把国家理解为一个共同体的时候,那恰恰是在这种本性上的伦理实体意义上来说的。因而,对国家来说,根本上重要的,只能是其作为一个自身本性上的伦理实体所必然要求的伦理文化,或者伦理实体文化。
因此,“四个自信”的、特别是其中的道路自信的时代深层难题实际上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确切地说,不是一般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深层的“我们”伦理实体的“文—化”问题。在此需要同时说明的是,必须警惕在这种问题上的泛化抽象的理解和处理方法,这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所在。“道—路”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的深层表征。这个系统乃是一个作为共同体的国家的诸领域结构的生态伦理实体系统。然而,真切地能够保证该系统之为该系统的深层生态所在,正是该系统的切己的文化,而不是表层现象的外来的西方文化或者文物般的自身历史上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西方文化以及我们自身历史上的文化,都是凝炼形成我们“中国”“现代”“文—化”的素材和土壤。因此,照搬西方的文化,正如照搬我们自身历史上的文化,都是行不通的,“生搬硬造”。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36.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70.
[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9.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杨军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