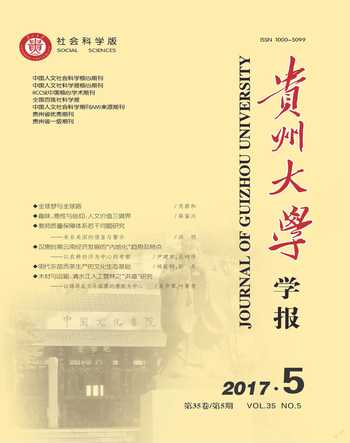矿业与边疆治理:清朝对云贵地区矿业衰落的调控
2017-05-30杨亚东
杨亚东
摘 要:清代云南和贵州分别为全国铜矿和铅矿的重要产区,清代中后期,滇铜和黔铅由盛转衰,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有成本增加,官价过低;燃料短缺,运输困难;私采泛滥,课税沉重等。为挽救滇铜黔铅生产日益下滑的颓势,清廷采取了控制成本、改善运输;提高官价、补助资金;蠲免厂欠、降低课税等措施。这些调控手段短期内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终无法遏制云贵矿业衰落的势头。清廷运用多种经济和政治手段对滇铜黔铅衰落问题进行的调控,反映了王朝国家对边疆地区经济和社会问题治理的思路与对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政府对经济和产业调控的理念、思路。
关键词:
清朝;边疆;矿业;衰落;调控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5-0103-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5.17
云贵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清代云南和贵州分别为全国铜矿和铅矿的主要产区,其后,出现了由盛转衰的趋势,清廷
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手段,但最终无法挽回颓势。学界对清代云贵地区矿业衰落原因的探讨,由于史料缺乏,未形成定论。徐斌认为,云南铜业的衰落与封建政府矿业政策的桎梏及其自然条件限制有密切关联,能源紧缺与交通运输困难是造成云南铜业衰落的重要原因。[1]文思启认为云南社会生产力落后与矿冶业发展不相适應的矛盾是造成铜业衰落的重要原因。[2]刘朝辉认为在自然原因背后,官发铜本与产铜成本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以及铜政弊端是导致云南铜业衰落的重要原因。[3]李中清认为面对产铜成本的飙升,政府补助金的减少是造成云南铜矿业衰落的致命原因。[4]287-295肖本俊认为,清乾嘉时期的“山荒”及随之而来的“薪柴价高”“炭路日远”等问题是造成滇铜业衰落的重要原因。[5]罗时法认为,沉重的课税是造成贵州矿业凋敝的主要原因。[6]袁轶峰认为清代贵州大定府铅铜业由盛转衰的原因主要是流民问题、粮价问题、私采滥采、贪污等。[7]学术界针对清廷应对和调控云贵地区矿业衰落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李中清对清代云南地方政府为遏制滇铜生产衰退所做的努力进行了阐述。[4]282-286刘朝辉就清廷面对滇铜供应不足、成色低潮等问题采取的调剂措施进行了论述。[3]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滇铜黔铅衰落的原因进行再认识,同时分析阐释清廷应对矿业衰落的调控措施,从而管窥王朝统治者在治理边疆过程中对矿业衰落等经济和社会问题治理的思路及对策。
一、
盛极而衰:清代中后期滇铜黔铅的衰落
清代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以铜、铅开发为代表的矿业取得了较大成就,无论从矿业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之前任何时期,“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二千年”[8]。清代中期以前,云南的铜矿业和贵州的铅矿业开发取得重要进展,对国家的货币铸造、枪械弹药生产、生活器皿制造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中后期,滇铜和黔铅由盛转衰,留下了中国矿业发展史和西南边疆开发史上浓重的一笔。
(一)滇铜由极盛到衰落
铜是清代铸币所需的重要原料之一。云南铜矿资源丰富,史料记载:“盖鼓铸铅铜并重,而铜尤重。秦、鄂、蜀、桂、黔、赣皆产铜,而滇最饶。”[9]980云南铜矿开采历史悠久,“产铜矿区,元时为大理、澂江,……明、清两代发现矿苗者八十三属,开办者三百余厂,岁供京、滇铸钱及八路采办之需。当乾隆三十八、九两年,每岁产铜约一千二百数十万斤,额课九百余万,而商贩不与焉,可谓空前之极盛时代矣”。[10]129
研究清代前期云南矿业开发的政策,不得不提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在《筹滇十疏》中建议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励和税收优惠措施,招揽“本地殷实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投资开发云南矿业,同时对招商开矿成效显著的官员给予优先提拔,甚至“酌量给与顶带”,
参见《云南通志》第29卷《艺文三·筹滇十疏》。
清廷采纳了蔡毓荣的建议。但由于铜业开发前期资金投入比较大,且开发过程中存在较大风险和不可控因素,加之云南地僻民穷,如蔡毓荣所期待的“殷实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凤毛麟角。面对云南铜矿开发中的资金问题,康熙四十四年(1705),云贵总督贝和诺上奏对云南铜业实行“放本收铜”,即“于额例抽纳外,预发工本,收买余铜”[11]4977。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使官府实现了对货币铸造的主要原料——铜的生产垄断,有效保障了国家货币的稳定,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刺激了云南铜业的发展。
随着“放本收铜” 政策的实施,云南铜矿开发的规模不断扩大,产量迅速增加。“康熙四十九年(1710)云南产铜不到50万斤。到雍正三年(1725),铜的年产量达到100万斤。乾隆二年(1737),又上升到1 000万斤。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云南的铜产量增长了20倍。其后,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云南平均每年的铜产量都保持在近1 000万斤的水平上。直到19世纪中期,铜产量仍未明显衰减。那时,云南铜矿已经生产了超过50万吨的铜,相当于同期世界铜产量的五分之一,中国铜产量的一半。”[4]269可以说,“滇省铜政,累叶程功,非他项矿产可比。”[9]980
然而,云南的铜产量并未一直保持上升势头,甚至年产一千万斤左右的水平也未能长期维持。嘉庆九年(1804)七月,云南巡抚永保在奏书中感叹:“每见各厂月报,办铜多不足额,办理时形掣肘。虽京运勉强不致有误,而各省采买,即间有不能随到随拨者,迥非二十年前之情形可比。”参见《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云南巡抚永保奏折(嘉庆九年七月二十日)。虽然经过多方调剂,勉强办足京运所需铜斤,但却无法保证采买滇铜的其他各省的供给,以致“各省委员到滇,均不免稍为守候”。[8]178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三年(1823),广东、湖北、浙江、贵州、湖南、福建等六省的八运委员因云南无铜供应,在滇连年滞留守候,无铜济铸的各省不得不采取停炉减卯、采买商铜接济等措施来临时应对。
刘朝晖认为:“相对于滇铜供应数量的问题,其成色问题更为严重”,及至嘉庆、道光年间,陈滇铜成色不足的问题已非常严重,“京局不得不设炉改煎,所需火工银两由各厂店员及运员赔补。”[3]从办铜数量的持续下滑和滇铜成色不足等问题来看,嘉道年间开始,云南铜矿衰落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尽管部分年份余铜出现一些波动,但下滑趋势已不可逆转。
(二)黔铅由兴盛到凋敝
铅是清代铸币的重要原料之一,也有部分用于制作火器的弹丸。贵州铅矿储量丰富,清代时是全国重要的铅锌矿的产区,雍正、乾隆年间,随着矿禁的开放,贵州铅矿开采取得了较大发展,黔铅生产运销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
康熙五十七年(1718),贵州威宁府猴子银铅厂、五十九年(1720)威宁府观音山银铅厂相继获准设厂开采,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乾隆朝·卷49)《户部·杂赋上》。短短几年,贵州铅厂就有了较快发展,雍正、乾隆年间,黔铅产量有了较大提高。“威宁州的朱砂厂,雍正时期年产铅 20—30万斤,乾隆时达100万斤以上。绥阳月亮岩厂也由30余万斤到 100 余万斤。年产铅100万斤的有丁头山、达磨山、榨子厂、大鸡、小洪关等地的厂矿。各铅厂产量最高的是莲花厂,年产量达 500—600 万斤之多。全省各府厅州县产铅量最大的是威宁州,年产为 1 000 万斤以上。乾隆年间贵州全省年产铅在1 400 万斤左右。至道光时产量大减,仅及乾隆时的1/3。[12]170
嘉庆以后,贵州许多铅厂纷纷封闭,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贵州铅厂仅有福集、莲花塘、济川、天星扒泥洞、永兴寨、水洞帕等处,
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194)《户部·杂赋》。
与乾隆年间兴盛时已无法比拟。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贵州巡抚李庆棻奏报:“黔省福集、莲花二厂,岁供京、楚两运白铅六百余万斤,每年所产有一百余万斤缺额,自乾隆四十五年始,俱以旧存余铅凑拨,日形支绌。”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11),乾陵五十三年八月戊午。
道光八年(1829)十二月,道光帝谕内阁:“黔省妈姑、福集等铅厂因开采年久,峒老山空,砂丁采取匪易。新发白岩子厂夏间雨水过多,漕峒被淹,招丁车水,需费不少,炉户倍形疲乏。” 参见《清宣宗实录》(卷148),道光八年十二月戊子。由此可见,嘉道年间开始黔铅开发以无法阻挡之势步入衰落期。
二、
本非一端:滇铜黔铅衰落的原因分析
(一)滇铜衰落的原因分析
《新纂云南通志》对滇铜衰落的原因有如下分析:“滇铜几遍全国,后厂情盛极而衰,原因本非一端,然最大困难其故有五,属于采办方面者:(一)官给铜价,难再议加。(二)各路取给,数难议减。(三)大厂逋累,积重莫苏。(四)小厂收买,涣散莫纪。”[10]133归结起来,导致清代云南铜业极盛而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成本骤升、采炼艰难
铜矿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生产成本非常惊人,清代云南铜矿开采随着开采规模的日益壮大,矿区聚集了大量的矿业人口。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奏称:“现在滇省银、铜各厂,聚集攻采者通计何止数十万人” 参见《张允随奏稿》(卷7)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奏报遵奉查奏云南永顺东南徼外卡瓦输诚纳贡情形,并备陈亿万厂民生计折(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马琦根据滇铜产量及人年均产铜量推算出“清代滇铜矿业人口平均约7.6万人左右,乾隆朝年均为9.3万人,最高时达14.2万人。”[13]131尽管清代云南铜业的从业人口准确數量无从查考,但无疑是非常庞大的。如此众多的人口,需要消耗的生活物资非常巨大,仅以粮食一项,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此问题,早在雍正五年(1727),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奏疏中就有如下分析:“开采矿厂,动聚万人,油米等项,少不接济,则商无多息,民累贵食。”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52),雍正五年正月壬子。
乾隆十三年(1748),针对日益上涨的米价,张允随认为:“米贵之由,一在生齿日繁,一在积贮失剂,而偏灾商贩囤积诸弊不与焉。……乃近年米价亦视前稍增者,特以生聚滋多,厂民云集之故。”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
是年六月,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在奏折中亦认为:“米价之贵,总由于生齿日繁,岁岁采买。……(云南)粮价亦不甚贱者,由于出产五金,外省人民走厂开采,几半土著;且本省生齿亦繁故也。”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六月壬午。由此可见,由于大量的矿业人员聚集,导致米价的不断上涨,而米价的上涨,又进一步增加了铜矿开发的成本。
除此之外,清代云南铜矿采绝大部分依靠薪炭焚烧加热,烧煤加热的矿厂很少,这样一来,矿厂周围的树木大量被砍伐。在刚开始生产时,炭薪还可以就近砍伐林木取得,“初辟之矿,入必不深,而工不必费。” 参见《滇南矿厂图略》(卷2),王太岳《论铜政利病状》。
随着铜矿生产规模的日益壮大,矿厂周围的树木被砍伐殆尽,势必向更远的地区砍伐林木,于是,薪炭产地范围不断向外扩展,与矿厂的距离不断增加。史料记载:“凡厂槽多日久,遂至附近山木尽伐,而炭路日远,煎铜所需炭重十数倍于铜,成铜之后再需煎掲,运铜之费必省于运炭。” 参见《滇南矿厂图略》(卷1附),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
获取薪炭日益艰难,势必导致薪炭价格上涨,进而增加生产成本。到了乾嘉时期,为了满足云南铜矿生产的薪炭需求,大量森林被砍伐,普遍出现了“炭价日贵”“柴薪路远”等问题,这不仅给当地生态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而且大幅度增加了铜矿采冶的成本。
2.运输困难、工本不敷
云南属于多山地区,自古交通条件恶劣,几千年来物资运送均靠人背马驼,尤其是铜矿多位于深山老林中,运输极为困难。到了嘉道年间,“开采既久,窝路远而且深,厂丁背运矿砂,往返不能迅速,是以数日所得,尚不及从前一日之获”。
参见《道光朝军机处录附奏折》,云南巡抚陆建瀛奏折(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窝路”指的是通往矿山山腹的狭窄的通道,厂丁在里面只能匍匐爬行,经过长年开采,各矿山的“窝路”越来越远,以至于运输矿砂异常艰辛,另外,从成品铜的运输过程来看,云南铜业运输也极其困难。由于运输路途遥远,运输周期长,严中平先生感叹:“我们估计大部分京铜,从产地到京师,非经两年的搬运不能到达。若以路程最远的回龙厂而论,三年怕还不够云南铜产区域,全在深山峡谷之中,在云南境内,铜产几乎连一尺的水道都无从利用,每年那一千二百万斤的铜料,主要靠人的肩头,马的脊背和和最简陋的牛车来输送”。[14]34严先生提到的水运“时时有沉没之虞”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七月,“云南委员黄澍领运京铜九十四万一千九百余斤,行至四川大湖滩、大黑石滩暨湖北江陵县马家赛地方,三次遭风沉溺,除捞获外,共计未获铜二十万余斤。”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34),乾隆五十四年七月戊子。
同月,“云南委员漆炳文领运五十三年三运一起京铜七十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三斤,在湖北归州沉溺铜七万斤……”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辛亥。
一月之内就有两起沉船,可见事故之频繁,由此也不难看出,清代滇铜运输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官府提供的“工本”已无法支撑厂民包括运输等在内的各种开销,这从“厂欠”的大量出现可窥见一斑。所谓厂欠,高其倬在奏折中是这样解释的,铜厂“各种杂用,亦系价外开销”“更有将打出之铜偷卖花销、悬项无交者,虽现在而赤贫,或逃亡而无着,悬项累累,名曰‘厂欠,此系铜价外亏折之项。”
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辑)》,云贵总督高其倬、云南巡抚杨名时,查奏铜斤利弊情形折(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尽管造成“厂欠”的原因很多,但“厂欠”既然为“铜价外亏折之项”,但大量“厂欠”的出现,表明“不敷成本,则炉户等不特无利之图,而先领之工本,不能缴还”,
参见《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云南巡抚永保奏折(嘉庆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这亦反应了铜厂的衰落。
3.盗卖私铜、追欠遗症
清朝规定,矿民“不论领与不领工本,产铜一概不许私自出卖,私卖的叫做‘私铜,查获了,其铜没官,其人罚役。”[14]7嘉道年间,云南私铜现象较为严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矿政的实施,是滇铜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道光三年(1823),御史龚绶奏请“查禁私铜以裕鼓铸”,道光帝谕旨:“滇省奸商盘踞各厂,铸铜为锣锅,转发各处行销……。各衙门胥役多与勾通。地方官欲查拿私钱,铺户徒受其累,而奸宄之徒,从无一人获案。” 参见《清宣宗实录》(卷52),道光三年五月己巳朔。
以上足见私铜泛滥,影响官铜生产和解运,清廷要求严行查禁,于各省采办可期无误。
另外,追缴厂欠亦是造成滇铜衰落的重要原因。李中清统计了云南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嘉庆十九年(1814)近一百年间部分年份铜矿厂欠损失情况,厂欠累计最高值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527000两白银,是年蠲免厂欠398000两白银,年平均损失白银79000两。到了嘉庆十九年(1814),蠲免厂欠9665两白银,年平均损失白银9665两。[4]285可见,嘉庆年间云南铜矿厂欠较乾隆年间有较大下降,嘉道两朝厂欠数额也呈逐年减少的态势,这一变化源于嘉道时期对厂欠的大力整顿和追缴,嘉道年间,针对乾隆后期厂欠数额逐年递增的状况,清廷制定了追缴厂欠的严格规定,将厂欠追缴与经放厂员个人利益直接挂钩,督促经放厂员全力追缴厂欠,据史料记载,规定甚至严格到“再有着厂欠,旧例如炉户故绝、停歇,无可着追,即于经放之员名下追赔。如经放之员家产尽绝,无力完缴,照例取具历过任所并无隐寄财产印结,由司加具总结,详咨原籍,提请豁免。”[15]824也就是说,经放厂员承担厂欠的无限责任,就算铜厂“故绝、停歇”,也要经放厂员以个人资产赔付厂欠。除非经放厂员“家产尽绝,无力完缴”,才能办理相关手续,“提请豁免”厂欠。在这样严格的规定之下,厂员惧怕赔累,要等见铜后才愿意发放工本。
厂员既然已不敢预发工本了,“放本收铜”政策刺激开矿的效用也就无法发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炉户缺少资金开采铜矿,清代云南“厂衰”问题只能是越来越严重了。
(二)黔铅衰落的原因分析
清代贵州铅矿开发从康熙末年至乾隆中期一路增长,成为全国重要的铅矿产地。到了嘉道年间,黔铅生产和运销成急剧下滑之势,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1.生产成本增加、官定价格过低
与滇铜衰落的原因相似,不断增加的生产成本以及官府定价过低成为黔铅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其中粮食价格始终是影响矿厂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矿产开发,需要聚集数量庞大的从业人员,进而出现粮食供不应求,结果必然导致粮价上涨,粮价上涨又反过来增加矿厂生产成本,这是市场规律所决定的。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贵州按察使介锡周奏报:“米贵之由……加以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场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游民日聚。”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以粮食价格为代表的诸多生产、生活资料上涨,必然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而反观官定铅铜价格则增长缓慢,雍正八年(1730),贵州巡抚张广泗奏称:“(贵州)各厂所费工本多寡不一,其收买价值议定每百斤一两四五钱不等,另加驮脚盘费,运往永宁、汉口等处销售,现在时价三两七八钱及四五两不等,除归还买本脚价,每百斤可获息银一两四五钱不等”, 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贵州巡抚张广泗,奏为奏明事(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應该说雍正年间官定价格已经很低了,但勉强能够维持生产。到了乾隆年间随着各项生产成本增加,低廉的价格导致铅厂获利甚少,铅厂自然也就缺乏生产动力了。
2.官员腐败冲击、私采偷卖泛滥
官员腐败亏空是造成黔铅衰落的另一条重要原因。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威宁州知州刘标亏空大案被查处,乾隆皇帝痛心疾首地说到:“贵州刘标亏空铜、铅价本至二十余万之多,自来侵亏帑项犯案,从未有若此之甚者。……黔省吏治狼藉至此,实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将伊等严加治罪,以示创惩”。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852),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庚申。
另外,官府不如期向铅厂发给工本,对矿厂正常生产也是极大的打击。如“威宁州知州高玮管理铅厂,支放厂员工本并不如期给发,以致厂员张祥发所办新旧白铅俱有亏短……”。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874),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庚辰。
私采偷卖行为是矿业开发中的“痼疾”,很难根除,这也是造成矿厂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代贵州铅矿开发中的私采偷卖现象也非常严重,咸丰五年(1855),清帝谕旨:“四川、云南、贵州各省多有产铅之区,所采铅斤,半归官卖,半归商销,向无例禁之文。惟黑铅有关军火,若任令行店市商照常贩运,辗转销售,莫究归宿,流弊滋多,必当严行禁止” 。
参见《清文宗实录》(卷172),咸丰五年七月壬申。
以上史料足见清代贩卖黑铅现象日益严重,必将进一步加速黔铅衰落的步伐。
3.自然灾害破坏、硐老山空封闭
自然灾害往往导致矿厂遭受重大损失,比如在生产过程中漕硐被淹和运输途中运船沉溺。前者如道光四年(1824年),云贵总督明山奏报:“黔省威厂额办铅斤,因近年产矿不旺,炉户缴铅濡滞,又值上年夏间大雨,漕硐被淹,不能烧办,递相积压,共有炉欠铅一百八十九万九千五百一十斤,核计银三万三千六百七十六两零。”
参见《清宣宗实录》(卷74),道光四年十月丁丑。
运输途中沉船事故多有发生,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贵州委员朱毓炯、薛清范领运京铅,遇风沉溺,俱经陆续捞获五万三千余斤。”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426),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己巳。
硐老山空是矿厂生产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很多矿场不得不因此封闭,大量矿厂封闭势必影响矿业发展。乾隆五十三年(1788),贵州巡抚李庆棻奏报:“黔省福集、莲花二厂,岁供京楚两运白铅六百余万斤,每年所产有一百余万斤缺额,自乾隆四十五年始,俱以旧存余铅凑拨,日形支绌。查厂产不旺之故,实缘开采已久,漕峒日深,且挖取时遇山泉,常需雇工淘水,工费更增……。”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戊午。
三、
杯水车薪:清廷对滇铜黔铅衰落的挽救与调控
(一)对滇铜衰落的挽救与调控措施
针对清代中后期云南铜厂日益衰落的严峻形势,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控制成本、广觅子厂;提高铜价、补助资金;改善运输、蠲免厂欠等手段进行应对和调控。
1.控制成本,广觅子厂
铜厂采炼成本不断增加,是造成滇铜衰落的重要原因。其中,米价上涨是导致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清代云南督抚采取各种措施平抑矿区米价:一是采取积极措施扩大矿区耕地面积、新修水利设施,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云南总督爱必达奏请:“云南东川府蔓海开河招垦,建坝蓄泄,……拟开渠引注蔓海,可溉熟田,荒芜亦资垦辟。边徼民夷无力,借帑兴工,来秋征还。”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07),乾隆二十一年二月戊辰。
二是调运其他地区的粮食缓解矿区粮食紧张形势,进而平抑米价。乾隆九年(1744)三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臣张允随就昭通、东川两府平粜之事上奏乾隆帝:“因上年昭通、东川两府秋成歉薄,恐春夏之交民食不无掊据,奏明动发铜息银二万两,令驻扎永宁转运京铜之同知谷确,于东川一带购买川米,以供青黄不接时平粜之用。”三是规范粮食交易,提倡公平售卖。张允随提出:“地方官劝谕有米之家运米如市,公平售卖,仍动常平仓谷出粜,以平市价,并通查各属,如有米价昂贵、民食不敷之处,令地方官加意体察,借给籽种,以助春耕;应行平粜者,即详请平粜,总期有济民食,毋拘成例;其余蒸熬糜谷等弊,亦严加査禁。” 参见《张允随奏稿》(卷6),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奏报筹买川米于昭通、东川两府平粜折(乾隆九年三月初五日)。
为弥补大矿课额之不足,清廷还实行“广觅子厂”的措施。所谓“广觅子厂”也就是在大矿周围找寻开采小矿,这些小矿不另纳课,其出产用于弥补大矿课额之不足,这一措施也对缓解滇铜衰落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据史料来看,乾隆年间开辟的子厂数量最多。如东川汤丹铜厂就有多个子厂,“九龙箐子厂,在汤丹厂西南一百里,乾隆十六年开采,年获铜三四十万斤。聚宝山子厂,在汤丹厂西七十里,乾隆十八年开采,年获铜五六十万斤。”[15]638
2.提高铜价,补助资金
提高铜价对刺激铜厂生产具有重要作用,清代铜价由国家定价。“中央政府制定铜价主要根据矿石的品质和开矿的难度。各矿的产铜额根据矿床的大小规模而变化。尽管有一系列的变化因素,每个矿普遍的趋势还是非常清楚的:在年产铜额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铜本数额越大,价格必然逐渐上升。”[4]281清代曾多次提高云南铜价以帮助铜厂渡过生产困难,同时也刺激铜厂的生产。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五月,乾隆帝谕旨:“滇省各铜厂前因马骡短少,柴米价昂,每铜百斤,准其暂加价银六钱,俟军务竣后停止,嗣后加恩展限一、二年。今念该省频岁虽获有秋,而米粮、柴炭等价值,仍未即能平减,着再加恩展限二年,俾各资本宽余,踊跃开采,庶于铜务有裨,而厂民亦得资充裕。该抚仍留心体察,俟厂地物价一平,即行奏明停止。” 參见《清高宗实录》(卷908),乾隆三十七年五月甲辰。
以上史料说明,清廷此次提高铜价是为了暂时帮助云南铜厂渡过难关,待“物价一平,即行奏明停止”。
除了提高铜价之外,清朝统治者还通过发放补助金的形式帮助铜厂渡过困难,发展生产。乾隆三十六年(1771),云南地方官府要求各个铜厂在每个矿的附近储备半年的谷物、一年的油料和煤,以备不时只需,铜厂无法负担储备这些粮油所需的数额巨大的费用,云南地方财政给予了补助。这一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东川矿区稻米价格立即降了下来。[4]284另外,云南地方政府还通过向铜厂发放“水泄工费”补助金,以弥补洪水浸淹对铜矿生产造成的损失,降低铜厂生产成本,刺激生产。对于“水泄工费”,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各厂采办铜斤,并未酌给水泄银两。嗣因开采年久,漕硐深远。产硔之区,一至夏秋之际,即被水浸淹。厂民无力提拉宣泄,采取维艰。所有义都厂水泄,经总督杨、巡抚汤奏准,于顺宁局铸息银内,自(乾隆)三十一年起,每年酌给银三千两。……三十七年,巡抚李条奏,水泄银两,应按照实获铜数酌给,以免糜费。义都厂,每办铜一万斤,给予水泄银六十五两二钱一分七厘四毫。奉部复准,于省局铸息银内动支。”[15]820补助金的发放,对刺激铜矿生产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补助金制度),云南省级地方政府又把铜产量推回到1 000万斤以上,1767年铜产量攀升到700万斤,1780年又上升到1 100万斤。就我们所知,从1765到1805,平均每年的铜产量至少和以前时期持平”。[4]286
3.改善运输,蠲免厂欠
铜斤运输上的极大困难是造成滇铜衰落的重要原因。清朝中期,统治者先后疏浚、修凿多条通往省外的水陆通道,为改善云南铜斤外运条件提供了支撑,如开通金沙江、盐井渡、罗星渡三处通川河道,就为节省运通费用产生了积极作用。乾隆五年(1740),云南总督庆复、云南巡抚张允随奏请开凿通川河道,七月底经军机大臣鄂尔泰等议准,动帑兴工金沙江。云南督抚制定分段次第施工、委员专管、宽筹工价、安设草房站船运储物资、采办川米川盐、请领工本等多项措施,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16]47-49历时六年半,金沙江工程完工,该工程为缓解滇铜京运威宁道的运输压力,降低运输成本起到了积极作用。史载:“开金沙江,将滇省铜斤改由水运,每年可省陆运之半,则威宁及昭通两路余出马匹,办运自见敷裕”。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221),乾隆九年七月戊戌。
乾隆十一年(1746),张允随奏报:“查三处河道(金沙江、盐井渡、罗星渡),……自完工以来,运发京铜,就现在办理,较从前陆运,每年实可节省银一万五千五百余两。”
参见《张允随奏稿》卷7,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遵旨奏覆通川河道较先前陆运节省银两数折(乾隆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为挽救日益衰落的云南铜业,清朝统治者还采取了蠲免厂欠的措施。厂欠的蠲免意味着由官府承担了铜厂的债务,从而造成官府的财政损失,但该举措的实行对减轻铜厂生产压力确实起到了作用。乾隆、嘉庆年间,清廷多次蠲免云南铜厂厂欠,李中清先生统计了1720—1814年间部分年份云南铜矿厂欠损失情况,兹节录如下:
(二)对黔铅衰落的挽救与调控措施
针对清代黔铅日益衰落的形势,清朝统治者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对其进行挽救和调控。
1.控制成本、清查私矿
米价是影响矿厂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有效控制不断上升的米价,贵州当地官员提出:“崇俭禁奢,清查酒肆,通都郡邑官为定数,新疆村寨一概禁止。尤在劝开垦、惩奸民、兴水利以开其
源。”与此同时“饬令地方官凡遇报垦荒山,务即亲复勘明,给照为业。其无力引水之田,则照例官借工本,限年完项,分别升科。”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
除此之外,贵州地方官员还提出了“赈粜”的对策,乾隆十三年(1748),护理贵州巡抚布政使恒文复奏:“……现贮(米)百四十万石,即遇偏灾,足备赈粜。”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17),乾隆十三年六月壬午。
从以上史料来看,清代贵州官员对控制米价的措施是得法的。
雍正初年,贵州地方官府对私矿进行大力整顿,将其纳入官府监管之下。雍正二年(1724),贵州巡抚毛文铨奏:“尚有丁头山、齐家湾等处铅厂,昔日俱属私开,即前折奏闻之滥木桥水银厂,从前亦无分文归公之处,今逐一清查,现檄藩司议定抽收之数”。
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毛文铨,奏请查私开矿厂酌议抽收款项归公折(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经过此次大规模整顿,大部分私厂开始抽课纳税,成为国家监管的合法矿厂。
2.提高铅价、降低矿课
提高铜价能有效调动矿厂的生产积极性,清朝统治者注意到了此问题。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贵州巡抚李庆棻奏准“黔省福集、蓮花二厂,……日形支绌。查厂产不旺之故,实缘开采已久,漕峒日深。……而福集厂每铅百斤价一两四钱,莲花厂价一两五钱。又每百斤抽课二十斤,计炉丁得数,每百斤仅获工本一两一二钱,自难踊跃赴采。请照滇省加增铜价例,每百斤加价三钱,即于解运京铅节省水脚银六万余两内拨补养廉等项外支给。”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戊午。
又如,乾隆八年(1743)二月,贵州总督监管巡抚张广泗奏准:“莲花、砂硃等厂,矿砂既薄,食物俱昂,炉民无利可图,人散炉停,出铅日少。请将每斤一分有零原价定为一分五厘,一面收买,一面发运。”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85),乾隆八年二月辛亥。
除了提高铜价外,清朝统治者还采取降低矿课来刺激生产。如道光八年(1829)十二月,道光帝谕内阁:“黔省妈姑、福集等铅厂因开采年久,峒老山空,砂丁采取匪易。新发白岩子厂夏间雨水过多,漕峒被淹,招丁车水,需费不少,炉户倍形疲乏。……所有该厂等应抽二成课铅,准照滇省新铜抽课一成之例,暂减一成,以纾厂力。” 参见《清宣宗实录》(卷148),道光八年十二月丙寅。
四、余 论
清代“滇铜”和“黔铅”都共同出现了“盛极而衰”或是“由盛转衰”的变化,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生产成本的急剧增加、开采难度的日益加大、自然灾害破坏、“铜价”“铅价”增长幅度比不上成本增加速度,私矿泛滥等。清廷采取了一些列诸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价格、查禁私矿、发放补助金、蠲免厂欠等措施,短时间内使矿业衰落问题得到缓解,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云贵地区矿业衰落的趋势,随着清朝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和西方殖民者入侵,滇铜和黔铅的衰落势不可挡。
加之矿民及其与采矿相关的从业人员纷纷失业,這些失业者逐渐演变成为一支反抗官府的力量,在与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民变结合之后,共同加剧了清朝后期的边疆统治危机。
回望这段历史,“滇铜”和“黔铅”的兴旺,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带动了西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滇铜”“黔铅”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也有政治的原因。清廷对此采取的调控策略和措施有其可取之处,一是清廷注重综合施策、多管齐下,将挽救矿业衰落当做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手段,一段时期内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二是清廷注重因时因事,分类指导,针对“滇铜”和“黔铅”衰落的不同原因,分类采取了不同的调控措施,当然这些措施的实行是与两省地方大员的矿政理路相匹配的。三是清廷尤其注重运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矿业衰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经济问题,当然传统社会之下经济往往受制于政治。在清廷挽救矿业衰落的措施中无论是降低成本、提高价格、降低矿课、补助资金,都体现了现代政府对经济和产业调控的理念、思路。这样的理念和思路出现于19世纪对中国西南边疆矿业的调控和治理上更有其可贵之处。
参考文献:
[1]徐斌.试析清中后期云南铜业衰落的原因[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4):50-55.
[2]文思启.林则徐与云南矿冶业[J].思想战线,1985(4):85-89.
[3]刘朝辉.嘉道时期滇铜供应问题探析:兼论嘉道时期云南铜矿之衰落[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77-83.
[4]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肖本俊.清代乾嘉时期云南矿区的“山荒”与滇铜业的衰落[D].昆明:云南大学,2011.
[6]罗时法.清代前、中期贵州矿业略考[J].贵州社会科学,1986(4):59-64.
[7]袁轶峰.清代大定府铅铜业衰落的原因探析[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3):5-9.
[8]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教研室.清代的矿业: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志九十九:食货五:矿政[M]//清史稿:卷124: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
[10]盐务考三[M]//龙云. 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册:卷149.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11]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卷14[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2]贵州通史:第3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13]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4]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5]云南通志:艺文志:云南铜志[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12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6]刘若芳, 孔未名.乾隆年间疏浚金沙江史料:上[J]. 历史档案, 2001(1):47-61.
(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