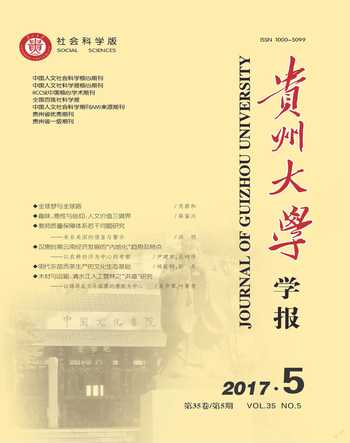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探析
2017-05-30蒲应秋王萍
蒲应秋 王萍
摘 要:唐宋时期是四川地区茶叶生产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四川地区种茶范围宽广,茶叶亩产量较高。据此可知,唐代四川地区茶叶年产量大约在1千万斤左右。记载前、后蜀时代四川地区茶叶生产的文献资料甚少,从零星的茶史资料记载中,可以窥见当时茶叶年产量大概在1千万斤的生产水平。宋以降,四川地区茶叶生产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宋政府在四川施行榷茶及茶马贸易政策,为研究宋代四川地区茶叶产量提供较为准确的数字,我们结合各类文献记载当时四川地区的茶叶生产状况,认为宋代四川地区的茶叶年产量达到3千万斤左右应当无疑。
关键词:
唐宋;四川;茶叶产量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5-0087-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5.14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生产发展迅速,茶叶产量有了很大提高,这引起茶史学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的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然而,学界对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唐五代时期的茶叶产量,学界基本上采用推理、估算的方法得出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的概数。尽管这些数据与实际数据存在一定偏差,但是学者对此做了开拓性研究,值得肯定,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关于宋代四川地区茶叶产量的研究,学界依据相关文献记载四川地区的茶叶生产状况,对宋代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探讨较为客观。但是学者对于宋代四川地区茶叶产量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四川地区茶叶年产量不高,达不到三千万斤的生产水平。针对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
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至今未见文献对它有明确的记载。然而,在笔者所搜集的资料当中,仅有几条资料与之相关,为便于分析,现胪列如下:
1.杨晔《膳夫经手录》云: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犹必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
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重之,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新安草市,岁出千万斤。[1]8
2.张唐英《蜀梼杌》载:(天复)三年,(唐)昭宗还长安,(王)建奉表贡茶、布等十万。[2]364
3.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开平四年五月,岐王屡求货于蜀,蜀主皆与之。又求巴剑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贞勤亦至矣,若与之地,是弃民也。宁多与之货,乃复以丝、茶、布、帛、七万遗之。[3]8723
4.脱脱《宋史》载:蜀户部员外郎、知制诰、工部侍郎、云安榷盐使毋守素“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籍其蜀中庄产茶园以献,诏赐钱三百万以充其直,仍赐第于京师。[4]376
综合上述材料反映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唐代四川地区的茶叶年产量达到唐人杨晔认为“岁出千万斤”的生产水平应当可信;第二,五代四川地区茶叶年生产能力亦应接近千万斤水平。
遗憾的是,上述这些材料未能说明当时茶叶生产的具体年产量,好在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研究学界对唐宋时期茶叶产量探讨较多,但对当时茶叶总产量的研究,学者观点分歧较大。如陈椽认为唐代茶产量大约为今200万担。陈椽:《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88年第57页。郭正宗认为唐代茶叶产量可能是几千万唐斤,宋代茶产量估计是1亿斤,合今6万吨以上。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258页。李家光估算唐代四川茶叶产量在6 600万斤。李家光:《巴蜀茶史三千年》,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方健认为唐代茶叶产量约在6 000万斤,五代茶叶产量与唐代茶叶茶叶产量持平,宋代茶叶产量达到1.5亿斤水平。方健: 《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朱重圣认为南宋时,四川四路茶叶产量约为2 000万斤。朱重圣:《宋代茶之产区及其种类与产量》,宋史研究集(第15辑)。因此,博采眾家之长,本文以唐代茶叶产量最低数值计算当时四川地区茶叶产量,其结论较为客观。
如陈椽认为唐代茶叶产量超过1亿斤,其中私茶达到10万吨[5]55-56。方健认为唐代茶叶年产量约为6 000万斤[6]79。由此可见,学界认为唐代全国茶叶年总产量在1亿斤至6 000万斤之间。同时学界还认为唐代产茶州的数量最少为42州郡[5]44-45,最多为98州郡[7]19。如前所述,唐代四川地区茶叶分布范围遍及3道23州。如果我们以唐代全国98个产茶州计算,四川地区的产茶州约占全国产茶州的23.5%;再以唐代全国茶叶年产量6 000万斤为标准,那么唐代四川地区的茶叶最低年产量也在1 408万斤左右,这说明唐代四川地区的茶叶年产量达千万斤应当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这与唐人杨晔“岁出千万斤”之说恰好相吻合。
此外,有的学者研究认为唐代采摘的新鲜茶叶的亩产量在143市斤[8]43或182.7斤[9]47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以唐代四川地区最有名的产茶州—雅州为例,推算当时该地区的茶叶年产量。唐玄宗天宝十二载,雅州的面积为13 478平方千米[10]212。这里仅以州境千分之一的植茶面积换算,即植茶面积为20 217亩,故唐时雅州的新鲜茶叶年产量约为289~369万斤,说明雅州新鲜茶叶年产量不低,这是雅州的情况。又,我们以唐玄宗天宝十二载,产茶州境面积最小的费州来计算茶叶产量,其州境面积为1 780平方千米[10]207,同样以州境千分之一的植茶面积换算,即植茶面积为2 670亩,则唐代费州的新鲜茶叶年产量约为38~49万斤。如果我们以雅州与费州新鲜茶叶年产量的平均值169~203万斤作为唐代四川地区各产茶州茶叶年产量,如前所述,唐时四川地区产茶州为23州,这就不难算出唐代四川地区鲜叶茶年产量在3 887~4 669万斤。当然,这是新鲜茶叶的产量,若换算为干毛茶鲜茶与干茶的折算率大约为25%,见朱自振,唐荣南:《由茶叶历史谈恢复茶园夏令生态系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206页。也应当在971~1 167万斤。故综合而论,唐代四川地区干毛茶的年产量在971~1 408万斤应当成立,因为四川地区是当时全国重要的产茶区,茶园面积相当广泛,且有的产茶州以此为业[11]8084。
五代十国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囿于文献资料匮乏,其具体数据无从统计。我们只能通过文献资料中有关茶叶记载的只言片语,推测当时四川地区茶叶年产量的大概数据。如前蜀“(王)建奉表贡茶、布等十万。”又给予歧王李茂贞“复以丝、茶、布、帛、七万遗之”;后蜀毋守素以“蜀中庄产茶园以献,诏赐钱三百万以充其直。”[4]376等信息,很好地说明当时四川地区的茶叶生产继续向前发展,否则不可能在朝贡的物品中,多次言及茶是蜀地的大宗贡品。五代十国时期,前、后蜀政区范围体大体与唐代四川地区的范围相当[12]29-30,即四川地区的主要茶产区仍在前、后蜀政区范围内,故可推测五代十国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年产量亦当接近唐代茶叶年产量971万斤到1 408万斤的水平。
二、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
北宋中叶,朝廷在四川施行榷茶政策,加强对四川地区的茶叶生产、销售等环节的管理,并在官方的文书中多次记载买茶、卖茶等相关情况。因此,宋代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数据来源相对准确。我们综合各种文献资料,能够较为准确地计算北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
北宋政府在四川地区施行的茶业政策以神宗熙宁七年(1074)为界限。熙宁七年前,四川地区茶业政策是“听民自卖”时期;熙宁七年(1074)后为“榷茶专卖”时期。此后,宋政府在四川地区的榷茶政策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也未作更改。宋代四川地区“听民自卖期”的茶叶产量无法准确统计,但“榷茶专卖”政策实施后,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记载较为具体、可靠。因而,我们探讨北宋四川地区茶叶产量主要以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后的数据为准。据脱脱《宋史·食货志》载:
(熙宁)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趋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13]4498
这则材料表明,宋政府榷禁蜀茶始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榷禁的蜀茶被运往秦凤、熙河等地与西番人交换马匹。北宋政府在四川地区设置专门的机构都大提举茶马司,掌以川茶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换马匹。
自熙宁七年四月,差太子中舍三司干当公事李杞,著作佐郎梓夔路察访司备差遣蒲宗闵相度成都市易务,得旨令市易司经画收买茶货,专充秦凤熙河路博马,更不相度市易。当年十一月,权发遣三司盐铁判官公事、提举成都府利州路买茶公事李杞,同提举成都府利州路买茶公事蒲宗闵,应买茶博马州军,并令李杞等提举。遂命杞与提举刑狱序官,蒲宗闵与提举常平序官,后又令与转运判官序官,自后因之。置都大提举及主管、同主管,各因其资品高下除授云。
《哲宗正史·职官志》: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收摘山之利以佐调度,凡市马于蕃夷者,率以茶易之。产茶及市马州郡,官属得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18]4134。
此则材料详细介绍了都大提举茶马司的设置经过和权限范围。由此说明宋代都大提举茶马司记载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较为可信。由于宋朝廷榷禁川,导致民生艰难,同时,蜀地官员向朝廷上奏反对榷禁蜀茶的奏折,也提供了一些蜀茶产量数据。如,知彭州吕陶向宋廷数次提出反对榷禁蜀茶的奏折当中,多处提及当时蜀茶的年产量。现将吕陶奏折当中有关蜀茶产量的文字摘录如下:
每岁约以五万驮应副熙河,仍设秦、泾原两路卖茶之禁并如黄廉之请,则自可得一百万贯以助边计,以行博马法亦不阙少。又何必独禁三处以贻斯民之忧乎?其它诸路所入素薄。宜一切舍之,以与商旅庶为昭来之渐也。又况蜀茶岁约三千万斤(原注:元丰七年二千九百一十四万斤,八年二千九百五十四万八千斤)。除和买五百万斤入熙河外,尚有二千五百万斤皆属商贩,流转三千里之内,所谓住税、翻税、过税者,亦可得五十万贯(原注:旧例住税每斤六文,客人买出翻税每斤六文,两项可得二十五万贯,所过场务,远者十处,近者三两处,再远者四五处,过税每斤收二文,五场共收十文,又可得二十五万贯。熙宁七年,兴元府一处收茶税七百万余斤,计钱四万二千余贯。以此推之,其数必有)。自榷法之行,茶之忧牙税、脚息、头子、笼索等钱,皆为无名之敛。今既解去罗网,一切不问,第以一贯之茶,纳长引钱百文,则人情简便,必亦乐输,又有十余万贯(原注:川茶贵者每斤三百文,贱者三、二十文。今总计为五十文,凡二千五百万斤计一百二十五万贯,乃得常引钱十二万五千贯)[14]34。
上则材料是吕陶在熙宁十年(1077)向朝廷上奏的折子,它是发生在北宋政府榷禁川茶以后的事情。自宋廷榷茶以后,政府垄断茶叶买卖,因此政府很可能准确地掌握茶叶产量。吕陶在奏折中说“每岁约以五万驮应副熙河”,驮是宋代的计量单位,一驮相当于今天的100市斤。不难看出,北宋政府每年从四川运到熙河销售的茶叶大约在500万斤,这足以说明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不低。吕陶的奏折还提到蜀茶“岁约三千万斤”,亦即蜀茶年产量在3 000万斤左右,并且还指出元豐七年(1084)、八年(1085)蜀茶年产量都在2 900万斤以上,很接近熙宁十年(1077)3 000万的年产量,这说明蜀茶年产量基本上在2 900万斤至3 000万斤之间,这为每年输送到熙河500万斤茶叶提供了保障。
有学者对吕陶“蜀茶岁约三千万斤”的说法提出质疑。其理由是吕陶在另一奏折中说:“两川所出茶货,较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14]3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贾大泉认为蜀茶年产量峰值达到3 000万斤应当无疑问。笔者赞同贾大泉先生蜀茶年产量在3 000万斤的观点,理由有三:其一,吕陶作为地方官员向朝廷上奏折子,条陈反对榷茶,主张通商,必须核实清楚蜀茶年产量,得出通商与榷茶,哪一个方案更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才能说服朝廷蜀茶通商不至于影响国家边防大计,也才能达到弛禁通商的目的。因此,他连续列举元丰七、八年茶产量和当年(熙宁十年)的茶产量在2 900万至3 000万之间是经过认真考察后作出的结论;其二,吕陶“十不及一”的说法未免带有宋代文人常见的匡算和估计,缺乏精确和缜密性,但吕陶的本义是川茶与南茶相比,产量远不相及。因此不能望文生义,就一定是不及北方和东南的1/10,并且吕陶后来的奏折当中对“十不及一”的说法做了修正[15]。因此,这必然不会是“不足为据,并被他后来所放弃的推想”;三是根据吕陶奏折提供的数据可以计算蜀茶年产量。吕陶说:“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14]4吕陶的奏折很清楚地表明蜀地茶园的产量不低,虽然岁出三、五万斤茶叶的必定是少数,但是出一、二百斤茶叶的必占多数。吕陶又云:“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多以种茶为生,有如五谷。”[14]30显而易见,宋代四川地区的成都府路、利州路一带百姓种茶极为普遍,形成集中连片的茶叶产区。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邛、蜀、彭、汉、绵、雅、洋州、兴元府”等地的户数为792 693[16]157-158。据此,我们以这一带70%的人户种茶来计算,即有554 885户,若平均每户生产200斤茶,则茶叶年产总量为110 977 020斤,当然,这是新鲜茶叶的产量,如果我们再以新鲜茶叶换算成干茶的比率025来折算,则是27 744 255斤,这个数字与吕陶说蜀茶岁约3 000万斤相当接近。综合这三方面的情况来看,吕陶奏折中北宋时蜀茶岁约3 000万斤应当是审慎、比较可靠的数据。因此,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年产量在3 000万斤已无疑问。
三、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
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年产量史籍中也同样未发现所记具体数据,故笔者只能选择略有相关信息的成都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为代表,对当时该区的茶叶年产量进行分析。
先看成都府路和利州路。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绍兴元年,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场,(茶)岁产二千一百万零二斤。一千六百十七万系成都府路,九州岛军凡二十场。四百八十四万系利州路二州,三场。”[17]306从李氏记载来看,南宋时期四川地区仅成都府路和利州路茶叶年产量达到2 102万斤。其中,成都府路茶叶年产量为1 617万斤,利州路茶叶年产量为484万斤,成都府路和利州路的茶叶年产量分别约占总量的77%和23%,说明南宋时期成都府路仍然是最主要的茶产区。李心传记载成都府路、利州路茶叶年产量在2 102万斤以上的数据,还可以从赵开变更茶法后的茶引收入得到印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
朝廷遂擢开同主管川陕茶马,建炎二年十一月开至成都,大更茶法。仿蔡京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茶。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茶引钱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利头子在外……引息钱至一百零五万缗。绍兴复提举官,又旋增引钱至十。绍兴四年,每引收十二贯三百文,视开之初又增一倍矣。[17]353
从赵开茶法可以看出,以每斤平均收引钱60文,每年茶引钱为105万缗,即以每年所收茶引钱1 050 000斤(1缗即1贯等于1 000文)。不难看出,成都府路茶叶年产量接近1 750万斤,再加上利州路茶叶产量484万斤,即是成都府路和利州路每岁产量应当在2 100万斤以上,而且赵开之后的继任者又不断增加引钱,说明成都府路和利州路茶叶年产量不会低于2 100万斤。
其次看夔州路的茶叶年产量。夔州路是川东的一个重要产茶区域,但茶叶年产量却相当低,这从下列资料的记载当中可以窥探其茶叶产量。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绍兴十七年,韩球始榷忠、达州茶,即夔、合、广安置合同场,岁以八万斤为额。”[17]427显而易见,南宋政府在夔州榷茶的岁额仅有8万斤。另,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凡税租之数总二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二斤……利州路,夏三万七千二十八斤,秋一百七十斤;夔州路,夏七千九百九团。”[18]6469“团”是宋代度量茶叶重量的单位,每团相当于今天的25市斤,夔州路7 909团,可折合为今天的197 725斤,这反映了夔茶产量不高,以宋政府征收什一税计算,夔茶年产量当在1 977 250斤。该书又载:“禁榷以来商旅不通,委于民夷不便,遂于绍兴二十八年十一月内具申尚书省,乞将夔路茶住罢禁榷。后准户部符,止依已降指挥施行。本司今再行询究夔路茶味苦价低。不比他路茶货州”[18]6689。从材料记载可知夔州茶因茶味苦,官府榷禁无利可图。因此,绍兴二十七年(1157),知忠州董时敏上书朝廷要求停罢榷禁夔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
先是右朝请大夫董时敏知忠州,尝请罢榷夔茶,都大主管四川茶马公事许尹不可。既而,尹复言商旅不通,委于民夷不便。而都茶场以其前后异说,持之不行。及是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权提举茶马王之望复以为言,遂弛其禁。”[17]354
可见,宋朝部分官员主张弛禁夔茶,允许商人自由贩卖。然而,由于政府茶税过高,商人贩卖夔茶的成本增加。据徐松《宋会要辑稿》载:
夔茶一百斤,共三十四贯二百文。止卖得价钱二十六贯文;商人在达州东乡收买饼茶,每斤一百二十文,每团二十五斤,共三贯文,沿途又纳脚税三贯五十文,买关引二贯五百文,共八贯五百五十文,运往渠州合同场出卖,‘约度中价,止卖得六贯五百文[18]6498。
不难看出,商人购买100斤夔茶,需要34貫200文的成本,然而售卖仅得26贯。显然,商人贩卖100斤夔茶要亏损8贯200文,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商人不愿意贩卖夔州茶。又如商人收购达州东乡饼茶,其成本为8贯550文,然而,商人将夔茶运到渠州合同场贩卖仅得6贯500文,其亏损也很大。这反映了宋政府榷禁夔茶陷入无利可图,商人贩卖夔茶严重亏损的两难境地,导致夔茶滞销,从而影响百姓植茶的积极性,故夔茶产量不高,年产量约在197万斤左右。
据上述探讨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可知,南宋成都府路茶叶年产量为1 617万斤、利州路茶叶年产量为484万斤,夔州路的茶叶年产量约为197万斤。由此可见,南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最高者为成都府路,其次是利州路,最后是夔州路。有关潼川府路茶叶生产的史料阙如,因而无法统计,但从南宋时期成都府路、利州路、夔州路茶叶年产量可以确定南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年产量保持在2 100万斤的水平,这还不包括尚未统计潼川府路的茶叶产量。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对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的探讨得出如下结论: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依据文献典籍零星记载,据此推测当时四川地区的茶叶年产量大约在970~1 400万斤左右。两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较之唐五代有了很大提高。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年产量最高已达到3 000万斤。南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年产量虽略有下降,但总体来说,南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年产量应当不低于2 100万斤。因此,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在全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囿于唐五代及南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资料匮乏之缘故,其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运用推算,估测的方法,因而对唐五代和南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的结论值得商榷。故唐五代及南宋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产量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化。
参考文献:
[1]杨晔.膳夫经手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2]张唐英.蜀梼杌[M]//丛书集成新编. 台北:新丰文化出版公司,1986.
[3]司马光资治通鉴 [M].胡三省,音注. 北京:中华书局,1956.
[4]吴任臣.十国春秋 [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陈椽. 茶业通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6]方健. 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71-85.
[7]王洪军. 唐代的茶叶生产[J].齐鲁学刊,1987(6):43-49.
[8]王洪军. 唐代的茶叶产量、贸易、税茶与榷茶[J].齐鲁学刊,1989(2):14-21.
[9]周荔. 宋代的茶叶生产[J].历史研究,1985(6):42-54.
[10]翁俊雄. 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1]董诰.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1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吕陶净德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15]贾大泉. 宋代四川地区的茶业和茶政[J]. 历史研究,1980(4):109-124.
[16]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7]李心传,徐规.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8]徐松,刘琳,刁忠民,等. 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