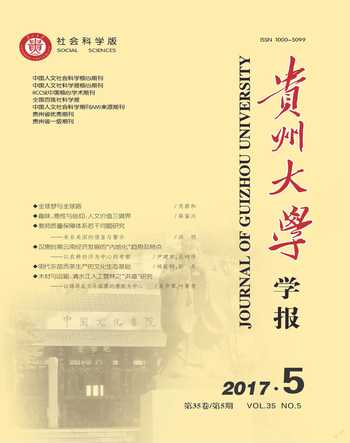贫困地区农户对扶贫效果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2017-05-30张自强伍国勇徐平
张自强 伍国勇 徐平
摘 要:基于贵州关岭县的农户调查,区分农户是否感知扶贫实惠和感知扶贫帮助程度的2个层面,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农户特征、社会保障、政策认知和政策评价4个方面共15个变量,分别运用二元与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各变量对农户感知扶贫政策实施效果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尽管物质给予能够增强贫困地区农户对扶贫实惠的感知,但包括农村低保、农村养老保等农村社会保障措施在内的制度完善才有利于提高扶贫政策的帮助程度,基于农户可行能力塑造的社会网络建设是扶贫开发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贵州;扶贫;可行能力;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5-0070-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5.11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得中国农村减贫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贫困线多次提高,2011年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显示,农村贫困人口仍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10年的2 68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2.8%。据《国家人權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2012—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2%,农村贫困人口减少6 663万人。然而, Zaman等针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国家的研究发现,尽管经济增长有助于贫困的下降,但收入不平等却会加剧贫困的发生,作用正好相反。[1]以县为单位的扶贫策略有利于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但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2]值得注意的是,隐形贫困的存在使得脱贫的群体很容易再次陷入贫困,即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显然,通过个体自身能力的修复来摆脱贫困存在瓶颈,多维制度设计与社会网络构建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着力方向。
根据Sen的观点,贫困的实质在于可行能力的丧失,包括教育、技能、健康、机会等内容,扶贫重点从消除物质贫困向缓解能力贫困转变。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贫困线标准忽视了包括教育、卫生、福利在内的非收入特征的制度安排。在扶贫资金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的脱贫却越来越困难,[3]即存在“越扶越贫”的现象。
扶贫措施开始从单纯地关注援助资金的规模到全面地考虑制度建设转变,国际发展援助开始“制度转向”[4]。新时期贫困性质的转变包括:一是地域性贫困,由自然环境条件所致;二是个体性贫困,即素质性贫困,由个体健康、劳动能力等条件所致;三是体制性贫困,如二元经济体制引发的贫困。[5]扶贫开发也开始从“粗放式”向“精准式”转变,2013年,《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建立风险、脆弱性预警机制,提高扶贫效率。[6]
对能力贫困而言,农村社会保障是直接针对收入贫困,应具备显著的减贫效应。[7]农村“新贫困”特征的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政治与社会权利的缺失或被排斥。[8]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陈立中在实证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影响的基础上,建议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9]蒋选和韩林芝基于灰色关联分析发现,农村义务教育对贫困消除具有显著影响。[10]薛惠元运用倍差法实证分析发现,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11]樊丽明和解垩实证检验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发现,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工作性质及地区变量同时同方向地影响到贫困及脆弱性。[12]
在关注政策减贫客观效果的同时,现有研究还注意到了贫困地区农户的主观满意水平。肖云和严茉基于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户调查,分析了农户对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户家庭特征、扶贫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等。[13]王宏杰和李东岳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实证分析发现,农户对扶贫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14]陈小丽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社会发展、扶贫投入等多个方面评价了扶贫效果的影响,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影响权重较高。[15]
现有研究注意到了新时期农村贫困特征的转变,强调扶贫政策或措施不再仅仅是物质给予,而更侧重于基于制度保障的脱贫能力塑造;实证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户对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然而,贫困表征多维,在侧重于贫困率、贫困户收入增长等客观成效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农户对贫困状况改善的主观感知。对此,本研究基于贵州关岭县的农户调查,结合农户禀赋与能力塑造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在分析影响农户是否享受扶贫福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户评价扶贫效果程度的影响,探讨农户扶贫效果认知的影响因素,为提高扶贫政策或措施的实施效果提供参考借鉴。
一、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扶贫开发战略和政策研究调查》课题组2016年5—6月对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农户问卷调查。关岭县隶属于贵州省安顺市,是国家级贫困县,调查样本选取具有代表性。问卷调查采取随机入户形式,主要集中在顶云乡、永宁镇、断桥镇等多个乡镇的10多个村,结合访谈进行。共发放问卷310份,收回问卷260份,其中有效问卷252份。
2.变量选取
基于以往研究对影响农户贫困因素的分析,本研究将影响因素分为农户特征、社会保障、政策认知、政策评价4个方面共15个影响因素。其中,农户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常年外出打工、是否经常生病、土地面积;社会保障包括是否享受农村低保,是否享受农村养老保;政策认知包括扶贫对象是否准确,扶贫资金使用是否公正,扶贫政策是否真正需要;政策评价包括政府对扶贫的重视程度,扶贫政策实施满意度,农村“低保”效果,农村“养老保”效果,“新农合”效果(如表1)。
自变量中,年龄x11、受教育年限x12和耕地面积x15为连续变量,其他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受访农户年龄最低为17岁,最高达91岁;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最小为0公顷,最大为1.07公顷;农户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6.59,受访农户的教育程度比较低。需要说明的是,调查问卷中涉及到“农户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问题,受访农户基本都参与了,所以在社会保障的变量中未纳入这一因素。
3.模型设定
二、实证估计
运用stata 12.0统计软件估计得出表2。从表2可知:二元logit回归结果中,LR chi2(15)值为49.25,相应的p值为0<0.05,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Pseudo R2值为0.41;有序logit回归结果中,LR chi2(15)值为136.01,相应的p值为0<005,模型整体拟合度也较好,Pseudo R2值为056。二元logit回归结果中,社会保障中的变量影响不显著,政策评价中的变量影响比较明显;有序logit回归结果中,变量影响显著性较小,社会保障与政策认知中的变量影响均不显著,各变量的具体影响如下:
第一,农户特征变量的影响。一是农户“受教育年限”x12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05,且统计上不显著。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认为获得扶贫实惠的可能性越低,这可能与自身人力资本未得到发挥有关。如果只是救济性扶贫,农户脱贫能力未得到自我塑造,人力资本作用效果较小。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扶贫政策带来帮助的有序logit回归结果中,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系数为0.11,也不具有統计上的显著性,但作用方向为正,作用强度较高,表明当扶贫政策或项目实施如何利用到农户自身的人力资本时,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资本发挥的作用相对越大,对扶贫政策产生帮助的作用评价也就越高。
二是农户“是否常年在外打工”x13变量对是否享受扶贫实惠的影响系数为1.50,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户享受到扶贫实惠的可能性越高,这可能与地方政府鼓励劳动力转移有关。然而,该变量对扶贫政策帮助的有序logit回归结果的系数为0.56,且统计上不显著。即常年在外打工农户对扶贫帮助评价越高的可能性越小,表明常年不在家的农户对扶贫政策了解程度有限,对扶贫政策效果的评价相对就低。劳动力转移不仅能改善家庭贫困,还有利于城镇化建设,地方政府积极性较高,农户享受到的政策红利越大。
三是“是否经常生病”x14变量对是否享受扶贫实惠的影响系数为0.48,且统计上不显著。即农户健康状况越差,能够享受到扶贫实惠的可能性越高,健康状况越差的农户享受政府救济相对越多。该变量对扶贫政策帮助的有序logit回归结果的系数为-1.79,且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即健康状况差的农户确实能享受到扶贫实惠,而且认为扶贫政策带来的帮助越大。显然,农村医疗制度的完善对于扶贫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性,但农村缺乏大病救济制度,越是严重的疾病,能够享受到的扶贫帮助越是有限,“因病致贫”时有发生。相比于其他变量,该变量的影响系数非常大,可见农户对此的重视程度。
第二,社会保障变量的影响。农户“是否享受农村低保”x21变量和农户“是否享受农村养老保”x22变量,对y1和y2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但统计上均不显著,表明农户能够享受到农村低保或养老保的政策福利。但感知扶贫实惠的可能性越大,认为扶贫政策帮助的程度越小,说明农村低保与养老保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两项政策的实施对农户感知扶贫效果的提升作用有限。
第三,政策认知变量的影响。一是“扶贫对象是否准确”x31变量对y1和y2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77和-0.47,且统计上均不显著,说明扶贫对象准确与否对农户扶贫政策实惠的感知不存在必然相关性。
二是“扶贫资金使用是否公正”x32变量对y1的影响系数为0.47,且统计上不显著,表明扶贫资金使用越公正,农户感知扶贫实惠的可能性越大,农户了解具体扶贫政策项目的实施,甚至参与相关扶贫政策与项目的讨论,对扶贫实惠的感知水平相对就越高。该变量对y2的影响系数为-0.38,即农户认为扶贫资金使用公开、公正,对扶贫政策带来实际帮助评价高的可能性越大。由此可以认为,扶贫资金使用的公开、公正,不仅能增强农户对扶贫政策的感知,了解到存在“实惠”,而且能影响农户感知政策“实惠”的大小,“公开”有利于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至少避免“流失”,农户能理性地对待扶贫资金的使用。
三是“扶贫政策是否真正需要”x33变量对y1的影响系数为2.3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该变量对y1的作用强度与显著程度都比较大,即农户认为扶贫政策越是真正需要的,对扶贫实惠的感知程度越高,表明扶贫政策在满足当地农户实际需求上更能影响农户对扶贫效果的判断。而且该变量对y2的影响系数为0.69,也具有比较大的正向作用,但不显著,表明尽管扶贫政策是自身需要的,但认为政策产生的帮助较小。由此可知,农户不仅关注扶贫政策是否满足自身需求,更重视得到满足的程度,“救济式”扶贫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户需求,但农户更需要脱贫能力的塑造。
第四,政策评价变量的影响。一是“政府对扶贫重视程度”x41变量对y1的影响系数为-3.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政府对扶贫的重视程度越低,农户感知扶贫实惠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表明政府重视贫困户识别、农户需求、扶贫资金使用等方面,能够提高农户享受扶贫政策的实惠。且该变量对y2的影响系数为0.91,统计上不显著,进一步表明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政府对贫困的关注与重视程度决定了扶贫效果与效率。
二是“扶贫政策实施效果”x42变量对y1和y2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93和3.17,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越满意扶贫政策,感知扶贫实惠的可能性越高,对扶贫政策产生帮助评价高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三是3项农村公共服务中,只有“‘新农合效果”x45变量对y1和y2的影响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且影响系数分别为-105和120。即农户认为“新农合”效果越低,感知扶贫政策实惠的可能性就越低,对扶贫政策产生帮助评价低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表明农村医疗制度建设对农户脱贫更具有建设性价值。而且健康影响农户人力资本,保障农户健康的制度越完善,农户人力资本提升可能性越大,脱贫能力也就相对越强。
三、结论与启示
1.结论
基于贵州省关岭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将影响农户对扶贫效果的评价从2个层面展开,即是否感知扶贫实惠和感知实惠帮助的程度,结合以往研究成果,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农户特征、社会保障、政策认知和政策评价4个方面共15个变量,分别运用二元logit回归和有序logit回归,分析了各变量对农户感知扶贫实惠与实惠帮助程度的作用机理,结论如下:一是农户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常年在外打工、经常生病和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少,农户感知扶贫实惠的可能性越高;二是享受农村低保、农村养老保的农户感知扶贫实惠的可能性越高;三是扶贫资金使用公正、政策符合自身真实需要,农户对扶贫实惠感知的可能性就越高;四是政府对扶贫工程重视程度越高,农户对扶贫政策实施越满意,“新农合”实施效果越好,农户感知扶贫实惠的可能性就越高。
2.启示
从实证估计结果看,影响因素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农户人力资本的作用,包括教育、健康、农村医疗变量均具有显著影响。“救济式”扶贫难以满足新时期农户脱贫需求,自身能力的塑造才是摆脱贫困的关键。其中,人力资本的提升能显著改善农户生产与创收能力,避免物质脱贫的脆弱性。从对扶贫政策产生帮助的影响结果看,有关人力资本的变量才是影响农户对扶贫效果判断的依据,对此,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在内的教育服务对于地区和农户脱贫具有深远意义。二是扶贫公开透明的重要性。由于制度依赖与权力寻租的存在,部分贫困地区存在“越扶越贫”的脱贫怪圈,扶贫项目实施与扶贫资金使用的公开并不一定能显著改善扶贫效果和扶贫效率,但能增强社会监管与监督,至少能避免扶贫资金使用的“使命漂移”,在“公开”的基础上逐渐引入市场参与机制,扩宽扶贫资金使用的市场化途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的帮扶程度。三是新时期贫困特征对扶贫攻坚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网络的制度建设对农村贫困兜底尤为重要,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在兼容地区环境优势或特征的同时,也需要切合农户脱贫需求。制度设计需要农户参与,强制性政府干预尽管能带来扶贫实惠,但农户感知实惠的程度较低,扶贫效果有限,引入农户参与途径后构建农户参与扶贫建设平台,制定满足当地农户需求的扶贫政策或制度,体现了扶贫“精准”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保障地区脱贫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ZAMAN K, SHAH I A, KHAN M M, et al. The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triangle: new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SAARC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 Business Research, 2012, 4(5):485-500.
[2]王志凌,邹林杰. 国家级贫困县“精准”扶贫效率评价:以广西27个县为例[J].貴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02-106.
[3]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4]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Chapter 6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J].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005, 1(5):385-472.
[5]吕炜,刘畅.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社会性支出与贫困问题研究[J].财贸研究,2008(5):61-69.
[6]黄承伟,王小林,徐丽萍. 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J].农业技术经济,2010(8):4-11.
[7]阿马蒂亚·森.论社会排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1-7.
[8]段文娟. 论“社会排斥”与农村“新贫困”[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5(6):11-14.
[9]陈立中.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J].经济学(季刊),2009(2):711-726.
[10]蒋选,韩林芝.教育与消除贫困:研究动态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3):66-70.
[11]薛惠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对广西和湖北的抽样调研[J].现代经济探讨,2013(3):11-15.
[12]樊丽明,解垩.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J].经济研究,2014(8):67-77.
[13]肖云,严茉.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对扶贫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2(5):107-112.
[14]王宏杰,李东岳.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44-49.
[15]陈小丽. 基于多层次分析法的湖北民族地区扶贫绩效评价[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76-80.
(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