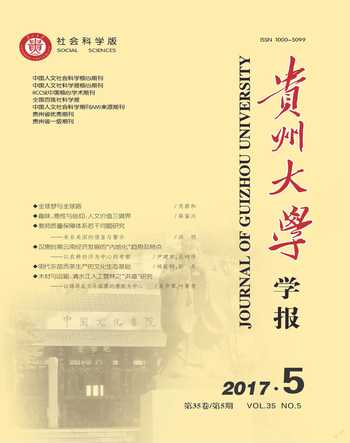审美相对主义:解构及其限度
2017-05-30邓军海
摘 要:相对主义,无论是审美相对主义还是伦理相对主义,几乎成了20世纪以来知识界的一种“政治正确”,甚至以一种“绝对”面孔出现。变成绝对政治正确的相对主义,不只理论上自相矛盾,而且实际上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旨在解放,却完成了人的奴役;旨在开放心灵,却导致心灵的大封闭。至于审美相对主义,则是审美教育的致命杀手,使得审美教育变得不再可能。相对主义要成就开放心灵,而不走向反面,恰恰必须为学界颇为流行的解构设限。
关键词:
相对主义;绝对主义;解构;趣味;审美教育;开放心灵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5-0042-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5.07
對于美的相对性的体认,几乎跟对美的哲学思考一样古老。无论是古希腊所谓“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1],还是中国先秦的“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庄子·齐物论》),似乎都在约略暗示,美丑之分,与个体、阶级、文化、时代密切相关,并没有关于美的普遍标准(universal criteria of beauty)。“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审美风尚,此日为美,彼日则丑,美丑之分,乃相对而非绝对。此等体认,一旦上升为哲学思想,就是审美相对主义(Aesthetic relativism)。
在“什么都行”(Whatever Works)的后现代,“趣味无争辩”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之类的相对主义,便会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学的默认原则。然而,当相对主义成为一个原则,显得有些绝对之时,我们是否要问:“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本身,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罗素曾不无苦涩地说:“尽管我不知道如何去拒斥对于伦理价值主观性(subjectivity)的论证,但我发现自己不能相信,荒淫残暴的所有错处就是我不喜爱它。”[2]假如罗素并非无理取闹,那么我们也就应当问自己:相对主义推至极致,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视相对主义为“自明真理”,视解构形而上学为“政治正确”,视绝对主义为嘲笑靶子,是否有条件反射式思维之嫌?换言之,“解构”是否其限度?当然,在考察这些问题之前,先说说相对主义的贡献。
一、审美相对主义与人的解放
相对主义大行于世,与绝对主义(Absolutism)声名欠佳有关。每一个时代所高悬的审美理想(The ideal),到头来,往往会成为昨日黄花。西施之颦,一旦奉为理想,争相仿效,只能徒增笑柄。更有甚者,“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高悬的审美理想,往往会成为一种压迫,成为对人的奴役。当代女性主义者娜奥米·沃尔芙(Naomi Wolf)的《美的神话》一书,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一点。
沃尔芙说,长时间的静默之后,女性最终在1970年代走上街头。经过20年的激进活动,西方女性终于推翻了关于她们社会角色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获得了法律、生育、教育、就业方面的一些权益。然而,看似解放的女性,依然处于奴役之中。这种奴役并非来自政治,而是来自审美,或者说来自“美的神话”(The beauty myth,其实译为“美的迷思”更好,这样才不至于辱没远古神话):
美的神话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种称之为“美”的品质,客观且普遍地存在着。女人必须去体现它,男人必须去拥有体现着“美”的女人。这种体现(embodiment)对女人是一种律令(imperative),对男人则否。[3]
美的律令,逼迫着女人去养颜美体,瘦身整容,追求时尚与完美。沃尔芙告诉我们,在她的书1992年初版之后,她收到无数来信,都在诉说着“美的神话”的压迫:无论黑人白人,她们打小就知道,审美理想(The ideal)必然是身材高挑苗条、皮肤白皙光洁、金发碧眼。而且她们都感到,自己并非如此。于是,无论年青还是年老,她们都充满对变老的恐惧;无论苗条还是肥胖,她们都为努力达到理想身材而忍受苦痛(suffering)。于是乎,即便是第一世界的富足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受束缚的女性,她们虽然享有前辈所从未享有的自由,却依然处于男性的压迫之中。沃尔芙的结论是:
美就像金本位一样是一种通货体系(currency system)。也和所有的经济现象一样受政治因素左右。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美是维持男性优势(male dominance)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套信仰。[3]沃尔芙的这个观察,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一语道尽:“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4]
美变成压迫,不但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艺术也概莫能外。一旦某些人或某些社会群体认为他们自己所把握的就是艺术或美的普遍标准,或者全社会公认有这么一个普遍标准,那么,艺术的厄运也就不远了。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指出,“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往往也是最不宽容的时代”[5],更何况艺术上最不伟大的时代。
解除美的律令的压迫,最便捷的武器就是相对主义。在相对主义眼中,那些看来具有普遍性的标准或理想,究其实乃特殊性,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并无那么大的权威。
二、审美相对主义与开放心灵
对于弱势群体,相对主义有助于解除压迫;对于强势群体,相对主义有助于促成包容。人天生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倾向,总倾向于以己度人以己度物。维柯所谓人类心灵的两条公理,揭示了这一点:
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做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6]82
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6]83
前一条涉及评价,后一条涉及认识。无论认识还是评价,人总是由近及远,借已知世界以解释未知世界。可以说,以己度人之“己”,往往是认识和评价的起点。然而,当人固守此一起点,不再由已知世界向未知世界迈步之时,这一起点也就同时成为终点,这样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里,以种族中心主义最为臭名昭著。像十字军东征、两次世界大战之类的历史劫难,其背后实有种族中心主义在作梗。日人今道友信指出,人类历史想要消除战争,任重道远,并不那么容易。这是因为,战争虽然有经济或政治方面的原因,但绝不限于此。假如战争仅仅出于这方面的原因,那么,“就有可能依靠经济调停和政策妥协而消除紧张关系,就可以避免整个世界卷入战争的悲剧”。然而,战争之因不限于此,战争背后最大的推手是种族中心主义:
如果各个国家把纠缠该国家的传统和思想视为绝对,几个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确信自己的优越的话,那么,就连本来不过是物欲上的争执,也会转化为以人类最为珍视的精神性的生命为赌注的争斗。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7]
无论哪种民族文化,都会视杀人为恶。然而,种族优越感却给了杀人者杀人的道德勇气,使得种族仇杀有了神圣光环。当此之时,即便杀人者深知自己难免被杀,但种族中心论往往会赠给他殉道者的声名。当此之时,战争就不仅仅是物欲争执了,而成了舍生取义的圣战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种族中心主义几乎无所不在,穿衣戴帽也不例外:
我们是如此倾向于把自己的文化习惯所允许的服饰行为假设为自然的和固有的(“男人当然要穿裤子!要不然他穿什么?”)。[8]
我们称外国人为“老外”,称自己听不懂的语言为“鸟语”,纳闷黑人为啥会长得那么黑——凡斯种种,也许隐隐约约地暗示出,即便是普通老百姓,其实打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倾向,认为自己民族才是正常,其他都异常。据说,在康尼博士(Doctor Kane)游历到密士海峡的爱斯基摩诸小部落的时候,土人们因发觉他们自己不是世界上仅有的人类,感到很是惊奇。[9]这种惊奇,对于部落这样的“封闭社会”来说,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反应。这种惊奇,一般会导致两种极端结果:一种是固执。虽然面前站着一个人,但仍然坚持认为本族是世界上仅有的人类。于是,这个不速之客要么被消灭,要么被称为“野人”,最好的待遇也不过是“化外之民”这一名称。这些不同结局中贯穿着一个共同认定,即只有本族才配得上“人”这个名称。这一认定,是种族中心论;另一个结果则是走出固陋,走出种族中心论。正视站在面前的这个不速之客,虽然和本族差异甚大甚至截然不同,但承认他跟本族一样,同属人类。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M. 蓝德曼曾这样界定种族中心论:
初民感到自己和动物非常密切,而他们绝非与他们的同类如此全面地保持同一性。甚至在埃及这样发达的文化中,作为人的特权只留作埃及人的专用。所有的外族人都不是人。这种现象叫作种族中心论。[10]与人禽之别比起来,种族差異实在算不得什么;同样,与本族之内的阶级差别来说,种族差异也似乎小了很多。种族中心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人即便与动物认同,也不愿与人认同。其中原由并不在于种族差异,而在于种族意识。人类学家艾·古曼(Alan Goodman)指出:“不同种族的差异其实并不大,是种族意识夸大了其间的差异。”[11]159种族差异一经种族意识夸大,那就终将免不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了。
文化相对主义的最大好处在于,有助于克服人类天生本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正视他者,尊重他者,理解他者,欣赏他者。
三、相对主义与人的沦落
然而,审美相对主义固然可以解除压迫、开放心灵,但假如推至极致,认为审美之事“趣味无争辩”,乃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则也不乏危险。美国大画家惠斯勒(Whistler)的这段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有位时髦贵妇对惠斯勒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惠斯勒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钱钟书对此事做了幽默而又深刻的引申,值得细读:
真的,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桩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12]概而言之,人之为人,就在于人能区分一己利害与客观是非,区分一己好恶和美丑善恶。“趣味无争辩”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式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之危险在于,将利害好恶混同于是非善恶,以己见为天理,以为自己喜欢的就是好的美的。这不是人的逻辑,而是兽的逻辑。
善恶不等于一己好恶,美丑也不仅仅是个人口味问题。审美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一样,推至极致,将使人类的价值世界分崩离析。
西南交通大学舒群教授曾自述其思想旅程说,宾克莱(Luther J. Binkley)的《理想的冲突》(Conflict of Ideals)一书,对他的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我看来这本书所披露的情况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文科学结束了。各种理想的冲突使理想的概念化为漂浮无据的论点,词语的开放使意识形态转变为CI、广告词和无意识习惯,任何道德律令不过是个人为自己选择的游戏和CI而已,没有什么绝对性。[13]185
既然没有什么价值是绝对的,任何道德律令只不过是情调,只不过是游戏,只不过是所谓CI(企业标识),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言,那么,所谓守望所谓坚持所谓铁肩担道义,统统都显得愚不可及。舒群教授说,他由此彻悟,获得新生。1996年初,他以在“语词的海洋里已彻底浮出水面”的自信投入新生活。所谓“新生活”的定义就是:“像出租司机那样,哪里叫唤,就奔向哪里!”[13]186
笔者不禁纳闷:假如上帝和魔鬼同时召唤呢?当然,极端相对主义者会说,根本没有所谓上帝和魔鬼。然而,假如是希特勒召唤呢?这种彻悟,是否是另一种更可怕的迷途?这种新生活,是否也会制造人间地狱?假如相对主义者忘记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观点”的存在,那么,以人生解放和文化包容为职志的相对主义,将不免导致人的沦落。
四、审美相对主义杀死审美教育
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 H. Gombrich),显然没有舒群教授那么乐观。他说:“文化相对主义哲学的过分流行只能导致人文科学的崩溃。”[14]6假如所谓人文学科还有所谓守护人类精神家园之类的使命,那么相对主义的流行,就远远不是什么福音,而是披着“解放”外衣的死讯;假如美学还算是人文学科的话,那么,审美相对主义也许就是美学的内部敌人。
台湾学者汉宝德指出,审美相对主义之流行几乎会判审美教育的死刑。因为,假如人人都以为自己有自己的审美标准,那还要审美教育干什么?[15]
休谟承认“趣味无争辩”是常识,但他也提醒我们,还有与之截然对立的另外一个常识:
谁要硬是说奥基尔比和密尔顿、本扬和艾迪生在天才和优雅方面完全均等,人们就一定会认为他是在大发谬论,把丘垤说成和山陵一样高,把池沼说成和海洋一样广。即使真有人偏嗜前两位作家,他们的“趣味”也不会得到重视;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宣称,像那样打着批评家招牌的人的感受是荒唐而不值一笑的。遇到这种场合,我们就把“趣味天生平等”的原則丢在脑后了;如果相互比较的事物原来近乎平等,我们还可以承认那条原则;当其中的差距是如此巨大的时候,它就成为不负责任的怪论,甚至显而易见的胡说了。[16]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趣味无争辩”,可以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我们必须承认趣味(taste)有高下之分:“‘趣味通常意味着良好或糟糕。”[17]
美国学者特德·科恩(Ted Cohen)指出,趣味这一概念,无论在日常用法还是在哲学用法中,主要有两个含义:
一方面,它使人想到一种对于较好事物的偏好,如“他的音乐趣味无可挑剔”;一方面,它还暗示出一种区分各种细节、将它们一一辨别出来的能力,如“他对酒的趣味可靠无误,总能鉴别出产地和年份”。[18]
前者系个人爱好,后者系品鉴能力。前者有高下之分,后者有精粗之别。所谓趣味无争辩,只有在你喜欢李白我钟爱杜甫的意义上有效。假如我喜欢吸毒你喜欢祈祷,我了无所见无动于衷你却见微知著了然于心,我此时再说趣味无争辩,就不只是有些过分了。
克尔凯郭尔曾描述他听莫扎特音乐的体验:
初闻莫扎特的音乐,我的心中便充满惊喜,对它钦佩有加,顶礼膜拜。从那一刻起,我就一直以一种亲切与感激之情沉思着这样一个问题:古希腊乐观的世界观称这个世界为cosmos(完整、和谐的系统——译者注),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精神运行其中穿行其内的透明而有趣的装饰体。[19]1
这种体验令人不由想起《礼记·乐记》所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伟大音乐的感染力,会使人领会宇宙秩序。精细之趣味(refined taste),会领悟到伟大音乐之伟大。假如我们可以将审美教育分为善感、趣味、境界三个阶梯,认为审美教育之任务就是“保护并培养人的敏锐感受,成就高尚趣味,追求阔大的心灵境界”[20],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极端相对主义与审美教育格格不入。因为,只有承认感有利钝、趣有高下、境有大小,审美教育才有必要和可能,而极端相对主义者并不承认这一点。对极端相对主义者来说,“幸福来自偶然,荷马、莫扎特之英名来自机会”。这种想法对平庸之辈的确是莫大慰藉,因为它可以促使他们相信,他们之所以不能与荷马或莫扎特齐肩,“只是命运错点了鸳鸯谱,是世界犯的错误”[19]1。
贡布里希说,从“一个价值系统与任何一个别的价值系统优劣相当,一幅宋代绘画的杰作和一张明信片也不分轩轾”这种纯粹的相对主义出发,既无法书写艺术史,也无法书写文明史。[14]2假如连艺术史、文明史都无法书写,又如何从事审美教育?
五、相对主义的两个版本
艾伦·布鲁姆(Allen Broom)在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在美国大学生中间,相对主义可以说是天经地义。倘若你提醒他们说,这并非不证自明还须仔细思量,“这会让他大为惊讶,就像要求他对2+2=4提出质疑一样”[21]1。
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那是因为,基础教育将“相对主义”当作唯一的美德(virtue)来灌输。学校教学生对绝对主义的危险保持警惕,不是因为其谬误(error),而是怕不宽容(intolerance)。于是在美国大学生中间,“真理的相对性不是一种理论观点(theoretical insight),而是一种道德要求(moral postulate)”[21]1。
布鲁姆承认,相对主义是“开放”(openness)的必要条件。但是,假如相对主义变得不可问询,以一种“绝对”面孔出现的时候,它带来的并非开放,而是封闭。因为假如真理是相对的,那么,人必然会失去追求真理的热情。既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又何必去古圣昔贤或异域哲人那里去聆听教诲。心灵大开放往往带来心灵的大封闭,因为这样的开放“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别人”,它带来的是固步自封:“相对主义泯灭了教育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原动力。美国年轻人对外国的了解和兴趣越来越少。”[22]9
正因为大开放会导致大封闭,布鲁姆区分了两种开放:
一种是冷漠的开放(the openness of indifference),它受到双重意图的推动:贬抑自己的知识自豪感;使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任何人——既然我们不想成为求知者。
另一种开放则鼓励我们探索知识和确定性,历史和各种文化为此提供了有待审察的各种辉煌范例。这种开放激励着探索的欲望,它使每一个严肃的学生生气勃勃,兴致盎然——“我要搞清楚什么对我是好的,什么能让我幸福”,而前一种开放则阻滞了这种欲望。[22]9
前一种开放是“无所谓”,后一种开放则是“有所求”;前者扼杀求知欲望,后者点燃求知欲望;前者冷漠,后者热诚。相对主义者,关心人类福祉的相对主义者,定然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
事实上,与两种开放相对应,相对主义也有两个版本。借用休谟的表述来说,一个就是“趣味无争辩”“趣味天生平等”;一个则是既承认“趣味无争辩”,又承认趣味有高下精粗之别。前者可称为激进(radical)相对主义,后者可称为温和(moderate)相对主义。前一版本的相对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所有价值都无道理可言,是非对错全视情况而定,并无理性依据。后一版本的相对主义承认价值的相对性,但并不认为它们是“单纯不合理的任意的狂想”;它承认道德差异,但这意味着我们更应当理性地选择生活方式:
根据这种解释,认为各种道德评价都和我们的历史时代以及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文化有关,并不是要贬抑各种道德,反倒是想帮助我们制定一些条理清楚首尾一贯的基本原则,以指导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的行动。[23]13
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前者称为非理性的(irrational)相对主义,将后者称为理性的(rational)相对主义;或者称前者为冷漠的(indifferent)、放任的(laissez-faire)相对主义,称后者为热诚的(sincerely)、严肃的(serious)相对主义。
真的有些怀疑,声称《理想的冲突》一书改变其人生观的舒群教授,是否曾将此书导言部分认真看完。因为正是此书作者宾克莱,区分了相对主义这两个版本。在宾克莱看来,流行的相对主义往往成了人放任自流的借口:
既然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如果我以不同于你的方式去“得到快乐”,那你就没有权利反对我的行为。这样,“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就常常被用来为不管什么样的行为作感情辩护。[23]10
作者所心仪的相对主义,则是寻求美好生活的那种:
关于道德理论中的相对主义不会将人们引入绝望和荒唐的境地;相反,它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它要求每个人作严肃认真的努力去选择他认为对于他个人、对全社会都是最有意义的那些价值。[23]18
这两种相对主义之别,借用套话来说,分别反映着两类“无知”:一种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的无知,另一种则是“苏格拉底式的无知”;前一种无知不再求知,后一种无知启发真知。
美国学者罗伯特·C.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说:“自康德之后,欧洲哲学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斗争的故事。”[24]哲学史也许能隐约说明,相对主义虽然占据现代哲学之主导地位,那也是给绝对主义留有辩驳余地的相对主义,而不是流行的那种以“绝对主义”面孔出现的无可辩驳的相对主义。
六、解构及其限度
20世纪,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时代。[23]6至今,斯风犹炽,甚至愈吹愈烈。中国亦不例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前几年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抽样调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个问题:“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许纪霖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核心价值的危机。”[25]许先生将此相对主义盛行之因归结为“价值实用主义”。就国民整体或时代环境而言,此解释可谓探本之言;然而就知识人而论,尤其是为相对主义推波助澜的知识人而言,此解释又略显不足。
相对主义之理论资源,多之又多。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以及行为主义心理学“似乎”为相对主义提供了科学基础。
上世纪20年代,仍有人主张女性以及某些种族、階级天生低等。为反对这种论调,故有文化相对论的兴起。文化相对论尤其盛行于美国,他们提出行为主义的证据,宣称后天环境的奖惩可以大幅改变人的行为。行为主义之父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说:“给我12个健康的婴儿,用我的方式教养他们,我保证可以随意挑选任何一个婴儿训练成任何一种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当然也可以是乞丐、小偷,不论他的才能、性向、志愿、种族。”参见〔美〕南茜·艾科夫:《美之为物》,张美惠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页。至于历史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则给相对主义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甚至有论者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文化相对主义之张本,言说连时空都是相对的,更何况文化,何况价值。
文化相对主义的确跟爱因斯坦相对论扯不上丁点关系,就像曾有前贤借进化论以论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人类社会之通则一样,此等论证不只一种理论天真,更是对科学之无知。就中国学界而言,知识界所流行的相对主义最为直接的理论支持,可能就是90年代引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入驻中土,基本上没有遭遇强敌,很快就在理论界形成了另外一种“政治正确”。这个理论界当然包括美学界,而且有可能首先是美学界。因为引进后现代热潮之主将,大多美学或文艺学专业。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精英立场之类的大帽子,解构、颠覆、狂欢、去经典化、告别崇高等流行策略,约略可以暗示出,后现代话语在中土,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学术政治话语,而且政治的成分要多一些。
当一种哲学话语或立场或姿态变成一种政治正确之时,正是我等需要警惕之时,因为当此之时,它早已成为教条。即便是旨在“解放”的哲学话语也不例外。而且历史经验似乎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正是那些热衷解放的哲学话语,一旦成为教条,将会带来更大的思想禁锢。“解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解放”话语。
加拿大学者笛文·邦尼卡斯尔提醒我们:“除非你受到压制,否则你不需要解构主义。”[26]88换句话说,你可以将“解构”当作一种策略来反抗压迫,但当你将它当作一种“主义”,一种政治正确的“主义”,那就跟“造反有理”差不多了。因为,deconstruct(解构)一词源自德语的abbauen,意思是“拆开”或“拆毁建筑物”[26]88。
毛崇杰先生指出:“解构主义在欧洲遭到的最大争议是它与虚无主义的关系。”[27]解构之所以和虚无主义扯上暧昧关系,也许正与学人想在解构主义里面寻找一套价值观和生活哲学有关:
你可以运用解构主义来颠覆压制你的权威,但是如果你想到解构主义者那里去找一套价值观或一种生活的哲学,那你就进入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和唯我论的世界——一个实质上每个人都是孤立,无法相互沟通,社会群体因没有和谐而瓦解的世界。[26]91
遗憾的是,在学术会议上,许多学者口中的“解构形而上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类学术口号,不但成了心照不宣的学术政治正确,有时候还仿佛义正辞严。
王乾坤先生曾谆谆告诫,当我们忙于喊这类学术口号时,总得先知道“逻各斯”和“形而上学”是什么吧,否则,我们就是“先自以为是地对其做经验化处理,然后打倒这些‘稻草人”。[28]要知道,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嘲笑柏拉图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没读过或读不懂的人,更没资格。至于那些正因读不懂就瞧不起柏拉图的人,当然就用不着说资格不资格,充其量只能呵呵了。
七、美的多样性与矛盾性
卡尔·波普尔曾说:“相对主义是知识分子犯下的许多罪行之一。这是对理性和人性的背叛。”[29]这话听起来虽有些刺耳,但是,当相对主义以自明真理的姿态出现的时候,此语的确是探本之言。
就美学而论,之所以是对人性的背叛,那是因为“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是因为“孩童深受美的吸引”[11]37,因为“人对美的反应是自发的、无法抗拒的,美的经验很早就开始,而且深植心中”[11]45。
之所以是对理性的背叛,借用美籍俄裔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的话说,是因为相对主义混淆了“多样性”与“矛盾性”:
审美观的分歧证明的不是美的现象是相对的,是对立冲突的,而是证明美的体
现形式是多样的,正如社会文化“相对主义者”的解释那样。一个人能同时欣赏不同种类的玫瑰、杜鹃花、苍穹或暴风雨的海洋、贝多芬和巴赫,并不证明美感、审美和美的事物互不相容,那只是显示了美的丰富多样性。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不是美的相对性和矛盾性。“相对主义者”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属性:美的多样性(在多样但平等的美中,没有敌意、矛盾和冲突)和虚无的、相互排斥的矛盾性。[30]换言之,审美观的分歧这一事实,证明的应当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而不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它所要求于我们的,应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1990年,费孝通在日本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的演讲。会议结束时,他写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题词。,应是学着去欣赏他者(the other)的美,欣赏其他时代其他地域其他文化的美。假如审美观的分歧,证明的只是各人有各人的审美观,只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么,“各美其美”,就成了我们的宿命。因为,既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么,我又如何能够“美人之美”;既然“什么都行”,我又何必“美人之美”。相对主义,或者再严格一点,以“绝对”面孔出现的相对主义,之所以看似包容实则褊狭,看似开放实则封闭,原因就在于此。
贡布里希曾说:“我们能从科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包括从真正的社会科学那里学到的东西,不是相对主义,而是虚怀若谷。”[14]272假如美的多样性并不等于美的矛盾性,假如审美相对主义的确有滑向“各美其美”式自我封闭的危险,那么贡布里希的这句话,可以说,就是对美学研究者的有益提醒。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相对主义大行其道,甚至泛滥成灾。
八、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诸君读到这里,假如拙文还有些看头的話,想必也约略看到,相对主义虽颇流行,甚至被知识界引为“政治正确”,却并非百分之百的结实可靠;绝对主义虽声名欠佳,甚至“政治不正确”,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要不得。
话说到这份上,不谈谈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到底孰是孰非,似乎说不过去。因为就此打住,拙文就好像只是各打五十大板,接着就装好人和稀泥,两头都不得罪。
窃以为,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完全不必势同水火,你死我活。
因为有时候,根本用不着这两个大词。比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面对品类繁盛、姿态万千、活泼热烈的大自然,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这两个词似乎都用不上。即便你非得要用相对主义一词,那你也必须注意,这异彩纷呈的“美”,只是“美”的万象,其背后有一个绝对:“天地之大德曰生”。同理,“君子和而不同”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来形容,也总是扞格不入。因为君子,只要是遵道而行的君子,势必是姿态万千;一树繁花,无论怎样的异彩纷呈,总有一条根。C. S. 路易斯曾说,世俗之徒总是千人一面,圣徒则是姿态万千。[31]圣徒之姿态万千,背后或上面或里面,有个“道”,有个“神”。
假如上面这些不是胡说,那我们也大概能体会到,审美绝对主义之所以沦为压迫,乃是有些非绝对之物僭居绝对之位。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所树立的“审美理想”,就相当于将一朵花或一种花的颜色气味姿态树为标准,要其他的花朵都照着这个样子开。这类僭越的结果,当然是“我花开尽百花杀”。
而审美相对主义之所以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之虞,乃是因为非绝对之物干脆不承认自己背后有个绝对,就相当于每一朵花都要自本自根,每个人都孜孜于活出个性。人孜孜于活出个性,到头来肯定是千人一面,纷乱得近于乏味;花朵坚持着自本自根,坚持着自我实现,大概很快就会凋谢枯萎。
借用《朱子语类》卷二十七反复叮咛的“一本万殊”之理来说,假如我们非要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二词,此二词也不在一个层面,争不起来。因为绝对的是“一本”,相对的是“万殊”。
现代知识将杀死上帝视为了不起的解放,当然就根本不会承认这个“一本”,于是绝对主义和相對主义不仅势同水火,而且殊途同归——二者都会导致美的死亡,只不过杀法不同而已。前者是“我花开尽百花杀”,后者则是让“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
说到这里,大概又牵涉到古今之变这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问题——虽然汉语学界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问题小得不能再小,根本不是问题——拙文也该就此打住了。结束之前,再引用一下C. S. 路易斯的一句话,对我们思考现代哲学中的绝对与相对之争,或许有所裨益:
关于非终极问题,一颗开放心灵是有益的(useful);关于理论理性或实践理性之根基(ultimate foundation),一颗开放的心灵就是白痴。[32]
诸君想必还记得,前文曾区分两个版本的相对主义,也曾区分两种“开放”——那种旨在解放却最终完成人的奴役的相对主义,对应于后一种开放;至于那种不会将美的多样性混同于没的相对性的相对主义,则对应于前一种开放。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7:27.
[2]BERTRAND R. Notes on Philosophy[J]. Philosophy, 1960(35): 146-7.
[3]NAOMI W. 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2:12.
[4]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4.
[5]乔治·桑塔耶纳.美感[M].缪灵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9.
[6]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7]今道友信.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M].李心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7.
[8]玛里琳·霍恩.服饰:人的第二皮肤[M].乐竟泓,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67.
[9]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3.
[10]M·蓝德曼.哲学人类学[M].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0.
[11]南茜·艾科夫.美之为物[M].张美惠,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12]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M].北京:三联书店,2002:50-51.
[13]李泽厚,吕澎,赵士林.自然说话[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14]E.H.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M].范景中,曹意强,周书田,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中文版导言.
[15]汉宝德.美学漫步[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111-113.
[16]休谟.论趣味的标准[M].吴兴华,译.古典文艺理论译丛[A](第5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4.
[17]达布尼·汤森德.美学导论[M].王柯平,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
[18]彼得·基维.美学指南[M].彭锋,等,译.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1.
[19][丹麦]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M].封宗信,等,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20]邓军海.美育三阶:善感、趣味与境界[N].光明日报,2010-3-16(理论版).
[21]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2]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导言:我们的美德[M].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3]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马元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4]罗伯特·所罗门.哲学导论:综合原典阅读教程[M].陈高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215.
[25]许纪霖.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J].信睿,2012(12)
[26]史笛文·邦尼卡斯尔.寻找权威:文学理论概论[M].王晓群,王丽莉,译.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27]毛崇杰.走出后现代[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186.
[28]王乾坤.文学的承诺[M].北京:三联书店,2005:14.
[29]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范景中,李本正,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4.
[30]皮蒂里姆·A. 索罗金.爱之道与爱之力:道德转变的类型、因素与技术[M].陈雪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34.
[31]路易斯·C S. 荣耀之重[M].邓军海,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95.
[32]路易斯·C. S.人之废[M].邓军海,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2.
(责任编辑:方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