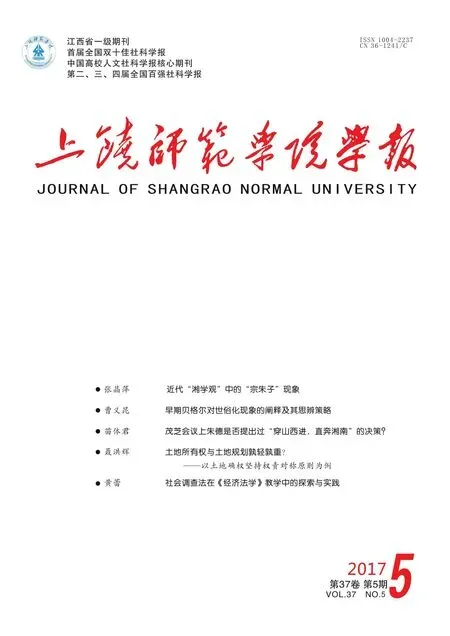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若干问题研究
2017-04-14郑旭
郑 旭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若干问题研究
郑 旭1,2
(1.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401120;2.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重庆400025)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对于金融机构有无犯罪主体资格、是否需要特定犯罪目的、扰乱金融秩序如何理解、社会公众的界定和判断以及集资参与人的法律地位等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通过结合典型案例进行理论分析可知:金融机构具有犯罪主体资格;本罪是目的犯、结果犯;社会公众可以界定为30人以上的不特定对象;集资参与人不是刑事被害人。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有其特殊性,惩处和预防犯罪均值得关切,对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要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注重通过惩处犯罪来减少非法集资犯罪行为的效果。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金融机构;金融秩序;社会公众;集资参与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商业银行法》首次提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同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施行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后被1997年修订的《刑法》所吸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个特征条件,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及社会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3月25日施行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社会公众的认定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然而,无论是理论界人士,还是司法人员,由于所持理念、所站立场不同,加之相关规定本身所固有的缺陷等原因,人们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集资参与人的法律地位等问题持有不同观点,实践中的司法判决亦不统一。由此,本文将对金融机构的主体资格、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扰乱金融秩序的理解、社会公众的界定和判断以及集资参与人的法律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金融机构的犯罪主体资格问题
我国刑法学界曾经针对单位能否构成犯罪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这种争论以立法确认单位犯罪而有所平息,但并未终结。有学者认为,单位犯罪指单位的代表人、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员,经单位决策机关或负责人员决定,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1]235。根据《刑法》第176条第2款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即单位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未经批准,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自然人或单位,如地下钱庄、会社、公司企业等,向社会公众开展吸收存款业务;二是经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虽然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法定主体资格,但为提高收益和市场竞争力,以擅自提高利率等违反《商业银行法》等法律规定的手段吸收公众存款。对于后一种情况,金融机构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说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理论界存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肯定论者认为,相关法律规定并未把有吸收公众存款主体资格的金融机构采用提高利率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公众存款排除在本罪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方式之外[2]。否定论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种法定犯,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都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应该对《刑法》第176条第2款中所说的“单位”进行限制性解释[3]。折中论者认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擅自采用提高利率的违法方式吸收存款的情况,《商业银行法》已具体规定了行政处罚,一般不宜作为犯罪处理[4]。
笔者认为,金融机构可以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主要理由是:第一,《刑法》第176条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本罪,金融机构也是单位,没有超出刑法中“单位”含义的文义射程,而且也没有例外规定将金融机构排除在本罪的犯罪主体外。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单位犯罪主体进行限制解释,没有根据。第二,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以提高利率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情形,2015年修正的《商业银行法》第74条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的同时,还规定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也是金融机构成为该罪犯罪主体的法律依据。第三,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种危害性表现在金融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导致金融市场秩序的混乱,且阻碍国家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实现货币总量供求平衡的政策)功能发挥上的危害性,不比非金融机构小[5]。现实生活中,与非金融机构相比,人民群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赖程度更高。金融机构以违法擅自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公众存款,人民群众也不易辨别其非法性,更容易积极参与集资。
综上所述,在现行《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情况下,通过限制解释等方式否认金融机构的犯罪主体资格,或者一般不宜作为犯罪处理的观点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相关观点不具有法律依据,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二是违背了刑法适用平等原则。从刑法适用平等原则考量,如果将金融机构之外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对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却不认定为犯罪或不作为犯罪处理,不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资格,否定论和折中论的观点值得商榷。
二、本罪是否为目的犯
“目的犯”这一概念由德国刑法学者首先提出,是指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的特定目的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是“有目标地追求”符合行为构成的结果[6]。特定目的,不是指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而是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之外的,对某种结果、利益、状态、行为等的内在意向;从目的与刑法规定的关系来看,目的犯中的目的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目的;二是刑法分则虽无明文规定,但根据条文对构成要件的表述以及条文之间的关系,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目的[7]275。
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人将所吸收的资金用于多个方面,如用于发放贷款、投资理财、个人消费等。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人因生产经营缺少资金而吸收存款,并将所吸收的资金真实用于生产经营的案件大量存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解决融资需求。行为人基于不同的目的吸收资金,其主观目的是否影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换言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具备行为人特定的主观目的,即本罪是否为目的犯。从《刑法》第176条规定的字面意义上看,看不出本罪的成立需要具备特定目的。不过,行为人所非法吸收资金的去向,确实反映了其实施非法吸收存款时的主观目的。对于本罪是否为目的犯,理论界存在两种对立观点。否定论者认为,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并不将所吸收的存款用于信贷,而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也构成本罪[8]。也就是说,不管行为人将吸收的资金如何使用,无论是用于货币经营等金融业务,还是用于正常的企业生产、经营,甚至个人挥霍消费,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肯定论者认为,只有当行为人将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用于进行货币经营时(如发放贷款),才能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才应以本罪论处[7]687。换言之,即使行为人未经金融管理机构批准,实施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但并未将吸收的资金用于货币经营等金融业务,而是用于其他方面,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反映出其没有经营金融业务的主观目的,不具有违法性,其行为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理论界的观点不同的是,最高司法机关采取了折中态度,即符合《解释》规定情形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
笔者认为,将本罪理解为目的犯,比较适宜。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渊源及其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犯罪分类不难看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之所以犯罪化,根本原因在于该行为侵犯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主要区别在于金融业主要是专门经营货币、资本业务,其吸收公众存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进行货币的经营,因此,只有将吸收的资金用于资本经营或货币融资等行为,才可能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司法解释采取的折中态度,不仅有结果责任之嫌,而且容易导致司法裁判的随意性。实践中,司法机关基于从严惩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立场,无视所吸收资金用途之差异,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将吸收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人判处刑罚的案件大量存在,这不但有悖于立法目的,也不利于民间融资市场的发展。因此,建议立法机关明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以经营资本和货币为目的的犯罪,将吸收的资金用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等,则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不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亦能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化预留空间。
三、本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刑法中的“结果”是指行为所引起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结果。根据结果在刑法中的不同作用,可以分为“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作为加重情节的结果”和“作为处罚条件的结果”。如果缺乏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犯罪构成就不完整[9]。行为犯和结果犯之分就是国外刑法理论从结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作用上对犯罪作出的两种分类,构成要件中只规定了行为内容的犯罪为行为犯,构成要件中规定了结果内容的就是结果犯。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直接规定犯罪既遂的概念,更没有规定什么是行为犯或结果犯。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学者们通常是在讨论犯罪既遂的标准时来区分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如我国有学者认为,行为犯指以法定的犯罪行为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这类犯罪的既遂并不要求造成物质性的和有形的犯罪结果,而是以行为完成为标志;结果犯,不仅要实施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即以法定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与否,作为犯罪既遂与未遂区别的犯罪[1]287。
具体到本文所研究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刑法》第176条的规定,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没有原则性争议。但是,在本罪的犯罪既遂标志上,是实施了法定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还是不仅实施法定行为,同时还要求发生法定危害结果,即本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的问题上,不仅理论界分歧较大,而且也是实践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亦是案件处理过程中法律适用的难点所在,确有必要予以探讨。对此问题,一种观点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行为犯,“扰乱金融秩序”仅仅是对行为属性的描述,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符合《刑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的,就违反了我国的金融管理制度,扰乱了金融秩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且是犯罪既遂。另一种观点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结果犯,只有造成了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的结果才构成犯罪[10]。
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结果犯。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从《刑法》第176条的条文看,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之后表述“扰乱金融秩序”,是对行为结果的描述。否则,如果“扰乱金融秩序”是行为属性,则有重复表述之嫌,不符合成文法的简洁性要求。第二,从本罪法定刑的设置看,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罚,这属于结果的范畴,与此对应,作为第一档法定刑的适用条件“扰乱金融秩序的”,无疑亦属于结果之范畴。第三,从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看,追究本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标准中,对犯罪数额、吸存对象人数、损失数额、影响程度和后果的列举,也能够表明本罪是结果犯。最后,从司法效果上看,将本罪理解为行为犯,会将一些没有造成金融秩序混乱或者使金融秩序陷入混乱危险的行为纳入犯罪圈,造成不当扩大惩处范围,不仅不利于企业或个人的融资需求,更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相悖。因此,“扰乱金融秩序”是对行为危害结果的概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既遂的标志是危害结果的发生。需要说明的是,法定危害结果不仅仅是指客观、有形、物质性的损害结果,还包括侵害结果和危险结果。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结果是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所造成的现实侵害事实与现实危险状态[7]166。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结果,既可以是现实的、有形的,也可以是危险性的、无形的。也就是说,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不一定现实地造成金融秩序混乱的有形结果,也包括给金融秩序造成无形的危险状态。比如,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几十万元,并不必然现实地扰乱金融秩序,但可能会给金融秩序造成混乱这一危险状态,所以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四、社会公众的界定和判断
根据《解释》第1条的规定,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要件之一,但《解释》并未明确界定何为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的判断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认识分歧,理论界对此也是莫衷一是。《解释》起草人员对社会公众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两个具体判断标准:“社会性是非法集资的本质特征,指向社会公众即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判断:一是集资参与人的抗风险能力。法律干预非法集资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公众缺乏投资知识,集资对象是否特定,应当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判断;二是集资行为的社会辐射力。”[11]在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相关问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起草人员的解释说明更值得信赖,甚至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当然,起草人员的解释说明能够帮助司法人员理解规定,方便案件裁判,具有一定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起草人员观点是否合理,论据是否充分,司法分歧是否实际消解,仍需考察探讨。
笔者认可起草人员对社会性特征内容的理解及社会辐射力的判断标准,但对其提出的以集资参与人的抗风险能力为基础进行分析判断集资对象是否特定的观点,不甚赞同。原因有二:一是立论原因有待商榷。起草人员认为法律干预非法集资的主要理由是不能完全成立的,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多数观点认为动用刑法规制非法集资的主要原因是非法集资行为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正如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所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非任意行为,须有国家有关部门作出规定予以限制。否则,势必造成金融秩序的紊乱。”[12]可见,法律干预非法集资的主要理由并不是起草人员所阐释的那样。二是该标准的可操作性不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往往涉案集资参与人众多,甚至有的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发案,集资参与人更是不计其数,如何判断社会公众是否缺乏投资知识及承受损失风险的能力,本身就是一个难题,通过这个标准判断集资对象是否特定,着实令司法人员为难。况且,国家相关部门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非法集资的行为方式、危害性,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的社会环境下,甚至在行为人非法集资初期,相关部门介入并予以处理时,一些集资参与人还百般阻挠。如果仍然认为社会公众缺乏投资知识,与常识、常情、常理难以相符。相反,集资参与人为追逐行为人所宣传的高额回报,即使发现有投资风险,也会置之不理,积极参与集资行为。正如有学者所言,此时,他们往往将理性投资的意识抛之脑后,甘冒风险,积极配合集资人进行非法集资活动[13]。因此,将集资参与人的抗风险能力作为判断社会公众的判断标准,并不可取。
通过考察司法案例,《解释》《意见》的出台,以及起草人员的解释说明,并未能消解司法判决不统一的现象。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些司法机关仅从自然属性方面认定社会公众,认为吸收存款的对象3人以上,就是社会公众。第二,在既向单位内部职工又向社会上的人吸收存款时,司法机关对单位内部职工是否认定为社会公众,做法不同。第三,在“中间人”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社会公众认定不同。
笔者认为,要消除分歧,防止不同法院之间相互抵牾的判决,应合理界定和理解社会公众的内容与判断标准。实际上,社会公众具有两个属性,“公众”具有定量的属性,即多数人;“社会”具有定性的属性,即不特定性。因此,建议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来界定和判断社会公众。
首先,虽然不能仅将集资对象的多寡作为判断社会公众的唯一标准,但是人数标准是社会公众最直接的反映,如果人数不多,就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认定是否为社会公众。《解释》第3条第1款第2项为我们界定社会公众提供了参照标准。该款规定: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公众”的人数划定为30人以上,具有法律依据。其次,社会公众还须具有不特定性,至于不特定性的判断,笔者认为前述司法解释起草人员的观点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可资借鉴。
五、集资参与人的法律地位问题
自从我国《刑法》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来,案件中的集资参与人是否属于刑事被害人,素有争议。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有的认定其为被害人,判决行为人赔偿集资参与人的损失;有的判决书没有认定其为被害人,但仍判决行为人赔偿其损失;有的判决书对此不予评判。理论界对此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集资参与人不是刑事被害人。从立法意图上看,集资参与人不是刑法保护的对象;集资参与人不具有被害人地位的正当性;将集资参与人作为被害人,会带来多方面的副作用[14]。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集资参与人是被害人。从立法发展、指导案例、犯罪客体以及司法效果来看,存款人不享有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的观点,忽略存款人财产权益受损的事实、剥夺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15]。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认为,应分两种情况确定集资参与人的地位:一是被非法吸收的存款及利息已被提取的集资参与人不能认定为被害人;二是明知对方吸收存款的行为是非法的,为了获取高额利息等非法利益,还存款于该非法吸收存款者处,构成“参与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因而他们同样不能作为被害人,否则,如果不明知且利益受到损害时,属于被害人[16]。
集资参与人的法律地位问题关涉案件的实体处理和程序选择,如不能统一认识,司法混乱状况始终不能消除,司法权威也会受到质疑,所以,立法机关不应回避这一问题,交给司法机关任由其处理,对此予以明文规定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在立法、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未作任何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的集资参与人不具有刑事被害人身份。
首先,从立法意旨上看,我国《刑法》之所以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侵害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不是非集资参与人的财产权所有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人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离不开非法集资参与人的参与,就像传销参加者一样,集资参与人的行为同样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其次,从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表述看,《解释》表述为存款对象或存款人,《意见》表述为集资参与人,两个文件均未表述为被害人。可见,最高司法机关、公安部等部门没有认可集资参与人的被害人地位,否则,可以直接表述为被害人。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有两种处理方式,即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其中,责令退赔是指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然而,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涉案财物的处置问题上,《意见》也明确规定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应当依法追缴,包括支付给集资参与人的利息、回报等,并未规定责令退赔。追缴有回溯犯罪结果和收缴特殊财产的双重意思,可以将追缴理解为没收和追征[17]。这一规定也反映出集资参与人不享有刑事被害人的权利。
再次,非法集资参与人受趋利心理膨胀的影响,急于赚钱,丧失理性,是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数量爆发式增长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非法集资参与人参与集资活动,应当对自己行为及后果独立承担责任,愿赌服输。如果认定非法集资参与人是刑事被害人,则其具有赃款返还等权利,这是变相激励人民群众参与集资活动。欲从根本上有效规制非法集资犯罪行为,须变激励性规制为制裁性规制。充分发挥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活动的引导作用,使集资参与人回归理性,消除急于获利心理,否定集资参与人的刑事被害人地位,并没收、追缴行为人通过非法集资活动获得的资金,是有效之策。
最后,如果将集资参与人认定为刑事被害人,会增强刑法的负外部性。“外部性”是经济学中的概念,其含义是未在市场中进行交易而产生的额外成本或者收益。“外部性”有正、负之分。其中,“负外部性”是指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给其他人施加额外成本的外部性。“成本”与“收益”是“外部性”的经济学定义的主要角度,可以类比为法学中的“权利”与“义务”。借用经济学中“外部性”的概念,“刑法的正外部性”是指主体在行使权利时将其可由自己行使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且没有施加任何义务;“刑法的负外部性”是指主体在行使权利时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义务施加给其他主体。具体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而言,根据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作为集资参与人,都是基于追求经济利益而参与集资,其损失是由其自愿行为造成的,如果将其认定为被害人,通过法律手段、投入司法成本为其挽回损失,是让其他主体为其承担义务;如果集资参与人的损失无法挽回,则很有可能造成上访、闹访,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破坏社会秩序,给人们的工作、生活等造成不利影响。
故而,立法机关为消弭实践中的争议及不当做法,应明确集资参与人不具有刑事被害人地位。
六、结语
在非法集资行为多发易发、迅猛增长的现实背景下,刑法规制手段十分重要。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不能处于缺位、失灵状态,应当及时有效地为司法活动提供规则,消解司法混乱。围绕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一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积极献策,观点纷呈,为司法裁判提供了多种思路,对此,应予充分肯定。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有其特殊性,惩处和预防犯罪均十分值得关切,不能顾此失彼。对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要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注重通过惩处犯罪来减少非法集资犯罪行为的效果,唯有如此,刑法规制之目的方能实现。
[1]高铭暄.刑法专论[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35.
[2]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9.
[3]李希慧.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几个问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4):36-38.
[4]朗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M].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61.
[5]李永升.金融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169.
[6]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86.
[7]张明楷.刑法学[M].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75.
[8]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321-322.
[9]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陈忠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3.
[10]刘建.金融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330.
[11]刘为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11(5):25.
[12]周道鸾,张军,熊选国,等.刑法罪名精释[M].4版.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318.
[13]刘宪权.刑法严惩非法集资行为之反思[J].法商研究,2012(4):123.
[14]张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难点问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2):41-42.
[15]汤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存在被害人[N].检察日报,2015-08-12(3).
[16]石经海.如何确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的“存款人”的诉讼地位[J].人民检察,2003(4):50.
[17]王利荣,谢玲.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没收违法所得[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84.
Study on the Crime of Illegally Absorbing Public Deposits
ZHENG Xu1,2
(1.School of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2.People's Court of Jiangbei District,Chongqing,400025,China)
In terms of the crime of illegal deposits from the public,the need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have criminal subject qualification,or the specific criminal purpose,to way to understand disrupting financial order,the definition and judgement of the social public,and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fund-raising,in China's criminal law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all have long been controversial issues.Through analyzing theoretically and combining typical cases,people can learn tha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criminal subject;the crime is Absichtsdelikte and Erfolgsdelikte;the public can be defined as the non-specific object not more than 30;fund-raising participants are not criminal victims.Since the case of illegally absorbing deposits from the public has its particularity,punishment and prevention of crime are worthy of concern,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in the premise of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is supposed to focus on redu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llegal fund-raising by punishing crime.
crime of illegally absorbing public deposits;financial institutions;financial order;social public;fund raising participants
D914
A
1004-2237(2017)05-0072-07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5.012
2017-01-1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CFX023)
郑旭(1983-),男,河南柘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E-mail:justice2018@126.com
[责任编辑 许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