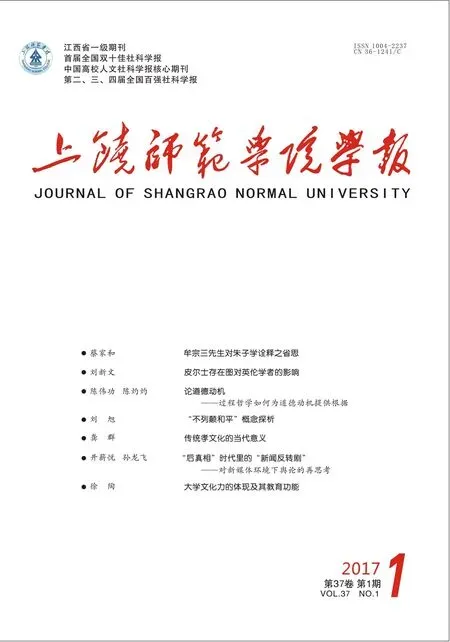鄱阳湖地区理学文化的五大特性
2017-04-13冯会明李豪
冯会明, 李豪
(上饶师范学院 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鄱阳湖地区理学文化的五大特性
冯会明, 李豪
(上饶师范学院 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鄱阳湖地区素有“理学渊薮”之称,理学文化是鄱阳湖地域文化的基本内核。鄱阳湖地区理学文化具有尊信程朱、捍卫道统的执着性,和会朱陆、兼容并蓄的融合性,砥砺节操、慕道安贫的理想性,实学经世、学贵践履的务实性,文节俱高、刚正义烈的忠诚性等五大特性。
鄱阳湖地区;理学;特征
江西尤其是鄱阳湖地区是理学开源之地,素有“理学渊薮”之称。“理学发源于江西,主要的学术研究在江西,最后定型于江西,又从江西为起点,传播于全国。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体系化,在江西这块土地上最后完成,这是江西对儒家思想丰富和发展所作的贡献。”[1]如果说江西是理学的“故乡”,那么鄱阳湖地区可称为理学的“摇篮”,是宋、元、明时代理学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
理学文化是鄱阳湖地域文化的基本内核。理学在鄱阳湖地区兴起、传衍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呈现出鲜明的特征,表现为捍卫道统的执着性、兼容并蓄的融合性、慕道安贫的理想性、学贵践履的务实性和刚正义烈的忠诚性等五大特性。他们尊信程朱,捍卫道统,以求道、卫道为己任,批判佛禅,驳斥老庄,论辩阳明,竭力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在学术上又和会朱、陆,兼采朱、陆之长,强调主敬存心;在修养上慕道安贫、砥砺节操,重视为己之学;在学风上倡导学贵践履,实学经世,为理学增添了务实的风气;在为人处世中,刚正义烈,追求文节俱高,忠顺朝廷,服膺正统,具有强烈向心意识。
一、尊信程朱,批判佛老,捍卫道统的执着性
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恪守师训,笃信程朱之学,以求道卫道为己任,处处维护着程朱理学的权威与纯洁。
宋元之际的介轩学派,尤其是以朱子故里婺源的理学家们为代表,他们以生活在朱子故里为荣,从心理上服膺朱子,尊崇朱子,强调“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2],是朱熹理学的忠诚卫道者。他们崇仰朱熹的人格,对其顶礼膜拜;在学术上笃信程朱之学,视其为圣学,不容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固守朱学本旨,捍卫师门成说,对于有违朱子学说的“异端邪说”群起而攻之,打上了深深的尊朱烙印。
元代以程钜夫、吴澄为代表的理学家,不遗余力地推崇程朱,使程朱理学最终获得了元朝最高统治者的认可,登上了“国是”的宝座,朱熹的《四书集注》也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程朱理学在元代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立志接武朱熹,继承道统,跻身于圣贤之列,在学术上以朱子为宗,奉朱熹学说为圭臬,致力于探寻朱学本旨,阐扬朱学未尽之蕴。
明初程朱理学更是一统天下,“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非朱氏之言不尊”[3],进入了理学的述朱期,有如黄宗羲所谓:“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4]179在这种氛围下,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崇信程朱,奋志圣贤之学,对彰显孔孟之道和程朱学说不遗余力,表现出强烈的求道与卫道热情。
吴与弼读过《伊洛渊源录》后,不由感慨道:“睹道统一脉之传,不觉心醉……于是思自奋励,窃慕向焉,而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5]587认为致力于圣贤之道,乃学问之大本。从此放弃科举功名,立志圣贤之道,以传承程朱理学为己任。
胡居仁一生“奋志圣贤之学”,在明代“正道显晦,异学争鸣之日……毅然以斯道自任”[6]10,成为明初诸儒中恪守朱学最醇者。娄谅也是“明正学,迪正道,为世鸿儒”[7]42。罗伦“其学专守宋学,精研经学、义理”,他敬佩圣贤豪杰,学成圣贤成为其一生的追求,并在言行上规行矩步,效法前贤,以求“无不合乎圣贤已行之成法而已”[4]6。张元祯也卓然以斯道自任,笃好濂、洛、关、闽之书。被称为“紫阳功臣”的罗钦顺,从小立志“为圣人之徒”,一生以求道、卫道为己任,“卫道身微每自珍”,即使在阳明心学流行天下,大江南北翕然从之的形势下,依然如中流砥柱,对程朱其学说崇信不疑,对“孔曾思孟之书,周程张朱之说,是崇是信”[8]25。
清代婺源汪绂,一生谨守程、朱之道,其学“以宋五子之学”为旨归,以传承程朱学说为己任。“双池居贫守约,力任斯道之传。”[9]“其学涵泳六经,博通礼乐,亦恪守朱子家法。”[10]为捍卫朱子理学道统,扭转世道人心,他著《理学逢源》,窥圣学之旨,以正本清源,不使邪说诬民,被誉为“守朱学之干城”“为朱子后一人无疑”。
为了维护程朱理学道统,他们批判佛、老,视之为危及程朱圣学的异端,对其痛加批驳,以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
朱熹在隆兴元年,就与汪应辰反复进行儒释邪正之辨,展开了对禅佛的批判。朱熹认为儒学虽然可借佛禅来解说,但不等同于儒、佛同道;佛禅中虽有可汲取的养分,但不能说儒、佛相成,并著《杂学辨》,将张九成《中庸解》、吕本中《大学解》、苏轼《易解》、苏辙《老子解》,一道视为以佛老说儒的“杂学”,对其系统批判,以免它们“流传久远,上累师门”[11]。
吴与弼曾叹息道:“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难矣!”[12]7240把宦官、佛教的泛滥,看成是明代政治的两大毒瘤,惟有割之而后快。
胡居仁更是一位批判佛、道异端的勇猛斗士,“先生之辨释氏尤力”[4]30。他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对佛、道二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定禅佛有损圣人之道,说:“杨、墨、老、佛、庄、列,皆名异端,皆能害圣人之道。为害尤甚者,禅也。”因为“禅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功夫与儒家最相似。”[6]85禅佛顿悟速成的易简工夫,使学者为求捷径,而陷于其中。胡居仁还认为:“老、庄之说最妄,老氏虽背圣人之道,未敢侮圣人,庄子则侮圣人矣。”[6]86夏尚朴评价道:“敬斋之学,笃信程朱,攘斥异教,有功于吾道甚大。”[7]30
罗钦顺更是“详细讨论佛学的第一个中国学者”[13]。他认为禅佛是危及孔门圣学的一大异端。“异端之说,自古有之,考其为害,莫有过于佛氏者。”[8]46他认为:“释氏至于废弃人伦,灭绝天理,其贻祸之酷,可胜道哉!”[8]2并对禅佛的“明心见性”“虚无唯灵”及“顿悟说”进行了学理上的剖析,强调儒、佛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圣人本天,佛氏本心”[8]80。高攀龙认为:“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4]1110黄宗羲认为罗钦顺的辟佛,有大功于圣门。“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有大功于圣门。”[4]10
清代宋之盛等“髻山七隐”也力辟禅佛之非,认为禅学盛行会亡种亡国,反对“援禅入儒”,视之为疏粝掺入芝术。他批驳佛教以知觉言心,不务格物穷理,有如引镜照镜,不过是以空印空而已。“释氏只以空寂妙圆为究竟,而视理为障,岂得同科。”[14]程山谢文洊认为学术之坏,坏于禅学与俗学。因此,欲复兴儒学,就须深辟禅学之非。
由此可见,尊信程朱,恪守师训,批判禅佛,驳斥老庄,以卫道为己任,竭力维护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成为鄱阳湖地区理学家的共同特征。
二、和会朱、陆,兼容并蓄的文化融合性
浩瀚的鄱阳湖不仅汇聚了赣江、信江等五河之水,且可容纳、扩散八方文化。其“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区位优势,方便了学者们南来北往的交流,各地文化在此碰撞、交融,成为理学思潮激烈交锋的地区,呈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特性。
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在尊崇程朱的同时,并不恪守门户,对其他学派持宽容、接纳态度。鄱阳湖地区是朱学、陆学交互影响的区域,抚州金溪是陆九渊的故乡,是陆学的大本营,具有“和会朱、陆”的传统土壤。程朱理学自形成之日起,便与陆九渊心学论争不已,并在论辩交锋中,互相接近,相互交融。饶鲁双峰学派、鄱阳三汤之学、吴澄草庐学派,都以和会朱、陆为特色,呈现出集朱、陆之长,兼容并蓄的学术特点。
吴澄打破朱、陆的学术藩篱,博采两家之长为己所用,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吴澄既得朱熹理学之真传,又熟谙陆九渊心学的真瑞,在继承朱熹理气论的同时,又提出“理在气中”“理气未始相离”的命题,同时吸收了陆九渊“心本论”观点,发表了“道具于心”的主张。对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吴澄主张以“尊德性”为体,“道问学”为用,内以主敬以尊德性,外以格物而致知,认为“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15]3037。力求将陆学的“高明简易”与朱学的“笃实邃密”相结合,弃两家之短,集两家之长,致力于“和会朱、陆”,建构兼容朱、陆之长的理学新体系。
明代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在学术上“守宋人之途辙”,他们“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12]7222。但在“一禀前人成法”的同时,也有所创新发展。他们在朱学的基础上,吸收了陆九渊心学的因素,在坚持理本论的同时,重视心的作用。
吴与弼对朱熹的心性论进行改造,将“心”提升为核心概念,认为“寸心含宇宙,不乐复如何?”[5]368确立了心的本体地位,成为明代“心学”第一人。在修养方法上,他提出了“反求吾心”的修养方法,认为“理”是“吾心固有”,只是被气禀所拘而蒙有尘垢,要通过“洗心”“磨镜”等“反求吾心”的浣洗功夫,去除尘垢,达到“心性纯然”的境界。在存心方法上,提出了“主敬存心”和“静中存心”的涵养方法,把“敬义夹持”当作“洗心之要法”,尤其注重平旦之气的静观和枕上的冥悟夜思。
被称为明代醇儒的胡居仁提出了“心与理本一”的命题。他说:“盖心具众理,众理悉具于心,心与理一也。”[6]15认为心与理都是宇宙的本体,把理本论与心本论融合起来,主张“存心穷理,交致其功”[6]15。而娄谅之学“以主敬躬理为主”[7]41,将吴与弼的“洗心”“涵养此心”之说,进一步阐发为“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4]44。娄谅还是阳明心学的启蒙者,黄宗羲评价道:“姚江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4]44张元祯的“是心也,即天理也”的论断,黄宗羲谓其已先发阳明“未发时惊天动地,已发时寂天寞地”[4]1082之蕴。
由于鄱阳湖地区既是朱学传播的重要阵地,又是陆学的大本营,有明显的兼综朱、陆的趋向,具有“和会朱、陆”的学术传统。宋元之际,“鄱阳三汤”之一的汤汉,“补两家之未备,是会同朱、陆之最先者。”[15]2843而吴澄更是和会朱、陆的集大成者。明代的理学家们,在继承、恪守朱学的同时,吸收了陆学的本心论,以治心养性、主敬存心作为工夫本原,避免朱学的“支离”之弊。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融合性,表现为能容纳各方,兼综朱、陆,取长补短。正是这种宽广的胸襟,使鄱阳湖地区成为江西最具文化底蕴的单元。
三、砥砺节操,慕道安贫的理想性
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重视为己之学,崇尚道德人格,将人格修养,视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圣贤之道,指导自己的日用常行。他们笃行仁义,甘受寂寞,以克己安贫为实地,不醉心于科场成败,不汲汲于功名追求,保持了理学家的风骨气节。他们砥砺节操,慕道安贫,以成圣成贤作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懈追求。
吴与弼、胡居仁忧道不忧贫,对道的追求使他们忘却物质的贫乏,认为求道、行道就必须安于贫贱,不可贪慕富贵,做到穷不改节。吴与弼说:“至于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4]3他生活贫困,躬耕自食,但淡泊自乐,严守操行,“非其义,一介不取”[12]7240,一生“随分、节用、安贫”,“盖七十年如一日,愤乐相生,可谓独得圣贤之心精者”[4]3,在贫病交加之中守节依旧,“誓虽寒饥死, 不敢易初心”[4]25。李贽称赞其人品“有孔门陋巷风雩之意”[16]。
胡居仁也是“慕道安贫,日寻孔颜之乐”[17],虽然“家贫甚,鹑衣箪食,尚不继,或为之虑”[18],但却说:“身已闰义,屋已闰书,大处足矣,不必琐求。”[18]他看淡物质的贫富,追求的是道德的完美和心灵的愉悦。他淡泊名利,“与人语,终日不及利禄”[12]7232,“一切势利纷华,举不足以动其心”[6]6。时刻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用苦行僧式的修炼,期望成为凡间的圣人。罗伦也在言行上效法先贤,规行矩步,淡泊富贵名利,“于富贵名利泊如也”[12]4750。时人赞叹其品行可以“正君善俗”[4]1072。罗钦顺更不愧圣人之徒,立身行世可钦可典,其德行如浑金美玉。他说:“有志于道者,必透得富贵功名两关,然后可得而入。”[8]12认为只有摆脱富贵功名的缠扰,才可步入圣贤之域。
明清鼎革之际,谢文洊及程山六君子、星子宋之盛等髻山七隐不仕清廷,避居山林,耕读授徒,砥砺风节,企图中兴程朱理学,以挽救世道人心。谢文洊主张学以切己为要,以主敬为本,以济世为用,潜心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且躬行实践,在日常生活中以圣贤的言行规范自己,他们以高尚的志节和人格操守为世人所称道。
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明道重义轻利,“凡事须断以义,计较利害便非”[4]23,淡化了对功名的追求,把程朱学说向着专讲心性修养、追求道德人格的方向发展,以成圣成贤作为不懈的理想追求。他们笃志力行,独善其身,以高尚的品德赢得了时人的尊重。侯外庐先生评价他们“是封建社会的‘正人君子’,安于贫贱,刻苦自励,授徒著书,以此终身。他们不同于口谈仁义,行同狗彘的那些假道学”[19],这也正是鄱阳湖地区理学家的写照。
四、学贵践履,实学经世的务实性
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在学风上提倡学贵践履的经世实学,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言,力图避免空谈义理,将道德性命与经世致用分离开来的理学流弊。
元代程钜夫制定科举程式,使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从体制层面上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且为理学注入了务实的风气。他力纠理学家高言空谈、疏于实政的流弊,提倡事功之实,对宋末朱子后学谨守朱子矩镬,热衷章句训诂,拱手高谈性理的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于事功之实,文儒轻介胃,高科厌州县,清流耻钱谷,滔滔晋清谈之风,颓靡坏烂,至于宋之季极矣。”[20]他强调学术要关注百姓日用,他说:“儒者之通患,在议论多而事功少。”[21]他主张重视政事治绩,把“躬行”务实看成重中之重,从而使“元代理学具有务实的特征”[22]。
明代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虽然不沉迷于科举,不热衷于求仕做官,但位卑不忘忧国,仍然关心社会现实,关注百姓民生。吴与弼为答谢英宗的知遇之恩,作《陈言十事》谢表,提出了“崇圣志、广圣学、隆圣德、子庶民、谨命令、敦教化、清百僚、齐庶政、广言路、君相一德同心”等十项建议[23],希望皇帝提高道德修养,革新政治,实现王道德治。
胡居仁尽管以布衣终身,但对现实社会依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死读圣贤书的迂腐之人。他认为学问要和事功、践履结合起来,否则就是“谈而无用之空言”,提出了“为政者,以修身为本,爱民为重,求贤为急”[6]151等不少实用的政治主张。
罗伦在家乡,倡行乡约,制定《戒族人书》,教诫宗族子弟与乡邻,要求“不争田地,不占山林,不尚争斗,不四强梁,不败乡里,不凌宗族,不扰官府,不尚奢侈”[24],对当地教化和公序良俗的形成大有裨益。
张元祯多次担任朝廷要职,晓达国家政治,且主讲经筵,成为帝王之师。因此章懋说:“今日士大夫晓达天下国家事,惟张廷祥。”[25]他不仅是一个理学家,更是一位能臣干吏。
罗钦顺更是一位满怀入世热情和济世抱负的学者,他提出了“经世实学”的主张,要求一切言谈、学说,都应有益于国计民生,反对空谈心性、谈玄弄虚的学风,提倡“学贵践履”的“实学”,开创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
明清之际,学界反省明朝灭亡的原因,普遍归咎于理学特别是王学的“空谈误国”,认为正是其空谈心性,不务实事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要求抛弃明心见性之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江永“以矫正宋明理学空疏之弊为任”[26],将“六经注我”的空谈之风,扭转为“我注六经”的实学之路,立志“以经学济理学之穷”[27],他注重考据训诂、不务空谈的学术特点,开创了徽派朴学的一代新风。
被誉为清代“帝师元老”的朱轼是集理学家、史学家和重臣于一身的理学名臣,培养了乾隆这位杰出帝王,且为清初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巩固和理学在鄱阳湖地区的普及作出了积极贡献。朱轼强调理学的经世致用,认为“六经皆圣人经世之书也”[28]。
五、文节俱高,刚正义烈的忠诚性
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注重气节。“文章、道德、气节”成为他们人生的三大追求,将名节忠义视为立身之本,不断涌现出文节俱高的刚介之士,正如同治《赣州府志·旧序》所载“豫章理学节义,为海内师表”[29],刚正义烈、文节俱高是鄱阳湖地区理学家的真实写照。
南宋嘉定年间,李道传将“文节俱高”视为江西士人的独特品格。他说:“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然尝论之,此八九公所以光明隽伟、著于时而垂于后者,非以其文,以其节也。盖文不高则不传,文高矣而节不能与之俱高,则虽传而不久。是故君子惟其节之为贵也。此八九公者,出处不同,用舍各异,而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贬以求合。”[30]“文节俱高”“不肯少贬以求合”成为江西学人的文化特征。
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注重名节,有杀身成仁、为道殉情的书生意气,有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
注重名节,廉介恬退,这些品德在介轩学者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如许月卿、马端临就是以气节闻名的学者。他们在宋亡之后,以风节相砥砺,抵抗元朝的征召,安贫乐道,保持了理学家的风骨气节。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鄱阳湖地区理学家的“文节俱高”,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庆元党禁森严,朱子学说饱受打击之际,部分弟子畏祸回避,托辞归去。黄榦不禁感叹:“向来从学之士,今凋零殆尽。……江西则甘吉父(节)、黄去私(义勇)、张元德(洽)。江东则李敬子(燔)、胡伯量(泳)、蔡元思(念诚)。……大约不过此数人而已。”[31]172一时间,朱门冷落。但鄱阳湖地区的朱门学子却奋勇向前,对朱子的尊崇,对理学的信奉,不因时局的变化而改变,依然孜孜以求,不离不弃。在“伪学之禁方严”时,对那些“为远害思归者”,董铢正色责之,喻以理义,使“诸生翕然以定”[31]454。滕璘宁绝于仕途,也不屈于韩侂胄的权势。时“韩侂胄当国,或劝先生一见,可得掌政,先生曰:‘彼以伪学诬一世儒宗,以邪党锢天下善士,顾可干进乎?’”[15]2292时任崇政院说书的柴中行,移檄令自言非伪学。但柴中行却明确表示:“自幼习读程氏《易传》,如以为伪,不愿考校。”[15]2638
朱熹去世后,尽管朝廷严禁门徒会葬,但周谟、李燔、黄灏等人均戴星徒步,不远千里前往会葬朱熹,表现出威武不屈的节义精神。
在宋、元鼎革、存亡绝续之际,鄱阳湖地区的理学家们更重国家大义,高标民族气节,以风节相砥砺,做到临大节而不可夺,表现出凛凛正气,铮铮铁骨和忠义之心。如许月卿、谢叠山,他们抵抗元朝政府的征召,宁做南宋的遗民,也决不做蒙元的高官,或是慷慨赴死,或是绝食殉国,展现了鄱阳湖地区理学文化刚正义烈的内核。甚至在清帝退位后,还有江西人张勋的复辟,表现出强烈的忠君情结。胡思敬不禁在《国闻备乘》中感慨道:“清待赣人薄,赣人报独厚。”[32]
康熙二十二年,江西学政高璜在《江西通志》序中,纵论江西的文与人,他说:“(江西)故大不如吴,强不如楚。然有吴之文而去其靡,有楚之质而去其犷,吾必以江国为巨擘焉!议者常少江人,谓其立异而难服。夫立异者,矜之疾;难服者,愚之疾。诚有之,不知立异,则无工言语、识形势之习;难服,则不顾利害、去就,与天下争是非。可杀,可去,而不可使为不义。此人君乐得之以为臣,人父乐得之以为子,人士乐得之以为友。”[33]认为忠义节气是江西文人重要特征,“可杀,可去,而不可使为不义”成为江西文人的生动写照。刚正义烈,文章节义正是鄱阳湖理学文化的基本内核和精髓所在。
总之,鄱阳湖地区是理学之渊薮,理学在这里萌生、传承、发展、繁衍,使鄱阳湖地域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理学文化烙印。鄱阳湖理学文化展现出的捍卫道统的执着性、兼容并蓄的融合性、慕道安贫的理想性、学贵践履的务实性和刚正义烈的忠诚性等五大特性,对鄱阳湖地区民众的人格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渗透在民众的日用常行之中,可以说,理学精神不仅浸润了鄱阳湖民众的血液,且积淀于民众的心理,浩瀚的鄱阳湖,不但滋养了江西的身体,还安顿了江西的灵魂。
[1] 吴长庚.朱熹与江西理学[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124.
[2] 周晓光.新安理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0.
[3] 何乔远.名山藏:第七册[M].扬州:广陵书社,1993:5194.
[4] 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吴与弼.康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 胡居仁.胡居仁文集[M].冯会明,点校.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7] 夏尚朴.东岩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 罗钦顺.困知记[M].阎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9]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六三:双池学案[M].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2433.
[10] 钱穆.清儒学案序[M]//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71.
[11]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记疑[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397.
[12] 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 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M].台北:台北泓文馆,1986:341.
[14] 宋惕.髻山文钞:卷下:复约斋书[M]//陶福履,胡思敬.豫章丛书:第200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805.
[15] 黄宗羲.宋元学案[M].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李贽.续藏书:卷二一:聘君吴公[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91.
[17] 杨希闵.胡文敬公年谱[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9.
[18] 区作霖,冯兰森.余干县志:卷一二:人物志二理学[M].刻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
[19] 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20] 程钜夫.雪楼集:卷一四:送黄济川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79.
[21] 王明荪.元代的士人与政治[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190.
[22] 朱汉民.中国学术史:宋元卷[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713.
[23] 杨忠民,段绍镒.抚州人物[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58.
[24] 罗伦.戒族人书[M]//王竞成.中国历代名人家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315.
[25] 章懋.枫山章先生语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22.
[26] 徐道彬.论朱子学背景下江永的学术抗衡[J].朱子学刊,2013(1):238-256.
[27] 徐道彬.皖派学术与传承[M].合肥:黄山书社,2012:96.
[28] 朱轼.史传三编:卷三:胡瑗传[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0.
[29] 周令树.重刊明天启赣州府志序[M]//魏瀛.同治赣州府志. 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30] 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三三:附录·谥文节公告议[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11.
[31] 黄榦.勉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2] 孙献韬.张勋传[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154.
[33] 谢军.江西省方志编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272.
[责任编辑 邱忠善]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o-Confucianism Culture in the Area of Poyang Lake
FENG Hui-ming, LI Hao
(School of History,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
The area of Poyang Lake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headstream of Neo-Confucianism”. The Neo-Confucianism culture is the basic core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Poyang Lake. This kind of culture has the following five characteristics: the persistence in respecting and believing Cheng and Zhu, and upholding conventional viewpoints; the syncretism of matching Zhu and Lu, and inclusiveness; ideality of sharpening principles and of being content with poverty and devoted to belief; practicality of learning classics and putting them into practice; loyalty with lofty quality and uprightness and honesty.
the area of Poyang Lake; Neo-Confucianism; characteristics
2017-02-05
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X040)
冯会明(1968-),男,江西上高人,教授,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E-mail:1355425271@qq.com
B244.7
A
1004-2237(2017)01-0016-07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