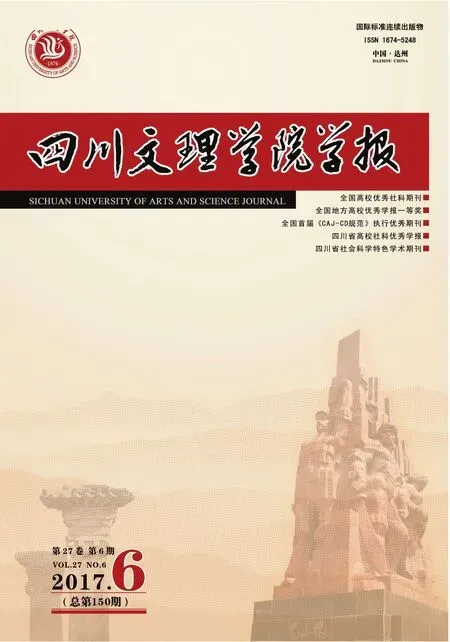巴特勒建构“酷儿理论”的策略与困境
2017-04-13李雪梅
罗 毅,李雪梅
一
人类,作为浩瀚无垠的宇宙中的物种之一,凭借着科学技术神奇的魔力,成为地球上的绝对主宰。构成人类这个大类别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因为生存状态、学历背景、文化与习俗以及生活经历与阅历方面大相径庭,其个性、情绪、性格、思想、尊严及生活的呈现样式也便是迥乎不同。超过70亿的人生活在地球上,可以环绕赤道14圈还多,这是何其庞大而恐怖的生物群落!就这么一个独特而不可一世的群落,在性别(Sex)与性属(Gender)上的分类竟然出奇的简单,就两个:男、女,非此即彼,绝对“二分”。
男人,抑或女人,物质表现形式是身体。身体本身是构成世界的原形,远古以降,人类以自己身体为原形去构想宇宙的、社会的乃至精神的形态。身体是一个迷人而深奥的问题,吸引着古今中外学者不懈的研究与探寻。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把身体(Body)分为五种: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从生理学、解剖学的角度去看待时,身体便是肉体(flesh)。[1]1从亚里士多德延续下来的医学建构了身体的单性/肉体(one-sex/flesh)认知模式,该模式建立了一个纯粹的假设:“女人只是男人的一个畸形的变体”,女人“具有与男人完全相同的器官,只是被悄然放在了错误的位置”,因此“女人是倒错的”,“是不完美的男人”,[1]36女人“因而被界定为残缺的次等生物”。[2]单性肉体模式的成果是:为身体建构了一个单一的性别结构——男性身体结构。[2]这种认识论是父权制度的产物,在父权制度下,男性是世界的主宰,是绝对的主体;女性是男人的附属,是客体,是“他者”;女人自身没有作为人的独立价值,仅仅是作为一个符号表征的形态而存在。基督教教徒塑造的圣洁纯净的圣母形象只是女性的宗教身体形态,是男性世界创造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神话图腾。女性在宗教与医学同构的视域里是“狂乱的力量”,是“非理性、畸形甚至是罪恶的化身”,[2]宗教圣母身体形态只不过是男性世界用神话叙事为女性构建的行为规范(nor m),女性接受这个宗教身体形态,膜拜这个形象,也就接受了男权(父权)社会为女性量身定做的规范,男性世界借用宗教的神话与谎言构建了“男性权威中心的神话景观”。[3]后现代的消费主义(consu meris m)似乎是女人建立完全的自我主体之所在,在这里,女性的自我设计是完全自由、完全独立的,化妆品、服饰、首饰、发型、发饰以及美容等各种方式与手段悉听女人调度,为其所用,以塑造她们自己渴望的高贵气质与完美的身材与形象。表面上看,消费主义把女性推向了中心位置,把男性推向了边缘地带。实质上,女性在为自己设计或规划迷人气质与傲人的曲线的时候,潜意识里必然遵循着社会认可的某种模式,不无讽刺的是,这种模式的制定者认定者往往是男人。“男人的欲望与隐形权威潜藏于表面自主的消费内部”,[2]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对女性身体的“消费”。
单性/肉体模式理论深深滋养着弗洛伊德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在阉割情绪理论(Castration Co mplex)和阴茎嫉妒理论(Penis Envy)中,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女孩孩提时代与异性伙伴玩耍时,无意中窥见自己兄弟或玩伴的阴茎“大”而“明显”,不由得为自己体内内嵌的那个不起眼的东西而沮丧、自卑,长此以往,自卑情结把她们变成“阴茎嫉妒的受害者”。[3]弗氏如此推论的前提是男性中心主义(Male Centralis m),“女人是不完整的或不完善的男人”,而“男人是规范、是标准”。[3]当小女孩发现自己的“先天缺陷”是由生育自己的母亲带来的,在阉割情绪与阴茎嫉妒的催化作用下,小女孩断然割断对母亲的依恋,而将注意力与爱转向父亲,对父亲像情人一样地爱恋与依附,进入所谓的俄狄甫斯情结(Oedipus Co mplex)——恋父情结——阶段。弗氏的传记作家厄内斯特·琼斯(Er nest Jones)将这一理论调侃地称作“阴茎中心论”。弗氏从生物学、解剖学的视角来看待两性差异,把文化差异简单而武断地归结为生理差异,自负地放言,解剖就是命运。“一条阴茎”就让弗氏天马行空的遐思,建构惊世骇俗的“闳言高论”。男性解构大师乔纳森、卡勒对弗氏的“阴茎中心论”展开猛烈批判,认为这种近乎荒谬的论调纯粹就是“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3]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娜·波伏娃(Si mone Beauvoir)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提出一个观点,她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4]309堪称对“阴茎中心论”的绝妙回应与反击。
17世纪晚期,解剖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阶段,哥本哈根杰出的解剖学家卡帕斯·巴托兰(Capas Bartholin)在1668年制作了三幅独立的女性生殖器官图画,详尽地呈现了女性与男性不相同的生殖系统,是对盖伦(Galen)所谓的“男女解剖同形论”的公开反击。巴托兰从科学实证的角度雄辩地证明另外一种“不可通约的”性别存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生理学、道德和文学中的女性》《女性青春期:生理学、卫生学、医学的观点》《女人的秘密》《性爱艺术》等著作纷纷问世,生物学、解剖学的进步为人们带来新的认知,同形论的单性/肉体认知模式的影响被大大地消解。男性和女性的生物学性别“在本质上不是平等不平等的关系,而是需要阐释的一种差异关系”。[1]215“性别,像人类一样,存在于一定的语境之中,把它从散漫的、具有社会决定性的环境之中孤立出来的尝试注定要失败”,[1]22子宫、卵巢、阴道、月经、怀孕、生育——这些与男人迥然相异的性特征——建构了与男性同样实实在在存在的另外一种性别形态,不是放错位置的男人的变体,而是女人本身,“女人就是女人,不仅在器官方面,在任何地方,在所有事物上,无论是道德方面还是物质方面都是这样”。[1]209生物学基础构建了两种性别,对男人与女人做的社会区分,并确立女人的社会存在、地位与作用的性属就成为一个必须要讨论的话题。“性属不是固定的生物学差异和历史上偶然发生的社会关系两者调和的范畴”,相反,“它既包括生物学的又包括社会关系的因素”,是“建立在性别之间感受到的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组成元素”。[1]1717世纪至19世纪的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医生、科学家,力图用他们的知识与权威构建一幅政治图景,女性在那里只是一个无效的、无价值的、无用的”性别,[1]197是一个空范畴(empty category)。尽管他们的社会理想是“男人最后成了家庭和国家的首脑。男人,而不是女人,制定了社会契约”。[1]218可是,这种话语权威建构的旧的男女秩序必然崩塌,双性/肉体模式必将取而代之。双性/肉体认知模式并非是对单性/肉体模式认知理论的终结,双性/肉体认知模式只是承认女性的生物学性别的存在,仅此而已。在社会层面,女人依旧是“第二性”,是男性世界的附庸,听命与服从于男性世界的统治需要。当然,双性/肉体模式是男/女性别社会二分结构建构的基础。女人的存在,为二分哲学理论提供了分类样本。女性主义认为,性/性别的二元结构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政治、社会、文化及历史共同作用的产物。美国布朗大学医学教授、基因学家安妮·福斯特-斯特林(Anne Foster-Sterling)说,“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划分是一个社会决定”。[1]136安妮的观点可以这样解读:人从母体呱呱坠地,其生物性别便随之确认,社会通过规则、权力、制度、文化对人的性别再定义,这种被定义的性别就是性属,是政治与权力的产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男性至上的世界,也不得不然把“第二性”女性纳入,来构建人类的社会性。从身体的单性/肉体到双性/肉体的探讨与争论,人类经历了一段漫长而黝黑的历史。无论是单性也好,双性也罢,两种认知模式对身体的辩论要么是生物性的,要么是社会性的,两种认知模式的建构目的都是通过政治的权力与文化的权威完成对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的规训与掌控,身体成为权力政治争斗的场所与工具,一处本来很私密的空间,沦为了权力的表征。两种认知模式都是借用话语的权威对性别或性属做界定或下定义,划定人体意义的范畴与半径。其实,人的性别还真不是男/女非此即彼的二分这么简单。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类细胞遗传学发现:人的体细胞的46条染色体按其大小、形态能够完成23对配对,第一对到第二十二对叫做常染色体,为男女共有,第二十三对是一对性染色体(Sex Chro moso me)。性染色体正常的情况下,雄性个体细胞的性染色体对为XY,雌性则为XX。[5]临床也发现XXY、XYY的性染色体异常配对形态,在个体生理上的表现便是男女性状异常,科学的实证为我们揭示了更多性别存在形态。安妮认为,从男性到女性这两种性别之间至少还应存在五种甚至更多的性别,分别是:男性、偏男性(II型)、两性人(III型)、偏女性(I型)、女性。人们把这种偏离于男/女性别的其他存在形态被称作“第三性”。[6]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示了人类性别多样化存在形态的可能性。
二
心理是肉体重要的物质活动,是对客观存在的复杂反应。心理对自我性别的体认与设计,把人的性与性别模式带向了多元。同样是肉体,有的肉体里面长着卵巢、子宫、阴道,有的肉体里面长着睾丸、阴茎,有的肉体里面两种生殖器官都长着。长着子宫、阴道、卵巢的肉体里面活跃的是可能是男孩心,她们从言语谈吐、仪表、仪态、穿着打扮上,模仿或扮成男孩的样子;长着睾丸、阴茎的肉体里面跃动的可能是少女心,他们尽量从说话、仪容、仪态、穿着打扮把自己扮成女孩。女人身男人心,男人身女人心,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在同一具肉体里面撕扯、争斗,难以调和。女人心里喜欢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女人,男人心里装着的可能是另外一个男人。他们/她们享受的情爱方式是男男相爱,男分男舍,女女相亲相爱,如胶似漆,情爱取向背离正统,被视作“异类”(heter ogeneous)。对于人类这种偏离常态的情爱方式,1869年,法国医生Benkert创造ho mosexuality(同性恋)这个术语来描述。在他看来,同性恋是指那种“对异性不能做出性反应,却被自己性别相同的人所吸引”的情爱表现形态。[7]古典理论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社会学、解剖学、遗传学及性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通过分析、实验与研究等手段对同性恋做出解读:性变态、性变异、性倒错、性心理障碍、精神病症、性偏离,这些带有歧视性的术语就是学者们研究同性恋行为时使用的“标签”。弗洛伊德与英国性学家蔼理士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性恋不是病态(abnor mality),是一个变态(parasexuality),是性角色认同的“倒错”(per version)。[8]西方学者对同性恋形成机制的分析与解读分两个层面:生理机制与社会心理机制。无论是哈默对抽样的同性恋兄弟做的DNA做分析,还是Bailey和Pillard对孪生兄弟姊妹同性恋者做的对比实验研究,在与同性恋有关的基因所处的染色体区域,以及染色体标记并非导致同性恋的必要条件,“没有找到哪一个基因是同性恋基因”,[9]换句话说,生理因素导致的同性恋的观点还没有在实验室得到实证,[9]本质主义的生理机制说在研究上的困顿为社会建构主义的话语赢来了表达空间。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是法国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社会建构主义论者对本质主义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性、性别、性取向并非与生俱来,男人/女人、同性恋/异性恋的区别与分类是社会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同性恋的成因究竟是先天的抑或是后天的,至今尚无定论。
对同性恋的研究与争论还在继续。同性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古已有之,于今更甚。古希腊崇尚男性美,爱慕男性,喜欢男子汉气概,同性恋行为在政治、军事与文化界的名人圈内极为流行,《会饮篇》是柏拉图对同性恋最经典的礼赞。[7]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军是一支最勇猛的军团,士兵全是同性情侣,被敌人攻陷后,集体选择自杀,死于自己情侣的怀抱。[7]年轻的凯撒大帝在旅行途中认识一位异国君王并为之情迷。爱宠安迪诺斯殒命于尼罗河,哈德里安皇帝悲恸不已,倾尽国力以大理石和各色玉石为其塑像,立于全国各地,以志纪念。[7]
1895年,爱尔兰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及唯美主义运动倡导者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与昆斯伯里侯爵的儿子道格拉斯(Douglas)陷入同性恋而被起诉,作家败诉,作品全部被封杀,英名扫地,最终穷困潦倒,客死法国。
中国古时候也“男风盛行”,《左传》《诗经》《史记》以及《汉书》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0]战国年间魏安厘王宠爱龙阳君,西汉汉哀帝宠爱董贤,春秋时期卫灵公宠爱弥子瑕,三段同性恋情为后世留下了三个典故:“龙阳之好”、“断袖”、“分桃”。三个典故成为男性同性恋的雅称。
对于女性之间的情爱,1890年,“蕾丝边”出现在医学辞典里面,描述女性间的情欲关系,“蕾丝边之爱”用来描述女性的性爱。“蕾丝边”系英文单词Lesbians的音译,指女性同性恋。Lesbians一词与Lesbos(莱斯博斯岛)有关,莱斯博斯岛是希腊的一个小岛,位于爱琴海东边。公元前7世纪初,著名抒情诗人萨福(Sappho)住在莱斯博斯岛上。萨福诗歌创作上才华横溢,柏拉图盛赞她为人间“第十位缪斯”。萨福的诗体自成一格,西方诗歌史称之为“萨福体”。萨福短暂的一生写了许多歌颂爱情的诗篇,诗歌流露出对女性的深情与依恋。因遭到女恋人的拒绝,萨福伤心欲绝,绝命于悬崖。萨福诗情与恋情备受世人的钟爱,人们根据萨福的名字(Sappho)派生出来Sapphis m这个英文单词,意指女同性恋;根据她住的岛屿Lesbos一词而派生出来Lesbians这个英文单词,与Sapphis m是同一个意思。从Sapphis m与Lesbians两个英文单词的来历,我们知道古希腊人对同性恋的宽容以及同性恋的流行。
中国历史上将女同性恋称作“对食”或“结客”。《汉书·外戚赵皇后传》记载:“房(宫女名)与宫(宫女名)对食。”[11]古时候被征选入宫廷里的女子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做杂役,见到的男人不过就是被阉割的太监,情无所寄,爱无所依,寂寞、孤独、空虚、幽怨的时光里,宫女们与在宫廷朝夕相处的姊妹产生了情爱。“对食”成为女同性恋的隐语,千百年来一直在宫中流传。《道县志》记载,清末至民国时期,富家闺女,豆蔻年华,情窦初开,因不满旧式包办婚姻,又不敢自由恋爱,对异性存畏惧心理,遂同性相恋,结为姊妹,常同屋同居,早晚相伴,俨如夫妻,甚至相约不嫁。此种“结拜姊妹”的风俗被称作“结客”。[11]
当今,“法律文化与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10]中西方对同性恋文化的包容与接受的程度大为不同。无论法律或民众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如何,同性恋在蓬勃生长,成长为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7]网上有一组数据,是对一些国家男性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比例而做的调查,数据显示:荷兰男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的20%,雄居首位,然后是美国10%,德国10%,中国7%,法国4.5%,英国1%。[12]
加拿大、瑞士、挪威、英国的英格兰与威尔士、美国的部分州通过法律,允许同性恋结婚。挪威2011年“通过同性恋婚姻法,允许同性恋同性恋在教堂进行婚礼”。[10]各个国家同性恋人数占国家人口的比例是如何的呢?网上有这样一组调查数据:加拿大同性恋人数639万,人口占比为18%;荷兰288万,占比为17%;德国811万,占比10%;美国2800万,占比10%;挪威63万,占比13%;英国702万,占比11%;瑞士75万,占比10%。[13]笔者无从考证数据的来源及其信度,但是,这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世界同性恋文化的蓬勃与繁荣。在中国,李银河教授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里对同性恋亚文化群(subculture)做了广泛与深入的调查研究,她估计我国同性恋者人数在3000万至4800万之间,[8]网上显示的数据表明,我国的同性性取向人数在6550万,占比为5%。[13]在我国,“法律对同性恋婚姻可以说是一种规避,或者说我国在同性恋婚姻方面处于一种特殊的真空状态”,[10]同性恋不被法律承认与接纳,民众不理解,甚至歧视,同性恋者蛰伏于没有光亮的角落,为了避人耳目,一些同性恋者不得不穿着异性恋婚姻的外衣去搞地下同性恋恋情,同性恋者不愿、不敢或者羞于公开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6550万这一个数据可能更接近真实。
三
提到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不得不提到一个英文单词“queer”。新牛津英汉双解词典(第2版)对其解释是:
The wor dqueer was first used to mean homosexual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it was originally,and usuall y still is,a deliberatel y off ensive and aggressive ter m when used by heter osexual people.In recent years,however,gay people have taken the word queer and deliberately used it in place of gay or ho mosexual,in an atte mpt,to deprive of its negative power.
词典对queer的释义,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
1.queer一词首次用来指称同性恋的时间可以定格在20世纪早期;
2.异性恋者用queer一词来称呼同性恋,带有侮辱与攻击的意味;
3.男同性恋者故意使用queer一词(而不是传统的词汇如gay/ho mosexual)来称谓自己,目的在于消解queer这个词汇承载的负面力量。
西方学界对queer族群的性行为及其特征做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葛尔·罗宾(Gayle Rubin)的Queer Theory:Wester n Thoughts of Sex in the 90s是那个时期的重要研究理论成果。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的李银河教授对Queer Theor y极为关注,她投入极大的热情去研读这本著作,并把它译介到中国。李银河将Queer Theory译为“酷儿理论”,也有学者将其译为“怪异理论”,queer做形容词用时就有“怪异”的意思。在中国学界,以“酷儿理论”为学术术语的研究成果比“怪异理论”的多,也许可以在“酷”文化里面找些理由。“酷”文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酷”源于美国青少年对英文单词COOL的挚爱,COOL,四个字母构成一个音节,发音与汉语的“酷”近似,声音开放、简洁、爽朗、响亮、通透,自然成为他们用来评价任何事情或人物专属词汇。刚开始的时候COOL的意义比较狭窄,指向那种冷峻的、冷酷而个性的行为或态度,后来泛指一切可值得赞美的人和物。[14]COOL传入港台,音译为“酷”,并为之添加“潇洒中带点冷漠”的新意。90年代以来,“酷”成为中国最为流行的校园用语,“能不能理解‘酷’几乎成为是否年轻的标志”。[15]45在穿着打扮、仪容仪表、言行举止及与人相处方面卓尔独行、我行我素、率性任意、个性十足,就是年轻人的“酷”。突破传统强势话语的钳制,解放天性,张扬自我,张扬个性,是青少年追捧“酷”的价值所在。李银河对queer拟其声,音译为“酷儿”,看似随意,实则是匠心独运,音、神、义和谐合一,精妙、准确、传神地传达出queer的意义指向:违世绝俗,放浪无羁,挑战传统,颠覆经典。Queer族群对传统的叛逆,与追“COOL”一族“强调自我,不受约束”的风格可谓是殊途同归。[15]46
20世纪90年代,因男/女同性恋(gay/lesbian)、双性恋(bisexual)、跨性别者之名结成的LGBT阵营出现分化,“新酷儿政治”渴望建构一个新的身份政治。在大学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引起学者的强烈共鸣,积极援引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对同性恋做新的研究与诠释,渴望为同性恋“正名”,为其建构政治化的性别身份,在这种背景下,酷儿行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结合便水到渠成,两者的结合催生了“酷儿理论”。“酷儿理论”一经问世,便成为学术宠儿,备受瞩目,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做文献检索,可以检索到100多学术著作,书名里面包含“酷儿”这样的词汇,“酷儿”研究的广度与热度可见一斑。“酷儿理论”对性身份问题研究的成果与贡献已经远远超过LGBT。利兹大学专门招收从事性别、性学与“酷儿理论”领域的研究的研究生。[16]
“酷儿”到底是什么呢?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的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博士对“酷儿”的定义是,“酷儿是这样一个术语,它希望你在出席一个会议之前不必出示身份证”,[16]异性恋也好,双性恋也罢,都可以加入酷儿运动;男/女同性恋者并不是真正的“酷儿”,因为“酷儿”不使用任何具有明确的性别身份或性取向的标签,“酷儿”是对社会性别规范性的反驳。[16]性别、性取向的含糊性是巴特勒赋予“酷儿”的特征。巴特勒认为,“性别表达背后并没有性别身份”,[16]“主体和身份都是由表达通过性别这一规范性行动在身体上的操演而被建构的”。[14]性别规范通过身体的行为来作用于主体的建构,身份认同包括“行为、姿势和欲望”三个要素,众所周知的是,“这些行为和姿势是表演性的(perf or mative),因而它们表达的性别身份带有虚构性”,[17]因此,巴特勒的结论是,“性别在本质上是建构的”。[17]当然,这个结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没有任何质的区别,或者说,巴特勒在援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来建构“酷儿理论”体系。
“表演”是巴特勒论证性别建构观点的核心词汇,那么,性别身份是如何通过性别行为的表演来完成的呢?当代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语言有着重要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语言的功能是促进理解,“重复、或者引用是语言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18]因此,重复性(reiterative)与引用性(citational)是语言的两个重要的特征。[18]重复和引用、规范与性别表演,这四个东西是如何关联的呢?巴特勒在《身体的重要性》(Bodies That Matter)一书中借用重复和引用两个概念对她的“性别表演”理论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述:表演性不是单一的、一蹴而就的行为,是重复的、引用的实践;“性的规范”以“表演的方式生产身体的物质性”,[17]性差异得以物质化;“性别规范是重复性的,必须在重复中发生作用”,[17]因此,可以推论的是,“性别身份是性别行为反复表演的效果”,[17]所谓本质主义(essentialis m)的“性别身份”是不存在的。“身体通过引用和重复已有的规范持续不断地巩固身份认同。”[17]“一个人作为‘我’在时间中存在的基础,根本上取决于一切社会规范,作为我的‘我’不仅是规范构造的,也依赖于规范”,[19]对规范的重复与引用,身体的“我”得以建构与确认。“重复性表演并不是被动的,它在实施过程中同时产生对规范的抵制力量,削弱了规范的强制效果”,[17]因此,在性别认同的过程中,身体一边对规范做妥协,一边对规范做抵制,性别认同的偏差在对规范的抵制过程中悄然发生。[17]巴特勒同时指出,性别表演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群体性的。“群体性”一词表明:尽管巴特勒一再强调性别的表演性,但是她也承认性别的社会性。每一个生命个体不可能单独制造(do)自己的性别,“一个人总是与别人一起或者是为了别人而制造性别的。”[19]“自我的形成中必然包含他者,他者是自我的形成(doing)的一部分,因此,从一开始,自我就已经被消解了。”[19]波伏娃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域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做了分析,“存在于自身并为自身存在”的“一个儿童”不太容易“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性别的人”这样的事实。[4]309小女孩依恋母亲,眷恋母亲,母亲对她精心培养,就是希望自己的宝贝“能顺应女性世界”,[4]324保养容貌、保持魅力、端庄优雅,像母亲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有“女性气质”,“女人味”。[4]324-325表面上看,小女孩在社会规范里得到教养而慢慢长大成为亲人及社会接受的女人,为自我建构了一个社会性别与身份,但是,在与“他者”母亲的互动中,为了讨得欢欣,她主动选择放弃自主的权利,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客体。小女孩希望借助母亲的力量帮助自己建构自我主体,母亲的协助却悄然“消解”了她的主体身份建构的努力,也“消解”了她的自我主体。小女孩的成长案例无疑是“我们彼此消解”的这一论断的有力佐证。[19]108“消解”是巴特勒“性别表演性”理论里面一个重要的术语,小女孩成长的案例证明:“消解”的意思不能等同于消灭,“消解”是为了“强调自我的社会性”,[19]108是将“自我的社会性以及自我与他者、与社会拧在一起的关系”的一种途径与策略。[19]“要作为‘我’来生活,前提是得到社会的承认,而承认的标准是社会规范来决定的。”[19]“承认”(recognition)是将个人融入社会的唯一路径,“承认”不谋求对规范的颠覆,“承认”寻求的是与规范的共处。
性别表演的重复与引用“在制裁和建构的角力中孕育着颠覆性的反抗力量”,[17]这就是“酷儿”的力量,也是巴特勒的“酷儿理论”的重要观点。通过“性别表演理论”,巴特勒进一步阐释了她的“酷儿理论”:性别不是一个稳定的身份,是流动的,开放的,可以改变的。人的性倾向在性别表演中也是流动的,固化的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身份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可以确认的是此一时的同性间的性行为,或者彼一时的异性间的性行为;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身份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人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具有多元的可能。[20]巴特勒通过“性别表演理论”“将同性恋表演政治化”,[17]力图建构一种“性别政治图景”,质疑和挑战“男权统治和异性主义(heterosexis m)主导的社会秩序”。[17]
LGBT自从结成联盟以来,就一直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抗争持续了40年。在英美等国,“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 ont)、“同性恋平等运动”(Ca mpaign f or Ho mosexual Equality)、“英国防卫联盟”(English Def ense League)以及“人权运动”(Hu man Rights Ca mpaign)等同性恋组织纷纷成立,为他们渴望的一个理想社会去抗争,去奋斗,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性取向都将得到解放,男人和女人的性别角色都会被取消”。[16]3740年的抗争,LGBT人士“从一个受法律迫害的少数派变成了受法律保护的群体”,[16]可是,“法律上的平等往往会导致LGBT人士沿着阶级界线出现观点分化”,[16]“LGBT人士沿着阶级界线而分化以及他们在政治观点上的分化”,[16]可能会破坏“LGBT人士具有的共同利益”,[16]分化的LGBT阵营渴望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身份政治”,能够包容“不同身份的联合”。[16]性别表演性理论的建构,让每个人都在理论上能够打破生理性别的束缚与规范的制约,实现自己渴望的、自己为自己设计的性别身份,开放的、流动的身份图景满足了所有那些游走在主流边缘的人群,像“人妖”这种因为生存所迫而做的身体改变去从事色情表演的族群,也有了被接纳的社会空间。在“性别与性领域”里面的社会活动家,[16]从事学术研究的理论家,意识到LGBT的局限,逐渐放弃使用LGBT这一名称,投入到“酷儿”的麾下,以“酷儿”之名从事文学或艺术创作,在“酷儿”的旗号下组织社会活动,“酷儿反抗”(Queer Resistance)以及“酷儿反削减”(Queers Against the Cuts)等反削减团体于2010年相继在英国伦敦成立。[16]
巴特勒高度重视表演,认为“重复的性别行为”是“身体的一种仪式化的公共表演”,[17]性别身份是时间长久的“积淀而成的动态产物”。[21]问题是,在月经、哺乳、产孩这些属于女性的时刻,性别身份还在流动变化吗?进入男女分割严格的公共空间如卫生间,性别身份在表演吗?同性恋者以婚姻方式相处时,扮演“丈夫”角色的男人(女人)“就像异性恋男人一样有男人气概”,扮演“妻子”角色的女人(男人)就“像异性恋女人一样有女人味儿”,[22]这些表演的身份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吧?美国学者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对巴特勒的表演理论做出了一个经典的追问:对于一个确定的个体的人,在他/她身上是“存在一个永久的身份”,还是一个“持久不变的漂泊的灵魂”?[23]21这个追问代表着学界对“性别表演理论”的质疑。
与LGBT运动与思潮、酷儿运动与理论相伴相生、影响深远的是女性主义主张及其运动,各种形式与流派的女性主义主张及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波澜壮阔,方兴未艾。女性主义者共同致力于“性别解放”“性别平等”等运动的推动,为“妇女争取权力”,[24]最终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葛尔·罗宾是解构派的女性主义代表,她提出“性别制度”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两性不平等的根源”,[22]她认为不平等的根源是“性别制度”,而不是所谓的“经济、阶级制度”,“社会分工也是性别制度的派生物,是社会禁忌”,[22]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男女双方分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巴特勒把葛尔·罗宾的女性主义称作是“限制性别意义的女性主义”,因为葛尔“把性别限定于世俗所接受的男性与女性”的框架之内来做的研究。[23]自序1巴特勒对女性主义提出的性别观念与话语保持警惕与怀疑,“身体的划分为何只能按照男/女的标准来进行”?[24]为什么这个标准有着至高无上、君临天下的权威?建构这个标准的权力来自哪里?在巴特勒看来,一旦给赋予“某个性别”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异性恋的臣服关系”,[23]自序7在异性恋性行为里,在臣服的快感中,女人作为性别的存在只不过是向男人“展现女人性”,[23]自序7的一个符号而已,因此女性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不遗余力地“推翻、消灭性别”,[23]自序7或者努力把性别变得暧昧并且具有破坏力,[23]自序7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书中对“性别”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巴特勒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观点与态度无疑会对“女性主义理论构成具有挑衅意味的‘介入’”,自己也会“成为某些形式的女性主义攻击批评的对象”,[23]自序1并“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23]自序1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但巴特勒并不为之担心。“打破性别的二元框架”,“为性别打开可能性的领域”与生存空间是像她一样的学者应该具有的担当与使命。[23]自序2因此,巴特勒质疑男人/女人的二元分类,拒绝使用“女人”这个概念,唯有消解甚至虚无“女人”“女性”“女性气质”这些被文化建构的性别身份符号,才是女性走向自由的必然途径。可是,被政治与文化霸权规训的人类社会,实实在在地生活着一群数量庞大而“真实的女性”,[17]在两性权力关系、家庭关系、受教育权、参政权、社会工作权、社会地位等层面的处境,在“暴力和性侵犯”面前表现出来的无助、痛苦与绝望,[17]让有志之士痛心疾首,四方奔走,呼唤社会与法律的良知,女性主义者也积极参与其中,联合其他组织的力量来改变那些“真实的女性”的命运,促进社会的平等。“女性与其他性别少数群体团结协作”,[17]形成“群体权力”是解决女性困境的有效途径,[17]“女性团结的力量”是女性自我救赎最为直接有效的力量。[17]巴特勒也是女性主义者,但是她对身体、性别、性属、性行为等概念阐释的视角不同与其他流派的相去甚远,协商和对话无法真正构建:“性别规范”是一张“界定我们的生活”的巨网,[24]这张网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空间。只要身在“网”中,性别解放的目标就无法真正实现。跳出性别之网的有效途径便是“性别表演”,因为“性别规范”一旦“被复制”,“他们就被身体实践运用及引用,这些实践也具有在引用的过程中改变规范的能力”,[24]可是,为了构建“群体权力”,还得把“女性”这个性别放进“性别规范”的“网”内,回归传统的性别二元框架,这是巴特勒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其实,并非巴特勒固执己见,她只是想通过自己的视角释放善意的提醒:“性别解放的目标”不一定非要建立“在维护两性分隔的传统模式”里面,[24]“性别表演与性别消解”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质疑和否定性别制度中的二元对立逻辑和文化强制逻辑”来实现“性别解放”的目的,[24]242既彻底解放“现存的两种性别”,又彻底解放那些“不在性别规范之中的、倍受压迫歧视的性少数群体”,[24]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两种论调、两种声音朝着相反的方向角力,不相容,不避让,不妥协,女性主义救助弱势女性的力量难以有效聚合。巴特勒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酷儿理论”为自己打开的是一处孤独的生活空间与逼仄的社会空间。不过,巴特勒并不孤独,她的“声音”已经传播到整个世界,所有人都在“聆听”。
[1](美)托马斯·拉克尔.身体与性属[M].赵万鹏,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2]肖志慧.视觉艺术中的女性身体形象[EB/OL].[2017-03-16].http://www.artlinkart.co m/cn/article/over view/595i Axl/genres/critique/S.
[3]杨莉馨.解剖不是命运[J].女性文学研究,1994(2):149.
[4](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百 度 百 科:染色体 [EB/OL].[2017-03-20].http://baike.baidu.co m/link?url=R2C3-A0 Rwyi HQ_u Yv59s El7Leb ZTZbw Muu Rr B1Ci QBevJl V1 v7x5ah Kniyc0r mNgJewq Dc G47-90x BANTd T HQWg1 Ww-y AMI42 TXti Nbv RUPo-e5Re NxaIwps8f Qoby Nj.
[6]百度百科:第三性.[EB/OL].[2017-04-15].http://baike.baidu.co m/link?url=7BVNl G V5 K26-c Yl CbJ-ugip Yqfquvh9 QAVp Vmc GRcq A0so Dcgc Wfi Yx PM91 L W6 QNpIt1d Taa5Jlp QLuu Bvp37Tqn8Z0 WIITACMRRTp-PAOOHx N4R3 m7DWE08C_Axep wg D.
[7]吴炽煦.西方对同性恋的认识与研究[J].湖北预防医学杂志,2003(5):114.
[8]罗 曼.同性恋研究文献综述[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34.
[9]李 阳,张延华,张海霞.同性恋形成机制[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6):16-20.
[10]金丽珍.中西方同性恋观的跨文化比较研究[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12):114-116.
[11]百度百科:女同性恋[EB/OL].[2017-04-06].http://www.zgxkx.org/sex/zgsex/201108/1033_2.ht ml.
[12]百度贴吧:世界各国男同性恋占男性人口比例调查[EB/OL].[2017-04-06].https://tieba.baidu.co m/p/3594074864.
[13]百度贴吧:全球同性性取向人数概况[EB/OL].[2017-04-06].http://tieba.baidu.co m/p/4714564803.
[14]高笑楠.性别操演理论的经验解释与女性主义方法论反思[J].社会,2015(3):121-125.
[15]杨永林.社会语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6](英)柯林·威尔森.“酷儿理论”与政治[J].毛兴贵,译.国外理论与动态,2013(12):36-42.
[17]何成洲.巴特勒与表演性理论[J].外国文学评论,2010(3):137-143.
[18](法)夏尔·拉蒙.德里达:能用“古典”方法来研究的“古典”哲学家[J].马洁宁,译.文汇报,2016(1):63-67.
[19]郭 劼.承认与消解:朱迪斯·巴特勒的《消解性别》[J].妇女研究论丛,2010(11):106-111.
[20]百度百科:酷儿理论[EB/OL].[2017-04-06].http://baike.baidu.co m/link?url=obi Knc92aPqsb9 Lx Pph N6 H6 TGTSTNAw Mk QFNQZ9 Mmmd Fqyt Y WRg VTAl w NYDVDR5hngp Y46r4TXYqj Mkdf b63 Air y_Pt R6k 8v0t6X_g GGSkxuu mo VPqu7f Mb-DGLpyIIi.
[21]孙婷婷.身体的解构与重构—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的身体述行解读[J].妇女研究论丛,2012(5):86.
[22]周 泓.西方女性主义研究[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77-80.
[23](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家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24]范 譞.跳出性别之网[J].社会学研究,2010(5):24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