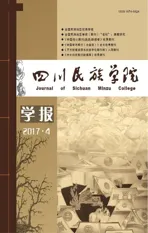莎士比亚作品在西藏的表演与藏文翻译
2017-04-12其美卓嘎
其美卓嘎
莎士比亚作品在西藏的表演与藏文翻译
其美卓嘎
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的地位举足轻重,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本文梳理和总结了莎士比亚作品在西藏的表演和藏文翻译的现象,发现莎士比亚作品在西藏表演和藏文翻译方面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与其他地区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莎士比亚;藏文翻译;斋林·旺多
莎士比亚在西方社会不仅家喻户晓而且是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托马斯·卡莱尔甚至指出莎士比亚是“迄今最伟大的英国人[1]”。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这本书中极力推崇莎士比亚,认为他是西方经典的核心[2]。莎士比亚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符号。相较于其他地区,西藏鲜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没有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莎士比亚作品在西藏的传播独具特色,本文用偶然性和特殊性总结了藏族演员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演绎和藏族翻译家斋林·旺多对藏文版莎士比亚作品的诠释。
一、莎学研究在西藏的偶然性
(一)莎士比亚作品在西藏地区表演的偶然性
在改革开放前的西藏,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人寥寥无几。目前也没有发现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对莎士比亚作品在西藏的演绎和诠释。在西藏的土地上首次表演莎士比亚作品是在1981年。西藏自治区话剧团表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藏族演员表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区话剧团演员们去上海学习的成果;他们是第三批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藏族班的学员,这是他们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时排演的节目。1981年03期的《上海戏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莎士比亚进西藏”详细记述了藏族学员们排演该作品的难度与效果;文章特别提到现今在西藏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演员多布杰和小品演员尼玛当时分别扮演罗密欧与奶妈时达到的良好的戏剧效果。文章作者小路认为多布杰和德央扮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水晶般透明”,而奶妈的角色被尼玛“演活了”;因此莎士比亚是“属于全人类的”[3]。可以说莎士比亚作品在西藏地区的表演是充满偶然性的,它不是西方文化直接在西藏传播的标志,也不是西藏与西方之间跨文明交际的直接产物,只是偶然的机缘巧合。改革开放后,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一批演员成为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藏族班的学员。在上海他们根据课堂上的所学与所见所闻集体排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回到西藏后他们表演了排演好的这场戏。至于他们为什么选择莎士比亚作品,就要讲到话剧在中国的发展。话剧是五四运动之后为了应和白话文运动而新兴的一种表演方式,并不同于传统的戏剧。话剧是根据西方剧目的表现方式改编的,它的源头在西方。西方剧作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莎士比亚,所以区话剧团的藏族演员们选择最经典和最有名的莎士比亚来呈现自己的话剧表演也是不足为奇的。
2006年出品的由胡雪桦导演的电影《喜马拉雅王子》是莎士比亚作品在西藏地区的第二次演绎。《喜马拉雅王子》改编自《哈姆雷特》,被称为藏版莎剧。虽然电影主演均为藏族演员,但是电影导演和编剧等工作人员均来自内地。该电影情节忠于《哈姆雷特》,但是电影主人公的名字不是常见的或正宗的藏族人名,是导演或编剧随意创造的类似藏族人的名字。电影中的戏服采用了某些藏族服饰的元素,但是在视觉上与传统的藏族服饰有很大的区别。胡雪桦导演将人们熟知的一个故事设置在遥远的喜马拉雅是为了建立一种新鲜感与独特的神秘主义,是为了给《哈姆雷特》新的演绎与独树一帜的视角,电影取景与人物创造是为了制造如遥远的史诗故事般的喜马拉雅与现代观众之间的距离感。莎士比亚作品在西藏地区的表演只有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胡雪桦的《喜马拉雅王子》。除此之外,莎士比亚与西藏的联系体现在个别艺术家对莎士比亚和藏文化之间的整合;最好的例子是赖声川的《菩萨之三十七种修行之李尔王》。这部看似荒诞的话剧被人称为是赖声川最成功的作品。赖声川是现当代最出名的华语戏剧导演之一,他被《亚洲周刊》誉为“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4]。《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而《菩萨之三十七种修行》是由十四世纪西藏瑜珈士葛西多美所著。看似南辕北辙的两部作品在赖声川的作品中得到很好的融合。回忆创作过程时,赖声川通过举例说道:“我感觉到《菩萨之三十七种修行》中的每一行似乎都在针对李尔先生说话”[5]。赖声川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呈现了人类各种各样的病症但是从来没有对症下药过,所以《菩萨之三十七种修行》能够为李尔王的病痛与磨难提供解药,呈现出一种因与果的关系。赖声川的《李尔王》被打上了浓重的西藏文化的烙印,这是基于赖声川个人的艺术创作和宗教信仰对《李尔王》再创造的影响。因此,西藏地区莎士比亚的表演充满了偶然性,局限于少部分人的创作与表演,没有达到像内地一样对莎士比亚妇孺皆知的程度。
(二)出版莎士比亚作品藏文翻译的偶然性
斋林·旺多先生是西藏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出版莎士比亚作品藏文版的翻译家。这与旺多先生的丰富多彩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旺多先生在1934年出生于现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一个叫扎东斋喜林的贵族家庭。1940到1945年,他在江孜县,日喀则市和拉萨旧式的藏语学校学习藏文。自1946到1952年,他在印度留学,是在印度大吉岭的英式学校圣约瑟夫学院学习英文。旺多先生个人的努力使他通晓英藏两种语言。从1953年到1976年,他先后在拉萨小学,江孜小学,日喀则干部学校等当老师,也在日喀则的一个电厂工作过。1977年到1984年,他在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教材编译局工作,而1985年到1991年,他在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工作并退休,被称为西藏导游的“祖师爷”。1991年退休后,他在发表了《西藏导游日记》和自己的藏文小说《斋苏府秘闻》。他主要的翻译作品是藏文版的《哈姆雷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分别出版于2002与2003年。斋林·旺多先生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填补了西藏地区没有莎士比亚作品藏文版的空白,是很有意义的开创之举。因此,旺多先生也被称为“把莎士比亚带到喜马拉雅的人”[6]。 可是藏文版莎士比亚作品的出版很大程度上只是斋林·旺多先生个人的成就,可以说与莎士比亚在藏区的研究几乎没有关系。目前为止,有关斋林·旺多和莎士比亚藏文翻译的文章只有三篇,一篇访问记录和两篇论文。这篇访问记录与两篇论文是望多先生被邀请到西藏大学开展讲座后,由藏大教师整理、撰写和出版的。
二、西藏元素对莎学研究的特殊性
(一)藏文化元素在莎士比亚作品表演中的特殊性
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青藏高原被人称为除南极和北极之外的第三极。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西藏不同寻常的文化。因此,人迹罕至的西藏和遍地开花的莎士比亚之间的联系备受莎学研究者的关注。世界上表演莎剧作品的剧团不计其数,但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上海和北京巡演时深获英国皇家艺术剧院的好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副教授黄承元在他的著作《莎士比亚中国行旅》中特别提到自治区话剧团的这场演出。《莎士比亚中国行旅》是黄承元呕心沥血十年研究中国化莎士比亚的著作。这本书荣获国际史嘉林2010年度最佳比较文学研究学术著作奖和纽约大学的卡拉威最佳戏剧研究著作奖,并提名入围美国戏剧研究学会学术著作奖。黄承元将藏族演员表演的莎剧当作中国莎士比亚千万面孔中独特而不可缺失的一员。西藏与莎士比亚之间的联系也被永远记录在这部学术著作中,成为了莎士比亚中国化旅程中偶然而独特的一笔印记。在2004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舞台实践》也特别提到了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该书作者系英国利兹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茹茹。她认为藏族演员表演的莎剧因为直白和奔放更接近伊丽莎白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表演。
《哈姆雷特》在西方文化中具有史诗般的地位;是除《圣经》之外在英语语言中引用最多的文本。黄承元在《莎士比亚中国行旅》中提到了《哈姆雷特》的改编电影《喜马拉雅王子》。《哈姆雷特》故事的地点从人们熟悉的丹麦搬到陌生而遥远的喜马拉雅使之更被增添了戏剧的张力,从而满足了观众对莎士比亚作品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好奇和戏剧化的想象。喜马拉雅地区的遥远和神秘也可能是胡雪桦导演将他的《哈姆雷特》的故事情境在古老的雪域高原重新书写的原因。著名的莎士比亚学者斯坦利·威尔斯认为造成《哈姆雷特》声名大振的原因在于该剧对死亡这一主题的探讨。生老病死是人类千古以来共同的话题,无人可以回避。藏族被人称作“向死而生”的民族,藏文化的支架与哲学体系都是以其死亡观来做支撑的。如何面对无法避免的死亡,如何为来生做准备等问题是藏文化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些问题贯穿了很多藏民的一生。胡雪桦导演将《哈姆雷特》的改编地点选在喜马拉雅也是别有用意,他似乎是用藏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来表现新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同样还有赖声川的《菩萨之三十七种修行之李尔王》,这是是藏传佛教视域下的对莎士比亚《李尔王》的解读。经历过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西方人往往喜欢将东方哲学认作是“古老的智慧”。赖声川版本的《李尔王》也因藏文化原因而在众多的西方莎士比亚剧团演出中独树一帜。
(二)莎士比亚作品藏文翻译的特殊性
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藏文翻译几乎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中文版西方名著的藏文翻译。与内地相比,西藏地区莎士比亚作品的读者数量很少,莎士比亚的研究人员更少。斋林·旺多先生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他的生活经历具有不可比拟性,他是少数能够在旧西藏学习藏文的藏民之一,也是很少数几个能够留学国外并在英式学校学习英文的藏族人之一。在旧西藏,大多数的藏民,从来没有接触过甚至听说过莎士比亚作品。虽然旺多先生的莎剧藏文翻译看似只是少众的活动,但是他的翻译成果在中国莎学研究层面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旺多先生的翻译成果具有开拓性的特点。旺多先生的藏文版《哈姆雷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出版于21世纪。这符合在全球化浪潮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和跨文化交流的新方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焕发新生命的方式之一就是翻译和引进世界文化中的瑰宝,并在跨文化交流中掌握一定的对话权。旺多先生的翻译成果对丰富藏文阅读资料和扩充西藏的翻译文学作品有很大的作用。与其他语言文字相比,英文到藏文的翻译作品存在着数量少,版本单一等特点。莎士比亚的藏文翻译的出现和旺多先生的个人努力能够起到领头羊的作用,促进西藏翻译文学的发展。其次,莎士比亚作品藏文版的出现丰富了中国莎学乃至世界莎士比亚的研究。藏文版的莎士比亚是中国莎学研究范畴中独树一帜的一种现象,是中国莎学研究视野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作品从英文到藏文的翻译过程必定存在着与英汉翻译不同的创造性改变,存在着异质性文化之间在翻译上的良性变异。这些都给莎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角度。
结 论
从莎剧表演和翻译作品两大主线分析后得知,莎士比亚在西藏的传播具有偶然性,即莎剧表演和翻译具有局限性,不具备普遍性,是少部分人的努力和个人的独特经历造就的结果。但是,具有西藏文化元素的莎士比亚的独特性不容忽视。从藏文化角度诠释的莎士比亚无论从表演还是翻译都存在着其他地区的莎士比亚研究无可比拟的特殊性。
[1]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2]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南京:意林出版社,2005年
[3]小路.莎士比亚进西藏[J].上海戏剧,1981年第3期
[4]马倩.赖声川喜剧作品中的东方意蕴和西方色彩[J].百家评论,2014年第6期
[5]杨洁.对映世界的乌镇戏剧节[J].文化交流,2013年第6期
[6]央视网.[OL]西藏首页.
[责任编辑:陈光军]
Performance of Shakespearean Works in the Tibet and Their Tibetan Translations
Qimei Zhuoga Zhuoma
Shakespeare was probably the most popular western playwright around the world. Thus he has become an icon of western culture. This thesis writes about the performance of Shakespeare's works in the Tibet and th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ks in Tibetan language. Due to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Tibet is seldom affected by western culture and Tibet has no history of western colonization.Thus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ks in Tibet does not demonstrate features of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 Performances of Shakespearean works in Tibet and Tibetan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an works demonstrate features of contingency and particularity.
Shakespeare; Tibetan translation; Draling·Wangdor
H059
A
1674-8824(2017)04-0105-04
其美卓嘎,西藏大学 旅游与外语学院讲师。(西藏拉萨,邮编:850000)
卓玛,西藏大学 旅游与外语学院讲师。(西藏拉萨,邮编:850000)